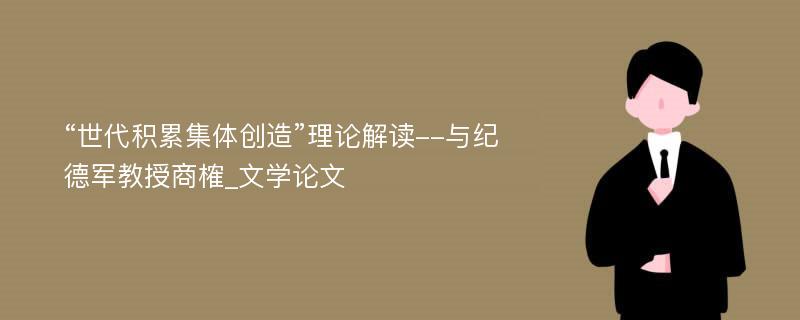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释疑——与纪德君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代论文,集体论文,教授论文,纪德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3-138-08
纪德君教授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一文(以下简称“纪文”),对徐朔方先生在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提出质疑。这篇文章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6年第3期复印转载,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朔方先生自2003年夏天不慎跌倒,导致颅内出血,至今尚未醒来,自然不可能对这篇批评文章作出回应。即使徐先生身体状况良好,他也未必愿意作出回应,他曾说:“我觉得许多同志对我的批评可以不作回答,因为许多问题都已经讲过,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炒一遍冷饭而已。”[1](P35)
纪文既然已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对这篇文章置之不理,不明就里的人就可能认为纪德君教授的批评真的很有道理。既然徐先生已不可能亲自作出回应,本人不揣愚陋,在此对纪文提出商榷,就当是“有事,弟子服其劳”吧。其实,即使不是徐先生的学生,看到像纪文这样的批评文章,也会提出质疑的。
一般说来,论文摘要是作者论文的核心,我们的商榷就从纪文的摘要开始。以下是摘要全文: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徐朔方根据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虽说有合乎实际的一面,但也存在偏颇与失当之处。它过分强调了民间说书艺人世代累积的创作业绩对名著成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导致这种偏颇与失当的主要原因,当与徐朔方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2](P135)
从摘要可知,纪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过分强调了说书艺人的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的创造性劳动,并没收了作家个体的著作权,因而是偏颇和失当的;二、偏颇和失当的主要原因是徐先生对“进化论”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
纪文的这两个主要批评论点是否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
先看第一点,要理解纪文的这一个论点是否正确,先要弄清徐先生是怎样认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徐先生说:
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有它独特的发展过程。宋(金)元时代,杂剧、南戏和话本的传世之作几乎都是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人的编写有时在重新回到民间、更为丰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等光辉灿烂的姓名包含着远非个人所能完成的劳绩。他们个人的创作水平只能部分地决定(或用来解释)归属于他们名下的作品的长短优劣。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描述这一类作品的属性,本书把它们命名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3](P1-2,自序)
这样的观点,徐先生1981年在论文集《论汤显祖及其他》的前言中首次提出,1986年又在论文集《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的前言中加以重申,后来在1990年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的《金元杂剧的再认识》中又再次重申。
徐先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是综合考察了宋(金)元明时期的包括杂剧、南戏、话本在内的小说戏曲,长期探索了它们的发展过程后得出的带有规律性的论述,而不仅仅是纪文摘要中所说的“根据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从徐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论述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传世之作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世代流传,二是经过书会才人、说唱艺人或无名作家编著写定,三是文人最终写成。他提出这一观点的用意,无非是提请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者们不要仅仅将目光盯在这些传世作品的最后写定者上面,把这些作品当作个人独创的作品加以研究,而是要看到这些作品在成书过程中其实包含了历代许多人的劳绩。徐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
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就是说作品的强和弱,优和劣,不能完全归功或归咎于个人,至少一半,甚或更多,要归功或归咎于在此之前世代民间艺人的劳动结晶。[3](P110)
《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如果有一半可以归功于这一位或两位编著写定者,那末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世代相传的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集体智慧,归功于以杭州为主的古代城市中广大的说话听众的无形的批评、指导,是他们的爱好、兴趣、鉴赏力和阶级、阶层的利益影响、左右以至最终决定了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作灵感。[3](P603-604)
据(《三国演义》)嘉靖本的署名,罗贯中可能是在不止一次的写定和增订中的关键人物。但是集腋成裘,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工增订作出贡献的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蒋大器和张尚德都可能在传抄和出版时或多或少地对它的提高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不少加工整理者中侥幸地有姓名留传的两位,更多的人都默默无闻地难以查考。[4](P9)
显然,徐先生比以往的研究者们更重视书会才人、民间艺人和无名作家在这些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前提下,“对它的编著写定者,无论是施耐庵、罗贯中或别的书会才人的劳绩,才能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3](P3,自序)。但强调书会才人、民间艺人和无名作家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从以上引文中“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等光辉灿烂的姓名包含着远非个人所能完成的劳绩”、“《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如果有一半可以归功于这一位或两位编著写定者”、“罗贯中可能是在不止一次的写定和增订中的关键人物”来看,徐先生丝毫没有想要贬低这些个体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意思,从以上引文及徐先生的《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中第五节为《〈水浒传〉的编著写定者施耐庵与罗贯中》,明确指出施耐庵和罗贯中为《水浒传》的编著写定者来看,更没有想要没收这些作家的著作权的意思。
纪文中多次引用《徐朔方集》及《小说考信编》中的文字,包括引用了《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和《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两篇文章中的文字,但它没有举出一条可以证明徐先生含有“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的文字,而对我以上所举出的可以作为反证的文字却视而不见。纪文批评徐先生的观点是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
再看第二点。纪文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由来”一节中说:“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不好断定”徐先生“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那又是如何得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与他对“进化论”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呢?
纪文又说:“导致徐朔方向前走出这么一大步(纪文指“贬低或轻视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创造性贡献”——引者注)的原因,可能也与他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经典命题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他曾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他们是大地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个人创作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的反映,那末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书上就能辨认出较为直接的人民群众的手迹与印记了。’”
纪文所引徐先生的这番话出自《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紧接我在上文所引“《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如果有一半可以归功于这一位或两位编著写定者”这段话后,见《徐朔方集》(第一卷)第604页,又见《小说考信编》第46页,纪文注释谓出自《小说考信编》第32页,不确。据徐先生在文末所署,可知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5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
徐先生这篇文章是篇旧作,写于20世纪60年代,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受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文章中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说了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属于过头的话,本不足为奇。因为徐先生早期的文章中有受当时思潮影响而说过一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类的话,由此而认定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即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影响下的产物,未免失之轻率。因为徐先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一系列论证这一观点的文章也大都作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这些文章中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类的文字。
那么徐先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知识背景是什么呢?是他的渊博、深厚的中外文学知识。徐先生于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时转入英语系。因为徐先生毕业于英语系,对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非常熟悉,这使得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不仅善于借鉴西方文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能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注重中外文学的比较,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徐先生说: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产物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代累积型的无名氏作品。《旧约全书》即《希伯来圣经》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经典。除个别段落外,它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年期间以希伯来文写成。它不是任何个人之作。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否出于盲诗人荷马之手一直是不解之谜。前两者由于民族和语种的复杂,后者则由于希腊沦丧在土耳其统治之下达四个世纪之久,三者虽然历史悠久却没有出现中国文学史上那么兴旺发达的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先后两个高潮即秦汉和元明清时期。由于多民族问题引起的纷争和饱受入侵之苦,阿拉伯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反映的是中古时代甚至更早的阿拉伯和西亚的风土人情,它迟至1717年才结束它的口头传说阶段而首次以法文版问世。最早以欧洲近代国家语言编写的英国叙事诗《见奥武甫》的形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之久,它叙述公元六世纪初丹麦、瑞典的故事,而完成于第八世纪前半。描写基辅大公(约877—945)的《伊戈尔王子远征记》大约在1185—1187成书。最早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德国、奥地利的《尼贝龙根之歌》成书迟早可说在伯仲之间。1450年前后德国古登堡揭开了近代印刷术新的一页。欧美国家不再具备出现我国那样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繁荣发展的社会条件了。
以上是我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一个宏观理解。[4](P56,前言)
徐先生的这段话,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他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提出的知识背景。纪文从一开始就引用了徐先生《小说考信编·前言》中表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一段文字作为批评对象,纪文所引的这一段文字与上面我所引的这段文字相隔不过两页,奇怪的是纪德君教授居然没有看到徐先生自道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知识背景这段话,反而要到徐先生在20世纪60年AI写作就的一篇旧作中找出一段只有在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表述的话语,用来证明徐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提出是因为片面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缘故。
纪文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非是想说明徐先生知识陈旧,观念落后,不能“与时俱进”,因此他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性也值得怀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20世纪50、60、70年代那样深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热衷于用一些带有教条色彩的经典命题来解释文学史现象,这样的研究现在已经不太有市场了,甚至可能会成为被轻视、嘲弄的对象。而给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扣上“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这样的帽子,正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徐先生认为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曾提出过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类似的论点,纪文对此不予认同:“可见胡适、鲁迅、郑振铎并未像徐朔方所说的提出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也极少否定过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的著作权,当然也就不会轻视或淡化这几位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这里需要辨明的是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到底有没有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过类似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不妨用这几位学者自己的说法:鲁迅认为《水浒传》“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5](P94-99);胡适认为:“《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6](P740)“《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6](P750)、“这一本小册子(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使我们明白《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6](P899)。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对这些作品的世代累积的演化过程作了较细致的论证①。即以《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为例,他在详细考述了三国故事的演化后,总结道:
(一)《三国志》通俗小说是早已有之的,在北宋时已被说书人在讲说着,在南宋时,似已有与《新编五代史平话》相同的《新编三国志平话》。(二)但今所有的《三国志平话》的第一部却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这一部平话似是民间传说中的《三国志》小说的一个写定本。(三)元末明初之际,有一位伟大的小说作家,即写了《十七史演义》以及许多英雄传奇的罗贯中氏出来,依据着陈寿的史传,将虞氏本的《平话》完全改写过,而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即《十七史演义》之一)。(四)罗书行,而虞书遂废。罗书的最早刊本似在嘉靖元年。自此以后,传本至夥。……(五)到了清初,有毛宗岗者,第二次翻开陈寿、范晔诸人的史传,将《三国志通俗演义》重加修改。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九)演义的演化,总是沿了一条共同的大路走去的,便是愈趋愈近于真实的历史,愈趋愈远于民间的传说。民间的传说驯至另成了英雄传奇,而演义则结束于‘章回体’的白话历史的一个局面之上。”[7](P210-220)
虽然在这些早期研究者的笔下还没有出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样的概念术语(因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术语是徐先生提出来的),但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体小说具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特点。而徐先生正是沿着这些先行者所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从而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的。
其实,就是与徐先生在一些具体作品是不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问题上发生过争鸣的学者中,也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属“集体累积”作品是经过胡适、鲁迅等人认定的。这里不妨举李时人先生为例。因为李先生在《西游记》、《金瓶梅》研究上的观点与徐先生不同而多次被纪文在批评徐先生时使用。李先生在为最近出版的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一书所作的序中说:
关于《水浒传》是经过长期“集体累积”才最后成书的作品,中国现代的研究者,胡适、鲁迅以来,一般是没有疑议的。虽然有人从文学的角度更愿意强调“最后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但也无法否认《水浒传》有一个“集体累积”的过程。不过,《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虽然同为“集体累积”,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这亦是《水浒传》在形式内容、文学风格和精神意蕴上不同于《三国志演义》的原因。[8](P2-3)
可见,李先生也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是“集体累积”作品,并且认为《水浒传》为“集体累积”作品是经过胡适、鲁迅认定的。
上文已引徐先生在《徐朔方集·自序》中关于“宋(金)元时代,杂剧、南戏和话本的传世之作几乎都是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的论述,由此可知,根据徐先生的定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指“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的作品,罗贯中、施耐庵这些光辉的名字自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作品的编著写定者。徐先生的论述本来是非常清楚的,似乎不应当有什么歧义。可是纪文并不这么理解。纪文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用来批驳徐先生在明代“四大奇书”方面的一些具体论点的,虽然纪文的批评也不无可取之处,但许多时候的批评则是“偏颇与失当”的,这里试举几例:
一、关于《三国演义》,纪文在引了徐先生的“从晋陈寿《三国志》和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开始,三国题材逐渐由正史进入传说(包括民间口头传说和文人的野史笔记),然而进入以说话为主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说话艺人有的本来是文人,找不到别的出路,被迫以此为生,如南宋、金、元和明初的书会才人,另外又有中下层文人的参与。《三国演义》为我国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最悠久、最典型、最完整的范例”[4](P1)之后,批评道:“这种说法的失当之处,就在于它有意无意地把作家所依据的创作素材等同于作家的创作,过分强调了作家对民间文艺创作的依赖关系,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的著作权。”徐先生的《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文一共六节,探讨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各种版本、《三国演义》的定本等问题。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之间还应当有些环节,由于这些环节后来失落了,导致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无论如何徐先生的文章与“有意无意地把作家所依据的创作素材等同于作家的创作”是扯不到一起的。不知纪文是如何界定作家的创作素材的,也不知纪文所说的有关三国题材的民间传说、话本和戏剧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仅仅是素材与作品的关系是如何得出的。
二、关于《水浒传》,纪文在“徐朔方认为:‘从《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杂剧可以想见,接近《水浒传》小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经形成了’;‘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因为‘《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所以说‘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之后紧接着批评道:“元代水浒故事是不是一套完整的故事,是否接近《水浒传》,这还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即便确如徐朔方所说,可是要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恐怕仍离不开一个文章高手的熔炼。”
以上纪文的引文看似非常连贯,其实是将徐先生的《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一文中相隔10页的属于三个不同小节的内容断章取义地精心捏合在一起的,看似天衣无缝,实际是大大歪曲了徐先生的原意的。
现取收入徐先生《小说考信编》的原文,核对说明如下:“从《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杂剧可以想见,接近《水浒传》小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经形成了”,见《小说考信编》第37页,这句话后还有一句“虽然,它的某些重要情节可能还没有最后定型”被纪文删除,这是文章第二节《作为口头文学的水浒故事在元代形成》中的内容;“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见该书第41页,这是第四节《〈水浒传〉是世世代代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中的内容;“《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也为第四节中的内容,完整的句子是“从以上五个方面看来,在现在所见的《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见该书第46页;“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第五节《〈水浒传〉的编著写定者施耐庵与罗贯中》中的内容,全文为“上文论证了《水浒传》大约成书在元末或明初,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那末谁是它的编著写定者呢?”见该书第47页。
纪文将徐先生文章中属于三个不同小节的相隔10页的文字掐头去尾,巧妙地拼接在一起,尤其是最后一句引文中去掉了“那末谁是它的编著写定者呢”这句最为关键的话,故意将徐先生文章的完整意思割裂开来,并且歪曲了徐先生的原意,从而达到批判徐先生的目的。
其实,徐先生在在这部论著中不仅第五节《〈水浒传〉的编著写定者施耐庵与罗贯中》是专用来讨论《水浒传》的编著写定者的,而且在第四节《〈水浒传〉是世世代代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中开头的一段话就是肯定最后写定者的功绩的:
长篇小说《水浒传》如同《三国志演义》一样,是在世代相传的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常识了。但总有一位作家最后将它记录、整理、加工以至创作成书;更可能的是在初次成书之后,又有人出来加工、创作使小说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许是一次、两次,也许是几次之后,才达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在世界小说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度。[4](P39)
论著中第五节整节及第四节中以上引文正是在说明“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离不开一个文章高手的熔炼”的,不知纪文为何要将徐先生的完整意思割裂开来并且对徐先生的论述横加指责。
三、关于《西游记》,纪文批评道:“今本《西游记》与它之前的西游记故事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均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已呈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石昌渝即说:‘……与前两种奇书相比,《西游记》更鲜明的表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又说:‘……这种合乎情理、比真实还真实的荒诞,构成《西游记》的独特风格。这是一种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李时人也说:‘《西游记》的谐谑是一种熔滑稽、讽刺和幽默于一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既然《西游记》‘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并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属于集体创作呢?”
这一段批评文字颇有意思,“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是石先生的认定,“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是李先生的认定,他们两位是主张《西游记》为个人独创的,因此有这样的认识。可以说他们的认定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作为一家之言,无可厚非。而徐先生是主张《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当然与石、李两位先生的看法不同。这里用石、李两先生的看法来作为批判徐先生的武器,用广东话来说是不是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如何鉴定石、李两先生的看法一定正确,徐先生的看法一定不正确呢?退一步说,认为《西游记》最后写定者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西游故事世代累积发展的事实并不矛盾——从某种角度上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写定者也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
四、关于《金瓶梅》,必须指出,徐先生认为《金瓶梅》也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确实有很不完善甚至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如按徐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不是由《水浒传》“武松杀嫂”衍化而来,而是与《水浒》中这一情节同出一源即有关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传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成书过程是如何“世代累积”的,徐先生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是他的《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遭到较多学者质难之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徐先生及韩南、浦安迪、梅节、陈益源等许多中外学者所揭示的《金瓶梅》中存在的众多的问题,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会有的问题。因此,《金瓶梅》究竟是文人独创的作品还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但纪文中下面所提出的针对徐先生的批评显然是颇成问题的:
(一)“主张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之作,‘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风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生活的鲜明印记’,而且其中有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和人物(如狄斯彬、凌云翼)到了明嘉靖以后才出现,那么又怎能说它是世代累积的呢?难道明人明事在宋元时就开始‘累积’了吗?”纪文这段话中的两处引文没有交代出处,我在徐先生的文章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处引文不知出自何人之文章,我也没有时间去一一找出来。退一步说,即使这两处引文为徐先生所说,也无妨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因为既然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么它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作品,而以宋朝为背景的作品中出现了明朝嘉靖以后的人和事,这说明到明朝嘉靖以后该作品还处于累积过程中或接近于写定。这不正是提供了《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证据吗?
(二)“《金瓶梅》虽然题名中有‘词话’两字,但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纪文可能误读了徐先生的文章,以为徐先生将《金瓶梅词话》看成是讲唱文学。其实徐先生从来没有认为《金瓶梅词话》是讲唱文学,不过他倒是说过《金瓶梅词话》保留有说唱艺术的痕迹:“词话就是话本,两者并无本质区别。词话可说是话本的早期形态,在它由说唱兼重发展成为说话为主时才通称为话本。按照这样的观点,《金瓶梅》词话是元明世代累积型小说唱的成份保留得最多的一个标本,不妨称之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块活化石”[4](P255)、“从《金瓶梅词话》本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不是作家个人创作。即使后来写定者作了极大改动,以致他的加工使得原有词话的面目全然改观,他也不可能把说唱艺术的痕迹删除净尽。”[4](P69-70)
(三)“《金瓶梅》中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这在《红楼梦》那样精心结撰的小说中也照样存在,不能以之作为判断是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的原则。”无可否认,《红楼梦》中虽然也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但这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同一人所作应当有很大关系。即使是中外文学史上别的个人独创的名著中,偶尔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也在所难免。但中外文学史上好像并没有哪部个人独创的名著,存在着《金瓶梅》那样大量的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据徐先生介绍,美国韩南教授在论文《金瓶梅探源》中“指出九种话本和非话本小说的情节曾被《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多次大段地被《金瓶梅》引用,有的作为唱词,有的作为正文的描写或叙述之用;另外引用套曲二十套(其中十七套是全文)、清曲一百零三首。它们大都散见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吴歈萃雅》等曲选中”[4](P77);香港梅节先生“发现词话套用《怀春雅集》诗词十七首,经台湾陈益源先生增补为二十一首(其中重出一首)”[4](P6,前言)试问在《红楼梦》或别的个人独创的中外名著中存在如此多的大量引用别人作品的情况吗?
综上所述,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并不是某种观念引导出来的主观臆测,而是建立在前人研究与他自己的深入考察与综合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学术观点;徐先生的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并没有完全否认作家个人创作的功绩,只是针对以往小说史研究中过多强调个人创作成就而作出有益的反拨(“许多研究者一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面在实际上却又无形中把它们作为个人创作看待。”[3](P2,自序)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接近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也更能够对具体作家与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这一总结性的观点难免也有不够周全的地方,尤其涉及到具体作品是不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他的判断有时可能不那么正确甚至可能还有失误。他常常批评别人,同时也常常受人批评,任何严肃的有助于将问题引向深入从而推动学术前进的争鸣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为徐先生所欢迎的。但纪文对徐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批评,从立论上看,恰恰犯了观念先行的大忌,而不是从徐先生的具体论证出发;从逻辑上看,纪文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与作家个人创作完全对立起来,并将这种观点强加到徐先生头上,这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
注释:
①郑振铎相关论文原载《中国文学论集》(1929年)和《佝偻集》(1934年),后编入《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郑振铎全集》第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标签:文学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金瓶梅论文; 读书论文; 罗贯中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纪文论文; 水浒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