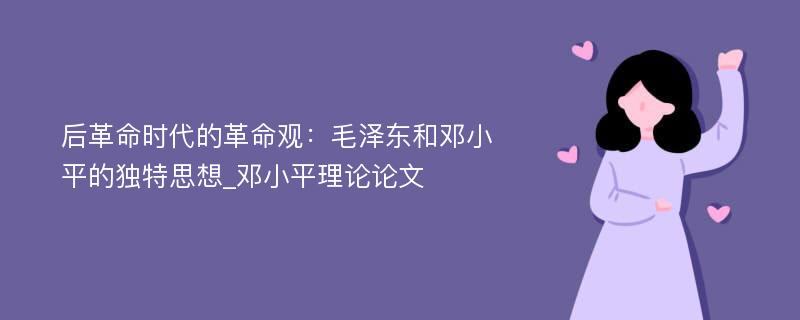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特论文,时代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宣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按照传统的观点,随着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也就进入了后革命时代。那么,在后革命时代,革命究竟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以何种形式存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回答。
一 两种性质的革命
毛泽东作为在革命中崛起的领袖,对于“革命”这两个字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偏好,他的口号是“不断革命”。1956年初,当全党还沉浸在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中时,他就已经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吹响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新号角。毛泽东豪迈地提出要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向自然界开战。1957年,他通过反右斗争,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概念,从而为党原本认为已经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新的领域。1966年,更发展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性质的革命: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如何处理这两种性质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从而为建设性质的革命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因此,毛泽东的设想是把两种革命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这样,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既可以为建设性质的革命提供动力,又能够保证建设性质的革命的正确政治方向,避免建设走到邪路上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就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革命并举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1955年7月,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进入后革命时代,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的思想[2]。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求继续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3]。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同样体现了毛泽东试图将两种革命并举的愿望。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也提出了两种性质的革命。一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即改革;一个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指出:这两种革命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自身的革命。前者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后者解决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邓小平认为这两种性质的革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为现代化扫清障碍,是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改革的根本目的。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的两种革命并举的思想,又将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转换为“以改革促发展”,真正找到了两种革命的结合点。
二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结束,下一步就要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然而,由于国际上的影响,国内的“右派进攻”,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经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反复思考,提出:“单由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4]这实际上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半任务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刚刚开始,以后还要长期进行下去。
应当说,在后革命时代,的确仍然存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毛泽东作为斗争经验极其丰富的政治家,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实践证明,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同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不能采取强制和压服的手段,只能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尺,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只能是实践。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当时的认识也并不是完全清醒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高压和思想专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矛盾,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一概上纲为阶级斗争,进而称之为“革命”,实际上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如胡乔木所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面,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5]毛泽东还提出进行这个革命的最有效方法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四大”号称“大民主”,实质上却是一种变相的思想专制,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
毛泽东晚年最为看重的是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向“走资派”夺权的“政治大革命”,也包括以“斗私批修”为纲领的“思想大革命”。就后者而言,“文化大革命”与1957年提出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脉相承,把矛头指向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前者而言,“文化大革命”比“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所谓走资派。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造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像苏联那样蜕变为修正主义,才能防止中国“改变颜色”。
应当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敢于正视党内阴暗面,并且不惜采取非常手段向党内阴暗面开刀,这种彻底的革命立场和政治勇气是无与伦比的,让那些沉迷于争权夺利、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庸俗政客们相形见绌。问题在于,毛泽东对于产生这些阴暗面的原因作出了误判,没有看到问题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仿效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密切相关,反而认为根源在于所谓修正主义,即“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7]。诊断的失误导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彻底开展阶级斗争,铲除修正主义滋生的土壤。
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估量越来越严重,解决问题的手段也越来越激进。如果说,“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最后,宣称要打倒的敌人实际上一个也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也没有一个走资派。历史事实无情地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虚幻。毛泽东执着地相信:持续不断地搞好阶级斗争,就既能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又能调动人们的革命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更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在毁坏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得混乱不堪,不成样子。诚如胡乔木所言: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5]在历史进入后革命时代以后,仍然坚持把阶级斗争当作革命的主题,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当作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动力,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在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赋予革命以新的内涵,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的重要命题。
依据邓小平的看法,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在我党历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表现形式,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这次革命彻底推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革命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以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为表现形式。政策的重新选择,最根本的在于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而体制的重新构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就不是改良,就不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体制这个层次上来一个质变。中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革命的目标,是要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8]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固然,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革命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放生产力,扫除的障碍是剥削阶级和腐朽落后的旧社会制度;第二次革命则是以重新选择政策、重新构建体制的方式解放生产力,扫除的障碍是旧政策和旧体制。但是,邓小平透过这些形式的不同,看到了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质:即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邓小平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将当代中国的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一种崭新的革命观。以往人们虽然也认识到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但总是将其表现形式限定于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方式,是革命的唯一形式。而邓小平从实践中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一次普通的改革,而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体制转轨,它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丝毫不亚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因而也应当纳入革命的范畴。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判断一场变革是不是革命,依据的是生产力标准,主要看其性质是不是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拘泥于它的表现形式。这就大大拓展了革命的外延,赋予这一概念以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生命力。邓小平这种崭新的革命观,反映了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革命本质的深层把握。邓小平认为,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9]。这就抓住了革命的要害、革命的灵魂、革命的本质。注重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一革命的本质,而不拘泥于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邓小平革命观的一大特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界,对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重要命题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相当一部分论者受传统革命观的局限,认为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是从转义或广义上使用“革命”的概念,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改革的重视,是为了给改革贴上政治的护身符,甚至是出于一种语言表达的惯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清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的本意。我们只有认识到邓小平将革命定义为一切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变革而不是局限于阶级斗争,才能明白:在邓小平心目中,改革的的确确是革命,而且是一场本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三 生产力方面的革命
毛泽东一贯认为,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同年12月8日,他在与全国工商联部分代表座谈时,更为明白地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3]
正由于此,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之时,毛泽东立即向全党发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提出要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1957年3月, 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明确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1958年初,他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3]。
可以说,1956年到1958年,毛泽东最常讲到的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种革命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有着质的不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和平建设性质的革命。1957年3月29日, 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10]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实现革命性质的转变,其态度是坚决的,这一思想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的,也是非常及时而又难能可贵的,与党的“八大”决议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完全一致,应当给予高度的评价。
还应该提到的是,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的概念,并将其称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个革命”[10]。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同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说到:“我们是进行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地提高。”[10]作为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9]的崭新命题。邓小平认为: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面貌,因而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全国人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一重要命题出发,邓小平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高度阐述了他的新革命观。他针对以往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观,强调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最根本的革命。”[9]这一重要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是一个足以导致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革命观、重新认识革命概念的重大命题。在这里,邓小平的语气是层层递进的:他先是肯定“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将过去视为革命转义的内容纳入革命的本义范畴;继而指出它是很重要的革命,使其成为革命家族内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员;最后又强调“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最根本的革命”,从而使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赋予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如此之高的地位,是不是有夸大其辞之嫌呢?恐怕不能这样看。其实,邓小平认定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恰恰表明了他对历史、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发生的任何革命(亦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最终目的都在于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只有生产力自身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社会生活的面貌有了彻底改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的价值才能得以最终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不是最根本的,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意义。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将导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因而它是最根本的革命。
对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的无比重视,无疑是邓小平革命观的又一大特色。实现四个现代化,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焦点问题。他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充分体现了他对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这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的殷切期盼。
四 结语
比较后革命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革命观,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革命观各具特色。毛泽东的革命观,其最大特点毫无疑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力图把两种性质的革命结合起来,他找的结合点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指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2]这段文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是怎样看待两种革命之关系的。所谓“政治”盖指“思想、政治革命”,亦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与“技术革命”即经济建设的关系是统帅和士兵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政治挂帅”,也就是思想、政治革命挂帅,也就是阶级斗争挂帅,处在“君”的地位。中国有句古语叫“君为臣纲”,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成了其臣属——“技术革命”的纲。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盖源于此。
“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说必须始终以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为工作重点。毛泽东认为:工作重点要依当时的形势而定;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要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就应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而当资本主义复辟成为主要危险时,工作重点就要重新转向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
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相反,“大跃进”运动是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工作重点的。但即使在这时,“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坚持政治统帅经济,经济规律要为政治意志让路;要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工农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样做的结果,生产力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和发展,反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至于“文化大革命”,则干脆把革命的主要目标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而所谓“纯洁”,实际上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
“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11]。邓小平的革命观,最大特点在于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改革把矛头指向旧政策和旧体制,真正找准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要害,真正找准了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结合点。无论是改革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心都在于发展生产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不关心生产力以外的东西。与毛泽东一样,他也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多,也最坚持。他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但是,“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8],这是一种极为清醒的看法。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指出,在我党历史上,“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9]邓小平的意见切中要害,抓住了思想政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弥补了毛泽东只重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却忽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之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邓小平都避免采用“革命”的提法,他主张不要搞政治运动,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广大干部和群众。这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总之,对于邓小平来说,谈革命,就要围绕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他方面则不宜采取这样的提法。这样就把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引导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来,彻底扭转了那种一谈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避免重新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邓小平对革命的阐发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确实有着超越前人的理解。他的每一次论述都紧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主旨,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而且能够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跳出了传统革命观的局限,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提升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邓小平对革命的诠释,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而在细细品味之后人们又发现,他的诠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深刻领悟之上的。
他对革命的论述,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生产力观点出发的,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的革命观,既有“返本”的一面,又有“开新”的一面,既有正本清源的思想梳理,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既恢复了革命的真精神,又开辟了革命的新天地。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仍然固守传统的革命观,继续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就会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这样的革命严重背离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只能成为虚幻的革命。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裕,人们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革命以新的内涵,使革命的重心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实现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既与他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定位有关,也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透辟理解有关。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考察,正确地认识到时代主题已经转向和平与发展,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确立了革命重心战略转移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思考,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8],“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8],在这样一个结论之上,确立了革命重心战略转移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实现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也是因为他站在了毛泽东的肩膀之上。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思想有着深刻的领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更是有着痛彻的体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全面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决否定在后革命时代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同时又把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思想发扬光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以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内容的新和平革命,史称“第二次革命”。新的革命虽然不象第一次革命那样“慨而慷”,但在和平的外表下却涌动着改天换地的神力。它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所释放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更是世所罕见的。它的内在冲击力一点也不亚于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它促使中国现代化运动在短短20年内就出现了质的飞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面貌。历史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新革命观的正确性。但是,追溯邓小平新革命观的思想来源,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应当淡忘毛泽东这一宝贵的思想贡献。
对于革命时代的革命理论,人们关注的已经很多了;但对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理论,人们往往重视不够。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后革命时代对于革命的独特思考,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他们的革命观,必将推动人们对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动向有进一步的认识。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革命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