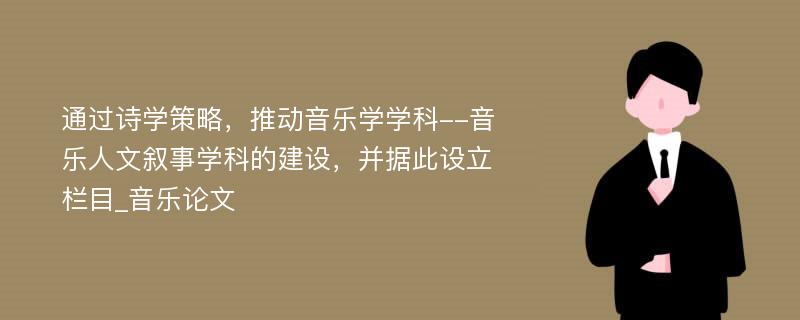
通过诗学策略,驱动音乐学学科建设——音乐人文叙辞今典,并以此设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音乐论文,人文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体叙辞/Key—words:●诗学策略 ●诗/史关系 ●音乐人文叙辞今典 ●音乐人文叙辞编年
相关叙辞/Sub—words:●《乐记》
诗/史关系,是诗学策略的本原所在。
然而,当下针对者,就是对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现实功能(操作)性质的话语系统与具有抽象结构(运作)意义的叙事结构。
大凡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同为诗者。是故,以普通历史记载之主要工具文字语言而言(包括以音乐历史记载之主要工具音响而言),诗为史之第一能指者,且诗史互证。因而,综观中国音乐学的历时发展与共时相关,则诗/史者,相属也。
诗者,古训有三:承,志,持。依此三训而今解,此“诗”分别指认文字语言、人事记述(可引申为“思”“心志”)、度量衡定(可引申为“中正”)。
显然,此“人事记述”及其引申“心志”“思”,与文字语言义近,故而“字/志”相通。
进而,此“度量衡定”及其引申“中正”与叙事最为接近,故而与“史”者也最为亲和。
遂,以“诗/史”相属者,为“诗史互证”之本。
诗者,作为有别于口头本文的书面文本,则无疑,既为史之名,又为史之实。诚然,音乐学是一种具非常学理性质的学术研究,因此,作为直接当事人的音乐学家,必然会随时随地面临如何针对其术语概念体系进行技术规范处理的问题。然而,凡话语系统、叙事结构与其所属学科合式者,均系自足生成,而非人为造成。是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自足规定。
显然,不同话语对象及其主体的集结,将形成全方位的合纵联横。作为对象,既在事实,又在文献;作为主体,既有投入,又有退降。
以人文学界经典个例者见:比如,王国维治学,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互相参证(汪荣祖,1992a:46)。再比如, 德国史学研究中的语文考证学派者,倪不儿,推进信史的建立;洪保得,提出史学致知的两大步骤;兰克,除了发扬语文考证方法外,重视原手史料,开档案研究的先河;以及国学大师章学诚“六经皆史”,陈寅恪“从史实中求史识”;等等(汪荣祖,1992b:48—50)。除此之外, 就是将不同文本,包括:口头文本,书面文本,电子文本,血肉文本及其相关者,设入文化人类学之框架内,并基于历史哲学之上,进行互向考掘,并形成有序之系谱,从而求得:史之实在与理之纯粹。
至此,关于诗学策略。即通过叙事(纪事/纪实,叙述/论述,叙辞/术语,事思并鉴/诗史互证/事思诗史相属),对事项/事象状态、思维/思想方式、诗学/诗义策略、史变/史原轨迹,进行整合,从而回到“元叙事”。并通过叙辞自身的折叠,以增加叙事之厚度。诚然,此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并非是对叙事的叙事, 也不是对设定的预设或者后设,而是对人文化遮蔽的祛除,对意识形态假象的还原,即:绞断“主体后”之延续,以敞开“主体前”之原真。
于是,作为对叙事原真状态(有别于“原在”)的折返,是以叙辞今典为当下基点,远及文化元典(经典,古典),旁及俚俗别典。或者,逐及古典,经典,以至终及元典,再转而旁及俚俗,别典。即把叙辞作为叙事对象入典,将术语当作具体学科乃至理论的概念模型,并随着操作堆积的不断深入,再逐步进行元理论的提升。对此,有关“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已成为显者,而潜者所在,便为“词与义”的互动关系。依前者见,法国当代思想家傅柯,曾在其《临床医学的的诞生》前言中说道:我们必须超越其内容及逻辑形式,去检视语言的最基础层次——亦即“事物”(choses)与“词语”(mots)还未分离、看(voir)及说(dire)仍是同一件事——之领域。(原注解:mots具有单语(词语)之意味,也是傅柯一贯关注之问题。物之沉默世界,只有经由对言语活动进行发掘,方能呈现)(傅柯,1994:4—5及注7)。以后者言, 如果,藉此叙事模型引申,那么,词之混乱世界,只有经由对其意义结构进行发掘,并建构相应的系谱,方能呈现;是为“词与义”。由是,词与物:重点在于“名/实”关系,表示对术语所指对象的认识与理解;词与义:则重点成为“实际/符号/意义”关系,表示在对术语所指对象有所认识与理解的同时,又参与和拥有对术语能指本身的认识与理解,亦即:在“事物的秩序”之后,再建立“意义的系谱”。因而,所谓回到“元叙事”,就是在“叙事/叙述/叙辞”之不同层面的呈现之后,在“超验/基础/反省/时间”之集大成之后(利奥塔,1996:231 ),依然:意识形态是为居住家园,人文叙事是为话语依托。
诚然,叙辞作为一个存在,将对学科成型作出最后承诺。就像“通过叙事对事/思/诗/史进行整合,并通过叙辞自身的折叠以增加叙事之厚度”(韩鍾恩,1997;193)一样, 之所以“叙辞”凸显并再度关注诗学策略,则有两个作为在:一、叙辞编年,并通过术语/概念体系,作为学科发展史写作驱动;二、叙辞今典,再通过术语/概念体系,作为学科发展史写作合力。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叙事对象,因而,也有特定的文本,以及相应的叙辞。以中国音乐传统为例,作为基本前提,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具元典意义的定位,则首选《乐记》无疑。一者,它所体现的思想,可以被视为有文字记载中国音乐历史之正宗;再者,在此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它也基本上处在主导位置上;况且,依其文本所示,不仅提供系统的范畴,又成就相应的叙辞——音乐本体/乐本,音乐现象/乐论,音乐规则/乐礼,音乐行为/乐施,音乐表现/乐言,音乐行态/乐象,音乐情智/乐情,音乐能昨/乐化(详见后续个案)。
由此,跨越一大步,将时段截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前后,或者以中西文化发生关系断代,尽管,此刻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处在断裂的边缘(指已然成型的中西文化相遇,乃至冲突),但是,当时中国文人对音乐的关注,进而,对音乐的叙事,则仍然启用旧式“文言”作为语具,并且,依照陈时“论语”作为依托。跨过世纪界桩之后,尤其,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叙事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则西语便逐渐融入其中,于是,“文言+西语”的叙事,不仅成就为一种样式,而且,也渐渐形成为某种时尚。进而,随着叙辞变化的日益强化(语式和辞相),则叙事方式也开始骤变:凡事界划或者定义,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或者古典的范式(近乎逻辑式的演绎推论和分工后的种类归属),很明显,一西这方式已然贯通。从此,“二分状态/两相关系”(有别于传统的“合一状态/综合关系”)的学理模式开始普遍起来,以至于成为抵达“定理/公约”顶端的中介。
在此之后,别一个景观:于不同历史时段的诗学历程,或者叙辞的意义定位。以20世纪下半叶为例:50、60年代,是轴心化权威话语时段,多核心术语群,趋共性化倾向,呈树形结构,载统制性语义;70年代“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高压出现话语断层,是典型的无话语时段;80年代,是多种话语无序时段,多割据术语群,趋个性化倾向,呈平面结构,载并存性语义;90年代,是边缘化无权威话语时段,多琐碎术语(已难以成“群”),趋立体化倾向,呈滚动结构,载复合性语义。综观以上,其总体取向为:话语所指相对拆解,庆语能指逐渐凸显。针对于此,则新的诗学策略理应是:批判50年代以来专制集权话语(官僚文化宫殿),汲取80年代末以来大众口头话语(俚俗文化狂欢节),接续长期以来有传统可循的文人书面话语(精英文化圣坛),并力图消解与拆除由“官文化、士文化、僧文化圣坛走向俗文化狂欢节”的种种势力,以使得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日益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面对频繁消解的中心和瞬间拆除的底基,当代人不断发出呼救式的箴言,继尼采断言“上帝死了”(人之所以“在”的主宰不在了)、傅柯断言“人死了”(人之所以“在”的主体不在了)、利奥塔断言“知识分子死了”(主体之所以“在”的思想不在了)之后,又有人给出一个寓言:“语言死了”(思想之所以“在”的用具不在了)。于是,当我们以“知识架构”的名义再次出场的时候,又不得不从新面对——通过“叙辞”诠释历史。
通过“叙辞”诠释历史。它将涉及:物象的叙事,事象的叙事,人相的叙事,辞相的叙事。甚至,可以把不同种类的文化交织在一起,通过“描述和分析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活力和影响的领域(force—field)”,关注“它们如何给了每一种文化以特殊的组织和风格, 如何构成了文化活力的储存库”(任可,1998,215)。进而, 必然成就一种“档案意识”和“知识间性意识”:通过“原始叙事文本”“直接间接引述文本”“之后研究文本”的逐个层级滚动(叙辞今典),去不断“考掘”存见文献(叙辞编年)。所谓“照着他说”“接着他说”“借着他说”,无非,仍然在“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当中;其实,“通过我”,把“照着他说/接着他说/借着他说”加以整合,则就成就起一个新的叙事格局:“六经注六经”。也许,这才是最最根本意义上的“知识架构”,以及“可信之产权”“可靠之安全”。哪怕完全悬置任何重力下垂,仅仅留存几许文字,它也会布满历史的印迹。于是,通过“叙辞编年/叙辞今典”,甚至,不惜时段结构(布罗代尔,1992:1—18)的“程序逆动”, 把“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史/经验史”建构起来。
傅柯说——这里所关切的不是要把话语中立化,使它成为代表其他物的符号,或是要深入它的内部以求触及其中静默不为人知的部分。相反的,我们要维系它完整状况,并使它在本身最复杂的状况下出现。简言之, 我们想要作的是排开“事物”(things ), 不要使其现身(depresentify)。我们想去塑造它们在目前丰厚结实、立即体现的完满状况,这个状况我们通常视为话语原始的律法,……用只出现在话语对象之规律化形构来代话语出现前那神秘不可测的“事物”的珍藏,去定义这些话语对象(objects)而不提及事物的基础, 但同时将与其其形成话语对象的规则连接起来,就这样构成了它们历史性出现的条件。我们要写作一部有关话语的历史,这部历史不会使话语对象坠入其所源生的低等境域中,而是要铺陈统治话语对象四散蔬离的规则间之关联。(傅柯,1969:129—130)
于昌,从最最简单单纯的地方开始,经过时间的中介,又在最最基本本原的地方终结。
就这样,被还原者,以此方式样态——
……在这里,曾经有一天……
一个古老叙事。既在事实文本,又在文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