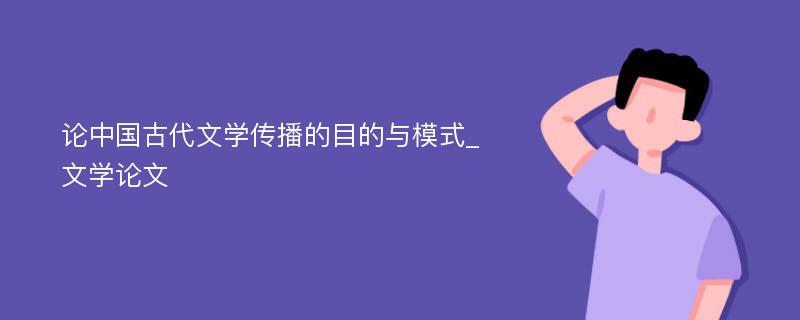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与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方式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4)02-0045-06
既往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而言,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文学自身的通变诸因素外,来自传播方面的推动和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并值得注意的因素和动力。
作为学术概念的“传播”是多义的:在词源学上,它具有信息的分享和信息的传递两方面意义,而就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感情。一般说来,“传播是由:发送者、传递渠道、讯息、接受者,以及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效果、传播发生的场合,还有讯息所涉及的一系列事件”组构而成的[1](P5)。社会科学意义的传播大体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同时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在本质上是流动的,因此它呈现着动态且复杂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似也遵从了上述理论规律和特定的原则,而且体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本文对此所做的描述和说明,即是为了揭示其与文学发展以及与新文学建设有关的规律性表现和一定理论质素。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
尽管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文学的起源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并随其发展而发展却毫无疑义。在文学的发展运动形式中,传播是其重要形式之一。这里我们首先提出的是:古代文学在其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传播,是因为怎样的目的?亦即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是什么。
(一)察民意观民风。作为传播目的的察民意与观民风,是指统治阶级指派专人或专门机构收集民歌,加以整理和演奏,以此来考察社会情况。以诗为例。虽然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形式是神话,但作为自觉创作且含有明确主体意识的文学体裁却是诗。尤其是肇始于周朝的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政治的盛衰状况,即所谓“治世之音安而乐,亡国之音哀而衰”,因此,统治者可以通过其来“观民风,察得失”,考察他们的政治情况。出于这样的目的,统治阶层主动地大量收集民歌,并“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做法,在周朝是政府派“行人振木铎以求诗”,或用一些年老无子之人充之[2],汉朝以后则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所设的“乐府”机构来进行。汉乐府、南北朝乐府都是这一与政治有关措施的产物。因为统治者对民歌的此种采集和编排,以及在政府高层和更大范围内演唱,古代的诗歌便因此得到较好的传播。
(二)政治劝谏。周朝统治者除注意通过民歌考察其政治情况外,还鼓励公卿大夫献诗,其时称为“赋诗言志”,于是许多居庙堂之高的官僚就写了不少诗,对时政提出意见和批评,并传到最高统治者那里。此一传统发展到汉朝,就嬗变为以大赋来歌功颂德。当时许多士人利用大赋对政治进行赞扬或稍作批评,这也就是后来所谓“劝百讽一”的大赋传统。这一传统再被发扬就表现为后来的以诗歌或文章指摘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3]。这方面较早的作家有西汉的贾谊和晁错。他们的《过秦论》与《论贵粟书》都是为谏诤其时政而作。至唐代则出现了白居易和柳宗元。前者以发动和领导“新乐府诗”运动而著称,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之创作动机指导下,写了不少像《秦中吟》、《寄唐生》一类“使权要者扼腕”的政治讽喻诗;后者则主要将外任地方官时的所见所闻发为干预时政的文章,如《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在此目的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赋文章得到很好的传播。
以劝谏政治为目的而实现文学传播的另一表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所涌现出的士阶层,他们面对当时激烈动荡的时代和期待改革的社会,产生了许多政治主张和改革社会的理想,为了使这些社会改革意见被某些诸侯国所信用,士们便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以文章和说辞来干预国家政治,而其时的文章和说辞,便是广义的文学。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文学传播的结果是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沸腾局面,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等。
(三)抒发情怀,豁展怀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对此,唐人韩愈在其《送孟东野序》里有相当精辟的概括:他将自然界的和古代社会的不平而鸣的现象作了纵向的归纳,并揭示出不平而鸣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事实,明确指出:人在遭遇不公引起愤怒或不满的情绪时,作为情绪的主体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来将这一情绪发泄出来,用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和情绪稳定。其实,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很多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著作都是痛苦灵魂的呼叫,是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控诉。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一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恰好是以抒豁怀抱为目的的文学传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形成过一个源远流长的咏怀传统,而在传播学意义上,这个传统所造成的文学创作都是以抒豁怀抱为传播目的的作品。大略统计写作这种作品的作家,可以从先秦大批士人算起,再到东汉张衡、蔡邕、赵壹,以及魏晋时的“三曹”、“七子”、阮籍、嵇康,直到明代小说家周清源、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等,列出一个系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说文体抒豁怀抱的情况。在惯常的理解中,利用文学艺术抒愤豁怀往往是诗人所为,但我们在小说史上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明初传奇小说作家群落中。其时以瞿佑、李昌祺为代表的这一群落,他们的“风情丽逸”性格和“感离抚遇心怦怦”[5]的命运遭际所引发的激荡情怀,在明初那个理学氛围浓郁的时代里只好借助小说来表现。
(四)教育与教化。“诗三百”产生以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曾经被作为教材,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志鸟、兽、草、木、虫、鱼;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不学诗,无以言”[6]等言论即可说明此点。在此文化背景下,春秋战国之际曾出现了一个用诗时代。“诗三百”因为充作教材的缘故,在学习、外交和游说场合中被广泛传播着。与之近似的文学经典是后来的《文选》,该书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选取了自先秦至南朝的若干诗文。该书后来成为读书人的最基本教材之一,借着科举制度,它对于文学传播的功绩是非凡的。这还不包括因它启示而出现的《乐府诗集》、《唐宋八大家文钞》等“文选”系列在传播方面的贡献。
以教化为目的的传播也几乎同时发生,孔子在以诗教人的同时,也曾对这些古诗“去其重,取其合于礼仪者皆弦歌之”[6]。此后,以文学“宏教化、厚风俗、正人伦”的教化意识就作为传统而因袭下来:无数秉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人在写文为诗时大都以此价值观相约束,并自觉地在作品中进行宏扬,于是大规模的文学传播也就造成。他们中不仅有那些身为官僚的文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通俗文学作家,甚至连那些大写恋情、色情小说的作家们也标榜他们是按情教的目的来进行创作的。
(五)自娱与娱人。该目的与抒豁怀抱有性质上的相同,二者只在动机的程度上表现出特定区别。文学作品既然可以抒豁作家的怀抱,也自然可以自娱和娱人,尤其是当中国古代的文学由严肃、功利渐向艺术与游戏方面倾斜以后,以自娱与娱人为目的的文学创作就逐渐增多。就诗而言,有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玄言诗;就词来看,由于它如李清照所言“别是一家”,是诗的解放,因而很少有人将写词视为严肃创作,这样,以之自娱和娱人也就顺理成章;就小说而言,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严肃的面孔出现:较早的小说是“发明神道之不诬”[7]的搜神故事,到唐朝则主要用来“行卷”,即考前通融,宋元时就更演变为“不枉教座间星拱”的伎艺表演,至明代,尽管小说家们不断自重其文,但充其量不过是“倚枕、随航、雨窗”的“解睡之具”[8],也主要是用来娱人和自娱的东西。对此,明小说家凌濛初说得很实在:“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9]但自娱也好,娱人也好,小说却因此而传播开去。
(六)艺术鉴赏与文学价值追求。中国古代从东汉末年就出现了人伦鉴赏和人物品评,魏晋时,此种现象再伸展到文学领域,遂有文学上的论文和诗品。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锺嵘的《诗品》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到后来,文学鉴赏在上流社会的文人圈中更以一种文学沙龙形式表现出来,其主要的形态就是高层文人组成的小群体,他们相互间的文学鉴赏,便形成一种很有力度的文学传播,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某某体”。南朝沈约、周颙为代表的“永明体”、徐陵和庾信为代表的“徐庾体”,初唐“上官体”,宋初“西昆体”,明初“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都是其代表。这些“体”中所包涵的文学传播情况是:高层文人群体或以文学创作相酬唱,或以文学艺术相讲求,或以文学为目的而竞相追新,总之,是以文学鉴赏为旨归的,而这样的结果在传播学意义上,则形成文学传播的波圈。况且,此种由高层文人组成群体的沙龙性文学传播,其力度是相当大的,其传播之广有时也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如“徐庾体”“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10];“西昆体”则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11]。
与之相类似的是以追求文学价值为目的的传播。此种传播虽也往往以士人群体为传播源,却非前所述的文学沙龙而表现为文学流派:一群作家对某人的文学价值观念表示认同,便以此为目的从创作或文学理论主张方面进行追求,由此形成特定的文学团体或流派,从而开始或兴起文学上的传播。如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以白居易为首的唐中期“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的辛派词人,明代的“公安派”、“临川派”等。
(七)射利糊口。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文学渐渐染上了商业特色,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当时刚刚兴起的通俗小说上,到元代便转移到戏剧体裁上展开,至明、清,则这两类文学体裁都比较特出。其时由于作家社会地位的低下,很多小说家和戏剧家出于谋生方面的考虑,不得不把著书的目标锁定在“为稻粮谋”,如此一来,他们的创作,以及由此创作而直接产生的文学传播就带有了非常明显的商业射利目的。此点在明末清初小说家和戏剧家那里有突出的表现。冯梦龙、凌濛初、周清源、李渔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小说家和戏剧家主要为养家糊口而创作,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又表现得比较突出,于是以商业为目的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就在此实现。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非常明确地道出了这一事实:“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钞撮成编,得四十种……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一方面是小说家要写,一方面是书贾要买稿出书,而市民阶层则希望读到这样的作品,小说和戏剧就在这种充满商业气氛的氛围中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是与传播同步的,所以其传播过程应该是从先秦到晚清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因此带来的问题是,由于这一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诸多的不同时代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传播不惟其目的多种,其传播方式和手段也同时呈现为多样化,亦即每一时代大都有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比乐弦歌。就文献所载的文学作品而言,学界一般认为较早的文学作品是《诗经》,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地进行,较早的文学传播方式便是比乐弦歌。
如上所论,因为统治者政治考察目的而得以传播的“诗三百”,就主要采取了这一方式。在该民歌集的扩散过程中,尤其是传达给天子的时候,是用谱上弦乐而实现的,这就是“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关于“诗三百”凭借配乐和弦歌方式传播的情况,文献多有记载。《墨子》曾记孔子“弦歌三百,歌诗三百”[12];《论语》亦述,“古者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去其重,取其合乎礼仪者”,还有该书所记载的颜渊“发歌商颂”[6]等。此外,《诗经》中的颂诗是郊庙演唱的祭祀歌曲,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原也都是祀庙歌曲,这些诗歌也都是通过弦乐演奏来实现其传播的。以比乐弦歌方式传播文学在汉代以后主要靠“乐府”这一国家机构来实现,再后来又逐渐发展出词、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等文学样式,它们尽管体裁内容有所不同,但在传达上却都是靠比乐弦歌来完成的。宋代关于“凡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及苏轼的“大江东去”词应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来唱的记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作者行吟与吟游。限于发表和传播的条件,先秦时代的文学传播主体更多的是作者本人,在此情况下,诗人行吟便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用的就是“行吟泽畔”方式。行吟似可更上推至孔子时代,其时《论语》所记的“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重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一形式的体现;该书另一章所写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也属此类。
行吟的传播方式到后来演化为诗人在游历中以诗歌发布自己的感受,这种文学传播方式似可称为吟游。唐代李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少年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此过程中他写下了不少壮丽的诗篇。杜甫的许多诗篇也是在其游历中发布的,如“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较大的边塞诗人群落,他们壮游塞外,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和军中艰苦及自己壮志,他们所采取的诗歌传播方式也可以视为吟游。宋元明清时代,以吟游传播自己作品的文学家仍大有人在,明代的袁中道、清代的刘鹗堪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游居芾录》,后者则是《老残游记》。
(三)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游是暂时留恋山水而游仙和隐逸则是长期留恋山水胜地,两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方式有所差异,游、隐于名山胜水的作家,主要采取吟游,虽少行吟之“行”,但“吟”却一样。山水诗、游仙诗,以及田园诗和咏怀诗是这一方式传播下来的文学成果。谢灵运、谢眺可视为此方面的佼佼者。以游仙和隐逸而传播的诗歌大多是游仙诗、山水诗和田园诗,但如果就作家的主观动机而言,这些游仙诗和田园诗似又都可归结到咏怀诗里。
在古代中国,游仙的表现比较单纯,而隐逸却相对复杂。后者可以分为身隐,即穴居岩处,以及市隐和吏隐,即隐于朝市。如果身隐者是诗人,则传播的文学是游仙诗、山水诗或田园诗;而市隐和吏隐的诗人所传播的文学则主要是咏怀诗。前者我们举孔稚圭、郭璞、吴筠,后者举明代的顾麟和唐伯虎为例。
隐逸田园是穴居岩处的旁系,通过此种方式来获得名声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古代史上代不乏人,而尤以东晋陶渊明和唐代孟浩然著称,前者成了田园诗歌的鼻祖,后者尽管没有走成终南捷径,但所获的美名却足偿其付出。
(四)周游列国、聚徒讲学与科举考试。这主要是散文或文学性文章传播所凭借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史上,散文的传播主要是靠聚徒讲学和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着。春秋战国之际,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为了发布和传播自己对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意见或规划蓝图,他们大多采取聚徒讲学或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在讲学方面,这些人大多如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孔子有“弟子三千”,墨子有“三百之众”;而在周游列国方面,他们又常常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所谓“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在此种艰苦的努力之下,他们围绕着诸如“克己复礼”、“兼爱非攻”以及“仁政”等有关政治方面的主张所写成的含有文学性质的散文得以散布和流传。
(五)谏诤与酬唱。前者是封建社会臣子对于君主所应履行的一项任务,后者则是封建社会君臣、士大夫间交际手段之一,但在中国古代,它们也作为散文和诗歌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来。早在“诗三百”时代,士大夫就曾以诗谏诤,到汉代则是以赋以文谏诤。西汉那些“劝百讽一”的大赋和政论文都是这种谏诤方式传播出来的文学成果。唐代士人多以诗和表谏净,白居易的《秦中吟》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其代表。宋代士人则擅长以议论文来实现谏诤。
谏净的行为虽仅止于君臣间,但载谏的文章或诗文的传播却不止于此,好的谏诤文辞,其传播是相当广泛的,并不仅限在当朝,有的甚至传唱千古,如李斯的《谏逐客疏》和贾谊的《过秦论》等。
酬唱的传播方式在古代中国亦源起甚早,但其兴盛却是南朝的事。其时君臣多在文学方面有所遇合,诗文酬唱也就颇多,“宫体诗”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后来相互酬唱的对象由君臣降至王公贵族,再后来更进入到平民百姓,因相互酬唱而传播的文学作品也就难以计量了。仅以王公贵族士大夫的酬唱文学为例,就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元白”、“李杜”、“二十四友”、“竟陵八友”、“永嘉四灵”等文学方面的唱和群体,而因为这种酬唱所产生的诗文集和文学流派也为数甚多。
(六)传抄与印刷。前者是后者的原始方式,而后者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突出特征是它有了媒介物。传抄源起甚早,而印刷则大致兴于隋唐宋元时期,至明代而大盛。文学在传抄中获得传播自不待言,当年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所烧的书大多都是传抄的作品,后来出现的“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说法和“洛阳纸贵”现象均指的是传抄,明代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在流行的初始也是以传抄来传播的。明代末年,印刷技术有了大的发展,大量的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通过书坊印刷出来,社会上形成了小说“无翼飞,不胫走”[13]的局面。越到后来这种以印刷为传播方式的情况越普遍,并成为文学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之一。
(七)刻石与题壁。古代中国在印刷技术尚未展开时,由于文学作品发表阵地极少,有一些作品便通过刻石或题壁的方式进行传播。前者以李斯的泰山石刻为代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碑刻;后者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代表。同时这种情况还被大量写入小说,当作情节而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水浒传》中写到的武松杀人后在墙壁上大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及宋江酒醉后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
三、辅助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
除上所论及的几个中国古代文学主要传播方式外,还有几个辅助性的重要因素应该提及,这些因素主要有:
(一)作家品格及其社会地位。这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的辅助性因素之一。中华民族是个道德至上的民族,故对于人的品格极其看重,为这样文化价值观念所决定,在文学传播中,如果作家的品格高尚,他的作品必将因其人格而获得一定传播,且传播范围是与其品格的高度成正比:品格越高尚,其作品也就传播越广。孔子的著述成为经典而千古流传、屈原的《离骚》至今传唱,陶渊明的田园诗、杜甫的爱国诗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与此相近的是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时也与其作品的传播成正比。古代中国官本位的意识非常浓郁,身居高位的作家的作品有时便因其政治位势得到较广的传播,另外,有些位势显赫的作家往往喜欢罗致文学之士,在其周围形成一定的作家群落,这也有助于其文学的传播。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晋代的刘义庆,明朝的李东阳都曾是这样文学家群体的核心人物。
(二)艺术形象与故事情节。古代中国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及故事情节有密切关系。就前者说,作品的艺术形象越鲜明、丰富和生动,越具有深广的文化蕴涵,其被传播的范围就会越大,被传播的时间就越加久远。中国文学史上的项羽、刘兰芝、花木兰、诸葛亮、宋江、贾宝玉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易言之,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是与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时间成正比的。与此相近,作品的故事情节也与本作品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一部作品如果其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并有深刻的美学、社会学意义,该作品就有可能被广泛、久远传播。文学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木兰从军、七仙女故事、唐僧取经、三国分合等都属此类;反之则很快为历史所淘汰。
(三)统治者喜好。列宁曾说过,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的思想。将此观点引申到文学传播上也有其启示意义。古代中国,文学的传播往往与统治者的喜好有很大关系。一种文学题材或形式,如果被统治者所喜欢,则会有较大范围的传播。南朝的皇帝,尤其如梁元帝、梁简文帝和陈后主都喜欢宫廷艳诗,其时就有许多人创作和传唱宫体诗,该种诗便由宫廷走向社会;南宋的皇帝喜欢话本,通俗小说在那时的繁荣也与此有一定关系;在元代,杂剧和散曲深得蒙古贵族喜爱,于是便有杂剧创作和演出上的繁荣。
(四)语言与修辞。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本身的语言和修辞有较大的关系。通俗的语言、优美的修辞往往是一部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时代骈体文的流行在很大的方面就取决于作品的修辞之精美;《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的大范围传播,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作品所使用的通俗化语言;而杜甫诗的流传则取决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和修辞上的锤炼。
当然,决定和辅助文学传播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这里的罗列和说明仅仅是择要而已。
四、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思想
无论是传播目的,还是传播方式,以及辅助传播的要素,它们的出现和形成,就其根本而言,是由一定的传播思想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传播思想。儒家在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提升思想境界、融个体于集体之中、个人的价值和欲望以群体的价值和欲望为转移的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人文表达。后者则体现为文学传播意义。就此而言,他们主张以“文”作为道德内在的外现,并与这一内在共同构成君子形象,只有这样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具有文采、文雅之意。既而他们将人格上的“文”转移到语言表达上的“文”,从而提出具有文学传播思想价值的理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一思想对于其后的文学发展和传播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再次立言”。这是先秦时代史家就坚持的一种传播思想,它是在人们的功业理想层次上产生的,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到司马迁那里,这一思想被他以实际行动发扬光大:他把忍辱含垢写作《史记》视为等同那些古圣先贤立言以传世的功业一样,并极力强调“立言”是一件可以不朽的事业,并用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加强了这一主张。此一思想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在该文中,他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一思想发生以后,对当时和以后的士人影响非常大,其弟曹植就说“骋我径寸翰,流藻重华芬”。以后更出现许多持着“文章可立身”价值观的文学家。
(四)以幻为真。这一思想源于神话传说。神话作为文学源头,它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即真解释。因之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态,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史家在发表自己的作品时,持着这一思想,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干宝作《搜神记》“以发明神鬼之不诬”。
(五)声律传文。中国古代的诗文先是自然的声律,到南朝,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的“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开始了自觉地以声律传播,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这种思想到唐宋诗词繁荣时,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创作,以及明代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等。
通过以上的概略描述和说明,我们可以大致见出以下几点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以及与新文学建构有关的带有一定规律的现象和理论质素:
首先,我们可从中发现音乐在古代文学传播中的价值。音乐作为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之一,曾在古代文学传播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先秦的“诗三百”、汉代的乐府至晚清的戏曲都是凭借音乐来完成其传播的。其次,格律修辞在文学传播中亦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到南北朝以后,格律修辞开始由自发转为自觉,当自觉讲求格律修辞形成思潮后,便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创作主体在文学传播中具有巨大作用。因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尚品格、尚社会政治地位,所以在文学传播中作家自身的品格和政治地位便在其作品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亦即文学作品传播的广度往往与作家政治地位成正比。复次,作品本身对文学传播也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作用。在文学传播中,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越高,其传播的范围就越广,传播的时间也就越久远。最后,文学批评和鉴赏对于文学传播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凭借着文学鉴赏和批评,许多文学作品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另外文学鉴赏所形成的类似文学沙龙一样的作家群,往往还能造成一个文学传播核心,从而形成放射性的传播。
收稿日期:2003-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