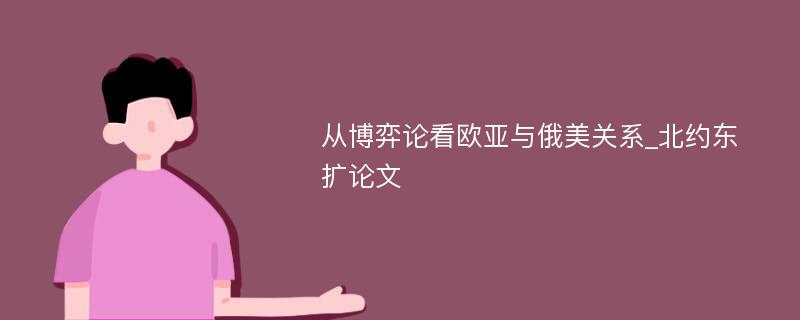
从博弈论视角看欧亚大陆与俄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大陆论文,视角论文,关系论文,博弈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欧亚大陆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心地位,西方政治学家们早已达成了共识。其中最著 名的当推英国的J.麦金德(1861~1947年)的“心脏地带”理论和美国的N.斯皮克曼(189 5~1943年)的“边缘地带”学说。J.麦金德的主要观点是:“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 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 界”(注: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ew York:Henry
Holtand Company,1942,p.62.)。斯皮克曼的主张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 ,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注:
N.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1944 ,p.43.)。尽管对于这些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国内外学术界看法不同,但从国际政治的 历史与现实来看,从近代的维也纳体系到现代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战后的雅尔 塔冷战体系,其始终、兴衰无不是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看, 影响人类历史面貌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恐 怖主义等各大思潮和运动均兴亡、盛衰于此。从文明、宗教形态来说,影响人类文化历 史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佛教、印度教和儒教均生于斯,发展 于斯,并争相扩大影响。从霸权国家的兴衰来论,近代以前的罗马、阿拉伯、拜占庭、 蒙古和奥斯曼土耳其诸帝国,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诸强国均是欧亚大陆 国家。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主要也是在欧亚大陆及其附属地带进行的。冷战时期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和主要舞台也是欧亚大陆。冷战结束以后,尽 管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惟一连接 全球四大洋的中心大陆,欧亚大陆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心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凸 现出来。作为一个非地缘意义上的欧亚国家和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地跨 欧亚两大洲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俄罗斯之间,围绕着欧亚大陆,特别是其心脏和“软肋 ”地带的主导权问题,必然有一番微妙而复杂的角逐和博弈,并对欧亚甚至全球的国际 政治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
博弈(game)原是运筹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运用到了国际政治和 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一般说来,其主要含义是:两个国际关系(政治)行为体为了博取 最大的利益,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博弈的形式多样而且 多变,既有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失为他方之所得,也有非零和博弈,即双方互有得失 的可能;一次性博弈和多次重复性博弈;合作性博弈,非合作性博弈。在特定的简单情 况下,围绕领土、资产、势力等资源发生零和博弈,但在大多数国际战略形势下,零和 博弈的概念完全不符合实际,国际关系本质上是非零和博弈,即“有限的敌对关系”(
limited adversary relationship)、“不确定的伙伴关系”。博弈者的行为往往取决 于博弈的结果及对方采取的对策、带来的信息等。冷战时期,苏美是全球两个主要的博 弈者。争斗的主要舞台是在欧亚大陆,争夺的主要对象也是欧亚大陆,特别是其周边地 带(如柏林、两个德国的边界、朝鲜半岛、中东和印度等)(注:关于冷战时期苏美在欧 亚大陆博弈的情况,详见白建才《苏美冷战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小 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 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战后随着东欧变成苏联 的势力范围,苏联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向欧洲中心地区推进。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看 ,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也一度与苏联结盟或准结盟。苏联的势力和影响波及 从南欧的亚德里亚海到冰天雪地的北冰洋,从北欧的波罗的海到东亚、东南亚的太平洋 ,从中欧的柏林墙到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横跨欧亚大陆的北半部和东半部,雄视 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令人生畏的超级大国。当时世界上任何 重大问题没有苏联的参与是不能解决的。美国急忙拼凑北约、美日同盟、东南亚国家条 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等,在欧亚大陆周边地带对苏联势力和影响(现实的或想象的) 进行围堵,遂有冷战时期柏林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和U—2飞机事 件的发生,以及在中东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从地缘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讲,应当说,这一 时期,苏联还是有所得的,处于比美国有利的、主动的地位,并单独成功地抗住了经济 技术上先进得多的西方世界多年(注:Разуваев Владимир Виталвевич:《Гео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Европы Росс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993г,с.50.)。苏美两大阵营决定世界的面貌。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特别重视,甚至不惜以武力进行威胁和干预,担忧、害怕其脱离自己的控制,有时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注:Дж.К.Гранвилл:《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ые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в Венгрии,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АФганистане—сравнителв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оцесса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я》,Москва,Всесоюзная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1993г.)。而美国在欧亚大陆西边的柏林危机和东边的朝鲜战争中均不能取胜,尤其是陷入了南边的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十分被动,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不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但苏联的优势后来逐渐变成了劣势。由于中苏交恶,特别是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 汗,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面貌出现不利于苏的重大变化。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国家,腹 部暴露过宽,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本是苏联之大忌。苏本应立足于防守,却自不量力, 贸然采取攻势,特别是阿富汗战争使苏联战线拉得过长,腹地拉得更宽,树敌太多,而 且东、西、南三面被困。苏力不胜任,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支撑不起其霸权主义的野 心。而美国利用阿富汗这个“陷阱”,趁机拆苏联的墙脚,在阿富汗牵制苏军,变被动 为主动。苏联的最终解体固然事必有因,且原因很多,阿富汗战争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 要的因素。苏军损兵折将近10万,劳民伤财,国内怨声载道,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四面 楚歌。如果说越南曾经是美国的“陷阱”,美国侥幸逃脱,那么,阿富汗就是苏联的“ 陷阱”,苏联却难逃此劫(注:В.Г.Андреев:《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ххв.》.Москва,《США и Канада》,1999No11;李兴:《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与苏联的兴亡》,载《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9年第6期。)。
冷战时期,苏美两霸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带,偶尔发生在亚欧大陆的 中心地带(阿富汗)和亚欧大陆之外(例如,拉美的古巴和南非的安哥拉)。两极、两大阵 营是当时国际关系体系的最主要的特征。其他亚欧大国,或为岛国(例如,英国和日本) ,或为海陆复合国家(例如,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它们此时均没有参与争夺欧亚 大陆主导权的实力和资格。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不再。
二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势力迅速地从欧洲中部地区后退,失去了波罗的 海三国、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俄疆界退向亚洲方向, 又回到了彼得大帝时期。由于国力和影响力的下降,俄势力从欧亚大陆中部的阿富汗、 东部的蒙古和朝鲜、南边的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收缩。俄直接面对一个广大而动荡的穆斯 林世界,地缘处境显著恶化了。但俄仍然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核大国、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其幅员世界第一,并超过了整个欧洲,其自然资源和人力潜力仍是巨大的。
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欧亚大陆实行三边(东、西、南)挤压、重在两翼(东 、西)、中间突破的政策。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非地缘意义上的欧亚大陆霸权国家和全球 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特别是欧亚大陆,因此,它力图掌握欧亚大陆 问题的主导权。美深知其主要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均是欧亚大陆国家。在欧亚大陆的西 部,美国通过与西欧保持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推动北约东扩和改革,操纵南联盟大选, 斡旋波黑战争和马其顿危机,使美国的影响和势力进入了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地区 。在亚欧大陆的东部,通过与日本缔结安全保障同盟加强军事合作,拉拢韩国,利用台 湾问题牵制我国,力图抓住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在南边,协调印巴争端和巴以冲突 ,制裁、空袭、军事打击伊拉克,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进行军事合作,制造中美飞机 相撞事件,帮助菲律宾政府“反恐”,利用南海问题对我施加压力。目前,美国在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驻军近百万,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欧亚大陆。2002年年初,美国防部向国 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列出了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7个国家。其中,俄罗斯 、伊拉克、伊朗、朝鲜、叙利亚和中国等6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苏美争夺的焦点往往是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带,那么,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政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及其“柔软的下腹部”——欧亚非三 大洲交汇地带。该地带包括东中欧地区(巴尔干和乌克兰),外高加索地区,中亚特别是 阿富汗,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东。这一地带呈一个巨大的横卧的S型,国小且多,边 界交错复杂,是各种民族、宗教、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各种矛盾和争端错综复杂,冷 战后更加尖锐。这一地带破碎落后,动荡不定,历史上也是沙皇俄国的领地或苏联的势 力范围,现在是俄罗斯的边陲,今日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势力之间的天然屏障和缓冲地带 。这一地带是美国的势力和影响难以抵达的“边远地带”,过去美国的军事势力从未能 进入这一地区。美国决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这样,在这一地带美俄之间势必有一 番博弈。冷战后,很多热点问题都发生在这一地带:北约东扩与反北约东扩,欧盟东扩 ,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马其顿危机,南联盟易名,车臣战争,里海石油和天然气开 发,打击塔利班的国际反恐战争,阿富汗的重建,伊拉克战争与重建,等等。在中亚地 区,北约、独联体、欧安会、上海合作组织都有影响,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印 度教和佛教都有一定势力。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利益与该地区密切相关 。
美国在这一中心地带实行西进(北约东扩)、东战(打击塔利班)、北挤(俄罗斯)、南威( 伊朗)的政策,软硬兼施,文(经援)武(武力)相济。对于穆斯林,美国根据自身利益或 挤压俄罗斯的需要,或支持,如在科索沃问题上支持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族,反对东正 教的塞尔维亚族;或反对、打击,如阿富汗的穆斯林政权塔利班;或者协调,如马其顿 危机,以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稳定;又根据与俄罗斯关系的变化,对车臣分裂势力或支持 ,或指责。对于独联体,美国力图削弱甚至挑拨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军事、文 化联系,特别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防止它们重新一体化,并增强自己对乌克兰的 影响(注:С.М.Самуйлов:《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НГ》,Москва,《США—ЗПИ》,1980No10;А.А.Лузан:《Украина и Россия:Факторы отэчуждения и сближения》,Москва,вестник МГУ,1998No5.)。借助于九一一事件,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了军事打击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军事势力进入了历史上它从未进入过的中亚地区,占据了这个亚欧大陆的制高点。目前,美在中亚阿富汗的9个邻国驻兵6万,设立了9个军事基地。独联体内的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巴基斯坦也抛弃塔利班,倒向美国一边。美军进了中亚不想走,除了获得一个军事落脚点,楔入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之间,使自己居于战略优势之考虑外,能源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为“谁能掌握中亚的能源出口,谁就能把握世界未来能源的方向和分配”(注:丁刚:《美军进了中亚不想走》,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14日。)。美先以反恐战争,接着以援助阿富汗重建为名,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一过去苏联曾经想占领但以失败而告终(1979~1989年)的战略要地。美军还进入格鲁吉亚,帮助格鲁吉亚培训反恐,两国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在俄格围绕反恐问题的矛盾中,美出于自身利益明显偏袒格鲁吉亚。美还企图借反恐之名肆意扩大军事行动,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国家。美国总统布什把亚欧大陆上的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称为“邪恶轴心国家”,动辄对它们进行军事威胁。美在中东欧、特别是中亚和高加索的军事行动企图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填补俄罗斯的势力真空,引起了俄的不安。在北约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3个原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基础上,美国再次启动了北约东扩的新一轮进程。2004年北约将东扩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原苏联集团成员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反对的立场不变,但冷眼静对,不再提危害俄“国家安全利益”。虽然地缘政治处境急剧恶化,特别是失去了乌克兰,切断了俄罗斯与欧洲联系的“大通道”和通往黑海的出海口(注:Збигнев Бжезинский:《Великая шахматная Доска》,Москва,МО,1998г,С.114~145.)。但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并不甘心自动退出欧亚大陆舞台。俄罗斯在历史上曾挡住了蒙古人的西征和土耳其人的北犯,又击败了法西斯德国的东进,在欧亚大陆上曾经书写过辉煌的历史。俄罗斯曾经是斯拉夫大家庭的家长,东正教世界的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同时,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大国心态的国家。独立以来,经过多年实践和痛苦的反思,俄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其外交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大西洋—欧洲主义到新欧亚主义、实用主义的演变过程,转而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既重视欧洲和大西洋,也重视亚洲和太平洋。俄强调自己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在各个层次上实行平衡外交: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东西、欧亚平衡。在东方,中国、日本、印度平衡,注重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西方,欧美平衡;在西欧,德、法、英平衡。俄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西边,反对北约东扩,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1999年俄特遣部队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在北约军队之前到达科索沃首府普里施蒂纳,造成既成事实,赢得主动地位,显示了俄军队一流的素质。俄甚至在2000年的军事学说中宣称以北约为主要对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这是对北约东扩的回应;顶住西方的压力,武力打击车臣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这是对北约东扩的警告。普京成功地解决了莫斯科人质事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作为独联体内的老大,俄认为自己在独联体有“特殊利益”,对独联体“维和”有“特殊责任”。俄致力于加强独联体范围内的经济和军事一体化,首先是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团结和联合。这三国占独联体国民生产总值的80%,人口有2亿。乌克兰放弃了独立后奉行的“一边倒”亲美外交,转而比较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形成令西方感到担忧的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实体(注:Ю.Годин,《Вступит ли Украина в славянский союз》,Москва,МЗМО,2001No4,С.101.)。在高加索地区,俄积极干预格鲁吉亚的事务,并扬言要进入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打击车臣恐怖分子,引起双边关系的紧张。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明显偏袒格鲁吉亚,提醒俄要尊重格鲁吉亚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俄态度强硬,并以武力相压,迫使格鲁吉亚作出让步,答应采取军事措施肃清潘基西峡谷的恐怖分子。俄还发展与阿塞拜疆的友好关系。在中亚地区,俄罗斯根据自身实力和亲疏远近,实行圈层外交,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关系和与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关系。俄在中亚有驻军,其军事力量重新出现在阿富汗,参与阿富汗的重建,并致力于加强和发展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抗衡美国对中亚的控制。在能源问题上,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拟议成立欧亚能源联盟,并与哈萨克斯坦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试图掌握里海地区能源开发的主动权。俄希望里海出口的石油经黑海北岸抵俄罗斯,而美国希望南下经巴基斯坦抵印度洋。在东南亚,美国继续加强与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的军事合作,极力要控制东盟的去向。俄则主动与东北亚的近邻日本、朝鲜、韩国和蒙古改善关系。在南亚,俄积极与印度发展军事、科技合作,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俄舰队开往印度洋与印度搞联合军事演习耐人寻味。2002年5月,俄美两国总统签署了《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俄罗斯—北约首脑会议正式签署《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文件。俄提出了外交新方针——“稳定的弧形战略”,即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来分别保卫俄罗斯的西(欧洲)、南(独联体)、东(亚洲)三面安全,在俄周边构成一个“稳定的弧形”。这是对俄地跨欧亚、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的继承,同时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俄对自身的重新定位,谋求与自身力量相称的国际地位。收缩力量,保卫周边安全,特别是亚欧大陆中心地带。俄是惟一的所有这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和伙伴,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和主动性。“稳定的弧形战略”貌似退缩,不再对抗,实则是养精蓄锐,卧薪尝胆,灵活务实,外圆内方,以退为进,并非“西倾”。
欧亚大陆“柔软的下腹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地带,包括中东地区(含地中海东 部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伊朗等)。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没有苏联时期那 样大的势力,但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伊拉克问题,俄罗斯团结法国、中国和德 国等欧亚大陆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主张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政治解决,反对美英动武,甚 至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并派军舰到海湾“观战”,搜集情报,表明俄罗斯的军事存在, 扩大俄罗斯的政治影响,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威胁如果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否 决美英提案,将要为此付出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价。但由于俄、法等国和国际社会 的斗争,美英知难而退,放弃了美英提案。当美英不顾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反对,绕过 联合国对伊发动军事打击以后,俄总统普京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美国必须停 止。俄拒绝美国提出的驱逐伊拉克外交官的要求,并通过伊朗对伊拉克难民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否认俄公司向伊拉克出售违禁武器,并说美方无根据的指责“会影响俄美关系 ”,强调俄罗斯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强调战后伊拉克重建要以联合国为主导。俄国防 部长还对美国侦察机频频出现在俄南部边境表示严重关切。俄还顶住美国的压力,发展 与伊朗的核合作,谋取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
三
在全球化时代,美俄之间在欧亚大陆上多为合作性的、多次重复性的非零和博弈,而 较少冷战时期的非合作性的、一次性的零和博弈。美俄之间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控,防止欧亚大陆上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维护巴尔干、中 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稳定,反对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经济的互补性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和共识。因此,它们在阿富汗战争、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能达成一致和妥协。俄借 助于美国之手除掉了它所不喜欢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与美国达成了削减战略性武器 的条约,与北约的关系从过去不平等的“19 + 1”机制到相对平等的20国机制,俄罗斯 容忍美军事势力在中亚的存在。但美俄之间仍然存在欧亚大陆主导权、势力范围和影响 力之争,美国的一超独大、单极独霸与俄罗斯不甘平庸的民族性格和大国心态之间存在 的分歧与矛盾是必然的。它们在伊拉克战争、中东(巴以)和谈、朝鲜核危机、伊朗核电 站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态度也颇不 同。在打击车臣分裂势力、维护俄联邦统一的问题上,在打击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恐怖 主义势力的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强硬的,在致力于独联体内部特别 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 上,俄罗斯的态度是积极的,并且得分。在北约问题上,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排队等 着加入北约”,“俄罗斯不会加入北约”。对于北约东扩,普京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 北约会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威望,但不会损害俄美关系。俄在无力阻止的情况下采取灵活 务实的默许态度。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博弈中俄罗斯处于守势。
美国作为一个非地缘意义上的欧亚国家,要维持世界霸主地位,建立所谓世界“新秩 序”,必然要争夺欧亚大陆的主导权。它的力量在于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和综合国 力的优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决定一切,但美有地缘劣势。俄罗斯把欧亚大陆看 作俄外交的主要环节,收缩力量于欧亚大陆,退出加勒比海、古巴和非洲。在力量不足 的情况下,甚至退出欧亚大陆南端——越南的金兰湾军事基地,而集中力量关注于自身 周边,即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软肋”地带。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其与周边的地缘、 军事、历史、文化的联系较密切。近几年来,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所以,从一定意义 上讲,俄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棋盘上的主要博弈对手之一。目前,总的态势是美强俄弱, 美攻俄守。博弈的焦点就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及其“软肋”——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地 。美国通过文(经济、外交、文化)武(军事打击)两手取得了某种优势地位。俄总体上处 于守势,但也不是不存在重振雄风的潜力和机会。
美国虽有“遏俄”、“弱俄”之心,但俄若失控,发生动乱,或俄过于软弱无能,不 能有效地控制其国内与周边,其危害性并不亚于其强大。所以,在博弈中美国也不得不 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
先欧后亚,先西后东,是美俄两国共同的传统。俄目前在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之 间寻求平衡,东西兼顾,欧亚并重。在经济上、技术上有求于西方,在政治上、外交上 借重于东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会完全接纳俄罗斯,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视俄为博弈 欧亚大陆主导权的主要对手。普京曾宣称俄也要加入北约,“稳定的弧形战略”也承认 了北约在欧洲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大概只是一种外交斗争的策略,实际上俄不 大可能完全融入西方。西方也不大可能完全接纳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加入北约,特别 是欧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东扩是不可避免的。中东欧肯定将“西行”。乌克兰将利用自己 处于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采取左右逢源、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 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中亚的局势将复杂化。北约、独联体、欧安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等 国际组织,以及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等宗教,将会在这一地区角逐。由于美国绕 开联合国,发动并取得了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还威胁要制裁叙利亚,俄、法、德、中 等欧亚大陆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持反对立场,中东局势可能更加复杂化。美国不会放弃在 欧亚大陆上对俄进行挤压,填补俄的势力真空,甚至利用车臣问题重新对俄施压,尽管 俄指责美是在搞双重标准。基于地缘和安全意义的考虑,俄罗斯与欧盟将会走向合作。 俄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美国与欧盟矛盾在增多,裂缝在 加大。而美俄之间将既合作又竞争。围绕亚欧大陆,特别是其中心和“软肋”部的主导 权和影响力问题,美俄之间进行博弈、明争暗斗,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会停止的。这 种博弈既有合作性的,一次性的,达成绝对效益和相对效益的双赢,也有非合作性的, 动态的,多次重复性的博弈,其绝对效益和相对效益充满了变数。虽然当前总的态势是 美强俄弱,美攻俄守,美国的优势和主动权更多一些,但不甘平庸的俄罗斯始终是欧亚 大陆上制衡美国霸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标签:北约东扩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合作博弈论文; 欧亚联盟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军事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