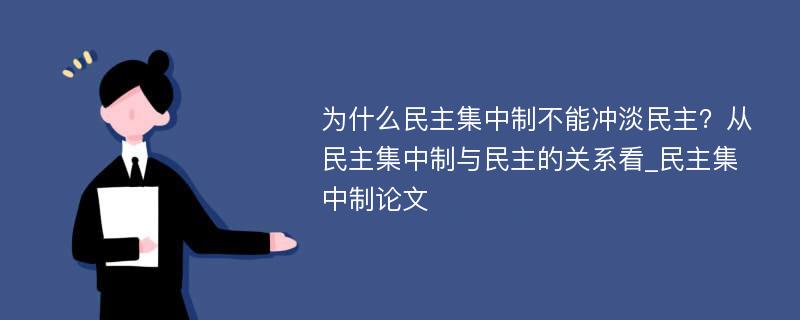
为何“不能以民主集中制冲淡民主”?——从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集中制论文,民主论文,开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和探讨民主集中制问题,往往大谈“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而始终不谈甚至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即使实际上涉及了,也在不经意间被“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所取代了。这样就把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歧途。其症结在于:“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着原则的区别。深入研究民主集中制而不探讨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侈谈什么“民主”与“集中”如何,这就必然陷入认识误区和陷阱而不能自拔。关于“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原则差别,笔者在《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一书中分三点作了分析论述,在此不赘述。不过有两点还是需要加以强调的。
1.在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糊涂观念或错误倾向。
一是把民主等同于民主集中制。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我国的国家民主时,往往要谈到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样两方面相结合。而又常常把与“专政”相对的“民主”视为就是“民主集中制”,似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以混同或者互换使用。甚至有不少人明确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之间可以划等号。如在一本大型文献资料书中有编者拟定这样一个标题:“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民主集中制”。这种说法和看法,可以概括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等同论”,用一个公式表示即:“民主=民主集中制”。
二是把民主看作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
很多人在谈论民主集中制时总是认定,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与“集中”这两者结合而成的,或者说,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的一半是“民主”,而另一半则是“集中”。这种看法和说法司空见惯,极其普遍,几乎在所有谈论民主集中制的文章和著作中随处可见。这可以概括为“部分组成论”,用一个公式表示即:“民主=1/2民主集中制”或“民主<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
三是把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完全对立起来。
这种倾向在国际共运中早已有所显露。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风云变幻而掀起的民主集中制“取消论”浪潮,把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对立起来的倾向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东和其他一些国家原先执政的以及非执政共产党纷纷宣布放弃、取消民主集中制。其基本“理由”不外乎是说:民主集中制与民主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而与官僚集中或专制的集中制倒是相同的或相通的;甚至它本身就是专制的集中制或官僚集中制;为了发展民主,避免“在官僚集中制的热牛奶中受熬煎”,就必须放弃、取消民主集中制。这种思潮或倾向可以概括为民主集中制的“取消论”或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对立论”。
这种国际思潮一度波及到我国。我国在强调发展民主的时候,有人误以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会削弱民主,影响发展民主,因而主张不再提民主集中制,用民主制取而代之。
2.不适当地抬高民主集中制,相应地贬低民主的倾向。
长期以来,在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不适当地抬高民主集中制,而相应地贬低民主。这种倾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其一,在以为民主只是手段的说法中,就逻辑地包含着“民主是为了集中”、“实行民主是为了更好地集中”。按照通常的理解,目的是高于手段的。这就不言而喻,使民主集中制的地位远远高于民主了。
其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处理人民内部各种非对抗性矛盾的“最高原则”。这里包含了用来处理经济、政治、组织、思想文化等无所不包的关系和矛盾。按此说法,似乎民主集中制成了可以包医百病的万能灵丹妙药。
其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时,有人对于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还嫌提得不够高,硬要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政治原则和政治范畴,把它与我国的“政体”混为一谈,甚至把它提高到“国体”的地位。
其四,有一个时期曾把对待民主集中制的态度问题提高到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六条政治标准”之一,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斗争的问题和分水岭,甚至当作是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之一。至今,把民主集中制问题视为关系党和国家性质和前途命运的观点仍相当流行。这些观点和说法,孤立地来看,似乎是在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颇有道理。但仔细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首先,这种对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的估价,言过其实;其次,更为严重的是,联系到对民主的态度,问题就显得更大、更突出了。相形之下,长期以来民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民主集中制低多少倍。这种不适当地抬高民主集中制而相应地贬低民主的倾向,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上有难以估量的危害。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特别提出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来加以研究和探讨,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区别
民主集中制只能成为民主性的组织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而不可能成为专制性组织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因此,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但二者毕竟有区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混为一谈。二者的区别,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集中制与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
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属于组织范畴。它在党的组织中,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国家政权机关中以及某些经济社会组织中,都是作为组织原则而出现的。这早已为有关的章程、条例所规定,几乎成了无须证明的“公理”,也大体得到了人们的共识。而民主则比民主集中制要复杂得多,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一点也是肯定无疑的,至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这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作为一种政党的基本制度,它是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组织范畴。列宁指出:“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6页)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对国家民主来说是这样,对党内民主来说也是这样。所谓党内民主,就是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根本制度。正如列宁所说:“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领导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决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列宁全集》第37卷第408页)这也是从政治上说的。
2.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由于它们性质的不同而必然带来适用范围的不同。总的来说,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在适用范围上要比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广泛得多。
首先,对于国家来说,民主既适用于“政体”,也适用于“国体”。这就是说,在“国体”意义上,就“谁统治谁”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多数人的政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是国家的主人,因而是民主的;同时在“政体”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国家,因而也是民主的。这表明,民主作为政治原则,既属于国体范畴,也属于政体范畴。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对于国家来说,却仅仅是实现民主政体的组织原则,只与“政体”有关,或者说,只适用于“政体”,而并不适用于国体,甚至根本与国体无关。有人硬把民主集中制与“阶级统治”、“谁统治谁的基本政治关系”相联系而扯到“国体”上去,这只能像列宁所批评的那样,“造成莫大的混乱”。(《列宁全集》第37卷第408页)
其次,在我国,民主作为政治原则,在党内、国家政治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群体团体中是普遍适用的。就是说,民主这一政治原则,完全适用于党和各种国家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无一例外。从领导体制来说,民主作为政治原则,既适用于委员制的领导体制或集体领导体制,也适用于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而民主集中制则与此不同。它作为组织原则,虽然笼统地说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有关各种组织,但由于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群体团体这些组织的领导体制有委员制(集体领导制)与一长制(首长负责制)之分,因而它在这些组织中就有不同的适用程度和适用范围。具体来说,不管何种组织,凡是在(也只有在)实行委员制、集体领导制的地方,都必须在组织上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凡是在实行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的地方,则不应该滥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是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行政首长或厂长(经理),要求他们在政治上遵循民主原则,发扬民主作风,是天经地义的;但要求他们在个人负责的体制范围内贯彻执行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行决策),却是根本不合情理的。在这里,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区别表现得最为突出。
3.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由于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适用范围,因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占有不同的地位。
民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一般地说,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要比民主原则、民主范畴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处于更高的层次和更高的地位。同样,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归根到底是由政治任务和政治原则决定的,并为政治任务和政治原则服务,正如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政治路线服务一样。因此,一般地说,民主这一政治原则要比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更根本、更具有基础性,处于更高层次和更高地位,而绝不是相反。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层次上,甚至把民主集中制置于远远高于民主的地位,那岂不是本末倒置、层次倒错吗?
三、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联系
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是民主的集中制,而不是专制的集中制,就表明民主集中制与民主有紧密的联系。那么,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概括地说,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和前提。任何组织,只有它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它在组织原则上才需要也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一个组织是非民主的或者说是专制的、独裁的,那它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决定的,受民主制约的。不仅民主集中制的是否实行取决于是否民主,而且民主集中制的实行程度和范围也取决于民主的实现程度和范围。比如说,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实行民主选举、集体决策,就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二,民主集中制能否在给定的“基本条件”下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环境和民主气氛如何。我们对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问题上(如选举、重大决策)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差不多都作了规定,这就是已经给定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但是,给定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并不等于民主集中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执行。它还需要有充分民主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如果缺乏这种环境和气氛,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无从谈起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往往执行得并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民主集中制的实施范围和严格程度将随着民主的扩大而扩大、发展而发展。前面两点着重从静态的、逻辑的角度说明民主对民主集中制的决定和制约关系。这里再从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范围和严格程度,必将随着民主的扩大而扩大、发展而发展。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那种把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对立起来,以为民主越发展、民主集中制就随之而削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在组织上的体现和根本保证。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联系和制约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就是说,不仅民主决定和制约民主集中制,而且反过来,民主集中制也制约和影响民主。这种制约和影响主要在于:民主集中制为民主服务,使政治民主在组织上得到体现和保证。没有民主集中制,民主就会失去组织保证而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与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二者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不能等同看待,也不能把民主视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或一个侧面,更不能对立起来。总的来说,民主要比民主集中制广泛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高得多,而不是相反。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也非常重要,主要也就在于它是民主这一政治原则在组织上的体现和保证。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与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正是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根本点上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对于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民主集中制是政治民主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上的体现和保证。
四、重大决策失误的深层根源:是违背民主集中制还是破坏民主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在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失误,其深层根源究竟是违背民主集中制还是破坏民主?这是一个与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的关系直接有关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1.一大误区:把重大决策失误归结为违反民主集中制。
重大决策的对错优劣及其执行情况如何,一般说来,至少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在认识上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合;二是在政治上是否实行民主;三是在组织上是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决策失误,无疑都是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认识论原则,在这一点上是无一例外的。然而,是否一定都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或民主原则)呢?那就不一定,而且情况比较复杂。
通常往往把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失误,包括像十年内乱那样的失误,归结为在组织原则上违背或破坏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归结为破坏民主。我以为,这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值得认真反思。只要仔细地不带任何偏见地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失误,其基本原因,除了决策者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背离之外,最根本的是在政治上破坏民主,而并不是在组织上违背民主集中制。这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前面所谈的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其次也涉及它们与认识论原则和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此姑且不论;再次是就组织原则来说,我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把重大决策失误归结为违背民主集中制,是难以说得通的。这可以从“文革”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2.十年内乱的症结:在政治上破坏民主。
我们知道,在十年内乱时期,有许多重大决策失误或错误决定、决议,也都是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经过表决而全体“一致”或基本“一致”通过的。如“九大”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十大”关于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决定;又如196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关于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等等,大都属于这种情况。拿“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来说,除了由于不够会议“法定人数”而拉入一些非中央委员的造反派凑数这一点违反组织原则而外,还是经过讨论和表决的,而且在讨论中没有反对意见,表决时除一位中央委员外,其他所有到会的中央委员都表示了赞成。于是,这项决定予以通过。对这种现象应当如何去分析呢?恐怕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归结为在组织原则上违背民主集中制。
对此,人们会说,绝大多数人对错误主张表示赞同,那是“违心的”。而问题的症结恰恰正在这里。那么,我们再往深追究,出现多数人“违心”现象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显然不在于没有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因为:一是在作决定时,既有“集体讨论”,又有表决,并经多数通过,这不能说违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二是执行决定时,各级组织和大多数人都在积极贯彻执行,不管“违心”也好,“真心”也罢,那时总的情况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就足以说明,不仅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得到了贯彻,而且“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等原则也发挥了其功能和作用,甚至严格得到了遵守。这怎么能说是违背或破坏民主集中制呢!实际上,造成普遍“违心”现象的深层根源正是在于:作为民主集中制之基础的政治民主惨遭破坏。那时,神化了的“一人之治”笼罩全党全国,在充满专制或“全面专政”的恐怖氛围中,有谁还敢、还愿真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志?一句话,正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民主或只有虚假的民主(如所谓“大民主”),才造成了普遍的几乎全党和全社会的“违心”现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如果主要领导人的主观认识违背客观实际,还要做出重大决策,那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四个服从”实施得越严格或执行得越“好”,情况会越糟,后果会越严重。因为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组织手段或工具,在为专制的政治和错误的认识的“服务”方面发挥了充分而重大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民主集中制在缺乏政治民主基础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一种最为可怕的扭曲形态或虚假形态。
由此可以看出,重大决策失误的原因,一般而论,除了违反认识论原则之外,既有违反民主原则的问题,也有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但这二者相比,违反和破坏民主原则是深层的决定性原因,属于“源”,而违反和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较为浅层的派生性原因,属于“流”。这种源流关系是不应当模糊和颠倒的。特殊而论,有些重大决策失误甚至会只违反民主原则,而并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总结重大失误的教训时,不应当停留在组织原则上,而必须深入到追究政治原则上。
3.苦口良药:“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
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无疑是合理的、科学的,并为我们党所反复强调。但在现实中往往执行得并不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内民主不充分,民主制度不健全,因而治本之道就在于实现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目标和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就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领导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民主制度相悖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逐步建立起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只有这个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