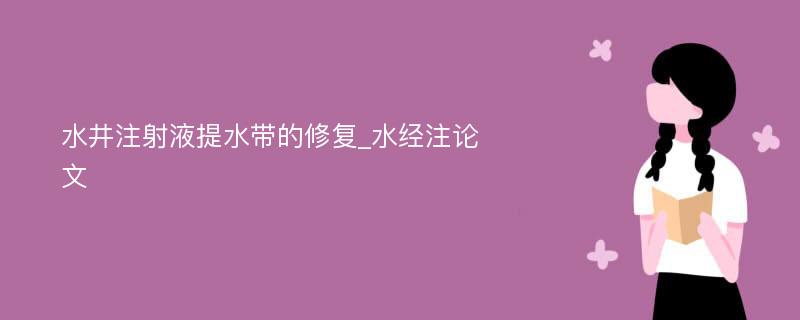
《水经注》举水条的复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经注论文,举水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郦道元创作《水经注》时,今鄂东举水流域是蛮族分布区。举水是《水经注》中叙述较详细的河流,今本《水经·江水注》(卷35)举水条云:“举水出龟头山,西北流,迳〔蒙〕龙戍南,梁定州治,蛮田超秀为刺史,举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阳,与弋阳淠水同发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东有南口戍,又南迳方山戍西,西流注于举水,又西南,迳梁司、豫二州东,蛮田鲁生为刺史,治湖陂城,亦谓之水城也。举水又西南,迳颜城南,又西南,迳齐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南迳白沙戍西,又东南,迳梁达城戍西,东南合举水,举水又东南,历赤亭下,谓之赤亭水,又分为二水,[右水](勤按:杨守敬因“分为二水”和下文有“左水”之文,补入“右水”二字,理由是充分的。)南流注于江,谓之举洲,南对举洲。《春秋左氏传》定公四年,吴楚阵于柏举,京相璠曰:‘汉东地矣。夏洰水,或作举,疑即此也。左水东南流,入于江,江浒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凤鸣口,江浦也,浦侧有凤鸣戍。’”文中提到的淠水,今称白露河,《水经·淠水注》(卷30淮水篇)云,淠水出弋阳县南垂山,又称白鹭河。今白露河与举水在河南省新县小界岭分水,南流的河道为今举水上源,即上引《水经注》之垂山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下简称谭图)第四册第36页也以今举水上源为古垂山水。这个定位是可靠的。
今举水上源既为古垂山水,则古举水上源不应在此。对确定古举水上源起关键作用的龟头山所在,舆志中有不同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76黄州府麻城县“龟峰山”条云:“县东六十里,山势嵯峨,上有黑白二龙井,即举水之源也。”又引《元和郡县图志》云:“县东南八十里有龟头山”[①]。谭图以今麻城市东南花桥河发源处的龟峰山(又名系马桩)为古龟头山,系马桩海拔1224米,为附近山地至大别山主脊一带的最高峰,在今麻城市东南约50里。《读史方舆纪要》云龟峰山在县东六十里,已使人难以断定此龟峰山是否即别名系马桩的龟峰山。而《读史方舆纪要》麻城县“蒙笼城”下云,“在县北”。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举水发源龟头山后,流经蒙笼城,这里就存在两种疑问。其一,如果《读史方舆纪要》之龟峰山即今系马桩,古举水只能以今花桥河当之,但此水的全部流程都在麻城的东南,不可能流过在县北的蒙笼城。《读史方舆纪要》何以出现自相矛盾?其二,如果《读史方舆纪要》所说县东六十里的龟峰山不是系马桩,又有哪座山足以当之?古举水上源又应是哪一条水?从《读史方舆纪要》的相关记载看,这第二个疑问无法得到答案。清《大清一统志》黄州府·山川“举水”条以今举水之东、花桥河北的阎家河当古举水上源,但是对于举水发源处的龟头山竟然只字未提。《读史方舆纪要》的模糊不明之处成了《大清一统志》的避而不谈之处,《大清一统志》对举水的定位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谭图以今系马桩当古龟头山,在距麻城的里数方位上同《读史方舆纪要》及《元和郡县图志》较接近,而发源于龟头山的花桥河确是西北流,同今本《水经注》的记载相合,因此谭图的定位较为可信。但是这样定位以后,与地图对照,举水的整个流程同今本《水经注》的记载只能部分相合,有数处不能通解,暴露出今本《水经注》举水之文的一些疑点。
第一,文中“举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其中因果关系的说明既没有必要,语意也不连贯,同《水经注》简练明晰的风格不合。
第二,谭图所定的古举水,今花桥河汇入阎家河后,西流与今举水、古垂山水相合,从地图看,古垂山水应是南流偏西与举水相合,这与今本《水经注》云垂山水西流入举水虽不能说绝对矛盾,但显然是一大疑点。
第三,按今本《水经注》之文,对照地图,举水与垂山水合后,应是西南流、转西北后南流,合麻溪河后西流与倒水合,其间西南流的河段很短,不足3公里。而今本《水经注》举水与垂山水合后,一直是西南流,所经有湖陂城、颜城、齐安郡,西南流的河段似颇不短。前面提到不足3公里的西南流的河段之间不可能容下三座城池,这个疑点相当地大。
第四,谭图以今浮桥河当古倒水,今浮桥河在中馆驿镇南偏西处西南流同举水相合,同今本《水经注》云倒水东南合举水不同。徐中舒、冯永轩认为倒水也就是西归水,因其流向向西,与水流东下的常规相反,故而得名[②]。如此说不误,今本《水经注》的倒水东南合举水却没有体现出西流、西倒的特点,而今浮桥河下流却是西南流入举水,以此水为倒水,倒是与西归、西倒名实相符。今本《水经注》的记叙是有疑问的。
第五,从图上看,举水与倒水会合后,有较长距离的西南流河段,远远超过举水与垂山水汇合后不足3公里的西南流河段的长度,然后才过赤亭,南流入江。而今本《水经注》于这段西南流的河道没有记载。既没有说倒水,也没有说举水西南流至赤亭。这个疑点恐怕只能以今本《水经注》的失误、错简来解释了。后文我们将看到,这个疑点同第三个疑点是相关的。
第六,今举水独流入江,而据今本《水经注》,则举水过赤亭后即分为二水,南流入江。杨守敬因举水“分为二水”之文,及下文又有左水,因而在“分为二水”之后,“南流注于江”之前,补入“右水”二字,并以今举水下游当左水,认为右水已湮塞。河流下游水道多变,这里虽然难以仅仅因为今举水独流入江,同今本《水经注》的下游分为二水不合,就断定今本《水经注》必误,但杨守敬认为右水已湮塞,仅仅是根据今本《水经注》有“分为二水”之文而做出的一个推论。赤亭当在今岐亭镇[③],仍在丘陵地区,距长江尚远,不能完全用下游河道的多变解释“右水”的湮塞,如果真有这样一条“右水”存在过,其湮塞多少应留下一些痕迹,在未找到其他证据之前,杨守敬的这个推论是值得怀疑的。
将谭图的定位和地图对照暴露出来的今本《水经注》举水条之文的疑点,说明今本《水经注》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讹误。石泉先生在论《水经注》史料的运用时说:“现存储版本《水经注》久已非本来面目,而是先已散乱残佚,后经唐宋以至明清的历代文人、学者多次进行了加工整理及订补之后,才成为今貌。这些‘订补’虽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但因其多据后世的地理观念,以致改得反而失真之处,也所在多有;而尤以梁陈之际经过大动乱,政区多有变易的荆楚地区有关地名方位为然。至今,内容紊乱费解以至明显错误未得订正之处,仍屡见不鲜,使人不能笼统凭信。此外,也还有些后世之人在原书正文之旁随手作注,被其他人辗转抄刻时,误窜入正文,遂致又增失误。加之郦道元是北方人,从未到过南方,亦常不免有隔阂、误解之处。……
但《水经注》又是一部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价值极高的地理名著。我们对它既要高度重视,却又不能不慎重鉴别,力求去伪存真之后,才敢放手引用,作为重要依据”[④]。据此,对今本《水经注》举水条记载中的疑点,也应考虑是否因后世学者的整理订补,反而造成今貌的失真。后世学者对《水经注》的整理一般是谨慎、认真的,因此即使出错,也有可能按照逻辑关系发现错误产生的原因,从而对被改动后失真的今貌进行复原。这要求对今本《水经注》的各个疑点进行系统、全面、相互参照地考察。
《说文》释“举”曰:“对举也。”通“与”。对举、相与,则应成双、成对。古举水实为发源于龟头山的两条水,龟头山犹如被两条水举起,两水故得举水之名。龟头山即今系马桩,举水发源于龟头山后,分为二水,右水即今花桥河,左水即今龟头河。后世对龟头山及古举水上源定位的分歧意见以及以今系马桩当龟头山暴露出的今本《水经注》记载的疑点,皆产生于后世学者对“举”的“对举”之义的忽视,将举水理解成发源于龟头山的一条水,并对《水经注》原文进行了整理。整理者可能为一人,或不同时期的多人,由整理过程的严谨看,似以一人的可能性为大,本文统称他或他们为整理者[⑤]。
2
复原工作按如下步骤进行:1.以发源于龟头山的左、右二水在今本中的相应文句,建立框架。举水出龟头山,分为二水。右水西北流,迳蒙龙戍南,梁定州治,蛮田超秀为刺史。……东南合举水。左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
举水分为二水,是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右)举水东南流后又注入举水,需作特别的说明。前文第一个疑点指出垂山水与右水的汇合,不需要作特别的说明,叙垂山水前后的“举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应是对右水合入左水的解释,但“举水”应作“左水”。今本“蛮田超秀为刺史”下的“举水又西流”一句同地图相合,原文中可能有此句,也可能没有此句。因为原文没有具体叙述垂山水如何与右水相合,这类情况在《水经注》一书中并不少见,多少有叙述不明之憾。整理者将“分为二水,右水”移至下游,对“左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这一句不理解,所以把它拆散,放在垂山水的前后,以补垂山水与右水汇合点的不明,并改“左水”为“举水”。在原文中,“蛮田超秀为刺史”后,以没有“举水又西流”一句的可能性为大。
2.在消去第一个疑点和第四个疑点中“东南合举水”一句的疑问后,可进一步把垂山水、倒水、赤亭水部分在今本中不易产生疑问的文句按实际流程的顺序插入前面的框架中。举水出龟头山,分为二水。右水西北流,迳蒙龙戍南,(举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出垂山之阳,与弋阳淠水同发一山,水之东有南口戍,又南迳方山戍西。……(?)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南迳白沙戍西,又东南,迳梁达城戍西,……东南合举水,左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举水又东南,历赤亭下,谓之赤亭水,南流……举水东南流,入于江,江浒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凤鸣口,江浦也,浦侧有凤鸣戍。在叙倒水之前,加入“举水又西流”,则更为通畅,但原文中不一定有此句。“东南合举水”是指在左水下游的汇合点,而不是倒水与举水的汇合点。由第二个疑点和第四个疑点以及河流的实际流程可以推知,今本的“西流入举水”,才是倒水与举水的汇合点。整理者将“东南合举水”作为倒水与举水的汇合点,“西流入举水”便被理解成垂山水与举水的汇合点,把本该在“迳梁达城戍西”之后、“东南合举水”之前的文句全部前移到垂山水后、倒水之前。把这段文句回移,则第二个疑点和第四个疑点便被消除,而且第三个疑点和第五个疑点亦同时消除。
赤亭之下的赤亭水应与今举水下游一样独流入江,举洲应在赤亭至长江的河段之中。整理者因为河流下游水道多变,把“分为二水”理解成赤亭水的情况,“右水”二字也被移至下游,并把举洲理解成举水入江处众多的江洲之一,所以在举洲之前补入了“注于江”三字。今本叙举洲之文不可通读,当是由于整理者对能说明举洲相对位置,很可能表明举洲不在长江中的原文不理解,因而删去了其中的关键词句。今本下文的“左水东南流”,原文应作“举水东南流”。因为按照实际的流程,发源于龟头山的左水与右水汇合处在赤亭水之上,整理者却将上文的“左水”改为“举水”,并将改动过的“左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拆散置于垂山水的首尾,下文的“举水”便改成了左水。原因仍在于整理者没有理解龟头山举水发源处的“分为二水”已包含了右水和左水,所以在看到已在今举水下游的左水与右水的汇合处提到了左水,以为左水是第一次出现,因而认定左水必在下游,与右水分流入江。
3.今本解释举洲的一段文句可能是后人注解,被羼入了正文之中[⑥],所以在复原中不录。举水条全文可复原如下:举水出龟头山,分为二水。右水西北流,迳蒙龙戍南,梁定州治,蛮田超秀为刺史,(举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阳,与弋阳淠水同发一山,水之东有南口戍,又南迳方山戍西。(举水又西流,)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迳白沙戍西,又东南迳梁达城戍西,西流注于举水。又西南迳梁司、豫二州东,蛮田鲁生为刺史,治湖陂城,亦谓之水城也。举水又西南迳颜城南,又西南迳齐安郡西,东南合举水。左水又西流,故是水合之。举水又南,东历赤亭下,又谓之赤亭水,又南流(注于江,勤按:三字应删,下举洲之文有脱误)谓之举洲,南对举洲。举水东南流、入于江,江浒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凤鸣口,江浦也,浦侧有凤鸣戍。
举水流域是北魏东豫州刺史、蛮族首领田益宗家族的领地或势力范围,《水经注》提到的梁朝蛮族刺史田超秀和田鲁生就是田益宗之子,因受到北魏的胁迫而投梁[⑦]。郦道元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曾任东荆州刺史,专门治蛮[⑧],对蛮地自然是非常清楚的,《水经注》中叙举水之文本可作为郦著的典范,却因后世学者的整理订补而变得面目全非,实可痛心。由此,本文也为石泉先生提出的今本《水经注》尤其是古荆楚地区的记载因后人整理订补反而失真找到了又一实例,对于泥信古书的人,又提出一个警示。
注释:
① 《元和郦县图志》卷27黄州“龟头山”条。
②③ 徐中舒:《巴蜀文化新论》,载《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冯永轩:《五水与五水蛮——两晋南北朝史札记一则》,载《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
④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⑤ 对“举”的“对举”之义的忽视,是同对门望的忽视相伴的。汉魏六朝时所谓的“举子”或“生子不举”同门望有关,个人的门望由父母双方的门望决定,整理者可能是门阀制度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宋代学者。
⑥ 此从石泉先生说。见《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第409页注69。
⑦ 《魏书·田益宗传》卷61。
⑧ 《魏书·酷吏传》卷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