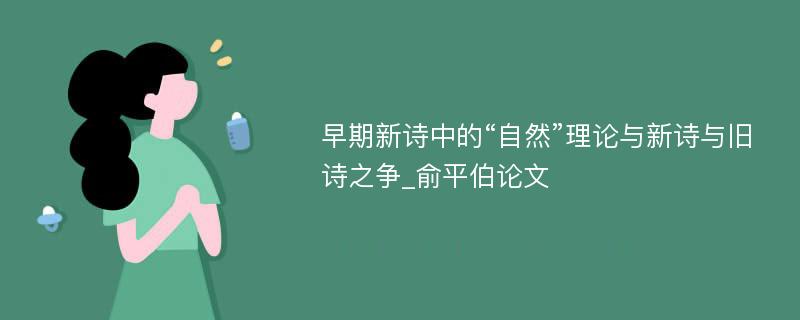
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诗论文,之争论文,诗中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早期新诗人对新诗的谈论中,“自然”之说相当盛行,或者说,此时“自然”论已成为人们对“新诗”的一个共识。这首先可以从新诗人的自我表述中看出。如郭沫若引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并将其阐释为“自然流露”,称“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然后郭沫若将这种“自然流露”的诗歌观念用于新诗上,认为“新体诗的生命”就在“自然”之说上①。在宗白华的诗歌意识里,新诗与“自然”也是紧紧关联的,“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②。此时,这种“新诗”与“自然”的话语共生的现象也体现在时人的谈论中。1920年,在吴芳吉的介绍下,郭沫若给陈建雷回了一封“谈诗”的信,在信中,郭沫若抄录了一首名为《春蚕》的诗,这首诗以春蚕“吐丝”作为“吐诗”这一创作过程的象征,并在诗中设置了一问一答:“蚕儿呀!/我且问你:/你可是出于有心?/你可是出于无意?/你可是出于造作矫揉?/你还是出于自然流泻?”“我想你的诗,/终怕出于无心,/终怕出于自然流泻;”在这首诗中,郭沫若强调了“自然流泻”这一新诗观念,在信中郭沫若还说“这首诗还不曾发表过,我只在日前钞示过吴芳吉君,我今更抄录给你,你可知我两人论诗的宗旨,大概是相同的了”③。这种在信札中谈论新诗并以“自然”论为同调的风气非常盛行。又如,在李思纯写给宗白华的信中,谈到对新诗人太玄、白情、沫若的评价,里面就有这样的观感:“太玄是深思的人,他的诗洗净了从前旧诗的精神面貌,他用细密的观察,自然的诗笔,去写出‘自然’与‘象征’的诗。”④可见“自然”成为批评新诗的一个重要标准。不仅如此,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与改动中,“自然”也是一个基本的尺度,如康白情收到田汉寄来的其夫人的诗稿,在发表时进行了改动,并在诗后附言说:“我为过爱这首诗,竟又把他改了好几处。改的不知道怎么样,但我总想他音节能够更谐和,体裁能够更散文,风格能够更自然,意思能够更深刻。”⑤这种状况被人描述为“文言薄皇古,白话喜自由。……滔滔天下是,名曰新潮流”⑥。在任叔永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今人倡新体的,动以‘自然’二字为护身符”⑦。
既然“自然”论在新诗诗学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对“自然”的阐释也成为与新旧诗之争相关的重要节点。正是在任叔永给胡适的信中,任叔永提出对“自然”的理解问题:“我以为自然的,人家不以为自然,又将奈何?……所以我说‘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个公共的理解。”⑧在这封信中,任叔永主要想就“自然”达成一个共识,所以提出要研究“自然”。此时对“自然”的阐释颇多,归纳有四:
一是以旧诗为自然。在任叔永致胡适的这封信中,任叔永还提出自己对“自然“和旧诗关系的理解:“古人留下来的诗体,竟可说是自然的代表,甚么缘故?因为古人作诗的时候,也是想发挥其自然的动念,断没有先作一个形式来束缚自己的。”⑨时人皆以“自然”为“新诗的代表”,任叔永以旧诗来争夺新诗的“自然的代表”的位置,这固然反映了支持旧诗者的某种策略或愿望,但也从反面说明了“自然”论的影响,就连支持旧诗者也不得不运用这一资源。针对这种说法,胡适在给任叔永的回信中作了回应:“四言诗(《三百篇》实多长短句,不全是四言)变为五言,又变为七言,三变为长短句的词,四变为长短句加衬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变为后一代的自然。我们现在作不限词牌、不限套数的长短句,也是承这自然的趋势。”⑩胡适先承认任叔永作出的这种“古人留下来的诗体”是“自然的代表”的前提,但是继而提出历史进化论的“自然”观,即“前一代的自然变为后一代的自然”,而且这种变化是“自然趋势”。
二是对“自然”的词义进行清理。在译介利渥(G.R.Elliot)的文章《新诗与新美国》时,吴宓称其文“实与吾心不期而契”,这篇文章批评的是美国的新诗,但吴宓在译介此文时,显然针对的是此时中国的新诗。当该文谈及“今之新诗人耽逐物象之自然”,吴宓即以“按”的形式对“自然”的英文意思作了解说:“译者按Nature一字,其义几经改变。自十九世纪之初迄今,则指花草木石无生之物及风云月露山水之形。与天及人相对而言,曰天理,曰人情,曰物象,故Naturalism宜译为物本主义或物象主义。近吾国人多译为自然主义,似不甚合。”(11)这种对“自然”概念的清理,无疑也是批评时人或新诗人对“自然”观念过于放大。
三是对“自然”的别种理解。如吴芳吉谈自然自由,正是反对文学革命,“文学则述作自由,断非身外之人得而干预强迫”。在一篇专门讨论“自然”的文章中,吴芳吉用诗歌与政治作比较,以政治比喻诗歌的“主义”:白话诗是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国粹守旧是复辟等。而吴芳吉所指的自然文学,则似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不相信要靠政治的:“自然的文学,是任人自家去做的,是承认人类有绝对之自由的。是不装腔作势,定要立个门面的。是以个人为文学上单位的,是打破那些蔑视别人的人格,只顾其私党之声势的。”(12)
四是以诗行行列整齐为自然。在胡适对自然的理解中,由旧诗向新诗的进化,诗行行列由整齐变为不整齐,这种文法的变化赋予了新诗“自然”的可能和品质,所以他的“自然”之说中更注重于新诗的外形——“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但在胡怀琛看来,所谓“自然”是一种阅读效果:“新诗当然没有固定的形式,然而无论长到若何地步,总要读起来觉得很自然,再也不能减一字;无论短到若何地步,读起来觉得很自然,再也不能加一字:这样才能算完全好。”胡怀琛依据这种对“自然”的理解,认为诗行整齐也是“自然”,“且既成为整齐之式,又极自然而非勉强”、“然用白话只管用白话,何必使之不整齐”、“在形式上的解放,是应该的;不过也要略有范围”(13)。吴宓则以诗与文的不同源头为论证基础,反驳胡适从语言上入手谈诗歌的问题,认为“整齐纪律为人类之天性”,“皆中国韵语自然之趋向”,因此,“诗歌句法整齐反较不整齐为自然也”(14)。
二
在这种情形下,“写”与“做”成为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话题,它不仅是某种写作立场的表达,还关涉到对诗与新诗的理解方式。这一话题是从郭沫若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延伸出的。1920年1月3日,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15)。“做诗”本来只是一个沿袭使用的创作诗歌的习惯用语,但这番话引起了郭沫若诗不是“做”而是“写”出来的意见:
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16)
郭沫若谈到自己的写作方式是“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的罢了”。他为这种写作方式所找到的依据是:首先,他认为“自然流露”为“上乘”;其次,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作了引申,认为它不仅仅是“忠于描写”,而且是“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诗的生存,如像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所以,郭沫若把“写”和“做”作了定义:“写”是“自然流露”,而“做”是“矫揉造作”。这样一来,郭沫若就将“做”这种普通用语变成了有特定含义的写作,并为它制造了一个对立面——“写”。这种基于“自然”论之上的“写与做”的论断,在这一时期的新诗中是相当流行的,时人不仅把“写”当作新体诗的特点,如郭沫若所说“新体诗的生命就在这里”,而且在评论和介绍新诗中常用这一标准来做价值判断。比如王任叔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一篇介绍徐玉诺的新体诗的文章后,郑振铎有一个附言:“玉诺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他写诗时决不能停留一刻去做修饰字句的工夫。如果一注意到字面的斟酌,便不能做下去了。所以他的诗里常常写了许多别字,这种诗才是真的能感人的诗!才真是赤裸裸的由真的感情中流注出来的声音。我们一班朋友常说的现在的诗人,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是有真性情的诗人。”(17)由于写作方式是“写”,导致“决不能停留一刻去做修饰字句的工夫”,还“常常写了许多别字”,对于“写”这种写作行为的极端强调和诗歌评价(“感人”)、诗人评价(“现代的是有真性情的诗人”)之间建立的关联,其根据正在于对诗和新诗“自然”的风格特征的认定,就像王平陵在《读了〈论散文诗〉之后》所下的断言:“以实质论: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18)
对于“写”与“做”两种写作方式的对立,是基于新诗“自然论”的理由。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虽然断言“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但是他在“写”与“做”之间又提出一种“整理”的方式:“新诗本不尚音,但整理一两个音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就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诗本不尚韵,但整理一两个韵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又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诗本不尚平仄清浊,但整理一两个平仄清浊就可以增自然的美,也不妨整理整理他。”(19)从“整理”这种方式的提出来看,可见康白情的新诗立场和郭沫若相比,有了一个微小的变化:“写”与“做”虽然还是对立的,但不再是两种绝对不可沟通的写作方式,且有了某种中介——“整理”,康白情继续运用“自然”之说赋予“整理”以“合法性”。
吴芳吉对于“写”与“做”的关系不同于新诗潮流中诸多诗人,在新旧诗之争中,他对由胡适倡文学革命而起的新诗持批评立场,并以其为“外国之法”的模仿,因此他认为“以为西洋诗体,是随便写出的,不是做出的。这句话,也是半面的道理”,其理由在于:首先,他认为诗本来是做的,因为“人的感情不发则已,要发为诗,就不免有故意做作之嫌”;其次,“要得新诗进步,恐怕还是要做”(20)。吴芳吉以绘画打比方,认为新诗“自然”的模样实际上是需要“做诗”的“工夫”的。
宗白华在《新诗略谈》(21)中回应了郭沫若的说法。他首先承认郭沫若在“写”与“真诗好诗”之间建立的关联,在这一前提之下,提出了“做”的可能——“不过我想我们要达到‘能写出’的境地,也还要经过‘能做出’的境地。因诗是一种艺术,总不能完全没有艺术的学习和训练的。”宗白华把“做”当作“写”之前的准备工作或潜在阶段。这种阐释一方面维护或受制于“写”这种写作方式的绝对优先性(亦可见此时此种观念影响之强大),又用另一种方式曲折提出了“做”的必要性。
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湖畔诗人的通信也讨论了这一话题,并得出和宗白华相近的结论,不过在“写”之优先性之下,更强调“做”的功用。在应修人1922年9月7日给潘漠华、冯雪峰的信中(22),继续谈到“写”与“做”的关系。应修人首先承认“写”之于诗的优先,“‘诗’要来时,只能写出”,但是“要写得一丝不走,美妙动人,这只须赖乎素来的‘学’”,而“诗人底修养,艺术化的化,和找材料的找,皆可说是做字的功夫”,因此,应修人也承认“这样的‘做’尽足为‘写’的源,而万不可轻视的”。
在《〈女神〉之地方色彩》(23)中,闻一多批评了郭沫若关于“写”与“做”的观念,认为“郭君这种过于欧化的毛病也许就是太不‘做’诗底结果”。随后,闻一多提出“选择”这一方式,将“选择”当作“创造艺术底程序中最紧要底一层手续”。闻一多之所以如此判断,乃是因为他对新诗提出了“自然”之外的另一标准——“美”。闻一多说“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闻一多先提出不同于(或高于)“自然”标准的新诗标准,然后从这一“美”的标准出发,推出“选择”的必要性,从而以“选择(做)-美”否定“不做(写)-自然”。这一动向亦反映了新诗发生后获得其合法性的重点由其对社会语境的诉求(“白话”)向诗的艺术(“诗”)的变化。这一点在俞平伯对“写与做”的重新阐释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写”与“做”的问题上,俞平伯的态度饶有趣味,他于1920年11月5日写的一篇文章《做诗的一点经验》,标题上就用了“做”诗而非“写”诗,而且俞平伯对“写”与“做”的内涵作了重新阐释。对于“做”,他引用了周作人翻译的《点滴》一书中授罗古勃的话来表达与“做”相近的意思:
授罗古勃solsgnt说:“情动于中,吾遂以诗表之,吾于诗中,已尽言当时所欲言;且复勉求适切之辞,俾与吾之情绪相调合。”(见《点滴》上卷117页)这真是诗人底自白。即修词底作用,亦无非想真实详细表出他自己的情绪。(24)
在这段话中,俞平伯把“做”当作“与吾之情绪相调合”、“勉求适切之辞”的“勉求”过程和“想真实详细表出他自己的情绪”的“修辞底作用”,这种对“做”的阐释实际上不同于郭沫若等人把“做”理解成“矫揉造作”、“做作”,而包含了康白情所说的“写”与“整理”两个过程的整个的诗歌写作过程。在这篇文章里,俞平伯还致力于破除“写”即“自然”的新诗神话:
盛兴来了,我们不得不写下来;若不来呢,虽要写也写不出,即写出来的也不是诗。随盛兴来的诗,未必定是好的,却还不失诗底精神。听他底自然来去,不加一些人为的做作,已是我深信的一条最有效的做诗方法。(25)
“写”不再是惟一有效的通往“自然”的写作方式,诗歌的创作被统称为“做诗”,在俞平伯的观念中,用“写”与“做”来区分好诗和坏诗、新诗和旧诗的问题变成了用“盛兴”、“兴会”来区分诗和非诗的问题。问题已然变化,那么“写”与“做”的关系不再被看作“自然”与“不自然”的关系,反而在“自然”论的基础上达成了统一。
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俞平伯的这种观念表达得更为明确:
写诗和做诗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如把“写”解作“直写”,“做”解为“做作”,那总是很有弊的。……但如把“写”解作“神来之笔”,把“做”讲作“精心结撰”,那自然不可菲薄了。
写和做本无优劣可言,只是一首诗“值得写做”“怎样写做”的问题。
真的创作,实是具备这两种方法,是一半儿做,一半儿写的,草率粗直的不是诗,装腔作态的也不是诗。写是适合诗底机;做是充实诗底力。若换上两个名词,一个是天分,一个是工夫。(26)
“写”与“做”不是对立的,而是两种并列的有效的写作方式和一个写作过程的两个阶段。“自然”不“自然”的问题不再取决于诗歌写作是“写”还是“做”,恰恰相反,“真的创作”是“写”与“做”都兼备的。因此,俞平伯提出,“写”与“做”都是“自然”的:
诗底写和做是内心的自然而然的两条出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这就是无方便的诗中的方便。(27)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俞平伯在《做诗的一点经验》的开头就申明“一点重要的观念”“就是好诗没有是‘天籁’的”,认为对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天籁”的“旧信条”“有重新解释的必要”,“要严密的解释”。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其实就是“自然”之意的通俗表达,俞平伯将之“重新解释”“严密解释”,也就是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对“写”这种写作方式的绝对强调加入对“做”这种写作方式的强调,强调真实、自然的好诗的写作方式是“写”和“做”统一的。
那么,为何俞平伯要将“写”和“做”统一起来呢?从俞平伯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稍窥端倪,在1919年写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俞平伯提出“使新诗的基础坚固”,“使新诗的主义和艺术都有长足完美的进步,然后才能够替代古诗占据文学上重要的位置”。然而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呢?俞平伯拿出的方案是“以后我们做诗,要增加他的重量,不要增加他的数量”,“增加”新诗“重量”的途径是“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28)。在新诗成立之时,由于要和旧诗划清界限,胡适、钱玄同等人都强调新诗区别于旧诗的“白话”特征,因而更强调表达过程的通畅性,所以把“写”这种写作方式视为不言自明的通往“自然”的写作方式,把“做”认为是不“自然”的写作方式。而当新诗成立数年后,新诗的问题由“白话”转移到“诗”之上,因而问题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诗本身的艺术性上,在这一背景下,“写”与“做”被重新阐释,“写”与“做”的对立关系也转变成了并列和统一关系,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成为“自然”论的一部分。
三
新诗的“自然”之说广为流布,并与“旧诗”的“格律”形成对立,在时人看来,新诗与旧诗的对立往往就是“自然”与“格律”的对立,在很多场合,甚至被误解或简化成“有韵”和“无韵”的对立,由此生发出自然与格律的关系、新诗是否是诗之类的话题。
1922年4月,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当讲到“文体”时,他给诗和文作了一个区分:“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并依据这一标准对此时流行的白话诗作了一番评论: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关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29)
章太炎以“韵”为标准,认为白话诗不是诗。这一番关于白话诗的议论也引起了议论,于是有一位听讲座并记笔记的青年曹聚仁写信和他讨论白话诗,在这封信中,曹聚仁对章太炎的观点质疑道:
先生树诗与文之界曰:无韵谓之文,有韵谓之诗。聚仁窃以为诗与文之分以有韵无韵为准,恐非平允之论。韵者诗之表,犹妇人之衣裙也。以妇人之衣裙加于妇人之身,曰是妇人也,诚妇人也;若以妇人之衣裙加于男者之身,而亦必谓之为妇人,宁有斯理乎?……
先生摈语体诗于诗之外,以其无韵也,而不知语体诗之为诗,依乎自然之音节,其为韵也,纯任自然,不拘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30)
在这段文字中,曹聚仁首先反对章太炎以“韵”来区分诗与文的前提,然后提出白话诗(“语体诗”)是有韵的,这种韵是“纯任自然,不拘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其意为即使按照章太炎的标准,白话诗也是诗。针对这种辩解,章太炎回答说:
诗之有韵,古今无所变。……夫文辞之体甚多,而形式各异,非求之形式,则彼此无以为辨。形式已定,乃问精神耳。非能脱然于形式外也。仆所谓形式者,亦只以有韵无韵为界。……诗乃人造之物,正以有韵得名,不可相喻。……以广义言,凡有韵者,皆诗之流。……只以诗本旧名,当用旧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别造新名。……苟取欧笑偶有之事为例,此亦欧美人之纰漏耳。何足法焉!(31)
章太炎并未回答白话诗是否有韵这一问题,而是坚持以“韵”为标准来划分诗与文,并认为白话诗应当“别造新名”,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并不承认白话诗是“诗”。
对于以韵来划分诗和非诗,并据此来认定新诗或白话诗非诗的看法,新诗人的态度不一,不过其反应大致有三:一是认为不应以“韵”来划分诗与非诗。譬如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中,郭沫若对流行的“无韵者为文,有韵者为诗”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最近国人论诗,犹有兢兢于有韵无韵之争而诋散文诗之名为无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之外,不知诗之本质,决不在乎韵脚之有无”,“诗可以有韵,而诗不必定有韵”(32)。二是认为新诗是有韵的,如曹聚仁在和章太炎论白话诗的信中所持的观点。三是认为新诗即使无韵不是诗也不要紧,如周作人在《过去的生命》的序中所言:“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33)
与以“有韵无韵”为标准来争论新诗是否是诗相比,关于“自然”与“格律”的阐述要复杂得多,换言之,“有韵”“无韵”的问题或者可以说只是个简化的立场问题,而“自然”“格律”的问题则不仅关乎立场,更展现了时人对于围绕新诗与旧诗之间诸多方面的问题的探讨和设计。
对新诗人来说,崇尚自然、反对格律自是当然,“新诗在诗里,既所以图形式底解放,那么旧诗里所有的陈腐规矩,都不妨一律打破。最戕贼人性的是格律,那么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格律”(34)。康白情的这种声音在新诗人中颇多同调者,俞平伯就有类似的表达:“一切桎梏无论在哪方面都打开,让个性自己去。”(35)从新诗的“自然”论出发,构建“新诗”与“旧诗”之间“自然”与“格律”的对立,是此时新诗人的惯常表达。这种对立不仅是诗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正如他们所说,格律和自然的对立实际上是“桎梏”和“解放”、“人性”和“个性”的对立,其根据在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
对新诗的反对者和怀疑者来说,亦将新诗与旧诗的关系指认为自然与格律的关系。邵祖平在《无尽藏斋诗话》中谈到新诗时描述说“近日新派为诗者多持无定韵无定言无定体之说甚者不知其所谓韵句及体制也”(36),在《学衡》的“文坛消息”栏中,吴宓介绍“英国现任桂冠诗人Robert Bridge氏所撰自由诗论”,谈及“今人所作大都意不顺句不洁音不谐之散文而已噫噫”,并针对中国的新诗提出“吾国人之学作自由诗者更可已矣”(37)。
与这种看法相应的是诗应该有无“格律”,或者说,新诗既然没有“格律”,那还是否成其为诗?
先来看看当时两种对“诗”的定义:
1.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有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Poetry is the intense and elev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n metrical language)。(38)
2.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像的意境,音节地戏剧地写出来,这种作品就叫做诗。(39)
定义1是由吴宓作出的,定义2由康白情作出,如果单看两个定义,确有相似之处,但其指向却不同。如吴宓的定义是先为“笔法”后为内容,康白情的定义是先规定内容再规定写法,在强调的重点上有前有后、有轻有重,而且在用词上,吴宓用的是“音律”,强调的是格律,康白情用的是“音节”,并未涉及格律。根据定义1,如果不具备“音律”,那么就不是诗。根据定义2,即使没有“音律”,但只要有“音节”,也能称之为诗。既然围绕着新诗的各方都公认新诗或白话诗是没有格律的,那么新诗或白话诗能否称之为诗呢?在相似的字面里其实含有相当分歧的冲突,这一矛盾的焦点就在“格律”上,所指向的是新诗作为诗这一文类的“合法性”问题。
一种观点是认为新诗不是诗。吴宓在一篇译介文章《葛兰坚论新》(40)中,依然用“按”的方式来直接批评中国新诗,吴宓先举出欧洲诗中的“Rhythm”和“Metre”,并下定义“凡相间相重者皆为Rhythm”、“相间相重皆依定规每段全相同者始为Metre”。根据这一定义,吴宓指出“Metre者所以区别诗文者也。自由诗仅有Rhythm而无Metre,故自由诗不得为诗”。这是介绍欧洲的情形(欧洲的自由诗不是诗)。然后吴宓回到中国诗歌,“吾国诗句由平声字仄声字相重相间而成者也。且依定规而每段相同者,故吾国之诗不惟具有Rhythm,且具有Metre,即平仄是也。吾国之文亦仅有Rhythm而无Metre,故平仄之有无实吾国之文与诗之别。无定平仄者不得为诗,故今之新诗实不得为诗”。吴宓根据以“Metre”区分诗文的办法,认为这是“世界古今诗之公性诗之通例”,并将“Metre”翻译或阐释成“平仄”,于是“平仄”成了区分中国诗文的标准。由于没有“平仄”这样的格律,所以吴宓得出结论“故今之新诗实不得为诗”。在另一篇介绍《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41)的文章中,吴宓继续“按”说:“今世诗人诺伊斯Alfred Noyes著《近世诗论》(Some Aspects of Modern Poetry,一九二四年出版)一书谓诗以声音之美为主。而声音之美必寄托于韵律。今世之诗学革命家破除韵律,侈言天才,于是声音之美全无,而所作者直不成为诗矣。”前文是引述欧洲划分诗文的标准,后者则引用欧洲诗人的诗论,从诗歌美学或文本效果入手,来论证新诗不是诗。
一种观点是认为新诗属于定义或范围扩大后的诗的范畴。李思纯在一封给友人的信(42)中就认为“吾国旧诗之所以有平仄音律五七言盖本于汉字之特质”,而新诗是“在单音独体之汉字下而强用之以造作拼音文字之诗”,所以“去常识已远”。这种看法和吴宓相似,认为新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但是接着他用了章太炎的一个比喻,“章太炎先生曰:日本佛教徒之奉真宗者食肉娶妻而自称和尚,犹今之为新诗者废音律规则而自称为诗”。章太炎在打这个比方时实际上是语含讽刺之意,并认为白话诗没有格律其实不是诗,要求白话诗另造新名。但李思纯在继续运用这个比喻时,将其意有所延伸,认为将新诗认为是诗,是“欲扩大和尚二字之意”。李思纯虽然认为新诗不是诗,但看出新诗成为诗的可能性是扩大诗的范围。
一种观点是从诗的功用和来源入手,论证有“自然”而无“格律”的新诗可以是诗。在李璜的文章《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43)中,首先说明“诗的功用,最要是引动人的情感。这引动人的情感的能力……都与诗的格律没有多大关系,——有时或全无关系”,然后从“中国最古的诗如诗经”“法国最早行世的诗如史歌”“都是不限于格律或全无格律的”这种诗歌史现象,得出结论——“可见先有诗然后有格律,格律是为诗而创设,诗不是因格律而发生。照诗的历史看来,是从自由渐渐走入格律的范围,近世纪又从范围里解放出来”。既然“自由”与“格律”与诗本身无关,只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新诗没有“格律”当然是诗,并且还符合“自由-格律-自由”的诗歌发展趋势。
对于新诗的“自然”与“格律”问题,郁达夫、郭沫若的阐释要复杂一些。他们首先将新诗与“韵律”而非格律相联,如郁达夫提出新诗是有“韵律”的,“韵律系人类的情绪自然所有的活动的形式”;然后将韵律进行分类,郁达夫认为“诗的韵律,大抵可分抑扬、音数、押韵的三种”,接着继续推论:“假如韵律的原则,不仅仅是几个规律可以包括得了,那么我们又哪里能够断定说‘自由诗’是不合乎韵律的原则的呢?”(44)通过这种层层深入,郁达夫指出“韵律”是“自然”的,而且不能根据新诗没有韵律中的一种而断定新诗没有“韵律”。郭沫若将“韵律”分为两种: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或曰无形律)与外在的韵律(Extraneous Rhythm,或曰有形律)。内在的韵律指“情绪的自然消涨”,外在的韵律指“甚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郭沫若提出“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45)。在此,“外在的韵律”的涵义与“格律”相近。通过这种分类和重新阐释,诗这一文类和“自然”相联系,而不再与“格律”必然相关。在这一阐释下,新诗具备了作为诗的天然“合法性”。郭沫若在这一分类基础上更认为“外在律底成分太多了”则是歌不是诗,因为“大抵歌之成分外在律多而内在律少。诗是纯粹的内在律底表示”(46)。这一说法也就是指陈“格律”反而不具有成为“诗”的“合法性”。
在早期新诗关于“自然”与“格律”的讨论中,各方所争论的中心为——“格律”还是“自然”是诗的必然要素,但所意指却在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一焦点上。大体上说,反对新诗者都以新诗没有“格律”否认新诗是诗;支持新诗者对诗和格律的关系作了重新阐释,认为诗与格律并不必然相关或自然是诗的必然要素;也有人将诗的范畴扩大,而将新诗纳入其内。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其论证所运用资源大体相似(比如诗歌的效用和欧洲诗歌发展的范例),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②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③郭沫若:《论诗》,《新的小说》第2卷第1期,1920年。
④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
⑤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
⑥熊家璧:《寄潭秋世兄》,《学衡》第20期,1923年。
⑦⑧⑨⑩胡适:《胡适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第12页。
(11)载《学衡》第6期,1922年。
(12)吴芳吉:《提倡诗的自然文学》,《新群》第1卷第4号,1920年。
(13)胡怀琛:《诗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16日。
(14)吴宓:《诗学总论》,《学衡》第9期,1922年。
(15)(16)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第7、11页。
(17)王任叔:《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
(18)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5期,1922年。
(19)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
(20)吴芳吉:《提倡诗的自然文学》,载《新群》第1卷第4号,1920年。
(21)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
(22)王训昭选编:《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0页。
(23)载《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24)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
(25)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
(26)(27)俞平伯:《诗底方便》,《民国日报·学灯》1924年3月28日。
(28)载《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
(29)(30)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75-76页。
(31)章炳麟:《答曹聚仁论白话诗》,原载《华国月刊》第1卷第4期,1923年。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72页。
(32)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6年。
(33)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1页。
(34)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
(35)俞平伯:《诗底自由和普遍》,《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
(36)(37)载《学衡》第14期,1923年。
(38)吴宓:《诗学总论》,《学衡》第9期,1922年。
(39)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
(40)葛兰坚著:《葛兰坚论新》,吴宓、陈训慈合译,《学衡》第6期,1922年。
(41)载《学衡》第63期,1928年。
(42)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节录)》,《学衡》第19期,1923年。
(43)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
(44)郁达夫:《诗论》,《达夫全集》第5卷,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187页。
(45)(46)郭沫若:《给李石岑的信》,胡怀琛编:《诗学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再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