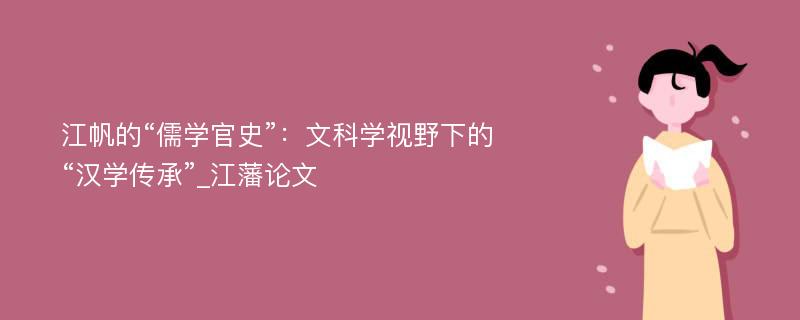
江藩的“儒林正史”——傳記文學視野下的《漢學師承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论文,正史论文,漢學師承記论文,傳記文學視野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國朝漢學師承記》,江藩纂,嘉慶二十三年(1818)初刻于廣州,是瞭解清代學術史的必讀書,然而歷來不乏批評者。“門戶之見”被公認爲該書最大的缺點。不過,由于所持立場不同,批評者對“門戶”的界定亦有區別:方東樹所謂的“門戶”是漢宋門戶,故而批評江藩“挾以門戶私見”(《漢學商兌》),宗漢學而詆宋學;謝章鋌則强調江藩的“偏見私情”,其在著録人物時,會優先考慮和他有“交游聲氣之情”的學者(《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支偉成持經學史家眼光,認爲是書“堅守壁壘,擯絶今文,是未免失之隘矣”(《清代朴學大師列傳·凡例》)。“門戶”,其實就是主觀性。批評者認爲,江藩在撰述時的主觀色彩過于强烈,以致《漢學師承記》未能成爲一部客觀的、全面的清代學術史。
欲應對以上批評,首先需要確定《漢學師承記》的文體屬性。也就是說,江藩是否在自覺地撰述一部嚴格的學術史?不妨從阮元和汪喜孫爲此書撰寫的序跋談起。阮《序》認爲,此書的目的在于明“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而汪《跋》在“匯論經生授受之恉”之外,還强調了江藩“通知作者之意”。綜合二人看法,《漢學師承記》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綜述清代漢學家各自的學術觀點,二是展示他們之間的師法傳承。由此看來,《漢學師承記》似乎的確如周予同所說,“是學術史的性質”(《清朝漢學師承記·序言》),那麽自然不應該具有過多的主觀色彩。
然而,江藩的《自序》却讓我們對這一判斷産生懷疑。《自序》的主體部份與阮《序》、汪《跋》對此書的定位並無出入:首先追溯三代以來的學術變遷,然後詳述漢學在清代的昌明,最後明示編纂體例與目的:“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采擇。”“備國史之采擇”,明顯是一部嚴格的學術史的定位。問題在于,緊接此句之後,江藩却添加了一段“多餘”的感慨:
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魏晋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于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澤,終老丘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慘膚,筮仕無門,賫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絶無過而問之者哉!
同樣是“經明行修之士”,爲什麽有的便可金榜題名、“策名廊廟”,有的却屢試不中,最終“賫恨入冥”?是否只能用“命偶”或“數乖”來解釋?這段話的危險性在于,作爲學術史家,其關注點應該限定于學術本身,而江藩却流露出對學人命運的“過度”關懷。更危險的是,此種關懷影響了江藩對《漢學師承記》體例的設定:“是記于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志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雕也。”質言之,在述學之外,江藩還想記人。
學術史與傳記文學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雖然史家可以選擇用傳記體述學,但其重點是傳主的學術觀點和師承關係,對傳主經歷則書其大概即可。而對于傳記文學來說,無論闡發思想或是記叙經歷都只是手段,最核心的任務是捕捉並呈現傳主獨特的精神與性情。江藩的問題在于,在編纂傳記體學術史時,没有克制住對學人命運的關注,導致《漢學師承記》呈現出一種文體雜糅的狀况,影響了其客觀性。但是,也正是這種文體雜糅,使江藩不自覺地將學術與學人置于一個關係語境當中。通過江藩的叙述我們看到,學術不但塑造著學人的一生,而且塑造著學人對生活的反思。
作爲傳記體學術史,《漢學師承記》有一個基本的行文結構:即“學述+行述”。學述無疑是江藩的寫作重點,雖然其在各傳中所占比重並不均衡——在惠棟、錢大昕、江永、戴震諸傳中可能達到全文的五分之四,而在汪元亮、賈田祖、李惇、江德量諸傳中可能僅有“究心經義”或者“讀書好古”等隻言片語——但是,依然是全書的叙事焦點和叙事動力,换句話說,决定著江藩對于傳主生活經歷的構造。《漢學師承記》的行述部份一般圍繞四個話題展開:學人的早年生活、性情、人際交往、人生際遇。我們看到,在江藩的叙述中,學術是以上四者背後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决定力量,是學人人生經歷的主綫。
關于學人的早年生活,江藩通常關注三個問題:出生之前的神异,早慧或晚慧,與學術的相遇方式。惠士奇、王昶、紀昀的降生,均有神异的徵兆。惠周惕夢明朝內閣首輔楊士奇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王昶降生之前,家中蘭花“茁兩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紫燕栖于楹,同巢异穴”。紀昀祖父“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因此,人們認爲紀昀是“靈物托生”。神异甚至伴隨著紀昀的成長,“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江藩對學人之神异來歷的熱衷,爲學人後來的成就提供了一個神秘主義的背景,也在二者之間預設了一種邏輯關係:他們似乎是先天便被學術選中的人。
學人們普遍的早慧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神异。《漢學師承記》中的學人大多“生而穎异”,“讀書十行並下”且“終身不忘”幾乎成了起碼的素養。在這樣一種語境下,閻若璩的晚慧就顯得十分特殊:
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异常。
閻若璩的“由鈍至悟”在今天的叙事話語中或許會被作爲勤能補拙的範例,但在江藩筆下,却是神异叙事的一種變體。首先,閻若璩在幼年時便被祖父點出成爲“一代儒宗”的潜質;其次,最終的“穎悟”是一次突然發生的神秘事件。那麽,“鈍”與“悟”之間的十年,僅是其本性顯露的障礙而已,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閻若璩早年經歷的不凡:他也是一位先天被學術選中的人,只是中間經歷了更多的考驗。
有的學人由于家學淵源,天生便知“學之所向”,如惠士奇、惠棟、盧文弨等——他們與學術的相遇是一種順理成章的事情。但還有一些學者,雖無父祖師長引導,却由于某種特殊的因緣進入漢學,終成名家。江永少年時本爲“世俗學”,一日在丘浚《大學衍義補》中讀到一段《周禮》的引文,立刻沉迷,“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遂通經藝”。江永與漢學相遇的契機竟是一部宋學著作,不能不說是一種奇异的因緣。戴震少時讀書私塾,“一字必求其義”,塾師不耐其煩,便給了他一部《說文解字》讓他自學,“學之三年,通其義,于是十三經盡通矣”。當然,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實仍由江永、戴震本人的素質决定,然而這也恰恰可以說明,學術對學人的選擇不是盲目的。
關于學人的性情,江藩尤其關注的是與學術相關的側面,以學術寫性情,以性情顯學術。這可以看成是《漢學師承記》的學術史性質所限——與學術無關的內容不宜納入傳記體學術史的框架——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恐怕也的確是學人性情中最爲突出的一面。在這一點上,學術史與傳記文學不謀而合。如寫江聲以《說文解字》爲宗,故而“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寫汪中“性情伉直”,“于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譏彈”。無論“不作楷書”還是“不輕許可”,均體現了傳主對個人學術觀點的偏執和捍衛,學術與性情相得益彰。最爲精彩的是寫閻若璩與汪琬論喪禮:
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復論難。琬著《五服考异》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昆山徐贊善乾學問曰:“于史有徵矣,于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没,子張尚存,見于《孟子》。子張没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嘆服。
這段話貌似論喪禮,其實是寫性情。汪琬任性使氣的一句挖苦,却引來閻若璩一本正經的長篇大論,一個認真得有些呆氣的學人形象躍然紙上,讓人忍俊不禁。
需要注意的是,以學術寫性情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當學術成爲刻畫人物的手段之後,易被置于從屬地位——這對一部學術史來說是否合適?如上引閻若璩論喪禮的例子,讀者根本不需要去瞭解他的長篇大論的具體內容,只要知道他在喋喋不休,那麽叙事的效果其實已經達到了。《漢學師承記》中還存在著一些“過度”的描寫。如寫張弨雅好金石,“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岩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况書,援據甚核”。此段文字的目的本是介紹張弨的《瘞鶴銘辨》,作爲學術史,說清楚其論證方法與結論即可。但是江藩却對他的探尋過程興致盎然,“乘江潮歸壑”、“藉落葉而坐”、“仰讀”的細節,甚至不乏詩意,與張弨“隱于賈”的身份形成一種張力。這些“過度”的細節與學術没有直接關聯,但却是刻畫學人性情的關鍵,可以作爲《漢學師承記》之文體雜糅的例證。
關于學人之間的交往,不外乎兩種情况:交好或交惡。背後的原因雖然多種多樣,但是在《漢學師承記》中,江藩僅僅突出一點,即學術觀點的相近或相左。這一部份內容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江藩本人與傳主的交往,當事人記當時事,可謂瞭解乾嘉學界的第一手資料。如記王鳴盛對自己的稱贊:“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禄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記與袁廷檮的交往:“藩與壽階少同里閈,後携家邗上,壽階館于康山,踪迹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此書的寫作目的是爲了張大漢學,在記録漢學家之間的惺惺相惜之外,自然也需記録與對手的論争。嘉慶四年,江藩在萬松書院當面指責袁枚:“今先生以五七言詩争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粗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于人心學術哉?”袁枚雖然反對考據之學,然對江藩的詩歌贊賞有加。江藩指責袁枚,僅是因王昶批評袁枚在前,“不忍背師立异”,可見清儒家法對學人關係的影響。
學人交往本是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份,江藩對此多花筆墨無可厚非。雖然略微偏重“交游聲氣之情”,却正是作爲學界一員的江藩對他所親歷的學林往事的客觀呈現。然而,在某些篇目中,江藩未能將對傳主的感情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導致了一種“過度”的感慨。余蕭客在世時,曾囑江藩補全《古經解鈎沉》。江藩作此傳時,已由當時十七歲的少年進入知命之年,因而感慨說:“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嘆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江藩年少時“好詆呵古人”,李惇曾從容勸諫。多年以後,江藩爲之傳,同時感慨說:“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此類感慨已與傳主學行無關,而是江藩個人的人生感悟的凝聚,對于傳記文學無疑是適宜的,但是對于學術史則顯得偏離主題。
那麽,這種“過度”的感慨由何而來?來自江藩《自序》中所表露的對于科舉時代學人命運的關注。關于學人之人生際遇的思考,其實本不屬學術史的範圍,但却是江藩編纂此書的動機之一。在總結乾嘉學術的同時,江藩總是抑制不住地追問:爲什麽學人精于古學,却總是時乖運蹇?江永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于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江永《鄉黨圖考》、《四書典林》澤惠士林,然而却只能爲他人做嫁。原因何在?似乎只能用“不祥”來解釋:志與天地擬者,自然會招來天地之忌。汪元亮的命運與江永類似:“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漢學師承記》還寫了一位有魏晋遺風的學人武億,“性善哭”:
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黄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于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
武億之哭,表達了對學人“寥落不偶”的悲慨。然而,上天對學人的迫害不只不得第一事。徐復死後,其婦被其兄“鬻爲土豪妾”,自刎而死。江藩論曰:“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六極”出《尚書·洪範》:“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六極之事,有一即不堪,然學人六極皆備,可謂上天的弃兒——被學術選擇,却又被上天遺弃,這就是江藩所展示的學人際遇。
毫無疑問,“學述”是《漢學師承記》的核心內容和主要價值。但是,江藩以傳記體述學,便將“學述”納入到了“行述”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說,江藩爲我們呈現的並非理念中的學術,而是學術的實存狀態,包括:學術對學人的影響,以及學人對學術的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學師承記》堪稱“儒林正史”,可與《儒林外史》對比閱讀。《儒林外史》討論的同樣是學術的實存狀態:當儒學异化爲純粹的考試工具、而不再與日常生活實踐相關時,儒林是一種什麽景象?相比之下,《漢學師承記》思考的問題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學術如何成爲一種生活?吳敬梓關注的是失去信仰之後的士人,而江藩關注的則是繼續堅持理想的士人。
江藩是乾嘉學者中的一員,因此,《漢學師承記》可以看成是乾嘉學者對人生的自我反思。通過對此書的叙事話語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漢學家的意識形態。我們發現,學術是此書叙事話語的核心,是江藩選擇材料、塑造人物的標準。在江藩的叙述中,學術决定著學人的降生,决定著學人的性情,决定著學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决定著學人的命運。學術是學人的人生軌迹背後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决定力量。學人甚至相信,即使爲天所忌、身罹六極,也是學術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學人本身的時乖運蹇,就有了一種爲學術而受難的悲壯意味。
問題在于,學人們在抱怨“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的時候,實際上有兩種預設(或者說期待):第一,通人並非常人;第二,學術應該給人帶來好的命運。可是,這兩種預設都無法成立:通人只是常人中的一員,學術與命運也無必然關係。正因爲心存預設,學人纔會在期待落空時格外沮喪,所以有意在學術與厄運之間建立聯繫,用想象中的受難來自我撫慰。這也可以解釋《漢學師承記》與江藩的另外一部著作《宋學淵源記》的文體差异。如果說前者的中心是“行述”框架中的“學述”的話,那麽後者的中心便僅僅是“行”。在宋學家的理想中,儒學既不是考試工具,也不是純粹的知識探討,而是一種日常生活實踐。他們秉持簞食瓢飲、顛沛如是的傳統,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因此,讀《宋學淵源記》會發現,宋學家很少有漢學家那種對命運的焦慮。相比之下,當漢學家堅持把經學作爲純粹的知識來探究,同時拒絶日常生活實踐時,很容易落入另一種形式的异化。
歷史著作總是會反映編纂者的主體性,所以,一切歷史著作中均有文學性存在。《漢學師承記》之所以備受指責,是因爲江藩的“門戶之見”(漢宋門戶、古文今文門戶)。實際上,“門戶之見”並非對此書影響最大的主體因素。江藩的確想寫一部反映“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的學術史,但由于他本人即爲乾嘉學人的一員,所記又多爲自己的師友,因而在撰述時難免會有主觀情緒的滲入。《漢學師承記》與其說是清代學術史,不如說是“我所親歷的清代學術史”,或者說是“江藩口述清代學術史”。而江藩對學人命運的“過度”關注,恰恰因爲他本人便是終身不第、時乖運蹇的典型。在《汪中傳》後,江藩自述云:“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産,迹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褲,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侄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漢學師承記》便是江藩的“哭”。如果說武億之哭是爲了他人,那麽江藩之哭則是爲了包括他本身在內的學人群體。雖然江藩未如司馬遷一般在全書的最後增加一篇《太史公自序》,但他實際上已經把個人的經歷與情懷融入全書。因此,我們甚至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漢學師承記》在正傳、附傳、又附的一百一十九位學者之外,還隱含著一部“江藩自傳”。
江藩的主體視角與身世之悲消解了《漢學師承記》作爲純粹學術史的性質,使之兼有了傳記與自傳文學色彩。這種文體雜糅不但没有削弱此書的史料價值,反而拓寬了其意義空間:我們不但可以閱讀文本,而且可以閱讀文本的叙事方式——後者中隱含的意識形態信息,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