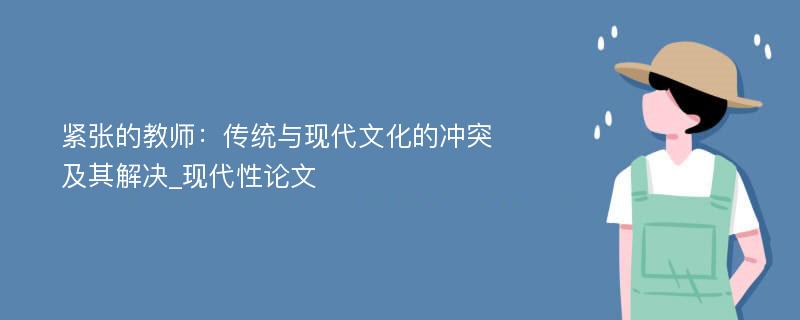
紧张的教师: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及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紧张论文,传统论文,教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5)01-0001-05 在走向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我们忘却了传统,却在现代中迷失;我们双手迎来了极具现代性的教育精神和课程文化,为理性和个人的光辉欢呼雀跃的同时,却不得不受制于前现代的文化规约。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互动,彰显出一种爱恨交加的紧张局面。 中国教育问题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龃龉而带来的矛盾和紧张更多地体现在教师这一实践主体上。在教师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三维空间内,教师不只是许多人说的戴着脚镣跳舞,而是“带着笑面具哭泣”。每一个稍有良知和智识的教师,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颉颃都会紧张不安、矛盾重重、无所适从,是纠结带来违背,是违背带来不安,是不安带来痛苦,是痛苦带来哭泣。如果说戴着脚镣跳舞是教师的外在表现,那么“带着笑面具哭泣”可能是教师内心的精神写照。笑是职业的标志,哭是内心的不安。本文力图发现教师的内心纠结甚至痛苦的深层原因所在,进而为教师的幸福谋求可能之路。 一、教师与他人:宗法权威与自觉理性、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 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凸显的过程,“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走向自觉……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1]由此,现代性的转换使得宗法血缘维系的前现代文化基因让位给自觉的、理性化的人本和法治精神,同时也带来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张扬。教师与他人关系的冲突和紧张也由此产生。 教师的紧张感首先表现在宗法权威与自觉理性的冲突上。在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或“长老统治”的社会里,教师有着与天地君亲并提的地位,“亲其师信其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话语都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下,教师用家庭伦理关系来规约师生关系,中国传统“情本位”的文化弥漫在人与他人处理关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以降,人更多地以独立的、自我的、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不再依附于诸如血缘、家族、村落等的群体关系,人存在的“单子化”促使人们在个体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承担对社会及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教师与学生和其他人的关系变成了现代意义上制度化的契约关系,权利和义务是度量教师行为的标尺。 深受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浸淫的当代学生,其主体性正在苏醒,对民主平等的权利诉求也日渐显现,当这种诉求与教师旧有的、和农业社会相适恰的专制权力相遭遇,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教师面对两者的冲突,一方面有着教师天然具有权威的深层职业潜意识,一方面不得不遵从法律法规的约束而实践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的这种紧张感让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矛盾重重,造成了表面上维护民主平等,私底下却通过各种手段去控制、窥探、监控学生。 其次,群体伦理让渡于个体伦理带来道德的世俗化,教师的德性伦理也沦丧为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非“我应该做什么”,它的基本概念是“好、善、德”而非“正当、责任”。当然,教师的德性伦理是与前现代“共同体”社会或“熟人社会”相适应的。当教育进入现代社会,“教育已经不再是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的价值引导,而成为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学补偿性构件;对人的机械论理解直接导致了教育建构的程序化和机械化,从而教师也就不再是‘道’的追求者,而成为人力资本的培训者。”[2]教师从前那种威严清俊的形象逐渐模糊,教师的道德产生了碎片化,个体主义的张扬取代了“公共善”的价值求索。道德只能置于自身之上,处于虚空之中,道德成了与社会无关的事情,成为教师私人领域的事情。 在这种转化中,教师仍然面临着选择带来的痛苦。我们教师教育中所要求的“人师”形象,“传道、授业、解惑”者的魅影,在现代性的言说中异化为“用教学技能高效率地教知识以保证学生考试成功的规范伦理,使教师职业自我意识和人生态度都充满着工具理性和利益至上的倾向”。[3]教师之间的竞争、唯成绩论等,让师生关系、师师关系变得狭隘、单调,更有个别教师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将教师的德性伦理肆意践踏,从此教师的生活世界便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当教师与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社会人的关系变成干巴巴的“守则”遵守和个人至上的合理维护,教师以何影响、化育学生?没有了融洽的关系,教师又怎不紧张和焦躁? 二、教师与自我:整体性与功能性、当下与未来 教师的分裂感和迷茫感不只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还体现在自我认同的危机上。“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这些认同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或者彼此强化,如职业上的、文化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认同可能与另一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4]教师自我认同的冲突和危机表现在生命意义的单向度和生存价值的虚无化两个方面。 在前现代,知识分子被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天职感”所召唤,是文化的传承者,甚至是与政统相抗衡的道统的重要力量。现代以来,“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原来充满了意义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世界割裂成一个个孤零零的机械碎片。在这样的彷徨、孤独之下,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5]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从立法者到阐释者(鲍曼),从普遍的知识分子到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从理念人(科塞)到专家(吉登斯)的变化,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过程就是现代性的后果逐渐显现的过程。 教师作为专门化职业之一,也通过蜷缩在自己的专业学科领域,来获得一种虚幻的意义。同时,教师作为知识人,其劳动在现代社会下也成为生产性的劳动,教师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其教学也由“成人”之教异化为训练和价值无涉的知识获得,“好像教育的内容仅仅是专门的技艺训练和实际知识的获得,以及给予孩子足以使他对世界获取一种见解的信息”。[6]教师劳动成了工具理性入侵的殖民地,“知识权力与现代性的经济生产结构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压抑性的力量”,[7]不只压抑着学生,也压抑着教师,将教师生命的意义异化为功能性的有用,将教师存在的整体性碎片化。 是用生命回应职业的需要还是用职业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是教师面临的两难选择。教师在生命的整体性与功能性之间游离,在市场逻辑与知识超越性之间矛盾着。他既不得已成为产品(学生)生产链上的一员,又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漠视而带来的痛苦。雅斯贝尔斯说,“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在这两种矛盾的冲动的压力之下,他的行为可能干扰生活秩序的平静与稳定。”[8]教师的紧张由此又增加了一层,这层来自生命意义的单向度。 另外一层教师自我认同上的紧张来自于教师生存价值的虚无,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对当下的不安态度上,鲍曼形象地比喻为“西西弗斯的苦难”①。 众所周知,现代性以人的解放、进步等为标语,宣告了与传统的断裂,宣告了人类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力量。现代性谋划最大的成就就是使人们对未来充满理想,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正如丹尼斯·贝尔认为的那样,“现代性之本质就是和过去的断裂,它把过去只看成过去,并为了现在或将来将过去一笔勾销。人被责令要更新自己,而不是去延伸存在之巨链。”[9]在贝尔的眼中,瓦解传统是现代性的内在含义,人之存在于是没有了历史感,变得单薄起来。现代性于是获得了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未来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为未来而存在的时代。[10] 现代性以进步为名,给现代人描绘了一张美好蓝图,人们就只顾抬着头朝着目标前进,却忘却了当下行走的意义,忘了为什么而出发。人对当下甚至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因为“当下是没有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下那么丑陋、令人憎恶以及不能容忍。当下是过时的。它来到之前就已经过时”。[11]教师就是用对当下的放逐和对未来的虚幻期许来抵抗当下的不安。教师的教学是为了学生未来更好的生活,教师的忙碌是为了民族和个人的明天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教师对进步的追逐和对未来的希冀。而没有了当下,教师就失去了反思能力,教师存在的历史性被割裂了,只有指向未来的利益期待,只剩下世俗的使用价值,教师工作忙碌却烦躁,重复却无意义,职业性的微笑下藏着麻木,充实的工作中隐藏着精神的虚无。教师如同进入了韦伯所说的“铁笼困境”,只剩下经济的冲动,“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2] 教师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似乎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困境。人的解放成了双刃剑,它把人推向宇宙中心的同时,也宣布了“人”的死亡。我们破坏了前现代(特别是儒家)重视对当下存在意义的传统②,人的生命存在的历史性从此断裂开来,导致一个丧失本真性的、紧张不安的自我。无怪乎萨特说,人就是命定的虚无。 三、教师与社会:代言人与托管人、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 从教师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讲,教师的紧张和焦虑感至少体现在宏观和中观两个维度。从宏观上看,教师在国家代言人(即经济复兴的推动者)还是托管人上焦灼不安;从中观上看,学校场域中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的矛盾,也带来了教师一定程度的内心紧张。 如上文所述,现代以来,教师与其他职业的边界逐渐模糊,被纳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之中。“在市场化思维下,学校、教师成了获取效益最大化的工具,成本与受益成了家长衡量教师的标杆,金钱成了教师和家长之间沟通的隐形纽带。”[13]教师被分裂为一个个拥有单独学科知识的“个体户”,知识在课堂上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被流通和检测,教师从此成了有知识的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人”。 市场规则对整个社会的重新规划,让知识分子原有的角色定位和生存方式经历着深刻变化,合乎效率在现代性下转化为合乎市场逻辑,进而在国家的宏大叙事下,教师“失语”了,教师似乎因为有了为经济复兴贡献的能力而获得了职业存在合理性。教师的教学“泛娱乐化”以及明星教师、各种最牛教师的出现,正是将现代性的“祛魅”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的社会“在技术专家和媒体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世俗意识形态。”[14]教师与社会的双向关系变成了单向的支配关系,教师不再有葛兰西所说的赋予国家权力以合法性的“托管人”角色,而注定要扮演一种非政治角色,在匿名性的政治下寻求生活的庇护,最终产生了教师存在的危机,即佐藤学所说的“私事化”现象。③ 其次,教师的紧张还存在于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的矛盾中。科层制是现代性所倡导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展现形式,中间存在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科层管理追求效率,立足整体、一致;而专业人员追求知识,立足个性化的表达。于是我们常常发现,教育改革往往总是自上而下的推广实施,并用一套严格的评估规范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估。“可以说,学校科层人员借效率在现代性中的得宠,假科学化管理之威,总是能够成功地践踏作为教育本真内涵的人性、自由和意义关切,并屡屡击败手持教育科学这个被现代性边缘化了的武器、高举‘人’这面被现代性单向度化了的旗帜的教师。”[15]而另一方面,教师的“消极不反对”则让教育变革流于形式,教师教学意义的阐述空间日益变窄,并逐渐沦为单纯的知识传播者,失去了教师职业的文化和政治意蕴。 教师就在这种权力困境中欲罢不能,“我”还是“我们”的争斗让教师陷进了权力漩涡,教师专业权力与科层权力的交恶让教师深陷泥潭而无法施展。在当今甚至还未理性化既已官僚化的学校权力中,教师若没有紧张感才是奇怪的事情。 四、教师的启蒙:走向幸福之路 作为外源型现代性国家中的教育,既有着命定的现代性的无奈,也更面对前现代进入现代的水土不服。同样,教师也在面对伦理道德、自我认同与权力等问题时,既有来自前现代的传统文化影响,又被现代性潮流裹挟其中,各种交杂和繁芜,让教师左右为难。这种为难并非只是教师的为难,也更是教育的为难,社会变革的为难。为此,寻求教师的幸福之路即是寻求现代教育实现之路,也或许唯有教师精神的坚定和平静,教育的现代性问题才可能会有澄明之时。 首先要正本清源。每一次历史的变革都是对传统的反刍和对新思想的融合。目前,我们既遗忘(遗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破坏)了传统,又没有完全走向现代性。正本就是要明白现代性是大势所趋,要厘清现代教育到底是什么,现代教师需要什么,特别是在面对当今全球化挑战以及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教育的批评大行其道之时,不被各种流行话语所误导,认清我国教师发展的现代性方向尤显得格外重要。清源就是要挖掘中国教师文化之根,让教师形象烙上中国印并赋予现代特色,避免教师在思想信念方面产生断裂性危机,从而让中国教师前现代的文化传统转变为现代教师发展的活水源头。 其次需要教师教育的启蒙。教师教育要恢复生命存在的历史性,成“全”生命,朗润生命,恢复教师职业的精神性、生命化,没有“成人”(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蕴的教师教育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甚至害人不浅。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适应型的教师,没有对教师批判思维和公共意识的培养,教师的政治智慧和公共理性基本缺失,但如果没有对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教育的深刻思索和定位,教师就只能深陷时代的迷雾,迷失方向,任由宰割。 最后,教师的自我解蔽是消除教师紧张的根本。“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被看作是现代性原则”,[16]个人的独立才能带来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也只有形成了自我意识,个体的主体性才成为可能。教师要在生活中自我解放,在阅读中观察,在观察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从某种角度来讲,教师的理性启蒙是真正解决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前提所在。 罗素说,人只有在自身主体价值得到肯定时才幸福.梁漱溟则认为,求得一份心安是儒家文化仁的根本。两者一个求之于外在的肯定,一个求之于内生的平衡,充分道出了中西方对幸福的不同理解。谋求教师的幸福,需要教师内心的不打架,而不打架则需要教师高度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实现,所以罗素与梁漱溟的不同言说并不矛盾。面对前现代与现代的颉颃,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社会的变革,但反过来,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性教育变革却往往容易陷入悖论,容易导致霸权而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没有自下而上的教师的启蒙和解放,遑论教育变革和教师发展无异于空中楼阁,水中探月,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教师的成长极具意蕴,且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2014-09-22 注释: ①“现代性的焦躁是西西弗斯的苦难,与当下不安的抗争采用了历史进步的形式”。见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鲍曼用西西弗斯不断推巨石上山而又不断失败滚落下来的神话,表达了现代人当下生活的荒诞和虚无。 ②李泽厚用“实用理性”说明儒家思想现实精神,即不需要宗教的狂热或神秘的教义,而是重视现世的行动以成“仁”。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28页。 ③私事化是佐藤学针对教职的“公共使命”意识的丧失提出的,认为教师工作应该超越个人利益,参与民主社会与文化建设。见佐藤学著,钟启泉译《课程与教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