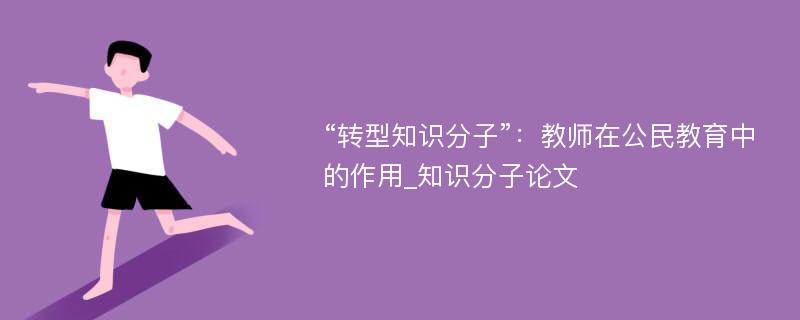
“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知识论文,公民论文,分子论文,角色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9-0102-07 学校不仅是一个传递知识的场所,同时更是一个培养公民品格的公共生活空间。教师作为学校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成员,其职业角色认同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公民学习和品格建构。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教师往往被视为课程知识及其价值体系的非反思性的授受者、知识的灌输者,“一个仅仅从事非创造性劳动的雇工、一个只是灌输既定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一个贬损自身魂灵的精神附庸”。①当教师以这样的职业角色投入教育工作的时候,他(她)只能成为一个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技术工匠”,失去作为知识分子所应当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与创造性。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也只能成为缺乏主体性与批判性的“知识人”,而不可能成为具有批判意识与创造意识的公民。显然,只有当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公民,他(她)才有可能在公民教育中发挥出积极的影响,才有可能促进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提升学生的公民品质。 一、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 关于“教师是否是知识分子”以及“教师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等命题,在目前的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议。按照《辞海》和《社会学百科词典》的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按照这个定义,教师无疑是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更为深刻的内涵出发,我们发现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曾指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的知识人,他们的特征不仅在于“有知识”,更在于他们以自身的理念、信仰来达成公共关怀,因而“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②也即是说,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并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而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公共良知和公共批判意识。余英时也支持了刘易斯·科塞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虽然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他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③因此,具备专业知识或科学知识仅仅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而具有公共关怀和公共德性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此两者的有机叠加,才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充要条件”。 那么,教师是否能成为如刘易斯·科塞以及余英时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呢?显然,在教育学领域中,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争议。只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教师批判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于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逐渐产生了认同。以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亨利·吉鲁(Henry A.Giroux)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者支持了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他们认为教师不仅是社会的代表者,主流价值观念的传递者,同时还是具有社会关怀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保罗·弗莱雷把教师定义为“文化工作者”,因为教师必须对异化的、压迫的、不平等的文化生活展开反思与批判,并且“对被异化了的文化的认识,产生改造行动,导致一种从异化中解脱出来的文化。”④因此,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播既定的文化,更是要引导学生反抗文化与价值观的压迫,从而使教育成为一项引领解放、走向自由的事业。 亨利·吉鲁则提出了一个更富有创造性的概念来概括教师的知识分子属性,他把教师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在亨利·吉鲁的描述中,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其含义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学流水线上的“技术工匠”,而是要把教学工作“转化”为具有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教师不应只关心学生的知识学习和职业训练,而是必须展开批判性的公民教育活动,引导他们的公民批判意识的成长,从而使学生从“知识人”转化为“批判的公民”,并且“使他们能够批判性地观察社会,在必要的时候改变社会。”⑤也即是说,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必须以自身公民批判意识和公共关怀意识来推动学生成为学校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批判者,并以自身的公民行动来寻求学校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理性建构。显然,亨利·吉鲁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教师角色的理论视角。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他(她)的职业角色已经远远超越于知识授受者,而成为了一个具有批判性、反思性与创造性的公民。而这对于公民教育工作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教师成为了公民,他(她)才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公民实践和公民榜样来影响学生的公民成长。这可以推动学校成为一个充满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的公共生活空间,而不是一个僵化的知识工厂。 亨利·吉鲁的观点在现实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下虽然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是其所提出的教师要通过知识分子角色的批判性、反思性与创造性来重新塑造学校公共生活、培育学生的公民品质,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而言,随着整个社会的公共性与民主性变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公民教育进程的不断推进,学生的公民品质的培育已经变得愈来愈重要。而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公民品质,则必定要依赖于教师的公民榜样和知识分子角色的发挥。因此,吉鲁的观点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即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不仅有利于学校教育以及公民教育的开展,同时也可以促进教师自身的观念意识和职业认同的彻底革新。这种革新体现为: 首先,教师工作不再是一种技术性或工具性的工作,而是一种反思性的智识工作(Intellectual Labor)。技术性或工具性的职业角色往往把教师视为课程知识的传递工具,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既定的知识及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但是,一旦教师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那么他(她)的工作显然不仅止于传递课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她)还要对课程知识展开反思与批判,以“这是谁的知识”、“为什么是这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否合理”等方式来对课程知识加以追问。当教师对既定的知识展开追问和反思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只是课程知识的纯粹的传递工具,而是成为了课程知识的反思者和创造者。在此基础上,教师能够更好地建构属于批判性的课程,实现课程知识的更真实、更具体、更有创造力的传递。也即是说,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他们事实上肩负着比单纯地传授既定的、法定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教育使命,即反思、批判和创造知识,思考知识背后的含义,从而完成知识的反思性的传递。教师不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技术性的、机械性的工作,而是看作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智识工作”,教师要通过自身的充满智慧的教学活动来启迪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造思维,引导学生对既定的知识进行理性的思考,使学生摆脱旧有的知识窠臼获得新的知识体验,从而增进公民的智识和理解。 其次,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与既定的教育模式、课程体系、价值观念系统保持合理的距离,但是也并非有意地制造冲突和对立的关系,而主要是形成一种合作与反思的互动关系。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往往受到既定的教育模式及价值体系的严格控制,教师作为国家、社会的代言人,承担着传递主流价值观的任务。甚至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教师职业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一个环节,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专业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被训练成为如亨利·吉鲁所谓的“理念和政治的文盲”(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Illiteracy),服从于既定的课程知识结构和既定价值体系的束缚,教育活动也就被简化成为教学方法的实施活动。⑥显然,这种教师角色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教育变革的需要。教师如果仅仅受限于既定的知识框架及价值体系,仅仅成为既有的教育模式的附庸,不但不能推动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反而会阻碍教育改革的实现。近十年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教师受到传统职业角色的束缚太过于沉重,使得他们失去了理解改革、参与改革以及推动改革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教师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显然不再是让他们成为既定的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的附庸,成为教育改革的绊脚石,而是促使教师在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反思既定知识框架和价值体系,成为一名具有独立性、反思性与批判性的教师,实现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教育使命和公共责任。 最后,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不仅要展开理念的批判,同时还要将“批判的理念”转化为“批判的行动”,以实践行动来促进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因此,教师应该跨越自身的相对狭窄的学科领域和专业界限,超越于学科、专业之外而获得一种公共性的批判意识。因为“一旦知识分子退缩进狭窄的专业领域,成为冷漠、狭隘、唯专业建制是从的套中人,则思想便失去了进化的力量,社会的良知也将无人看护。”⑦狭隘的知识人角色无助于文化知识的创造和公共社会的进步,它只会使教师远离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公共性。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显然不能丧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公共意识和行动意识,所以他(她)必须跳出学科专业领域的界限而采取批判性的态度来审视社会公共问题,形成社会公共关怀意识。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还应在公共批判和公共关怀意识的基础上来参与学校以及社会的公民行动,承担起改造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责任。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必须把理念批判与公民行动有效地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既有理念、又有行动的公民。同时,当教师真正以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来参与公民行动时,他(她)的这种行动也将深深地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公共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改造,从而成为一名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公民行动者。 二、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如前所述,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有必要与既定的教育模式与价值体系保持合理的距离,在合作性与批判性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与创造性。而通过这种知识分子角色的发挥,教师能够在现实的教育背景下反思既定的教育体系和课程模式,同时思考如何建构更为合理的教育体系,并且付诸公民行动。教师通过自身的公民行动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的公民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的发展,从而发挥出积极的公民教育影响,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的建构。因此,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他(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而是成为了学校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中的公民,承担着公民教育者的角色,为公民教育提供有效的支持。教师的公民教育角色体现为: 首先,教师通过对技术性、机械性的教育工作的反思,可以成为公民品质的促进者,引导了学生的公民品格与批判精神的发展。教师通过反思教师职业的贬值与教师技能的退化,在一定意义上重新确认了自身的知识分子属性,从而更加重视学生的公民品质的教育。教师职业的贬值主要是指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学校系统中的技术人员,成为学校管理和课程计划的被动执行者,而失去了主动参与、积极批判的公民角色。当教师意识不到自身的公民角色,他(她)当然也就很难在公民教育中发挥作用。教师技能的退化主要体现为教师的教育技能仅仅停留于知识传递的层面,而反思知识、批判知识等方面的技能与精神则面临着严重的退化。因此,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教师可以对自身的职业贬值和技能退化展开深刻的反思,避免成为谋取生活的教书匠,成为既定知识系统的灌输者“拒绝把自身的价值仅仅定位于知识的传输系统上,教学也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其中体现着自身那些无可替代的价值体验与专业旨趣”。⑧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可以更深入理解自身的教师角色,即教师不是技术工匠,而是反思性的文化工作者,是学生的公民精神和公共关怀意识的培育者。通过对于自身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教师可以重新思考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的角色使命,更好地实现培养公民品质的公民教育目标。而学生在这种批判性的教育活动中也将更好地成为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公民。 其次,教师通过重新思考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可以发掘出学校生活、课堂生活中潜藏的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揭示者与改造者。显然,那种认为教师职业是一种与权力关系没有任何“交集”的职业的观点是过于幼稚的。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教师不仅传递知识,同时还必须对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展开分析和批判。正如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Apple)所言,教育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学校课程传授的并非中性的知识,而是被权力关系所改造的知识。⑨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不能回避或者忽略这种课程知识与权力的隐性关系,而是应当正视这种关系。当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威胁到课程知识的真实性、公正性的时候,教师应当挺身而出加以矫正,并且引导学生认识到这种错误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危害性。教师有责任在课堂生活中挖掘知识与权力的不合法、不合理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曝光在学生的面前,推动他们去反思、去发现、去改造,直到这种关系不再成为课堂生活的障碍。教师也许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的正义秩序的建构者,但是他(她)可以在课堂生活中运用自身的独特的知识分子意识,来防止知识与权力关系在学校生活以及课堂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从而建构更加具有民主性、公共性的学校公共生活氛围,促进学校生活和课堂生活的民主,最终有效地实现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 再次,教师通过在批判基础上的教育建构活动,可以让自己成为学校生活的批判者和建构者。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教师的工作不仅是批判,同时也是建构。教师需要将批判性的话语与建构性的话语统一起来,让两种话语方式都发挥出作用。批判性的话语可以推动对既定的社会关系和课程体系的解构,而建构性的话语则可以引导合理的社会关系和课程体系的建构。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的批判性话语可以激发学生的公民批判意识,能够引导学生参与对社会生活、学校生活以及课程知识的反思。这种批判活动可以为学生的公民成长提供宝贵的经验,促进学生的公民批判精神的发展。但是,批判性的话语及其教育活动并不是教师工作的全部。在批判的话语之外,教师还必须寻求一种建构的话语,即引导学校生活、课堂生活的可能的建构。“转化性知识分子需要发展出一套话语,把批判性的语言与可能性的语言统一起来,这样,社会教育者就会认识到他们可以做出改变。”⑩如果教师的工作仅仅止于批判,那么就很难将学校生活中的批判活动与建设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同样不希望看到批判活动“到此为止”,而没有最终促进学校生活的建设和改善。只有当教师与学生一起对学校制度、规范、纪律等展开批判活动并且提供建设性方案的时候,学生才能受到更为积极、更为完整的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教师有必要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条件,在批判性的话语中结合建构性的话语,让学生感受到改造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教师要正确地运用批判性与建构性,从而使学生能够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并且把批判与建构统一起来,促进社会生活与学校生活的变革。 最后,教师通过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来传递公民价值理念,可以让自己成为公民“隐性课程”的创建者与实施者。教师在公民教育中将注意到,学校生活本身蕴含着一种“隐性课程”机制,它向学生源源不断地传递着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念。正如波兰尼(M.Polanyi)所指出的,教育活动在传递显性知识之外,还传递着“隐性的知识”(Implicit Knowledge),也可称之为“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11)隐性课程或缄默知识是那些不为人知或者很难被人的理性所认知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所发挥出来的能量并不比显性知识弱,甚至很多时候比显性知识的影响更为深远。公民教育无法离开隐性课程和隐性知识的支持,学生公民品质的发展有赖于学校生活以及课堂生活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知。因此,“如果教师想实施一种更全面的公民教育,他们不但必须理解隐性课程和正式课程的联系,而且必须理解课程与建构社会中的类似的知识模式和社会关系的原则之间的复杂关系”。(12)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隐含的价值观念往往是潜藏于显性课程之外的,它通过缄默的、隐性地方式传递给学生,发挥出潜移默化的公民教育影响。因此,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必须理解和发掘隐含在显性课程之下的价值观念(比如,课程知识背后隐藏的价值元素,课堂生活中的话语分布,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举止及其可能向学生传递的价值观念),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理性的反思,从而保障学校生活的隐性价值观念符合公民教育的需要。在课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教师的言行、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也将对学生起到隐性的公民教育作用,因为学生的公民成长伴随着对教师言行的模仿。所以,教师必须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及生活惯习,避免对学生的公民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总之,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显性课程和知识体系的传授者,同时更要认识到自己还是一名隐性课程及缄默知识的实施者,公民价值观将通过学校生活以及教师言行而隐性地触动学生的公民体验,发挥着促进或者阻碍学生的公民发展的效果。 三、教师通过“转化性”构筑学校的公共生活空间 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承担着批判性地重建学校公共生活的使命。教师不单纯是社会代表者或者体制代言人,教师与既定的教育体制的关系是一种既批判又合作的关系。教师应当在合理的限度内承担知识分子的公共职责与使命,对社会生活、学校生活以及课堂生活展开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工作。在批判与建构中,教师可以实现自身作为公民品质的促进者、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发掘者、隐性课程与缄默知识的传递者等公民教育角色,发展学校的公共生活空间,提升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因此,教师有必要发展自身的“转化性”意识,以此来更好地构筑学校的公共生活空间,推动学生公民品质的发展。 首先,教师要超越个体生活,引导学生走向公共生活。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名公民而存在的。教师不仅自身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成员,同时也要引导学生成为公共生活的公民成员。如果教师不能超越狭隘的个体生活,不能保持对公共生活的兴趣、热爱和参与,那么他(她)也很难引导学生去这样做。因此,教师必须致力于超越个体生活和专业生活,避免退回到专业和学科领域之内,“以学科专家为追求的理想,谋求自己在本学科教学技术上的成熟与优化,放弃公共身份,把自己等同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13)教师在狭隘的个体生活和专业生活中,只能走向学科专业化和技术化,这使得教师职业愈益脱离其公共使命。教师要想促进学校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建构,就必须从这种个体生活和专业生活中摆脱出来,真正以公民的眼光来看学校以及社会生活,积极投身于学校以及社会的公共事业。只有当教师从这种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他(她)也才能引领学生去关心社会问题,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追求社会正义,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如此,公民教育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学习,更是一种与公共生活紧密联结的公民实践。教师也不再仅仅是既定的课程知识的执行者和传递者,而成为了课程知识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者和参与者。通过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反思性、批判性、创造性与行动性,学生也将获得走出课堂、走向公共生活的公民勇气和公民主体性。在教师与学生的共同的公民实践中,学校不再是公民教育的唯一场所,因为公民教育已经融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成为了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教师要培养学校生活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形成教师与学生的公民学习共同体。当前学校生活空间潜藏着一种割裂学生的公民伙伴关系的强烈倾向,因为学校成为了各种恶性竞争以及成绩排名的场所,不仅是学生之间展开着激烈的竞争,教师与教师、学校与学校之间也围绕着考试升学展开着激烈的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瓦解了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使得相互争斗成为了常态,而学校教育也失去了培养学生的公民合作精神的生活基础。正如佐藤学教授所指出的,当今的学校已经走入了迷惘,“与其说学校是儿童一起学习成长的场所,不如说是丧失欢乐、丧失学习伙伴、也丧失自身的场所更为妥当;学校与其说是形成学习的亲和、实现民主主义的场所,不如说是发挥着排他性竞争,酿造优越感与自卑感,扩大阶级、种族、性别的社会文化差异的场所”。(14)在排他性的竞争中,学校生活丧失了欢乐,学生之间也不再是快乐的伙伴关系。学校不再是一个充满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关怀意识的场所,因为学校把提高升学率看得比建构民主生活空间更为重要。显然,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不能对这种“异化”的学校生活熟视无睹,不能让恶性的竞争关系阻碍青少年学生的公民精神的发展。为此,教师应当促进学校生活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建立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公民学习共同体。教师要让学生们了解到良好的学习生活不具有排他性,它是一种共赢的学习生活;它寻求的是一种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公民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挤、相互攻击的敌视关系。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在课堂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公民的共同体精神。作为学校公共生活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成员,学生不仅为自我的学业成就和考试升学而奋斗,同时也是为学校公共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发展和完善而奋斗。学生作为公民,在享有自身的公民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公民责任,承担公民共同体的公共义务。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引导以及公民共同体生活的建构,教师可以让学生认识到维护、发展学校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教会学生尊重公民共同体中的其他公民,意识到合作与协商是公民共同体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教师可以通过共同体生活把这些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提升学生的公民伙伴意识和合作精神。 最后,教师要致力于建构一种新型的师生交往关系,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契合于学校生活的公共领域属性。新型的师生交往关系是对传统的知识交往关系的全面超越;在新型的师生交往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生活不再只是围绕着知识和考试,而是围绕着公民品格的培育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在这种新型的交往生活中,教师与学生作为学校公共生活的公民,遵循着公民伦理的基本规范,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到交往活动当中。对于学生而言,教师不再是一个无限高大的课堂专制者、知识授受者以及价值灌输者,而是一个在人格上平等、在角色上对等、在权利上平等的公民。教师不再能够凭借自身的教育权力来侵犯学生的公民权利(比如学生的受教育权、隐私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教师的权力行使必须接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接受学生的公民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当然,学生也必须尊重教师的权利,不得以损害教师权利的方式来开展学习活动。教师与学生作为学校公民共同体的成员,均应当自觉地维护对方的公民权利,同时也自觉履行自身的公民责任。因此,在公共性的学校生活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关系不再只是知识关系,同时也是一种体现出正义性的公民交往关系。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必须让自己的教育工作满足公民伦理以及正义理念的要求。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就是要把公民的权利、责任、正义的理念融入到课堂生活中,使学生在课堂生活中接受到全面的公民教育。教师在课堂公共生活的建构中,要努力超越传统的知识模式,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关系成为一种以公民理性、公共伦理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可以把教师和学生引导到正确的公民教育方向,在社会、学校以及课堂的交往生活空间中思考权利、责任、正义、平等等公民价值理念,同时也引导教师和学生以公民价值理念来检视学校生活,促进学校生活的公共性建构。这是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所能够给学校公共生活以及课堂公共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也是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共同创造公共性的学校生活空间的基础。 注释: ①吴康宁:《教师: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年第4期。 ②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⑤⑥⑩亨利·吉鲁:《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迈向批判教育学》,朱红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9、154页。 ⑦车丽娜、徐继存:《寻找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教师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车丽娜:《“教书匠”的式微与教师文化的重建》,《当代教育科学》2007年第1期。 ⑨阿普尔:《官方知识》,曲囡囡、刘明堂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1)Polanyi,M.The Tacit Dimension.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14。 (12)Giroux,H.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Towards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Bergin & Garvey,2001,199。 (13)王彦明:《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原因、诉求》,《教育导刊》(上半月)2011年第3期。 (14)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钟启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性知识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公民教育论文; 政治论文; 公共空间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