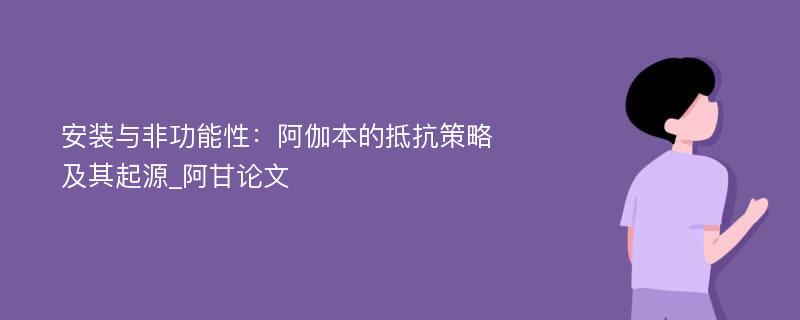
悬置与非功用性:阿甘本的抵抗策略及其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用论文,与非论文,阿甘论文,策略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阿甘本的思想发展中,福柯和本雅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权力及权力机制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重新思考就是福柯式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阿甘本的分析中,这些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我们常见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包括历史上的神学机制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权力机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就是设定边界,因此考察边界问题就成为我们反思权力机制的一个切入口。边界总是表现为各种对立机制,比如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裸体与穿衣的对立。阿甘本认为,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须首先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它的目标不是要找到先于对立的原初状态,而是掌握产生这一对立的机制,并使其失效”①。 一、边界及其机制 在考察边界和各种对立机制时,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这是阿甘本最常用的分析策略,这使他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看上去很相似,都有大量的对古典哲学和宗教文本的非常繁琐的词源学的阐释,都追溯到宗教和哲学的源头。阿甘本认为,当代问题如果不追溯到古代源头,是无法彻底理解的,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下的切入点必然采取考古学的形式;然而这种考古学并不是回归到历史的过去,而是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②在阿甘本看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也是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意向“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③但是,在相似的外表下,阿甘本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旨趣是不同的,虽然对古代的分析都指向当代,但在新古典主义看到古代理想范式的地方,阿甘本看到的却是深渊和“折断的脊骨”,是当代问题的源头和转折点。 阿甘本通过边界问题对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小说主人公K所做的就是重新勘定边界的工作。阿甘本把K和古罗马的土地测量传统联系了起来。古罗马的边界具有神圣的性质,它来源于对应的天体运行位置。因此,K的职业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人请他来干这个活,因此,他的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指派的,在阿甘本看来,这一职业选择既是一种开战宣言,也是一种策略,因为它使原有的边界成了问题,“K后来全身心关注的,不是花园与村子的房屋之间的边界问题。相反,由于村子里的生活实际上完全是由村子与城堡之间的边界决定的,这些边界同时又使村子和城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测量员的到来首先使这些边界成了问题”④。 在写作《城堡》的同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对边界问题的一些思考,这是以对精神世界的反思为起点的,经历的精神崩溃使卡夫卡开始反思精神世界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边界问题,内心所产生的狂野被描述为追捕,其中“自我观察不让任何表象停歇,不停地追逐它们,使它们成为新的自我观察的表象”⑤。阿甘本认为,在这里,追捕的形象让位于对边界问题的反思,也就是反思人类与人类之上的、超越人类的事物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反思。这也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追捕“只是一种表象”,可以说是“对最后的人类边界的一种攻击”,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对边界的攻击”。⑥阿甘本认为,在《城堡》中,“对于最后边界的攻击”正是这样一种攻击,“它针对的是把城堡(上层)与村子(下层)分隔开来的那些界限”⑦。 对边界的攻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上帝或最高权力,这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城堡主人伯爵老爷从来都没有被真正讨论过,斗争的目标只是天使、信使和作为其代表的各级官僚,因此,这里关键的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冲突,而是在神的问题上与人类的谎言之间的残酷斗争。阿甘本认为,这就像“在法的大门口”这个寓言故事所表现的,重要的并不是对法的研究,而是“对守门人的长期研究”,在法的大门口的乡下人,正是由于持续地坚持这一研究,才能在诉讼之外终其一生,而不像约瑟夫·K一样被卷进诉讼致死。因此,真正的欺骗恰恰是守门人的存在,也就是从最低级别的办事人员、检察官直到最高法官的存在,他们的目标就是诱使他人进行自我诬陷,从而进入法的大门,而这一大门只通向诉讼。因此,阿甘本认为,土地测量员要清除或推翻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建立起来的界线、区分和障碍”⑧。 边界或界线的设定是为了区分事物,但边界的设定并不能阻断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并且这一联系会以各种伪装继续发挥作用,就像先知虽然早就从西方历史上消失了,但他在各种伪装下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阿甘本追溯了先知这一形象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指出与先知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创造和救赎之间的对立,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对立都统一于真主或上帝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或实践。阿甘本认为,不管这两种工作的起源是什么,创造和救赎确立了神圣行为的两极,同时神圣行为作为人类反思自身问题的场所,也反映了人类行为的两极。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分,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既相互区别、相互对立,但又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仍然以某种方式隐秘地联系在一起。在阿甘本看来,在人类的每一种生存状况中,真正独特的是这两种工作无声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相互交织,“是预言性词汇和创造性词汇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是天使的力量和先知的力量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⑨ 并且,创造与救赎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创造在先,救赎在后。阿甘本通过对《古兰经》的分析指出,在伊斯兰教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救赎先于创造,因此,看起来在后的实际上却是在先的。“救赎不是对堕落的造物的一种拯救,而是使创造变得更易理解,它赋予创造以意义。因此,在伊斯兰教中,先知之光被认为是所有存在中的第一道光……救赎作为对修复的一种迫切要求而出现,而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它先于任何恶行而出现,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表达了救赎之于创造的优先性。”⑩因此,阿甘本认为,实际上拯救先于创造,“行动和生产的唯一合法性似乎来源于这样一种能力,即拯救已经做的和生产的一切。”(11)在创造与救赎的关系中,和它们之间既分割对立又密切联系这一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先后顺序,这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同样独特的,就是把这两种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时间,以及创造先于救赎但在现实中后于救赎,正如救赎后于创造但在现实中先于创造的那一节奏”(12)。 二、悬置、非功用性与停歇 如何清除或推翻边界所设立的对立机制呢?仅仅考古学式地追溯对立机制,并逆转对立双方的位置是不够的,就像阿甘本在评论当代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对立时所论述的,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在今天取代了创造与救赎之间的对立,经由宗教传统的世俗化过程,这些领域逐渐失去了对之前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全部记忆。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近于精神分裂般的特征。今天,这两种被割裂为不同主体的神圣行为迫切需要一个交汇点,迫切需要一道跨越冷漠的门槛,从而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统一性。它们通过互换角色实现了这一点,但这其实仍然是分裂的。“因为,批评家成了‘监护人’,为了模仿艺术家已经放弃的创造工作,不经意地取代了艺术家的地位,而已经没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则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拯救工作,尽管不再有任何东西需要拯救。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创造和救赎都不再触及它们之间割舍不断、爱恨交织的印记。”(13) 在探讨复活之后的荣耀的身体问题时,阿甘本从另外一个方面触及了这一问题。荣耀的身体的问题,也就是在天国中得到复活的身体的本质和特征问题,在宗教神学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阿甘本以荣耀的身体为范式,探讨了人类身体的形象和可能的使用方式问题。荣耀的身体遭遇的最大挑战是生殖和抚育问题,因为在宗教传统中,复活的身体不再具有这些实际的功能,那么如何解释荣耀的身体还具有和这些功能相关的器官呢?在神学的阐释传统中,这些器官不可能是无用的、多余的,因为在完美人性的状态中,没有什么是多余的。阿奎那的策略是,使器官与其特定的生理功能区分开来,从而处于某种悬置状态,而悬置的器官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展示的功能,它展现了本身的善,也就是说,虽然每个器官有其生理功能,但生理功能没有实现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处了,它展示了原本具有的生理功能。阿甘本认为,正是在这里,身体的其他使用方式第一次得到了阐述,并因此提出了他关于非功用性(inoperality)(14)的理论。“就像在广告和色情图片中,商业或身体的拟像只具展示性而毫无实际用处,它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施展了其诱惑力,因此,复活中被闲置的性器官将展现生育的潜能或善。荣耀的身体是明示的身体,它只具有展示性功能,而不具有实际功能。在这一意义上,荣耀是与无功用性(inoperality)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5) 基于荣耀的身体的这一悬置的、非功用性的器官,阿甘本探讨了对身体的不同使用方式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悬置的器官和工具并不意味着另一种使用方式,相反,它表明它的存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用途,也就是说,超出了原有的对立框架,并因此带来了消解这一异化的对立框架的可能性。“就像丢勒作品中散落在忧郁天使脚边的各种人类工具,也像孩子们游戏之后散落一地的玩具,脱离了使用功能的客体成了谜,甚至使人不安。同样,复活之人的身体中永不再使用的器官——即使它们展现了人类特有的生育功能——并不表现这些器官的其他用途。复活之人的明示的身体,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真实和‘有机’,其实外在于任何可能的使用领域。”(16)在这里,阿甘本借鉴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的“无用哲学”对非功用性问题进行了阐述。佐恩-雷特尔通过对那不勒斯渔民尽力驾驭小摩托艇、司机努力发动废旧汽车的观察,提出了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他开玩笑地称之为“无用哲学”,也就是说,只有当某物不再有用时,它才对那不勒斯人有用。他的意思是,那不勒斯人总是在技术工具和机器坏了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它们。一个完整的运行良好的事物总是让那不勒斯人烦恼,因此他们总是回避它。并且,通过把木块推到合适的位置,通过在合适的时机顺手做一些小的调整,那不勒斯人使他们的工具按照他们的意愿发挥作用。佐恩-雷特尔认为,这一行为包含了一种比我们日常的技术范式更高的范式:当人们能够对机器盲目、充满敌意的自动性提出反抗,并学会如何把它们应用到未知的领域和使用中去时,真正的技术才开始出现。他举的例子是卡普里岛大街上的年轻人把一个坏了的摩托引擎改装成了一个可以制作冰激凌的设备,在这个例子中,引擎继续转动,但完全基于新的欲望和新的需求。阿甘本认为,“无法使用(inoperality)在这里不是停留于自身,而是成为一种敞开,成为一种‘开门咒语’,指向一种新的使用方式的可能性”。(17) 在荣耀的身体中,器官与其生理功能之间的分离第一次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对原有边界的悬置发生了,在这里原本可以打开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但宗教神学却在此止步不前,它把这种分离移置于神圣领域,使它本身崇高化,而不朝向任何可能性。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对非功用性(inoperality)的展示被置换成了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在其位置上,我们找到的是荣耀,它被视为非功用性在特定领域的凸显。对器官脱离其生理功能的展示或空洞地重复其功能,这无非是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正如罗马凯旋中胜利的将军展示其武器和勋章,它们既是其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其荣耀的方式。复活之人的性器官和肠道仅仅是神圣荣耀镌刻在其罩袍之上的秘密符号和象征花纹。”(18)荣耀不过是在一个特殊领域(即宗教神圣领域)把非功用性独立了出来,用这一方式,原本朝向一种新的使用方式的可能性,现在被转化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阿甘本在此也对常见的编年史进行了批判,认为并不是宗教现象是起源,后来才出现了世俗化,而是教会和神职人员在某一时刻捕获了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在这一时刻宗教介入进来,把悬置和变得失去作用的人类活动独立出来,移置到神圣领域。在这里,阿甘本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宗教的解读,列维-斯特劳斯把我们常用的基本宗教概念解读为能指过剩,认为它们本身是空洞的,并因此可以负载各种象征性内容,即具有“零度象征价值”的能指,对应于某些人类活动和客体,宗教通过仪式性机制使其悬置,把它们分离出来,并重新加以符码化。 宗教把这一悬置行为仪式化,使其变成一个静止的姿态,使其成为上帝的荣耀的象征;而阿甘本所提倡的非功用性(inoperality)则强调,这一悬置是一种敞开,它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停止了原有的行为或对立模式,使其失去效力,因而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但这种新的可能性不是对旧的对立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旧的对立的一种展示。“这里要做的是使任何朝向某个目的的行为实践变得无效,从而开启一种新的使用方式,这不是对旧的使用方式的废弃,而是始终立足于旧的使用方式并使它呈现出来。”(19)因此,赤裸的、单纯的人类身体在这里不是被移置于一个更崇高的实在领域;相反,它是被从一种曾使它与自身相分离的巫术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获得了通向自身真理的途径。这种使身体与自身相分离的巫术,也就是附加在身体上的各种边界及其机制,而悬置并展示这些机制,则是破除这些边界的一个切入口,是导向新的可能性的入口。因此,在阿甘本看来,真正荣耀的身体不是他者更为机敏、优美,更具光辉和精神性的身体;它就是身体本身,“这时非功用性去除了身体上的魔咒,并使它朝向一种新的可能的公共用途”(20)。 在荣耀的身体中,神学阻碍了身体通向真理的途径,但神学也往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范式,正如阿甘本所说的,“具有深厚神学渊源的分析往往是切中要害的”(21)。他认为关键在于既在神学复杂性中对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又超越神学视野。正是在犹太教传统中,阿甘本发掘出了悬置、停顿和非功用性的神学范式,他认为在犹太教的安息日中,神圣的不是创造,而是所有工作的停顿。他引用了《圣经》中的两段话:“第七日,上帝完成了造物的工作,就在第七日放下一切工作安歇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上帝在这一日安歇,放下了创造万物的一切工作。”(22)“要谨记安息日,奉为圣日。六天要从事劳动,做一切工作。但第七天是耶和华你上帝所定的安息日。”(23)在这里,以色列人在庆祝安息日时的情形被称为menuchah,阿甘本称之为安歇,即inoperality。安歇的不仅是世人,也包括上帝。犹太教传统界定了安息日不能从事的活动,它们广泛地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整个领域。阿甘本认为,这并不是说人们必须在安息日弃绝一切活动,问题的关键只在于这些活动是否以生产为目的。因此,在犹太教传统看来,不具建设性含义的纯粹破坏性行动并不构成被禁止的行为,因此也不被视为是对安息日静养的一种违背。做饭和点火是禁止的,但节日大餐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界定庆典的安歇不是不活动和弃绝一切活动,而是敬奉,一种特定的行为和生活模式”(24)。 这一节日范式的意义是什么呢?阿甘本认为,在当代生活中,我们尽管还在庆祝各种节日,但这一神学范式所包含的意义已经失落了,他从普鲁塔克在《宴饮问题》中记述的“驱逐贪食”的庆典仪式来追溯了这一庆典模式的意义。他认为,在这一庆典仪式中,赶走象征“贪食”的奴隶,并不是为了安抚上帝,从而获得物质的财富和丰盛的食物,“因为被驱逐的不是饥饿和灾荒,而是‘公牛般的饥饿’:这一兽类般的永不能满足的进食”(25),因此,赶走“贪食的”奴隶意味着驱逐某种形式的贪食(像野兽一样贪吃或狼吞虎咽,以满足某种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无法满足的食欲),从而为另一种进食模式腾出空间,也就是说,使贪食失去作用。因此,在阿甘本看来,吃不再是某种被禁止的行为,它不再朝向某一目标,而是一种无功用性和安歇。 阿甘本认为,在现代语言中,古希腊术语“公牛般的饥饿”仍然在医学术语中保留着,它逐渐指代一种饮食方面的紊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饮食紊乱已经在当代社会中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这一紊乱的症状典型地表现为反复地暴饮暴食,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并且在暴饮暴食后立即催吐,强行吐出吃下的东西。催吐,是指暴饮暴食症患者把手指伸到喉咙深处,或者通过服用催吐剂,把之前吃的东西强行吐出来。阿甘本认为,在暴饮暴食症研究的一开始,求助催吐手段就被视为诊断这一病症的必要部分,尽管确实有一小部分病患没有发生过这一行为。催吐,这一看上去似乎与暴饮暴食完全相反的行为,为什么会被视为暴饮暴食症诊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呢?阿甘本认为,催吐体现了某种净化的功能,通过催吐,暴饮暴食症患者似乎是在消解他们身上的公牛般的饥饿,从而用某种方式净化自己。在这里,起作用的同样是悬置、非功用性和停歇机制。暴饮暴食症患者吃下食物后立即用催吐的方式吐出吃下的东西,同样是把动物性的饥饿吐出来,使其失去作用。 因此,阿甘本所提出的悬置、非功用性和停歇是指通过有意为之的停顿,使之前发生作用的机制展现出来,从而使这一机制失去作用。就像在安歇与安息日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安歇既不是庆典日的结果也不是其前提(劳动的弃绝),而是与庆典性本身相吻合的,因为它恰恰使人类的姿态、行为和劳作中性化了,使其失去了作用”(26)。同时,这一停歇(inoperality)不是简单的对之前的机制的弃绝,而是前者的完美实现,在阐述安息日、工作和安歇之间的接近关系和几乎相互的内在性问题时,阿甘本引述了拉什对《创世纪》的评论,认为在安息的第七日,也有某种东西被创造出来,那就是工作的停顿、安歇本身。“甚至是工作的停歇也属于创造;它是上帝的劳作。但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作,因为它使所有的工作都失去了作用,使所有其他的工作都停歇了。”(27)原来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被从“现实生活”、从工作日界定它的理性和目标中解放了出来,暂时被悬置了,因此,“吃,不是为了果腹;穿,不是为了蔽体或防寒;醒来,不是为了工作;走路,不是为了去某个地方,说话,不是为了交流信息;交换物品,不是为了买卖”(28)。阿甘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庆典日都包含了这一悬置因素,并主要地从人们工作的停歇开始。通过这一方式,庆典揭示性地把自己表现为是对现有价值和权力的一种消解。同样,同时代人既依附于时代、又与其保持距离的这一奇特关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29),也是一种悬置与非功用性的关系。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同时代人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的时代。 在阿甘本这一关于悬置、非功用性和停歇的理论框架中,悬置和非功用性不是逆转和推翻现有的权力关系,而是使其体制机制呈现出来,对其进行反思,从而打开可能性空间。这与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拒绝工作”这一思想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作为一个基本的口号,“拒绝工作”不是像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是工人自发地在生产线上捣毁机器,而是说拒绝在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作,通过这种拒绝和停止工作,来质疑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体制,从而打开新的可能性。正像迈克尔·哈特教授在谈论当代对“非物质劳动”的颂扬时,认为我们对“非物质劳动”的积极性的肯定应当与“拒绝工作”的传统联系起来,对非物质劳动的肯定不应当简单地混同于提倡回到工作中去,回到劳动中去,提倡享受工作,而是对现有劳动形式的拒绝。他认为,“任何对劳动的肯定首先都来自于60年代工人运动中‘拒绝工作’这一传统。激进工人总是试图超越工作,把自己从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30)。因此,与“拒绝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对“真正的”工作的一种重新确认和对日常异化体制的揭示。在写作于1965年的《拒绝的策略》一文中,马里奥·特龙蒂对当时这一思想作出了解释,认为“停止工作意味着对资本的命令的拒绝,这里的资本是生产的组织者。停止工作是在特定时刻说‘不’的一种方式,是对于被设定的具体劳动的拒绝;是工作过程的暂时中断,作为一种持续的威胁,其内容来源于价值创造过程”。(31)“拒绝工作”反对传统工会斗争模式,认为它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要求分享劳动成果,实质是对既有秩序的肯定,成为了现有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而“拒绝工作”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设置了一系列危机,危机的每一时刻都需要发挥策略性,以便为新的飞跃打开大门。 “拒绝工作”的理念也是跟这一时期左翼特定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即他们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史观。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是创造历史的积极力量,工人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利用或者说收编了工人自发抵抗的力量,从而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这一自下而上的史观出发,这一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从各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反思,比如对现有的自上而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反思等。(32)这一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也能为我们理解阿甘本的一些理论观点提供某些线索,例如在创造与救赎的问题上,他更强调救赎,因为救赎是托付给人类的任务。阿甘本通过考古学式的研究发现,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尽管拯救的工作在重要性上先于创造,但却被托付给一个造物。他认为,“这里真正让人惊奇的是,对创造的救赎不是被委托给了创造者(也不是委托给直接来源于创造性力量的天使),而是托付给了一个造物。这意味着创造和救赎仍然是相异的,也就是说内在于我们的创造性原则并不能拯救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然而,可能拯救创造的或者说必须拯救创造的东西源自于这一原则,在地位和尊严上排在前面的实际上来源于在它之后的。”(33)因此,拯救世界的将不是精神性的、天使的力量,而是更为谦卑的肉体性力量,人类作为造物拥有的力量。 三、潜能与拯救 阿甘本批评宗教把悬置和非功用性剥离出来,放到一个独立的神圣领域,使其静止化,“用这一方式,原本朝向一种新的使用方式的可能性,现在被转化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34),从而阻碍了向新的可能性的敞开。那么,这一新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呢?阿甘本在不同的文章中用不同的概念来对此进行探讨,但从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如果土地测量员质疑的那些边界和界线不再有效,那么“真实世界”又会发生什么呢?阿甘本只是提到,这就是土地测量员被允许惊鸿一瞥的东西,但语焉不详。在《裸体》中,他也谈到,对裸体经验中美的去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冲淡神学机制,使我们超越恩典的荣光和本性堕落的幻觉,看见一个单纯的、隐秘的人类身体。而在《公牛般的饥饿》中,阿甘本认为,在庆典中日常的人类活动被悬置和变得失去功用,“其目的不是要把这些行为神圣化,变得不可触及,而是相反,使它们朝向一种新的——或更古老的——符合安息日精神的可能用途。”(35)但具体的可能用途从来没有在阿甘本的论述中出现过。而在《无人格的身份》中,阿甘本提出,我们必须为寻找人类的新形象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没有尽力去看清楚这一形象”(36)。在《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章》中,阿甘本甚至对这一突然闪现的新世界进行了质疑,正如他对无知领域所作的界定,“这里重要的不是一种秘密学说或高深的科学,也不是我们未知的某一知识。无知领域实际上可能并不包含任何特殊的东西……也许无知领域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其姿态。”(37) 那么,怎么来理解阿甘本所说的这种姿态呢?在阿甘本看来,重要的不是未来新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我们打断现状的行动和能力,是悬置和停歇行为本身所包含的积极力量。这也就是他在分析何谓同时代人时所说的,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感知这种黑暗并不是一种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意味着一种行动和一种独特能力。”(38)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热衷于感知黑暗呢?阿甘本从当代的天体物理学对此作出了解释:我们所仰望的夜空群星璀璨,而围绕群星的是浓密的暗夜,但暗夜并不是虚空,它也是由光构成的。“在一个无限扩张的宇宙中,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39)同时代人就是感知时代之黑暗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同时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这就是同时代的含义”(40)。 暗夜不是光明的对立面,不是光的缺乏,而是尚未抵达的光,这种对黑暗的感知也与阿甘本对知识的理解联系在一起。阿甘本认为,我们对事物无知的方式可能和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恰恰是我们对事物的无知界定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阐明无知领域可能恰恰是构成我们所有知识的条件——同时也是其试金石。强调无知领域并不意味着要对其进行探索,正像阿甘本所说的,无知领域甚至可能并不包含任何特殊的东西,而是要在无知与知的这一关系中对知识领域进行重新思考,“它意味着使自己与无知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使一种知识的缺场指导并伴随我们的举动,使一种顽固的沉默清晰地回应我们的言说。”(41) 阿甘本也用这一关系来重新解释了潜能概念,潜能不仅仅是一种可以去做的能力,它同时也是一种能不去做的能力,在结构上也是一种非潜能。“非潜能”在这里并不仅仅是指潜能的缺乏,没有能力去做,更重要的是指“有能力不去做”,可以不施展个人的潜能。阿甘本认为,正是一切潜能特有的这一矛盾——它总是一种在或不在、为或不为的权力——界定了人类的潜能。这就是说,人类作为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生物,有能力做某事,也可以不做,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界定个人行动地位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能力范围,而首要的是在与自身的可能性关系中使自己可以有所不为的能力”(42)。阿甘本并因此对当代社会中的权力机制进行了批判,认为德勒兹所批判的权力只是把人与其所能隔离了开来,但当前所谓的“民主”权力更阴险的方式是将人与其所不能隔离了开来,导致无所不能概念的泛滥。“今天的人们被与其所不能完全隔离了开来,被剥夺了能够不做什么的体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于是他总是愉快地重复‘没问题’,不负责任地回答‘我能行’,而正是在这些时刻,他本应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对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权力和过程束手无策了。不是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而是对自己的无能盲目无知,不是对自己能够做什么盲目,而是对自己不能做什么,或者说,能够不做什么盲目无知。”(43)而每个人可以胜任任何岗位的这种灵活性正是新自由主义资本本身的逻辑,它是今天的市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现在被内化于每个个体的主体性中,成为日常行为的准则。 阿甘本认为,那些被与自己的所能隔离开的人,仍然可以作出抵抗,仍然可以有所不为。但那些与自己的非潜能隔离开的人,却因而丧失了抵抗能力。那么,除了与同时代保持距离,并死死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之外,如何实现拯救呢?在阿甘本看来,拯救的对象并不是创造出来的一切,不是被创造的存在,也不是潜能,因为它除了是对创造的消解外没有确切内容,而是把创造与潜能结合在一起的悬置行为本身,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悬置和非功用性,使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范式显示出来,这一显示既是对原有对立的悬置,也是一种开启,这一悬置、展示和开启本身构成了一个张力场域。这一场域的意义,正如他在探讨荣耀的身体问题时所说的,“身体的新的使用方式只有在以下条件中才是可能的,即把非功用性独立出来,成功地在一个位置、一个姿势中把机能的运行与非运行、实际的身体与荣耀的身体、功用及其悬置结合起来。生理机能、非功用性和新的使用方式共存于身体的某一张力领域中,无法脱离这一领域。这是因为非功用性不是惰性;相反,它使行为中已经表现出来的潜能呈现出来。它不是在非功用性中失效的潜能,而是已经铭刻在器官的机能运行中并已分离出来的目标和模式。正是这一潜能,才能造就具有可能的新用途的器官,造就生理机能被悬置并失去作用的身体器官。”(44)在论述创造与拯救的关系时,他使用的是新门槛这一意象:“造物和潜能现在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门槛,在这里二者再也无法区分开来。这意味着当创造和拯救在无法拯救之物中重合时,人类和神圣行为的终极形象就出现了。因此,不可拯救之物,是指创造和救赎、行动和静观、运作和停顿每一时刻都并存于同一存在(或同一非存在)中,不留下任何剩余。”(45)在这里,拯救开启并“拯救”自身。当拯救把已经逝去的、无法忘怀的一切聚集于自身时,“这一工作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当然,它仍然是拯救,因为和创造相反,拯救是永恒的。尽管拯救比创造更持久,但它的迫切需求没有在拯救之物中耗尽,而是遗失在了不可拯救之物中。拯救诞生于行将迫近但没有实现的创造,终结于无法预测、不再有目标的救赎。”(46)正是因为没有目标,或者说取消了之前的目标,我们才可以说,一切皆有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理论家,阿甘本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对未来的新世界提出了构想,他提供的只是反抗的策略,他的分析永远立足于此时此刻,就像同时代人死死地盯住自己时代的黑暗,阿甘本的意义就在于此。 注释: ①Giorgio Agamben,Nud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66. ②Giorgio Agamben,Nudities,p.17. ③Ibid.,p.19. ④Ibid.,p.24. ⑤Ibid.,p.23. ⑥Ibid.,p.23. ⑦Ibid.,p.24. ⑧Ibid.,p.36. ⑨Giorgio Agamben,Nudities,p.4. ⑩Ibid.,p.2. (11)Ibid.,p.3. (12)Ibid.,p.4. (13)Ibid.,pp.6-7. (14)阿甘本在Nudities一书的各章中频繁地使用了inoperality一词,因为行文和语境的不同,我们分别译为非功用性、无功用性、停歇和安歇,它都意指某物不再使用,某些行为不再发生,这和他所说的另一个词汇——悬置是对应的。在类似语境中,他还交替使用的另一个词汇neutralize,消解、中和,指对原有各种权力机制包括神学机制的消解。 (15)Giorgio Agamben,Nudities,p.98. (16)Giorgio Agamben,Nudities,p.99. (17)Ibid.,p.100. (18)Ibid.,p.100. (19)Ibid.,p.102. (20)Giorgio Agamben,Nudities,p.102. (21)Ibid.,p.75. (22)《圣经·创世纪》(2:2-3)。 (23)《圣经·出埃及记》(20:8-10)。 (24)Giorgio Agamben,Nudities,p.105. (25)Ibid.,p.107. (26)Ibid.,p.109. (27)Giorgio Agamben,Nudities,p.110. (28)Ibid.,p.111. (29)Ibid.,p.11. (30)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Edt.,Radical Thought in Ital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6. (31)Mario Tronti,"The Strategy of Refusal",http://libcom.org/library/strategy-refusal-mario-tronti. (32)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Edt.,Radical Thought in Italy,pp.81-95. (33)Giorgio Agamben,Nudities,p.5. (34)Ibid.p.101. (35)Ibid.p.112. (36)Ibid.p.54. (37)Ibid.p.114. (38)Ibid.p.13. (39)Ibid.p.14. (40)Ibid.p.14. (41)Ibid.p.114. (42)Giorgio Agamben,Nudities,p.44. (43)Ibid.,p.44. (44)Ibid.,p.102. (45)Ibid.,p.8. (46)Ibid.,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