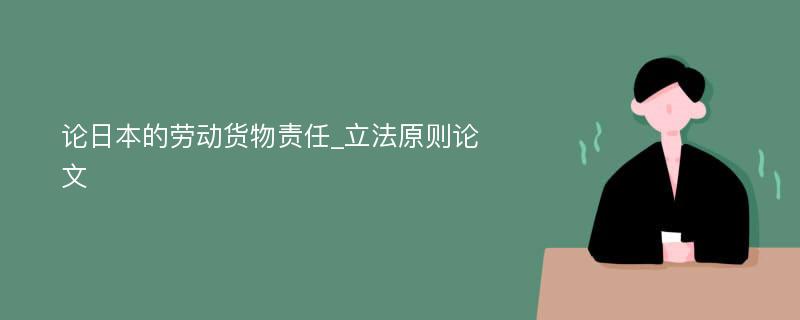
论日本的工作物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责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民法第717条对工作物责任做了如下规定:“1.因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的瑕疵,致他人产生损害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占有人为防止损害发生已尽了必要注意时,损害应由所有人赔偿。2.前款规定,准用于竹木的栽植或支撑有瑕疵情形。3.于前两款情形,就损害原因另有责任者时,占有人或所有人可以对其行使求偿权。”这是日本民法中唯一一条有关物的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日本民法从立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这近百年中,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高度危险、环境污染等因物而引起的侵权事故,时常使民法陷入窘迫之地。于是,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问题,民法学者开始逐渐扩大对第717条的解释,审判部门在审理案件时,也在不断引用第717条作为判决的直接法律依据。从而,使得第717条的内容早已超出立法者当初所规定的含义,土地工作物的内涵在逐渐淡化。与此同时,第717条随着社会的发展,承担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在日本民法特殊侵权责任制度中占据最为显要的地位。
一 工作物责任的适用范围
工作物责任是一种古老的侵权责任,罗马法中就有关于它的规定,并把它归属于准私法范畴之列,称之为“放置物或悬挂物致害”责任。主要适用于建筑物的外部堆置、悬挂的其他物品,并且该建筑物要面临人行街道、公共道路。
《日本民法典》第717条称“土地工作物”,并把“竹木的栽植或支掌”也纳入到了该范围。显然,日本民法立法者注意到了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区别,既然建筑物也属于土地工作物的一种,因此,不再单列建筑物,而统称为“土地工作物”。并且,竹木虽然与建筑物等无生命的土地工作物不同,但它也具有与土地相连、人工因素的特性,因此,也是土地工作物,适用土地工作物的责任。
土地工作物按照日本早期司法判例所确定的含义为“象建筑物墙壁、地窖那样的与土地相连接而建造的物”(大判大正元年12月6日民录18辑1022页);或曰“与土地相连接,由人工作业所建造的物”(大判昭和3年6月7日民集7卷443页)。从这两个判例为土地工作物所确定的含义可以看出,构成土地工作物的物必须具备两个要件:(1)与土地相连接;(2)由人工建造。据此,以下设施逐渐在判例中被列为土地工作物,而适用第717条,承担土地工作物责任。建筑物(大阪地判昭和30年4月26日下民6卷4号856页)、建筑物本身的组成部分:电梯、自动扶梯(东京地判昭和42年9月28日判夕215号168页)、悬崖的壅壁(大判昭和3年6月7日民集7卷443页)、电线杆(大判昭和7年4月11日民集11卷609页)以及桥梁、道路、隧道、堤防、矿山的坑道、游泳池等等;与此同时,凡不具备上述两个要件的,法院也通过判例排除了适用第717条的可能,如与建筑物相联接、与土地不联接的工场内的机械(大判大正元年12月6日民录18辑1022页)等等被确认为不属于土地工作物范畴。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展,特别是近代企业活动高度危险化的发展,为确保受害者能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救济,判例和学说对土地工作物的解释与前期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土地工作物概念所囊括的内涵不断被扩充,它所具有的两个要件也被不断淡化。原先曾被判例排除在土地工作物之外的情况,现在又被判例确认为土地工作物。具体讲,土地工作物的扩充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筑物内部放置的机器设备:有学者对大正元年12月6日大判的判例提出异议,认为把机械放置在建筑物中,与放置在土地上就导致不同的责任后果,是不合理的,并提出:与土地是否相联接并不是区别工作物责任的本质所在,工场内的机械一般来讲,在实际上是与建筑物作为一体的,因此,它与建筑物应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土地工作物。在此学说的影响下,司法审判中,工场建筑物内旋转的旋盘(奈良地葛城支判昭和43年3月29日判时539号58页)、石腊槽以及燃烧炉(东京地判昭和45年12月4日判时627号54页)、制面机(东京高判昭和47年11月29日判时692号14页)等等被确认为土地工作物。
(2)普通机器设备:按照立法者给土地工作物的含义,工作物必须与土地相联接,即必须具有固定性、接着性。但是,这一点现在已逐渐被淡化。虽与土地相连,但很容易被移动,本身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机器、设备已被作为土地工作物而适用第717条。这样的判例有:大型筒装瓦斯容器(长野地松本支判昭和40年11月11日判时427号117页)、自动贩卖机(东京地判昭和50年2月4日判时793号68页)等等。
(3)与土地自身为一体的设施:近来,象高尔夫球场(神户地伊丹支判昭和47年4月17日判时682号52页)、滑雪场(长野地判昭和45年3月24日判时607号62页)以及学校的运动场、游园地等等利用自然地形,在上稍加整理、保养或种植一些草皮、树木等,土地本身即是设施主体的,也被列为了土地工作物。这种土地工作物与建筑物等相比,其人工因素显然已减轻了许多。
(4)危险物、交通设施:把铁路和道岔作为保安措施,与轨道设施视为一体而适用工作物责任的判例,在地方法院及最高法院已出现过多次,如东京地判昭和26年8月15日判例(下级民集3卷1003页)、最判昭和46年4月23日判例(民集25.3.351)等等。
(5)环境公害设施:伴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公害问题已日趋严重,由此所引起的损害的法律适用问题,司法判例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生产塑胶人形玩具的工场,其溶化石蜡槽被作为危险设施与作业场地的建筑物一起适用土地工作物责任(东京地判昭和45年12月4日判时627事情54页)。在渡金工场流出的有毒废液把养鱼场的鲤鱼毒死的事件中,工场内的过滤装置也被确认为土地工作物,而适用第717条。[①]
除以上外,还有学者认为,伴随着企业的无过失责任化,土地工作物还应该逐阶段地再做进一步的扩大解释。即第一阶段,企业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机器设备全部适用第717条;第二阶段,不以土地为基础的汽车、飞机等运输业也应适用土地工作物责任;第三阶段,在企业中,因从事机械劳动的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损害,应看作是企业灾害,不适用第715条使用人责任,而适用第717条土地工作物责任,直接追究企业自身的责任。对于这种学说,日本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土地工作物责任的扩大解释是有一定界限的,不能无限制地任意脱离开它的原意,而把与土地毫不相关的纯粹的动产责任也囊括在其中。[②]
二 工作物责任与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的关系
工作物责任与《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的关系问题,究其本质即工作物当中,属于国家或国家机关所有或管理的那部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是适用民法中的工作物责任,还是直接引用《国家赔偿法》作为法律依据。对此,究竟采用哪种模式,日本法律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态度。
在《国家赔偿法》制定颁布以前,公共营造物因设置、保存瑕疵而造成他人损害时,一律适用民法第717条工作物责任的规定。[③]1947年10月27日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该法第2条规定:“(1)道路、河川以及其他公共营造物因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而致他人损伤时,国家或者公共团体对此负赔偿责任。(2)在前项场合下,如果损害是由其他人造成时,国家、公共团体有追偿权。”这样,道路、桥梁、政府办公楼、公立学校的设施等公共营造物再出现侵权事故后,其直接法律依据就由民法的第717条变更为《国家赔偿法》第2条。那么,民法第717条与《国家赔偿法》第2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对于上述问题,日本民法学者有人认为:《国家赔偿法》第2条是民法第717条的特别法[④]。还有学者提出:《国家赔偿法》第2条公共营造物责任从根本上与行使国家权力并没有关系,还应该把它看作是私法上的责任,其内容与民法第717条没有差别。《国家赔偿法》只不过把它明确一下而已。公共团体的设施造成损害适用《国家赔偿法》第2条,私人的设施造成损害适用民法第717条。[⑤]
但是,我们对比这两条法律规定,正象日本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首先,适用范围不同。《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营造物与民法第717条的土地工作物相比,它不仅包括房屋、桥梁等不动产,也包括飞机(东京地判昭和55年2月18日判时957号69页)、警察用的手枪(大阪高判昭和62年11月27日判时1275号62页),此外,还包括河川、湖泊、海岸等没有人工因素的自然的公共设施。[⑥]因此,前者适用的客体比后者范围要广。其次,民法第717条中占有者在防止损害发生尽到必要注意时,可以免责。而《国家赔偿法》第2条中没有免责事由,公共营造物的责任人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因此,公共营造物的责任人比私有不动产的责任人承担责任的程度要高。
由上可见,日本对公共设施,在前期采用的是民法体例,后期改为行政法体例。占有人承担责任的原则也由推定过失提高为无过失责任。
三 工作物责任的归责依据
纵观各国民事立法及判例学说,关于工作物责任的归责依据,各国规定不同,学者们也有争议。但将它们加以分类,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无过失责任。(二)推定过失责任。(三)混合责任(折衷责任)。在这种责任类型下又可分为两种:(1)不同的责任人承担不同的责任。(2)工作物占有人针对不同的受害人承担不同的责任。
日本民法学者对工作物责任归责依据,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学说。下面我们依次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进行考察。
日本旧民法仿效法国民法,在财产编第375条中,对工作物责任曾经规定: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的所有者对此等工作物因欠缺修缮或建造有瑕疵而坍塌所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可见,此时法律只要求工作物所有者承担责任,占有者不承担责任。而且,对所有者没有免责理由,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
起草现行民法时,法典调查会提出修改此条。在修改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参照了其他各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其中,受德国法律的影响最大。首先,对于建筑物的提法认为太狭窄,以规定一般工作物为好。其次,损害赔偿的责任者规定以能防止损害发生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其效果更好。基于以上认识,在第121次法典调查会上(明治28年10月7日),草案第725条规定:(1)土地工作物因设置或保管有瑕疵而致他人损害时,该工作物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2)前项规定适用于竹木的栽植和支持有瑕疵的场合。(3)在前两项情形下,损害原因另有责任者时,占有人可以对其行使追偿权。该草案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在审议过程中又作了两处修改:(1)在草案第一项后附加了但书,使占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免责,所有人承担最终赔偿责任。(2)与前项修正相联系,在第三项中追加了所有人的追偿权。其中第一点修正是在以下背景下出台的:草案讨论中,有人对不承认占有人免责事由提出批评,认为在日本房屋租赁的实际情况中,占有人一般财力都有限,如果只让占有人承担责任,对保护受害者非常不利。[⑦]由此,经修正后成为现行法。对于该条的侵权赔偿责任依据原则,起草委员穗绩陈重作了5点解释,其大意为:本条的规定还是以过失责任原则为基础的。以设置、保管有瑕疵为要件即是以过失为前提,而不问是谁的过失。它既可以是自己的过失,也可以是前所有人或前占有人的过失。只不过在前种情况下,直接依据过失责任原则,而在后种情况下,责任人本身没有过失,而替有过失的他人承担责任,这也只是对过失责任原则作稍稍扩大解释的结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公益上的理由”,便于受害人能及时得到赔偿,同时也督促占有人提高注意,及时防止损害的发生。总而言之,整个不法行为法以过失责任为原则,工作物责任也不例外。受立法者上述思想的影响,在立法后的初期,学者们也都多赞成工作物责任为过失责任原则的观点。[⑧]
之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生产经营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附属产品:危险、灾害频繁发生,并由此给人们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加强对广大受害者的保护。该问题使得工作物过失责任原则的观点受到冲击。恰逢此时,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德国的危险责任理论传入日本,由此,日本学者受到很大影响,并把工作物过失责任原则逐渐向无过失责任方面过渡。到大正元年,以危险责任理论为根据的无过失责任原则已占据主流。[⑨]
民法第717条并没有要求以过失为责任构成要件,只是占有人在尽到必要注意时,可以免责。因此,占有人承担的是介于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之间的一种中间责任,也叫过错推定责任。而所有人由于没有免责理由,所以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这种观点现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持有。至于为什么对工作物责任要比一般侵权责任加重责任,冈松博士提出,是基于报偿原则。既然物的占有人、所有人因物的利用而取得利益,那么,因物而产生的损害也应该负责。我妻荣博士等学者则提出:是基于危险责任原则。管理具有危险性的物的占有人、所有人平时对危险的发生应倾注足够的注意,而一旦危险发生,产生损害,其占有人、所有人就应该负责。这样可以促使占有人、所有人加倍小心,以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同样承认危险责任理论的加藤教授则认为:工作物责任并不是完全的无过失责任,应该把它看作是由客观的瑕疵而推定其主观有过错,或曰主观的过失产生了客观的瑕疵的定型化。
上述学说中危险责任理论对司法实践影响最大,下级法院审判中已在根据危险责任的观点审理案件(札幌地判昭和48年1月31日判时713号116页等)。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随着产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军工的发展,伴随有危险性的设施、设备在逐渐增加。而日本学者又认为,基于危险责任原则再另行在民法中规定特别责任的必要性又不是太大,因此就把第717条当作了特别责任的典范,以不断更新扩大对它的解释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以至到现在为止,工作物责任与立法阶段的含义相比,已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已有学者在工作物责任与无过失责任之间划等号,即“工作物责任=无过失责任”[⑩]。
由上可见,日本民法对工作物责任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由无过失责任到过失责任,再到推定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四 工作物责任构成要件中的瑕疵
按照通说,日本工作物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属工作物范畴。(2)工作物设置、保管有瑕疵。(3)损害与工作物瑕疵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这三要件中,工作物瑕疵最为关键。
工作物瑕疵最早被解释为工作物欠缺自身通常所应具备的性能,即性状瑕疵。它可以分为设置瑕疵和保管瑕疵两种。设置瑕疵是指工作物在设置时就已经存在的瑕疵;保管瑕疵是指在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瑕疵。瑕疵的这两种分类在实际上对审理案件意义不大。
但是,后来的判例逐渐突破上述性状瑕疵的瑕疵概念。工作物在欠缺安全设施和保障的场合下也被确认为有瑕疵。最判昭和46年4月23日(民集25卷3号351页)判例的判决中写道:在列车通行的专用轨道和道路交叉地段的道岔口,是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和道路交通安全而设立的。因此,为了完全发挥它的作用,应该设置相应的保安设施,并且,这些保安设施要和道岔口的轨道设施一起作为工作物来考虑。如果应该设置的保安设施而没有设置,即被认定作为土地工作物的轨道设施的设置有瑕疵,而适用于第717条。[(11)]由此抽象出一般原理:对应工作物危险性的程度应设置防止损害发生的设施,以达到作为该工作物所应具有的完全性。否则,即被认为有瑕疵。而是否达到这种安全性要依据工作物设置的场合、技术的可能性、不良状况的性质和程度、受害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客观地具体判断。一般来讲,工作物危险性越高的,对其占有人、所以人采取防止损害的措施的要求也越高。[(12)]
与上述综合各种因素认定瑕疵的客观说相对应,近来,又有学者提出瑕疵=损害回避义务违反,即瑕疵义务违反说。植木哲教授通过对数个工作物判例的瑕疵认定的分析看到:判决书中大多有道路管理者违反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没有设置安全设施而引起事故等等的表述。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判例是在依据违反义务来判断瑕疵。国井和郎教授也认为:在一些判例中,虽然说是依据客观说判断瑕疵,但实际上都先假想一种适当的完全的状态,然后再以它为标准来判断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采取的,即没有瑕疵;没有采取的,即认定有瑕疵。因此,实际上是在以是否违反义务在判断瑕疵。同时指出,以违反义务说判断瑕疵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在因自然现象而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交通障碍的场合下,不能说欠缺通常所应具备的安全性而认定瑕疵,但却可以以没有采取避难对策,违反义务为根据认定瑕疵。因此,义务违反说比客观说扩大了瑕疵的范畴,这在实践中有积极意义。第二,以违反义务作为责任根据与侵权行为法体系相调和,具有理论意义。第三,它可以促使道路管理部门改善工作。
但是,对于上述义务违反说,大多数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1)道路案件中,法院尽可能地向受害者一方倾斜,而扩大占有人、所有人的责任。以它为范例推导出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2)义务违反说以必须具有高度注意(防止危险)的义务为前提。而实际上,法律对工作物占有人、所有人是否都规定有该义务是一个疑点;(3)把作为特殊侵权责任的工作物责任重新拉回到第709条一般侵权责任中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4)依据义务违反说,受害者要想得到赔偿,必须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工作物占有人、所以人具有该项义务,并且在实际中违反了该项义务。而这对受害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客观说仍占据通说地位,实践中也仍在以之为根据审理案件。[(13)]
五 工作物责任的责任主体
关于工作物责任的责任主体,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基本上有三种类型(1)所有人责任说。(2)占有人责任说。(3)折衷责任说。
依据日本民法第717条,工作物致损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占有人,在占有人为防止损害尽到必要注意时,所有人成为第二责任主体负责赔偿。因此,日本是采用折衷责任说。
占有人即依据物权法占有理论而享有占有权的人,它既包括直接占有人,也包括间接占有人(最判昭和31年12月18日民集10卷12号1559页)。但是,在原则上首先是以直接占有人为责任人。因为,只有他才是实际上支配工作物,并具有与防止损害发生有密切关系的人。直接占有人的责任被排除后,负有修缮义务的间接占有人成为责任人(东京地判昭和50年3月10日下级民集26卷1—4号284页)。
所有人,毫无疑问,即对工作物拥有所有权的人。但是,当所有人把该工作物让给第三人还未进行移转登记就发生责任事故时,是由现实所有人(受让人)负责赔偿,还是由名义上的所有人(转让人)负责赔偿就成了争论点。有学者认为,从受害者来讲,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比较明确,易追究责任。固应以名义所有权人为责任人;但另有学者认为,不法行为责任是在于实体权利而产生的,因此,应以现实所有权人为责任人。大阪地判昭和30年4月26日(下级民集6卷4号856页)判例确认了后种学说,认为通过买卖、赠与等法律行为转让工作物,即使还没有进行移转登记,出让人也不负工作物侵权赔偿责任。
此外,依据第717条第3款,占有人或所有人承担工作物侵权责任后,如果发生损害的原因有其他责任者时,如前占有人或前所有人对工作物保管不善等,占有人、所有人对其有求偿权。
六 工作物责任的免责事由
关于工作物责任的免责事由,日本民法第717条的表述为“为防止损害发生已尽了必要注意”。这是个非常抽象的标准。占有人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被认定为尽了必要注意,在现实中并不是很容易就能下结论。学者们认为,应结合工作物的种类、性质以及利用者接近工作物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等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一般来讲,危险性高的工作物,其被确认可以免责的情况越少。
在现实中,法院对于占有人证明自己尽了必要注意的证据很少确认,一般不承认可以免责。现有判例中,被确认免责的只有不可抗力,即完全是由于不可抗力而引起工作物致损时,占有人才可免责(名古屋地判昭和37年10月12日下民集13卷10号2059页)。虽有自然力的原因,但同时工作物也有瑕疵,两者竞合而发生事故时,对于因自然力而造成损害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免责,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假设没有自然力竞合、损害会减轻的场合下,应相对减免占有人的责任。
以上探讨了日本民法第717条工作物责任,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民法虽然立法较早,但是,民法学者及司法判例随着科学技术、企业产业化的发展,对第717条做了相应的扩大解释。因此,第717条在条文表述上虽然没有变化,但它所囊括的内容以及基本理论早已超出了立法者的意愿,而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工作物责任制度。
注释:
①吉村良一:《不法行为法》,日本有斐阁1995年10月版,第191页、第192页。
②前田达明:《现代法律学讲座14·民法Ⅵ2不法行为法》,日本青林书院新社昭和59年5月25日版,第161页、第162页。
③加藤一郎:《注释民法19债权10》,日本有斐阁昭和56年10月10日版,第308页。
④前田达明书第168页。
⑤加腾一郎:《不法行为》,日本有斐阁昭和54年8月30日版,第194页。
⑥吉村良一:《不法行为法》,日本有斐阁1995年10月10日版,第228页。
⑦加藤一郎:《注释民法19债权10》,有斐阁昭和56年10月10日版,第304页。
⑧星野英一:《民法讲座6事务管理·不当得利·不法行为》,有斐阁1995年5月30日版,第530—539页。
⑨同上544页。
⑩吉村良一:《不法行为法》,有斐阁1995年10月10日版,第189页。
(11)川井健:《不法行为法》,日本评论社1995年5月版,第172页。
(12)好美清光:《基本判例双书民法(债权)》,同文馆昭和57年4月30日版,第312页、第313页。
(13)森岛昭夫:《不法行为法讲义》,有斐阁昭和62年3月25日版,参见第三章工作物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