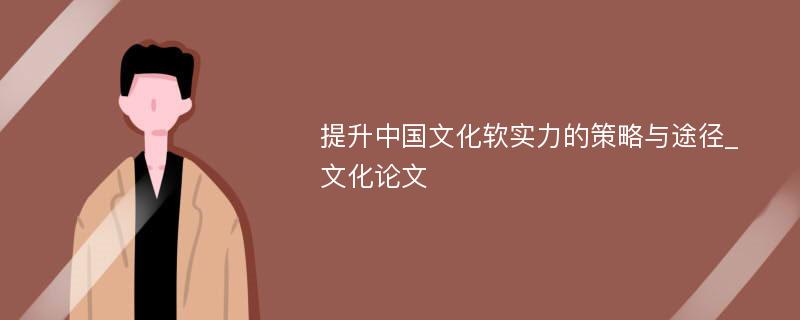
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策略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路径论文,实力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1-0041-05
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指文化自身蕴涵的内在力量,而且还包括一种能够被他者的认同、被别人接受的文化思想。所以,文化软实力并不是一个自我确认、自我命名的文化属性,而是一种通过广泛传播之后才能够兑现的文化力量。为此,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是一种“内外兼修”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我们在理念上明确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涵,而且还需要我们在方法和路径上明确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具体策略。
一、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无论对于我们构筑国家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还是对于完善公共文化事业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时代命题。中国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像蕴藏在地下的宝藏,如果不经过人工的开采、冶炼,它永远不可能“兑现”它的能量和价值。为此,传统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现代性转化,经过创造性的开发,才能够实现它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进而言之,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只属于过去,如果要让它所体现出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价值,必须要跨越时间的屏障,经过能量的转化,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所以说,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并不是一种自我确认、自我命名的文化属性,而是一种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能量转化、并且通过广泛传播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文化力量。
在文化产业迅速勃兴的时代,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内容的急剧增量也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面向异彩纷呈的现实生活寻找创意灵感之外,也必然转向传统文化寻找可以利用的创意资源。为此,我们电影、电视剧、动漫都面临着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的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它的现代性转化不是靠我们去教孩子背诵几句古代圣贤的格言,也不是靠我们复制一批传统文化的经典就能够奏效。它要靠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提升。这种创造性的提升既包括对传统物质传播媒介的升级换代,如用活动影像取代报刊纸张,用彩色图像取代黑白文字,用流动的互联网取代静态的印刷品。还包括对传统文化表述话语体系的现代性转型。即把一种原本属于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学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属于传播学、艺术学、产业学的新型表述形态。尽管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转化为一种故事在大众媒介上进行艺术化的传播,可是,我们毕竟能够将千年前的历史人物搬上银屏,能够把百年前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还要把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不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改写”与“重构”。特别是直接以古代历史为题材的文化产品,更要对创作素材进行必要的前期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此,才能够保证文化产品的精神质量。
毋庸置疑,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文化产业宝贵的创意资源,也是我们社会赖以发展的精神财富。对这些资源与财富应当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涵养。尤其要防止对其进行破坏性的开采。此前,在自然界我们曾经有过极其严重的教训,但愿在文化领域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提高流行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流行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战略力量。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面,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我们的流行文化产品还不能够承担对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播职能,我们的文化产品更多地只是体现了某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需要,而并没有彰显出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恒久作用。
我们指的流行文化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通俗音乐、歌舞晚会这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艺术形式。要建构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提高本土流行文化的核心竞争力。1990年,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加里·哈默(Gary HaMel)首次提出核心竞争力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领域。核心竞争力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将竞争机制的研究从通常的企业外部转向了企业内部,并且立足于通过企业自身的资源整合与潜力开发来寻求它在竞争中的制胜途径。我们在此所强调的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并不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商业意义上的竞争力,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它主要是指那些在文化领域独一无二的精神资源,通过对这种精神资源的开发、创造、传播,必将对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连对娱乐文化持有激烈批评态度的尼尔·波兹曼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代世界“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①只有在流行文化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才能够使其文化价值观在世界上广泛传播。韩国人没有把他们的传统艺术长鼓舞推向世界,而是把表现他们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电视剧、电影作品推向海外市场。日本人也没有把代表他们传统文化的国粹艺术歌舞伎推广到美国,而是把他们最时尚的动漫产品打入美国市场,日本现在动漫产品在美国的销售收入超过50亿美元,是日本钢铁在美国销售额的4倍。我们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同样是通过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姿三四郎这些来自于流行文化领域的大众艺术形象。我们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也不宜于在文化产品中去追求那种过于深奥的哲理,更需要的是把那些容易被他人识别与认同的文化意义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种能够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的流行文化产品,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对海外受众并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力。我们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便失去了一个有效的传播载体。固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流行文化产品都变成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具,但是,那些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力作必定会在这些流行文化的作品中产生,而不能期望还有另外一个专门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品的机构来完成这个使命。
流行文化在人们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既是一种娱乐的来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资讯来源②。“许多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因为流行文化露骨的商业性而对它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所提供的只是大众娱乐而非信息,所以没有什么政治效应。”③也有人认为流行文化只是通过纯粹的市场力量和享乐主义来引诱人④。这些看法显然对流行文化是一种偏见。事实证明,流行文化对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都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它的积极作用会使国家在推行其政治政策与国家利益时更加容易,也更加有效。
三、构筑软实力传播的硬实力平台
文化,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能够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根基,否则,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在构建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看到社会经济实力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文化的软力量不仅会失去彰显其魅力的传播平台,而且文化本身也会面临着衰微的困境。
现在,我们的电影在海外还没有建立通畅的发行网络,电视也没有覆盖全球的播出平台,舞台艺术也很少进入发达国家主流的商业市场。这些既需要文化产业自身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需要国家在硬实力方面增加力度,进行长远的战略性投资。文化产业通常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所以,市场的失利并不等同于一般产品的经济失利,同理,市场的胜利也不能够等同于通常的商业胜利。电影的票房收入、电视的收视效果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性经济指标,它还包涵着特定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体现着文化软力量的实现程度。尽管,我们不能把市场的胜利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文化胜利,但是,市场的硬指标同样也体现着文化的软实力。所以,经济的硬性指标实际上也是衡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尺度。一部电影就是具有再精湛的艺术技艺,再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没有人观看,那么,它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体现;一部电视剧就是具有再神奇的审美意味,再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果没有受众的关注,它的精神内涵又从何体现呢?我们应当看到,经济的硬指标是体现文化软力量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国电影在产业规模上不断扩大,票房节节攀升,电视剧的生产位居世界首位,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在市场意义上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的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认同,对于中国主流电影社会功能的确信。
中国之所以受到世界普遍的关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正是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才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文化的话语权,有了相对平等的谈判条件与相互磋商的议价能力,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经达到26个,成为世界上入选名录最多的国家。这些都反映出在日趋强大的经济实力面前,国际社会对我们文化价值的确认。就连约瑟夫·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是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根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⑤。这就是说,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对一种文化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文化往往是那种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的文化。人们在确认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之后,反过来才会对其文化的价值产生认同。包括以《文明的冲突》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强调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物质上的成功会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必然导致文化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所以,尽管有时文化会成为社会舞台的重要角色,但是经济依然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全面建设必然有赖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
四、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商业化输出
不论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通过政府的公共职能机构进行贯彻之外,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感性的、甚至是娱乐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此建立公众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文化只有被大众认同并成为全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⑥
尤其是中国要完成从经济大国向文化强国的历史性转变,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有限的本土市场内。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倾力生产外销型的文化产品。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包括流行音乐、舞台演出,都应当打造具有外销能力的标志性作品,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具有全球化的市场视野以及跨文化表述的能力。国家应当设立专项的文化产业基金,推进“出口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海外传播。我们不能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销售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要找到相应的文化产品才能够真正实现——不论这种产品是书刊杂志,是视觉影像,还是舞台表演,总而言之,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文化产品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单纯的文化理念并不能够直接地转变成文化的软实力。美国文化如果离开了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歌舞、麦当劳快餐、万宝路香烟、可口可乐饮料,它在哪里呢?我们的文化传播同样需要的是一系列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且还能够适应海外文化市场的商业取向。尽管海外市场的培育与形成并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实现的目标,可是文化软实力的践行必定有赖于海外市场对我们的认可。否则,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就是一句空话。
曾几何时,在我们的文化市场上起消费导向作用的几乎都是海外明星,世界著名品牌的代言人也基本上是港台演艺界的一线人物。而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品牌开始注意到内地演员的市场感召力,他们启用内地明星作为形象代言人。这表明我们的受众群体对于本土明星的认同度在提高。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除了表现题材本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之外,影片的市场业绩很大原因是来自于影片的“全明星策略”。尽管影片的明星叙事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影片成功的明星运作模式表明了我们的观众对于本土电影明星的心理认同。由此可见,电影的明星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占领电影商业市场的经济策略,而且也是一种本土文化的传播策略,我们应该利用明星制所产生的良性互动效应,引领文化市场的消费取向,把拉升文化产业的硬性经济指标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并行不悖的文化发展战略,进而推进我们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商业化的方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不是意味着把所有的文化产品不加区分地推向商业市场,而是应当根据文化产品的不同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扶助与支持,使它们能够在市场化的历史境遇中获得合理的生存空间。总而言之,市场之手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市场毕竟是要靠产品来说话的地方,所以,如何使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对扩大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建构具有当代性的国家形象
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封建社会旧中国的文化遗产、民国时代旧社会的文化符号作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需要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它们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我们期望别人认同的文化也不只是古老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是期望世界能够认同我们当代的文化形象。为此,我们应当按照当代文化的构成元素来配置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来搭建中国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来铸造我们的国家形象,来传播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所强调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直接演绎的影像变体,也不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里国家概念的翻版,在电影艺术领域它是指一种通过叙事逻辑建构的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内在本文”。这种“内在本文”不是显在于电影的影像表层结构中,而是通过影像叙事体与社会历史之间产生的“互文性”关系来呈现的。作为外在于电影叙事体系的国家理念,正是通过电影的叙事完成了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对文化理念的首肯。我们国家的社会政体是艺术作品中国家形象的生成基础,也是其表现形式的现实依据。我们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体制,决定了中国电影、电视中的国家形象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那种世界霸主的权力象征,而是我们社会力量的现实映现,它是与作品的叙事情节相互镶嵌的意义载体。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标志是飘扬的国旗、高悬的国徽、激昂的国歌。面对这些神圣的国家形象,作为国家的公民我们不禁会肃然起敬。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尊严与国家利益的象征。在中国电影的叙事体系中,作为一种体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表意符号,国家形象不仅通过具体的、标志性符号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电影的叙事方式和与现实的互映方式呈现出来。识别主流文化中的国家形象的表意方式,分析这些表意符号的生成路径,进而为主流文化提供一种可以依循、复制的表述策略,不论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是强化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都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体系内,以家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家、国一体通常是主流电影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特征:国家的畸变、动乱与家庭的离散、解体以及国家的整治、安定与家庭的和睦、重组是中国电影基本的叙事模式。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是这样一种以家庭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故事”。为此,在这些影片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变成为国家社会的一个缩影。正如影片的主人公许灵均所说:“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许灵均的“家”就是“国”。他对“家”的爱本身就是爱“国”情感的一部分。许灵均对草原这个家园的深情眷恋,正是他对国家之爱的具体体现。影片《上甘岭》中的“国家形象”是以全体守卫上甘岭的指战员共同咏唱《我的祖国》这首浓郁的抒情意境的歌曲来体现的。在烈焰纷飞、铁血横流的战场上,一曲抒发对祖国、对家乡思念之情的歌曲,以音乐/歌唱形式主导叙事内容的“国家形象”使观众个体的审美感受得到升华。因为在这种集体合唱的电影情景中,突出的并不是某个人物的所谓英雄性格,而是把整个叙事的焦点对准了超越个人性格之上的“国家形象”,她是故乡稻花飘香的美丽田园,是家园碧波荡漾的清澈江水。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集体歌唱中,国家的意义通过镜头的画面与音乐的旋律自然地呈现在银幕上,她成为观众心驰神往的一片美丽的家园圣地。
在许多中国电影的叙事本文中,“国家形象”是看不见的,甚至与“国家形象”相对应的象征之物——国旗、国歌、国徽也是“不出场”的,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叙事的动机、或是一种重要的叙事背景、乃至于一种潜在地推进影片情节进展的叙事动力而存在。影片《血性山谷》的核心情节——一个普通的农民,真正走向抗日征途,主动为八路军带路起,影片作者就采用了交响乐《红旗颂》作为主导的音乐形象,并且把它作为整部影片的主题音乐不断呈现在影片的叙事进程之中: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还是在黄土飞扬的行军中,《红旗颂》始终伴随着八路军将士的脚步。它的反复出现使这样一场动作强烈、情节惊险的战争影片,被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激情所浸染,把观众的个人情感升华到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崇高境界。
在国家形象的历史性建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观众对空间形态的国家认同。詹姆逊在《地理政治学:电影和世界中空间》中提出“认知图解”(cognitive mapping)的观点。他把电影的空间关系与国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要使电影院里的观众获得他们应当获得的“国家归属感”,而不能够使他们失去对国家空间的心理认同。观众的这种空间主体性的失落,将使他们无法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感受自我的文化身份。即便影片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但是由于失去了具体的空间认同基础,影片也难以建构与观众的真正心理认同感。所以,国家形象,是建构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上的一种互文性叙事结构,她的表述远比一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要复杂得多。
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认知模式中,当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他们更多的只是知道古代中国的艺术作品,知道中国古代的代表人物,而对于现代、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不知晓。其实,比这些认知的缺失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的文化认知模式中还具有许多理解的误差。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长期的文化建设与传播才能够得到改变。我们今天所做的全部努力,其实,仅仅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步而已。
注释:
①[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David Hesmondhalgh:《文化产业》,廖珮君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页。
③[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48-49页。
④爱德华·罗斯廷:《该死的米老鼠和巨无霸》,载《纽约时报》,2002年3月2日,第A17版。
⑤杨晴川:《中国提升“软实力”乃明智之举——专访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参考消息》,2006年8月10日第12版。
⑥丁言:《主流文化的“守土”责任》,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2005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