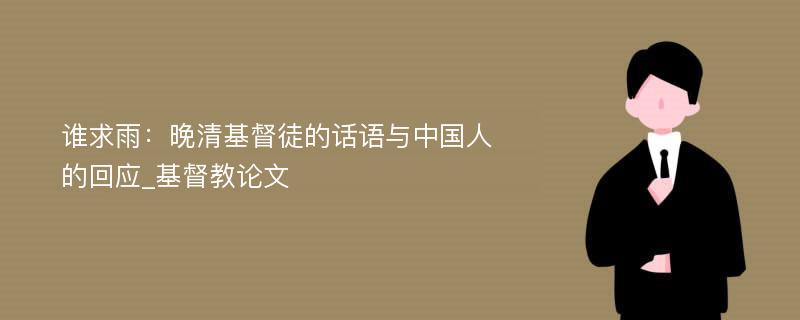
向谁求雨:晚清基督徒的言说及国人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基督徒论文,国人论文,向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家来说,旱灾等气象灾害会对社会带来沉重打击,因为它会造成普遍的生存困境并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古代,对气象进行理性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能力一直相当弱。此种状况,为诉诸于神圣存在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大量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地的农业社会中,旱灾往往都被赋予超自然的解释,从而被赋予宗教意涵,拥有相应的教义和仪式。在中国,求雨的信仰及仪式由来已久,且从未中辍。然而,晚清时代,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了关于降雨的竞争性解释,其中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宗教,对中国求雨信仰展开了持续的批评。其批评一方面激怒了中国本土求雨信仰的参与者,造成诸多教案;另一方面亦说服了大量新式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科学的降雨解释,虽然其宗教解释并未得到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广泛接受,降雨现象与神圣存在完全脱钩,求雨信仰遂成无本之木。 一、传统中国的求雨信仰 关于求雨的历史记载,有名的可以追溯到商汤祷雨。《尚书大传》记载:“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乃剪发断爪,自以为牲,而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数千里。”①商汤作为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以自己的头发和指甲替代肉身,作为牺牲来献祭。②但献祭和祈祷的对象,在这个记载中还没有明确指出。对此,《吕氏春秋》中则讲得很清楚:“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③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以旱灾来伤害人民生计的是上帝、鬼神,因此操控降雨的主体是“上帝”和“鬼神”,均为人格神。上帝与鬼神同在,表明这是一个多神论的系统。商汤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一己为牺牲,换取万民之福祉,体现出极高的道德品质,这是他求雨成功的关键。 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载的求雨(止雨)又别有特点。董仲舒详细记载了当时求雨、止雨的择期、服饰、祭品、跪拜、祷告、祷词、还愿等事项,且春夏秋冬各有不同。以春旱求雨为例,应该让县邑扫除社稷,行雩礼,让百姓在家求雨。在此期间,不能砍伐树木,要曝晒女巫、聚集蛇虫八天。在城东门外筑坛以通鬼神,树立旗帜,献上食物为祭。选择清洁、善于言辞的女巫为祭主。令祭主提前斋戒三日,穿苍色衣服,跪拜,向生养万物的“昊天”祈祷。根据董仲舒的解释,旱灾是阳压过阴,所以求雨仪式要选在“水日”,要多出现作为阴性的女人(包括女巫),即所谓“开阴闭阳”,从而使阴阳和谐。而降雨太多,则是因为阴压过了阳,而“阴灭阳,不顺于天”,请求止雨的仪式就是向“社灵”请求“废阴起阳”,因此仪式应选在“火日”,水井要盖起来,女性应尽可能避免公开露面。④在这里,求雨止雨的直接祈祷对象虽可能是地方的社稷神,但归根结底还是向生养万物的“天”祈祷。而“天”一方面是一个人格化的、有意志的神,所以它能理解人类的祈祷;另一方面似乎又等同于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是非人格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天”作为至上神,并未排除社灵等下位神的存在,而且在这一记载中已经出现了“龙”“蛇”等事物。所以求雨的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有层级的多神体系。与商汤祷雨中一样的是,祈祷对象均为多神系统,下位神均为人格神;不同的是,至上神由“上帝”变为“天”,其人格化特征弱化,非人格化特征强化了,基本被等同于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而且,董仲舒记载的这套信仰仪式中,求雨成败的关键,最主要的不是祈祷者的道德品质,而在求雨者能否有效地以阴性引致阴性,从而实现阴阳平衡,颇类于弗雷泽所谓的顺势巫术(模拟巫术)。⑤ 随着佛教等外来宗教的进入以及道教等本土宗教的兴起,中国各地的求雨仪式更加多样化。求雨的对象,既包括玉皇大帝、天、上帝,又包括各处的龙王,还包括佛教神祇,乃至于风神、雷神、云神等。1879年,清室发布了十多道回应地方长官酬谢雨神、敕封神祇的上谕,敕封的对象以龙神为主,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赵武、关羽、诸葛亮、城隍、五谷神、八蜡、道教诸神、佛教诸神、百里嵩、金龙四大王、朱大王、黄大王、栗大王、宋大王、白大王、陈九龙将军、元将军、王浚等等。⑥这些神祇,有的属于道教系统,有的来自佛教系统,大多则是地方英雄死后变成的神。神祇多样,并不成严格的体系,但也不构成激烈的互斥关系。与此同时,以非人格化的宇宙秩序为对象的求雨仪式并未中断,且常常与人格神的信仰混合在一起。清代儒士纪大奎(1756-1825)《求雨全书》主要以《易经》八卦为理论基础,设定了一整套向上帝/天求雨的仪式规则,规定了净瓶和旗帜的形状、颜色、大小、摆放方位、方位调整程序,仪式的主持者和参与者运动的步伐和顺序以及使用的祷词、经文等。⑦从这套仪式规则可以看到不同信仰系统之间的融合,仪式参与者包括僧人、道士、儒生等,八卦理论出自儒家六经之首的《易经》,净瓶插柳枝则是受佛教观音菩萨形象的影响。从该书所附1846年和1867年两位后学士子所写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晚清曾多次刊刻,其仪式规则在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信奉者,并在多地求雨中得以践行。 借用弗雷泽关于宗教和巫术的区分来看,商汤祷雨具有更强的宗教色彩,而董仲舒描述的求雨仪式带有更强的巫术色彩。⑧但在传统中国的求雨仪式中,这两种传统往往混溶在一起,兼具宗教性和巫术性。参与求雨仪式的,上至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大都严肃对待。1876年,北京旱灾,虽屡经设坛求雨也无效验,三月初四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认为“亟应及时修省,以迓和甘”,并怀疑是有冤狱未平所致,令刑部衙门认真清理一切案件,迅速审查案件,不准拖延积压,以免无辜者长期羁押于牢狱之中,有违天和。⑨次年旱灾,清皇室又下罪己诏,其中谓“上天降罚何不移于宫廷”,两宫皇太后率皇上露祷,长跪三四个时辰之久,仰望星空皎然,至于恸哭。⑩统治者的道德过错与旱灾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堂而皇之地放置到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来言说和实践。在各阶层的求雨过程中,通常还伴随沐浴、斋戒、祷告、叩拜、禁欲、禁屠等仪式和禁忌,甚至还有人舍身献祭。(11)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可以视为一种本土的宗教信仰传统。 二、晚清基督徒关于求雨的言说 不过,上述这样一套有关求雨的信仰及其仪式,在晚清时期遭到了持续不断地挑战。 这一进程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启的。183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广州办的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发了一篇题为《格物穷理》的文章,就降雨现象提供了一种竞争性的解释。文章虚构了三个人在风光无限的某处游玩。突然乌云密布,沛然下雨。其中一人问道:“不知此雨从何而来耶?天无门,云无窍,以漏之也。”另一人回答说,他数日前读到一本奇书解说格物之原,其中就讲到了雨的成因:“各山川、海面、林野、田亩,恒时飘散泄气,霄湿腾天,即成雾云而合也。雾集叆叇,愈久愈重,不可浮气,就落,正是下雨矣。”另两人都认可这种解释。后来三人再次同游,巧遇彩虹悬天。一人问彩虹是怎样形成的:“莫非虫蚁聚,着此五色矣?”那位博学之士又回答道:“晒雨相对,映照回光,虹霓就现。所看之五色,为光射之歪而着也。雨止,叆叇虹霓即散了。”(12) 文章若到此为止,不过就是一篇我们熟悉的科普文章,但文中还有多处涉及到上帝的解释。写到天朗气清,景色宜人时,“三人仰观俯察之余,咸相赞美万物之造主天皇上帝也”;写到降雨时,则问“其如是孰能御之”;谈到虹霓的解释时,又援引《圣经》中彩虹之约的故事说,虹霓即“系念上帝,与地上众生,所立之永约也”。(13)与此类似,该刊同期所载《露雹霜雪》一文解释了其它气象,其中谈到冰雹的时候,复述了一个《圣经》故事:上帝厌恶地上一个罪恶的国王,于是命令他的仆人伸手指天,以雷电和冰雹降于该国,毁坏人兽蔬菜树木等等,国王于是命人招来上帝的仆人,对他说:“寡人有罪,惟天皇上帝乃公义,而寡人与民作恶矣。汝宜祷天皇上帝,再不可行雷雹。”仆人禀告上帝,雷雹就停止了。如此这般,“令王知上帝乃天地之主”。解说者的最后结论是“雨露霜雹,咸服上帝之权,且遵其命”。(14) 分析起来,这两篇文章中关于降雨的新解释主要依据两种知识资源:一是基督教的宗教解释,一是科学的解释。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矛盾,正像雨露霜雹都服从上帝的权威一样,科学的解释也臣服于基督教的解释。此外,“格物穷理”这个标题是典型的宋明理学式的表达,文章言说路径与宋明理学也具有高度的同构性,都是主张从观察和理解自然万物从而体会背后的“理”。在这篇基督教的宣道文中,因为相信宇宙万物均为上帝所造并为上帝所主宰,因此观察和理解世间万物,即可体察上帝的旨意和诫命(即理)。无论是哪一种“格物穷理”,与后来现代科学的理解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对中国的求雨信仰,基督徒的这两篇短文虽未着一字,但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竞争性的解释。随时间推移,挑战的姿态越来越明显,许多即直接针对中国朝野的求雨信仰。1881年,传教士刊物《益闻录》刊载的《占雨论》一文,视望云占雨之术为“离奇之说,诞妄之谈”。该文先列举中国史书所载的一些准确“预测”降雨的记载,并指出“今之术士辈,往往援为故实”,接下来给出了一种解释:“此会逢其适,非演法果能致雨也”。换言之,成功“预测”只是碰巧。然后作者长篇介绍西方学者的相关解释,指出雨是云水下堕所致,而云又是湿气上升而形成的。地上湿热之气上升遇到寒冽之气,则凝结为露珠状的云。云遇到湿气,露珠融化变为流水,下坠为雨,这就是雨形成的原因。总之,“雨本乎云,云根乎气”。接下来,作者笔锋一宕,把传统中国各种关于雨的神话故事数落了一通:“韩子谓龙嘘气成云,妄说也;左太冲为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亦谬谈也;《罗浮山记》谓渊有神龟,人秽渊即澍雨;《华阳国志》谓天有井,故多雨;《列子》以赤松子为雨师,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此等论说,皆可侪诸梦中呓语。”作者虽批评传统中国关于雨的各种神话传说,但他却并非无神论者。他说道:“盖气为大造所生,雨亦惟大造所主。”(15)这里的“大造”即造物主。云与雨的转换固然有其运行规律,但是云、雨及其运行规律都是上帝所造,科学规律并不排斥上帝的存在。 在当时甚为流行的基督教自然神学中,科学是服从于上帝信仰的,宗教与科学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如果我们不跳出唯物/唯心、无神论/有神论、科学/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就只能把其宗教内容视为一种“历史的遗留物”,指责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中“夹杂着唯心主义臭味”。这样的批评显然无视传教士的首要目的是传教,而非传播科学知识,而且他们既传教又传播科学知识,是因为他们以自然神学有效地整合了二者。刘华杰教授曾批评今天许多学者往往以后设的科学观念去理解历史上的科学观念,因而许多科学史研究总是力图打捞历史文献中的“科学价值”“科学含金量”,力图“去伪存真”,对其中的宗教、“迷信”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指出:“传教士从来都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无须多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人们喜爱科学,在他们的活动和作品中就只看到科学,不能因为不喜欢宗教而想从其中简单地把它分离出去。”他提出,晚清基督徒的许多著作,与其说是自然科学著作,不如说是“科学-自然神学”作品。(16)这样的理解是更贴近历史真实的。 基督徒对中国求雨信仰的抨击,一方面是科学对非科学的抨击,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一神论宗教的基督教对多神论异教的打击。他们不是不主张求雨,而是主张不能向龙王等神祇求雨,而应该向上帝求雨。刊载在1881年《益闻录》上的一篇题为《求雨论》的文章,如此批评中国乡民的求雨方式:“延僧仗道,赛会迎神,或击鼓鸣锣,禹步作法,或书符诵咒,导众野游,撑空火伞,曝偶像于庙庭,描绘周星,竖旗旛于屋角,此等妄为,洵堪痛恨。而乡愚辈习俗成风,牢不可破,亦举世皆是矣。”无论僧、道,在基督徒看来都是可耻的异教,僧道信仰的神祗以及塑像,在基督教看来都是把不是上帝的事物当作上帝来信仰,是为“偶像崇拜”。作者痛斥偶像无灵,“既无实德又少真修”,求也无用。《春秋繁露》《周礼》《搜神记》等典籍中记载的种种求雨法,在作者看来当然也是异端邪说。中国的求雨,他唯一认可的是商汤的求雨:“惟成汤祷雨桑林,乃千古不磨之正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可商汤面对“大造”诚恳忏悔的态度:“灾害流行,大造所以示警惕也。成汤以六事自责,深恐以一人之愆尤,致伤万民之生命。其悛悔之心可知也。雨生于云,云生于气,造物为生气之大原,造物亦为司雨之大主。成汤之祷于野也,其意谓非造物之仁不能渥沾沛泽,则其探本穷源之学,亦云至也。”(17)作者并非反对一切求雨信仰,只是反对向种种偶像或异教神求雨,只有虔心向唯一的人格神(天/上帝/大造)祈祷,才是正道。 作者特别强调求雨者应虔敬,与该刊一年前刊载的一篇文章相映成趣。与该基督徒类似,松江儒士郭友松虽批驳传统求雨信仰的种种荒诞,但是对商汤祷雨一事独有肯定。全文重心在分析商汤剪发断爪,意在表达其虔诚祈祷之意,不能因为宋儒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丝毫损伤”的观念而有所非议。(18)郭友松是儒士,但他对商汤祷雨的理解和评价,对形形色色的求雨信仰的指摘,与基督教甚为相似,戏剧性地表现出当时儒学与基督教在此问题上的隐性“共谋”。究其根源,是因为基督教认为自然灾害是天/上帝的示警,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观念是部分重合的。而且《求雨论》的作者作为基督徒,显然是把商汤祈祷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了。这也是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定下的传教策略。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的人格神崇拜通常是多神论的,众神服从于至上神天/上帝/玉皇大帝,对至上神的信仰并不排斥其他神的存在。基督教所理解的神(上帝/造物主),则是排斥它神存在的绝对唯一神。“至上神观念并不否定其他诸神的存在,而只是把它们置于从属的地位。绝对唯一神观念则有所不同,它不仅肯定神的至上性,而且进一步肯定神的唯一性。”(19)以这位基督徒的标准看来,只有向上帝/天求雨可以算得上正统(因为利玛窦定下的联合儒士、排斥佛老的规矩,基督教通常不承认道教的玉皇大帝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皇室及民间向龙王等各种神祗祈祷的求雨都是异端,体现出基督教严格的一神论特征,对于多神信仰有强烈的排斥态度。 三、中国人的两种回应 基督徒对中国的求雨批判,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以贯之的。但分析起来,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神宗教对多神宗教的抨击、正统对异教的排斥;科学对非科学的排斥。中国人的回应,相应地也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激烈地报复基督教对本土信仰的排斥。通常而言,中国的信仰系统之间有着很大的兼容性,只要承认一个共同的至上神(天/上帝/玉皇大帝可能被等同起来),众多下位神就可以相安无事,通力合作。可是,当多神论遭遇一神论时,唯有至上神可以获得认可,其余诸神崇拜都要被斥为异端崇拜、偶像崇拜,或者斥为迷信。(20)在不少地方甚至有基督教徒捣毁佛像、关帝像、观音像等行为,如1863年直隶平山县教案缘由之一即是基督教教民将当地某寺中金装古佛、观音大士神像挖孔去心,将天王神像剜掉双眼,摔断手臂,从而导致当地居民对教民的围攻。(21) 近代中国不少宗教纠纷就源于这一分歧。许多基督徒,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不参与家族的祖先祭祀仪式,不参与地方社群的求雨仪式等宗教活动。而地方社群的求雨仪式,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和强制性。比如,禁屠求雨的过程中,违背屠宰禁令是要遭受惩罚的。基督徒拒绝参与这些公共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自外于所在的地方社群,从而导致排斥和敌对,并可能产生更为激烈的正面冲突。1862年直隶柏乡县发生了一起民教互殴事件,其原委大致如下:某些村民人了基督教,不信向关帝求雨之说,遂拒绝与别的村民一起求雨,也拒绝承担酬神赛会的开销。但降雨之后,他们的庄稼同样获得雨泽滋润。村中生员和民众认为这些教民坐享其成,于是出言讥嘲,导致互殴。(22)次年,京师北堂教士蓝田玉在通州乡间遭到殴打。据地方官员报告,五十多村民抬着龙王塑像,让幼童手持柳枝,前往普济闸取水。根据当地求雨的仪式规则,路过之人须下马站立路旁,待求雨队伍走过后再离开,以示对龙王的恭敬。当天蓝田玉等人骑马经过求雨队伍时,众人命令蓝田玉等下马,后者不信这一套求雨仪式规则,拒绝下马,遂酿成群殴事件。(23)1869,直隶广平府永年县民众把求雨不应归咎于基督徒对(中国人的)神明不敬,上干天和,于是拆毁了当地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并砸毁了教堂家具。(24)本土求雨信仰的公共性和强制性,遭遇基督教强硬的绝对一神论立场,几乎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而这种信仰上的冲突,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00年华北旱灾,许多求雨活动无法奏效,最后都被归咎于传教士和基督徒不敬天地、不祭祖宗而触怒了上天之故。这种归因几乎传遍整个华北地区,最终造成对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大肆屠戮。(25)这些观念的斗争,并非纯然是底层民众的作为,许多教案背后都有地方士人乃至地方官的怂恿,因而这种观念的冲突也发生在基督教与中国知识阶层之间。(26)因此,这种反击式的回应,固然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回应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回应方式。 另一种更为主流的回应方式则是接受基督徒带来的科学解释,同时完全抛弃求雨信仰,无论求雨的对象是中国宗教中的天、龙王、关公、玉皇大帝,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因为趋新的读书人阅读基督教的“科学-自然神学”时认定:降雨与否,既非玉皇大帝、龙王、关帝、上帝等人格神的意志在主宰,与阴阳、五行、八卦等宇宙秩序也无甚关系,只是地面之水蒸腾而上成云,遇到气温变化,遂降落而成雨。基督徒的“科学—自然神学”认定,水变成云再形成雨的过程,其动力和法则并不是自足自立的,而是仰赖于上帝的意志;可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水蒸腾为云再降落为雨的过程,其变化的动力和法则都在自然内部,而无需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主宰。他们并不赞同“科学—自然神学”的内在一致性,他们认定科学与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也是矛盾的,他们把科学从自然神学中剥离了出来。(27) 举例来说,1906年《东方杂志》一则百字短文解释印度某地降雨特别多,是因为当地峰峦障天,又正当海湾,海水蒸气上升,被西南风吹入湾中,凝滞不动,一遇山上冷气,即降为雨。(28)同年《竞业旬报》上刊载的一篇科普短文,则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解释了雨的成因,而且还旗帜鲜明地以此挑战传统对雨的认识以及求雨的信仰和仪式。针对中国人认为雨是天上落下来的看法,作者指出:“据现在的人考究起来,原来这雨是从地上来的。”接下来作者举烧饭时锅盖上的水珠的成因为譬喻,解释雨水的形成:“这地球上那江河洋海的水,被这太阳晒热了,也就有许多部分的水,化成水汽,冉冉的向上升起,遇了那冷空气就凝住了,后来越来越重,或是那时天气的冷热有什么变动,那空气一变动,那汽水便一滴滴的落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雨’了。”(29)《竞业旬报》只是中学生刊物,而该文作者是不到15岁的胡适。(30)由此可见关于降雨的科学解释已经相当普及了。考虑到胡适这一代人在将来的巨大影响,科学解释的普及度和影响力更不容小觑。 雨的成因虽并不复杂,但是即便到今天,人类也很难有效地影响降雨,更不要说在100多年前了。因而,在晚清期刊上看到的各种求雨新法,也花样百出,千奇百怪。中国读书人的言说明显因袭了基督徒的科学解释,同时剥除了其宗教意涵,神的主宰权绝大部分被转交给人类自己。 一类求雨新法是种树引雨。1873年,传教士刊物《中西闻见录》报道美国某处新垦之地,本来降雨稀少,但因种植庄稼,挖井灌溉,田苗遍野,最终降雨愈增,其解释是“地气上腾,故天气下降也”。文中并引申说,禾苗可以引来降雨,树木更足以引来更大的降雨。(31)1902年另一传教士刊物《万国公报》上一则《种树致雨》的短文,则试图解答为何某些近海地方也会缺少雨水。作者认为那是因为无高山大林,空中常缺阴气;或者因在高山一侧,为高山峻岭所隔,云在山另一侧即已遇阴气而成雨,“惟多种树木,则天气地质皆有变化”。该文举埃及为例以说明种树引雨的效用,说埃及原本五年一雨,因多种树木,后来已经变为一年一雨,将来也许变为四季一雨。最后,作者还建议中国缺少雨水的北方植树引雨。(32)该短文被中国报人主办的刊物《政艺通报》《选报》原样转载,又被《浙江五日报》以“农商工艺新闻”的形式节要转载。(33)可见种树致雨这种新方法及其背后的原理被不少中国知识人接受。 植树引雨对于饱受旱灾的人来说,奏效还是太慢了。另一类方法则是以种种方式促进及时降雨。大约在1897年,国人编辑的《新闻报》就曾报道美国有人把氢气和氧气放进氢气球,把球升入空中,用电线通电把气球轰破,马上就会下雨。(34)十年后,《振群丛报》旧事重提,不仅细节讲得更清楚,而且作者还相信:“按此法果能收效,不几夺造化之功用乎?”(35)诚然,若这种人为的方法可以奏效,主宰降雨的各种神祗大概是会失业的。这里体现出来的是神力与人力的消长关系。 1898年,国人创办的《格致新报》报道,德国某人发现一个现象:在1883到1892年间,德国首都的雷阵雨多出现在星期一,而很少出现在星期四。最后发现其原因是星期一、星期二纱厂停工,所以降雨比较多,而星期三以后各厂开工,烟囱大量排放,所以雨少。(36)该则报道题为“煤烟御雨”,并放在“格致新义”一栏中,想必以为此法甚可借鉴。次年,康有为等人创办的《知新报》又报道西方科学家考虑把空气压缩为液态,在高空释放,其下之气若含充足水分,就会凝结为云,转而成为雪、冰雹,在下落过程中转成雨滴。文中还提到在空旷地面焚烧火药,加以炮声震动,即可降雨。(37)1902年,《选报》根据日本报纸的报道,介绍当时日本科学家制造机器向空中放电,历二日而获降雨。选编者由此感慨“近来艺学化学之精,有可以人巧夺天工者”(38)。 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用炸药轰炸云团了。1907年,传教士刊物曾简要介绍,近百年来科学家试验发现,用炮声轰震空中之湿气,遂成降雨。(39)不过这种办法,并不那么有效。当时报刊也曾报道美洲和澳洲有人做试验却最终失败。(40)还有华人报刊较为详细分析炸药致雨的方法之所以缺乏稳定的成效,是因为影响降雨的复杂因素,并根据美国的另一个案例提出了改进意见。(41) 尽管人工降雨的成效如此不确定,但这不影响新式读书人对传统求雨信仰的弃若敝屣,也不妨碍他们对科学的乐观态度。不到15岁的胡适就断言:“那有雨没雨,都是关于这天气上的事,并没有什么神道,也没有什么雨师龙神的。可见得那些人一遇了大旱的时候,便去磕头拜揖的去求雨,真是愚蠢得狠可笑了。”作者根据科学知识而断定降雨与超自然力量(神道、雨师、龙神)无关。那么为什么求雨有时候会真的应验而降雨呢?小胡适的解释是,求雨的时候,人群聚集,锣鼓喧闹,“就是那人群熏蒸的气,也就可以使得那空气生很大的变动了,何况再拿这锣鼓的声音去震动这空气呢”,空气变动了于是就会下雨,“讲究起来到底不是什么神道的力量呀”。(42)作者的这个解释真可算是强词夺理了。但是这一幼稚的解释正好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表露出科学主义的佞妄,以科学解构神迹,力图驱赶任何超自然力量,把任何事物的因果关系都限定在此岸世界,即使力不能逮,也勇往直前。再如刊发于1908年《滇话报》上的一篇短论。因为雨的成因是地上的水受日照变为水蒸气,升腾上空而变云,降落下地即为雨。所以,“雨是绝对不可求得下来的”。既然如此,那么“无雨的时候,要来求雨,究竟求些什么呢?”“或者说是求天地,怎奈天是一股气,地是一个球。或者说是求玉皇,求龙神,怎奈玉皇龙神,是木雕泥塑的,他一样都不知道。”(43) 求雨的时候,求的是什么呢?这的确是个有代表性的时代问题。作为祈祷对象的神祇是否真的存在已经大为可疑,乃至被断言根本不存在时,宗教信仰就岌岌可危了。传统中国人理解的天地可能并不被理解为人格神,但却并非死物也非机械,它能对人世间的言行善恶洞若观火,会做出公正的奖惩,会因怜悯世俗之人而给予补偿和安慰。正因如此,天地才长期作为神圣存在被敬畏,被信仰,被供奉,被祈求。而今,天只是“一股气”,地只是“一个球”。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天和地,分别指大气层和地球,这样的宇宙(天地)无智慧、无意识、无意志,它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任何回应。既然如此,求雨遂显得十分荒唐可笑。而作为人格神的玉皇大帝、龙神也被断言并不存在了。认为玉皇和龙神只是木雕泥塑,实际上是把神像等同于它所代表的神,这个推论肯定算不上严谨,严格说来并无法否证神衹的存在。但无论如何,作者对神圣存在没有信心。信心的丧失,主要是因为在一套更具说服力的解释面前相形见绌了。1908年,时年17岁的胡适主编的《竞业旬报》上刊载一篇短文,以讽刺的笔调勾勒乡民求雨的荒诞情形,题目就是“还是这样求雨吗?”(44)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求雨是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信仰传统,求雨信仰的参与者上至庙堂,下至贩夫走卒。求雨的对象既包含形形色色的人格神,也包含非人格化的宇宙秩序。一方面,形形色色的求雨仪式带有道德意涵和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又往往包含巫术色彩。晚清时代,传教士以科学服务于传教,以正统反异端的立场展开关于求雨的言说。他们带来的“科学—自然神学”提供了新的降雨解释。一方面,降雨是水变云而再变雨。另一方面,降雨操于上帝之手,而不取决于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或是玉皇大帝、龙王等人格神之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选择了传教士言说中的科学解释,而拒绝了科学背后的宗教预设。他们认定,降雨与否,既非玉皇大帝、龙王、关帝、上帝等人格神的意志在主宰,与阴阳八卦之法则也无甚关系,它只是地面之水蒸腾而上成云,遇到气温变化而降落而成。这些自然现象既不受神的主宰,使自然现象呈现如此状态的宇宙秩序也不再对人类道德状态做出回应。换言之,无论人类是行善还是行恶,与这些自然现象都不再构成因果关联。人们需要做的,是把它们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和利用,使之服务于人类的意愿和福利,从求雨到人工降雨的转变就是突出表现。总之,随着解释范式的转移,对这些自然现象的旧有理解中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那些曾经对人类世俗生活具有主宰作用、对人类道德状态做出公正奖惩的神圣存在,被放逐了。这不是说求雨就此绝迹了(民国时期仍有不少案例),而是说,求雨作为一种信仰传统,其正当性在知识阶层中变得甚为可疑。换言之,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求雨的信仰传统,从本土的信仰传统和文化传统中游离出来。在古代社会,知识阶层与下层社会的信仰世界虽有所区别,但只是同一信仰传统的不同层次;而今,知识阶层放弃了本土信仰,与下层社会发生了文化断裂,而且由于他们同时也拒绝外来信仰,从而使他们成为现代中国反宗教的主导力量。这种取向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走向。 ①伏胜:《尚书大传·附序录辨讹》,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 ②详参郑振铎:《汤祷篇》,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2—89页。 ③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00—201页。 ④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求雨第七十四”“止雨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426—439页。 ⑤[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56页。 ⑥详参张洪彬:《天变,道亦变:晚清宇宙论之转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1—72页。 ⑦纪大奎:《求雨全书》,《纪慎斋先生全集》,杭州刻鹄斋藏版,光绪戊戌(1898年)孟冬刊本。 ⑧[英]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光绪二年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⑩徐一士著、徐泽昱整理:《近代笔记过眼录》,中华书局,2008年,第170页。 (11)《杀身求雨》,《申报》1879年8月18日。 (12)《格物穷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10月。 (13)《格物穷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10月。 (14)《露雹霜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年10月。 (15)《占雨论》,《益闻录》第109期,1881年。 (16)刘华杰:《〈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7)《求雨论》,《益闻录》第110期,1881年。 (18)云间郭友松:《成汤祷雨论》,《益闻录》第44期,1880年。 (19)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20)晚清基督教对中国多神论的批评,可参见胡卫清:《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414-494页。 (2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351-358页。 (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382-385页。 (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同治六年—同治九年),第238页。 (25)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0-74页。 (26)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咸丰十年—同治五年),第300-313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27)参见杨象济:《洋教所言多不合西人格致新理论》,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018页。 (28)《雨最多处》,《东方杂志》第3卷第10期,1906年。 (29)期自胜生:《说雨》,《竞业旬报》第3期,1906年。 (3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68-69页。 (31)《栽树引雨》,《中西闻见录》第6期,1873年1月;《腾云致雨说》,《格致汇编》第6卷,1891年。 (32)《种树致雨》,《万国公报》第156期,1902年。 (33)《种树致雨》,《政艺通报》第5期,1902年;《种树致雨》,《选报》第11期,1902年;《种树致雨》,《浙江五日报》第1期,1902年。 (34)原刊未见,转引自当时国人创办的文摘报,见《新法得雨》,《集成报》第15期,1897年。 (35)《致雨之法》,《振群丛报》第1期,1907年。 (36)《煤烟御雨》,《格致新报》第5期,1898年。 (37)《焚药致雨》,《知新报》第97期,1899年。 (38)《机器造雨》,《选报》第11期,1902年。 (39)《炮声致雨》,《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255期,1907年。 (40)《用炮致雨》,《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241期,1907年;《酿雨未成》,《万国公报》第45期,1892年。 (41)《炸药致雨之法》,《万国商业月报》第17期,1909年。 (42)期自胜生:《说雨》,《竞业旬报》第3期,1906年。 (43)《俗弊六则》,《滇话报》第5期,1908年。 (44)《还是这样求雨吗?》,《竞业旬报》第30期,1908年。疑即胡适自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