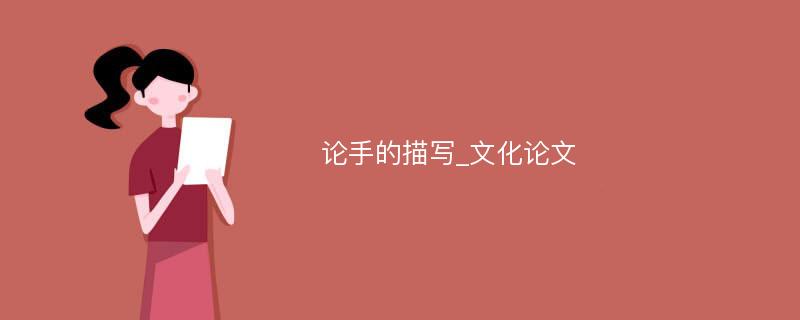
浅谈手的描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尔扎克这样写《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的主人公:“出身的标记即使不是全身都有,单看他毛茸茸的大手,皮肤打皱的手指,粗大的骨节,四方的阔指甲,也就够了。”作者抓住手的形状特征,寥寥几笔,就交代了赛查这个“移植到巴黎的乡下人”的身世。而《水浒传》第三十一回里,写武松在酒店里受到店主人的怠慢和抢白,生气得“跳起身来,叉开五指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把店主人打个踉跄,直撞过那边去……半边脸都肿了,半日挣扎不起。”这一掌,就把武松的神采和武功显示出来了。
手的形状及其动作的描写,能够很简洁地点出人物的特点,传出人物的精神,甚至成为刻画人物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因而得到了中外作家的重视。我们再看《儒林外史》一段趣味横生的描写:
第三回里,范进因为中举喜极而发疯。他平时最怕岳父胡屠户,众人就央请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使其清醒。谁知嘴巴打过之后,姑爷是清醒了,而“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连忙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这段描写虽然夸张,但也合情合理。因为在胡屠户的心目中,范进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可以随便打骂的“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而是下凡的“文曲星”和“老爷”了。打过之后手发疼,是由于“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作者抓住胡屠户的手进行描写和渲染,把胡屠户的微妙心态刻划了出来,逼真地传出了这个势利小人的“神”,收到了极强的讽刺效果。
俗话说:“画马难画走,画人难画手”。描写人物的手要肖其形而传其神,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从作家们丰富的创作实践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要求。
首先,描写手要抓住形状上的特点。
有人这样描写利比亚元首卡扎菲的女保镖的手:“这只手粗大有力,虎口处有铜钱大的伤疤,手指上是又粗又黑的圈圈,显然是练武留下的痕迹。她干这行已经有九个年头了。”单看手指的描写就很有特点:习武而形成粗黑的圈圈。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羊脂球就不同了,她的手指保养得好,就像一根根“香肠”;科学家法希尔从事印染法研究,有人描写他那长期被染剂渗透的手指,“像煮熟的大虾腿”;而白居易《卖炭翁》里的主人公年复一年地在终南山伐薪烧炭,则是“两鬓苍苍十指黑”了。描写手的形状,除了抓住职业的特点之外,还可联系人物的气质、才能和品质。例如高尔基这样描写托尔斯泰的手:“他的两只手生得很古怪:它们难看,上面高高低低地布满了胀大的血管,然而它们又显得富于特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莱奥那多·达·芬奇可能有这样的手。人有这样的手可以做出任何事情。”这就是从创造力的角度进行描写的。
其次,要写出只有这个人物才有的手的动作。
张天翼在《华威先生》里,写了主人公的一个特别的手势,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这手势实在是很纤巧很美妙的了,然而正巧显示了华威先生伪装高雅的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还看清他原来是一个热衷名利、招摇过市的文化官僚,而决非抗日救亡的志士。
人的性格不同,手的动作也就有所差异。鲁迅先生善于把握这种差异。他写阿Q发了财,“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台上一扔道:“现钱!打酒来!”一把抓出,随手一扔,好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而写孔乙己付钱,手的动作就大不相同了。他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然后“排出九文大钱”。他喝酒也是得意的,能付出现钱更是得意的事。然而他没有像阿Q那样发过“横财”;他的大钱全靠抄书赚来,得之不易,所以要用双手一文一文地依次排出来。他花钱时心里有点酸溜溜的味道。
再次,要非常注意手的变化。鲁迅的《故乡》写“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见到少年时代的好友闰土时,着意描绘了他那双手的变化:“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从“红活圆实”到“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形成强烈的反差,使人触目惊心;实际上反映了闰土艰辛的人生,形象地概括了他从可爱的“小英雄”到“辛苦麻木”的“木偶人”的变化过程。这是描写手在形状上的变化。还可以通过描写手在动作上的变化来表现人物。如《儒林外史》里写严监生在临终前,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大家猜不透他的用意,最后还是赵氏明白了他的心意,原来是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严监生“恐费了油”,于是上前灭掉一根,严监生这才“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从“伸着两个指头”到“把手垂下”,作者通过描写手的动作变化,表现了人物的极端吝啬。
不论是手在形状上的变化,还是在动作上的变化,都是一种前后对比的手法,是自身的对比。其实还可以通过不同人的手的对比来表现人物。赵树理在《套不住的手》里,写劳动休息的时候,陈秉正老人要吸烟,想烧一堆火。他“用两只手在身边左右的土里抓了一阵,不知道是些什么树皮皮、禾根根抓了两大把。”一个中学生也去抓,“手指已经被什么东西刺破了,马上缩回手去。”这么一对比,陈秉正那一双“铁钯一样”的手同中学生很少参加劳动的手的差别,便突现出来,透露了老人的劳动经历和朴实的品质。
描写手的形状、手的动作、手的变化,都是为了刻画人物,揭示主题,绝不能离开文章的需要为写手而写手。法国雕塑家罗丹在塑造巴尔扎克像时,曾抡起大斧砍断了那双被学生们称之为“举世无双的完美的手”,因为这双手被塑得太突出了,突出得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罗丹告诫学生说:“记住: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比整体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描写人物的手有什么最重要的“诀窍”,这句话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