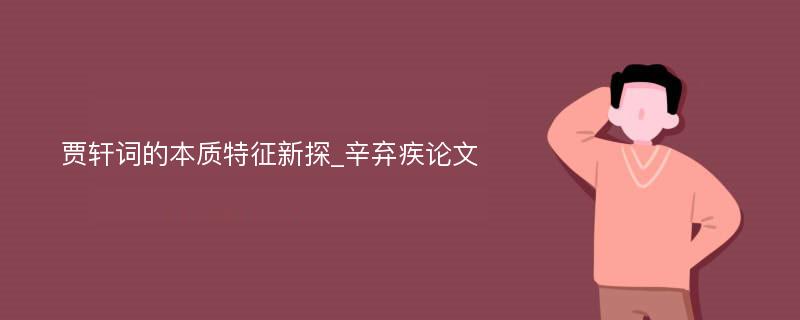
稼轩词本质特征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本质特征论文,稼轩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豪放婉约论辨析
豪放说、非豪放说、豪放婉约结合说(含刚柔相济说等等),此三大类大致可以涵盖前贤及当今学术界对于稼轩词本质特征论述之要。笔者认为,稼轩词的本质特征既非豪放,又非婉约,也非婉约与豪放的结合,而应该在婉约豪放的藩篱之外,另辟蹊径,重伐山林,方可见到稼轩体之真谛。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豪放者欲其气势恢弘。”就“豪”的因素而言,“天风浪浪”,拔山盖世,确实是一种崇高之美。从外在风格来说,稼轩体也确实存在着某种貌似豪放的风格,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豪放、婉约之说,仅仅是唐宋词体外在风貌的描述,其中理由颇多,先略举两点:其一,从唐宋词体贯穿始终的对立因素来说,豪放和婉约只是词体风格审美的表层现象和阶段性的现象,并非是贯穿词体整体生命的对立两极。豪放词始创于东坡;而东坡之前,词体已经历了从温花间到李后主、到柳永、再到张先等“始创瘦硬之体”的几个历史阶段。若以豪放、婉约说阐释词史的演进,则在东坡之前,词体成了只有婉约而没有豪放的单性繁殖的怪物,这是从根本上违背词史规律的:东坡之后,少游体、美成体都与豪放无涉,直到稼轩体出来,东坡体才得到响应;稼轩体虽然有一个词人群体响应,但若从词体变革的宏观角度看,稼轩体最终被白石体取代,乃至整个南宋词的后期,都是白石体、梦窗体、草窗体的天下。这样,从宏观而言,则唐宋词体中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两大词人苏东坡与辛弃疾,就成了空谷足音、响应寥落的两个孤立的词人(稼轩词派之响应者如三刘等,都不足以进入温柳苏辛周姜之列)。就个人而言,苏、辛在最为优秀的词家之列;但作为词体、词派,苏辛却成了非主流的豪放词派——婉约为正宗、为主流,豪放则为别格、为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豪放说与婉约说实际上都降低了苏辛的词史地位,它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诠释苏、辛两大词体的本质特征及各自成功的原因。其二,从豪放、婉约两派的字面意义来说,豪放一词近乎贬义,因为婉约比豪放更为接近词本体乃至诗本体的本质特征。稼轩词中“放”的因素,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许是存在的;婉约派也许更多地体现了词本体约束、自律的特点,而苏辛一派则更多地具有“放”的特点。但是,这种解释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词本体作为一个词体生命,是生生不息未尝有片刻之停歇的。若从不变者而观之,则词本体一直就是区别于诗本体、文本体的一个特殊存在,不论怎样变化都不出词本体的生命范畴之内;若从变者而观之,则每个里程碑式的词体,都有着区别于他者的自身特质:南唐体不同于花间体;柳永体不仅不同于南唐体,而且也不同于花间体;少游体也同样不同于花间体和柳永体。他们都为词本体增添了新的因素。譬如,柳永在词中增添了风尘俗语和慢词长调,少游体在词中接纳了士大夫的情爱雅词,易安体则使词本体接纳了士大夫日常生活化的雅格等等,不一而足。因此,不能说苏辛一派就是对于词本体的“放”,而所谓婉约一派就完全是对于词本体的“约”;两派都是既有放(相对于词本体内部而言),也有约(相对于诗本体和文本体而言),只不过存在着放和约的不同程度而已。如果说,婉约之“约”与豪放之“放”,还多少体现了两大派别的本色与非本色、自律与拓展的相对所具有的属性,则豪放之“豪”就是对苏辛一派的贬抑。“豪”字先天地就输给了“婉”。因为委婉、沉郁比之高调、豪迈,更为接近词本体乃至诗本体、文学艺术本体的本质。高调、直白,先天地远离审美。相对于晴朗的夏日阳光,雨雪霏霏、秋风落叶、细雨凄凄,无疑更具有审美意义,体现生命悲哀的秋天以及唤醒生命意识的春天更为具有诗的审美意义;相对于豪迈的升平盛世,一片忧郁的天空更为具有打动人的力量。欧苏讨论的“悲苦之词易好,欢愉之词难工”,“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注: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诗文选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0页。),其实并非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诗歌本质的大问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诗人就应该承受时代的苦难,就应该是暂时不被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得志的,就像东坡的一生贬谪,稼轩的英雄失意,他们都是时代的孤独者、批判者、清醒者、沉郁者。人类社会凭借着这一类文化精英之个体生命的悲哀而得到反思,得到批判,得以前行。在古代,诗歌的本质首先是悲剧的,喜剧是文学艺术的第二属性——诗歌也同时具有娱乐的属性,应该成为人类劳作之余的欢乐载体,但这只是它第二属性的功能;只有在幸福的蓝天下,才有让诗歌展示第二功能的空间。相对于大多数词人词体来说,他们大多展示的是诗本体之第二功能;只有苏辛两大词人,以词体充分表达了他们或凝重旷达的格调、或悲壮沉郁的情怀、或睿智深沉的思考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所以他们才成为唐宋词人中最优秀的两大词人。对本时代君主和太平盛世的赞美,从来就不能与对时代的悲壮体验同日而语。从屈原、司马迁,到李杜,再到苏辛,没有一个是豪放者;有些是表面的豪放,骨子里却是极端的悲哀。豪放者只能是文学史中的二流,譬如以相如、子云为代表的粉饰太平的汉大赋,还有虽然属于批判范畴却缺乏内在的沉郁深重,从而远离艺术之本质,譬如被划入豪放派的其他一些词人,正是因为其豪迈的高歌而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废弃物,因为他们没有了苏辛内在的思索、内在的悲郁,只是写出一些叫嚣怒骂的豪迈文字而已。因此,悲壮沉郁,正是稼轩体有别于豪放词派其他词人的重要区别所在,也是苏辛有别于其他一些所谓婉约词人如周邦彦、姜白石等之所在。从东坡体的“人生如梦”到稼轩体的悲壮沉郁,都说明苏、辛恰恰不是高调的,说明以“豪”论苏辛并不准确。
豪婉论既然仅仅是词体表层风格之不准确表述,那么,应该何以界说稼轩体呢?笔者曾经提出,雅俗之消长是贯穿词体全部历史的两大对立因素。以上文所举词体为例:民间词为俗,早期文人词为雅;温花间为俗,南唐体为雅;柳永体为俗,东坡体为雅等。以雅论苏,对于解决东坡体的词史地位,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东坡体不再是前无古人(仅有范仲淹的几首词为先声)、后乏承续的怪异现象,而是前有张先、晏殊等先一步的以诗为词,后有少游体、美成体的雅词承续;直到白石、梦窗之后,雅词乃成为南宋词最后的归结。(注:王洪:《论东坡雅词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但以雅俗消长的理论解释稼轩体仍嫌不足:在东坡体确立了词体的雅格之后,柳永代表的俗词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东坡体处于由俗而雅的变革时期,故其地位易于确立;稼轩体处于雅格词派的深化期,就不宜再以雅俗论辛词。词史发展到稼轩体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设法区别稼轩体和白石体这同样是雅词的两大派系。
综上所述,对于稼轩体本质的认识路径,首先是跳脱出豪放婉约之说,其次是跳脱出“雄深雅健”的以雅论辛,应该使用新的理论,尝试新的认识途经。笔者拟使用词本体这一理论,阐发其“悲壮沉郁”之词体特质。悲壮沉郁,既是苏辛士大夫文人词与温柳之伶工词之不同,也是苏辛等哲人英雄非专业词人词与白石后的专业词人词之不同。同时,悲壮沉郁,也划清了苏辛之间的不同,标示了稼轩词之独特的词体属性。总之,这是比之豪婉、雅俗两大范畴更为深入一个层次的体认。
悲壮沉郁:稼轩体的本质特征
(一)酿豪放为悲壮,抗高调而沉郁
按照传统的豪婉论的说法,相对于婉约的剪红刻翠、词为艳科,豪放词主要指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作为表达政治思想的载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经国大业,主要是须眉男儿的职责;同时,在用诗词表达这种豪情壮志的时候,难免使用大字眼,写时间则为千年,写空间则是万里,或写饮酒则为千石:“坐中豪气,看君一饮千石”(《念奴娇·西湖和人韵》);或写跳跃的视野:“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征埃成阵》);或写万里长鲸,蛟龙貔虎:“鏖战未收貔虎”,“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或用奇峰峻岭,金戈铁马、英雄豪杰之类具有阳刚之美的词汇,构成鞺鞈铿鍧的意象和音响,给人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酣畅淋漓的审美快感;等等。这种“大而美”的审美特征,确实给予词本体以新鲜的内容,这是不争的事实。
诗大词小,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诗本体在发展到唐诗的时候,更以大的境界为美。无论边塞还是山水,境界都以阔大雄奇为美,从而与盛唐之音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协调,而近体诗的制约,更使这种表达方式成为某种定约。即便是柔弱的两宋,在诗体表达中,诗人的目光也常常是阔大的,是“落木千山天远大”,是“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诗人之视角并不在一个时间空间做长久的停留。而词体在其一产生,就以“小而好”为其特质:“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3页。)俞平伯先生曾说,传统婉约词专以“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迥异于“长江大河”的“清溪曲涧”(注: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正是这一体认的艺术表达。小而好,不仅仅是小令之篇幅小,而且还在于视角小:往往是一个空间的铺展、一个时间的顺延。这种变革,实际上是诗史(指包含诗词曲的广义诗史)向现当代诗歌的一种流变和演进。现代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这种心灵狭深之处的指向。小词的出现,即以狭深的小境为特征,但正如明末陈子龙所体会的:“既生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雅、音调之美,此类前哲已备,无可独造者也。”(注:陈子龙:《仿佛楼诗稿序》,《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8页。)辛弃疾的时代同样如此。稼轩体必须另辟蹊径,必须为词本体增添新的内涵,才有可能别立一宗,也才能得到创新的快感。而词本体先由外在形式——词牌体制的小而好,再到秦观、周邦彦的词体虽大,境界却小、视角却小。气格纤小,就客观上要求着大而美的审美风范的出现。词本体的形式要求、南宋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氛围(词客体)、稼轩其人“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词主体)三位一体,就呼唤出稼轩体豪放阔大的外形特征。但如果稼轩体的本质就是一个豪放可以概括,则稼轩之前的南渡体词人,如同时的陈亮、之后的刘过等人,其用事之志、恢复之心、悲愤激烈的程度、词作表现的豪放程度,比之稼轩更有甚者,为什么惟有稼轩体拥有如此崇高之地位?显然,稼轩体在豪放的表层之内,尚有更深层次的审美价值存在。
对此,古今之学者也不乏体会。周济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龠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注:周密:《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12页。)现代学者缪钺先生也有相似的体会:“吾少读稼轩词,知其雄壮而已,识力日进,解悟渐深。”(注: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所以,稼轩词似最易领会,一个“豪放”似可以概括;也最难领会,“惟稼轩词之难以领会”,是也。这种解悟渐深的体会是什么?缪钺先生的体会是:“余读稼轩词,恒感觉双重之印象,除表面所发抒之情思之外,其里面尚蕴含一种境界,与其表面之情思相异或相反……使其作品更跻于浑融深美之境。此其所以卓也。”(注: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仍需再深入探究。
如上所论,稼轩体的本质特征可以用“悲壮沉郁”四字概括。悲壮与豪放,看似差不多,其实相差甚远。豪放是昂扬向上的,类似戏剧中的喜剧、轻歌剧;悲壮则是悲剧,是正剧。以音乐来比,豪放似是高音部,宜以唢呐、板胡之类伴以铙鼓;悲壮则近乎大提琴,是忧郁的、抒情的、深沉的。两者之间有着雅俗深浅的不同。豪放词以政治情怀为主题,相对于词为艳科的儿女情长,当然有雅俗之别,但是,雅俗的内涵,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南宋之后,雅词已经成为词坛绝对的共识,俗词基本上被词本体清除出门户。这样,在词本体中的雅内部,必然会有进一步的界定。譬如,豪放词以政治情怀为主题,堂屋特大,气象恢宏,比之姜夔、吴文英的雅词,就有着词体题材的不同;但同样在豪放词内部,又有着辛弃疾的悲壮崇高之美与他人的豪放激越之美。相比之下,稼轩体更为含蓄蕴藉,有更深层次的雅文化的审美意义。
周济曾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注:周密:《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12页。)这确实是极有见地之论。豪放的高调与沉郁的低调相比,后者更为符合词体甚至诗体的美学特征。稼轩体之后的豪放派,因走向叫嚣怒骂而使人生厌;直到现在,仍有一些高调诗歌,使人望而生厌。这都说明了“豪”字之不宜。因此,这“敛雄心,抗高调”的美学选择,正是稼轩体与豪放词风格不同之处的根本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固然说过,“(稼轩)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这是关于稼轩体“豪放”特色的论述;“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这其实是“悲壮沉郁”主体世界托寄于词的别样表达。
(二)他者化为自我,昔我对比今我
细细体会我们不难发现,稼轩体比之其他豪放词人,在表达激越政治情怀时的方式有明显不同。陈亮等人一气直说,说得痛快,无异于当庭痛斥,无异以词为奏折文章,只拥有时代大我之普泛,而乏小我之亲切;稼轩体则将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激烈壮怀融入自身的难酬壮志,以小我之窗口凝视大我之时代,则时代莫不着我之情感。诗歌是最具有个人化的本体,在抒发诗人自我之情怀时,往往是以一滴水而映射大海。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生活之个人化、政治理想之小我表述,才使稼轩体在本质上并非豪放而毋宁说是悲壮。
就其生命历程来说,稼轩经历了由青少年的理想人生到中晚年现实人生的悲壮历程。由于理想高远,才华横溢,英雄不用,其词风遂有失意之悲壮。在我们所阅读的所谓典型的“豪放词”中,莫不如是。譬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读者只观“看剑”、“吹角”、“八百里”、“五十弦”之类的豪迈字面,却没有注意到,起首词人就说“醉”说“梦”。醉中看剑,梦中吹角,皆是虚幻之意,从而将这种豪放的画面,统统笼罩在悲剧的氛围之中。于是,越豪放也就越悲壮,越激越也就越沉郁,且妙在词人并不说明,一直到“可怜白发生”的结尾,才隐隐吐露出内心深处之隐痛,正如陈廷焯所体会的“沉雄悲壮”(《云韶集》卷五),也如同梁启超感受到的“无限感慨,哀同甫亦自哀也”(《艺蘅馆词选》丙卷引);若将此类词视为“豪放”,则真如稼轩词所说:“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首《水龙吟》词,也同样说明了稼轩体的大我情怀的小我表达:“遥岑远目,献愁供恨”,则一切景语皆为情语,“千里清秋”之阔大,皆在“江南游子”“愁”与“恨”的视野之中。
稼轩凡写战争及国家危亡之事,多化作人生之回忆,是将他者化为自我,昔我对比今我,将人生之种种经历、情感、体会,经过漫长岁月之沉酿,来写出现实之心境,如同美酒佳酿,时越久而味愈浓,昔越豪而今愈悲也。所谓“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往往是由“追亡”之过去时态,幻化为“今不见”之现在时态,所以,其情感表征往往会失去当年的豪放激越,而化为当下的悲壮沉郁,正所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皆见《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是也。以今说古,故事莫非今愁:“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由于有了小我,故有个灵魂所在,多种对立便在其中得到了统一;无论古今,无论情景,无论悲喜,经过小我之目光,都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的美丽景致,与刚刚悲叹的“兴亡满目”构成一体,由平和再推向悲壮——“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以上均见《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其他豪放词人与稼轩相比,难免相形见绌。如南渡体词人李纲《苏武令》(上片):“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音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就时间而言,多是现在时,多是书写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与稼轩的时态不同,角度不同,风格自然也就不同。李纲另有七首咏史词,应该说对于稼轩的以故说今有所启迪,但李纲的咏史词就显得古今他我未能打造为一体,如《喜迁莺·真宗幸澶渊》:“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从中固然可以想见其现实指向,但却只是大我义理上的,而非小我情感上的。
(三)以典故凝铸意象,托他人表达自我
一般人都会直觉地将词体使用典故的变革算在豪放词派的头上,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在词本体的生命历程中,东坡体首先大量用典。东坡体之本质特征,在于词体的雅化,而其所以用典,也正是这种雅俗较量中的有力手段;稼轩体是在词体中使用典故的又一大词体,但使用典故的直接参照物,已经由雅俗消长变为豪放词派内部变革的需要,也就是说,稼轩体既然要“抗高调”而“敛雄心”,使用典故就成为抗高敛雄的极好手段。
稼轩体之所以大量用典,应该从词本体演进以及词本体与诗本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角度来审视,才能深入理解。就其自身先天的体制而言,词本是写给女性的(首先是写给歌女演唱的)、自身也具有女性特征的特殊诗体;词最初原与学问典故无涉,是一种纯情表达。从白居易、温庭筠、李后主、乃至欧阳修,在他们的词作中都见不到学问的踪影;直到东坡体的出现,才为词本体的机制中增进了学问的因素。词体本身也是诗体之一种,其内部当存在着对于典故方式的需求。因此,东坡体虽曾受到批评家“非本色”的指摘,但仍然受到广大词体受众的喜爱。
词本体生命演进的规律,是在不断破位之后的不断复位,在不断放纵之后的约束。豪放之“放”与婉约之“约”,正是词本体不断破坏又不断约束的过程。没有放纵,则难以前进;没有约束,则不成规矩。在东坡体的放纵与词体破位之后,除了少量的词人词体如山谷体、方回体效法东坡体用典之外,词史发展之主流如少游体等,仍然在纯情词体的范畴之内,至美成体则出现另外的格局,那就是婉约派用典而豪放派反而极少用典,呈现婉约与豪放交错纷呈的局面,也就是说,应该称为“婉放”与“豪约”。其中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但也可以想得明白:典故就其本质而言,是更为凝练的意象,是高雅的意象,它与词本体要眇宜修、含蓄蕴藉的本质并不冲突。从传统的豪放与婉约两大派别来说,典故更应该为婉约所有,因为婉约更为讲究含蓄,而豪放则更多直露。但为什么本应属于婉约的典故方式,反而由所谓豪放的东坡体始创呢?这就是由婉约之“约”字所制约,它能够充分体现词本体的自律性。由于词本体在产生初期是由民歌词而来,不用典是民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文人词在摹仿民歌词中,就先天地形成了自然清丽的词体特征。然而,在柳、苏的雅俗较量之后,词体的雅化便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用典既合于雅化趋势,又与词体含蓄要眇的特征吻合,于是作为北宋集大成的美成体之用典也就成了必然的抉择。美成体大概是所谓婉约派的第一次大量用典,象征着词本体对于典故方式的正式接纳,或者是东坡体之后的再确认。典故与雅格,是美成体与东坡体之间的主要关联。
但是,美成体之后的南渡体和易安体这两大词体,都不以用典为特色(前者多直白,后者多提炼寻常语入词,是柳永体词语尘下的雅化提升)。一方面,在山河破碎的历史时期,用典并非适宜,而词本体每当接纳新的因素之后,也往往会有一个往复的确认过程。这样,稼轩体之大量用典,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自稼轩体对于典故意象的大量使用后,婉约内部与豪放内部都分化出用典与不用典的两大阵营。这本身就说明了豪放婉约之说的弊端。稼轩体之用典,更进一步将典故改造为词人表达思想的直接语言。也就是说,词人很多的思想可以使用典故来间接表达。博大深邃的华夏文化,成为稼轩其人孤独灵魂对话的客体、倾诉悲壮沉郁情怀的载体、建构语言修辞的媒体。诗本体中发展到江西诗派的流程,由稼轩体直接嫁接到词本体的生命之中,随后,又反转过来强烈影响作用于诗本体之生命,由此便催生出更加璀璨的诗词艺术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