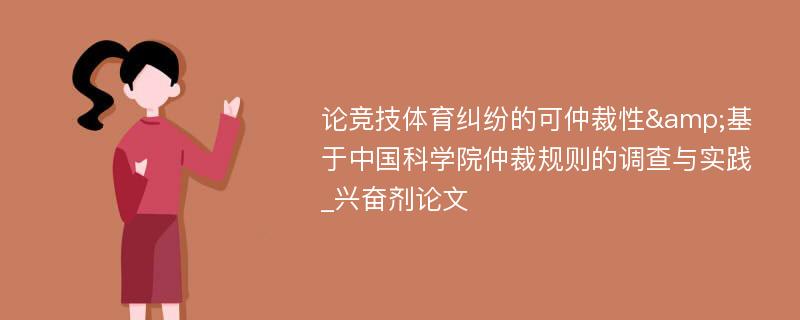
论竞技体育争议之可仲裁性——立足CAS仲裁规则及其实践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则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CA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1)10-0005-06
修回日期:2011-08-12
1 可仲裁性之界定
无论国际商事仲裁抑或国际体育仲裁,它们在本质上皆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结合,最集中体现仲裁这一属性的方面即为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它反映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是“在各国公共政策所容许的范围内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界限[1]”。在司法与仲裁实践中,可仲裁性问题还常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混淆在一起[2],尽管逻辑上二者互为前提,但是可仲裁性仅仅限于法律对仲裁范围的设限,与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显属两类不同范畴。
可仲裁性问题具有层次性,最典型的分层法是将可仲裁性划分为主体可仲裁性(subjective arbitrability)和客体可仲裁性(objective arbitrability)[3]。主体可仲裁性涉及主体要素是否具备提交仲裁解决争议的适格问题,又称属人理由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personae),它尤其关注特定的主体,诸如国家奥委会、地方权力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因其地位或功能是否具备申请仲裁的主体资格;客体可仲裁性涉及仲裁争议事项能否以仲裁的方式予以消解,又称属物理由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materiae)[4]。
一般意义上的可仲裁性问题仅指客体可仲裁性,即仲裁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它关涉的是争议事项作为仲裁主题在法律上的适格问题。主体可仲裁性是对客体可仲裁性的延伸分析,因为从严格的逻辑上讲,国际体育仲裁能否进展关键取决于各国立法对争议事项的确认与限制,作为仲裁主体要素的当事人只要具备辨别是非、理智而清醒的判断能力即可。换言之,只要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是出于自身的理性欲求,是两个自由意志的偕同,是主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真实结果,则他们的地位、功能、状态通常不在考虑之列,侧重考虑的则是他们之间的争议是否具有商事或体育方面的可仲裁性。
鉴于国际仲裁实践中,判断某一争议是否具有商事性或体育性并非易事,因此需要引申出一些辅助判断标准。在这一逻辑进程中,主体的地位和功能成为判断客体性质的辅助线,从而形成主体可仲裁性问题。主体可仲裁性是客体可仲裁性的延伸评价指标,它的功能在于,在错综复杂的仲裁实践中辅助判断客体属性;主体可仲裁性功能的发挥及其存在应归结和立足于客体可仲裁性,在仲裁实践的具体操作中必须为着客体可仲裁性进行立体综合的评价,而不得独立自为。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将主体可仲裁性和客体可仲裁性还原为当事人的仲裁适格性(parties capable of arbitration)和争议的仲裁适格性(disputes capable of arbitration)[5],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下文将立足于客体可仲裁性对竞技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专题考察。
2 竞技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
对于国际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笔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三个层次,即应然态的可仲裁性、法然态的可仲裁性以及实然态的可仲裁性。
应然态的可仲裁性是指,从伦理和道德的深层出发,能够提交仲裁化解争议的当然适格性。它脱离国别体育伦理个性,直指为各国所公认的、可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的资格或能力。它构成法然态和实然态可仲裁性标准的标准,是批判和指引后两者更替和变革的超越性指标,它表征的是体育仲裁争议事项的理想设定。
法然态的可仲裁性是指,各国立法、条例、国际条约通过肯定或否定、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容许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体育争议事项,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可仲裁性概念。法然态可仲裁性是公意与私意叠合的产物,它是在应然态可仲裁性基础上根据各立法者的意志作出的保守调整,是附加国别或地区的现实考虑后对应然态可仲裁性进行的实证修正。它同时也为体育争议当事人圈定了仲裁自治的具体界限,在法然态可仲裁性框架内当事人之间的实然态可仲裁性得以可能,法然态可仲裁性是衔接理想与现实的过渡环节。在国际体育仲裁实践中,法然态可仲裁性主要体现在体育领域最具影响和威望的《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之中,同时国际体育仲裁院CAS(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下简称为CAS)仲裁规则也对仲裁争议事项的范围问题作出了概略的指示。《宪章》第74条对仲裁主题范围作出了正面但宽泛的界定,对比CAS仲裁规则相关规定可看出,后者在仲裁争议事项的范围上比《奥林匹克宪章》之规定更为确切。在ICAS/CAS《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第1、27、47条所构成的规则体系中,体育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被大致勘定,它们构成理解国际体育界法然态可仲裁性的必要参考。
实然态的可仲裁性是指,体育争议当事人在纠纷产生前后实际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也就是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所具体约定提交仲裁解决的具体问题。它不能逾越法然态的可仲裁性范围,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极限。由于仲裁本身作为一种自治性救济制度,将哪些争议或争议的哪些方面提交仲裁均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当事人实际约定的仲裁争议事项也就构成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范围,任何逾越仲裁争议事项、擅自扩大仲裁范围的仲裁裁决将引起各国立法和司法的否定性评价。此种否定性评价在国际上常存两种做法:一是明确规定,撤销整个裁决中超越管辖权的那一部分,其余部分有效;二是未作明确规定,法院可自由裁量撤销整个仲裁裁决或者撤销部分仲裁裁决[6]。由于瑞士联邦法院作为最具权威的、受理质疑和挑战CAS仲裁裁决的管辖法院,它在评价CAS裁决合法性时所适用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立法态度如何,将左右着CAS裁决的命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该法相关内容。《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条规定,裁决超出提交仲裁的请求范围,可请求法院撤销该裁决。该规定明确了仲裁庭在仲裁案件时的可仲裁范围,以及超越实然态可仲裁性时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也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请求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由是观之,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递进性地包括应然态(A)、法然态(B)及实然态(C)三个维度,三者的关系应为(A≥B≥C)。应然态可仲裁性立足体育仲裁之本质对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作了最宽泛的圈定;各国立法或判例在此基础之上考虑本国特殊处境而对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作了国别限制,形成具体的立法规定或司法判例;在法然态的可仲裁性标准内,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条款中所确定的争议事项即为实然态的可仲裁性。对受理体育争议的仲裁庭而言,它们必须从两方面考察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以决定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仲裁管辖是否合法:一方面,应确保该争议事项具有实然态的可仲裁性,即所受理体育争议属于当事人约定提交的范围;另一方面,应确保该争议事项具有法然态的可仲裁性,即便该争议属于当事人约定提交的范围,也必须遵守所适用的法律所限定的范围。应然态的可仲裁性一般不需要在具体仲裁实践中进行考虑,只是在仲裁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过程中才有可能对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应然态的可仲裁性并不影响体育仲裁的具体进行,而只是影响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3 可仲裁的竞技体育争议之特征
体育仲裁实践中据以评价体育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标准是法然态可仲裁性,它须得满足两个特征,即与体育相关(sports-related),并且具有处罚性(disciplinary)。第一个特征标志出体育争议有别于商事争议的个性,第二个特征则标志着竞技体育争议有别于一般商事性体育争议的个性。一般的商事争议及商事性体育争议之可仲裁性限于平等者之间的争议,唯有竞技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才要求其仲裁对象具有非平等者之间的处罚属性。
3.1 相关规范
对体育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两个要件的理解需着眼于对以《奥林匹克宪章》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的整体解读。《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体育领域的基础性文件,它的精神和内容是理解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阿基米德点。根据《宪章》第74条的规定,CAS受理并展开仲裁必须依据ICAS/CAS之《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该法典第1条明确规定:为通过仲裁解决与体育相关的争议,由此设立ICAS和CAS两个机构,此类争议尤其包括反兴奋剂纠纷。法典第27条和47条进一步对此类争议作出界定:
第27条规定:一旦当事人同意将与体育相关的争议提交CAS仲裁,该法典的程序规则应予适用。此类争议包括两类:一是产生于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或产生于事后仲裁协议确定的事项之争议;二是在各体育协会、联合会或体育机构立法或规章许可的情况下,或在特定上诉仲裁协议有约定的情况下,针对上述机构内部所属纪律机构(disciplinary tribunals)或类似机构作出之决定而提起的上诉争议。第47条有关上诉仲裁的规定基本上重复了第27条的内容:“只要体育协会、联合会或体育机构立法或规章许可,当事人一方可对上述机构所属纪律处罚庭或类似机构的决定提起上诉,或者在缔结了特定仲裁协议情形下,当事人一方根据上述机构之立法或规章穷尽法律救济后可提起上诉。”
可见,对可仲裁的竞技体育争议事项的界定是由三级规范构成的:《奥林匹克宪章》+《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各体育协会之章程。具体言之,第一级是《奥林匹克宪章》的总括性规定,该规定在性质上属于一个转致条款,其本身对于仲裁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并未明示,而是借助对《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之指引来充实和完成,后者则构成判断可仲裁体育争议事项的第二级规范。在法典上述三条款中,可提交CAS上诉仲裁的主题得到初步明确,即必须“与体育相关”,并且是“针对纪律处罚庭或类似机构作出的处罚性决定”。但对于纪律处罚庭或类似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之范围与界限,法典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完整界定。为弥补这一不足,法典也借助了转致艺术,即能够上诉到CAS的体育类处罚性决定之性质和种类,取决于受仲裁条款或特定仲裁协议约束的体育协会、联合会或体育机构的章程或《宪章》之规定。因此,对体育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判断进一步延伸并被泛化到各奥运类或受特定仲裁协议拘束的非奥运类体育机构之立法或规章中,并构成界定可仲裁竞技体育争议的第三级规范。
这三级规范体系采取层层递进的演绎方法,一方面保证了范围界定的严谨和圆融,消除了体系内可能存在的重叠与空白,另一方面它维持了可仲裁竞技体育争议事项的动态和开放,各体育机构可对自身纪律处罚决定的类型予以动态调整。尽管争议事项可仲裁性之界定流于宽泛,但我们仍然能够结合国内、国际规范以及仲裁实践对“与体育相关的处罚性决定”进行深度考察。
3.2 与体育相关(sports-related)
体育界对体育纠纷的认识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有观点认为,体育纠纷是因从事体育活动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一种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它是在体育活动中以及解决与体育相关的各种事务中,各种体育活动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体育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7]。该观点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竞技性体育争议。在奥林匹克赛事领域,权威的官方文献对体育纠纷最精确的界定是ICAS/CAS《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指出:“此类纠纷涉及与体育相关的原则性问题,或者涉及影响体育以及一般地关系或关联于体育之任何活动的实践或发展的金钱或其他利益问题。”相对于《奥林匹克宪章》“与体育有关”的抽象规定,法典的阐述表达了它对这一概念具体化所进行的力所能及的努力,它将体育纠纷分解为三类主题,即与体育相关之原则性问题(principles matter)、金钱问题(pecuniary matter)和其他相关的利益问题(interests matter)。但与其说法典明确化了体育纠纷的内涵,毋宁说它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它用本身亟待具体化的、同样抽象的概念在堆砌着一个循环界定,即“sports-related”就是“sport and activity related or connected to sport”。
应当注意到,尽管奥林匹克规范体系以及ICAS仲裁法典对体育纠纷的具体类型并未明示,但都毫无例外地特别强调了体育领域中反兴奋剂问题属于可仲裁的竞技体育争议。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运动本身就富含竞争性、对抗性,运动员或参赛团体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或为了超越极限、刷新纪录等原因而服用兴奋剂药物,从而根本摧毁奥林匹克“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并造福人类的理想”[8]。兴奋剂问题在国际体育领域泛滥成灾并非危言耸听,有观点甚至认为“奥运会是兴奋剂和腐败的组合[9]”。
兴奋剂服用问题很可能牵涉各国刑事立法问题,希腊、法国等国家法律就如此[10]。我国刑法将服用特定类型兴奋剂药物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尚未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畴。无论何种定位,都将影响此类争议的可仲裁性,因为具有可仲裁性的事项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自由处分性,而刑事问题和违法问题不具有此种特质因而存在可仲裁性的危机。然而仲裁实践却无可置疑地确认了兴奋剂问题作为竞技体育仲裁主题的适格性,CAS通过仲裁裁决明确认定:“运动员与体育协会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性质,不存在刑法适用的空间。对于‘疑罪从无’(in dubio pro reo)原则,罪刑法定原则(nulla poena sine lege)和……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规则而言尤其如此[11]。”在另外一个仲裁案件里面,仲裁员对运动员服用大麻的行为进行了评价,并对自身的权力作出了限定:“仲裁庭认为,从伦理和医学角度而言,服用大麻是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然而,国际体育仲裁院并不是一个刑事法院,它不颁布也不适用刑法规范。本庭必须在体育法的关系范围内作出裁决,并且不会作出从未有过的制裁或处罚[12]。”仲裁庭的意见清晰地传递出如下信息,即仲裁庭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兴奋剂问题尽管可能关涉刑事立法,但仲裁庭有权在体育关系限度内作出裁决,它具有体育法上的可仲裁性。
CAS的仲裁实践以及相关规范体系对反兴奋剂问题的态度促使更多类似案件提交CAS裁决,以至于“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因使用兴奋剂而引起的争议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争议中最主要的类型。……兴奋剂争议变成了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分院和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仲裁的主要争议[10]。”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为例进行纵向量化比较,可以统计得出兴奋剂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体育仲裁主题范围中的权重。2000年悉尼奥运会CAS特设分庭审理的15个案件中,涉及兴奋剂的案件有4个[12],约占26.67%;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兴奋剂问题一跃成为CAS特设分庭的三大主题,“雅典奥运会产生了空前规模的兴奋剂案件。在以往的夏季与冬季奥运会中,运动员曾被发现使用禁止药物,但与雅典奥运会的结果却无法相比。在奥运村开放与闭幕式结束的期间内,有超过20名选手被指控兴奋剂犯罪。这导致相关运动员被剥夺了3枚金牌,1枚银牌与3枚铜牌。其他兴奋剂违规团体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受到了取消比赛结果并禁止参加奥运会的处罚[9]。”兴奋剂控制与消除问题必将成为全球体育领域共同攻关的难题,也将是CAS等机构进行体育仲裁的重大主题。尽管它同时也构成某些国家刑法打击的对象,但由于其“与体育相关”的属性而具有当然的可仲裁性,这是竞技体育仲裁对传统仲裁的突破和发展。
3.3 处罚性(disciplinary)
作为与国际民商事仲裁事项截然对立的一个特征,国际竞技性体育争议属于更具行政性质的处罚性决定,其结果直接导致仲裁庭在法律适用上的行政化,即合同法规则较少得到适用,行政法的基本思维和规则渗透到竞技体育仲裁之中。CAS在2002年的一个裁决中就认为,作为被申请人的国际泳联违背了行政法领域的比例原则,罚责不当,应予平衡[13]。竞技体育争议的行政性表现为其处理结果的处罚性,对此应作如下反面排除:
3.3.1 平等关系排除
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为民商事关系。民商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益对抗,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原则,当事人任何一方无权命令和制裁另一方。此类纠纷不具处罚性,它一般地属于国际商事仲裁的主题范畴,而根据《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第47条的规定,能够作为CAS上诉仲裁事项的是由体育协会内部所属纪律处罚庭或类似机构作出的决定。正如学者所言:“在与体育实践直接相关的争议中——排除产生于与体育相关的商事合同的争议——适用的一般原则并非源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合同法,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刑法或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因此,“公法和刑法原则(如罪刑法定、处罚的比例性、行政事务中的善意原则、规范文本解释原则),而不是与国际合同法相关的原则(如当事人自治、有约必守、善意、当事人的正当期望)在奥运会特设分庭仲裁中发挥作用[12]。”
3.3.2 技术规则排除
为防止过度涉入竞技体育从而影响竞赛进程中裁判员的独立地位和判断能力,并防止仲裁员僭越其职能而质变为赛事裁判,CAS为自己颁定了一条法则,即涉及技术规则运用的“赛场裁决”(field of play decision)不在仲裁庭管辖和审理之列;另一方面,技术规则的运用方式则不能豁免于仲裁庭的审查监督。由此,CAS仲裁庭作为“裁判的裁判”明确了自身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界限,它在维护赛事裁判独立性及在必要的时候予以介入二者之间设定了完善和成熟的平衡,使自身不致被纠缠于在理解和运用竞技规则上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难题,而能在适当的距离和位置上从容和客观地评价赛事裁判运用技术规则的方式是否背离正义精神。在理解“技术规则排除”此一准则时应把握如下要点:
其一,“赛场裁决”是竞技规则的典型运用,因此不具有体育法上的可仲裁性。在加拿大某运动员诉国际联盟(FISA)案中,该案涉及对“赛场裁决”的界定,从而确定案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加拿大选手就其因在半决赛中妨碍相邻航线的南非赛船而被罚出决赛,该项处罚意味着加拿大选手将不能参加该赛事中的任何后续比赛,其不服该裁判决定而上诉至FISA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维持了原裁定之后,加拿大选手将争议提交到CAS特设仲裁庭。
加拿大选手需要证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将该案所针对的事项非属“赛场裁决”,以此证明其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加拿大选手认为,上诉事项并非赛场裁定,而是执行委员会的裁定。CAS特设分庭认为,执行委员会适用规则正确,它在制裁方面享有广泛的裁量权力,且该裁定属于依其规则所赋予的权力范围。特设分庭指出,仅在委员会专横行动或越权的情况下,它才可以依据裁量权审查该裁定;执行委员会在本案中运用规则并无错误,仲裁员因此不得再次管辖并评审理定。
本案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所有CAS仲裁中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不干涉裁判的裁定。裁判在赛场上是最有资格也是最有权力作出赛场裁定的人士,仲裁员应仅在裁判违背诚信裁决的前提下才进行干涉。二是仲裁员不应仅为了其自身所认为的公正结果,而依裁量权推翻一项裁判的裁定。仲裁员仅在该裁定是武断作出,或超越权限的情况下,方能审查赛场裁判所作出的裁定。在这两类案件中,主张裁定不当的人将承担举证责任[9]。
与此案类似,在CAS特设分庭裁决的另一个案件中[14],朝鲜国家奥委会诉国际滑雪联合会,认为后者所属纪律委员会剥夺朝鲜滑雪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决定应予撤销,因为主裁Hewish的裁决受公众压力的不当影响是“有违公认的社会规则且专断的。”CAS特设分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重申了以下两点:第一,CAS仲裁庭对于公断人、裁判员、或其他官员在竞技场上作出的“赛场”裁决不作审查。这些公断人、裁判员或官员有权力适用特定的比赛规范或规则。第二,仅在有证据——通常为直接证据——证明恶意的情况下,仲裁庭才得审查赛场裁决,在此情况下,例如“随意”、“违反职责”,或者“不良意图”等任一用语都意味着存在某种对特定参赛团队或参赛者的偏向或歧视[14]。
其二,技术规则或竞技规则的运用不具有可仲裁性,但此类规则运用方式上的瑕疵,诸如腐败等恶意(bad faith)、或被恶意适用(malice)、或被专断或违法适用(arbitrary or illegal)[15],则具有可仲裁性。较早确立这一准则的典型案件当数Mendy vs.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e Boxe Amateur(AIBA)[16]。该案发生在1996年7月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法国拳击运动员Christophe Mendy不服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的处罚决定而向CAS特设分庭提出申请。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因其在比赛中击打对手腰部以下而取消其竞赛资格。虽然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出仲裁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但仲裁员依职权主动提出了该问题。这一争议的核心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申请人是否击打对手腰部以下。仲裁庭创设了如下规则,即一切产生于体育事项的争议均可仲裁,而无论其主题为何;但当争议涉及竞技规则或技术规则的适用时,仲裁庭应当避免干涉竞技场上裁判、公断人或其他官员的裁定,除非此类规则被不当适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也一直坚持认为,对技术规则或者游戏规则提起的是否违法之诉不能由法院或者仲裁庭进行审查,因为游戏规则不属于法律范围[12]。据此,CAS特设分庭以不可仲裁为由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其三,竞技规则是确保竞赛和竞争正确过程的规则,它不同于法律规则,后者不得豁免于仲裁和司法审查。WCM-GP Limited诉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Motorcycliste案[17]涉及技术性规则(technical rules)或赛事规则(game rules)的解释,尤其是涉及赛事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比较分析,从而有助于理解和判断争议主题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仲裁庭明确了赛事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区别:所谓“比赛规则”,是指意在确保比赛和竞争正确过程的规则,除了在极例外的情况下,此种规则的适用不得进行任何司法审查;所谓“法律规则”,则是在比赛或竞赛过程之外发生的,能够影响行为人司法权益的成文法规则或判例规则,基于这个原因,它必须接受司法审查[17]。
需要指出的是,不受审查的竞技规则范围近年来正在缩小,“竞技规则不可审查”的原则受到挑战。一些学者对竞技规则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认为体育不能也不必游离于法律范围之外。CAS对此的态度是谨慎介入并保持克制,因为相比于仲裁员,体育裁判更了解事实,并且更加熟悉如何运用技术规则,裁判在决定技术问题时比法律专家处于更为有利位置。因此,裁判的决定优先是有意义的,除非该决定明显侵犯了运动员的权利,或者以仲裁员的话来说,它是“法律上的错误,一个错误的或者恶意的行为”[12]。
4 结论
综合衡量上述因素,对可仲裁的竞技体育争议之界定可借鉴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对“商事”进行鉴定的方法,采取非穷尽列举、附加正反两面界定的方式,即它是直接关联于或产生于体育领域的处罚性争议,该争议一般针对体育协会所属纪律处罚机构的决定而提起,涉及与体育相关的原则性问题,或者涉及影响体育以及直接关系或关联于体育之任何活动的实践或发展的金钱或其他利益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运动员或团体参赛资格确认、奖章的归属与返还、裁判或其他官员恶意执法等问题,尤其包括反兴奋剂问题,但不包括与体育有关的民商事争议、裁判等执法人员在竞技场上依据“竞技规则”作出的赛场决定。根据该定义,具有可仲裁性的竞技体育争议事项含有如下四个特征:
其一,它直接地、而非一般地关联于或关系于体育或运动实践。此一特征将它与一般地产生于体育或运动实践的民商事体育纠纷剥离开来。其二,宏观层面上,它主要包括三类法律关系,即与体育相关的原则性问题、金钱问题和其他利益问题,由此展开形成体育仲裁的三大主题群。其三,微观层面上,上述三类法律关系具体展开为参赛资格确认问题、体育管理特许权授予问题、反兴奋剂问题等,但不限于上述典型纠纷类型。其四,可仲裁的竞技体育争议明确排除民商事体育类纠纷、技术规则的适用纠纷,但裁判类执法人员诸如恶意地适用竞技规则时,其执法方式具有可仲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