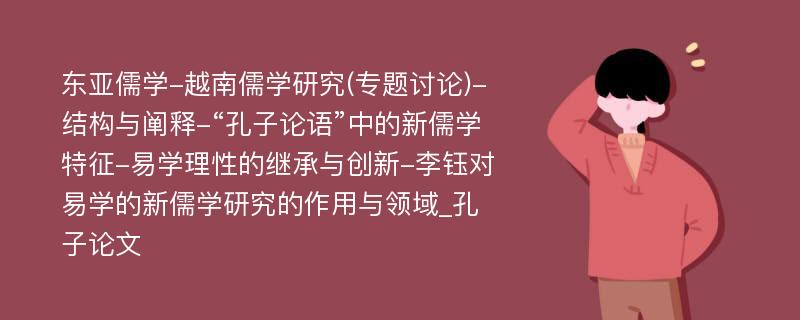
儒学在东亚——越南儒学研究(专题讨论)——结构与诠释——范阮攸《论语愚按》的理学特质——易理的承接与创新:黎敔理学易学的角色与论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理学论文,论语论文,东亚论文,越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8-0022-09
结构与诠释——范阮攸《论语愚按》的理学特质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院长。
两千多年来,儒学在与越南传统文化的融合中持续发展,形成了具有思辨性、实践性特色的越南民族儒学。在众多的儒学著作中,越南儒学家范阮攸(1739—1786)的《论语愚按》算得上是较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 《论语愚按》一书共分为四篇——《圣篇》、《学篇》、《仕篇》、《政篇》。范阮攸之所以把《圣篇》放在该书之首,是为了表明其希贤希圣之心迹。这也是其价值理想和人生标的。以圣人盛德的事实,以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圣人的学问威仪、为人处事、居处服食、应事范物等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给人以感性的圣人形象,而不是虚无飘渺,从而引导人们学做圣人。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首要有学做圣人之心之志。范阮攸认为,孔子从十五自志于学至七十不逾矩的成圣历程,是一个“积累勉学”的过程。他与俗学务求超躐、不按次序不同,是出于至诚之心,而卒有成。从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可体认到,学不仅是广采博纳知识,重在提升体认水平、道德修养、人格理想,而达从心所欲的自然自由的思想境界。
学习必须自谦,孔子不仅每事问,而且虚心求学,终身学不厌、教不倦,这便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的缘由。为什么学而不厌?范阮攸体认“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 说:“盖《易》道无穷,圣心亦无穷……圣心无穷,有以见《易》道之无穷,何厌之有,学者宜深思矣。”譬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引申之至于千万亿兆,无非道之所在,求无穷之道和圣心,自然不厌;只有不厌,才能坚持不懈,终身事之。
学做圣人之心之志立,进而明如何圣之为圣有三:
一是天即圣、圣即天。一般学者只“知求圣人于圣人,不知求圣人于天”。天作为终极的可能世界,即理想境界,如何与圣人为一?范氏在解释《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时说:“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之身,斯文所恃以在也。由文王至于孔子,斯文之在孔子必矣。有可必之理于天,匡人虽暴,安能以夺天理哉!”圣人是道的体现,圣人之身就是道的载体和安顿处,即是道得以存在的所依恃处。这里道与天理相近,天若不要消灭“斯文”,则天理在孔子,天理未亡,圣人自存,谁能得而害之。
圣人之所以与天融合,是由于天道、天理与圣人相通,作为观念性的天道、天理必须通过圣人来呈现和显现其生命力、影响力。一次孔子病重,子路请求向天神地祗祈祷,范氏认为,“疾病自可以从容而顺适乎理,亦何所事于祷哉”!《论语·子罕》篇又载,孔子病重,子路要成立治丧处,后来孔子病渐渐好转,孔子说:“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范氏解释说:“顺其自然,有则有,无则无,可以对越上帝,又乌用由之行诈哉!”无臣而有臣,不仅是欺诈天的行为,而且是逾越礼的行为,因此孔子很生气。如果说天道、天德、天理是外在的、超越的,它需要通过圣人来体现的被动型外输内应交感相合结构,那么,诚意则是内在的、隐藏的,人以其诚意的主动型内求外应感动相合结构。被动型与主动型两种天与圣感应相合结构形式,既把圣提升到形而上的天地境界,又把圣落实于人间世界,这是圣之为圣的价值理想。
二是圣人纯理无欲。“圣人一饮一食,莫非天理,斯须必谨,毫厘不差,一点人欲之私,不得以动之。学者能即此反之于心,省之于身,逐节而加察焉,虽未造至善之地,亦庶几不失其正矣。”范阮攸据孔子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性本善说,认为“君子小人其初皆具天理之性,保其理则上而为君子,失其理则下而为小人,毫厘一分,天壤自隔”。人之初虽都具天理之性,但习相远而分别,便自隔为君子小人的品格人性。天理人欲,凡事都要辨别,恭、慎、勇、直本为天理之自然,违之便违反了自然的礼则,就是私欲了。范阮攸在诠释“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② 时说:“孔孟之后,世之学为儒者多矣,惟其立心伪而不真,故其学只为名誉利禄,不干自己分上事。盖为学则同于君子而操心则入于小人,所争理欲一毫之间,遂有君子小人两样之别。”后世儒者心伪不真,学是为了名誉利禄之私。学圣贤之书虽同,但两者目的不同,理欲之争,君子小人之分。
理欲之间,“私欲日长,天理日消,患害之及其可免乎”!理欲、公私处消长变化之中,“一辰蔽锢于物欲之私,固不能以正道自持”。天理为公,人欲为私,人为物欲之私所蔽,便私欲长而天理消。所以,“君子小人,只争公私二字”。范氏在诠释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③ 一段时说:“夫康子以‘使’字问,有为之私心也。圣人以‘则’字答,自然之公理也。为政者诚究乎此心存乎公而不存乎私,则民之化之,不待‘使’也”。季康子要“使”人民,这是出于私心,孔子的回答是出于自然的公理,为政者只有出乎公理,而不出于私欲,人民自然受教化。为政者的道德力量对治理国家有重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圣人纯理无欲,这是圣之为圣的标准。
三是中和仁义。范阮攸以《中庸》的“致中和”诠释孔子闲居的心态气象。“中和”就是性情未过中,未过中便是正。“圣人性情之正,哀乐未尝过中。独至于颜氏则恸而不自知,盖恸其可恸,亦中也。”朱熹认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④。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了,孔子很悲哀,跟从孔子的人说,您(孔子)太悲哀了。范氏认为未尝过中,恸其可恸亦为中,体现了圣人性情之正。“性情之正,圣人自然而然。”性情之所以中正,是由于圣人无私。“圣人应物之心,常如明镜止水,虚灵而不伪,中正而无私”,以此圣心应物,没有不可弃、不可化、不可为之物、之机、之时。无私便是公,从公出发便能公正。“存之公则施之正,夫好善恶恶,人心所同,理欲分而同者,反相悬隔。”唯仁者能公正,能好人,能恶人。
范阮攸又从公私、善恶、义利视阈来观孔子的“和同”问题。他在诠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⑤ 时,将义利与和同对应,以分殊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讲义而不讲利,即为公而不为私;小人同而不和,讲利而不讲义,即为私而不为公。君子公开论争交辩而不失和气,小人利聚而冲突,结党营私而离异。君子和而不同的外在呈现是和平见于气。尽管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但可自然顺理、心地和平、气象平和。“其处己接物,温和平易。”
在范阮攸看来,圣人出于仁义之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及物,便“仁民爱物”,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致中和。范氏说:“仁乃圣人之全德。”这种全德,体现于爱物。“圣人仁物之心,触处发见,岂若禁杀放生,如异端者所为哉!”禁杀放生是出于爱物之心的行为活动,犹现代的环保主义者。但爱物与爱人相比较而言,范氏在诠释“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⑥ 时说:“爱人重于爱物,仁之心必有等差。观此则知墨之道可辟矣。”在当时,养马人的价值不如一匹马的价值的情况下,孔子问“伤人乎”是人道精神的体现。承认爱有差等,与人的心理及社会交往活动的实际相符合。墨子“兼相爱”的不别亲疏,不讲差等,在当时社会很难实行,也不合实际。
仁作为圣人的全德,“仁常在我”,“仁者本心之固有”,不是外铄的。“仁非自外至也,自然固有之良知也。未有用力而不足者也,由用力自可以进于好仁恶不仁之事。”仁是生而具有的固有良知,它具有先验性和内在性。与仁相关的是义,仁义对称,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关怀和最高道德原则及人格理想。仁内义外,仁由主体自我心性而外推,由己及人及物;义便是由外在客体需求而内化端正自我心性,要求主体自我道德、人格、情操的修养。仁义相须,便进天地气象境界。
范氏在诠释“放于利而行,多怨”⑦ 时说,效法于利而行动,这是违反义的自私的行为,就会招致很多的怨恨,所以要重义而戒利。又在诠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⑧ 时讲:“然以义制命,以人成天,又在乎自修而已矣。盖不安于天命,而为无益之忧固不可,委之天命,而忽自修之实亦非宜。”人生百岁亦要死,天既生人,人要在有限生命大限内自修,而实现人生价值。人通过自修而提升道德水准和能量,以人的道德人格力量,达到制约命与成天,弥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无中介环节的缺陷,提出“以义制命,以人成天”的思想,凸显人的道德理性的能动力量,批评了不安于天命的无益之忧和委于天命而忽自修等两种弊病,突出了人的自修的重要性,这样命为义命,天为人天,义与命、人与天互动相资,圆融不二,这便是圣之为圣之所在。
二 为圣是人的人格理想,实现理想需要学,学可从格物致知始,即穷至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以至所知无不尽,然后诚意正心,然后自天子以至于百姓,皆以修身为本。范阮攸认为,为仕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所以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孝悌为仁之本,所以修身不可以不事亲,力行孝悌,见贤思齐,成己成物,明德新民。交际能敬,责善辅仁,友以义合。“无非心得躬行之教,由希贤而希圣,自成己而成人,儒者之学,无余蕴矣。”
学是为圣的修养工夫,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的修养工夫犹道之须臾不可离,学与仕相依不二,仕是学的实践工夫,学持以助仕之善。范阮攸说:“‘仕’字从士从人,盖非士非人,诚不足以言仕也。”作为一定社会中追求人生价值的士人,首要是“君臣大义,原诸天地,本诸人心,士之未仕则学事君之道,既仕则行所学以事君,有志于上,犹得其中,苟志于中,不免于下,又况所志既下,其何以行臣义合人道,俯仰于天地间哉”!仕分上仕、中仕、下仕。人要立志于上,即立志要高,才能得中,立志于中,不免得下,若立志于下,就很难行事君之道之事。圣人的职责是为斯世斯民,在春秋礼崩乐坏之时,圣人心存斯世斯民。“圣人固欲行道以救世,而终不枉道以从人。”这是从上仕而言。
就中仕来说,范阮攸在诠释“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⑨ 说:“君子之道,莫大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能以恭敬惠义为主,虽其人未必纯乎道,其事则合乎道矣,学者勉焉。”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这是君子之道。公叔文子推荐他的家臣馔,他们同时做了国家的大臣。范氏说:“忘分荐贤,顺乎理也。顺理则气象光明,不亦文乎!在上位当存文子之心,而后无遗贤。”忘掉名分的分别而荐贤才,这是顺理,顺理就气象光明正大。在上位的人,应存文子的心,所以孔子认为,可以谥文子为“文”了。
下仕是孔子所批评的对象。“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何如其知也。”⑩ 范氏诠释说:“《易》所以微显阐幽,推往知来,惟能穷《易》之理以致用,然后可求《易》之神以稽疑。文仲僭礼则悖理矣,悖理何足以用《易》而专务谄龟,岂不惑哉!”既僭越礼,又悖《易》理,专谄于龟,而迷惑不智。他又诠释“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11) 说:“文仲罪在知字上,盖天位非己所可私,既知有贤而不与之共,则此位私矣。虽居与盗何异,然举而上不用则奈何,曰要在诚心,不为塞责,诚未有不动。”知柳下惠是贤人,就应诚心推荐他,给他适当的官位,不给其位置,便是以位为私。孔子曾要弟子对冉求“鸣鼓而攻之”(12)。因为当时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替他搜刮财富,范氏按曰:“圣人深责冉求,所以为万世聚敛之臣戒也。夫挟才而不穷理,徒以聚敛而导其君,本借谋国以谋其身,不过适以误国而误身……圣人之道,反而求之心身,则岂至急于求仕而甘为不义之行哉!”历代不仅有聚敛之臣,亦有聚敛之君,其结果导致国败人亡,是为君臣戒。
仕之上、中、下,开出仕之不同范例标准。由《学篇》学为圣的修养工夫,到《仕篇》的为仕实践工夫,为《政篇》如何为政积累了扎实的思想、修养、知识、素质、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为政者从事政治管理,首要的是正己。范氏在诠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 时说:“为政者当著力在‘帅以正’三字,正之外别无所谓政也。帅者其机在我,而不在人也。知所以帅,则先务正己而人自正,不知所以帅,则专欲正人而人亦不可正。公私分于一念之微,而感应之理间不容发。苟有志于政,其无以圣言为可忽哉。”政者正,关键在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不正己而正人,人也不得其正。这里的重点是要辨君子与小人。范氏说:“才德兼备,所以为大人;苟无其德,而但有其才,则小人而已。故学者必当以理御气,使理胜而气平,则骄吝不生,而所谓才者浑然于德中,有德之实而无才之名矣。”君子德才兼备,小人无德有才,两者用心相反,善恶有别。“君子之心都是仁,苟有一息之间断,则不免于不仁;小人之心都是不仁,虽有一隙之暂明,亦不得为仁。”由君子小人仁不仁之异,而有义利、公私、善恶、和同、周比之别。通过观人而辨识人才,以便尚贤使能。
在《政篇·观人类》中,范氏对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14),作了独到的诠释:“幽阴之气,不可无于天地间,女子小人之类亦不可无于人间。天地不能不养阴,人亦不能不养女子与小人也。惟知其为难,于不近不远求其中,使不孙与怨无由而生,夫然则善养,不见其难。”天地既有阳刚之气,亦有幽阴之气,不仅有其必要性,亦有其合理性,无阴便无阳,阴阳互补互济、互渗互存,所以天地不能不养阴,人间亦不能无女子小人,也不能不养女子小人,女子与小人不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有其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有男无女,人类就不能延续下去,天地男女的絪緼构精的融合,才能化生万物,否则天地人类就会消亡。人们唯知其难,只要在不近、不远求其中,那么亲近的无礼和疏远的怨恨,便无由而生,这样就可变“难养”为“善养”,就无所谓“难”了。从形而上天地幽阴之气存在的合理性,到形而下人间女子小人存在的合理性,其论证有据有力。
礼乐是古代社会的根本大法,是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有力方法。孔子对于当时诸侯、大夫破坏、僭越礼乐的行为,予以激烈严正的抨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5) 以仁为指导的礼乐,才合乎人道。范氏在诠释“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6)说:“一念之敬,敬必无不极其至;一念之僭,僭亦无不极之至。呜呼!圣人制礼作乐,本以维持防范,使上下之分截然,而后世权臣反僭其防范维持之具,为僭逾陵偪之资,为政者尚无使至此哉。”对礼的敬畏与僭越只在一念之间,礼乐本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防范社会失序、道德失落的功能,但后世权臣借礼乐制度作为其僭逾陵偪的资源。“礼始乎夫妇,而莫于君臣,一有所失,则名分紊,纲常乱矣。”纲常名分是防范违礼的道德力量。
范阮攸在诠释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17) 时按:“人皆知礼之严,有子独知礼之和,严其体,和其用也。”礼为严体和用。他用《周易·履》的卦象兑下乾上及其《象传》:“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来释“等级截然”的严体,犹乾的刚健。“《兑·彖传》:“兑,说也”,说与悦通,“说而应乎乾”。此兑为乾之应和为用,所以范氏释曰:“一阴行乎五阳之中,兑说附于乾健之体,此章大意似之。”
孔子不仅爱好音乐,而且谱乐曲。《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当他听到《韶》的乐曲时,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进入审美情感的艺术心境。范氏说:“舜之道发于〈韶〉而传于夫子,平日默契之于心,忽然触之于耳,徘徊想象,宛然蒲阪泰和堂上精神,此时之乐,亦与斯世同之也欤。”乐教陶冶性情,提升德操,所以乐是德之形,即其表现形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己、观人、礼乐最终是为了处理好与民的关系。如何临民?一是为政以德。“为政者以德为本领,本领既立,凡事顺理去做……去不正而归于正,禁令刑罚,虚设而不用。”德政的核心是“范其心”,使其“有耻且格”。“治民当范其心,不当束其身。政刑束其身也,德礼范其心也。束其身者但能使民之惧而不敢犯,范其心者乃能使民之耻于不善,而化于善。”这便是王道与霸道的分野。二是王者以理使民。“王者以理使民,故可使民之由其理,而不使民之知其理。伯者以术使民,故不必使民以晓其术,而但务使民之愚其术,然则使由不使知,其圣人不得已之心耶。夫礼乐刑政,皆使由之具,而性命精微,岂凡民之所能知哉!”王霸之别就在于以理或以术使民,礼乐刑政都是使由之的工具,尽管圣人不得已如此,但以理使民是符合仁政和仁爱之心的。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仁者之心也。然必欲无一物之不被,无一处之不彻,虽仁至者,势亦有所不能。古之圣人知此,故皇皇汲汲不自满足,尧舜不自知其为治,夫子不自知其为圣,皆犹病诸之心所推也。”仁者之心以天地万物皆吾一体,所以能博施于民。但尧、舜和孔子都以难能做到的“其犹病诸”的心境,不断追求而不自满足。四是恭敬事业。“恭即所谓钦,所谓敬也。是故兢兢业业,无怠无荒,皆钦敬之存,典孰礼庸,服章刑用,皆钦敬之推,一由于天理之当然。”怠政、荒政是对民不负责,终日乾乾、恭敬兢业,是为政者之职守。五是节用富民。“为政不知节用,则取民尽锱铢亦不足矣。故王者务富民,不务富国;务生财,不务理财。后世惟汉文帝知此义。嗟乎!聚敛之臣,相望于世,亦有若之罪人欤。”民富才能国富,国富才能国强,聚敛之臣,竭泽而渔,民贫国弱,亡国之象。所以,范阮攸在《论语愚按·政篇总说》中云:为政“其本在乎正己,是以古先圣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皆是正己底道理。事业著于一辰法式,垂于万世,宇宙赖以主宰扶持,以不入于禽兽”。以正己推之于日用之间,则可以知古代及后世盛衰洽乱的现象,都不出帝王的正与不正。故为政者当以此为鉴。
注释: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雍也》。
③ 《论语·为政》。
④ 朱熹:《中庸集注》,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⑤ 《论语·子路》。
⑥ 《论语·乡党》。
⑦ 《论语·里仁》。
⑧ 《论语·颜渊》。
⑨ 《论语·公冶长》。
⑩ 《论语·公冶长》。
⑾ 《论语·卫灵公》。
⑿ 《论语·先进》。
⒀ 《论语·颜渊》。
⒁ 《论语·阳货》。
⒂⒃ 《论语·八佾》。
⒄ 《论语·学而》。
易理的承接与创新:黎敔理学易学的角色与论域
向世陵
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哲学院,北京 100872
向世陵,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学曾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维形态,但进入清代中期,已逐步走向衰微。到19世纪中叶以后,本已边缘化的理学更是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学”的对立物而遭到多方面的批判。然而,在中国的近邻越南,却有黎敔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仍然以理学为学术真谛,并以弘扬理学去对抗西方的船坚炮利。不过,黎敔所说的理学实质上是易学:“理学者,易学也。是以义理明而文明始进;文明愈进而易学愈明。”② 的确,按照《周易·系辞传下》的说法,文明是由伏羲仰观俯察而画八卦开始的,并经神农、黄帝和尧、舜等人进一步发扬推进。所以,文明与易学之间就是一体而互发的关系。
一 理学在中国的出现有一个显著的标志,这就是理学道统论的成立。理学家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禹往后圣圣相传,其依据即在《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而重点就是其中所说的道心人心。与此不同,黎敔的易学虽以理学为指导,但与中国理学家所论传道传心的重心有异,“时中”成为他最重要的理学易学原则。因而,黎敔根本不提在“允执厥中”之外的其他十二字,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易道”的“时中”上。所谓:“圣虽继圣,心犹传心,至尧舜禹三圣授受,始曰‘允执厥中’。然则中之为道,实自尧舜发之;惟中之本于易道之时中,又未见尧舜明之。”③
黎敔将易学的远取近求之方与理学的分殊以求理一之方相协调,认为所求取的结果正是易道的“时中”。尧舜禹固然发明了“中”之为道,但由于未能明确此“中”本于易道之“时中”,所以不应列入易学的道统序列。易道的真正传承者,是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四圣。但是,黎敔的解说与宋明理学家论《周易》作者的“人更四圣”说并不完全一致。在他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象辞(大象)》和爻辞,而孔子则作《彖辞》、《象辞(小象)》和《文言》④。就是说,他并不同意朱熹肯定孔子作《易传》十篇的观点,认为孔子只是作了“释演”文王卦德的《彖》文和周公爻辞的“小象”,以及从爻象中“揭出”的《文言》⑤,而并未作《系辞》、《说卦》、《序卦》。至于《杂卦》,他则根本没有提及。当然,《系辞》以下各篇,虽然是后人“亦欲假借圣人以明作《易》之由”而成,但有它们自身的价值,不必废弃。“择善而从,学者亦节取焉可也。”⑥。黎敔对《易传》各篇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力求发明前圣后圣传承的联系和区别。他虽然肯定程朱的义理易学,但在不少方面与程朱存在着差异。
在黎敔看来,孔子因时制宜、随时取中而“删书”、“赞易”,后之学者才得以知道自伏羲而下历代圣人的心传。在文本上,“(孔子)辞虽繁简不一,而一以明易道之时中,此所以继羲、文、周三圣而为四,而今之学者亦可以知尧舜禹三圣心传之一中,盖本于易道之时中者也。”⑦ 孔子最恰当地将上古圣人传承而下的基本精神予以了集中的揭示,传心就是传中,而此中就是易道之时中,是孔子随时取中“赞易”的结果。孔子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贡献而能与其他三圣相并列。
至于孔子文辞的“繁简不一”问题,黎敔以为,其实在文王和周公那里也是存在的。文王的卦辞和周公的象、爻辞作为儒者心身性命不可或缺的卦德,是“随时之学”的核心。而“随时”者,“随时以取中”也。为了“取中”,繁还是简就不能执著。比如,文王卦辞的目的在于发明该卦的义理,所以较之伏羲所定卦名只有一两字来说,当然就是“辞繁”;周公爻辞的目的在随机应事,自然需要讲清楚,然简约又能揭示爻辞之意是为最佳,故孔子象辞(小象)相对于爻辞又显得简约。
黎敔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在这里举了一例,即坎卦上六爻:
兹姑以坎一爻言之:“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玩其意,则坎至上出险无援,虽交离有系用徽纆之象,惟非可走之丛棘而亦走之,夫亦何往而非凶?故以失道象之。而必并以上六存之,盖无上字,不见出险水溢之意。其辞约意该如此。而人之出险自负,肆意妄行,亦已足为鉴戒,何必多言?倘就文辞上论,则坎无丛棘之象,纵然援引成章,想亦文章无用,学者玩而味之,勿谓周非孔思,孔异周情,方为会读。⑧
^^坎卦上六爻辞之意,结合象辞的论断,是坎卦发展到上爻,身临险境且无人援助,处于一种向离卦转化但又“系用徽纆”的被绳索捆绑的困境中。(到此还不知谨慎)非要从无路可走的荆棘丛穿行,这样做怎么不会是凶的结果呢!所以其象征是“失道”。孔子作象辞,所以要加入“上六”二字,是因为如果没有“上”字,临险水溢的凶意就显现不出来。可见孔子决不多用一字,言简意赅已趋完善。至于人涉险又自负自傲,恣意妄行,本身就成为后人的鉴戒,又何必多言呢?
就象辞文字而论,孔子于坎卦未提丛棘之象,其原因,想来是即便援引爻辞而论及丛棘,于文章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所以未及。学者于此要细加领会,而不能得出孔子象辞与周公爻辞冲突不和的结论:“周、孔二圣爻象,皆先意会然后言传,惟周以意形言,孔又以言会意,辞虽繁简不同,而悔吝吉凶无不若合符契。”⑨ 周公观爻意而有辞,孔子则以象言发周公之意,二圣各自侧重和言辞繁简有不同,但指向和归结处却若合符契。
当然,孔子“辞约而意赅”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再完善。事实上,辞约也有辞约的问题,所以后来会有程颐《易传》和朱熹《本义》的阐释和发展。然而,朱熹对不同圣人共同完成的《周易》所作的绝对性评价——“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等⑩,却是黎敔所绝不同意的。黎敔说:“惟谓孔子之《易》非周文之《易》,而‘周易’亦非伏羲之《易》,而别释之,是又最为杜撰之处。”(11) 在黎敔看来,四圣之间尽管有若干的差别,但前后相承,义明理合,在共尊易道之“时中”的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后圣对于前圣,其学说往往是一种扩充推进的关系。例如:“一彖文乃卦德也。圣人原体天时而推出人事以名状之,故凡一句一字,无非至理之所存。惟孔圣彖文,又因文圣彖文,而包括人情物理以扩充之,初非可以异同言也。”(12) 不论是文王卦辞还是孔子彖辞,体现的都是卦之精蕴,都是圣人以人事昭示天时的作品。按理学“理一分殊”的构架,字字句句可以说都是天理之所在,所以需要认真领会。两者间的关系,孔子的“彖文”是以文王的“彖文”为基础,再通过对人情物理的概括予以扩充阐发。所以,黎敔作《周易究原》,其中仅有的包括卦辞和彖辞在内的乾坤两卦,都是彖辞紧接卦辞,注解统一放在彖辞之后,将卦辞与彖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释。那么,“孔彖”对“文彖”就是丰富和推进的关系,而绝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异同对比上。
二 由于前圣后圣文辞繁简的不同,后人的注解能否准确理解和阐扬圣人卦爻辞的辞义,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黎敔以为,后人在“体格”上可以仿效《文言》的方式去做,并且,在借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附上自己的见解。他说:“后人如欲明晰字义,令人一览便知,则其体格亦从乾坤二卦《文言》,而以《程传》厘正之。束结要明,系于爻辞之下,而约之曰:故象曰云云。如此,则爻象辞意自然见得分明。”(13) 黎敔的《周易》研究注重创新,并不遵循固有的经传疏解体例。在他那里,一方面,体例格式按照《文言》,《文言》不但是孔子对乾坤二卦卦爻辞辞义的引申阐释,而且还采用问答体和其他说明句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发明,使人容易明白:另一方面,辞意概括须以程颐《易传》去“厘正”。这说明仅仅明白字义即止步于训诂的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讲明义理,这就应当自觉以作为理学经典的程颐《易传》为依归。在字义和义理都得以阐明的前提下,注释者应将自己的理解简洁归纳并系属于相应爻辞之后,再引象辞作为证明。由此,则《周易》爻辞、象辞的辞意也就都能明白了。
在这里,黎敔信守的实际上是两个原则,一是《程传》对《周易》辞意和思想阐释的经典指导;二是《象辞》(小象)乃是卦爻意旨的简约概括,因而可直接引用,不需要再解释。所谓“一爻辞中亦从《程传》厘正,而以‘小象’约之,无须复释象文”(14)。事实上,他自己著《周易究原》,就可以衡量的乾坤两卦注解来说,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实践的。
黎敔注解乾坤,将两卦的爻辞和象辞合为一组,统一进行阐释,这在体例上与《程传》、实际上也就是王弼《周易注》所创造的体例并不相同。后者是爻辞与象辞分别独立注解的。从各爻看,乾坤两卦从第二爻到第六爻(上爻),遵循的是严格的“以‘小象’约之,无须复释象文”的原则(15)。即在注解的最后,引证“象曰云云”作为全爻辞意阐释的归结。然而,在乾坤二卦之初爻,情况却有不同,即黎敔在“象曰云云”之后又作了解释。下面分别作一考察:
先看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黎敔解释说:“乾,阳道君道也。初阳犹微,体乾者凡事坚忍不敢轻动,如阳气之待时未进,以左右民,故象曰:‘阳在下也。’何则?君初即位,其阳之始生乎!”(16) 乾道作为阳道也就是君道。但君主权威的树立必然有一个过程。一阳初始,势力尚微小,能深谙乾道(君道)者就当坚忍沉着,不能轻举妄动。如同阳气未到时节还不能长进以助养民众。解释到此,辞意已经发明,在一般情况下,以《象辞》“阳在下也”一句归结潜龙(君主)的不动就可以了。但在这里,黎敔却认为还未完。“阳在下也”如果不加说明,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无可奈何的情势,所以还需要再加阐释,意味君主初即位的不宜动作不是消极的无奈,而是审时度势、自觉选择的结果,如同阳气始生而不可遏一样,韬晦是为待时而动。那么,象文如果不假“复释”,过分简约,就确有“形言未尽”而学者未易晓的缺陷。
然而,这是否遵循了以《程传》去“厘正”的原则呢?参考一下程颐的相应解释:“初九阳之微,龙德之潜隐,乃圣贤之在侧陋也。守其道,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时;自信自乐,见可而动,知难而避,其守坚不可夺,潜龙之德也。”(17) 可见,黎敔的注解与程颐之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再看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黎敔解释说:“坤,阴道臣道也。初阴尚微,体坤者凡事战兢不违礼度,如阴气之严寒必来,以慎辟难,故象曰:‘驯致道也。’何则?臣初试政,其阴之始凝乎!”(18) 坤道作为阴道也就是臣道,但臣道的确立(建功立业)必然受到限制。一阴初现,能深谙坤道(臣道)者必须谨微小心,严守礼法。如同阴气必然走向严寒,谨慎收敛才能避免灾难。解释到此,辞意已经发明,在一般情况下,以《象辞》“驯致道也”一句归结由初霜到坚冰的走向就可以了。不过,坤卦只训释到此,黎敔仍有意犹未尽之憾。因为“驯致道也”所说顺习严寒的必将到来,并不能直接揭示臣道的作为。所以,还必须再加发明,说明为臣者刚步入仕途承担朝政,就要像阴气始凝须注意预防寒冰一样,无时不提醒自己,万不可大意。这样的释义才更为完整。但由此一来,黎敔就不是简单衡之以《程传》,因为《程传》对坤卦初六的注解是以小人、小恶喻阴生,因而应当防微杜渐而戒于初。故他“从《程传》厘正”的原则又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黎敔在《周易究原·序》中曾说,程朱所作《易传》、《本义》对《周易》之“原”的探究“一切指为自然,而未尝推出其所以然”,“遂使传心之要典,几成口授之虚文,湮晦至今”。所以,他要“继往开来”,求理学家未尽之所以然。“凡先儒之未发者发之,已发而未明者明之,已明而未约者又约之”,使易道经由他之手而得以发扬光大。事实上,黎敔始终坚持的随时取中之方,是易学也是理学的基本精神。它本来就不认同僵化不变的原则,一切以义理的简洁明白为基准。
第三,《周易究原》是黎敔的主要易学著作。他曾说自己是因不满于当时“旧书过繁而新书过简”的《周易》研究现状而“重修《周易》”的。时势的需要成为他著述的重要考虑。当然,如从“学科”本来的要求说,注解《周易》应当是全书。但出于“非旦夕之可能完毕”和“恐学不及时”的担忧,加之理学的“义理渊微”一时也难以弘扬光大,所以他“去繁就简”而确定了自己十分特殊的撰著体例。
在《周易究原》中,黎敔对乾、坤二卦的注解相对完备,所解包括:卦名、卦辞(文王彖)、彖辞(孔子彖)、爻辞、大象(周公爻、象)、小象(孔子象)。《易传》余下部分,《系辞》以下各篇因被认为非圣人所作而排除在外;《文言》则系孔子从爻象中“揭出”而来,故也可以省略。在乾坤之后的其他六十二卦,黎敔则只阐释了卦名、文王彖文和周公大象三类;其余再省略的部分——周公爻辞、孔子彖辞和象辞,参照他上面所说,时间和精力不济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从积极的层面说,乾元坤元作为天地阴阳生成的基础,注解本来应当周到细密;而其他众卦,就可以遵循他一直倡导的简约的原则。
具体而论,黎敔所以略去周公爻辞、孔子彖辞和象辞这些部分,还有他自己特定的考虑。他在接下来论及文王、周公和孔子三者撰著的一致性时,曾解释说:“至如孔彖与周爻、孔象,皆临事随机之不可缺。但究之孔彖,乃合文王彖文,与周公六爻应援,而别设随时之义。如文言之教人,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道也,岂释文王之彖哉!宜乎孔易非文,前人有是论也。”(19) 黎敔首先提及的孔彖(彖辞)、周爻(爻辞)、孔象(小象),正好是他注解屯、蒙等其他六十二卦所省略者。这三者虽说都是“临事随机之不可缺”,但从其产生来说,都是在文王彖文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卦的卦辞事实上也可以被看作全卦辞意的基点。从此基点出发,“孔彖”既用于解释文王卦辞,与卦辞就是相合的关系;同时,“孔彖”也与“周爻”形成前后的接应援助关系。所以,三者构成的是一个统一整体。至于其他部分如《文言》,因系出于随时教人的需要而撰,其所关注的是从个人修身推广到天下国家的平治,并不直接是对卦爻辞本身的阐释。
其实,《文言》中并没有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大道”,将两者联系起来,只能是按理学的思辨予以引申发挥的结果。但在黎敔看来,却正是要认定这是孔子从时势需要出发,在《周易》之外“别设”的教人之义,它本来就无关乎卦辞。如果弄不清这一点,就很容易像前人如朱熹等一样,得出孔《易》非文王《易》之类的怪论了。
当然,黎敔在这里也有因不赞同郑玄、王弼以来的经传编排体例,而对《易传》篇目间的关系所作出的某种自觉的思考。事实上,朱熹的《周易本义》就已经是将经与传分开来编排。尽管黎敔对朱熹将前圣后圣之《易》分割开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对朱熹采用“古《易》”即将经与传分开编排的做法,黎敔却予以了继承。他曰:“(《文言》)仍拟亦从古《易》各自为卷,而分附于上下二经之后,以别于经。倘若又从王弼、郑玄旧套,而原增入乾坤,则爻象自爻象,而《文言》更自《文言》焉耳。谁则于众言殽乱之中,而唾骂成章,以破却孔易非周之妄议。至如爻象,则辞简易赅,亳发不爽,诚所谓前圣后圣一揆者也!”(20) 《文言》在王弼已增入乾坤二卦之中,排列于周爻、孔象之后。但在黎敔看来,这会导致“爻象自爻象,而《文言》更自《文言》”的问题,即不能明白《文言》本是孔子从爻象中“揭出”来的“一段天然文字”,《文言》与爻象之间,是“似同非同、而似异亦有非异”的关系。即在黎敔,《文言》的作用是启发后人认识爻象辞义的入门文字,所以不应与经文混淆。否则,便难以真正破除“孔”《易》非“周”《易》的“妄议”。至于周爻与孔象之间,辞简意赅,可以清楚看出前圣后圣之言如合符契的特性。
黎敔不认同王弼的附《文言》入乾坤,但对于王弼扫象数而开创的以义理解《易》的新风则又是完全赞同的。称赞说:“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此说最好!学者果能参考而沉思之,则三百八十四爻,无不迎刃而解。”(21) 从一般道理说,玄学是义理易学,理学也是义理易学,承接理学的黎敔肯定王弼之说,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或许正是从义理考虑,将《易传》各篇分拆而将《彖》、《象》、伎言》“增入”六十四卦之中,就既会影响到人们对上下二经文本自身的理解,也不易看清羲、文、周、孔尤其是文、周、孔前圣后圣相传的思想脉络,所以他要尽力纠偏,以澄清和发掘圣人之学的真实蕴奥。
黎敔的纠偏在他的时代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在西学借船坚炮利进入东方之后,东方的传统学术已被排挤到边缘:“继以泰西航海东来,而奇技淫巧日新月盛,人皆眼花而心醉,群而趋之于名利之场,流弊至今,而《易经》视为废纸。”所以他要潜心研究《周易》,“以为性命心身之龟鉴,无如命途舛籍,瓢巷空颜,永言道统之传”(22)。黎敔所论,虽已有百年之远,但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弘扬光大东方文化的“性命心身”之学,仍是今日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注释:
① 黎敔(1859—?),字应和,越南南定省长天府万禄社人,自称为“越南国春长府万禄社狂士”,系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越南知名学者。据何成轩考证,黎敔著作主要有:《周易究原》(1916年)、《礼经》(1928年)、《大学晰义》(1927年)、《中庸说约》(约1927年)、《论语节要》(1927年)、《附槎小说》(1900年)等。
② 黎敔:《存疑并序》,见《周易究原》,上册,页四十一右。
③④⑦ 黎敔:《易道合论》,见《周易究原》,上册,页十四左至十五右。
⑤⑧ 黎敔:《存疑并序》,见《周易究原》,上册,页四十右、三十六左至三十七右。
⑥ 黎敔:《解疑略论》,见《周易究原》,上册。页四十一左、四十二右。
⑨⑿⒀⒁黎敔:《存疑并序》,见《周易究原》,上册,页三十七右、三十七右至左、四十右、三十七左、三十七左。
⑩ 朱熹:《易三·纲领下·三圣易》,见《朱子语类》,第1645、1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⒂ 其实,黎敔这一原则并不限于爻辞和“小象”,他对卦辞和“大象”的注解同样也是如此。参见本节稍后部分相关论述。
⒃ 黎敔:《上经·乾》,见,《周易究原》,上册,页五十六右。
⒄ 程颐:《周易程氏传·乾》,见《二程集》,第7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⒅ 黎敔;《上经·坤》,见《周易究原》,上册,页五十九右至左。
⒆ 黎敔:《附录·续释文王彖文序》,见《周易究原》,上册,页五十三左至五十四右。
⒇(21)(22) 黎敔:《存疑并序》,见《周易究原》,上册,页四十左、三十九左至四十右、三十五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