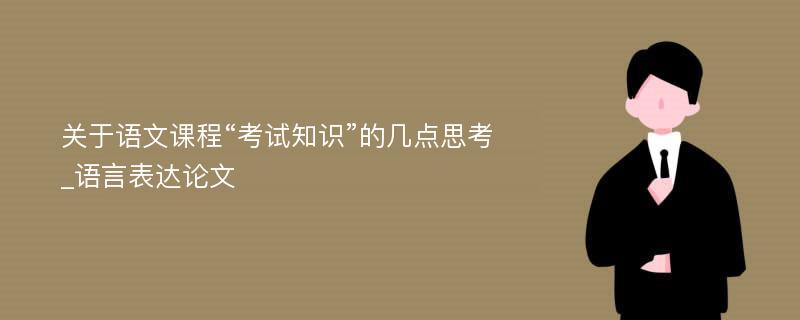
对语文课“考知识”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课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权威的考试机构出的两道考查语文基础知识的试题。
例1:
(1)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
A.这个经济协作区,具有大量的科技信息,较强的工业基础,巨大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较丰富的动植物、矿产、海洋、旅游等资源。
B.当太阳完全被月亮的身影遮住时,与神女般若隐若现的“海尔—波普”彗星相比,清晰的水星亮晶晶地伴在被遮的太阳旁,金星、木星也同时出现在天宇。
C.出版社在1997年第一季度社科新书征订单上提醒邮购者:务必在汇款单上写清姓名及详细地址(汇款单内注明所购的书名、册数)。
D.今年春季,这个省的沿海地区要完成3700万立方的河堤加高和河口截流改道工程,任务重、工程难、规模大。
(2)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今年春节期间,这个市的 210辆消防车、3000多名消防官兵,放弃休假,始终坚守在各自执勤的岗位上。
B.(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深受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C.她把积攒起来的400元零花钱,资助给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赵长波,确保他能够支付读完小学的费用。
D.3月17日,6名委员因受贿丑闻被驱逐出国际奥委会。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关于这起震惊国际体坛的事件都作了详细报道。
(1)题的C项,“‘海尔—波普’彗星”这一类名称能不能用引号,能用,又怎样用,《标点符号用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使用中,有加引号的,如“1947年,‘西可特—阿林大陨石’降落在苏联西伯利亚”;也有不加的。这种地方加不加引号,不会产生意思的出入,只是各人的习惯不同,用例的多少而已,很难说是原则问题。两种用法都有,没有明确的规范,凭什么断定其中的是非呢?(2)题ABD三项的语病是明显的,标准答案是C项。但是C项也不干净。从和上文“把”的对应看,“给”是需要的。但是,“给”放在“资助”之后,却又不妥。“给”和双音节动词的组合有其习惯。凡双音节动词可带对象宾语的,一般不再用“给”,不能带对象宾语的,就得用“给”;我们会说“把 (拿)……赠送给……”,却不说“把 (拿)……援助给……”。“资助”的用法和“援助”一样,后面不带“给”。语感稍强的人会感到这种说法别扭。这种别扭绝不亚于B项的“深受……所欢迎”。
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若是碰到这种题,大概都会发愣,就是写下答案,恐怕也说不出多少理由,瞎碰而已。跟这种试题交道打多了,便会发现做这种题简直就是在赌博,是输是赢就靠运气。
这种情况,即便不是标准化试题——即便不是考试,也在语文知识教学中普遍存在。试看下面的例子。
例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郁达夫《故都的秋》)
思考题:这段文字的内容是用什么手法表现出来的?
答案:比较,排比。
这节文字表达的是作者对故都北平秋天的情愫。固然,说比较和排比是作者表达这种情感的手法,没有错。但是,表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是哪种表现方法或辞格所能囊括的。譬如,排比在这里之所以能传达作者的深情,还有待几个“来得”构成反复的辅助;全段“秋天”、“秋”的多次反复,形成了浓厚的抒情氛围。又如,整段两个句子,各句中的分句长短相间,整散错落,是带来深长情味的重要因素,也属于语言形式上的表现手法,等等。总之,正是这些已经有名目的和还没有名目的各种手法的综合作用,才汇成这段文字悠长的韵味。现在,你答“比较,排比”就对,你说“反复,错落”就错;不能凭自己对这段文字的体会去寻找作者将感情传达出来的方法,而必须牢记别人给定的说法,别的都不行。这到底是浅陋还是专制主义,抑或是浅陋的专制主义?
语文(尤其是中文)和数理化不同,许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是”或“非”所能解决的。且不说对读物内容的理解的见仁见智难以划一,就是对语文基础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对同一对象也会有不同的认识,都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就是看起来涉及“通”或“不通”的语言规范问题,其间也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不是“是”或“非”所能解决的。至于和理解角度相关的一些所谓语文基础知识现象,很多时候,其实涉及的并非“是”或“非”,而是“哪一个更好”的问题。在教学或测试时,我们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却不一定都能设定一种或多种理解的角度。对一个具有开放性的词语、句子乃至语段,若不设定理解角度,就很难判断哪一种理解更合理,如此,又怎能用一个标准答案去评判各种不同的理解呢?面对着就一个具体的语文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往往会感到无从说起。使他们感到困惑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对知识的无知,也不是对文章内容的不理解,而是题目的表达和问题的提法,不知道提问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答案。有时候,就是知道提问的意思,但由于问题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只好瞎碰。像上述的例1的 (1)、(2)两题,考生只能像赌徒押宝似的选择答案。对多数考生来说,最可怕的不是题难,而是问题本身没有清楚的是非界限,用一种其实是钻牛角尖的理解做标准答案,对其他具有合理性的理解宣判死刑。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现象:语文水平越高,认识个性就越强,面对着一个语文现象时所想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多,但由于缺少背景条件,答题时抉择也就越困难,和既定答案不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于是失分的概率也就越高;与此相反,只记住教学中的说法,想法越单一,理解的个性成分越少,表述越公式化,碰钉子的机会也就越少,考试成绩也就越高。这就像面对着“1加上1等于几”这样的问题,小学生的回答会比数学家更干脆利索一样。
将这种现象和语文教育的实际效果联系起来考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僵硬的语文知识,这样死板的教学法,这样说一不二的测试方式,所形成的,不会是学生的语文能力,更不会是语文素质,而只会是教学的应试功能;并不只是教师们为了升学率而围着试题转,还因为整个教学机制只能适应实际上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语文水平的考试。
考试本身并不坏,各行各业都有考试,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车床操作会导致工人不去练真功夫,也从没有听说过实弹射击考不出射手的水平。考的就是所用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一遛就清楚了。问题在于考什么,怎么考。语文具有直接的实践性,生活中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运用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试,按照实际运用的方式来考,就能测出一个人真实的语文水平。如果我们抱着这种观念去看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就会发现,语文教育各种问题的最终根源并不在指导思想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上,而在我们对语文水平的认识就定位在语文知识的掌握上,而现行教学系统中的这套知识系统和语文实践没有直接的联系,除了应付考试,难得有别的用处;我们的语文教师,除了教材中的这些知识,无论是读是写还是别的语文实践,其实并不比一般人懂得多。我们甚至会发现,由于语文教师长期同这种僵化的知识打交道,他们对鲜活的语言的感受往往更为迟钝,他们在阅读理解上往往更容易钻牛角尖而忘记了常情。如果不信,我们不妨随便拿一种语文教材,看看它对课文内容的表述,看看它所出的习题,看看那些教学参考书对这些习题的回答,便能发现反映在其中的是什么样的语文观念和知识结构。我们可以设想,当这些东西成为考试的命题背景时,会有什么样的试卷,这种考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在涉及语言的规范性 (如字音,字形,词法,句法等)时,搞个标准答案也无妨(只是这个答案应当真的“标准”)。但是,在言语活动中,更多的是非规范性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对或错,而是优和劣。优劣和对错,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评价系统,并且有着不同的教育意义。“优”的并非尽善尽美,“劣”的也不是一无是处。拿汉语的标点符号来说,尽管国家对各种标点的一般用法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使用时,汉语中标点符号用法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只要不涉及语意上原则的出入,用逗点还是用句号,用冒号还是用破折号,句中间停不停顿,很多时候是两可甚至是多可的,也就是说,几种用法都是允许的,不能说哪一种对哪一种错。但是,若认真加以推敲,这些不同的用法有时可能在语意或表达效果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其中一种用法可能更贴近作者的本意些,或者意思更显豁些,读者理解起来更容易些。这当中既有个人的习惯问题,也有表达效果的优劣问题。懂得区别这些不同,学会精益求精,远比懂得对错重要。
哪怕是在规范性的问题上,若只知道对错,不仅会造成认识的僵化,还会严重阻碍语文能力的发展。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只去注意规范的问题,尽力避免错误,而不大会去注意语言的质量,而造成优劣感的迟钝。这一点,在语文教师和作家们所写的文字上有明显的反映。大凡语文教师所写的文字,往往在语言上很注意句子成分的齐全,前后词语的关联,而不大注意灵动的表达,所以,他们所写的文章往往语言拖沓,语言在形式上连贯而思维不流畅,缺少生气。而作家则不同,他们的文章似乎更注重思维的活跃,更注重内容的内在联系和表达个性的张扬,较之语言的规范,他们更在乎表达风格的独特和语言的风致,很多时候,他们似乎有意在语言规范性上走钢丝,甚至故意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但最终却为读者所认同,赢得喝彩。比较这两种文字的差异,探究其表达的心理背景,关注点的不同恐怕是重要原因。由于职业习惯,语文教师重视表达的规范,也就是对错,而作家则重视表达的质量,即优劣。规范是优劣判断的底线,底线以上的就不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更好的问题,这两者不能混淆。将优劣问题当作是非问题来处理,用两分的方法代替多等级的水平认定,必将造成认识的简单化,不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我认为,语文知识教学,应该区分以下几个问题:
一、复杂的和简单的
看起来是简单的往往实际上是复杂的,看起来是复杂的往往实际上又可能是简单的,而这简单和复杂往往又是可以转化的。譬如文言语气助词,每一个词都表达一定的语气,但又存在着交错的情况,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语气,要结合语境来分析。可能教材的编者认为这样辨认起来太麻烦,于是就来个干脆的:陈述句后边的就是传达陈述语气的,判断句后边的就是传达判断语气的,祈使句后边的就是传达祈使语气的,疑问句后边的就是传达疑问语气的——在鸡身上的就是鸡毛,在鸭身上的就是鸭毛!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呢?《阿房宫赋》里“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中的两个“也”若换成两个“矣”,也通,但话语的味道很不一样。作者用“也”不是简单地追求句式整齐一律。甚至可以这样说,此二句中的微言大义,就是靠这两个“也”传递出来的。这个句子中的“也”难道仅仅是陈述或判断语气所能说清的吗?在这里,对和错的判断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文言知识中,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其他语文知识中,说简单又不简单、说复杂又不复杂的情形也很普遍。在这种问题上搞一刀切,其对和错就没有多少意义。
二、深刻的和肤浅的
复杂的东西往往也是深刻的。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只看表面,实际上也就是把深刻的东西肤浅化了。而有些时候,作者的话其实没有很深的背景,但因为各种原因,读者却肆意穿凿,导致歪曲原文。这些,在语文教学中都是常见的。譬如分析作品的“炼字”,教师们总是说哪个句子的哪个词用得如何如何好,它有什么什么的含义,要求学生体会后说出好处,以致教师的板书总是将那些所谓用得好的词语摘出来,特别加以强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词语无所谓好赖;只要用得恰当,就都是好的。写作时词语的斟酌,从根本上说不是用词的问题,而是“炼意”的问题,只有锤炼思想,使之更为深刻明晰,深化意境,使之更为丰厚精致,然后寻找恰当的言辞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这才有了精彩的表达。就拿“推敲”来说,“推”和“敲”这两个动词各有各的意义,没法分出优劣;对贾岛的诗句,人们“推敲”了一千多年,各种说法依旧难分轩轾,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意境,谁也说服不了谁。将境界的问题归结到用词的问题,甚至归结到用那一类词的词性问题,只是在表面上滑来滑去,这就将深刻的东西肤浅化了。相反,有些东西原本是作者信手拈来随便说说的,本无深意,一拿到语文课堂上,就变得艰深起来了,深奥得叫人难以理解。譬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中说到有人“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文中,“捧”也好,“一路挂过去”也好,无非是随手讥讽一下“送去主义”的可怜相。可是,因为是鲁迅的文字,于是一味深挖,崇洋媚外呀,卖国主义呀,这一串帽子全都“挂”上去了。文章原本说的是文学艺术的问题,你却一味往政治上挂靠,还用这种理解来做“标准答案”,衡量别人理解的对错,这叫什么呢?
三、多样的和单一的
词语的选择,标点的运用,修辞的分析,文体的辨别,这等等知识的运用,都存在着限制性和选择性的统一问题;运用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又并不是非此即彼,而存在着弹性。在这些问题上,涉及的是优劣,而不是是非,有些恐怕连优劣也谈不上,只是习惯不同而已。把这一类有弹性的问题当作是非问题来对待,就会带来许多麻烦。我们常常见到一些练习或试题截取课文中的一段文字,并从中抽掉一些词语或标点让学生填空,不和原文一样的就算错;列出几个句子让学生指出修辞方法或分析复句层次,和标准答案不一样的就算错;列出一些文言词语或句子要求学生解释或指出句式,只允许有一种答案。更有甚者,是规定一首古诗的理解必须有哪些字眼,一篇作品的艺术特色只能有哪几个方面,一个作文题必须涉及哪个或哪几个话题。
在这里,我们不想一一分析这些问题的弹性。这种弹性,凡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都清楚。我们只想指出,这类东西原就无法划一,就是相同的意思也可以有几种表述,何况有些问题本来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的呢。这么一对一,就把人的思想给统死了,把教学方式也给统死了。
四、随机的和模式化的
文章的生成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随机性,因此,读和写都有其规律,却没有什么模式。比如,文章的思路,是作者按表达目的把自己认为必须讲的内容按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话题序列。这种序列,既有大致的计划,又有随机的生发。大致的计划,使得基本内容有合乎逻辑的轨迹可寻,而随机的生发,往往又和总的计划没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有些段落,其内部层次是由意识的流动产生的,和我们的段落结构模式根本不相干;规律当然是有的,但不是我们所拟的那一套逻辑模式所能包容的。当然,按照那套模式来讲课是方便的,组织统一测试,并用以此得来的成绩来评定教和学也是容易的,阅卷的误差小,也容易操作(甚至无须人操作)。但是,搞语文教学原就不是为了图省事和方便;有时,从改卷看来是很统一和很公平的操作,从反映考生的实际水平看却很不统一很不公平。道理很简单:模式无法反映和评价随机的东西。
五、相对的和绝对的
一个段落,一个句子,乃至一个词语,它的具体意义是在互相联系中显示出来的,是联系赋予其具体意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是,在阅读教学中,段旨的归纳从来都是按照所谓段内结构的模式就段论段,而很少从全文的思路去认识;文言释词,从来都是按字(词)典的义项去对号入座。所谓语境意义,就是根据具体的句子确定对应哪个义项,却很少想到字(词)典的义项只是划出大致的几类用法,而无法说明语境中的具体词义,按义项的说明去翻译,多数时候很别扭;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文章体裁,作者在构思时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记叙、议论、说明、抒情等表达方式也只是在这种大致倾向和作者的写作意图的联系中才能得到说明,而不能仅从文面的某些体征断定是什么表达方式或什么体裁,更不能认为一种文体就有一种内容结构格局,得用这种格局去一一照套具体的文章。但是在语文教学中,一旦给一篇课文作了文体定性,就用这种文体的套路去肢解文章。这真正是削足适履。文体的分类,原本是出于特定的认识目的和研究需要,按照某一标准进行逻辑划分的结果,离开了具体的需要,分类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容易把多个分类系统混淆起来,造成混乱。但在读写教学中,从小学到大学语文,记叙、议论、说明三种文体一以贯之,既看不到分类的需要,也看不到分类的标准,文体分类的意义从来都是莫名其妙的,似乎根本无须搞清。而这些搞不清的东西偏又生出许多僵硬的“知识”,于是,圈内圈外的人就大碰其钉子。
看起来,将优劣问题用是非的判断来处理是应试的产物,甚至只是标准化试题的产物。其实不然。人们为什么不用标准化题型去测试写作能力呢?那是因为大家知道作文无法用这种方法测试。显然,用标准化试题去测试语文知识的运用和阅读理解,是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标准化——是非化,根子还是在对语文活动本身的认识不深刻。事实上,就是在标准化试题出现以前,语文教学中就存在着专制现象:该怎么理解一篇课文、怎么认识一种语文现象都有说一不二的“规范”,全国只有一个答案。在这种教学专制下,只有对错的选择,不讲优劣的差别;对的就没有缺点,错的就一无是处。
因此,语文知识教学,必须划清规范与非规范的界限。在有关规范的问题上,是是是,非是非,不能含糊;而在非规范问题上,则不能用“是”或“非”去判断各种语文现象,应当还给合理的意见或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以公正的评价,还给学生理解个性从而让他们获得对自己理解的信心。在这类问题上,教师们应多点宽容,不要苛求。在语文方面,人与人相比不是犯不犯错误的区别,而是犯的错误多少的区别。这种宽容,带来的恐怕不是人们语文水平的下降,恰恰相反,很可能是语文总体素质的提高。
标签:语言表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