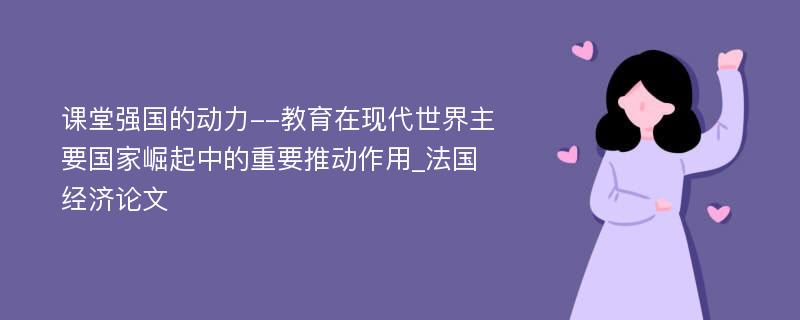
教室里的强国动力——教育在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教室里论文,过程中论文,近现代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6)03-0005-10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以“新的智力水平”来解释1600年以后欧洲的崛起。他引用伊拉斯谟关于人的理性发展的论述,说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智力水平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1] (P16-17)。把教育看作是促进国家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这种观点不仅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可以见到,而且也是很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以及世界很多国家政府的一个共识。1972年,日本外务省为纪念日本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一百周年而编写了一本标题为《教育与日本现代化》的小册子,也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一百年时间里实现现代化,教育是“创造这种卓越成就的比较基本的力量之一”[2] (P1)。
我国正面临着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研究近现代以来教育对促进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重要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都是比较领先的国家。在这些所谓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意义都非常重要。
英国的教育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教会的掌控之下。教会掌管教育虽然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教会在宗教扩张的同时也使贫民子弟有机会进入教区学校和教堂附设的识字班,在诵读圣经和学习教义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受教育机会,基本的文化教育也得到了普及。正如奥尔德里奇(R.Aldrich)所说的那样,在英国,“从中世纪开始,普及教育的理想便能以基督教的语言来表达了”[3] (P34)。1646年,苏格兰议会批准枢密院关于每个教区都必须建立学校的决定,并作出了要为学校提供房舍和支付校长工资等具体规定[4] (P311)。基本教育的普及,为英国产业革命和国家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096年就已经存在的牛津大学和1209年即已形成的剑桥大学①,尽管也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作为传授高深学问和探索新知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对英国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作用绝不应忽视。如果没有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和发展,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培根、牛顿的出现以及当时的经验自然科学兴盛是不可想象的,工业革命恐怕也无从谈起。17世纪末,英国又出现了开设自然科学和实用职业课程的中等学校(academy),这些中等学校大多私立(因而亦称tuition academy),其培养的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等一批人,实际上成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教育补助金法案,开启了英国教育的国家化发展进程。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全国划分学区,在缺少学校的学区兴建学校,实施5—12岁强迫义务教育。1902年,英国政府颁布巴尔福尔法案,要求郡议会和郡独立市也设地方教育局来管理当地的学校教育。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通过增加拨款等手段逐步掌握了教育领导权,并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1828年,无宗教背景的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一场“新大学运动”在英国展开,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教育更加成为英国产业革命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到1851年举办伦敦工业博览会时,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地位已经确立。
欧洲大陆的荷兰、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兴盛,也同样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海上马车夫”荷兰很早就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早在1575年,荷兰就建立了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登大学,紧接着又有弗兰克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哈德维大学、乌德勒支大学等大学相继建立。当时,外国很多遭受迫害的新教教徒和进步学者都避居荷兰,著书立说。如笛卡尔、惠更斯,现实主义画家伦勃朗等,都曾长期居住在荷兰。一时间,阿姆斯特丹和莱登成了欧洲的出版印刷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英国的新大学运动等高等教育的变革也曾深受荷兰的影响。可见,历史上荷兰的强盛与教育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法国当然也不例外。1833年,法国颁布基佐法案(Loi Guizot),规定每个乡必须设立一所初等小学,每个省会及六千人以上的市镇必须设立一所高等小学,每省设师范学校一所,并规定了教师薪俸的最低标准。这一法案促进了法国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850年,法国政府颁布教育自由法,天主教乘机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在普法战争失败以后,法国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大力推行教育改革。1881年6月和1882年3月,两项费里法案(Loi Ferry)先后获得通过,法国开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1890年,激进共和派在法国执政以后,更是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将一些高级初等教育学校改建成工商实科学校,对劳工子弟进行实用性课程的教育,同时在中学和高等学校的教育内容中充实科学和实用技术,并初步确立了法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制度。进入20世纪,法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开始了以电力和石油等现代能源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创新也走在世界前列。
德国和美国这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更是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在这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年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途径,而与农业社会和以作坊式生产等为特点的初级工业社会相比,这种发展道路对教育的依赖程度更大。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是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早在1559年,威丁堡公国的大公就颁布学校教育章程,提出要将文化启蒙的学校“建立在每一个山村”[5] (P173),此后整个德国都纷纷效仿。同样,宗教在德国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529年,梅兰克顿发表了为萨克森王国制定的学校计划,其中也提出“传教者也应该训诫人民送他们的孩子上学,这样,把孩子们培养起来在教堂传授正确的教义并以聪明和能干的才智为国家效力”[5] (P175)。世俗和宗教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有力地推动着德国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619年,德国威玛尔地区颁布的学校教育规章就确立了强迫义务教育的原则,规章要求本地区的校长和僧侣登记和劝告6—12岁儿童就学,并规定必要时由地方政府勒令家长履行其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此后其他地区纷纷仿效。到18世纪,普鲁士各个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6] (P92-93)。1809—1810年,洪堡在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大臣期间,提出对普鲁士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他创办柏林大学,重视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推动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为提高德国的国家创新水平和能力开辟了有效途径。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德国后来居上,快速彻底地实现两次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正如卡尔金斯(C.C.Calkins)在其《美国史话》中所说的:“很久以来,我们美国人就倾向于期待正规教育能够解决我们许多最严峻的问题。”[7] (P1)早在独立之前,移民来到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就很重视其子弟的教育问题。1636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刚建立六年,北美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就建立起来,其校门口的石碑上铭刻着这样的话:“自从上帝引领我们平安来到新英格兰……我们希望和追求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推进教育而传之子孙,因为我们深恐当现在这些传教士去世后,将来的教会里只有目不识丁的牧师了”。这一例证同时也说明了宗教起初在美国教育发展中也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捐资哈佛大学的约翰·哈佛本人就是一名牧师。在1647年通过的《老骗子撒旦法》(The Old Deluder Satan Law)中,普及教育与浓厚的宗教意味也紧密交织在一起。1837年,贺拉斯·曼出任马塞诸塞教育委员会首任秘书长,在他和一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得以在美国逐步确立。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而且使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更加直接,而且更广泛地被认识。
高等教育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对产业升级换代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早在1862年7月2日,美国总统林肯就签署了著名的“莫雷尔法案”,通过划拨土地或将土地变成基金等方式,资助各州五年内至少开办一所学院[5] (P489-491),开设实用课程。这一举措开创了高等教育直接为工农业生产培养实用人才的新理念,大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在美国人心目中确立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初级学院运动。二战结束后,这类两年制学院又被称作社区学院。两年制学院的兴起不仅为美国普及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而且进一步拓宽了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特别是在二战结束美国启动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之后,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迅速扩展,在为美国培养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照德国洪堡理念建成。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兴盛,美国人创造性地将这种大学办学模式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结合了起来。纵观美国的兴盛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如今美国人在国家发展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与他们长期重视发展教育是分不开的。
再看日本这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崛起时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已经接近成熟,人类社会正逐步迈向工业化的顶峰,并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再后来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教育在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日本经济起飞是最早的。日本学者永井道雄按照经济学家W·罗斯托的研究,认定“日本开始起飞的时期是从1878年(明治11年)到1900年(明治33年)”[8] (P1)。回顾日本的教育发展历史,可以明显看到教育发展与日本经济起飞之间的呼应关系。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基本教育法,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提出为6—14岁儿童普及初级教育并建立中学和大学,向民众开放教育机会,从而为日本奠定了“飞跃的先决条件”②。1879年,日本又模仿美国教育制度,公布了教育条例,以代替先前的教育法,日本的教育开始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快速发展。1885年,森有礼担任日本内阁制下的第一任文部大臣,现代教育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1893年,文部大臣井上毅根据其“人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构成富强国家的“无形资本”的思想,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873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只有28.1%,而到1903年,已经超过90%[2] (P23)。与此同时,从1885年到1913年,日本GNP总值翻了一番强[9] (P164-166)。
1946年4月,美国教育代表团发表报告书,要求日本对其教育进行全面改革。从此,日本开始了其二战后的一系列教育改革。1947年,日本颁布实施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提出保障教育机会均等,为“建设既有民主又有文化的国家”而实施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10] (P1)。同时,大量开办的新制高中,使日本高中教育得以在更加强调普及性和大众性的理念指导下获得发展,并且拓宽了通向高等教育的道路。1949年,新教育体制下的四年制大学开始开办,到1969年,日本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突破20%。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GNP开始超过英、德、法等国。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民总资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的经济大国。二战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日本因长期重视发展教育而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被完全毁灭,战后这一成绩又在新的水平上适时地获得了提高。1960年,池田内阁通过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工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劳动力的未来趋向,积极解决发展人的能力的问题,包括教育、训练和研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2] (P55)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与他们长期重视教育的发展确实是分不开的。
在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崛起过程中,教育促进的绝不只是经济发展,更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民族生存能力的整体提升。
在近现代世界史上,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业生产在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实力增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小农生产相比,大工业生产中需要运用的知识和技能更加复杂和专业。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者的培养和训练模式的依赖性更大。同时,人们在知识生产中的协作与竞争关系,知识传播和技能训练的模式及其效率,逐步取代了农业社会的宗法关系而成为普特南(Robert D.Putnam)所说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③ 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一种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财富增长和教育事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当今世界仍然表现明显。纵观近现代世界史,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近现代的崛起,并非只是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结合的结果,更是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特征的新型社会资本迅速增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表1 部分国家国民账户和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的历史变化(1890—1990)④
(1)国民账户[1]:现价亿货币单位 (2)每万人口在校中小学生数:人 (3)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人
别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1980 1990
美 (1)131 187 353 915
912 1004 2883 515310155
2732057650
国 (2)
2021 2040 1937 1996 2244 2080 1814 2202 24982045 1866
(3)
25.4 21.1 39.1 56.8 89.6110.1 176.5179.6389.7
534.1551.2
英 (1) 14
18
21
6042
67
114 226 4422010 4790
国 (2)
1299[2] 1457[2] 1540 1478 1400
… 1384 1583 17471796 1509
(3) …
…
…
… 13.4
… 22.5 25.3 48.262.6 78.3
德 (1)237 325 458
…
719
… 1197[3] 3824 8010
1673024480
国 (2) … 1591[5] 1745 1225[6]
1305 1188[7]
1373[8] 1165 1438 …783.7
(3)6.1 8.9 10.9 14.3[6]
19.7 7.2 21.7[8] 42.4 72.1 … 165
法 (1)289 328 409 1754 3341
… 1020[4] 2970 7830
2808065090
国 (2)
1492 1464 1475 1212 1157 1364[9]
1271[10] 1548 1508[11]1469 1275
(3)5.2 7.8 10.2 12.9 19.4 30.9[9]
36.5[10] 45.2108.8[11]
158.5206.7
日 (1) 11
24
39 159
147 394 394701550073300 240000
424000
本 (2)782 1090 1165 1628 1733 1948 2221 2330 17781840 1648
(3)3.8 5.8 9.8 14.3 28.2 34.1 48.1 76.2161.0
156.8172.6
资料来源: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第四版),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表格中每万人口中中小学生数和大学生数系根据该书中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得出。
一个国家的崛起,其财富的积累和增殖,不仅表现在这个国家的物质再生产的能力中,而且还表现为它的知识再生产能力。历史越是发展,知识再生产能力的作用就越是显著。人类历史进入近现代工业社会以后,由于工业化大生产对知识再生产的依赖性更大,大规模地培养有知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需。于是,学校教育这种通过班级授课制实现规模化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人才培养新方式,首先在崛起中的欧洲产生并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尽管夸美纽斯创立的以班级授课制为特征的学校教育最初并非产生于英国、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这种新型教育方式在当时欧洲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新型教育方式,不仅直接提高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知识传播和技能传授的效能,而且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知识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学校教育使欧洲掌握文化知识的社会成员迅速增加,加快了欧洲国家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速度,提高了知识与社会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程度,进而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知识生产力,而知识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更高水平的生产方式来创造和累积财富。
教育不仅培养从事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劳动者,还培养了社会管理者,这里既包括直接从事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人员,也包括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去的广大民众。正是通过普及教育,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其社会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参与、影响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进而也推动着社会制度的完善。回顾近现代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政府、宗教团体和个人等广泛开办学校,尽管他们都出于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但客观上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民众学会了认识《圣经》上的文字,同样也可以运用这种本领来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者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进而还可以运用从学校得到的书写本领来把自己的思想以署名或匿名的方式公诸于众,传递到远方。教育的日益普及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民众日益普遍地形成了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进而共同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鲍尔生在他的《德国教育史》中曾这样描述18世纪的德国:“受到学校教育影响的群众不断扩大……于是一个爱好读书、阅报、观赏戏剧,关心艺术与科学和重视政治生活的广大有教养的阶层,遂逐渐形成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也在这时开始出现”,于是他得出结论说:“18世纪的强迫教育更为19世纪群众地位的得到提高,打下了基础”[6] (P102)。民智的普遍开启带来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正是不断普及的教育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催生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萌发与生长,进而成就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实现了有关国家在近现代的崛起。
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实是一种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很多方面。近现代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表明,经济富强、技术发达或者军事力量的强大,都并非只是一个国家国力增强的唯一体现,甚至可以说这些都不是一国之崛起的最为重要和最长远的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增强过程中,决不应忽视国家文化力量的增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力量的作用往往要比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作用更加久远。孔子、柏拉图时代曾经最为强盛的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如今早已不值一提了,但那时文明古国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力量,却至今仍是一些国家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一部分。回顾西方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人们接受、传播和创造文化的能力得到增强,还为文化创新争取和建构了更加宽松和有利的环境。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当时的西方解放了经济的生产力,而且也解放了文化的生产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积累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力量,这是它们的综合国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教育不仅教人以知识和技能,还养成人的道德品格。教育促进国家崛起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在教育达成社会公众道德的普遍改良上。社会道德水平也是综合国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论述其“社会资本”理论时就认为这一概念与“公民道德”(civic virtue)有着紧密联系[11]。如果是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或者是适合时代要求的道德,那么它应该是构成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教育不仅可以提高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进而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养成国民合乎社会和时代要求的个人品德,促进、维护和保障个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建立社会整体的道德共识,从而改善社会运作状况,推动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譬如,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包括通过宗教训诫,近现代西方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全社会公认的诚信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括经济交易在内的很多社会运作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说,通过普遍提高民众道德素养,建立和维护适合时代要求的道德体系,这也是教育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根本上说,教育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就在于通过开启民智全面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决不应该把“文明”这个概念简单地还原为财富、技术或别的简单东西,而应对其作更加丰富而全面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并不是国家崛起的最终目的,而是国家崛起的手段之一。近现代西方国家通过教育的普及不仅促进了其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增强,而且还在另一更加深刻久远的意义上实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今天看到民众相互尊重、关心社区和爱护环境等良好的道德和生活习惯,就不能不认识到国民素质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最了不起的部分,它直接代表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与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因素相比,教育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要素,对国家崛起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特性,同时,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分析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往往是综合而全面的。对一个国家的崛起来说,教育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培训劳动力以满足经济生产的需要,而是通过培养“人”实现了对社会进步总体进程的影响。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这些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崛起的助推器,并且“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1] (P243-244)。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点燃这三大助推器的正是教育激发出的人类智慧的火花。仅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知识方面,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给了英国人一个全新的宇宙;政治方面,早在1688年,英国人就通过光荣革命在世界上率先以君主立宪的议会体制取代了封建君主专制;生产方式方面,18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是直接奠定了富强的英国及其世界霸权的基础。这几大方面的历史进程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奇波拉(Carlo M.Cipolla)在阐述工业革命的历史时就曾经说过:“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他认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是因为英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12] (P10-11)。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都是英国人民创造的,人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人的因素而言,正是普及的教育为科学与大众生产生活的融合,特别是为学者们的科学研究与工匠们的技艺相结合,为社会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教育的作用尽管通常很难立竿见影,影响却是长远而深刻的。这一点在近现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的崛起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历史偶然事件,而是从文艺复兴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开始了的一个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育潜移默化却影响深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英国的崛起是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开始的,但早在12世纪中叶,英国人就建立了牛津大学。15世纪后期,小教堂的增多使得教授“识字初级读本”的基础学校在英国普及开来,并且中学和大学此时已经逐步取代修道院承担起了学术和教育的职能[13] (P544)[14] (P149)。16世纪,英国贵族们的生活风尚就从崇尚骑士文化转向崇尚知识和教育,形成了以接受教育为荣的社会风气。到17世纪,以贫民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教区慈善学校等大量涌现。这都为工业革命和英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的作用虽然缓慢,但这种影响往往是长远而深刻的。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欧洲贵族从文法学校旧式古典教育中获得的实用知识,实际上比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比劳工阶层子弟所获得的实用知识都要少。然而,这种有趣的教育差异尽管没有立刻引起阶级统治的更迭,甚至起初一些新兴资产阶级还以效仿百无一用的贵族教育为荣,但由于接受贵族式教育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能力和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日渐式微,最终还是必然地导致了贵族阶层的没落,进而带来欧洲诸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革。更发人深省的是,那些从实用角度看来似乎毫无价值的贵族式教育对社会进步并非毫无积极作用,特别是它对青少年进行的坚守信念、捍卫正义、忠诚谦逊、扶助弱者等品质教育和优雅语言、得体礼仪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其积极的社会效应甚至可以说已延续至今。
教育对一个国家发展和崛起的作用还常常表现出间接性和复杂性,这在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也有所体现。教育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总是要通过它所培养出来的人作为中介,藉由具备一定能力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来促进国家的崛起。所以,教育首先是满足了人的发展需要,然后才谈得上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很难用“教育——人才——经济发展——国家崛起”这样一类简单的模型来解释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培养人,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可以借助多种多样的机制来发挥其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意义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James B.Conant)曾经说过的,美国的大学并不像欧洲那样特别强调培养某一专业方面的人才,“具有美国特点的大学与其说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崇拜个人发展的地方”[15] (P699)。如果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大学似乎是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脱节的,但事实上,正是高等教育这样一个看似不合理的特点,推动着美国崛起的步伐。教育通过传授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推动其介入社会生产生活并不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促进了科学知识与工匠生产活动的结合,更是直接推动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崇尚创造发明风气的形成。
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文化和科学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越是突出,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也越是明显。在前工业社会中,农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要生产方式,人的勤劳等品格和手工技能直接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科学知识在普通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甚至连贵族们也较少学习科学知识,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只需由少数掌管天文和气象观察的官员等掌握和运用就够了。家庭教育和少量的文法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主要形式,一般民众的教育则主要控制在教会手中。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学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教育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日渐突出,兴办教育也因而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时期,大规模复制是获取工业生产利润的主要手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以班级授课制为特征的现代学校教育产生并发展起来。教育通过大规模培养掌握一定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包括培养专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脑力劳动者,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国家崛起。如今,历史发展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意义在各类教育中凸显出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班级授课制所遵循的大规模复制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要求。近年来,教育的发展又重新呈现个别化特征,强调个别教学的网络学习、家庭学校(home-school)等新型教育方式又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产生出来。这种个别化的新型教育也可能成为将来国家发展和崛起的新制高点。
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当然也不是无条件的。要发挥好教育在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应当创造有利于教育发挥其作用的条件。
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其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纵观近现代西方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社会和国家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是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教育普及的重要因素,这是教育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国家教育体系尚未形成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多为教会支撑和掌控。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由国家投资兴办并掌管的学校教育体系逐渐成为一国教育事业的主干部分。当国家教育体系形成之后,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日益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政府通过税收来集中社会资源兴办教育事业,学校教育在近现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教育的普及程度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殖民时代的美国,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的欧洲移民登陆北美新大陆,1647年旨在普及教育的《老骗子撒旦法》就在马萨诸塞颁布,规定满50户的城镇都必须任命一名教师来教本地所有儿童读书写字,满100户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教师薪俸由儿童的父母、雇主或全体居民承担。美国建国以后,只用了60年左右的时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克州等就先后实现了以税收资助学校教育的合法化。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大多数州都建立起了免费的公立小学[7] (P3-14)。美国人通过这种投入获得了多方面有形或无形的回报。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美国劳动力每人每工时实际GDP也随之提高。经计算,两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达到0.934,呈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增加投入以促进教育发展在提高个人单位时间产出能力方面的作用。
表2 美国劳动力生产能力与教育投入历史对照(1940—1970)⑤
年度19401946〔1〕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联邦财政总支出(百万) 9,22911,02822,78733,72451,87674,678
131,332
联邦及地方教育总投入(百万)2,638 3,356 7,17711,90718,71928,56352,718
每人每工时个人实际GDP〔2〕 58.5
68.7
80.1
94.2 104.9 125.7 137.2
资料来源:( 1)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Bicentennial Edition,Washington,D.C.:1975.p.948; ( 2)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 Statistical Portrait,Washington,D.C.:1993.p.93.
当然,教育投入亦须科学合理方能真正有效地促进教育发展,这也是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促进作用的条件。所谓教育投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好对教育如何投入、投入多少、投入到哪种教育和哪一级教育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一系列问题,才能在教育投入与国家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譬如,20世纪60年代政府大笔的投资的确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获得巨额投资的研究计划,把许多教授从课堂里吸引了出来”,研究工作的额外负担——“要么发表,要么发丧”(Publish or perish)——“经常使他们忽视其教学职责”[7] (P33-36),导致大学教学质量下滑,甚至成为美国60年代后期全国性学生骚乱的直接诱因之一。这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短期难以消除。
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思想和技能要适应时代要求,这是教育在国家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条件。如前文所述,在近现代欧美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人文主义曾是通过教育不断散播并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潮之一,但是,当工业生产方式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以后,原本进步的人文主义教育在科学知识的传授方面又变得迂腐过时。正如蒙田曾嘲讽的那样,人文主义学究们把学问挂在嘴边只为了炫耀,在这种教育中,人们“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去填充记忆力,却让理解力和道德心灵空虚着”[16] (P376)。后来,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和实科中学先后产生出来,众多科学知识进入了中学和大学课堂。根据1756年新哥廷根大学格斯纳教授出版的《论文科中学的组织》所描述的情况看,当时实科中学在德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6] (P396-399)。正是这种发生在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使得适应时代要求的知识、思想和技能适时地在相关国家得到传授和应用,促进了这些国家在近现代的发展和崛起。这方面也不乏相反的例证,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国家主义教育,压制学校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自由,推行以神道教、政府和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改革,最终将日本引向战争,并招致毁灭性的打击,可谓损人害己。日本外务省1972年出版的小册子《教育与日本现代化》中也承认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国家主义教育的失败”[2] (P35-40)。这些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我们在教育中传授的思想、知识和技能是否符合时代要求,直接决定着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是否能正确地发挥其作用。
从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来看,为教育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给予其多样化的发展空间,也是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发展中重要作用的一个条件。只有教育的自由发展,才能产生多元思想的碰撞与创造力的激发,从而带来根本上源于人本身的推动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就世界主要国家的近现代发展而言,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往往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一个在教育中禁锢思想、压制人才和束缚创造的国家是很难获得长远发展进而实现崛起的。1808年,在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前两年,拿破仑也对法国的大学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但两国采取的方针政策恰好相反。拿破仑通过政府制定的严格规章来控制大学,大学被置于政府官吏的控制之下,教授只是讲课教师和监考人员,而不是学者,探索和创造精神在大学里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与此同时,曾被拿破仑征服的普鲁士在洪堡等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引导下,鼓起勇气走了一条与拿破仑相反的道路。他们把培养政府未来官吏的任务委托给大学,并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洪堡强调自由的学术研究,鼓励教授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并把新知识带进课堂,也要求学生在掌握科学原理的同时努力参与研究工作,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创新精神和思考能力。五十多年后,法国也不得不开始按照德国洪堡的路线来改造教育,“这就充分证明:听任教育自由发展比妄施控制与约束是更为优越的”[6] (P126)。
近现代世界历史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社会(the schooled society)兴起史”[3] (P180)。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证明,国家的崛起有赖于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了人的发展。教育通过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而意义深远的促进作用。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促进作用的各种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指望在教育发展中立刻得到回报。教育发展在社会进步和国家崛起过程中带来的综合影响,往往是政府短期的计划难以预期的。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在教育发展上有长远的眼光。
本项研究获得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的支持,谨致谢忱。
注释:
①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网站的校史介绍,http://www.ox.ac.uk/aboutoxford/history.shtml,和http://www.cam.ac.uk/cambuniv/pubs/history/centuries.html。
②W·罗斯托语,转引自〔日〕麻生诚等:《教育与日本现代化》,刘付忱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页。
③“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阐释,是指一种存在于民众个人间交往关系中的经济资源,是一种社会网络以及由这种社会网络产生的相互信任与互惠模式。参阅:( 1) Putnam,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 2) Putnam,R.D.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00; ( 3) Putnam,R.D.( ed.) Democracies in Flux: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④数据注释:〔1〕国民账户(National Accounts)数据,英国、新加坡均为GDP,印度为国内生产净值NDP,法国1950年前和1959年后为GDP,德国1945年前为国民生产净值NNP,1946年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均为GDP,前苏联(俄罗斯)1956年后为物质生产净值NMP,1930年以后日本为GDP,除上述特殊情况外,国民账户栏中其他数据均为GNP;〔2〕仅含国立小学(state school),当年中学在校生数据不详;〔3〕1950—1980年德国为东西德数据合计,即东德NMP+西德GDP;〔4〕法国1960年1月以后的货币单位为新法郎,1新法郎=100法郎;〔5〕仅含小学生数;〔6〕为1925年数据;〔7〕为1939年数据;〔8〕为1951年数据;〔9〕为1946年数据;〔10〕为1954年数据;〔11〕为1968年数据。
⑤数据注释:〔1〕1945年统计数据阙如。〔2〕每人每工时个人实际GDP是指以1958年为100计算,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每人每工时的国内国民个人实际生产总值(real gross private domestic product per man-hour)。
标签:法国经济论文; 日本大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