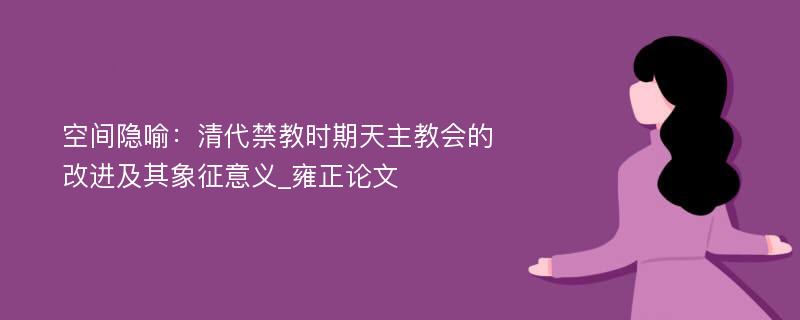
空間的隱喻:清代禁教時期天主教堂的改易及其象徵意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堂论文,清代论文,象徵论文,改易论文,禁教時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B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5)04-0061-09 在歷經明亡清興的易代戰火之後,清代前期天主教迎來了一段短暫的發展高峰,此時期西方傳教士聯袂入華,在各地建堂立會,吸引民眾入教。然而,到了康熙後期,隨著禮儀之爭愈演愈烈,天主教會在華的活動日漸面臨不利境遇。雍正即位後,正式確立禁教政策,嚴禁天主教傳播。在清廷禁教的諸多措施中,其核心内容涉及到如何處理大量分布在各地的天主堂這類習教場所。在清廷頒佈的禁教令中,只籠統提到各地天主堂“改為公所”,①其真實情況卻很不明晰。鑒於目前對於清代禁教時期天主堂改易的具體情況尚未有專文細加深究,本文利用從地方志中爬梳的資料,結合其他相關中西文獻史料,考察清代雍正、乾隆、嘉慶禁教時期天主教堂的改易狀況,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針對宗教空間的上述改易行為所蘊含的文化象徵意義。 一、教堂改為官署、公倉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清廷正式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在華傳教士除部分懂技藝者留京效命外,其餘皆禮送澳門安插,同時,也下令關閉京師之外的天主堂,“所有起蓋之天主堂,皆令改為公所。”②由此掀起了百年禁教的序幕。 隨著禁教令的頒發,各地官府在執行朝廷禁教政策的過程中,普遍需要考慮如何處理當地天主教堂的產業。除了一部分教堂被封存或者變賣外,官府通行的做法是遵行朝廷“改為公所”的旨意,將教堂改作公用。而在具體改易過程中,則略有差别。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一部分教堂被改為官署,如湖北漢口鎮仁義司巡檢署:“雍正五年增設,署在居仁坊舊天主堂。”③福建寧德縣:“城内公館,舊以布政分司署為之,國朝雍正間裁禁天主教,改北門内天主教堂為公館,即今所。其分司署石堂巡司移寓其間。”④廣東增城:“營參府署左營守備行署在北門大街右廢天主堂故址,守備雖駐龍門,因公赴增之日多,乃葺而居之。⑤湖南長沙:“縣丞署,原在錢局,雍正七年廢天主堂為今署。”⑥湖南衡陽:“縣丞舊署原係天主堂,雍正二年奉文飭禁,改作縣丞署。乾隆二十一年移駐查江、衡清兩縣瓏房,買為公所,即今神農殿,詳祠祀。”⑦江西新建縣:“上諭亭,在瓦子閣,廢天主堂改建,為張掛上諭之所,與官銅庫共基。官銅庫在瓦子閣,廢天主堂改建。”⑧ 除了官署之外,天主堂還被大量改作公倉,如廣東新興縣:“北倉在縣治東北,雍正六年將天主教房屋改建,正廳一間,倉廒十六間,計儲榖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三升七合。⑨福建邵武府:“廢倉二,一在建南道署舊址,一在北門天主堂舊址。乾隆十六年變價解司。”⑩江南松江府華亭縣:“常平倉,雍正元年以府城内天主堂改建。”(11)“常平倉三所,一在縣大堂西,十一間;一在婁治東,十一間,係天主堂改建;一在雲峯寺西,二十一間,係陸文遂入官屋改建,名陸家厫。”(12)奉賢縣:“常平倉,分府城内天主堂。雍正五年知縣舒慕芬改建。”嘉定縣:“常平倉在嘉定城内,雍正七年知縣傅景奕改天主堂建。”(13)寶山縣:“倉厫因縣治濵海地濕,雍正九年,知縣傅景奕在嘉定縣城東門天字型大小四圖,卽天主堂改建,倉房七間。十二年,知縣文鐸在西門内天字型大小六圖建造大門一間,官廳一間,倉房四十三間。乾隆六年,知縣胡仁浚在縣治北門内岡字型大小四十三圖建官廳一間,倉房二十間。”(14)雍正年間江寧府上元縣“常平倉,因西洋天主堂改建,在漢西門内。”(15)雍正年間法國耶穌會士也記載其在漢口的天主堂亦被改作公倉:“我們在漢口的教堂受到漢陽的官員們的保護,一直沒有被挪作他用,剛剛被新來的總督指定作為糧庫低價放糧給小民百姓。”(16)長沙府湘潭縣:“天主堂常平倉十六間”。(17)“城總社倉一間,即天主堂常平倉側,貯穀七百七十五石四鬥一升”。湘潭縣這所被改為常平倉的天主堂,即是康熙年間知縣、教徒姜修仁所建:“附天主堂,舊在縣署西,康熙二十四年知縣姜修仁建,修仁即奉其教者也。雍正四年禁毀,今其地改建常平倉。(18)揚州府江都縣:“常平倉,一在本縣舊城内軍儲倉之舊基,雍正九年,縣令胡詳建厫房十二間,雍正十一年,縣令朱添建厫房六間,乾隆五年,縣令五添建倉廳三間,厫房十間,共計厫房二十八間。一在甘泉境内新城戴家灣地方,計厫房十三間,雍正九年,縣令胡以入官之天主堂房屋改建。”(19)江西撫州南城縣:“天主堂,在黃家嶺天一山下,西儒駐劄焚修,順治戊午年重修,雍正二年毀,改建倉屋。”(20)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在改易各地天主堂過程中,地方官府將其改成常平倉的比例較高。常平倉是清代備荒倉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府通過這些分布於州縣城的官倉,囤積糧食,在平糶、出借、賑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社會功能。雍正年間,各地出現了大量將天主堂改易為常平倉的情況,這與此時期清廷重視常平倉的建設是相符合的。雍正即位後,十分重視倉儲體系的建設,除了諭令各地建立地處基層鄉村的社倉之外,也強化了對常平官倉的建設與管理。與此同時,鑒於“以常平之穀為國家之公儲,關係己身之考成”,(21)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級地方官員自然樂於將天主堂改易為常平倉,從而達到既符合朝廷要求,同時也為自己博取政績的目的。而作為重要的施政措施,這種改易天主堂為常平倉的做法,也常常會被視為地方官員值得誇耀的宦績而被記錄在各種地方文獻中。如江西建昌縣天主堂被改成常平倉,就成為時任知縣李朝柱個人生命歷程中一段重要的記憶:“李朝柱,字東崖,山西臨汾人,監生,雍正二年官建昌知府,才識明敏,喜任事,在官三年,建義學,修樓櫓,營試廨,改天主堂為縣倉,百廢具舉。”(22) 二、教堂改為書院、社學 除了官署、官倉之外,書院、社學等地方教育場所也是禁教時期天主堂改易的主要目標之一。實際上,清前期謀劃禁止天主教傳播的地方大員,其主要的想法就是將天主堂沒收改為書院、義學,如康熙末年福建巡撫張伯行曾經試圖向清廷上疏,將天主堂改成義學,其所撰“擬請廢天主教堂疏”云:“伏望皇上特降明詔,凡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歸本籍,其餘敎徒盡行逐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為諸生肄業之所,以厚風俗,以防意外,儻其不時朝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館供億足矣。”(23)雍正元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發起禁教,也是“以西洋人行教惑眾,大為地方之害,請將各省天主堂改作書院、義學,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門,俟有便船歸國。”(24) 清代科舉制度漸趨完備,各地普遍重視書院、社學教育,士大夫也將復興儒學教育視為義不容辭的職責,因此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發現當時不少教堂被改為書院、社學。如福建福州:“理學書院,在化龍街西,舊為天主堂,國朝雍正元年,總制滿保、巡撫黃國材檄毀,知縣蘇習禮允諸生請,改為書院,中祀周、程、張、邵五先生。”(25)福建將樂縣:“先是,正學書院未建之先,故有正音書院。院前為天主教堂,雍正元年奉詔禁革,七年,設正音教職一員,尋寢。邑中義學權於斯設焉。”(26)福建福清縣:“興庠書院在西隅大街,舊天主堂地,雍正元年奉文改設,别祀儀會。紳士僉請撫憲黃、總督滿捐貲重建,祀二程、常公,以為肄業之所,登科甲者各豎匾其中。”(27)山西絳州天主堂也在雍正二年被時任知州、江西南城人萬國宣改為東雍書院,(28)絳州地方志書中記載了這段改易歷史:“東雍書院在城内正平坊,故明王府業,國朝初西洋人據為天主堂,雍正二年知州萬國宣逐回,改東雍書院。”(29) 除書院外,也有一些地方將天主堂改建為義學,如山西太原:“義學,在大北門街,雍正五年巡撫覺羅石麟改天主堂建,延師教授,歲給廩餼。”(30)廣東新會縣:“古岡義學在金紫街,舊為西洋天主堂,雍正五年奉文改為公所,十一年知縣張埕據生員甄相等公呈,詳請為義學。”(31)雍正年間廣東保昌縣的一所重要社學——湞江社學,也是改自天主堂:“附社學:湞江,順治己丑兵燹後遂廢,今失其處。雍正辛亥,署縣逯英改天主堂置,義學就圮,遷於此。”(32) 三、教堂改為祠宇宮廟 除了上述官署、官倉、書院、義學之外,從資料中可以看出,也有相當多教堂被地方官府改為祭祀先賢的祠宇宮廟。如湖南郴州:“韓公祠,祀唐昌黎伯文公韓愈,祠舊在州學内,後遷建北湖右岸,元末毀,明正統間知州袁均哲重建。正德時知州沈照改建城隍廟東,易名景賢祠。明末毀。國朝康熙五十七年知州范廷謀因城南門外天主堂舊址改建,今仍之。每歲春秋二仲致祭,陳設儀注與濂溪祠同。”(33)景賢祠是奉祀韓愈的先賢祠,而福建地方因為是朱子學的發源地,不少天主堂被改為奉祀大儒朱熹的朱子祠,如寧化縣:“朱子祠,祠在城北翠華山下,雍正十三年邑人贖回天主教堂,祀文公朱子。乾隆元年,奉文廢天主教,其教堂變價充公,黃象禹等倡捐祀田,督學王傑為之記。”(34)邵武府建寧縣朱文公祠“在北門内。邑舊無祠,雍正元年詔毀天主堂,邑令皇甫文聘改為文公祠,制主懸額,因廟制未妥,配享未設,複於雍正五年捐俸四十金為倡,從新改建,買田八畝二分,又撥縣前官地店租銀一十兩,以供春秋祭祀。”(35) 上述景賢祠、朱子祠都是天主堂改成的專祠,而一些地方的天主堂則被改易為合祀眾多鄉賢的祠宇,如福建延平府天主堂:“在普通嶺下,順治十二年建,雍正元年改為閩賢祠,祀楊、羅、李、朱四先生及眞子、黃子、蔡子、胡子、陳子等諸賢,因即祠為書院。”(36)江南長洲府長洲縣鄉賢祠:“闕里分祠,在文一圖通關坊,祀先師曁肇聖、裕聖、貽聖、昌聖、啟聖五王……雍正二年,布政司鄂爾泰並拓天主堂地,裔孫興豫捐建。”(37)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天主堂改易而成的祠宇類中,節孝祠所佔比例較多,如浙江平湖縣:“節孝祠,在縣治西西司坊東太平橋,雍正元年奉旨詔舉行,四年,知縣楊克慧建,舊為天主堂基,凡邑内節婦貞女題旌者咸祀之。乾隆四十年知縣劉雁題重建。”(38)廣西臨桂縣:“節孝祠……在十字街,即舊天主堂,知縣湯大瑜詳署巡撫韓良輔改建。”(39)江南太倉州:“節孝祠在城東街,國朝雍正三年知縣將天主堂改建。”(40)蕭山縣:“節孝祠,在西門外德惠祠旁,雍正四年知縣門鈺奉文建……屋在西山麓,卑濕沮洳,日漸頹圮。乾隆七年,邑人林震等請於知縣姚仁昌,申詳各憲,移建城内,拆改天主堂為節孝祠。”(41) 明清時期,因為理學的滲透與倡導,社會上大力提倡婦女節孝觀念,雍正即位後,更是極力推崇,雍正元年,“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42)因此各地普遍建立節孝祠,這也成為地方官府的一項重要營建與教化工作。而隨著天主教傳入後,一些婦女皈依天主教,並參與宗教聚會,這種“混雜男女”、“夜聚曉散”的宗教活動,一度被視為與儒家節孝觀相抵觸的行為而遭到批判。禁教期間各地天主堂被改易為節孝祠,也恰好迎合了這種社會需求,一方面,官紳可以借此舉警諭天主教吸納婦女入教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包含著響應朝廷褒揚儒家貞潔孝道的意義。 除了先賢祠、節孝祠等表彰類祠宇之外,從現有資料可知,禁教時期還有一部分天主堂被改易成各種宮廟,如雍正八年(1730),著名的杭州天主堂由總督李衛改建成天后宮。(43)上海天主堂則被改易成關帝廟:“天主堂初在縣治北,西士潘國光建。相傳天啟間長安中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為已顯於唐之世,時徐光啟假歸里居,西士郭仰鳳、黎寧石與語契合,乃為建堂於居第之西。崇禎二年,光啟入朝,以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薦修曆法,有欽褒天學之額,懸之各堂,而上海居最先。西士潘國光以舊建堂卑隘,市安仁里潘氏之故宅為堂。康熙四年,眾西士奉旨恩養廣東。雍正二年,上允浙閩督臣之請,部議處分,除在京辦事人員外,不許外省私留,是堂改為關帝廟及敬業書院。前志載院後有觀星臺即此。”(44) 天后和關帝都是明清時期列入國家祀典的重要神衹,其信仰活動與廟宇營建通常被視為帝國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遠非其他民間信仰神衹可比。因此,天主堂被改易為這兩類列名國家最高祀典神衹宮廟的行為,在國家與地方層面上就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徵意義,對於中西雙方來說,都十分重視這種改易的話語權。而在晚清的還堂事件中,圍繞著這兩類宮廟與天主堂的複建,也表現出較為複雜的狀況,這一點將在後文略加分析,此處暫不贅。 除了上述天后宮與關帝廟這樣的重要祠廟外,還有一些天主堂被改易成其他類型的神廟,如海南瓊山縣著名的萬壽宮,就是輾轉改自天主堂:“萬壽宮,在城内西南隅,乾隆四年,副使劉庶、總兵武進升、瓊州知府李毓元、瓊山縣知縣杜兆觀捐建。中為正殿,八角龍亭一座,内朝門一座三間外,東西朝房十間,午門一座三間,外東西官廳二間。乾隆十一年,巡道謝櫏、總兵黃有才、署瓊州府知府于霈、瓊山縣知縣楊宗秉協捐增建内朝房十間,午門外照牆内戲臺一座。先是地原係廢毀天主堂,雍正八年總兵官李順奏請為武義學,乾隆三年奉文裁革。”(45) 萬壽宮主要是奉祀許真君的南方道教體系民間信仰宮廟,而北方地區也出現了天主堂改易成當地普遍奉祀的民間神靈宮廟的情況,如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天主堂,就被改易成為奉祀北方驅蝗之神劉猛的宮廟:“劉猛將軍祠,在祥符縣延慶觀西,舊係天主堂,宋景定間建廟,相傳神姓劉名銳,即宋名將劉錡弟,歿而為神,驅蝗江淮間有功,雍正十二年奉文建。”(46) 總之,在清代禁教時期,各地天主堂普遍被改易成上述官署、官倉、書院、義學、祠宇宮廟等公共場所。此外,還有一些天主堂被改易為慈善場所,如山東武城縣天主堂於雍正十二年(1734)被改建為普濟堂,(47)湖南巴陵縣普濟堂也是乾隆十年(1745)由岳州知府黃凝道改自天主堂。(48) 四、改易與空間隱喻:一種象徵意義解說 由上可見,清代禁教時期曾經圍繞著處理京師之外的天主堂問題發生了一次全國性的改易活動。清初地方官府在改易各地天主堂過程中,基本上都是秉持朝廷旨意,將其更改為官署、公倉、書院、義學、祠宇宮廟等公共空間。而這些“公所”類建築,在性質上與一般私人空間不同,往往在地方社會生活中具有高度公共空間特性,含有很明顯的國家意志與話語權力意識,因此,不難理解,各級地方官府改易天主堂為各種地方公共空間的活動,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建築空間使用功能的轉換,同時也是地方上一次展示“崇正黜邪”的舉措。在上述宗教空間改易過程中,其教化意義被突出強調。大量的天主堂被改為書院、義學、先賢祠宇,就凸顯了以儒學來抵禦外來學說的政治文化意義。在這種話語情景下,清代禁教時期改易天主堂的活動,往往也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徵意義,其改易歷史會被反復強化,如前述浙江平湖縣天主堂改節孝祠,乾隆年間知縣劉雁重修時,專門撰寫碑文,再次強調了節孝祠改自天主堂的歷史: 乾隆四十年春,余蒞平湖之三日,凡祠廟合祀典者,次第展禮,而節孝一祠獨頹然就圮。退而考其創建之由,實雍正四年易天主堂為之。天主堂者,前明西洋人舍館也,其人既去,其館久虛,改建之初,第仍其故宇塗墍之,迄今五十年,木朽瓦裂,蓋所由來者遠矣。粵稽往史所紀旌門之婦,尤者專祠,非有奇行者,表厥宅里而已,未聞合祠以祀之也。欽惟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元年,崇飭教化,獎淑表貞,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日月之光,照及陰崖,陽和之布,達於窮穀。所以樹風聲而勵名義者,典至巨也,澤至渥也。閭閻之毅魄、貞魂,無不銜感朝廷嘉惠弱孀之意……(49) 與此相類似的,崇明縣節孝祠改自天主堂的歷史也在時人所撰《崇明縣節孝祠碑》不斷被強調,認為節孝祠“蓋自雍正三年奉世宗憲皇帝詔毀郡邑天主堂,改祀節孝,而祠始有專屬。”(50) 在清前期禁教大背景下,改易天主堂的活動甚至會與打擊邪教的事件緊密聯繫在一起。如陝西城固縣天主堂被改為書院義學,雖然是一次改易活動,然而其改易過程卻因被渲染為一次地方官府精心實施、攻破邪教團體的行動而變得異常生動複雜。清人程岱葊所撰《野語》一書中記錄了清代禁教期間知縣程雲毀改城固天主堂的經過: 天主之說已詳第八卷,今程子翔述其尊甫稼村刺史毀城固天主堂事,與前迥異。堂在城固東關外鄉僻處,愚民被惑者多,吏役不免,故破獲較難。頭目三人,首衣藍,曰藍臣府;次衣黃,曰黃臣府;又次衣紫,曰紫臣府。其教以天為主,故稱臣府。其冠類古方巾,袍則蓝、黃、紫。外裼以他色,褙子皆異錦為緣。其堂甚峻,廣容千人,四面開門,中庭深奧,室宇環繞,路徑縈紆,誤入者迷不得出,率被致斃。所奉十字木架,高與人等,沉檀為之,飾以珠貝。行教之期,堂内鐘鼓鳴,諸門盡闢,奉教者各服其服,畢聚堂下,焚香聽命,頭目按冊點名,相率登堂,向架羅拜。步伐止齊,肅如行陣。拜畢,頭目登座,開講其經,大指述天主困苦成道巔末。講畢,眾匪齊聲朗誦,各各納錢而退。平日不茹葷酒,凡娶婦,先與頭目共寢數夕,方歸新婿,名曰供奉,恬不為恥。宰是邑者,以吏役掩護,因循未發。刺史廉得其實,密約武員,託他故,率帶兵壯千餘人往捕。至則峻宇繚垣,四門固閉,無間可乘。有民壯徐智者,素勇敢,超垣而上,餘兵壯疊肩繼登,遂開門入。刺史率弁兵圍守要隘,又選精強兵壯百名進捕。三頭目率眾來禦,遂獲二人,其一遁入内,官兵迫之,忽竄入小門不見。恐墮其計,命兵壯四門齊進,歷數十戶,至一室,見兩婦並踞於床,面有懼色,遂搜獲之。餘匪或擒,或逸。於是將各犯解省,按律懲辦。爰毀其堂,改為義學云。按此說惟奉十字架為天主教本色,其茹素斂錢,則各邪教通弊,而非天主教所有。至服飾詭異,婦女供奉,罪為尤重。向聞邪教多託佛老為名,此獨託天主為名,可謂每況愈下矣。(51) 由上引文可見,這次城固天主堂改易事件相當具有戲劇性。天主堂被描述為高牆巍聳、易守難攻的異教中心,知縣程雲最終通過武力打擊的方式才得以攻破,最後將其改建為宣揚儒家中心觀的義學。儘管這則筆記透露出不少疑點,尤其是存在著將天主教與民間宗教混淆的情況,但其中包含的“崇正黜邪”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在這次改易過程中,深刻體現出了官僚階層竭力維護帝國儒家價值觀的努力。同樣,清代禁教時期一些天主堂被改易成祠宇宮廟,也隱含了宣揚本土先賢、神明信仰,以國家正祀來抵禦天主教“邪說”的象徵意義。雍正八年杭州天主堂被李衛改建為天后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次改易事件之所以引起普遍關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持改易者乃是浙江總督李衛本人。在雍正年間禁教過程中,各地天主堂頻遭改易公用,然而李衛卻是親自主持改易活動中地位最為顯赫的地方大員之一,所以其舉動自然引人注目;其次,李衛將杭州天主堂改為天后宮,曾為此專門上奏請示雍正帝獲得准許,被視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因此,此舉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最後,他曾為此次改易活動專門撰文樹碑,這就是著名的《改天主堂為天后宮碑記》,隨著碑記廣為流傳,其舉動廣為人知。 李衛改易天主堂為天后宮,其理由是天主堂作為宗教公共空間,其建築形制適合廟宇所用: 顧其制皆崇隆巍煥,非編戶之所可居,空之又日就傾圯,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於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為天后宮之舉也。(52) 也就是說,李衛此次改天主堂,首先是其注意到了天主堂建築空間的獨特性。天主堂“崇隆巍煥”,不利於改建民居,儘管其“規模制度,與佛宮梵宇不相符合”,但在功能上卻與中國傳統廟宇並無差别,“字樣諸凡合式不用更造,只須裝塑神像”,(53)即只要更換崇拜對象便可使用。此外,李衛顯然也注意到杭州天主堂的另一個特别之處,即這座建築曾與清聖祖康熙聯繫在一起,它是傳教士用康熙南巡時所賜銀兩而建: 西洋人之居武林者,聖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兩之賜,此不過念其遠來而撫恤之,彼遂建堂於此而顏其額曰勅建。夫曰勅建,必奉特旨建造,今以曾受賜金,遂冐竊勅建之名,内外臣工受白金之賜者多矣,以之築室,遂可稱賜第乎。干國憲而冐王章,莫此為甚,他復何可勝道耶。(54) 顯而易見,李衛並不認同杭州天主堂為康熙“勅建”之所,他認為這是傳教士冒竊清聖祖康熙御賜名義,借此增加杭州天主堂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因此,他希望將之改換為名正言順的國家認可的宗教神聖空間。康熙二十三年(1684),媽祖被朝廷勅封為“護國庇民妙靈顯應仁慈天后”,正式上升為具有帝國象徵意義的國家守護神衹,此時利用朝廷禁止天主教之際,將杭州天主堂改易為供奉天后的宮廟,不僅可以正本清源,攘除邪說,同時也包含著借改易天主堂為天后宮的行動,並以天后信仰來宣威海外的象徵意義: 荒誕狂悖者宜去,則有功德於人者宜祠也。冐竊勅建之名者宜毀,則列在祀典者宜增也。天后之神,姓氏顛末見於記載者雖亦未可盡信,然我朝聖聖相傳,海外諸國獻琛受朔者,重譯而至,魚鹽商賈出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計日而出,尅期而還,如行江河港汊之間,而天后之神,實司其職,神之靈應呼吸可通,功德之及民,何其盛哉。誕罔不經者去,而崇德報功之典興。毀其居室之違制者,改為祠宇,撤其像塑之詭秘者,設以莊嚴,夫而後武林之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異端邪說乆且漸熄,其有闗於風化,豈淺鮮哉。(55) 總之,李衛此舉充分利用了天后信仰在清前期社會影響力上升的時機,其改易天主堂為天后宮的行動,深刻隱含著以國家正祀來抵抗異域淫祀的用意。此後,由建築形制高大巍峨的天主堂改建的天后宮一度成為杭州的一個文化象徵,“廟貌隆煥,獨冠郡城”。(56)其改易天主堂的行為,也因其撰文樹碑而廣為流傳,成為有清一代官紳間津津樂道的反教衛道情感聚焦的一個標志。 有意思的是,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被迫重新允許天主教入華傳教。因為法國等列強在不平等條約中加入了歸還舊堂產業的要求,於是天主教會在各地紛紛追索上述禁教時期被沒收改易的天主堂產業。而在還堂過程中,上述被改易的宗教空間所賦予的象徵意義,又再次因為西人的還堂要求而得以展示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處理還堂過程中,類似改易成官署、公倉等“世俗類”公共空間的天主堂建築物及其基址,給還過程中在地方上所引發的爭論較少;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於已經改成書院、社學、祠宇宮廟等被賦予較強象徵意義的“神聖類”公共空間,其還堂過程則曲折複雜,雙方之間爭執頻發,甚至釀成中外交涉事件。例如上述陝西城固天主堂就經歷了一番還堂周折。咸豐十一年(1861),法國公使哥士耆就向清政府要求“照約飭還”,然而卻歷經曲折:“其城固教堂基址已經改建書院,查有碑記可憑。從前曾有就城外三里之大河壩地方給與地畝抵還之議。屢催漢中府,並委員前往妥籌,旋據稟稱,傳到教人左大元等,皆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為詞,當經批催商辦等情。”(57)直到同治五年(1866),該教堂才將“原址清還”。(58)至於前述著名的杭州天主堂,也經歷了一番還堂風波。咸豐十一年,法國領事美理登向總理衙門要求歸還杭州天主堂: 杭州府舊有天主堂地基,經改建天后宮,亦應給還等語。並將杭州天主堂舊址畝糧圖冊一本,又抄錄改建天后宮碑記一紙,封送前來。(59) 然而,在恭親王奕訢等人看來,雖然杭州天主堂改天后宮事實清楚,但因為事涉宮廟,所以其歸還並不簡單: 至杭州天主堂舊址,據美理登抄錄前督臣改建天后宮碑記及戶口田畝糧稅四至地界,並從前置買原委清冊。臣等雖未據浙江巡撫知照前來,但所抄碑記,久為人所傳誦。而圖冊亦甚明晰,諒非飾詞妄請。既已改為民間廟祀,亦未便遽行給札交還,仍應移咨浙江巡撫,體察情形,如舊地可還,則還之,否則,照依舊址畝數,另行擇地,酌量給予,庶於民情撫務兩無妨礙。(60) 儘管因為資料所限,我們僅僅知道這座被李衛改為杭州天后宮的天主堂,歷經一個多世紀後,又在晚清時期被改回了原來的天主堂,(61)但其中所蘊含的波折,一定是難以勝數。 在晚清還堂過程中,天主教會往往強調依照條約規定,“各省舊有之天主堂,仍按原地交還方合”,(62)此舉顯然不僅僅是要求返回舊有產業那麼簡單,而是同時包含著一種宣示道義平反的特别用意。然而,由於禁教時期舊天主堂改成的祠宇宮廟,歷經時光流傳、歲月輪回之後,也已經成為地方社會中一種具有重要文化表徵意義的“神聖空間”。對於這種富含著地方情感認同的象徵空間,承擔著本地教化職責的晚清官紳們也是不會輕易讓步的,因此雙方之間在還堂一事上很容易發生衝突,同治年間長洲(江蘇吳縣)一則涉及還堂的記載就形象地揭示出了這種情況: 蒯德模,字子範,安徽合肥人。咸豐末,以諸生治團練,積功清保知縣,留江蘇。同治三年,署長洲……治有天主堂,雍正間鄂爾泰撫蘇,改祠孔子,泰西人伊宗伊以故址請。德模曰:“某官可罷,此祠非若有也。”卒不行。(63) 本文通過考察清代禁教期間天主教堂的改易情況,試圖說明,對於天主堂這類具有特殊意義的建築物,在滲透進帝國國家意志後,其改動已不可能只是空間功能的改變這麼簡單。清代禁教時期,遍處各地的天主堂除了一部分改為官署、公倉等場所,發揮其居住與儲糧作用之外,也有相當多數被改為書院、社學、先賢祠、節孝祠、宮廟等帶有教化意義的場所。而圍繞著天主堂改易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值得解讀的事件,由此反映出不同階層的群體,都力圖賦予這次改易天主堂不同的文化意義,或者展示儒學教化,或者宣示國家正祀,這也表明清代帝國官僚階層竭力維護帝國儒家價值觀的努力。而清代後期,隨著天主教重新獲得傳教自由,天主教會在按圖索驥、重新奪回天主堂的活動中,也不得不面對清代前期教堂改易過程中所呈現的這種複雜狀況,從而為天主堂的改易與還堂,渲染上了一種空間上的隱喻意義。 ①《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四,雍正元年十二月,第251頁。 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57頁。 ③(乾隆)《漢陽縣志》,卷十三,乾隆十三年刻本。 ④(乾隆)《寧德縣志》,卷二,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⑤(嘉慶)《增城縣志》,卷四,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⑥(乾隆)《長沙府志》,卷十一,乾隆十二年刊本。 ⑦(乾隆)《衡陽縣志》,卷二,乾隆二十六刻本。 ⑧(同治)《新建縣志》,卷十八,同治十年刻本。 ⑨(乾隆)《新興縣志》,卷十一,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⑩(光緒)《重纂邵武府志》,卷八,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11)(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乾隆)《華亭縣志》,卷二,乾隆五十六年刊本。 (13)(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四,嘉慶七年刻本。 (15)(道光)《上元縣志》,卷八,道光四年刻本。 (16)(法)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3冊,朱靜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93頁。 (17)(乾隆)《湘潭縣志》,卷十一,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18)(乾隆)《湘潭縣志》,卷二十一,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19)(乾隆)《江都縣志》,卷七,乾隆八年刊,光緒七年重刊本。 (20)(同治)《南城縣志》,卷二,同治十二年刻本。 (21)《雍正上諭内閣》,卷五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光緒七年刻本。 (23)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一,清乾隆刻本。 (24)藍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乾隆十九年刻本。 (26)(乾隆)《將樂縣志》,卷十四,乾隆三十年刻本。 (27)(乾隆)《福清縣志》,卷五,光緒二十四年重刻本。 (28)(民國)《新絳縣志》,“名宦傳”,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29)(光緒)《直隸絳州志》,卷三,光緒五年刻本。 (30)(光緒)《山西通志》,卷三十五,光緒十八年刻本。 (31)(道光)《新會縣志》,卷三,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32)(乾隆)《保昌縣志》,卷五,乾隆十八年刻本。 (33)(嘉慶)《郴州總志》,卷十三,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34)(民國)《寧化縣志》,卷十二,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35)(乾隆)《建寧縣志》,卷七,清内府本。 (36)《延平府志》,卷十三,同治十二年徐震耀補刻本。 (37)(乾隆)《長洲縣志》,卷六,乾隆十八年刻本。 (38)(光緒)《平湖縣志》,卷九,光緒十二年刊本。 (39)(嘉慶)《臨桂縣志》,卷十五,嘉慶七年修、光緒六年補刊本。 (40)(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一,嘉慶七年刻本。 (41)(乾隆)《紹興府志》,卷三十七,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42)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一,咸豐六年刻本。 (43)(乾隆)《杭州府志》,卷七,乾隆刻本。 (44)(同治)《上海縣志》,卷三十一,同治十一年刊本。 (45)(咸豐)《瓊山縣志》,卷四,咸豐七年刊本。 (46)(乾隆)《續河南通志》,卷十三,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47)(乾隆)《武城縣志》,卷十四,乾隆十五年刻本。 (48)(乾隆)《岳州府志》,卷十五,乾隆十一年增修刻本。 (49)(光緒)《平湖縣志》,卷九,光緒十二年刊本。 (50)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三,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51)程岱葊:《野語》,卷九,道光十二年刻、二十五年增修本。 (52)(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媽祖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37頁。 (54)(55)(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6)翟均廉:《海塘錄》,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58)(59)(60)(6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末教案》,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535、579、197~198、198、515頁。 (61)(民國)《杭州府志》,卷九,民國十一年本。 (63)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六,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