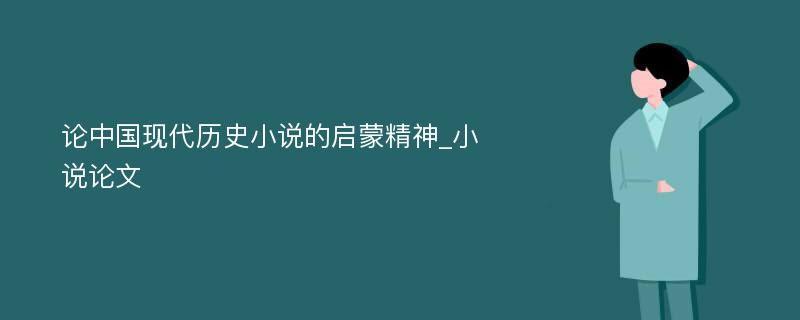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启蒙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史小说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小说(注:本文所谓“现代历史小说”就时间而言,指“五四”新文学30年间(即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时段)作家重叙历史的小说文本;就文体而言,指具备现代小说叙事型态的作品(不包括历史演义与传奇)。由于本文试图选取启蒙视角完成对历史小说创作主题的一种解读,故并未涉及对象的全部。)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历史小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特质,作家们往往在叙写历史的同时,又落笔于眼前的现实,自觉追求历史叙述与现实文化语境的紧密关联,从而使历史小说创作不仅在时间意义上与新文学相伴生,而且在精神价值上同样印证着整体文学观念的演进。“描写过去,而不添加我们自己感觉的色彩,那是办不到的。是的,因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家到底是在向现代发言,他便无意间会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写作”(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正是这样一种重叙历史的愿望使一部分历史小说作家获取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力量。同时,“五四”以来形成的以民主与科学的眼光重新思考、发现历史的文化启蒙与思想革命这一时代精神,一并激起了许多作家识破历史透见人生真面的自觉追求,通过理性的审视获得历史真知被视为民族新生的必要前提。
“启蒙”在18世纪的欧洲就是反对中世纪封建愚昧的思想武器,思想家们致力于用理性之光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的蒙蔽,寻求思想自由与个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弘扬思想革命的启蒙精神,同样要求人们冲破蒙昧主义的束缚,并将矛头明确地对准了长期禁锢和麻痹着国人灵魂的封建主义传统。“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注:郑振铎《玄武门之变·序》,开明书店,1946年版。)。对历史小说的这一要求体现着现代作家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参与文化重建的时代愿望,这种愿望首先便落实在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一个个“识破”题旨中。
如果说厚重与复杂是历史本身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那么当这种复杂厚重的历史变得越来越难以看清时,时空的流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历史迷障的形成更多地来自人为的造设,“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见《鲁迅全集》第 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封建秩序中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尤其使历史充满了欺瞒和虚诈,于是,它成为作家们所要着力戳破与瓦解的一个历史幻象。
“天命”从来都是支撑着封建秩序的主要思想根基,这种观念首先替帝王圣人们打出了一面秉承上天意志的历史幌子,正是这种虚妄的“公理”成为“治人者”冠冕堂皇地对“治于人者”进行欺瞒的前提,如果“天命”观仅仅是为统治者们增添一种虚伪的荣耀与装饰,那么它还只能算一个无稽的历史妄谈。然而,这种观念凭借封建秩序中正统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渐渐渗入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之中,甚至,变成一种似乎源于他们自身的观念时,其历史反动的本质就分明地显露出来了。“天命”观的不断得以强化使已经处于蒙蔽之中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失去反抗的自觉与可能。即便他们已经朦胧地觉察到了既有秩序的不合理,他们的反抗也难以有一个准确而致命的指向。郑振铎的《汤祷》着意对有关商汤祷天求雨的传说进行重新解释,从而叙写出一个富有历史深意的新故事。久旱无雨的灾祸在给农民们带来饥饿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一次寻求自我解救与新生的契机,他们甚至已经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汤。“该是那位汤有什么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下了那么大的罪罚。这该是由那位汤负全责的!”于是,人们缚起商汤,堆好干柴……这位心虚而胆怯的帝王也几乎真的成为农民们祈求拯救的牺牲,然而,一次为民祈雨之举终于还是变成了为汤祈命:紧要关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恰到好处地及时淋熄了已经燃起的干柴,也浇灭了人们心头难得的反抗之火。“那位汤又在万目睽睽之下,被村长们、祭师们护掖下柴堆,他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暗暗的叫着惭愧。人们此刻是那么热烈的拥护着他!”在这里,万民相信的最高权威是天帝,所以他们只能永远俯首听从天命,天雨之所以能够替代汤的鲜血,是因为汤虽是一个被动者,但仍如往昔一样被置于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被看作一个足以救民水火的人物。何时汤能够被人们看清乃至看轻,包括“汤祷”的虚妄,何时万民方能真正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人。那曾经使汤帝感到莫大惊恐的反抗者们眼露的“诡异的凶光”在小说中几番出现,只是在历史上这“凶光”太少闪亮了,受人宰治的民众们更多的是温顺与盲目的惊奇和感激。作者完成无情的揭露之后没有忘记留下一个透见历史光明的希望:“只有那柴堆还傲然的植立在大雨当中,为这幕活剧的唯一存在的证人。”
正是因为历史小说作家们对“天命”思想的识破没有仅仅停留在撕开统治者身上那层历史外衣而将笔触探入被统治者锈蚀的内心,所以才让我们见出作家们开启民智的良苦用意。即使历史已经向前迈进了几千年,鲁镇的祥林嫂依然要承受来自同处下层的柳妈有意无意地编制出来的地狱神话的恐吓。对于封建秩序中的民众来说,为保障帝王崇拜而从历史妄谈中异化出来的天地迷信,本来是一种被动的外来的附加观念,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民众之间一种自觉不自觉的通用信条,并且主动地相互制造相互传播相互强化相互欺瞒,从而使心灵脱去蒙蔽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愈益艰难而漫长。历史小说作家们呼应着鲁迅式的文化启蒙愿望,继续作揭示病痛寻求疗救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俊民的《心与力》、曹聚仁的《焚草之变》、宋云彬的《隋炀帝之死》……以及茅盾著名的《石碣》,其主要价值也正体现于这种自觉的努力之中。尽管出现在李俊民笔端的舜一再被剥去“圣人”的外衣而显出虚伪与狡猾,但《心与力》中的下民们依旧用欺人亦自欺的妄言成就着“舜天子”的大名:“我亲眼看见井边冒上了一个神龙的头,慢慢地,龙身上的龙麟,龙爪,都看见了。过了好久,他才变还了舜天子的样儿;我看,他才是真命天子哩。”即使是在揭竿而起的梁山泊这个反抗群体中,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念依旧作祟,使英雄好汉们终究难脱“替天行道”的渺茫与尴尬:“我刻东岳庙的神碑,也刻这替天行道的鸟碣,就是这么一回事。提起什么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石碣》由于发现并触及了历史上农民起义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症结,使这篇取材于旧作的历史小说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内蕴,并从一个层面上显示出现代作家历史小说与古典历史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异。
对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识破不仅需要准确地抓取其核心内容(如“天命”观)从而直接撼动它的中心支柱,也要求历史小说作家们能够多方面地戳破那些思想观念赖以维护与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封建秩序中的教育与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足以杀人的软刀和利刃。《晓风杨柳》、《鬼谷子》、《鼠的审判》这些小说分别选取父亲、师长、官吏等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明显承担着价值规范与言行惩戒责任的社会角色来叙写各自的历史人事,当然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随意拾取。指斥封建统治者的律法徒有一个“明镜高悬”之类的自我标榜也许并不难,但真正完成一种有力度的历史识见,还必须在识破者自己的观念中确立一个与虚伪的对象根本对立的价值标准。在李俊民的《鼠的审判》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富有历史新质的观念及其在封建律法面前所显示出的冲击力量。《史记·酷吏列传》中西汉的张汤可谓一个为统治者执法卫道的极端典型,作者以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小说中所要展开抨击并加以摧毁的封建法律秩序的代言人乃至化身就更容易凸现其残暴与欺世的本质,也更能反衬出作者所依凭的“生命的律法”合乎自然人性的崭新内涵。这种新的律法不仅要保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而且更肯定“生命的发展是无比的向上的力”,以这样的法则作为标尺,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张汤们的罪责就不再止于以法律为名造设历史的骗局,其更大的罪恶在于对生命的根本蔑视。正是他们在反人性的封建秩序中为人类制造了一个漫长的恶梦:“你把自己生命的权限提得太高了,你生命的纵放早飞越了你应得的发展,你的生活驾在成千成万的尸骨以上。”这种任意翻弄所谓“法律”的权柄草菅万民的暴虐,显示出强权秩序下人道的沦丧。对人性的根本背离所能得到的最终结果便是历史的施暴者自身也无法逃脱真正铁定难移的生命律法的惩处。“你想以大肚皮的烈焰来收葬成千成万的飞蛾!结果呢,这烈焰也埋葬你自己了!”尽管作者采用了一种近乎直抒的叙述笔调使小说带有一种声讨的痕迹,但由于作者贯注进作品一种富有时代感与历史真理性双重特质的主体情志—对生命的热烈肯定,所以这种声讨之声虽显生硬却毕竟有力。《鼠的审判》可视为历史小说中这类题材的代表作,特别是颇具点睛意味的结尾,不仅克服了全篇叙述中时有的生硬感,而且依旧保持着入木三分的思想力度,从而使作者最终完成了对“张汤”这个有名的酷吏形象极具历史概括性与启示意义的叙写:刚从自己沦为“鼠辈”阶下囚的恶梦中醒来,张汤马上又跌入更为恐惧的现实中,皇帝赐死的旨意已下,“请君入瓮”的命运既定,他却还未摆脱早已化入性情血肉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带来的惯性欲望——“他留下的纸条是说明他的死是由于三长史之流的构害,他是明料到武帝会因后悔而杀死三长史的”。
在封建统治阶级对人们软硬兼施地推行自身一套观念与意识时,残暴的律法毕竟还是一种较为显见的工具,而满口尽是仁义道德的谎言,头上带有万世师表荣冠的“授业解惑”者们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扭曲蒙蔽着人们本应健康的心智。在正统严密的封建教育规约下,施教者本身也往往既害人亦害己。即使退隐山野的陶渊明虽然表面上从大一统的集权秩序中脱身出来,实际上也仍未逃离无形的士大夫观念樊篱为封建社会中“父亲”这个角色设下的迷障(唐弢《晓风杨柳》)。晋宋更迭之际的陶渊明,虽然倍感现实的痛苦与激愤,却无力作出任何实际的抵抗。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们,因为一直接受着自己淡泊超世,清静无为的思想灌输而显得一个个“柔弱得像羔羊,一点也没有反抗”时,他终于开始了自我反省。“渊明感到一阵内疚。”“我还得写下去,我得留一点教训,我要写到天明。”这种教训的取得在聂绀弩笔下的《鬼谷子》中,却已付出了流血的惨重代价。在这里,“最可宝贵的”生命再次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法则,凭着它作者逼视着“老学究”鬼谷子一步步认清了自己那些“正是王公大人们所喜悦的”学问怎样欺骗着世人“为了主人的事,要献出生命,要成仁,要取义……”。于是,像要离这样的学生,“二十多岁的血性男子”,永远失去了青春与生命,甚至甘愿让娇美的妻子可爱的幼子作无谓的牺牲,换回的结果却是“谁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死而变得好些”。这种历史悲剧经由作者对梦幻世界一群地狱冤鬼的描述而显得更加怵目惊心。死后的要离对鬼谷子的质问,“先生,如果你还有人心,请想想看,我们的生命岂不就为这样一些无聊的事而存在么?又岂不为这样一些无聊的事而失掉?”连同成千上万的无头尸身发出的“偿命!偿命!”的呐喊,久久回荡在小说内外,它与《鼠的审判》等一系列作品一起,无情撕扯着涂满伪饰的历史表皮。
识破带来真知,同时也唤醒人们对理想人生的憧憬,“我们的社会里,难道还少‘像猪一样的互相吞噬,而又怯弱昏迷,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的人么?……这还算什么人生!我们无可奈何乃希望文学来唤醒这些人;我们迷信文学有伟大的力量,故敢作此奢望。我以为在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最大的急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注:茅盾《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45 期, 1922年8月1日。)。新文学开拓者们这种对人的觉醒的内心渴望赋予现代作家一种建设“人的文学”的自觉追求。当作家们于历史的审美追寻中一再贯注着主体的理性反思时,他们所依凭的也正是“生命与人”这样一个观照法则。即使是被巨大的成功映衬得无比辉煌雄壮的历史事件,对于作家们来说,最为敏感的仍是遮蔽在冠冕堂皇的历史帷幕背后那些悖于人性的种种历史丑恶。同是面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茅盾的《大泽乡》抓取的只是一个反抗压迫的形象,但由于叙写粗率,小说显得非常单薄,作者自己也明确表示“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我一直不喜欢它”(注:《茅盾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380页。)。这段历史在宋云彬的《夥涉为王》中, 叙述上也有直白生硬之嫌,但明显地要比《大泽乡》更为厚实,原因正在于作者没有简单化、平面化地重叙历史人物,引起宋云彬最大关注的是胜利之后的陈涉的另一面:从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蜕变为贪图一己权贵、对民众失去同情心的新的压迫者。对陈涉这一个体形象的历史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农民反抗群体的否定,相反,由于本篇中的陈涉并不一直代表农民大众,作者便有可能在深入剖析这一形象的同时,期待着作为被压迫者历史象征形象的“农奴们”达到一种最终的觉悟。农奴们从陈涉的传奇经历(由农奴而一变为王)中明白他们也并非永远是奴隶,这只是一种盲目的初步觉悟;而从陈涉成为新贵之后对昔日同伴的冷漠乃至残杀的态度中,悟出“陈涉已经不是我们的同伴,而是我们的仇敌了!……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一切应享的自由和权利”。此时方是真正的觉悟,即不作奴隶之后也并非要去作新的压迫者,而是争得做人的权利和自由。这里,作者在历史中的农民身上寄托了“五四”以来“人的觉醒”的知识分子心态,特别是一种富有主体精神的自觉反抗意识更可视为对“五四”以后新文学中一个极有价值的文学题旨的成功表现——真正的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真正自主的全面发展而非施舍的或被动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的积极肯定与热烈颂扬是“五四”以来“人的发现”的一个习见视角,在此观照下不但众多的新文学作家对现实人生作出了价值全新的判断与选择,也使历史小说获得了又一个重估历史再现新知的启蒙思路。总体上的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所带来的“疑古”的时代心理落实到历史文学创作中便是相当数量的“翻案文章”相继涌现,其中的不少篇什较为集中地致力于端正长久积成的看待女性的历史谬见,重新叙写出一个个富于新质的女性形象,历史剧创作中的《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潘金莲》(欧阳予倩)、《杨贵妃之死》(王独清)等弘扬女性解放精神的意旨早已为人共识,而历史小说中并不罕见的相类之作虽不乏善陈却显然需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关注。冯乃超的《傀儡美人》,端木蕻良的《步飞烟》,沈祖棻的《马嵬驿》分别选取了各自的视角,多方面地显示着还女性以历史真面、女性应得之权的自觉追求。历来被视为妖女的褒姒一直承负着覆亡西周的历史罪责,而在冯乃超重构的那段历史中,她却成为一个来自草地与牧场,向往森林溪水以及一切“自然的人声”的美丽而单纯的少女,《傀儡美人》显然是从对自然本真的肯定完成了对女性的一种重新识见。《步飞烟》的所本是唐人的传奇旧作,其殉情故事也属文学史中熟知的题材,端木蕻良重新叙述的意义在于走出了笼罩在旧作中的封建伦理观念造设的道德迷雾,以一个几乎走向极致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形象呼应着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启蒙主义理想吁求。也许最富审美价值的女性形象当属女作家沈祖棻倾注心力叙写出来的“那一个”杨贵妃了。在《马嵬驿》中的杨玉环身上,女性作家赋予了一种同类题材中并不显见的女性意识,沈祖棻准确地抓取了“女色亡国”这一传统定见的一个文化意蕴——在男性意识占据中心地位的社会中,对女性的爱的超离竟成为通达人生顶点的一个必需品格,这种对女性的漠视在封建秩序中显得更为突出。玉环临死之际道出了作者从这个古老传说中悟出的历史新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是从古以来千万个女人的悲哀。别了,你好好地努力你的事业吧……在历史上,你还是一个有功德的贤君啊!你放心吧!”正是由于作者在玉环身上寄托了自己对女性境遇的某种普遍体认,所以她在全篇叙述中一再对玉环加以“诗意般”的赞美。称之为“诗意般”的赞美,主要并不在于那些叙述语词如诗一样华丽,而是因为这些颂词的诗性成分远远大于其历史真实性,作家面对历史时主观情志的介入在这里十分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一种补偿心理。身处现代中国的沈祖棻们依然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出这种充满激情甚至失于偏执的女性礼赞,可见现实世界中相应的女性价值“缺口”仍然需要一种诗意的填补。
启蒙精神作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始终随文学乃至文化选择的历史衍化而消长起伏,即使是在40年代,我们仍能看到类似《步飞烟》那种“五四”气息浓郁的作品,可见,正像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李季等作家的优秀之作在新的美学理想基础上有机地融会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文学题旨一样,历史小说凭着其题材优势也作出了保持新文化运动历史追求的相同贡献。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张汤论文; 沈祖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