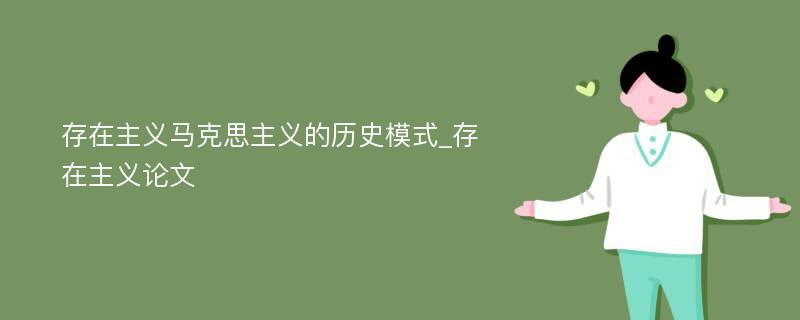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在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六十年代,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这一时期,萨特写作了《辩证理性批判》、《共产党人与和平》等大量著作,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不过,萨特并未能够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虽然,这时他在探讨“人”的主题时,也把历史作为他哲学思考的对象。但他对历史的思考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存在主义的。他正是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构建历史的模式。
一、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
萨特在扮演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开始用马克思的表述方式谈论历史与人的问题。他说人创造历史,但是,人创造历史这一点不能局限在个人身上,作为个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还不是历史的动力。因为,人创造历史首先是在诸如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等先前实际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先前的条件,但如果没有这些先前的条件,人也就无从创造了。正是先前的条件,为人变革历史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方向和物质的现实性,人创造历史,无非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超越先前的条件。
对于人创造历史的活动来说,先前的条件是一个现实的规定。而这个先前的条件也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物化。因此,先前的条件把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与“过去人”的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是先有了“过去人”的创造活动才产生了现在的创造活动。
当然,一个个人也可能会说,历史与我不相干,因为我没有创造它。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外在于他的,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他人必须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如果没有他人的劳动和实践,他的存在也就会成为不现实的了。可见,对于创造历史的活动来说,人与他人以及过去的人是一个综合统一的总体,也正是这个综合统一的总体才是真正的历史动力。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屡屡看到,一个集团实践活动的成果为另一个集团所摘取。比如农民运动的受益者往往是封建地主阶级,从而使农民运动失去了行动的真实意义。但是,在萨特看来,“这并不是说,作为人对历史的实际作用的那种行动不存在,而只是说,其达到的结果——即使符合人们自己提出的目标——当人们把它放到总体化的运动中去的时候,根本不同于它在地方范围所出现的那样。”(《方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页。)因为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封建地主阶级重新获得了胜利,但是农民运动已深深地把它的印记打在历史之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所以,“人就是这样创造历史的,这就是说,他在历史中把自己客观化,又在其中把自己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它是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特有的成绩——对人显得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客观的结果中认不出他们的行动的意义(尽管局部地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成功的)。”(同上书,第68页。)
萨特说,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每天经过我们的手自行创造着。之所以我们意识不到历史的结果是由我们所创造的,之所以我们的时代自己创造自己却不认识自己,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在其表现上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是由于没有把握到创造历史的人的总体。人与人在活动中的分歧、理论囿于个别集团的眼前利益等等统治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把人们创造历史的真谛掩盖在种种神话之下,成为一个朦胧和秘密。所以,正确认识人的活动对于创造历史的意义就需要总体的观念,即在历史的总体化中、在历史的未来中来看待人当前的活动,因为,只有在一个将来的总汇的基础上,从这个总汇的作用和对这个总汇的矛盾上,才能够发现自己和自为地设定自己。
在此,萨特把历史看作人的活动的总体,看作是人的活动及其条件的综合统一,并像卢卡奇那样,要求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历史,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泛泛叙述时才表现为这样,一旦萨特进一步对历史问题发表意见时,他的存在主义本质就暴露了出来。
二、历史是人为了人对现实的超越
萨特在对人创造历史和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作出一般规定之后,就提出了人为什么创造历史的问题,涉及到这个问题时,萨特似乎要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体的人的实践。
萨特认为,人不是为了历史而创造历史,人创造历史是因为历史具有为了人的意义。人的活动是为了人而对世界的改造。这种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在个体的人和人之间进行的,当“他人”为了自己生存的目的,在他身上实现了某种东西的同时,他也通过“他人”达到了同样的结果。这样一来,他与“他人”就共同实现了对先前条件和现有社会环境的超越,即创造了历史。萨特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对某种情况的超越,在于他能够做到对别人在他身上所实现的东西反过来有所作为,尽管他从来没有在他的客观化中认识到自己。”(同上书,第69页。)历史在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情况下展开,但却确定无疑地为了人。
人改造世界的活动首先是根源于人的需要。人的现实状况和现存的关系对于人来说是匮乏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唯有依赖于人的实践。实践具有双重的性质,“对现存的关系说来,实践是否定性;不过它永远是否定之否定;对所指望的对象说来,实践是肯定性;但是这种肯定性是通向‘不存在’,通向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同上书,第70页。)也就是说,实践是人克服现实状况的努力,是人站在目前决定着他的那些实在因素之上,对某种他希望产生的和即将到来的对象的争取。因此,人在实践活动中既逃避和拒绝现存一切因素的关系,又跃进到和实现着即将到来的关系。一句话,人的实践活动是扬弃,是不断地用未来否定现在和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活动。通过扬弃,既否定了又创造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并使其成为历史发展的环节。而历史的发展就意味着人的需要的更新,或者一些最基本的需要的不断满足。
萨特说:“个人之所以把自己客观化而且参加历史的创造,就是因为他超越现存的情况而趋向可能的领域并且实现所有的可能性之中的一个:于是,他的计划就具有一种现实性,虽然本人可能不知道它;同时,这种现实性,由于它所表现和它所产生的矛盾,影响着事变的进程。”接着,萨特进一步指出:“应当把可能性理解为双重的规定:一方面,它在个别行动的中心本身之中,是作为目前所无而正因其无而揭露实在性的‘未来’的示现。另一方面,它又是为集体性所支持和不断改变的实在的和经常的实际的未来。”(同上书,第71页。)
以择业为例,在现代社会里,对保健医生的公共需要不断地增加,但从业人数却大大地不足,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构成了一种实际的、具体的和可能的未来,即选择保健医生的职业。同样道理,在社会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时,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就大大超过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某些人就会放弃在未来成为哲学家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对于个人来说是直接受着他所能认识到的利益要求所决定的,社会对他的选择作出集体性的支持也是基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并通过给予他能意识到的利益来进行的。虽然历史总是向人们打开更广阔的永远开放的可能性,但个人只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行动,因为个人只看到自己的直接利益。当他作出选择和从事实践活动时,实际上是在创造历史,但却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创造历史。
虽然个人创造历史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个人行动中却体现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个人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集体,进而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行动反映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这种愿望和要求又包含着社会深层的历史趋势,因而个人的行动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根源,一旦个人的行动扬弃自身的特殊性而走向普遍化,就使历史运动成为一个现实的总体化过程。
在萨特看来,历史只是人们无意识的结果,人们在历史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历史的总体性正是个人私利的交汇,而在本质上依然是个人利益,所以,萨特的眼中只有个人和个人的活动,他永远看不到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的行动。
三、历史根源于个人的实践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看到,萨特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来理解历史的,认为历史无非是社会中的个人各自为了自己的目的的活动的客观结果,所以说,历史是根源于个人实践的,历史的总体化实际上是个体总体化的客观化。
然而,我们在历史的运动中经常看到的是集团的行动,在每一次历史事变中,都显示出了集团的力量。每一个历史事变都是在特定时期彼此对立着的集团的矛盾统一体,集团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这些集团的存在和改变,而集团自身性质、结构的改变和矛盾对立的平衡或非平衡状况,又决定了历史事变的方向与进程。因此,历史发展的量直接的承载物是集团,集团是反映在历史表象上的主体。
但是,萨特认为,集团决不是离开了个人的抽象。在他看来,对集团在历史事变中的作用的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历史事变的深层是个人在起作用,集团只不过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和桥梁,集团也是个人创造的。当然,在个人创造集团的同时,集团又把权力和效力给予个人,接受这各给予的人也就成了集团的创造物,成了集团的代表和象征。个人永远是不可还原的因素,一切集团都铭刻着个人的印记。当集团的结构能够包容个人的特殊性时,集团中处处都突出地显现着个人的特殊性;当集团的内部结构不允许个人的特殊性存在时,那么这个集团无非是把个人的特殊性普遍化,即集团在整体上表现为个人的个性。因为,集团在为自己创造出领袖时,往往是把集团个人化了。因此,集团也需要从个人那里获得理解。
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称作“历史人学”。萨特说,这种人学的“真正任务并不是描述一种从来不曾存在的抽象的人的实在性,而是不断地向人学提醒所研究的过程的存在的各个方面。人学只研究种种对象,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由于它,‘变成的对象’又归结于人。人学如果用对‘变成的对象’的各种过程的研究去代替对人的对象的研究,这才配得上它的名称。它的任务是把它的知识建立在合理的和有理解力的‘非知’上,这也就是说,如果人学用自我了解来代替自我不了解,那么历史的总体化才是可能的。自我理解,理解别人,存在,行动:这是一个唯一的和同一的运动,它把直接的和概念的知识建立在间接的和理解的知识之上,但是永远不脱离具体,也就是不脱离历史,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理解它所知的一切。(同上书,第128页。)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体的人的理论,所以,他要求把“‘变成的对象’又归结于人”,但是,他又提出“用对‘变成的对象’的各种过程的研究去代替对人的对象的研究”,提出“自我理解,理解别人,存在,行动:这是一个唯一的和同一的运动”,提出“把直接的和概念的知识建立在间接的和理解的知识之上”,这时,他是把人放置在历史之中,放置在具体的集团之中的。因为只有在集团之中,个体才需要在理解自我的同时也理解别人,并且在这种理解中形成集团的结构和实现集团的功能。也就是说,集团需要统一的理论和原则来规范集团中的一切个人。作为集团的理论和原则,它保留同时又超越(扬弃)个人理解方式的特殊性,因而,在这种理论和原则中,不再象在个体的人那里一样,问题以询问者的姿态出现,而是“询问者、问题和被讯问者只是同一个。”(《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版,第315页。)这样一来,似乎萨特突出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环境,即把人放置到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萨特的考察坐标并未发生变化,他的思维基点依然是个人。
萨特认真地探讨了诸如融合集团、誓愿集团、制度集团等社会集团形式,他发现,随着集团的演进和更替,越是集团具有较高的组织性,个人在其中进行活动时,就越是以异化的方式机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集团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总体化的实践,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病态”,使实践为“反实践”所代替,使实践的人性为无人性和实践过程的无思想性所代替。
因此,融合集团把人组织起来,使“群”变成集团,而在制度集团中,人们重新堕落为“群”,仅仅由物质的统一和同一的环境虚假地结合在一起,就如工人在同一企业中劳动,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采用同样的技术,他们甚至遭受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共同利益,他们的活动只是分别地进行的,每个人的活动都是与他人的活动分离的,他们单独地进行斗争,每个人为自己而斗争,结果是同样地遭受他们共同的命运。萨特说,在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在身体上与他人不同,并且因为有一种实践上的敌对关系或对他们的相互存在的实际上的无知,象许多墙壁一样把他们隔离开来。”(同上书,第341页。)直到有一天每个人都对共同的命运觉醒了才组成融合集团。
群的实践不同于集团实践,但却是在集团中进行的。对于历史来说,群的实践是最普遍的实践形式,不过,历史的总体化却是直接地在集团实践中展开的。因为,历史事变决定了历史运动的进程,而一切历史事变都是由集团实践来完成的。所以,在历史总体化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自由的泯灭和惰性实践的滥觞。可见,无论是群的实践还是集团实践,都不能充分体现实践的主动性,萨特研究这些社会实践的形式,恰恰是为了证明它们的反实践性,从而表明个人实践是真正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
四、历史与个人的辩证法
萨特认为,历史总体化根源于个体的实践,同时,历史总体化又为个体的实践提供了辽阔的领域,没有历史的总体化,个体的实践就会在某一具体总体上中断而无法继续展开。因为,个人本身的可能性是社会可能性的总体化和丰富化,个人的东西是作为社会的必然因素而产生的。“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的性质。但是人的真实性又是在他经常以他的实践扬弃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之下被规定的。”(《方法问题》第70页)
人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人能够超越他现在的所是,能够超越他现在所做的,能够克服自己的命运,个人的东西使社会丰富起来。一句话,客观处境制约着人,但人能够超越客观处境。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能力,历史总体化就成了个体总体化进程中常新的处境,历史总体化使人失去自由,又为人重新获得自由准备了条件。
个体的实践不断地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它在每一次这样做时,又继续指向可能性的领域。“可能性的领域,是能动的人超越其客观情况而奔赴的目的。同时,这个领域,也紧密地被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性所决定。”(同上书,第70-71页。)可能性领域不是任意的可能性,它是被整个历史所决定的、而且包含着它所固有的种种矛盾的现实的可能性。历史规定着人的实践,人的实践又创造着历史,这就是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由于思考历史的总体化问题,思考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萨特开始用一种新的自由观取代《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对自由观,努力去证明自由对客观状况的依赖性,指出自由不但在选择领域而且也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这时,萨特主张没有现成的自由,自由是应当在斗争中争取的和应当在劳动实践中获得它的真正性质。要获得自由,就不应当保持现状,而应当努力改变现状。萨特认为,实践是人的现实的人性,所以实践活动也就成了实现自由的手段。由于实践活动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和受社会制约的,每个人的实践既实现着个体的总体化又服务于社会,从而被纳入到历史的总体化之中。
在实践的基础上来理解自由,使萨特的自由观中引进了必然性的因素。因此,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大谈“作为自由的必然性”和“作为必然性的自由”。人的实践赖以发生和展开的“变化了的物质”领域、客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总体化进程都是社会世界的必然性。必然性以实践活动的物质手段和对象化的结果的形式,作为必然的因素进入一切人的活动之中。而人的活动恰恰是为了自由。
因此,萨特宣布,必然性的王国是人们的自由实践的无机形式,在人的实践中自由和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总体化正是这种必然性,它与个体总体化的全部联系也都存在于的实践中。如果说集团的社会实践推动了历史的总体化的话,那么这只是表现的历史表层上的现象,而在历史的深层中则是个人的实践,所以历史总体化作为一咱必然性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又必要的。
在萨特看来,自由是被克服了的必然性,也就是说,自由不在于人服从必然性,而在于控制必然性。显然,在集团的社会实践中不能达到控制必然性的目的。相反,集团的社会实践只能产生必然性,个人在集团的社会实践中的活动仅仅是惰性的、机械的执行,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因此,克服必然性、控制必然性的活动就只能是个人的实践,个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依赖必然正是为了克服必然和控制必然,使必然向自由转化。
可见,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中,概念体系的宫殿是建立在个人实践的基石上的,个人实践直接的就是个体的总体化;当个人实践经由集团社会实践的中介而走向历史时,造成了历史总体化;个人实践无论在个人的总体化和历史的总体化中,作为结果创造着必然性;而对必然性的克服和控制又必须在个人实践中实现。所以,萨特的历史模式实际上仅仅是个人实践的运动。当他研究历史时,个人是这种研究的出发点、评判标准和逻辑的终点。因而,这种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依然是存在主义的。所以说,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存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