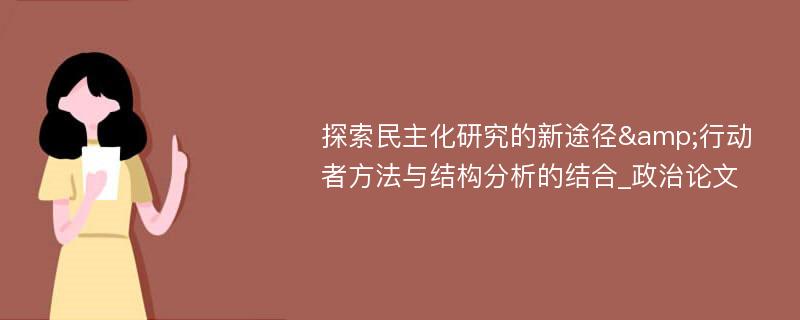
寻找民主化研究的新路径:行为者方法与结构分析的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结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8-0025-10
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格局,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的深入发展。但是,在一百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二十多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①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随着处于“灰色区域”的国家日益增多,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便将这些国家分别贴上了半民主、形式民主、假民主、弱民主、部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虚拟民主的标签。②这一做法标志着民主化研究已经从转型阶段向巩固阶段转变,人们开始对转型之后民主政权的维持和稳定、民主制度的巩固、民主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民主的前景展开广泛的、深入的讨论。
当民主巩固、民主质量的探讨逐渐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们发现,民主化研究中盛行一时的行为者方法或过程分析已经无法解释政治转型之后民主发展的现实。之前曾经被忽视的结构方法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宏观因素在民主巩固进程中成为关键变量,那些解释民主转型动因和过程的方法不再适用于解释民主巩固。由此看来,寻找新的方法来分析转型后的民主发展,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行为者方法
在20世纪50—70年代,研究民主的大多数文献使用的是结构方法。关于民主前提的假设包括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以及能够创造民主生存的外部因素等,其中频繁被提到的民主前提是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政治领导的角色、战略互动以及其他过程因素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强调不够。
20世纪70年代以后,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③。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民主化几乎波及了世界的所有角落——不管是较为发达的国家还是极其贫困的国家,不管是市场经济社会还是传统农业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均卷入了民主变革的运动中。而且,这次民主化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历史趋势面前,大多数新的主流民主化文献不再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而是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战略选择、战略互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如机会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在强调政治领导的独立作用时,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决定主义均遭到拒绝。例如,莱文指出,“有效领导、组织力量、共识形成、对制度化的注意等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结合起来决定性地创造和巩固民主”④。林兹等人指出,“我们认为,政治生存和解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个政治设计的问题”⑤。尽管林兹偶尔也强调过结构因素对民主命运的重要影响,但他总体上认为,政治领导对许多国家民主巩固的成功发挥了决定作用。对此,韩国学者申都哲总结道,“在概念上,一个国家中可行民主的建立不再被看作是高度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相反,它只是被看作是精英中间的战略互动和安排,在不同类型的宪法、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选择的结果。……民主不再被看作是在一个不同的土壤中进行移植的稀少的、脆弱的植物。民主被看作是一个被制造的物品,可以在具有任何民主工匠和改革者的地方产生。通常人们认为民主可以制造和推进,甚至在一个文化和结构条件完全不利的环境下生存和成长”⑥。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斯托已开始挑战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将行为者的能动性纳入民主化研究中,实现了从功能主义方法向过程分析的转变。为了在功能论与过程论之间进行区别,他放弃了一般研究中关于民主“前提”的思路(除了一个背景条件,即国家整合),将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前阶段、抉择阶段和习惯阶段,并分析了关键行为者在这些阶段的不同作用。⑦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罗斯托将行为者方法通过精英的观念取代了结构方法。此后,行为者分析逐渐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行为者分析的主要途径包括奥唐奈尔、普沃斯基等的“精英内部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以及卡尔和施密特等的“精英—大众互动模式”等。“精英内部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优先考察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政治转型视为具体环境中各种政治精英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的活动。政治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精英作出政治选择、实施特定的政治战略、策略的活动,其核心是不同政治精英之间互动和战略选择的过程。奥唐奈尔等人在总结关于政治转型的初步结论中指出,“政体转型的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其中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⑧一些研究者如普沃斯基运用博弈论来具体分析精英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探讨了政治精英所选择的策略以及彼此经过理性计算后采取的策略。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倪炎元概括了精英互动过程所包括的若干要素:一是策略互动强调个别行动者的选择,行动者具有自主的辨识和行动能力,不受经济、文化、制度等外在结构的制约,选择本身固然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最终结果还是基于行动者的自主决策;二是为了达成某些选定的目标,任何行动者都拥有若干对行为后果估算的策略,政治转型就是不同政治行为者策略抉择的互动结果;三是由于任何抉择和策略都无法预知后果,因而策略互动论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尽管不确定的程度不同,但通常指行为者在无法知道其他行为者策略情况下的抉择。⑨
尽管精英互动分析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垂青,但仍有学者指出,仅仅关注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是不够的,民主转型涉及各种各样的行为者,还应当包括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社会运动以及国际行为者。转型研究尤其要注意从精英与社会或大众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卡尔和施密特从政治行为者(精英与大众)的战略变化来划分政治转型的属性空间。他们认为,政治行为者的战略选择促成转型,而战略的具体内容形成政权变革的具体形式,“行为者及其选择的战略界定了转型从而发生的基本属性空间”。按照精英与大众战略互动的关系,他们划分出四种转型的类型:一是协定型,即转型是由各派精英经过协商而达成多边协定。二是强加型,即精英分子使用武力推翻掌权者而单方面有效地促成了政权转变。三是改革型,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把政治妥协的结果强加于现政权而无须诉诸暴力。四是革命型,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在这四种类型之间,还存在着更多的混合类型。现实中发生的政治转型,大多数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⑩吉尔也认为,转型研究过多关注精英的地位,忽略了大众在构造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在东欧、南欧等地区的国家中,精英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博弈对于理解转型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1)
按照转型学者的观点,任何一个转型过程都是独特的,民主转型的典型特点就是不确定性。(12)“在转型形势下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料的事件、不充分的信息、匆忙和危险的选择、在动机和利益之间的混淆、政治认同中的灵活性甚至是不确定性,以及特定个人的能力,在决定政治结果中往往具有决定作用。”(13)不可能事先知道有哪些行为者,而且行为者的态度和偏好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化。因此,转型学者认为民主化的一般规则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寻找一些概念工具。当然,也有学者尝试总结一些普遍规律,主要集中于转型方式的研究。例如,普沃斯基、亨廷顿等通过对民主转型过程中主要行为者的分析,提出了转型博弈的一般过程:在转型过程中,主要政治行为者包括前威权政权内部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它们之间相对的力量、地位和战略互动构成了不同的转型方式。威权政权中的改革派试图通过自由化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但却不被强硬派所接受。在民主反对派中,温和派愿意与威权政权的精英进行谈判,但激进派却拒绝合作。这样,当强硬派与改革派结盟、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时,就会形成两个对立的联盟,双方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威权政权或是保存下来,或是遭到解体。如果改革派与温和派结盟,并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当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而改革派又同温和派结盟时,将出现无保证的民主。当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温和派又与改革派结盟时,将出现威权政权的自由化。(14)
由于坚持认为转型过程决定了转型的结果,行为者方法重点分析了转型的方式。除了卡尔和施密特划分的协定、强加、革命、改革四种类型外,夏尔根据领导权和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渐进、决裂、斗争、和解等四种民主转型路径。(15)亨廷顿则从谁领导民主化进程划分出变革、置换、移转等方式。(16)另外,卡尔和施密特还认为,相对于通过改革或革命的转型,精英领导的转型(不管是通过协议还是强加)更有可能产生民主,尽管结果或许比较有限。(17)在大量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普沃斯基认为,政治转型的展开通常伴随一连串的协商、妥协的过程。当各方能够找出一种制度安排——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在民主竞争中受到过多损害——的时候,民主化才有可能。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的结果。(18)在核心行为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成为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通常认为,协议赋予了转型更多的确定性,因为没有人赢得或失去所有东西。最普遍的协议是在威权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和民主反对阵营中的温和派之间达成。例如,一些拉美国家的军队放弃权力是为了交换免于被追究在威权时期侵害人权的责任,从而在协议中确立军队的某些特权或保留领域。然而,从民主稳定的角度来看,协议存在着不少缺陷,因为它限制了代表和责任的范围。而且具有悖论的是,协议往往是通过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协议是由少数的行为者制定的,它们减少了竞争性和责任,这些少数行为者制定了政策议程,它们扭曲了公民原则”。(19)
作为对结构主义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者分析更强调民主化的现实过程。民主化的原因被认为是内在于转型过程本身之中,而非取决于特定的结构条件。行为者方法对民主化研究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不仅因为它注意到了能动作用,也意味着与功能主义方法的脱离,不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将西方的发展历程看作是民主发展的唯一道路。但是,行为者方法在抛弃结构分析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忽视了结构因素,行为者的作用往往被夸大。(20)实际上,当人们分析转型过程中某个短暂的时间段时,可以发现所有的事物都不确定:少数精英的选择和决策的确让人感到振奋,但是,一旦民主转型结束,民主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民主巩固和发展时期,行为者方法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民主制度虽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迅速建立,但转型后的民主稳定、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并非少数精英所能够营造和维持。托马斯·卡罗瑟斯指出,20世纪80—90年代的民主推动者信奉这样的观点:民主政治推动者的“无先决条件”的狂热激情已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民主转型模式,其表现特征是决定性的突破——一个国家的旧政权土崩瓦解,随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选,继之以历时很久的国家改革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强化。(21)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完全符合这一模式。在东欧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逻辑上的战略选择模式成为与事实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些国家政治转型的动力更多地要从国际背景、经济条件中去寻找,尤其从原苏联经济的衰退与西方国家的长期演变中去解释。转型学者忽略了行为者行动的自主性和能力必然受到周围结构的限制,走向了极端即行为者决定论,其结果是不受限制的选择和唯意志论。这意味着,行为者方法所强调的行为者能动作用在民主巩固时期无法解释民主的稳定和巩固,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范式。
二、民主巩固的研究范式:从行为者方法转向结构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化几乎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不需要考虑任何结构条件,甚至在那些被认为最不可能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如布隆迪,民主也幸运地降临了。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环顾世界时发现,很少有新民主化国家被认为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民主巩固的则更少。在解释为什么新生的民主选举政府中只有少数朝民主和巩固的方向发展,而多数则沦为脆弱的半民主政府甚至解体的过程中,人们重新发现结构因素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阶段。无疑,政治领导和过程因素在民主巩固中是重要的,但无论政治领导人作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他们都不可能创造奇迹。政治领导人至少在有利的结构条件下活动,才能够成功实现民主化。
在解释是哪些结构因素导致了民主化的成功时,学者们众说纷纭。研究揭示,不同国家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在推动或阻碍民主化的结构因素中,被认为与民主化、民主巩固联系最广泛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阶级结构、先前是否存在民主制度的历史经历、民主化之前新世袭制或威权政权的历史、是否具有建立在农业经济或劳动力密集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外部政治环境、是否具有累积性和极端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是否存在高度的部族分裂和社会分裂,等等。
在结构分析中,最早分析民主化的理论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学派。利普塞特曾经提出关于民主前提的著名观点,如“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22)。根据此观点,宏观结构条件如平均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水平在民主国家程度更高;有效的政治体系,尤其是长期的有效性,可能产生合法的政治体系。但这一观点和其他的现代化理论遭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反驳。一个普遍的反对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N型的:穷国与民主之间显示统计上的相关,但在中等收入国家中这一关联性不存在,在高收入国家中又出现这一关联性。(23)
通常情况下,新民主国家面临着经济困难和一大堆的经济政策选择问题,其核心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新民主国家或许享有短暂的经济蜜月期,即以政治上的收益换取短期经济上的失败,东欧国家最为典型。海哥德和考夫曼认为,经济危机中转型的国家与非危机转型的国家相比,第一届民主政府往往经历更为严重的经济赤字或衰退。此时,民主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表现决定了民主政权的未来。(24)普沃斯基也认为,新民主政权的维持依赖其经济表现。大多数民主转型的国家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那些对公众要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将因民众抗议而不得不修改经济改革计划,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长期来看,这使得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众抵抗伴随着经济改革而采取的强制措施的运动,将导致政府可能回到威权主义。(25)新民主国家经济表现得糟糕进一步引发分配问题。海哥德和考夫曼指出,当威权政权的限制被排除后,过去的分配冲突重新出现,导致过去被压制群体的要求爆发,这些要求同时也伴随着过去优势团体为了确保自己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大量的利益要求是新民主政权最后要面对的问题。(26)从经济危机中转型而来的政府,既面临着改革的机会,也面临着政治困境。经济危机要求新民主精英采取有效的措施缓解经济情况。由于这一原因,行政机关必须具有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政策计划,从而破坏了民主的巩固。
一些学者由此认为,新民主国家更容易解体。因为新民主国家必然会遇到政府效能的问题,这一问题腐蚀政权的合法性并导致其不稳定和解体。由于政府效能须通过中长期的政府活动才能体现,新民主政权因没有过去的成就而处于不利地位,短期的政策失败将导致人们对政府效能的不满。因而,新民主政权早期的经济表现好坏对于获得合法性是关键的。
另一个强调结构因素的理论是关于社会结构、公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摩尔较早时期的研究认为,社会阶级结构的构成对民主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并指出资产阶级是民主发展的关键因素。(27)汝什麦尔等人沿袭了这一研究传统,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阶级联盟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阶级权力、国家权力和跨国的权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民主是极其重要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联盟在民主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8)然而,近年来由于阶级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明显发挥作用,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次阶级的社会力量即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90年代初苏东剧变,草根政治组织、反对派组织开始涌现于政治舞台并异常活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并在随后的民主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达蒙德指出,公民社会有助于“发展、深化民主巩固”,通过提供限制国家权力的基础、取代政党在推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提高民主公民的政治技能和效能、教育民主国家的大众、构造政党之外表达和传递利益的各种渠道、产生广泛的利益以减少政治冲突的多极化、录用和训练政治领导人、发展冲突协调和解决的技术、使公民尊重国家和参与国家活动等。(29)米歇尔·戈德哈特将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主要功能归结为两种模式:一是反威权主义模式,即将公民社会描述为反威权政权的政治反对派,反对镇压性统治的普遍的、侵入性的制度,通过使公民免于这些制度的压制而更新政治;二是新托克维尔模式,即强调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团体生活所体现的民主功能及其效应,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独立空间,通过在一个法治的背景下动员独立的政治行为者和保护公民权利,来推动公开、参与的价值以及国家的责任。(30)
对文化的强调历来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民主化研究中,人们重点研究政治价值和态度在政权转型和推动民主中的作用。文化传统或政治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所有政治活动得以展开的空间或环境。根据这一观点,民主要求在其公民中具备某些特定的价值,如阿尔蒙德等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民主与公民文化是最相适的。大多数民主化研究者也认为,如果民主要巩固的话,威权习惯和思维必须让位于民主文化。加斯梯尔抛弃对民主的社会经济解释,认为民主化主要依靠民主观念的扩散。在他看来,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在特定国家中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31)林兹等人认为,民主直到人们认为它是小镇上唯一的游戏时才得到巩固。换言之,民主巩固既涉及政治制度层面,也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构成民主文化的民主观念、价值、信仰成为民主巩固的基础,民主要成功的话,这一层面的变革必须发生。直到大多数人将民主政府看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形式,民主才得到巩固。但政治文化研究也遭到了不少的批评,政治文化分析的缺陷在于它无法回答人们的态度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革。在这一理论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民主价值到底是民主政治体系的原因还是结果的争论。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具有民主价值的国家即他们所谓的公民文化,比那些低水平公民文化的国家更有可能产生和维持民主。但穆勒等人指出,两者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另外一面,即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产物而非原因。(32)更有说服力的似乎是达蒙德和林兹认为在民主态度和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33)
结构分析的第四个重要维度是关于政治制度对民主稳定和巩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特定政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宪法和选举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对民主的支持方式。最初是关注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不同,后来则分析一些更为具体的制度如选举制度、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对民主巩固的影响等。二是政党制度变量,许多人认为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是支持民主的关键力量。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研究最初源自林兹的研究,研究途径是通过一个独立变量(政体类型)来分析另一个依附变量(民主巩固),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甚至以后。梅尔瓦宁等人总结了林兹关于总统制的五个缺陷:在总统制下总统与议会互相竞争合法性;总统的任期固定而显得僵化,相比于议会制对民主不利;总统制产生一种被称为零和游戏的结果,即赢者通吃;总统制相比议会制,在统治风格上更不利于民主;总统制下政治外部者更可能赢得总统的职位,导致民主不稳定。(34)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鲍尔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政体类型与民主生存之间的关系不大。(35)对总统制、议会制研究提出批评的代表是霍罗维茨。他先是批评林兹局限于拉美地区的研究,并认为除了政体类型的影响外,其他因素如选举制也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当议会制采用多元政党制时,也鼓励了赢者通吃的结果。(36)其后,研究者开始转向多变量的研究(政体类型、政党制度或领导权),并且提出一个不同的依附变量(更一般意义上的善治而非民主巩固)。梅尔瓦宁强调总统制与分裂多党制的结合对民主是有害的,在指出1967-1992年间总统制国家很少有效运行的现实后,认为总统制比议会制更不可能有利于民主稳定,并认为总统制与两党制之间存在关联性。(37)梅尔瓦宁等人进而认为,即使在总统制中,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具体实践,在拉美,总统的权力差异巨大,与此相联系的政党制与选举制的差异也较大,这些差异甚至与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差异同样重要。(38)利法特则更关注选举制度的选择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指出比例代表制尤其是共识民主在部族分裂的社会中比多数民主更适合,同时也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要好,议会制与比例代表制的结合是最好的制度选择。(39)
关于政党制度对民主化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政党分裂程度,政党体系的稳定性,一党主导制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卡冯内和安卡认为,碎片化的政党体制不利于民主巩固,强大而稳定的政党制度要避免多党制,因为多党联盟往往是不稳定的。一党统治可能会对民主制运行起到阻碍作用,但高度的政党分裂更可能影响到多元选举体系中政治制度的稳定。在多元选举制下,当政党分裂程度达到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一党多数政府时,就有可能对民主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威胁,而在比例代表制下则不太可能。当联合政府成为常规而一党执政成为例外时,政党制度是否高度分裂问题就不是很大。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并不会因为政党制的高度分裂而遭受质疑。(40)更多的学者则强调政党及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对于民主巩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非洲地区,政党组织软弱,制度化水平低,政党体制发展不均衡,政党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的联系明显不足,由此阻碍了民主运行的基础性功能即代表功能,导致新民主国家的不稳定。(41)
最后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是外部环境。毫无疑问,稳定的、民主的外部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周边正在经历政治转型或改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稳定,可能导致与邻国的冲突,威胁民主的巩固。相反,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地区经济的整合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提高了民主巩固的前景。史蒂夫指出,如果没有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南美国家还不可能处于民主巩固的进程中,该地区的民主巩固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互为加强。(42)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是国际力量促进、维护民主进程的行为。《国际人权宣言》、《世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促使许多国家按照宪政民主的标准活动,国际人权组织、欧洲人权大会等纷纷采取行动来推动、维护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但是,由于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国际力量干涉下的民主发展并不是都成功,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中,成效有限。国际组织以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也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而且,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有可能会破坏其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这也是外部环境对民主发展产生不确定性作用的一个因素。
近年来,在民主化研究尤其是民主巩固研究中,结构方法又成为了主要的分析路径。的确,民主转型主要是一个政治事件或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政治精英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转型后的民主巩固却不仅仅是一个变革事件,更主要地是民主在社会整体中稳定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需要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综合的协调发展,才能得到巩固和持续。从这一角度看,结构因素较之精英的战略选择必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结构方法在民主化研究中重获青睐并非偶然。
三、民主化研究:寻找一种新的路径
在民主化研究中,结构分析方法强调宏观外部条件,关心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注重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变革的结构和环境因素,认为政治体系的变革是由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或现代化的进程等决定的,因而,他们试图通过逻辑推断去寻找政治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结构方法往往简单地把西方发展了数百年的民主结果视为发展中国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如全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较高的识字率等,给人以“西方中心论”的印象。结构方法的另一个内在缺陷是它易于落入决定论的窠臼。它假定,如果发现一整套足以解释可观察到的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那么,一旦这些条件全部满足,则政治转型就不可避免。换言之,如果原则上充分列出那些条件就能解释政治转型的话,那么,恰当的研究方法就是对历史共变模式进行比较统计研究,而唯一可能的政治战略就是等待那些客观条件的成熟。(43)结构方法的第三个致命缺陷在于,没有哪个结构因素被证明对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证明,经济发展并不是决定民主发展的唯一变量),有关文献提出了太多的变量,却没有指出这些因素之间的优先性和相互关联性。例如,亨廷顿列出了二十多个结构因素,总结出六个与政治领导相结合的结构条件,作为民主巩固的最重要原因。(44)戴蒙德和林兹也提出了十一个主要因素解释民主的成功或失败。(45)但由于缺乏一个或若干个决定性的结构变量,导致结构方法在民主化研究领域仍然颇受质疑。
对行为者方法和结构分析的不满使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综合解释的方法,倾向于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市民社会的发育、政治精英的战略、政治文化、种族关系、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殖民地遗产、外部影响、国际关系等来解释民主的产生。例如,民主化综合解释方法的代表亨廷顿认为,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异,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量,并假定这一自变量在解释所有民主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46)他认为,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各不相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解体。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导致的。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因素则主要包括合法性、经济发展、天主教内部的变革及其行动、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示范效应。(47)巴克全面总结了影响新民主政权稳定的两大因素:一是环境条件,包括政治遗产、国家观念和社会整合、经济力量、国际环境、内部危机;二是政治选择的因素,包括政治阶级、官僚、司法机关、军队、媒体和协会领导者等行为者的互动和选择。在分析了两类影响民主稳定的因素后,巴克认为,在解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时均是这些因素的不充分结合。一方面,每一种因素均影响着政治体系不同部分的持续性,民主的持续不可能依赖于任何单一的结构或意志因素。特定的结构或制度对社会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形成了一种条件,同时也影响他们决策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政治行为者选择的可能性也不是无限的。(48)尽管综合解释更系统地考察了广泛的历史事实,对民主化的归纳也更加符合事实,但由于缺乏一个普遍性的框架,不符合理论建构的要求,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罗列,不能构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方法。
迄今为止,对民主化的解释仍然主要围绕结构方法或行为者方法展开,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结构或意志在决定当前结果中的重要程度。结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结构限制了行为者独立活动的自由,这些源于历史或本国社会的结构是持续的决定因素。相反,行为者方法强调行为者独立于结构的特点,精英者的战略选择在民主转型过程及转型后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意向性和即时行为比长期的结构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由于结构方法和行为者方法均无法满足民主化解释的需要,目前还没有出现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民主化研究的一般方法。
民主化研究之所以复杂,在于民主化被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如自由化、威权政权解体、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民主深化等(大多数学者集中于民主转型阶段和民主巩固阶段的研究)。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在前提、条件、动力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在民主转型时期,公民社会和政府反对派的强大和活跃有助于推动威权政权的解体和民主政权的建立,但在新民主政权的巩固时期,公民社会却往往是导致民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一般地,民主转型基本上以建立宪政体制、自由选举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等为标志,主要是政治体制更替的过程,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行为者根据形势判断后进行互动和战略选择的结果,因而主观能动性、偶然性相对于结构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阶段,政治行为者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而非变革成为政治生活的要求,民主制度如何深入人心、如何形成民主文化成为民主巩固的主要内容。民主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结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能否生存和持续下去。这样,结构条件在民主巩固时期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某些结构条件比其他条件更有利于民主化,民主领导者在具有结构优势的条件下活动,民主化成功的可能性就更高。在大多数民主转型国家中,民主主义者推动了富有前景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但是,他们所在国家不利的结构条件阻止了他们的成功。取得民主巩固的国家基本上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不需要与新世袭制的传统进行斗争。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化无疑是这些国家政治精英领导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这些国家非常有利的结构条件。当然,结构条件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长期来看,一些国家的结构条件得到改善后,民主化的机会也大大提高。一旦经济得到连续发展,社会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如公民社会得到发展、受教育人口扩大、具有更多的可分配资源等。此外,若新民主国家持续时间较长的话,威权主义的特征将逐渐消失。政治精英和大众将获得更多的政治竞争和参与的经历,将更能够理解可预测的、遵守规则的政治的好处,由此形成民主文化。
在民主化研究中,恰当的方法应该是结构因素和行为者因素的有机结合。如卡尔指出,“即使在政权转型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好像限制条件最宽松、各种各样的结果都有可能,不同的行为者作出的决策还是受到社会经济结构和当前政治制度的约束”(49)。当然,某些结构因素还只是有利于民主产生的条件,民主并不会因为这些条件的具备而主动降临。亨廷顿指出,“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不论政治领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也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出现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在第三波民主中,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50)。一些表面上看似有利于民主化的客观条件的出现如经济自由化,并不表明民主马上到来,这些客观条件只是提供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待于政治行为者的现实选择。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或限制或推动可供选择的民主方案,它们可能决定了可供决策者考虑的选择方案的范围,或甚至事先便产生影响,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某一特定方案,也即显示出一种“路径依赖”的特征。反过来,政治战略的选择与政治精英们的行为,必须在上述现实所提供的宏观背景中展开,正确的战略选择只能是在与过去、现在的客观情势相结合中才能进行,只能在客观条件所创造的各种可能性或机会中去选择。例如,海涅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结构化的偶然因素(structured contingency)。这一概念假设,所有的政权内部均存在着历史形成的权力结构,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它们反映了既定的规则和制度,限制了行为者的策略选择。结果,行为者只能选择某些特定的方案。因此,政治结果并不完全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重要的结构因素的影响,结构因素与个人或团体的决策发生互动。历史结构构成了政治行为者的活动背景,然而他们并不是完全由结构所决定。在解释政治结果时,行为者本身也是重要的。(51)
因此,在解释民主转型以及民主如何得到巩固时必须回答如下一些基本的问题:哪些结构因素可以解释大多数国家民主化的实现?什么样的结构因素结合是民主化研究所必要的?具体讲,某种结构因素的结合在哪些国家的民主化解释中是有效的,在哪些国家则是无效的?以及在解释民主化时需要找出哪些行为者因素与结构因素的结合?关键的任务就是找到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有力地解释民主化的动因、过程及其结果。
寻求民主化研究的一般方法的另一个难题是地区乃至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一度阻碍了民主化研究追求普遍结论的努力。目前,大多数民主化研究基于地区或国别,较少进行综合的比较,因为研究对象具有地区性的特点。一些学者从南欧、南美国家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中美洲、中东欧、非洲或其他地区,值得怀疑。大多数南欧、南美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民主的经历,政治转型是回到民主,而且,南欧、南美地区受到如欧盟、美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主推动因素的影响明显。与南欧、南美不同的是,中美洲、中东欧、非洲的前民主经历十分有限。这些地区缺乏大众基础的、能够对经济精英和军队的利益构成制约作用的政党和工会,大众组织或政府反对派长期以来成为政府镇压的目标。这些地区的转型模式也是独特的,转型与追求和平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家在民主选举的同时内战仍在进行。此外,在中东欧、非洲,民族冲突、部族分裂对民主政权的维持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因素必须在民主化研究中得以考虑。正如伯恩斯指出,地区因素对民主化的某些方面没有影响,对另一些方面却是关键。换句话说,民主化有很多明显的共性,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52)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民主化都是某些一般的原因加上这个国家其他特有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成为民主化研究所不得不考虑的内容。
民主化研究是近几年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现实和研究均表明,民主化的动因、方式、过程及其结果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着差异。任何单独从结构因素或行为者角度出发进行分析都是不充分的,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注意不同地区、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民主化才可能获得更充分的、更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pp.5—21.
②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49,No.3,2002,pp.430—451.
③[美]亨廷顿:《第三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④Daniel Levine,Paradigm Lost:From Dependency to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40,No.2,1988,p.378.
⑤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olitical Crafting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s,in Robert A.Pastor,ed.,Democracy in Americas:Stopping the Pendulum,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9,p.41.
⑥Doh Chull Shin,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47,No.1,1994,pp.138—161.
⑦Dankwart A.Rostow,Transition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Vol.2,No.3,1970,pp.350—360.
⑧Guillermo A.O'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3—5.
⑨倪炎元:《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第19—20页,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⑩(12)Terry Lynn C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3,No.2,1991,pp.269—284,p.270.
(11)Graeme Gill,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Elites,Civil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Macmillan Press LTD.,2000,p.59.
(13)Guillermo A.O'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5.
(14)[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第49页,包雅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138—193页。
(15)Donald Share,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19,No.4,1987,pp.525—548.
(16)[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154—195页。
(17)Terry Lynn C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3,No.2,1991,p.270.
(18)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s a Contingent Outcome of Conflicts,in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eds.,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64.
(19)(20)Graeme Gill,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Elites,Civil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Macmillan Press LTD.,2000,p.53,p.44.
(21)Thomas Carothers,How Democracies Emerge:The "Sequencing" Fall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18,No.1,2007,pp.12—27.
(22)[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27页,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3)Larry Diamond,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in Gary Marks and Larry Diamond,eds.,Reexamining Democracy.Essays in Honor of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berry Park:Sage Publication,1992,pp.107—109.
(24)(26)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3,1997,pp.263—283,pp.263—283.
(25)[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第154页。
(2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8)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p.270—276.
(29)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9—250.
(30)Michael Goodhart,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2005,Vol.12,No.1,pp.1—21.
(31)Raymond D.Gastil,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mocra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8,No.2,1985,pp.161—179.
(32)Edward N.Muller and Mitchell A.Seligson,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647.
(33)Larry Diamond and Juan Linz,Introduction:Politics,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in Larry Diamond,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eds.,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Latin America,Vol.4,Boulder:Lynne Rienner,1989,p.10.
(34)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Shugart,Juan Linz,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A Critical Appraisal,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4,1997,pp.449—471.
(35)Timothy J.Power and Mark J.Gasiorowski,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0,No.2,1997,p.123.
(36)Donald L.Horowitz,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No.4,1990,p.79.
(37)Scott Mainwaring,Presidentialism,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6,No.2,1993,pp.198—228.
(38)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Shugart,Juan Linz,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A Critical Appraisal,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4,1997,p.463.
(39)Arend Lijphart,The Virtue of Presidentialism:But Which Kind of Presidentialism?,in H.E.Chehabi and Alfred Stephan,eds.,Politics,Society and Democracy.Comparative Studi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p.363—373.
(40)Lauri Karvonen and Carsten Anckar,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ird World,Democratization,Vo.9,No.3,2002,pp.11—29.
(41)Scott Mainwaring,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Journal of Democracy,Vol.9,No.3,1998,pp.67—81; 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asand,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Africa,Democratization,Vol.9,No.3,2002,pp.30—52.
(42)Franklin Steves,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n,Democratization,Vol.8,No.3,2001,pp.75—100.
(43)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 for Democrac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48.
(44)这些条件包括民主经历、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转型时机、转型过程以及转型后面对的情境问题([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5—46、324—332页)。
(45)Larry Diamond and Juan Linz,Introduction:Politics,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in Larry Diamond,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eds.,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Latin America ,Vol.4,Boulder:Lynne Rienner,1989,pp.1—58.
(46)(47)[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6、48—54页。
(48)Bruce Baker,Can Democracy in Africa be Sustained,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8,No.3,2000,pp.9—34.
(49)Terry Lynn C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3,No.2,1991,pp.269—284.
(50)[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120—121页。
(51)Jeffrey Haynes,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Africa:The Problematic Case of Ghana,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Vol.41,No.1,2003,pp.48—76.
(52)Valerie Bunce,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2000,pp.703—734.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