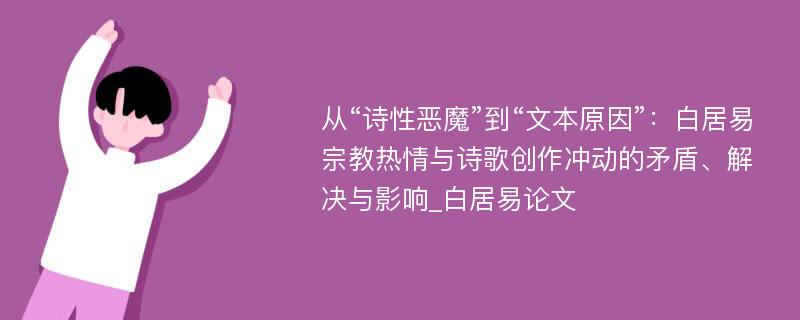
从“诗魔”到“文字因缘”——白居易宗教热忱与诗歌创作冲动的矛盾、化解方式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热忱论文,白居易论文,冲动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4-0058-04
中唐各诗派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不少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沉溺于诗歌创作。无论是李贺的呕心沥血、还是孟郊的苦吟都是这种沉溺状态的表现。其中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沉溺状态尤其明显,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一、“诗魔”
白居易对诗歌创作的沉溺,主要表现为他一生都痴迷于诗歌创作,还一再用“诗魔”、诗癖、诗痴、诗狂、诗仙等字眼来称呼自己。
如自称是“诗魔”的有:“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1](P2795)“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1](P1106)“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1](P2034)诗癖、诗狂、诗痴、诗仙等字眼屡见于他的诗章中的有:“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一销,此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况若遇神通。”[1](P407)“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1](P452)“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癫?”[1](P1144)“兴来吟咏徒成癖,饮后酣歌少放狂。”[1](P1958)“昔是诗狂客,今为病酒夫。”[1](P1321)
从16岁到75岁去世前几个月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沉溺于诗歌创作,视诗歌创作如同生命一般。
二、佛教热忱与“诗魔”的矛盾
白居易人生中另一大事是笃信宗教。他30岁以前开始接近佛教,之后“道情”不断加深,被贬江州时佛教热忱更是陡增,晚年皈依净土宗作为归宿。《景德传灯录》把他列为洪州禅门下如满的弟子,还说他“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2](P178)。而据笔者考察,他接触过的佛教流派有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用他本人的话是:“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1](P3782)其佛教信仰呈现出“不立门限,通学禅教各家”的明显特征[3]。白居易56岁时一诗最能体现其人生信条:“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岁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1](P1710)可见,他一生对佛教保持着热忱。
但众所周知,诗歌爱好与宗教热忱虽然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但这两种感情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其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一)佛教虽然流派众多,教义之间也有不同程度出入,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特别是在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上各流派之间有一致性。如几乎所有佛教宗派都把现实人生看成是一种因缘聚合,是幻象,是声色,总之是虚妄不实的,都提倡出世主义,因而也是反对人们执著于世俗生活享受的。反过来说,沉溺于任何世俗感情都有碍于体道,是“道心”不坚的表现。(二)一般佛教流派都认为,凡是能够用文字表示出来的东西都与终极的“道”有着距离,都只能算是小乘禅,因为“真如”是不可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例如禅宗就大力提倡“不立文字”,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白居易如此沉溺诗歌创作,既说明他对世俗生活的执著,也说明他的“道心”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
白居易本人也体会到了自己的宗教热忱与沉溺诗歌创作的冲突。他既看到诗歌创作妨碍了他“道”的精进,也看到了文字(诗歌创作)表达“真如”的局限。主观上,他曾尽力摒除各种世俗爱好,唯独对诗歌创作冲动无法克服。这导致他有时对佛教怀着一定的负疚感,还称自己诗歌创作冲动为“口业”:“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1](P1052)直到71岁,他还在慨叹,“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1](P2488)。“病来心静一无思,老去身闲百不为,忽忽眼尘犹爱睡,些些口业尚夸诗。荤腥每断斋居月,万虑消停百神泰,唯应寂寞杀三尸。”[1](P1793)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了宗教热忱而牺牲诗歌创作,不仅不愿意为佛教牺牲严肃的诗歌创作,就是连那些带有文字游戏的唱和之作,他也不愿意放弃(关于这类“游戏”之作,我们后面还有论述)。这样,他的佛教热忱与诗歌创作热情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紧张关系。
三、“文字因缘”
如何化解诗歌创作激情(诗魔)与宗教热忱之间的紧张关系,曾是白居易相当苦恼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他前期人生并不突出,因为他那时志在“兼济”,有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支撑,但随着政治失意与佛教热忱加深,二者的紧张关系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白居易一些文章和诗歌看,他为了从理论上解决二者的矛盾,确实作了一番努力。
那么,他是如何解释和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首先,他根据佛教的因果、转世等宿命论观点,肯定自己前生前世与诗歌有缘,这就是他说的“文字因缘”。如,在《与元九书》中,他曾说: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1](P2792)
后来,他还有类似言论:“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1](P2395)“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依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1](P1579)
用因缘宿命观点来解释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沉溺,承认前世有“文字因缘”,承认欠了“诗债”,此生在世间的主要任务是来偿还“诗债”的,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创作冲动根本原因(也即“诗魔”)的最基本的解释。下面这首诗歌就体现了这种解释:“房傅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1](P2359)
其次,他试图从佛教理论自身说明“诗魔”与佛教热忱之间并不相悖,而是相因。元和五年,他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诗中就曾对他和元稹早年的狎邪生活有过极尽声色的描写,不过诗的结尾却声明,这些描写并不在于艳情,而是想通过对青年时期经历的回忆来达到忏悔目的:“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其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偈化城,《维摩经》入淫舍,过酒肆之义也。”[1](P864)晚年,他在《苏州禅院白氏文集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其间根源无常,枝派六义,恢王教而宏佛道者,多则多矣。然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乐天,佛弟子也。备闻圣教,悟知前非。……愿以今生世俗之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1](P3789)在《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中,他也说,“我本有愿,愿以今生世俗之文字,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1](P3806)。按照这种观点,诗歌(文学)是“狂言绮语”,本不足道,但通过不断地写这些绮语来反思人生的虚幻不实,这样的诗歌创作却是有意义的。
再次,白居易吸收了某些佛教流派中肯定世俗生活的观点。中唐不少佛教流派反对执著于一端,反对把有与无、出世与入世等对立起来看。这些观点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世俗生活。如禅宗向来是以世俗化佛教流派著称,提倡“佛法在日用处,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语言所问处,所作所为处”[4]。认为过分强调修行反有碍于“道”的精进,只有在世俗生活中才能证悟自己。除禅宗外,佛教其他流派也有这类思辨性的观点。白居易正是汲取这种理论,为自己沉溺于诗歌创作找到了理由。他的诗句“离尽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就是对这种观点的证悟[1](P2115)。
据以上几点,可大致描绘出白居易的推理过程:既然上辈子欠了诗债,那么,诗歌创作就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为了偿还“宿债”,写诗的过程也因而成了忏悔的过程。以此推理下去,为表明宗教虔诚,他不仅不应回避创作诗歌,还要大量创作,目的是尽早还清“诗债”。也正是据此理论,他才“老偿文债负,宿结字因缘”[1](P1059),才“老病相仍,仍不废诗”,以至于75岁高龄还在“走笔还诗债”[1](P2578)。下面这首写于开成四年的诗可谓是对这个观点的总结:“每因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六贼定知无气色,三尸应恨少恩情。酒魔降伏终须尽,诗债填还亦欲平。从此始堪为弟子,竺乾师是古先生。”[1](P2402)
四、对后期诗学观念的影响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文字因缘”和“诗债”理论似乎是对诗歌创作价值的否定,实际却以退为进,变相地提高了诗歌创作的地位,把诗歌从传统的“言志”和“缘情”理论中解放出来。具体看,“文字因缘”与“诗债”理论,对白居易后期诗学思想至少产生了两点影响:一是它确立了白居易创作后期的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二是促成了他对“游戏”之作的肯定。关于此两点,我们分而述之。
(一)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
白居易前期关于讽喻诗的理论非常著名,为一般研究者所熟知。但在他这种理论下,诗歌的价值是依附于政治,诗人写作也只应受政治需要支配,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2792)除此之外的诗歌都应受到排斥。白居易过分强调文学有益于政治的理论曾颇为人诟病,因为他的理论既忽视了诗歌自身的审美特质,也忽略了诗人的主体地位。而他关于“诗债”和“文字因缘”的论述,实际上是肯定了诗人的个性与价值,也为那些与政治无关的诗歌找到了存在依据,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依据称为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肯定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也肯定了诗歌创作本身的意义。在这种理论下,诗就是诗,是独立存在的;诗人也不是政治的传声筒,是有个性的。这一理论对传统诗歌理论的突破在于,传统诗歌理论总强调诗歌创作的功利性,“言志”也好,“缘情”也好,其实都是把诗歌当成一种工具来对待。或者如儒家所认为的那样,诗歌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P14),或如一些诗人那样,将诗歌视为吟咏性情的工具。白居易却是在肯定诗歌创作本身就是意义,是人生价值的体现。白居易的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既提高了诗歌地位,也提高了诗人的地位。
(二)游戏诗学观念
一般而言,中唐以前的诗歌创作都包含着对“意义”的追寻,即诗歌创作都应该包含一定的意义(不管是社会意义或是抒发个人感情的意义),都应该是“有用”的。白居易的“诗债”和“文字因缘”理论自然也肯定诗歌创作应该有“意义”,有用。但如果仔细推敲,白居易“文字因缘”和“诗债”的主张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非常极端的理论,即以文为娱的“游戏”理论。虽然他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这个理论,但从他的言论和创作实践,我们却能看出此种倾向。
我们知道,白居易的诗歌包含了讽喻诗、闲适诗、元和体诗等多种体裁,它们或者关乎政治教化,或者为了抒发个人情感,基本上都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有用”的。但白居易还有相当一部分诗除用于自己娱乐(游戏)外,很难说“有用”,他诗集中的大量唱和诗就是如此。
中唐唱和之风很盛,白居易曾几次成为唱和中的主角。元和时期,元稹大量唱和;长庆期间,他与崔玄亮、钱徽等人酬唱;他任杭州刺史时,与此时任越东观察使和越州刺史的元稹再次酬唱。晚年,他中隐于洛阳,与令狐楚、刘禹锡、裴度等人也曾大规模地互相唱和。这几次唱和,留下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除用于个人应酬外,很难说有什么意义。而白居易毕生留恋这类文字游戏,乐此不疲,他的好友元稹说“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6](P663),是非常能抓住白居易迷恋文字游戏的心理的。其实,作为白居易“文敌诗友”的元稹往往是这类文字游戏的“同谋”,比如元稹曾故意用一些难度较高的韵脚写诗,并请求白居易和韵,结果导致了他们大量和韵诗的诞生。关于这个情况,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中说: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瓖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以足下来章唯求相困,故老仆报语不觉大夸。况曩者酬唱,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余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戏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颜,勿示他人以取笑诮。[1](P1463-1464)
这段幽默诙谐的文字正说明他们对待诗歌创作的“游戏”心理,其间多有文人间逞才使气的习气,是典型的为“创作”而创作。
以“游戏”为目的的诗歌创作对传统诗歌观念是一个很大挑战,它的产生是与中唐文化大背景有关。据我们考察,至少有两个因素影响了白居易的“游戏”诗歌观念。
其一,文人酬唱之风古来有之,通过酬唱进行交往是士林的景观。在诗赋被作为晋身阶梯的中唐,诗歌创作是身份的标志,不少人想通过酬唱强化自己的身份地位。白居易以酬唱为娱(游戏)正是受到了此风气的影响,或者说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和积极实践者。
其二,中唐社会世俗化导致了文学被作为一种消费品来对待的现象,白居易与元稹的创作都曾被作为消费的对象。如白居易的书判曾被印刷出来在“书肆”(书店)销售,他与元稹的酬唱诗被江湖上新进小生所效仿,又通过仿效被传播。这些作品的成功反过来更刺激了他们大规模创作。长庆时期元白二人再次唱和,与他们元和期间的唱和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反响有关。
至此,白居易自己也曾意识到在强调诗人本位意识和诗歌本位意识方面似乎走得太远了,也意识到“游戏”之作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他晚年回顾自己与元稹的诗歌创作时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有些诗歌是“率而成章”,缺少艺术价值。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期创作如《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春深二十首》、《不如来饮酒七首》、《何处难忘酒七首》等组诗,大多缺乏真情实感,很多只是韵脚上大做文章,并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属于刘勰极力批评的“为文而造情”。过分玩弄文字游戏之作给他后期诗歌创作带来了不良倾向,致使他后期诗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也为后世评论家批评他的诗歌缺乏艺术意蕴提供了口实。
五、“诗魔”与“文字因缘”背后的深层心理
“诗魔”与“文字因缘”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从“诗魔”到“文字因缘”认识的转变,与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进而导致创作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因为,从时间上看,“诗魔”、“文字因缘”等词大约出现在他丁忧以后,即翰林学士出院之后,也就是他新乐府诗(讽喻诗)的创作基本消失之后,特别是在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这类言语才逐渐多起来;从创作内容看,使他成为“诗魔”(包括“诗狂”、“诗癖”、“诗仙”)的不是他早年创作新乐府之类的讽喻诗,而是新艳小律(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元和体”中的小碎篇章)和闲适诗;从心理上看,他称自己诗魔、诗癖、诗痴时,既有对自己诗歌才能的自骄成分,也有自嘲成分。综合以上几点,我们认为,他的“诗魔”、“文字因缘”的出现与政治热情受挫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白居易早年志在有为,任翰林学士期间,对自己的政治期望尤其高,但江州司马之贬动摇了他的政治信念,造成了人生价值观的急剧转变。从“诗魔”到“文字因缘”是他政治热情退朝后重新调整人生目标的一种自觉行为,反映了他从政治身份向文人身份认定的过程。因此,他诗歌创作的沉溺状态应该是在他政治热情减退之后的心理补偿行为。
“诗魔”与“文字因缘”固然是白居易对个人创作心理的一种解释,但如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看,其创作沉溺现象就有一定的普遍性。前面说过,在中唐,视诗歌创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为之可以牺牲事业甚至生命者大有人在。如孟郊,不肯好好当官,宁愿分俸与人,也要给自己留下时间专心于诗歌创作,又如李贺呕心沥血,正是以生命为代价来从事诗歌创作的。白居易沉溺诗歌创作的现象,实际上还反映了中唐时期人们对诗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言志”、“缘情”之外,诗歌还有一定的交际功能(唱和)、自娱(游戏)等其他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