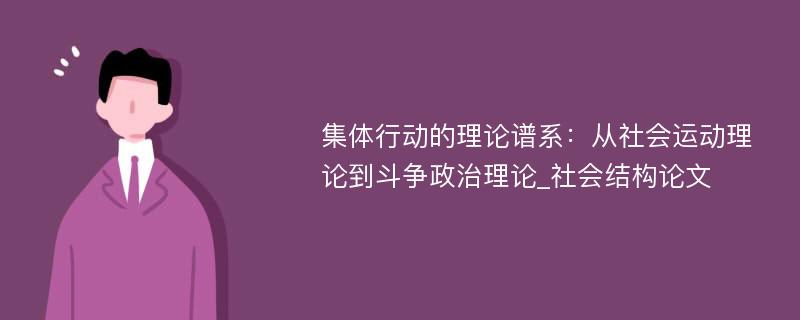
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谱论文,政治理论论文,集体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9)03-0013-08
社会抗争行为是所有社会类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任何政治制度类型所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朝夕相处、相伴相随。社会抗争与人类社会的这种共生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想知道,人类的集体行为究竟根源于哪里?它们的发生与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吗?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表面上乱哄哄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集体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类社会有能力通过努力降低或消灭社会抗争所造成的暴力结果吗?长期以来,社会抗争因为伴随着暴力行为而遭到人们的普遍诟病。在社会抗争研究的早期阶段,以法国思想家勒庞为代表的学者大多对社会的集体行动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集体行动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是暴民心理的集体反应,因此,社会抗争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大都具有负面作用,它们不可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比那些传统思想家走得更远的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予骚乱与颠覆政权的行动以正面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统治者一般倾向于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不过,学者们很快就摆脱了勒庞及其支持者的影响,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对待底层社会的抵抗行动,并且不断使之理论化,形成十分复杂和系统的有关社会抗争的分析概念、解释模式、基本假设以及方法论。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和革命之类的社会抗争已经完全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一、社会运动理论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常见的和主要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和抗争手法(repertoire),其历史十分短暂,按照蒂利的研究,社会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768年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被制度化,同时,这种抗议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发展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抗议形式。[1]在社会运动日益传播的同时,社会运动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五个阶段。
1.社会怨恨理论
1970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泰德·格尔 (Ted Robert Gurr)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试图探讨社会运动的心理根源。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轨等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此书中,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解释模型或者说解释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越大,反之亦然。格尔根据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期望没有变化,而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如果社会的价值能力不变,而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2]
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批判:其一,剥夺感并不足以促使人们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在社会运动产生之前,人们还需要弄清楚剥夺的根源是什么即行动的意识形态,而制造意识形态的人往往不是那些遭受剥夺的行动者;其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资源和有利的机会,否则,不管剥夺多么的严重,人们都很难走上街头;其三,在那些发达国家,人们走上街头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很可能不是因为存在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快就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
2.理性选择理论
与社会心理学派相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行为绝对不是非理性的,社会经常性地以抗议形式对抗政府也不属于一种病态状态,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理性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
但是,奥尔森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最集中的一点是关于他对集体行动的原因的解释,他把集体行动的动机仅仅局限于物质与个人。在塔罗看来,奥尔森的理论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进行罢工、游行、暴动和示威?[3]15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很显然,理性选择理论遇到了致命的问题。
3.资源动员理论
在反思社会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麦卡锡和扎尔德于197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1977年他们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同一个主题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这个理论被社会学家视为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模式。麦卡锡和扎尔德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与奥尔森一样,他们也承认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和动员那些缺少行动动机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4]
资源动员理论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及西欧的主要社会学期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这一理论。但是,资源动员理论的问题仍然是明显的:一是这一理论只强调运动中的正式组织的作用而忽视那些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像家族、朋友关系等草根社会的关系网络,通常在运动中会发生十分重要的作用;①二是这个理论模型来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它是否能够解释落后国家的社会运动现象,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4.文化构造理论
社会运动在以上几个理论模式的构建过程之外,文化论学者也在同时对社会运动进行理论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社会运动的相关文本来解析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他们强调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代表人物包括盖姆森(William A.Gamson)、斯诺(David A.Snow)、本福德(Robert D.Benford)、斯维尔(William Sewell)、麦克亚当(Doug McAdam)、麦卡锡(Johnn D.McCarthy)和塔罗(Sydney Tarrow)。文化构造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运动组织者要赋予运动以意义,以便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运动。
文化论者认为,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它把社会运动的成员和运动组织联系在一起,同时把社会运动的成员们互相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个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的时候就会追求他的行为与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个前提下,很多学者分析了一些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有的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新的替代概念,例如集体认同感和主框架来代替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文化)[5]。他们特别关注下面两种情形:代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得以清晰表达的信仰体系而明确组织起来的抗争行动,以及发生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共同体中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抗争行动。[6]21
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构造论的观点,只要建构出社会运动的意义,社会运动就会发生。然而,这种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运动按照塔罗所主张的那样呈现出周期性,而不是持续出现呢?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擅长利用文化符号而有些运动却显得逊色呢?
5.政治过程理论
社会运动理论的另一支力量是由查尔斯·蒂利领衔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蒂利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尝试对诸如社会运动这样的抗争行动加以模式化,因此在197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从动员到革命》,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放弃了对传统方法的追随,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过程方法,这个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于国际学术界,目前成为一个主导性方法。
在蒂利看来,像社会运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它们不会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形成,也不会在政治之外自行壮大与消失,事实上,集体行动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塑造的关系。他的政体模型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他的政体模型包括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即挑战者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括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
由于我们会在下面专门介绍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有关政治过程的理论就不再赘述。
二、革命理论
由于社会运动与革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因此,革命与社会运动在研究方法与基本立论方面常常出现汇合的趋势,革命或社会运动的理论经常可以相互解释。如果按照学科的标准,革命理论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运动基本相同,它同样经历过心理学(认知心理和挫折—攻击理论)、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人类学(意识形态和文化塑造理论)和政治学(多元主义理论)。但是,由于革命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要远远大于社会运动,因此,两者在微观方面出现了分离。1980年和2001年,著名学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分别发表了两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以简短的文字图绘了革命理论的发展阶段。她将革命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被她称作革命理论的四个代际。通过她对这四个代际的归纳,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革命理论的基本主题和研究现状。[7]
在戈德斯通看来,革命的第一代理论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叙述性的。他们设法辨别革命过程的主要阶段或者描述革命产生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变化。但是,他们的研究缺乏牢固的理论支撑。在第一代革命理论家那里,革命仍然是一种具有负面作用的盲动行为,爆发革命的社会是一种病态社会。
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与第一代不同,他们广泛吸收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与观点,积极建立革命的理论,希望用这些理论来解释革命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发生。具体地讲,他们主要包括三个理论传统:
(1)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研究与挫折—攻击理论。这一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包括戴维斯、格尔、史华兹和莫里森等。这些理论家认为,革命根源在于大众的心智状态,当这种心智进入“挫折”或“剥削”状态时,革命就可能发生。这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的来源各不相同,它们或来源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长期影响,或短期的经济失败或政治或经济的机会对某些群体的系统性封闭。
(2)社会学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逊、斯梅尔塞和哈特等。这些理论家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保持流畅的功能要取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各种亚系统之间维持需求与资源之间的总体平衡,这种需求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一旦受到破坏,社会处于“不平衡”或“功能失调”状态,革命就容易发生。
(3)政治学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冲突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蒂利、亨廷顿和阿蔓等。这些理论家吸收了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将历史事件看作是那些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结果。革命被看成是政治冲突的终极结果。在他们看来,革命形势的因素是利益集团冲突和资源控制之间的结合,它们超出了现有政治制度调节冲突的能力。
第二代革命理论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被看作可能的、促使革命原因的事件模型过于模糊,按照这种模型,几乎所有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文化、技术、军事、人口、组织都会导致潜在的革命形势。但是,理论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原因会导致革命而不是导致逐渐衰败。第二,在所有理论中,关键的变量很难在实践中测量,例如,蒂利和他的合作者对政治冲突进行了分析,但是,他们对关键条件(冲突强度和竞争性团体经过动员的资源)的测量则与民众暴力而不是与革命有联系。第三个弱点是,由于关键变量很难测量,所以要对革命形势的水平给予说明是不可能的,在第二代革命理论中,事实上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超越定量分析,因此,他们的分析无法精确地说明革命形势什么时候到来。第四,第二代革命理论家无法有效地说明为什么不同的革命会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有的革命能够带来多元主义的、开放的政体,而有些革命却带来一党制和威权主义的政体。
第二代革命理论为第三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几十年前因研究国际冲突、发展与现代化、人类学和农民研究而蜚声学术界。在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当中,巴林顿·摩尔和埃里克·沃尔夫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其他比较著名的理论家还包括米格代尔、林兹、斯科克波和艾森斯塔德等人。与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不同的是,早期的第三代理论家并没有创造革命的理论模型,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阐述基本观点,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第三代的理论创造奠定了基础。
这些新观点主要有五个:(1)国家的变化目标与结构;(2)国际政治与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组织压力的系统入侵;(3)农民共同体的结构;(4)军队的团结或分裂;(5)影响精英行为的变量。
尽管有些主题的研究目前仍然在继续,但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就像前两代一样同样面临着批评和挑战。它们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社会变化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得上是“革命”?尽管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分析彼此之间十分的接近,但是,他们在诸如社会变迁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是革命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斯科克波把中国、法国、俄国和墨西哥算作革命的国家,但是,埃森斯塔德却认为墨西哥的社会变迁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相反,他把墨西哥革命类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变种。
第二,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研究的革命案例太少。除了埃森斯塔德,多数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分析的案例太少。斯科克波的革命分析只建立在五个国家的社会变化的基础之上,即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1848年的德国;而佩奇的研究只分析了秘鲁、安哥拉和越南;尽管埃森斯塔德尝试涉及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中广泛的社会变迁,但是他的案例还是过于简单,无法真正地验证他的分析方案。
第三,关于农业结构对于农民革命参与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虽然农业结构被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看作是决定农民参与革命的关键变量,但是,农业结构的某些方面对农民革命行动的影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结论各不相同。例如,佩奇认为,无地的农民最有可能参与革命行动。但是,沃尔夫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是无地农民而是中产农民(即中等程度的土地拥有者)才是革命行动的主要基础。而斯科克波的结论更加地与众不同。她认为,不是土地拥有情况而是农民共同体的结构才是革命行动的决定因素。
第四,第三代革命理论分析没有能够说明革命进程中的共同特征。虽然从第一代开始革命的“自然史”学派缺少广泛的理论视角,但是,他们注意到某些事件的模式似乎与革命相同,例如,革命中“温和的”和“激进的”阶段的出现以及卡里斯玛与威权领袖的出现。这些发生在革命进程中的现象要求理论家对它们出现的频率与可能性进行某些解释。
第五,第三代理论家忽视了人口学数据的研究。诸如人口流动、结婚和离婚率、出身与死亡率、流产和严重犯罪行为等人口学变量受到革命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些变量没有引起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重视。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革命对一个社会的主要人口特征的影响是什么?人口学的某些趋势是否能够对革命做出预测?是否存在着与革命危机相联系的人口学特征模式?
20世纪90年代,革命理论研究进入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第四代际。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革命的原因、过程与影响。除了辨别革命的关键的因果因素和结果之外,他们还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理性选择分析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试图解释革命动员和领袖的微观过程。在第四代研究当中,革命理论家因此呈现出多方位的研究视角。
在对革命的原因分析方面,第四代的研究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二是国家、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1)国际体系
斯科克波在1979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十分敏锐地指出了国际军事与经济竞争对国内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按照她的观点,战争或经济转型的代价会破坏精英和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将国家财政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是,斯科克波的研究仅仅指出了国际影响如何可能促使和塑造革命。事实上,国际体系通过若干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推动革命。
(2)国家、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际环境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革命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精确影响以及革命的全面可能性,主要还是由国家权威、各种精英和不同群众团体(农民、工人和地方或种族或宗教少数派)的内部关系决定的。那些在财政上与军事上受到联合精英支持的国家是不惧怕来自下层革命的挑战的。
古德文、斯科克波和蒂利分析了国家—精英—群众关系的变化如何导致国家的崩溃和骚乱的。他们认为,仅仅国家—精英冲突甚至精英的自治地位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变化,相反,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国家是否拥有财政与文化资源来完成他们为自己、精英和群众设定的目标任务;第二,精英是否团结、分裂或极化;第三,反对派精英是否与群众抗议团体建立联系。
革命的过程分析是第四代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与意识形态。
(1)网络、组织与认同
革命动员所具有的差异性、竞争性与偶然性的本质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革命发展的过程。虽然结构条件可以为冲突提供舞台,但是斗争的形态与结果经常只受到革命进程本身的决定。精英们如何与民众抗议行动建立联系?个人怎样走到一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团体怎样形成范围广泛的联盟?领袖与群体是怎样主导革命的?在第四代革命理论家看来,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研究革命行动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因素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第四代理论的一个关键发现是,革命行动者不是单独行动。他们由事先存在的居住、职业、社区和友谊网络被征召为革命者。他们认同于这些事业与团体,并且为了这些事业与团体而牺牲自己。但是,这些认同特别是抗议认同不是天生的。为了创造与维持与革命有关的认同,精英和国家必须为那些平常称自己为工人、农民、朋友或邻里的人创造和加强新鲜的认知。某些认同越明显,国家与精英就越容易创造抗议认同。
(2)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
在第四代革命理论家那里,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是理解革命过程的一个新角度。他们认为,革命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精英或反对派或潜在革命者对问题的解释。在统治者那一边,即使是战争失败、饥荒或财政崩溃,他们也可以把这些危机解释为正常的、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灾害,而不是把这些危机归结为政府的无能。同样地,国家镇压抗议者的行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措施。事实上,哪种解释占上风取决于国家和革命领袖操控认知的能力,他们将他们的行动和目前的条件与现存的文化框架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任何一个文化框架都可以为革命或反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基础。例如,伊斯兰教为恐怖主义提供行动的基础。但是,革命意识形态是否出现在某个文化框架中,则完全取决于那个框架的因素如何适应某些特定的环境或者如何与新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意识形态除了为革命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道德外衣之外,它们还能够提升革命者的声势,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革命。
在戈德斯通看来,第四代革命理论尽管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主导理论,但是其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不同的是,第四代革命理论将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它会视稳定为维持政权的一个焦点条件;认同、意识形态、性别、网络与领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会视革命过程与结果为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8]因此,按照戈德斯通的理解,我们目前对第四代革命理论进行评价似乎显得过早。但是,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特别是第二代相比,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第四代理论的部分局限性和弱点。首先,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之间的分歧仍然十分巨大,对革命现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革命的定义与分类问题。其次,由于分歧太大,这些理论家的工作很难被整合到一个框架下进行,这样会影响到对革命研究的整体水平,例如,他们对革命的概念存在较大分歧,影响到对革命原因、过程与结果的分析。第三,第四代理论在方法论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他们事实上仍然在延续第二代的方法。第四,由于方法论的局限性,第四代革命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革命的微观问题。
三、抗争政治理论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演进过程中,革命理论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它至少是将被人们所诟病的非理性革命行为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为人类理解与把握自身的集体行为提供了相当可行的知性工具。但是,革命理论家仍然对自己的努力不甚满意,他们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各自为政”感到不满,分析概念、研究方法与核心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性阻碍了社会科学对人类集体行动的认知。因此,社会科学家在不断地反思。
在反思的基础上,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图绘抗争政治”,这篇论文被扩充为后来的《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部核心著作。最近几年,蒂利表现出超人的学术毅力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学术创造力,连续推出若干部学术著作,系统地论述抗争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②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社会运动、革命等抗争行为的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以相同的概念、相同的分析方法和相似的结论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避免因人为的学科划界带来的差异性而影响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这是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一个贡献。
在抗争政治理论家那里,他们以contention(我把它翻译为“抗争”)取代了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式。但是,contention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关键的问题是,理论家们将“抗争”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使这两者之间发生关系,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观察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从而构成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我们从抗争政治理论家对于“抗争政治”的定义可以发现这个理论与众不同之处。抗争政治指的是:
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6]7-8
抗争政治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抗争政治不同于如选举那样的一般政治,也不同于与公共政治无关的社会冲突。抗争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优点是不再在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划上界线,从而打通了不同抗争形式之间的研究壁垒。
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二大贡献是运用了政治过程的方法来研究抗争行为。1978年,蒂利发表了著名的《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和政治过程方法,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家全面理解社会抗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政体模型与政治过程方法主要是为了纠正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忽视政治因素的传统,这种理论与方法至少能够在方法论上缩短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之间的距离。
在政体模型中,蒂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结构,集体行动者与政体成员和政府之间如何互动起来呢?或者说如何让他们彼此之间动起来?因此,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整个过程。通过动态的分析,理论家从中找到促使抗争发生与发展的各种动力(抗争政治理论家把它们称作机制)。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机械地在结构因素与集体行动结果之间划上等号,但是大量的例外情况使得他们的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些结构因素在社会抗争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结构因素在过程演变中的不同结合方式。因此,按照政治过程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因素的国家集体行动的方式和结果却截然不同。
抗争政治理论强调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在蒂利等人看来,无论集体行动是社会运动还是革命,在它们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社会抗争展开的动力,“它们依据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性结果。”[6]37因此,与传统理论相比,抗争政治理论具备了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是抗争政治理论的普遍适应性。这并不是说抗争政治理论的结论无法挑战,而是说,它的理论框架是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权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抗争政治理论不同,社会运动的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很难得到验证,因此,理论局限性很大。而革命理论则是主要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理论家的研究尽管也是选取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为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革命的条件显然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200多年前革命形势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无法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事件。很明显,抗争政治理论能够将不同历史时段的抗争事件放到同一个框架之下,进行比较研究。
抗争政治理论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为中国学术界理解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能够为抗争政治理论发展与完善提供丰富的佐证资料。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国社会是研究社会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它是集体行动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们期待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中国不断深化下去。
收稿日期:2009-03-25
注释:
①例如,周学光与赵鼎新在研究中国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参见Zhou Xueguang (1993),"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58:54--73; Zhao Dingxin(2001),The Power of Tiananmen: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②蒂利的有关抗争政治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部:(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1650-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ocial Move ments,1768-2004.Boulder,Colo.:Paradigm;(2005)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2d ed.Boulder:Paradigm; (2006) Regimes and Repertoire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Paradigm Publishers; Contentious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