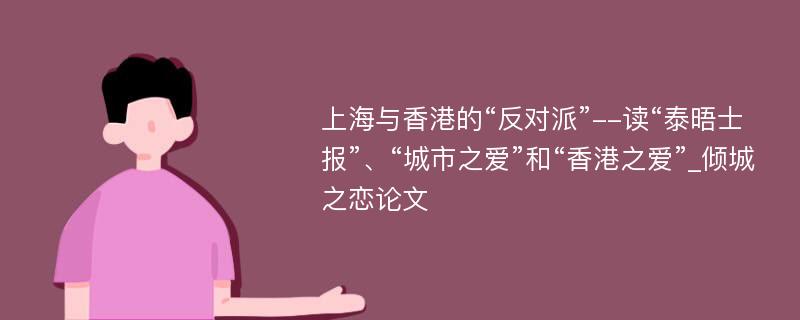
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之恋论文,对立论文,上海论文,姑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中国政治变化和城市急速的发展,进出于不同城市,几近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共同经验。城市之间的差异和不协调在他们身上激发起各种深邃的思考,构成文学作品的复杂内涵。叶灵凤《时代姑娘》(1932)、张爱玲《倾城之恋》(1943)和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993),三篇作品发表时间所横跨的幅度接近六十年,但三者讲述女性离开家庭,探索情感命运的出路时,不约而同将女主人公“离家”的路线安排在来回港、沪之间的地理路线上。事实上,三位上海作家(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设计都是不可易转的选择。他们均利用自身对另一个都市(香港)不同层面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与上海相对的故事背景,探讨城市和女性处境、情感发展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城市背景的出现,三篇小说描写女子出走家庭以后的命运,无法再被“五四”文学续写“娜拉走后”的几种写法所概括。① 简单而言,她们所面对的困境不再是“家”和“社会”或“家”和“精神世界”的对立,而是上海和香港的对立,也就是“城市”和“城市”的对立。她们的“家”不仅指向中国传统家庭,甚至概括了整座城市。对小说的女性人物来说,离“家”出走其实是离“城”出走,她们亦只有进入另一个城市,其感情和生活才能找着新的发展机会。只有从这角度思考,我们方能理解为何三位女子“离家”的路向,都必须被安排在“从港到沪”(《时代姑娘》)、“从沪到港”(《香港情与爱》)以及徘徊于沪、港两地之间(《倾城之恋》)的地理路线上。
本文尝试“并置”阅读三篇小说,探讨以下若干问题:第一,小说中城市地域和居住场所的转移,在女性人物探索情感的历程上有何具体意义?第二,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离家以后的命运发展,怎样对鲁迅所提出、“五四”文学反复讨论的两种结局模式——“回家”或者“堕落”,进行新的探讨和诠释?第三,小说如何展现三位不同年代的上海作家对香港的想象?他们又如何通过“论述”香港,反身定义自己(上海)的位置?这里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形象的问题。我们更需要进一步探究,作者为何要凭借另一个都市的文化压力,去讲述自己的“上海故事”。
《时代姑娘》、《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的女主人公秦丽丽、白流苏和逢佳同受婚姻约束(曾定婚或结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离开家庭,找寻情感命运的出路。假若我们将三位女子的“出走”视为一个过程,这过程基本上重叠了两个空间层面的变化:城市地域和居住场所。② 从此角度考察,三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至少有两方面的共通点:一、在叙述结构上,小说均借助城市场景的置换,具体呈现女主人公“离家”过程的转折点,即是她们决定去向的一刻。二、在整个探索过程中,女主人公进出港、沪两地所寄住的旅馆、酒店、公寓、出租房子、私人楼房等等城市居住空间,它们代表的特定生活模式及其隐藏的象征意义,与女性的情感命运发展互相观照。
《时代姑娘》的小说开首,即描绘香港鲤鱼门海港及对岸景色。③ 故事主人公秦丽丽虽然生活在南国小岛,却拥有30年代上海“新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健康(“她光润而坚实的手臂”、“结实丰满的肉体”)、擅交际(“好交游”)、受高等教育(上海江湾大学学生)。④ 香港之于她是“家”,是亲情和爱情的归属,但又离不开两难的处境:她私下与韩剑修相恋,却不敢违抗父命与银行家张仲贤订婚。表面看来,作品具备“五四”以来“问题小说”的格局,关注青年人自由恋爱和传统道德、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而经济和伦理道德的双重压力,又是新文学强调女性自觉以后首要面对的问题。不过,叶灵凤笔下30年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发展却有所不同:秦丽丽的考虑和选择,并不限于两位男性和两种婚恋模式(家庭安排及自由恋爱)之间。
秦丽丽对自身情感命运的探索,依据“从港到沪”的地理环境转移,被截然分成两个阶段。离港以前,她虽不愿接受伦理道德和经济压力下成就的婚姻,立意为自己报复。可是,她只能按照以婚姻作为“买卖”的价值观点,从负面角度加以对抗。其报复方法是精心安排在半岛酒店内奉献自己的“肉体”予韩剑修,着意令自己下嫁张仲贤以前变成不纯然的“货物”,藉此“嘲弄那高压着她的一切”。⑤ 报复计划虽然带来精神上的胜利,却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只有远离家庭、爱情和婚姻所连系的地方(香港),秦丽丽才能合理评估自身处境,在两种婚恋模式以外寻求第三种出路并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故事的转折点)。她在“从港到沪”航程上以文字方式(四则日记)理清问题,并判断面前的三种路向:她不要回到张仲贤的身旁做奴隶的女性,也不愿意与韩剑修维持原有的情感关系——假若因酒店发生的事情(肉体关系)而必须向韩剑修签下“卖身的契约”,始于自由恋爱的关系最后依然让她成为“长期的卖淫妇”。⑥ 最后她提出要抛弃一切,成为彻底自由的女性。秦丽丽对自由的理解,仅限于“无拘无束”的简单概念,她甚至将之等同风尘女子的生活,在上海主动跟随已有妻室的萧洁。不无讽刺的是,小说中唯一与题旨“时代姑娘”相关的讨论,就是由萧洁道出:“时代姑娘应该创造时代,不该跟了时代的样式走。⑦”可是他诱导秦丽丽走上的新道路,正是“堕落”的道路。
小说虽然否定两种婚恋模式,却没有成功为中国30年代的女性指出第三条可行的出路。相反,作者极力表现两种模式以外的“不可能”。女主人公寻找情感生活上自主位置的经过,一直紧扣她找寻家庭以外寄住地方的历程。而这些酒店、饭店、旅社等城市新兴出现的居住场所,一方面为她提供传统社会规范以外探索情感发展各种可能的空间(就是要在香港进行反抗,也得选择殖民者管理的半岛酒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暗淡的前境。秦丽丽上沪以后曾三次搬家:首先随萧洁的建议入住中国饭店,不再返回学校;第二次为着断绝家人的联络查问而搬往东方饭店,并与萧洁定下私密的关系;第三次为了逃避萧洁及其家人,搬往三马路的新惠中旅社。与《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相比,小说人物在酒店、旅馆内活动的描述都被大大省略,女主人公不断转换居住场所只表明暂时让她脱离束缚的自由地(上海),未能成为她真正的栖息处。秦丽丽“从港到沪”的“出走”是单向且义无反顾的。离开香港(家庭、爱情、婚姻)是为了“自由的上海”,可是这道路应如何走下去?代表了中国30年代女性的故事主人公“想到这里,心里不觉一怔,觉得皮肤上像吹了一阵冷风,起了一阵颤栗”。⑧
相较于秦丽丽,《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不仅“没念过两年书”,且是离婚妇人,她对自己及同时代女性命运的理解,更贴近社会实情而缺少幻想。小说打从白流苏跑回娘家七八年之后开始,讲述的其实是她第二次“离家”的经历。“离家”的冲动源自一场与兄嫂的争吵,一方面她不愿听从家人意见跑回夫家当离婚丈夫的寡妇,另一方面她亦意识到娘家不能久留的现实情况。兄嫂固然靠不住,就是想象中可祈求可依靠的母亲也叫她落空。夫家归不得,娘家待不下,40年代的失婚妇人还有什么去路?
白流苏决定再次“离家”的一刻已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欠缺金钱不能走远;二、欠缺学识也不愿干粗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心里明白余下的选择,就如徐太太的劝告:“还是找个人是真的”。⑨ 丽丽和流苏同样看透婚姻存在“买卖”成分,前者极力反抗,后者却因为洞悉世情而以婚姻为毕生“事业”,“出走”对她而言不过是“潇洒苍凉的手势”。⑩ 她的“出走”不仅与自由理想无关,更旨在再次觅得愿意委身跟自己结婚的男人。
离开上海往香港的最终决定,取决于白流苏能否确认自身价值——不是“五四”作家强调的女性自觉意识,而是女性的原始“本钱”。小说描述她“扑在穿衣镜上”,首要确定自己从外表看上去“还不怎么老”。然后仔细打量了身型体态:“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再从整体到局部,一一察看脸儿“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似的肤色、尖的上颌、窄的脸庞、宽阔的眉心,还有那双“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11) 镜前这个完美无瑕的影像,不仅增强了白流苏再次“离家”的信心,也成为她日后“犯险”与范柳原交往的凭借。(12) 在张爱玲其他小说里,都出现过女主人公“镜前自照”的场景。她们均要借助这番“客观”的自我审视,方能为自己的前途作出关键性的决定。《第一炉香》葛微龙第一次到访姑母坐落在香港半山、极富东方色彩的豪华住宅,就曾在长廊的玻璃门前“端相”自己:虽然平淡而美丽的“粉扑子脸”有点过时,面部表情也稍嫌缺乏,但“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而相较于橄榄色皮肤的粤东佳丽,皙白的皮肤倒又变得“物以稀为贵”。在双重比对之下(西方与香港),葛微龙这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反而增加了自信,敢于向姑母提出交换条件。(13)
白流苏“离家”过程中的进进退退(“沪-港-沪-港-沪”),配合了她与范柳原一场男女角力中“以退为进”的策略。整个展现在港、沪两地交替的“离家”路程上,香港为白流苏提供了命运转折的契机,具体表现为香港居住空间的变化。钱钟书曾以一座军事防卫建筑“围城”为喻,写人们对婚姻的矛盾态度和复杂的战略心理;张爱玲则着眼日常生活,藉“酒店”、“租住房子”和“家”三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居住场所的层递变化,写男女在爱情中从虚幻回落现实的过程。小说中白流苏曾先后两次“从沪到港”,香港的故事场景则从浅水湾的酒店迁往巴丙顿道的租住房子。酒店属于旅者,一切相遇都是巧合而短暂,忽聚忽散;租住房子虽然较接近平实的生活,依然是借来的地方,有别于长久的“家”(王安忆《香港情与爱》中关于居住场所的论述,更可作为《倾城之恋》的注脚)。白流苏跟范柳原,为的是“经济上的安全”。要突破这种浮光掠影、只能寄生于异地酒店的情感关系,白流苏突然返回上海,以退为进迫使范柳原带着“较优厚的条件”回到她身边。可是当她第二次来港时,范柳原只属意替她租下房子,让她成为自己的姨太太。假如故事就此结终,白流苏“盘算”、“忖量”的计划可谓全盘失败,范柳原引领她走向的不过是“堕落”的道路。
《倾城之恋》作为“传奇”的关键就在于堕落的道路,最终竟换成平庸而幸福的归途。小说中具体化的表现,正是白流苏入住的一座“租住房子”,不可理喻又合乎情理地转化成真正的“家”。她搬往巴丙顿道(充当姨太太)是迫于无奈的决定,纵然获得暂时安身的居所,还是“满心的不得意”。日军入侵,香港沦陷,促使流苏和柳原在精神上和言语上互相试探的恋爱方式,顿时变成买米、打水、做菜煮饭、扫地、拖地板、收拾房间等踏实的生活化的恋爱“过程”。讲究精神恋爱的范柳原也从中得到启示:“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14)”虚幻的情感落实到人间,白流苏也从姨太太的身份当上“名正言顺”的范太太。
《香港情与爱》的逢佳作为90年代的失婚妇人,对自己的前境有着与白流苏相异又相通的看法。小说中逢佳出场时已身在香港,她的身世以及“从沪到港”的离家过程,都被刻意隐藏在一段香港经历的背后。概括而言,逢佳每次“出走”,都是被男性(父亲和丈夫)“抛弃”间接所致的结果。父亲在上海舍弃她母女二人到香港,她长大以后就利用父亲对自己的愧疚,要求他替自己达成来港的愿望。同样,当丈夫提出离婚远走美国,她就千方百计移民此地。在一再被人家“抛弃”的人生里,逢佳不断寻求“出走”的机会。一方面她理解到自己“没读甚么书,身无长技”,在现实社会中难与他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在两性角力的关系中她一直处于被动、被抛弃的位置,她决心要同样赢取舍弃她的人所获得的机会,用“比过他几倍几十倍的好,叫他心里不安”,作为报复。(15)
逢佳从不考虑跑回上海的老家,也不祈求再藉婚姻获得生活的保障。她希望再度“出走”,把自己的前途悬空,从而创造各种变数。同样清楚认识到大都会男女关系中不纯粹的部分,逢佳较白流苏更坦然承认、接受这种以“交易”为本质的情感关系。(16) 故此,她可以毫无顾忌去安慰跟她交易的对手:“我们谁不欠谁。……我们本就是两相情愿。……我觉得很值得,没有吃亏,假如靠我自己去奋斗,这两年到不了这程度,……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错的,我倒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是用在刀刃上了。(17)”堕落的道路在逢佳的眼中是“重生”的机遇,她付出两年的青春替老魏带来人生中最后一道风景,而老魏就得成全她出国的愿望。
小说叙述逢佳离家经过只集中在香港的一段历程。小岛上逢佳和老魏的情感发展同样紧扣三个居住场所:“酒店”、“公寓”和“私人房子”。(18) 如果《倾城之恋》是以居住空间的转移呈现人们虚幻情感落实人间的过程,《香港情与爱》就分别细写它们“虚中有实”的部分,发掘逢佳和老魏的情感在每一个空间里“化虚为实”的可能。不论王安忆是否有意针对《倾城之恋》重写上海女子和华侨在香港的情爱故事,我们都可从中窥探她如何扩展张爱玲“香港传奇”的意涵。王安忆自言“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19) 张爱玲写传奇着重都市日常所见“悲欢离合”的人生里,平、俗中所包含奇异的成分;而王安忆则进一步考究都市“最普通的人生”里“虚中有实”甚或“化虚为实”最凝练的部分。故此,她注视大都市广告招牌和霓虹灯照耀下,那些楼房窗户所象征“最最恳切、柴米油盐的生计”,并补充说明“它们是香港奇景的坚牢基石。这是最最平实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测,它们就有多平实。(20)”她强调香港作为一个“大邂逅”、“大相遇”和“大机缘”,它所成就那种以“交易”为本、各有所图的男女关系,同样可以随着时间产生情义,彼此产生真心善待之意,甚至产生怜悯。(21)
酒店是逢佳和老魏关系的起步点,他们第一次在丽晶酒店(今天的洲际酒店)见面,往后在酒店“订立”二人的交易关系。虽然同为借来的地方,酒店却不及公寓来得亲切,这里王安忆注意的是不同空间内人们起居饮食的生活细节:“公寓是有表情的,酒店则没有。公寓的起居作息是有细节的,酒店是理论化的。公寓是注重过程的,酒店是目的性的。(22)”但是有了人的活动,冷静和淡漠的酒店房间还是能够显出温情,逢佳“聒噪的说话”、“沉入睡乡的鼾声”还是让老魏感到酒店窗外香港夜景的美“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美”。(23)
二人情感真正发展的阶段是在北角的公寓,老魏和逢佳的生活得以聚焦在煮饭、炒菜、泡茶、洗碗、洗衣服、看电视等细节上,这种“有汤有水有渣子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关系,正是“供他们一天天过的,不是一句句说的……,没一点虚的。(24)”公寓共处的日子虽然带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小动作,却无法抵消他们作为过客漂泊的心情。(25) 最后老魏还买下房子,建立他俩在香港的“家”。范柳原和白流苏、老魏和逢佳,他们都同样在特定居住场所的共同生活中有所领悟。前者因而建立起“长久的家”,后者组成的不过是“临时的家”。“临时的家”不能久存却带有“契约”性质,住在里面的人不是终身同道,“却是人各有志、守信践约、相互支持”,在人生短暂的邂逅中仍然推心置腹。(26)《香港情与爱》强调男女关系这种契约性质以及“化虚为实”的生活情节,对女子“出走”寻求“彻底自由”(秦丽丽)或再次寻找“长久的家”(白流苏)等故事,都有了90年代的重新演绎。
三篇小说女主人公“离家”的过程,均从一个城市进入另一个城市,两地的选取同是香港和上海。事实上,自30年代起,不少沪上作家偏好选择香港作为一个与上海相对的故事背景。叶灵凤另外两部中篇小说《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施蛰存的《港内小景》、穆时英的《公墓》、《Craven“A”》、《五月》和《第二恋》等篇的人物背景或故事情节也牵涉这个南方岛国,复杂的情况有待另文分析。(27) 到底上海作家为什么对香港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在哪个层面上,沪、港两地可以互相比对?
本文讨论的三位作家,只有叶灵凤曾定居香港。(28) 不过当他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写作连载小说《时代姑娘》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笔下的香港会成为自己下半生的居所。《时代姑娘》以南国小岛作为上海大都会的相对面,强调它朴素平静的环境:“碧绿的海水,海中蠕动着的船只,海面上飘荡着的白烟,远处的苍山,山中高低点缀着的房屋”。(29) 从文学形象学(Literary Imagology)的角度分析,小说对香港的描写,一方面凭借作者的游历经验,另一方面则糅合了同时代上海人对此地的普遍想象(也包括一定的误解)。(3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30年代香港都市和商业发展远不及已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但香港城市景观和市民生活的改变,还是受到文人作家的关注。叶灵凤当然意识到香港都市的发展情况,《时代姑娘》也多次表示香港在娱乐消费方面的发展较上海逊色。(31) 那么,作者描写香港为何仅限于它的自然景色?
从批判现代西化都市文明的角度而言,令叶灵凤心感不安的是上海大都会的发展,而相对上海能让他重享平静的地方就是都市化和商业化进程均较缓慢的香港。在这里,人们对于人生和恋爱尚能保持较为严肃的态度,上海的都市文明反而陷人于种种道德危机之中。秦丽丽虽努力反抗社会决定的女性命运,但内心始终受着传统道德观念的责难。故此她在堕落以后,不时怀念自己在“南国明亮阳光下”与家人和情人种种欢乐的景象,回想在“南国炎热天气中”自己单纯和认真的情感,又不断追问“到了上海,为甚么又突然这样的自暴自弃,度着几乎是类似卖淫妇的生活?”(32) 为了营造一种相对朴实的气氛以反衬风靡的十里洋场,小说描写香港就偏重于平静而朴素的自然风光。鲤鱼门的秋夜月色、清水湾的苍山绿水,正好比对上海混杂喧闹的人声和车声、南京路上“像吗啡针一样”刺激人们眼睛的各式广告霓虹光,还有声色犬马各种消费娱乐场所构成的都市景观。”叶灵凤以尚未完全发展、保有纯朴自然的都市反衬上海,其实与沈从文(京派)以乡村、自然所代表的朴素道德标准为据批判都市文明的做法十分接近。不过京派作品中象征乡村、大自然的北平,在《时代姑娘》里被换成南国小岛——香港,这种情况大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上海和香港在小说中作为相对故事背景的另一基础,是相近的政治和历史处境。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论者常提及的殖民地背景。叶灵凤更加针对当时日本侵华的现实情况,比对描写已祸及战乱的上海和“偏安”的香港。(34) 作者自首次来港(1929年夏)至执笔写作《时代姑娘》(1932年冬、1933年春)期间,中国东北和上海就分别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国内局势越见紧张。小说讲述秦丽丽急于返沪,除为了摆脱家庭约束以及婚恋纠缠的问题外,也是因为她对政局的关怀,“想早点到上海去看看战区和闸北”。(35) 小说再通过她的视觉,进一步呈现战后北四川路的萧条境况:冷落的街道、失却黄金时代神秘意味的商店、灯光幽暗的酒楼、路人仓皇不安的脸色以及摇摇摆摆的日本巡逻队。女主人公就在这种冷落幽暗的色调下探索前程。《时代姑娘》发表期间,上海表面上已回复平静,可是普遍市民还是对当前政局充满恐惧和忧虑(36)。作者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回忆、想象和书写南国小岛“偏安”的局面,它既反衬战后上海的萧条,亦成为暂时回复平静的上海的一种隐喻。眼前的上海危机四伏,暂得安稳的香港其实百年以前已割让异邦,两个城市的命运同样令人忧虑,而后者的历史更激发起叶灵凤对近代史上外力入侵、殖民统治深刻的感伤。所以小说描写韩剑修看着香港两岸怡人景色,不禁惋惜“这可爱的一切是早已属于异国的统治”。(37) 往后的历史证明,上海和香港最终都经历了更大的破坏,而叶灵凤亦亲身目睹两个城市的沦陷。
如果《时代姑娘》描绘的香港是30年代上海大都市的反衬,《倾城之恋》刻划的香港就是上海的平衡对照。不过张爱玲对两大城市的观察、理解和再现,都必须放在战争背景、“时代仓促”的氛围里加以考量和分析。上海沦陷不仅为张爱玲在文坛上缔造了发展空间,也教她首次体验日军统占下上海市“不经见的沉寂”以及压住每个人的“巨大的重量”(38)。不过,是香港的战事为张爱玲的人生和创作带来更加巨大的冲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返回上海的第二年(1943年),一连发表了七篇小说,并说明自己“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39)。其中她刻意写上海人“进入”香港的故事,也通过《传奇》某些篇章让香港“进入”上海读者的视野。《倾城之恋》选择香港沦陷为背景写上海人“进入”香港,既借助战争的“特殊空气”展现人生“戏剧化的一刹那”(40),亦利用故事人物“进进出出”两个在语言、生活习惯、西化现代化程度上有所分别的城市所构成的文化压力,极端表现上海人眼中香港的光怪陆离(41)。
张爱玲以香港作为上海的参照系,为两个城市寻找审视的距离。她在《烬余录》(1944)中回顾香港沦陷时提及:“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42)”因为有了距离,人才能“定下心来”,将好一段人生经历加以整理。其实这里所指的“距离”,除了时间、地域上的距离外,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距离,也就是张爱玲观察中国以至世间事物所追求“相当距离”的总体含义。
我们注意到,第一,上海始终是张爱玲理解香港的灵感泉源,只有通过两个城市的并置比对,作者才能准确描写香港。张爱玲写“战前香港的故事”,描述殖民地的深宅大院,以为它“比起上海的紧凑,摩登,经济空间的房间,又另有一番景象”;描写香港大户大家的小姐,认为她们虽然“沾染上英国上层传统的保守派习气,也有一种娇贵矜持的风格,与上海的交际花又自不同”(43)。上海、香港两个洋场城市的建筑和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均受西方文化影响,只有对照之下才显出他们各自的特色。在此之上,张爱玲更只有比较沪、港两地沦陷以后的境况,方能肯定上海在她心目中的优越地位。她以为“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战后发展“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44)。《倾城之恋》描述白流苏、范柳原在香港陷落以后设法回上海,也是相近的道理。战后香港的市面复苏太慢,“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莽莽的寒风”,对他俩来说“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久长之计”(45)。香港之于白流苏(张爱玲),从来不是久留之地,她却偏要借用这个“夸张”的城市,才能成全“倾国倾城”的传奇(《传奇》)。
“相当距离”的第二重演绎,就是“洋人看京戏的眼光”(46)。不少学者早注意到这种保持距离的审视“目光”,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被具体化为“华侨”或“归国学人”身份的男主人公(范柳原、童世舫、章云藩和佟振保)(47)。他们抱着不同预设去凝视象征“古中国”的上海小姐(白流苏、姜长安、郑嫦川和“红白玫瑰”)。不过,海外归来的中国男子能否完全代替洋人的眼光?他们想象中或回忆中“真正的中国(女人)”与西方人所见的“中国(女人)”又是否相近?以香港为背景的《倾城之恋》为上海小姐(古中国)提供了更复杂的参照系——一场来自印度公主萨黑荑妮、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相互“对视”(对峙):
流苏在那里看她(案:萨黑荑妮),她也昂然望着流苏,那一双骄矜的眼睛,如同隔着几千里地,远远的向人望过来。……萨黑荑妮伸出一只手来,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苏的手,问柳原道:“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来的?”柳原点点头。萨黑荑妮微笑道:“她倒不像上海人。”柳原笑道:“像那儿的人呢?”萨黑荑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帮子上,想了一想,翘着十指尖尖,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样子,耸肩笑了一笑,往里走去。柳原扶着流苏继续往外走,流苏虽然听不懂英文,鉴貌辨色,也就明白了,便笑道:“我原是个乡下人。”范柳原道:“我刚才对你说过,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那自然跟她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48)
当白流苏带着迷糊和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个全盘西化的英国殖民地为洋人设造种种“中国情调”的同时,她同样受到另一双眼睛所注视。萨黑荑妮“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她保持着地域和文化距离“如同隔着几千里地”注视白流苏,并判断她“不像上海人”。与萨黑荑妮持不同观点的,正是范柳原这个“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的华侨。他不仅以为白流苏是个“道地的中国人”,甚至是“真正的中国女人”(49)。这里,有关自我与他人、命名和被命名、定义和被定义、话语权力、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论述,都可被整套引入。
从注视中国(女性)的角度看来,范柳原与洋人的目光其实亦远亦近。他同样对中国(女性)充满想象,喜欢白流苏“善于低头”、穿着“月白蝉翼纱旗袍”的古雅形象,并留意她许多“很像唱京戏”的小动作,沉迷洋人倾慕那种古中国的“罗曼蒂克的气氛”。但由于出入中、西文化的经验,他多次表明自己很能辨别香港饭店那种制造给洋人看的“中国情调”,更能辨识洋人概念中“所谓的上海人”。范柳原作为“中国化的外国人”,既明白文化差距所造成东方的吸引力,却又不能自拔继续迷恋我们的“古中国”(50)。
至于白流苏作为整个“对视”过程的被注视主体(le sujet regardé),身上最少凝聚了四个层面的想象:我自以为的“我”、我希望别人看到的“我”、别人眼中的“我”,别人用言语修饰描述的“我”。(51) 相较于萨黑荑妮和范柳原对自己的注视和描述,白流苏却有不同的自我想象。在“乡下人”和“道地的中国人”之间,流苏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过了时的人”。在她而言,“过时”并没有跟不上时代潮流(“乡下人”)的贬义。相反,作为望族“穷遗老的女儿”,她淑女的身份、充当“贤慧的媳妇”和“细心的母亲”等学识本领,都只能在“过时”的旧中国社会里得以发挥(52)。她要用中国传统妇女的本子去摸索、饰演一个打破传统道德规范的角色,赢取范柳原的青睐。
《香港情与爱》是王安忆至今唯一直接书写香港的小说。相较叶灵凤和张爱玲分别以香港作为上海的反衬和对照,王安忆则更抽象也更直接地通过描写香港,表现她对上海的关怀。王安忆笔下的沪、港是两个互相重叠的城市。作者在小说中着意表现香港作为繁荣大都市、殖民历史传奇和“提炼过的人生”的象征(53)。这三方面的象征意义包含一定的普遍性和概括性,与作者一直通过写作来探讨的上海“底子”,有不少相通的地方(54)。《香港情与爱》通过逢佳“进入”香港的故事,让一位来自上海的女性及其身上附带的沪上特质与异质,得以和香港在地理、历史和政治层面上的象征寓意互相比附、互相发明。
香港之为“港”,本来就是个“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55),成就各种各样的“过客”以及浮世男女式的人物。王安忆运用香港在地理上这种既非大陆亦非海洋的“半岛”特点——边缘位置和“过渡”性质,为小说主人公的一段香港经历提供了一个颇具寓意的故事实景。第一,逢佳以三个地方总结自己三十六年的人生:“我这三十六年里,过了几世了?一世大陆、一世香港,澳洲的一世也要开头了”(56)。大陆是始,澳洲是终,香港则是逢佳人生历程的中转站。小说刻意省略了她来港前及离港后的遭遇,为要详述香港一段“过渡”的人生,“过渡”的场景。
第二,逢佳固然是香港的“过客”,但她在自家出生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外来户”。逢佳与王安忆许多小说里的上海人物一样,活在上海却同时是上海的“异乡人”(譬如《纪实与虚构》里的“我”;《富萍》里原籍扬州的富萍和奶奶、原籍浙江的师母、原籍苏州的吕凤仙、原籍浦东的戚师傅、原籍安徽的老婆婆和瘸孩子;《妹头》里原籍扬州的朱秀芝)。逢佳从前在上海被认为是江北人的类型,“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57)。如今在香港或日后在澳洲作为新移民,她同样摆脱不了身份问题上的边缘位置。
第三,逢佳的情人——来自旧金山的老魏,则是“没有国家只有籍贯的人”。从语言来说,老魏磕磕巴巴的英语、不灵光的汉语和流利的地方语,决定他作为外来者那种暧昧、模棱两可的身份;从体格相貌而言,他的孩子也是天赋“移民的面目”:“不像中国人、又不像美国人”,却倒反合符美国精神(58)。
香港作为英国的租借地(殖民地),在历史意义上它是借来的地方,它的繁荣也是建基于借来的时间。小说中香港的“租借”历史与男女关系的“契约”性质互相观照:“纵然英国租下香港一百年,就好像要作是千秋万代的计议,可是一百年不已到头了?一百年的契约尚且如此,更何况他[老魏]与逢佳。(59)”所谓“契约”性质,无论在历史意义上或是人物关系上都有两项特点:一、签订契约双方关系的建立按章则决定,并非从经验发展而来;二、契约关系不谈长久,在历史发展上永远是个“暂时”。故此,《香港情与爱》讲述的男女情爱不像夫妻关系,经岁月磨炼。相反,老魏与逢佳在生活上的融合是“迅速成就”。他们从外部条件着手,先决定“契约”关系中男女的角色和位置、权利和义务。至于二人对金钱的支配权、家庭生活的分工、日常的相处模式以及将来分离的程序,都是“有理性、有策画、对结果有所预测”。(60) 这种“按章建设”、“按部就班”的男女关系,正好因着时间的规限,被浓缩、被提炼成为概括化和约化的人生要义。也许,利用男女关系和城市历史互相观照来探究人生的隐微,向来是王安忆讲述她“上海故事”的方法。
总结上文所论可得出以下三个重点,并藉此回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第一,本文所论三篇小说描述女性离家(城)进入另一个城市,具体呈现她们在情感探索和精神思想层面上的转折。女性必须远离自身所属城市所代表的生活模式、人际网络和道德价值,进入另一个不同系统的城市寻求改变命运的契机。至于三位女主人公能否成功为自己的情感命运找到新的出路,则完全取决于她们能否在另一个城市寄住的具体空间内,通过日常生活与异性重新建立两性关系的秩序。换言之,小说文本中这些旅馆、酒店、公寓等特定的城市居住场所,为女主人公提供了传统道德规范以外开拓、发展情感的空间。《时代姑娘》的女主人公同时否定包办婚姻及自由恋爱两种婚恋模式,她多次转换饭店、旅社只为逃避家庭道德压力,所以小说对这些居住场所内男女人物的共同生活细节,一概尽付阙如。相反,《倾城之恋》和《香港情与爱》均详细记述男女人物在各种居住场所内日常生活的片段。前者借居住场所置换表现男女情感从虚幻回落现实的层递发展,后者则细写人物在三个寄住地方的生活细节,不断重复、深化表现浮世男女情感关系中“化虚为实”的部分。
第二,基本上三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离家以后都拒绝回家,但有意无意间却走上传统道德规范下所谓“堕落”的道路,当然她们对自身的选择都有不同理解。秦丽丽透过风尘女子的生活体现彻底的自由,在“堕落”的道路上进行反抗。白流苏对情感命运的考量,重点在于经济条件而非道德规范。故此,不论她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走上“堕落”的道路(成为姨太太),还是借着战争机遇重新踏上平庸而幸福的归途(范柳原的家),她关心的不过是生活是否得到保障而已。至于逢佳,她从来视情感的交易为“重生”的机遇,透过不断“离家”(上海、香港)寻找他乡可立足之地。基于不同的道德主题和意识形态,三篇作品均改写并重新诠释鲁迅以及“五四”主流文学对女性出走以后“不是回家,就是堕落”的预设结局。
第三,小说安排女性人物“从港到沪”、“从沪到港”以及来回沪、港两地的离家路线都是必然的布局;三位上海作家要替自己的城市寻找一个互相参照的地方,香港是不可更易的选择。大概作家批判城市,需要一个文学形象和价值体系相对不同的地域作为比较对象,这是京派文人写上海的方式。作家意欲探索自身城市各种流动可变的形象和特质,就需要一个“相近又相异”的城市作为参照。三篇作品均以香港为参照(反衬、平衡对照、重叠书写)进一步探讨上海,当中对南国小岛横跨30至90年代的描述,都透露作家在探索、描绘“他者”的同时,如何反身定义自己的位置。叶灵凤站在急速现代化都市化的上海,怀念都市发展过程中未完全丧失朴素自然的香港;张爱玲着意描述不同审视目光下的香港和白流苏,因为她一直意识到自己以及所属城市(上海)处于中、西夹缝的位置;王安忆细写浮世男女“虚中有实”的情感,同时指向沪、港两个繁华城市里沉实人生的一面。
注释:
①“五四”文学描写女子出走的结局,可简化地归纳为四种模式:回家、堕落、牺牲和遗憾终生。第一及第二种结局模式为历来学者讨论最多,它们基本切合鲁迅在1923年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的讲演中为娜拉前途所作出的预示。《伤逝》是表现女子出走后只有“回家”这条出路的典型例子,而曹禺的《日出》则是以文学形式实现了鲁迅对“娜拉走后”另一结局的预示。“娜拉走后”的第三种命运以牺牲作结。女主人公离家后仍受困于两种爱情(母子之爱和男女之爱)、两种婚恋(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之间,最后以死来表现“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反抗精神,冯沅君的《隔绝》是为代表。愿为自由(恋爱)牺牲的女主人公一直保持着启蒙者的姿态,甚至具备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第四种女子出走的结局模式:放弃家庭以成全个人事业和精神的追求,获得成功却终生遗憾。凌叔华和陈衡哲笔下的绮霞和洛绮思,分别走上相同的道路。由此观之,“五四”文学推想“娜拉走后”的故事及其结局模式有两方面的共通点。第一,女主人公面对的困局,基本是由“家”和“社会”或“家”和“精神世界”的对立所造成。第二,“五四”文学中女主人公的“出走”并非迫不得已的抉择,她们都是在“平庸的幸福”以外别有所求。子君出走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陈白露对自立生活的辩解(“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绮霞对家庭和事业的理性考虑(“想组织幸福家庭,一定不可以继续琴的工作,想音乐的成功必须暂时脱却家庭的牵挂”),不同程度上都表现了女主人公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和个性解放。这里所论“娜拉出走”几种写法,其实都符合了“五四”文学传统里唤醒群众和疗救社会的基本精神。参考鲁迅:《伤逝》,《鲁迅全集》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页112;曹禺:《日出》,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曹禺》上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页208;冯沅君:《隔绝》,《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2;凌叔华:《绮霞》,《凌叔华文存》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42页。
②“场所”(locale)的概念是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讨论社会“结构化”(structuration)时提出,他尝试将空间概念作为研究人类生活模式以至社会形成的结构因素。按其说法,“场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有严格疆域分界的区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场所的不同方法,就直接决定它们的特征。“只有当观察者认识到,一座‘房子’是具有一系列其他特征的‘居住场所’,而这些特征都是由人类活动中利用这间房子的方式所限定的,这间‘房子’才会被当作‘房子’来把握。”近年学者特别注意到文学作品描述的居住场所与小说人物活动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是典型例子。参考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6~207页。
③叶灵凤在小说开首描绘的鲤鱼门景色,是凭藉1929年第一次来港小住的体验,其描绘与侣伦的回忆亦多有相合。参考侣伦:《故人之思》,《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第128~130页。
④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79~480、514页。
⑤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516页。
⑥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516页。
⑦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508页。
⑧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500页。
⑨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193页。
⑩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11)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195页。
(12)当范柳原向白流苏表示自己向往精神恋爱,并要求她能多了解自己,白流苏“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缓缓垂下头去。”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10页。
(13)张爱玲:《第一炉香》,《第一炉香》(香港:皇冠出版社,1995年第十一版),第34、32、42页。
(14)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30页。
(15)王安忆:《香港情与爱》(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05~106、170、106页。
(16)当范柳原在电话中直道出白流苏“以为婚姻是长期卖淫”的想法,她立即感到被侮辱,“不等他说完,拍的一声把耳机掼下了,脸气得通红。”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16页。
(17)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137、166~167页。
(18)大概王安忆是以上海“公寓”的概念谈论香港的租住房子,而香港人说的“公寓”却另有所指。
(19)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原载《解放日报》,1993年3月。
(20)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31页。
(21)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5、15、103页。
(22)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72页。
(23)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39~42页。
(24)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97页。
(25)“睡在人家的公寓里,有一种漂泊的味道,这是比酒店还要漂泊的漂泊。酒店的漂泊是名正言顺的,人家公寓里的漂泊则带有遭遇的意思,是漂泊中的漂泊。”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75~76页。
(26)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90页。
(27)值得注意,叶灵凤于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到广州,1938年广州失陷前夕才到香港,自始在港定居。故其三部作品《时代姑娘》(1933)、《未完的忏悔录》(1934)和《永久的女性》(1935)均发表于作者来港定居以前。至于穆时英则在1938年和家人及朋友从上海撤退到香港,翌年回上海。故此,《公墓》(1932)、《Craven“A”》(1933)、《五月》(1933)和《第二恋》(1937)同样发表于作者南来避战以前。
(28)历来学者讨论叶灵凤与香港的关系,多集中在1938年他来港定居以后写作的香港掌故,其中以《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和《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为代表。叶灵凤正式离开上海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以后的事。当时《救亡日报》(夏衍主编)南迁广州,他随行并参加编辑工作。宗兰回忆叶灵凤其时“人在广州,家在香港”,“周末有时去香港看家人,一次去了香港回不了广州,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度过了整个的下半生”。可见叶灵凤没有预期定居南国,但又随遇而安。参考宗兰:《叶灵凤的后半生》,载叶灵凤:《读书随笔》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2页。
(29)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94页。
(30)文学形象学以为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异国形象,都是“社会的集体想象物”(Social imaginaries),它能揭示作者及其所属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和文化环境里的意识形态。与叶灵凤年代相近的穆时英,在小说《第二恋》开首描写的香港就呈现相近的面貌:“在透明的,南方的青空下,它戴了满山苍翠的树木和明朗的白石建筑物,静谧地浸在乱飞着白鸥的大海里边。”至于误解,《时代姑娘》写秦丽丽父亲因为香港小报对她不利的报导,曾多次去信催促她回港交代事情。曾有小说读者去信叶灵凤,指出当时“上海与香港之间是不通快信的”。参考穆时英:《第二恋》,《穆时英小说全编》(上海:长林出版社,1997年),第536页;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73页。
(31)小说曾直接论及“上海东西的式样比香港新得多”,而女性的时装款式亦以上海为尚。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88、508页。
(32)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530、567页。
(33)《时代姑娘》提及上海大量的消费娱乐场所,包括中国饭店、东方饭店、冠生园、新雅酒楼、沙利文咖啡座、文艺复兴咖啡座、辣飞花园(舞厅)、跑马厅、新光戏院、国泰大戏院、永安公司、祥生公司和德茂时装公司等等。
(34)叶灵凤形容香港平静的生活是“宋皇台偏安之局”,乃针对当时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而言。参考侣伦:《故人之思》,《向水屋笔语》,第131页。
(35)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80页。
(36)小说曾多次描述故事人物讨论当时国内不稳定的局势,例如:“政局恐怕又要有变动了”、“汕厦一带的海面或许会发生冲突”、“上海此刻表面上虽已经平静,可是四伏的危机却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参考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87、499页。
(37)叶灵凤:《时代姑娘》,《叶灵凤小说全编》下,第476页。
(38)张爱玲:《封锁》,《第一炉香》,第225页。
(39)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第57页。张爱玲在此文中谈及“香港传奇”的七个篇章,其实只有《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是以香港为背景,《心经》、《琉璃瓦》和《封锁》都直接写沪上故事。此文刊载在《杂志》第十一卷第5期(1943年8月),其时已经发表的小说只有《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和《心经》,至于《倾城之恋》、《琉璃瓦》和《封锁》都在同年8月以后陆续发表。
(40)张爱玲:《烬余录》,《流言》,第49页。相对而言,《封锁》、《花凋》则以日军占领的上海为小说背景。
(41)正如小说中白流苏第一次在船的甲板上远望香港的心情:“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02—203页。
(42)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43)张爱玲:《第一炉香》,《第一炉香》,第45、51页。
(44)张爱玲:《烬余录》,《流言》,第48页。
(45)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28页。
(46)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流言》,第107页。
(47)参考王子平:《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年),第133~139页。
(48)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07页。
(49)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06~207页。
(50)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04~206、212页。
(51)对于被注视主体(le sujet regardé)在自觉被注视的过程中所凝聚了四个层面想象的分析,概念源自罗兰·巴特在摄影札记《明室》中对人物肖像摄影的论述。参考Roland Barthes,La Chambre claire:note sur la photographie ( Paris:Gallimard,coll." Cahier du cinéma" ,1980) ,pp.29-33.
(52)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第206、210、222页。
(53)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独语》,第189页。
(54)王安忆在散文中谈论的上海和香港,也有不少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例如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她写上海“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与她描述香港“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互有相通。又如作者描绘香港的历史及其作为“大邂逅”、“大机缘”的特质,跟她回溯上海的发展及其城市本质,都可互相比附:“四百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鸦片战争一声枪响,降了白旗,就有几个外国流氓,携了简单的行李,到了芦苇荡的上海滩。……然后就有一群为土地抛弃或者抛弃了土地的无家可归又异想天开的流浪汉来了。他们都不是好好的、正经的,接受了几千年文明教养的中国农民,他们一无所有,莫不如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来试试运气。……上海是一个机会的世界,一夜之间,富人可以变成穷人,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参考王安忆:《“上海味”和“北京味”》,《漂泊的语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89—397页;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独语》,第187~189页。
(55)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独语》,第189页。
(56)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163页。
(57)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13页。
(58)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43~44页。
(59)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142页。
(60)王安忆:《香港情与爱》,第71~72、90~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