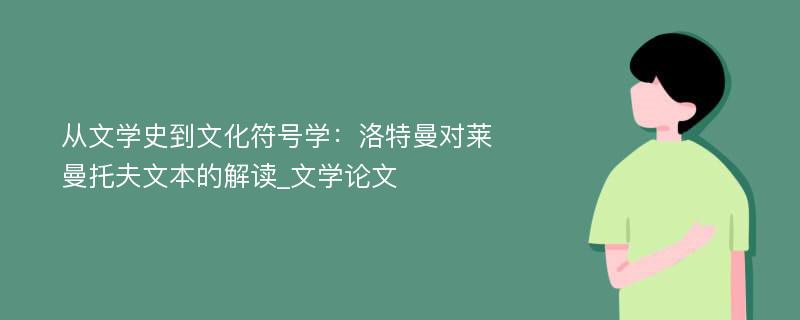
从文学史到文化符号学——洛特曼的莱蒙托夫文本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文学史论文,托夫论文,洛特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尤·米·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1922-1993)是俄苏著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和文化学家,享誉世界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创立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其文章与著作总数合计超过九百五十篇册。作为俄苏符号学的集大成者,他将“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精神、艺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现象均纳入其考察的范围,进行了深入的、别具一格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学术遗产;而其“广泛的研究兴趣、宽广的学术视野、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颇强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研究成果”[1](26)亦成为当今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语资源。 时至今日,作为一名符号学家的洛特曼早已闻名遐迩,但其曾经的文学史家身份却似乎被选择性遗忘。洛特曼最初就是以一名文学史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的,而后才在对方法论的反思中逐步完成了从历史到理论的华丽转身。 洛特曼早年曾从师于著名的俄国文学专家古科夫斯基教授,在导师的影响下,洛特曼早在大学时代就显示出了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浓厚兴趣。对于这一在俄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时期的学术兴趣伴随了洛特曼终生,卡拉姆津、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亦由此成为其最为关注的作家。相较于其他三位作家,洛特曼有关莱蒙托夫的著述数量并不是最多,但其所显现出的理论前瞻性与实践操作性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文将洛特曼的莱蒙托夫研究置于其由文学史至结构诗学乃至文化符号学这一学术思想演变历程之中进行观照与解析。 一、前符号学阶段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是洛特曼学术生涯中的“前符号学阶段”,这一时期他专注于文学的思想史研究,对文本的解读与其说是文艺学式的,不如说是历史学式的。正如西方学者舒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洛特曼的“前符号学著作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政治舞台的文学,其主旨在于区分作者的思想与决定时代面貌的社会思潮”。[2](177)在黑格尔哲学美学思想的指导下,洛特曼在对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中,力求揭示文学的社会属性,探索艺术因素与思想因素的统一,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莱蒙托夫研究当中。 《一本有关莱蒙托夫诗歌的书》(发表于《文学问题》1960年第11期)一文是洛特曼所有莱蒙托夫相关论文中较早的一篇。该文是为马克西莫夫的《莱蒙托夫的诗歌》一书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不仅对全书的得失做了公允的点评,还特别指出当时苏联的莱蒙托夫研究与普希金、果戈理和列夫·托尔斯泰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并非是对某篇作品研究的不足,而是体现在对作家“世界观、思想演变、创作方法的最根本问题”[3](772)的研究上。 次年,洛特曼又在《国立塔尔图大学学报》总第104期(1961)上发表了一组题为《文学史札记》的论文,其中有两篇短文《莱蒙托夫:有关〈哈姆雷特〉的两处联想》(《文学史札记》2)和《源自叙事诗〈童僧〉的注释》(《文学史札记》3)是专门探讨莱蒙托夫创作问题的。前者论述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莱蒙托夫的剧本《假面舞会》和抒情诗《诗人之死》的影响;后者则不仅对《童僧》中童僧与雪豹搏斗的场面描写和雨果的小说《冰岛凶汉》中冰岛凶汉与狼搏斗的场面描写进行了比较研究,还分析了普希金的叙事诗《塔齐特》对《童僧》的影响以及这两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作者文明观的差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特曼在《源自叙事诗〈童僧〉的注释》一文中对艺术作品中的“情节与文本迭合(сюжетное и текстуалъное совпадение)”问题所做的探讨。在他看来,情节与文本迭合通常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借用(заимствование)”问题,更多的则是作者“自己的特有的创意与已知的文学范例的论战、排斥与对抗”,实则体现了“作者艺术创意的独特性”。[3](546)有时,“情节的相近性”甚至“揭示了作者立场的深度分歧”,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识的论战”。[3](547)洛特曼有关情节与文本迭合问题的观点与法国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于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互文性理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是由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4](40)的,任何一个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其他文本,每个文本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他文本,共存与派生构成了两种互文手法类型。洛特曼在此虽未使用“互文性”一词,但其早在60年代之初便已触及这一问题的实质,不仅显现出了其超常的学术敏感度,也预示了其日后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走向。 此后,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文学中“托尔斯泰派”的起源》(发表于《国立塔尔图大学学报》总第119期,1962年)一文中,洛特曼通过对《童僧》等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思想特质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文学中不仅存在着一条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果戈理及此后的自然派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主线,同时,还具有一种所谓的“托尔斯泰式”倾向,即“对宗法民主制与自由劳动者的向往、对文明与现代社会体系的厌倦和对理想和谐的宗法生活的艺术再现”。[5](10)而这一“托尔斯泰式”倾向在莱蒙托夫的后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结构诗学阶段 1964年洛特曼《结构诗学讲义》的问世标志着洛特曼结构诗学的诞生。由此乃至整个70年代都是洛特曼符号学思想与方法的确立与表达阶段。文本概念自此不再仅仅具有“语文学研究的客体”意义,而成为符号学的一个关键术语。“文本是符号活动的结果与产品,是语言、艺术、文化的作品。”正是藉由文本的概念才确立起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化不是某种静态的、共时存在的整体”;它是“由对抗的文本构成的,这些文本即使处于不同的文化层面,也在不断的相互影响与冲突中”。为此,需要对“文本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各种类型的文学文化中区分文本的功能,描述文学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文本功能更替的动态性”。[6](8)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洛特曼开始着手对文本进行专题性分析,写出了《诗歌文本分析:诗的结构》(列宁格勒教育出版社,1972)一书。这部专著成为洛特曼结构诗学领域又一代表性成果。如果说《结构诗学讲义》偏重理论性,那么《诗歌文本分析:诗的结构》则更加偏重于“诗歌的结构分析”[3](24)实践。在这本书中,洛特曼不仅多次引用莱蒙托夫的作品来阐述诗歌文本结构分析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还辟有专章对莱蒙托夫的《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不,我强烈地爱着的并不是你》等爱情诗的语义结构进行了分析。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一诗虽然看上去只有寥寥数行,但其“语义结构”却颇为独特。诗中“浪漫主义系统”成为“打造莱蒙托夫文本概念内聚力的独特个性的背景”与“艺术语言”,具体而言,即诗中“‘我’和‘你’的特殊关系”构成了“该系统的语义中心”。“人的浪漫主义概念源自人的自然性、隔绝性、摆脱一切尘世束缚等理念”,“抒情性的‘自我’与生俱来的孤独既是对其独特性和脱俗的奖赏,同时又是诅咒,注定了其被放逐、不被理解”的命运,也“注定了其身上的恶与利己主义”。“试图冲向另一个‘自我’、渴望被理解、渴望爱情、友谊、与人民建立联系、对后辈的呼吁”与“类似接触的不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情节的张力”,实际上,这种接触“意味着丧失‘自我’的独特性”,也“消解了构成了该文化类型的基本对立”。 在“浪漫主义的爱情图示”中爱情意味着“欺骗、背叛和不理解”,而“对俄国浪漫主义传统来说”爱情则通常意味着“分离”,但是此外也还是存在“另外一条途径”,即“无法冲破爱情中不被理解的界限与悲剧性的、现实的爱情一起,创造了一种理想型的爱情渴望(любовъ-стремление),在这种爱情渴望中,客体并未被赋予独立个性,这并不是另外一个‘自我’,而是对我的‘自我’的补充,一个‘反自我(анти-я)’。‘反自我’被赋予了与‘自我’相对立的特点,即抒情性‘自我’是悲剧性的,是支离破碎的,而其爱情对象却是和谐的,‘我’是恶的,自私的,而‘她’是善良的,‘我’是丑的,而‘她’是美的,‘我’是恶魔,而‘她’是天使、女神、纯洁的少女。”“作为与‘我’完全对立的形象”,其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我的补充,我的理想异在(инобытие),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联系的”,爱情也由此摆脱了肉欲色彩。[3](163-164)既然“一切现实的爱情”中都存在着“对理想精神异在的渴望”与其“终极尘世体现”之间的矛盾,浪漫主义就把“爱一个女人实际上就是爱她身上的其他某些东西”这一“古老的文化母题”解读为“你爱的并不是你爱的那个人”,相应地就产生了“积极的功能性替代行动(акт замены)”,“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所替代,现实的女人被无法实现的梦想、昔年的幻想所替代,一个女人被其礼物或肖像所替代。”[3](165)由此形成了“我——你——替代者”之间在莱蒙托夫作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一诗中,“我——你——替代者”之间的矛盾被诗人消解,“‘我’和‘你’迅速被平衡并结合为‘我们’”。如果说“‘我’和‘你’处于分离状态”,二者在文本中的“替代者”——“我的胸口”和“你的肖像”——“在文本中则结为一体”。[3](168) 1975年,洛特曼又在《俄罗斯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莱蒙托夫的一处引文》,从“诗歌引语的心理”[3](756)角度对《诗人之死》进行了分析。洛特曼注意到诗中第三诗节中在韵律上与前面两个诗节完全不同,其中的“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歌唱的人”这一诗行,无论在词汇上,还是在韵律上,都是引用自巴丘什科夫1818年创作的书信体诗歌《致沙里科夫的大作》中的诗句“如同被他用这么有力的诗歌歌唱的/普希金的主人公一样”。在莱蒙托夫的诗中,“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歌唱的人”指的是《叶甫根尼·奥涅金》的连斯基,“他”指的是普希金。而在巴丘什科夫的诗中,“普希金”却另有其人,指的是普希金的叔叔瓦西里·里沃维奇·普希金,他也是一位诗人,而“主人公”指的则是《危险的邻居》中的布亚诺夫。事实上,莱蒙托夫只记得巴丘什科夫诗中的这两句,而这两句诗又在他的意识中发生了错位(сдвиг),于是连斯基就取代了布亚诺夫。在此,洛特曼不仅从“联想(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的心理”[3](757),还从诗歌的结构与语调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任何一个引语或联想从一个艺术文本迁移到另一个艺术文本都是经过了十分复杂的接近与排斥、语义迭合与错位等途径。”[3](758) 三、文化符号学阶段 进入80年代,在文化符号学领域游刃有余的洛特曼不仅依然保持着对文学史的浓厚兴趣,还赋予了这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以独特的符号学色彩,甚至将其最终涵盖于符号圈理论之中。他富于创造性地将符号学方法应用于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文学研究之中,在其8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有关莱蒙托夫研究的著述中,即充分展现了这一重要的思想演变轨迹。 洛特曼的《米·尤·莱蒙托夫(诗歌分析)》是与涅维尔季诺娃合著的《教师用书:9年级文选教科书教学法材料》(塔林瓦尔古斯出版社,1984)中的一章。作为教师参考书,洛特曼选取了《天空与星辰》、《被俘的骑士》、《在荒野的北国》、《梦》、《我一个人独自上路》等多首名作,从修辞学、主题学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诠释与解读,例如对《天空与星辰》中的反讽与同语重复、《被俘的骑士》中的隐喻、《在荒野的北国》和《梦》中孤独主题的分析等。 1988年问世的洛特曼的《在诗歌词语的学校: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莫斯科教育出版社)一书收录了《莱蒙托夫的诗歌宣言(〈编辑、读者与作家〉)》、《〈宿命论者〉与莱蒙托夫创作中的东西方问题》这两篇论文,鲜明地体现了洛特曼从结构诗学到文化符号学的转向,堪称洛特曼的莱蒙托夫研究代表作。 《编辑、读者与作家》创作于1840年,是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前一年的作品,在其晚期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莱蒙托夫历来吝于言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学生活”,但在这篇作品中“却表现得不仅像个诗人,更像一名批评家与辩论家”。[3](530)洛特曼在艾亨鲍姆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家”、“读者”和“编辑”的形象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了更加深人的思考。“编辑”之“庸俗”成为了“读者”的“批评对象”,而“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虽然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却都看到了当时俄国文坛之弊病,即“缺乏真实与素朴”。[3](531)洛特曼指出“作家”在诗中三次发出了“写什么”的疑问,他认为莱蒙托夫其实是借“作家”之口探讨了“在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尚属十分尖锐的文学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权力、恶的本性及文学中恶的描写原则等问题”,[3](533)“作家”的话语中呈现出了“诗歌世界的结构”,即“由天上的形象与声音构成的美好却是乌托邦的世界、被诗人归于未来的和谐世界与铁一般的诗篇打造出来的冷酷残忍的世界”。[3](541)洛特曼认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特点”即在于“批判精神与乌托邦主义”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交织在一起,果戈理、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等人的创作都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既不否定所处现实的可怕面目,也不否定在艺术中对其进行公正描写的必要性,他们要求的仅仅是这个世界是被高尚的乌托邦幻想所净化过的”。[3](539-540)莱蒙托夫如“先知”一般预言了“呼唤将批判性与乌托邦性结合在一起”的“作家”的“悲惨境遇”,甚至包括果戈理将手稿扔进壁炉的悲剧。但是,这篇作品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作为“对俄国文学来说在类型学上极为典型的传统的源头”,它“向艺术提出了崇高要求,其中包括那些艺术手段无法企及的直接改变生活的要求”,[3](541)日后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也证实了莱蒙托夫见地之深刻性与超前性。 《〈宿命论者〉与莱蒙托夫创作中的东西方问题》最早曾以《莱蒙托夫后期创作中的东、西方问题》为题被收录于《莱蒙托夫论文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5)中。这篇论文主要探讨了莱蒙托夫的东、西方文化类型观,折射出了洛特曼由结构诗学到文化符号学的转向,堪称洛特曼在莱蒙托夫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洛特曼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东方主题与东方文化形象一直贯穿于莱蒙托夫创作始终”,这既有浪漫主义自身创作倾向的原因,亦是由“19世纪30-40年代东方问题在俄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莱蒙托夫本人开始被西方文化类型与东方文化类型以及与此相关的两种文化的人的性格所吸引”。[6](605)洛特曼将莱蒙托夫的创作归纳为三种“类型学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差不多是平行发展起来的,它们与第三种模式的分界点为19世纪30年代中期。 第一种模式为“过去——现在——将来”,即“莱蒙托夫艺术世界的中心人物位移至过去(其外表的悲剧性利己主义特征被淡化,而审美英雄主义则被强化),被讽刺性描绘的渺小卑微的人群的形象被确立为现实,而‘天使般的’形象被赋予了乌托邦色彩,并被归为人类历史的起点与终点。”[6](605-606) 第二种模式为“来自民众的人——来自文明世界的人”。莱蒙托夫在较早的创作中曾将来自民众的人“等同于恶魔式主人公”,此后又将其定位为与恶魔式主人公“对立的‘普通人’”。 第三种模式源自“莱蒙托夫对俄国历史命运的思考”。“俄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既与西方对立,又与东方对立。俄国在这一类型学意义上就获得了北方的称谓,并与前两种文化类型构成了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与二者对立,另一方面,对东方来说它是西方,对西方来说它又是东方。”[6](606) 莱蒙托夫认为俄国欧化的结果是俄国这一“年轻文化”染上了“衰老文化”的“怀疑、彷徨与过度反省”等“弊病”。莱蒙托夫区分了“其所处时代的俄国社会中存在的几种文化心理类型:第一类是心理上比较接近普通人的类型,如‘高加索人’类型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第二类为欧化的无知者,如上流社会和格鲁什尼茨基,第三类是毕巧林类型”。洛特曼通过对《宿命论者》等的研究,揭示了毕巧林类型的复杂性。首先,毕巧林的欧化不仅体现于“其置身于欧洲浪漫文化巨人的世界,即拜伦与拿破仑的世界”,也体现于其所处的“已经逝去的、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历史时代”。[6](611)其次,毕巧林是“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欧化文化的人”,这就决定了其“性格的矛盾性,这其中也包括敏感性,在特定时刻作为‘东方人’及兼容不相容的文化模式的能力”。[6](614)最后,19世纪30年代日趋尖锐的波兰与高加索问题也被莱蒙托夫纳入到“俄国——西方——东方”这一“类型学三角”之中。“俄国的欧洲人”毕巧林“在深层意义上”正处于由“波兰(具体的西方)——高加索、波斯(具体的东方)——人民的俄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走私贩子、高加索人、士兵)”构成的“文化空间”之中。此外,洛特曼还将莱蒙托夫对“文化类型学问题的兴趣”以及对“历史上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的思考等问题置于文学史背景之中予以考量,勾勒出了“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勃洛克”这两条俄国文学发展脉络。[6](617) 与妻子明茨合作完成的《论莱蒙托夫的诗〈帆〉》(《塔尔图国立大学学报》总第897期,1990年)是洛特曼有关莱蒙托夫研究的收官之作。洛特曼称该文是“对《帆》的空间结构的文本研究试验”。诗中“每一个诗节的前两个诗行与后两个诗行的对置反映了‘物理空间’(第1—第2诗行)与‘评价空间’(第3—第4诗行)的对照”。[3](549)全诗共有三个诗节,每个诗节中都是通过“变换的评价取代变换的客观场景”,从而最终“打造出了总体结构的复杂性与整体的动态矛盾语义”。[3](552) 纵观洛特曼的莱蒙托夫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对其作品文本的解读与诠释方面,这从相关论文的名称上即可窥见一斑。洛特曼将莱蒙托夫研究置于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之下,置于结构主义与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审视之下,其研究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更具有文学理论意义,值得我国学者对其进行深度思考与多层面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