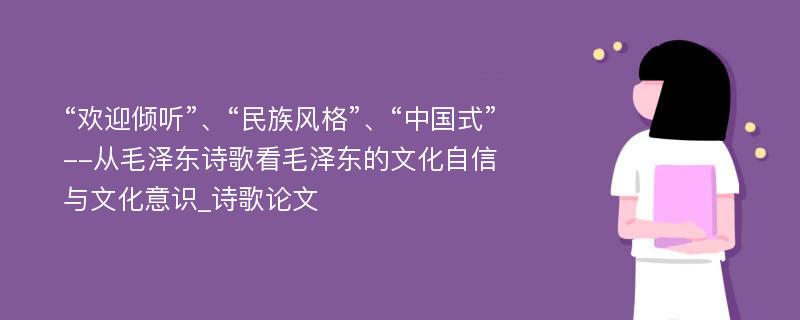
“喜闻乐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闻乐见论文,气派论文,中国论文,诗词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长期以来,毛泽东诗词以史诗合一的史诗品格和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等艺术风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这种风靡当年还有很多非诗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36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宾馆大堂和亿万人民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详的普及程度论,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代表作,基本上和“举头望明月”这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达到了同一级别。显然,这就要归功于毛泽东诗词本身的艺术魅力了,这也是政治淡出、文化凸显的一个结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约20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问题是人们都自自然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似乎天经地义,本该如此,却忽略了反向思考,比如从来就少有人设想过,如果毛泽东写新诗又会如何?_毛泽东为什么钟爱或者说选择了格律诗词这种古典形式?这是妙手偶得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所周知,新诗进入中国100年以来,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找到了新的资源,融入了新的元素,反映了新的生活,开出了新的生面。这100年,实际上也是新旧体诗暗中较劲和比赛的100年。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不停地此消彼长,但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时间都采取了不争论主义,各写各的,只做不说。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以他的襟怀、气度、魄力和眼光,对各种文化自然是兼容并包,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具体在新旧体诗的问题上,他老人家倒是终其一生钟情于古典诗词,并且身体力行,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而且还在上个世纪50年代集中思考并三次公开发表了他支持古典诗词的看法。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新诗发表的臧否意见是以半开玩笑的形式说的:“我是不读新诗的,除非给200块大洋。”
据多种资料载,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新诗发表的臧否意见是以半开玩笑的形式说的:“我是不读新诗的,除非给200块大洋。”这句话横空出世,前后语境也不可考,似乎是个孤证,据此就断言毛泽东否定新诗显然述缺乏说服力。但我们不能光听其言,还要察其行。据海外著名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1977年撰文研究“发现”,毛泽东《沁园春·雪》曾受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一词影响。胡词作于1917年4月17日夜,所咏实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发表于1917年《新青年》三卷四号,1920年3月又收入《尝试集》中。而青年毛泽东当时正是《新青年》和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此为毛亲口与斯诺所言),更何况胡词是热烈歌颂新俄革命的呢。据此,周策纵先生认为,毛必受胡词感动很深,故19年后用同一词调咏雪,而且其主题“雪”以及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即涉胡词开头“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句转变而来。毛词“千里”、“万里”也可能受了胡“一万里飞来”词句暗示。如此等等,言之凿凿。(参见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见唐德刚《胡适杂忆·附录》)
当然,毛词是否如周说,如此深受胡词影响,我并不认同。虽然周文也并无恶意,只是指出诗人创作间的一种相互联系与发明,更何况,毛诗创作历来转益多师,直接取自“三李”的诗句都并非个例。恰恰是周文这个研究心得我能接受,即毛氏《沁园春》在创作上受到胡氏《沁园春》一定的启发。因此,我就有了一个比较,当年胡适作为青年毛泽东崇敬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兼新诗第一大诗人(他的《尝试集》早于郭沫若《女神》一年出版),毛却对他大量的新诗视而不见(试想,像《两只蝴蝶》,像68首新诗中以“了”字结尾的诗句就达101句,这怎么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唯独一首《沁园春》却令毛泽东惺惺相惜,20年不能释怀。无独有偶,还有一个郭沫若的情形与此相类。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新诗泰斗又兼旧诗大家,与毛以诗友身份过从甚密。但终其一生,毛对其公认的新诗领袖地位和突出成就未置一辞(试想,像《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像“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怎么得了,又如何入得了毛的法眼?)却以旧体诗词乐此不疲地相互唱和了大半辈子。毛泽东号称“不读新诗”,恐怕最初就根源于对胡、郭的早期新诗印象。仅此两例,也足以看出毛泽东诗歌的取向了。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还是两首《沁园春》的比较,从比较中得出早年毛泽东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在师承与借鉴上,完全听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修养引领,下意识地就走上了一条亲古典而远现代的必由之路。说“下意识”,是说他当时还无意也无瑕于新旧诗的优劣长短之比较研究,只是跟着感觉走,用自己喜爱的形式,写自己想写的而已;说“必由之路”又分两点:一是先天的,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古典诗文对他的浸润与生俱来,深入骨髓;二是后天的,即戎马倥偬中的“马背诗人”更便于推敲凝练精短易记的格律诗,而难于抒写形式散漫、不拘平仄押韵的自由诗。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第二次对诗歌公开发表意见是在1957年,他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过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是他的表层意思,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他自己亲口对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给臧的信,笔者注)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见《毛泽东与梅白谈诗》,载《文摘周报》1987年3月26日)。大家知道,给臧克家写这封信,起因是《诗刊》要一次集中发表15首毛泽东诗词(具体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七律·和柳亚子》《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应该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地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此后还有两次分别是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词6首,以及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总出版的37首作品的《毛主席诗词》),而且这15首作品中除了“和柳亚子”的两首略逊之外,基本上都堪称是毛诗中的上品。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他的诗作影响也口碑日隆,一个大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为一种风尚。但恰是这一点又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忧患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在内心深处,正如他亲口对梅白所说,“一万年也打不倒!”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强大自信,同时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准的清醒定位,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坚定而真实的诗歌理念,也是支撑他一辈子笔耕不辍直至八十高龄还反复修改诗作的文化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历史主人公,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也理所当然是新文化的主要表现和服务对象。因此,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必须的。具体到诗歌而言,民歌是最接地气的地域文化和乡野文化的韵文化表达,来自百姓又为百姓喜爱,大可借鉴和学习。
毛泽东第三次也是最正式地对诗歌公开发表意见是在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期间。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的马拉松会议,前后开了一个月。但自始至终毛泽东心情愉快,多次在会上作长篇讲话,还兴致盎然又别出心裁地给与会中央委员印发了如《蜀道难》(李白)、《咏怀古迹五首》(杜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等历史上大诗人写四川的诗,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AI写作。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一次大会讲话中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799页)。
如果说前两次毛泽东还是以个人或诗人身份谈论诗歌(无论是口头揶揄新诗还是书面挑剔旧诗)的话,那么,1958年这一次则大不相同了,一是形式不同了,在党中央的正式会议上作正式讲话;二是身份不同了,以领袖名义郑重“指出”:“第一条、第二条……”毋庸置疑,无可商量。很显然,这决非他老人家心血来潮的信口开河,而恰恰是自1957年以来结合他自己的创作经验及多方回馈而深思熟虑又高瞻远瞩地得出的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明晰结论:形式是民族的。而它的基础“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毛泽东看来,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历史主人公,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也理所当然是新文化的主要表现和服务对象。因此,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必须的。具体到诗歌而言,民歌是最接地气的地域文化和乡野文化的韵文化表达,来自百姓又为百姓喜爱,大可借鉴和学习。为此,毛泽东不仅做文章极讲求明白晓畅,要像鲁迅一样“多用口语”,就更“神气”。作诗亦如是,一是少用典,去深奥(除早期的《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等几首抒发个人友情、爱情的诗作用典较多之外,此后作诗基本不用典了);二是多口语,更鲜活。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等等。不胜枚举,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我常说,毛泽东一个人看似在不经意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中国古典诗词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毛诗创作是有明确理念与追求的,而且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仅从形式上看,古典诗词的凝练隽永、短小精悍,整齐押韵、铿锵跌宕,把建筑美、音韵美集于一身,它不仅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与习惯,也符合整个人类的审美习惯与吟诵和记忆规律。往大里说,有唐诗宋词历经千年而传唱不衰有口皆碑,往小里说可举中国歌剧为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歌剧新作迭出,但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标志就是有唱段广为流传)我个人认为不过5部:《刘胡兰》、《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而这5部歌剧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唱词的民族化(当然也包括音乐的民族化),当然,这个民族化指的就是毛泽东说的“民歌”加“古典”的大体整齐押韵的歌行体或新民歌体。而与之不同的“外来体”歌剧,题材、主题可能不错,但歌词太不讲究对仗、韵脚,一味自由散漫、长短不拘(如宣叙调、咏叹调之类),结果往往是湮没无闻,甚至自生自灭了。于此我还想到自己年轻时有过10年学习写诗的经历,曾经下功夫背过“三李”“苏辛”,也背过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惠特曼、歌德、普希金、泰戈尔,甚至艾青、徐志摩。而今30年过去了,前者还略有记忆,后者充其量只剩得一鳞半爪了。由此观之,表面看来,民歌加古典创化出来的民族形式,一是便于接受,流传广泛;二是便于记忆,影响深远。而再往深里看,恐怕还有一层,那就涉及汉字及汉字思维了。由于汉字结构的独一无二的象形与会意,常常造成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比如一个“明”字,左日右月,我们一看到它,首先想起一个太阳,然后又想起一个月亮,太阳加月亮,当然大放光明,三重形象叠加,何其丰满、充盈、生动)。早在1908年,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就曾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所造成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最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转引自郑敏《一场关系到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诗探索》1996年第4期)并对此“汉字思维”特点惊叹不已——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问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本土出发,游学多年,在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终的选择是回归传统。
其实,百年以来,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华士子们也始终没有停止比较、探索与选择,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当然,他说的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大家,经、史、子、集、儒、释、禅,无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来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可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体西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身“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也曾先后留学英美,也曾迷恋过艾略特和罗伯一格里耶,但当他们回到台湾后,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余光中还专门为此撰文,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台湾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这又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说明了他们“好古”或“守旧”?或者说明了中华文化的惰性和强大的惯性,难道不可能或者更可能说明了恰恰是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本土出发,游学多年,在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终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如果再收缩到诗词创作的范围来看就更说明问题了。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样,开国元戎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古体诗的爱好者与大作手。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很多领导和将领。同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当然,他们都是旧瓶装新酒,以旧体诗反映新时代、新理念、新生活,成了此一道路上的开山与大师。他们的同道还有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聂绀弩、钱仲联、钱钟书等等。这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近、现、当代中国文化巨子的共同选择,从另一意义上说,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选择。时至今日,以发表旧体诗为主的《中华诗词》,其发行量与影响早已远远超过《诗刊》,这又可以说是代表了草根的选择。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重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描绘出的中国新文化发展蓝图三要素——“老百姓喜闻乐见”、“民族风格”、“中国气派”,说的是何等的好啊!毛泽东以他一辈子的诗词创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使毛泽东诗词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是不折不扣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典范之作!毛泽东前瞻性的诗歌——文化理念和成功实践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崛起,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