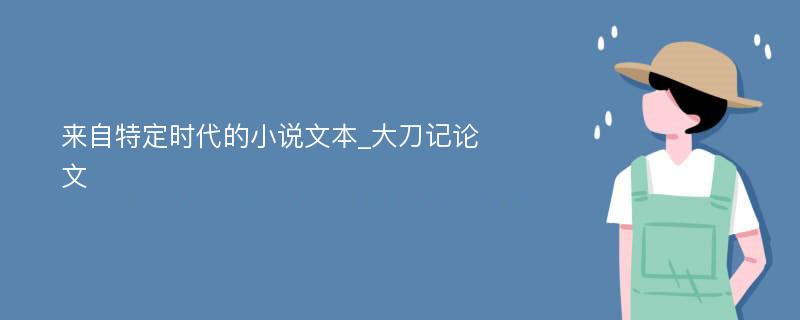
一部从特定时代走来的小说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时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56-05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出版于197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时,中国大陆出版的惟一一部反映共产党抗战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5年与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重新出版了《大刀记》。2015年,62集电视剧《大刀记》又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成为本年度影视界的重头戏。由于历史的原因,生成于“文革”中的文学作品大多被人遗忘了,而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刀记》不仅能够再版,而且还以更有影响力的视觉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两种不同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深思。诚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对于郭澄清这样一位特定时代的作家、他所在场的那样一段特定历史和他笔下的那一种文学,我们有必要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之重新认识和梳理,而不是回避。”① 作为一部特定历史年代的小说文本,《大刀记》不仅在社会政治巨变中生存下来,并在新的时代中依然保持了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攀附于时代政治之树上的寄生物,而是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吸取着富有活力的艺术之水而成长起来的生命体。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它接地气。 《大刀记》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农民革命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它的人物,还是它的叙事方式,都与《水浒传》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传》写了不同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描绘了上中下层统治者的腐败与邪恶,用“官逼民反”串起不同英雄人物的经历,而《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等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梁氏一家三代遭到地主恶霸的残害,梁永生和他的儿子也难逃厄运。“龙潭街—柴胡店—宁安寨—水泊洼—杨柳青—天津卫—兴安岭”这条长长的路线就是梁永生被逼无奈四处流落的道路,也是他成长的位移空间。在流落异乡的人生旅程中,梁永生逐渐成长,并在性格上不断发展。小说将穷人与富人的世界对立起来固然有其时代政治的影响,但梁永生与白眼狼的家仇却并非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梁永生反抗白眼狼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并伸张正义,其实也是底层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梁永生的道路也正如林冲一样是被邪恶势力逼迫的抗暴道路,所不同的是,梁永生在矿工何大哥与王生和老汉的启发下,最终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及穷人需要团结,并决定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梁永生的自发反抗道路由此引向了现代革命道路。 为了使当下的现代故事更深入地扎入民族文化的土壤,《大刀记》第一部巧妙地借鉴了《水浒传》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叙事模式,以梁永生背井离乡的生活和反抗仇人的迫害组织情节推进。《水浒传》梁山英雄们聚义后则四处征战,打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直至后来的征辽国、平方腊。这种以事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的结构为《大刀记》第二部所吸收。第二部中,梁永生领导地方武装,组织八路军大刀队,在鲁北临河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梁永生的带领和指导下,梁志勇、王锁柱、黄二愣等八路军战士迅速成长,大刀队成为地方重要的抗日武装。梁永生指挥大刀队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巧夺黄家镇、夜战水泊洼、围困柴胡店”,消灭了本地区的日伪军,获得最后胜利,这与《水浒传》后半部分的英雄悲剧基调完全不同。无论是第一部梁永生父子的抗暴斗争还是第二部大刀队群体的英勇奋战,小说的描写都是干脆利索、酣畅淋漓的,充满英雄气概。 《大刀记》还借鉴了传统小说用浓墨重彩描绘惊心动魄的故事,在细节真实上精雕细刻、在语言行动中刻画人物性格等手法,将传奇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说,《大刀记》很好地继承了《水浒传》的文学资源,并以新的时代观念和意识加以改造,重新演绎了山东英雄叙事的传统。英雄性格,反抗邪恶,伸张正义,机智勇敢,战无不胜……这些正是理想化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激情洋溢,乐观向上,顽强不屈精神的体现。《大刀记》吸收了这种传奇性和理想性的反抗斗争的书写方式,将其引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生活斗争中,赋予战争文学一种新的氛围和基调,这与小说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卡里斯玛型人物是相互依赖的。 郭澄清将《大刀记》的艺术之根深扎于《水浒传》中,显然是有着自己的认识的。小说创作于“文革”时期,受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郭澄清也不能不按照当时的文学要求突出其意识形态性。但是,他也深知,活动于他的小说世界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来自于底层的中国农民。他们饱受农村黑恶势力的欺压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自身就有着敢于反抗压迫的种子与展开斗争的因素。这种敢于抗暴的斗争精神,与《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是一致的。而且,《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成熟的叙事模式,不但对中国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小说文化和国民精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为生活于“水浒文化圈”中心的郭澄清,以其自身丰富的人生体验,深知《水浒传》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比如他在小说第一部写到主人公梁永生被迫逃到德州城时,就专门描写了他听人说书的情景。来听《三打祝家庄》的人不仅多,而且公开议论:“梁山将真是好样的!”“脚下这世道就该有这么一伙儿人!”而梁永生也听上了瘾,“方才,他的肚子里还肠子碰得肝花响,可一听入了迷,连饿也忘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刀记》出版的年代,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很大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活动,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与邓小平。而《大刀记》对梁山英雄精神的肯定与继承,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批宋江”的论调是不一致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寻常,《大刀记》才能冲破时代政治的藩篱,扎根于真实的历史土壤,成为至今也不曾被历史遗忘的抗战文学经典。 继承《水浒传》的艺术传统,努力写出中国农民身上那种不屈的反抗精神,不仅使《大刀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出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也使它在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大刀记》显然不是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单一继承,它同时也非常注重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上进行广泛的借鉴与创造,新型的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塑造,就是小说的一个新的创造。 “卡里斯玛”一词,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本意为因蒙受神恩而获得的天赋,后经西方社会学家韦伯、希尔斯等人的不断引申,泛指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感召力的特殊力量。在文学艺术中,“卡里斯玛”是指“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②。卡里斯玛型人物大致相当于所谓“圣人、英雄、先知、伟大人物、杰出人物、领袖”等等,具有象征性、中心性、神圣性、原创性、感召力等特征。梁永生正是《大刀记》中体现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他处于整个小说的中心,其他人物围绕在他周围,形成“众星拱月”的人物结构类型。由于被置于结构的中心,卡里斯玛型人物似乎总能与深厚的历史动力源相接触,显出超常的敏感、活跃甚至远见卓识。梁永生成为卡里斯玛型人物而区别于草莽英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他对革命理论的坚信不疑,对远大理想的神圣追求,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启蒙者”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实际代表了新的革命理论的“中介”,通过他们将新的思想意识传递给梁永生,逐渐改变了梁永生的性格。其中县委书记方延彬是梁永生的入党介绍人,他指导梁永生组织大刀队,并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与梁永生交流思想,从而使梁永生认识到个人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群众解放相结合。革命斗争理论和阶级解放的理想既是梁永生心目中神圣的强大历史动力,也为他提供了行为的依据和前进的方向。梁永生因此找到了自我的历史位置,走上了团结群众的革命斗争之路。他建立了地方武装大刀队,把革命理论付诸实践,开辟了新的历史活动,在临河区建立了新的规范和秩序。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卡里斯玛型人物的感召力或感染性。卡里斯玛人物具有使周围群众对自己倾心服膺的个人魅力,这种超凡的个人魅力不依靠强制而是凭借情感去建立和维持。这种情感上的巨大感染力是其他种种特征的总体的和直接的呈现方式。在小说《大刀记》中,梁永生制订行动计划及指挥作战时,并不使用强制性的命令,而是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也就是以对话的手法把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加以对比的比照法,是以对话激活引发对方发表意见的引发法。梁永生把队员们的意见汇聚到一起,通过大家友好地互相“争辩”显现各种方案的优劣,最终选出一致认可的意见。梁永生比较注重“开锁”式的思想工作,以具体生动的比喻或者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纠正群众和战士们的思想问题,使他们心服口服,从而促成行动上的统一。大刀队队员都盼望时刻与梁永生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群众把梁永生当成自家人,在他身陷困境时不惜生命保护他;甚至连敌人也在他的感化之下弃暗投明。以上种种皆表明了梁永生作为卡里斯玛型人物对周围人物的超常的征服力和巨大的感染力。他在卡里斯玛帮手和次卡里斯玛人物的协助下,教育征服非卡里斯玛人物,胜利征服作为对立面或敌人的反卡里斯玛人物。 在20世纪抗战小说中,这种富有巨大感召力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并不少见,比如《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等等。他们既具有传统英雄人物的勇敢、豪爽、富于反抗等个性,又接受了革命斗争理论的洗礼,成为那一时代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他们禀赋超凡的魅力,象征历史的进步方向,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实践,是抗战文本世界中熠熠生辉的形象。卡里斯玛型人物往往出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他们比普通人更敏锐、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历史条件,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原创力去改变历史。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③当下的中国正是一个处于转型期中的社会,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我们的时代也需要自己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来支撑新价值体系的建构。但是,“90年代以来,对于‘大历史’的强迫性遗忘在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和‘个人化写作’等为代表的文学潮流中愈演愈烈,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很难见到中国作家对于‘大历史’的有力见证或深刻反思,相反的倒是,‘大历史’冲动的严重受挫使得中国作家纷纷逃遁或龟缩于‘小历史’的把玩,犬儒主义蔓延国中,根本上支配着我们的‘大历史’力量一直被我们强迫性地遗忘。”④在解构英雄、反英雄成为潮流的文学时代,《大刀记》所留下的卡里斯玛型人物资源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启发我们重新寻找自己时代的英雄,建造现代的卡里斯玛,比如人文英雄、平民英雄等文学形象,从而整理混乱的价值体系,赋予现实更为积极合理的新的规范和秩序。 毫无疑问,《大刀记》是一部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追求的作品,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其阅读过程并不乏味,事实上,人们经常会体验到一种会心的阅读快感与审美愉悦。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郭澄清长期扎根于民间,深受民间的诙谐文化影响,制造了一种游戏性的抗战文学想象方式。 民间诙谐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俄国文论家巴赫金在谈到拉伯雷小说创作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拉伯雷的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说其怪诞的现实主义特征“是由过去民间笑文化决定的,而这种文化的雄伟轮廓是由拉伯雷的全部艺术形象勾画出来的”⑤。事实上,不仅是拉伯雷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中国作家与思想家与民间诙谐文化也就是民间狂欢节所体现的民间狂欢化文化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例如《西游记》《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故事新编》、“陈奂生系列”等作品中都有浓厚的民间诙谐文化色彩。《大刀记》也非常重视对这种民间文化资源的灵活运用,民间文化中那些有着特殊艺术效果的表现方式如夸张、讽刺、幽默等特征,经过作者的精心加工改造,被合理地吸收到小说文本中,让小说渗透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以这种狂欢化的方式来描写抗日战争,即使不是首创,也是对历史富有新意的解读。 《大刀记》对民间诙谐文化资料的借鉴吸收首先表现在反差形象的塑造上。梁永生及其所领导的大刀队,深受群众支持,他们智勇双全,与敌伪军进行游击战。大刀队利用多种方法与敌人周旋,将日伪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战无不胜,令敌人闻风丧胆。正是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建构显示了正面形象的不可战胜性。梁永生所具有的神圣性、原创性和感召力使身边的抗日军民感受到革命源泉的巨大力量,同时也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认同卡里斯玛型人物所代表的历史方向,感受到胜利最终的归属。卡里斯玛型形象的建立离不开反面形象的刻画。对于日伪军形象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凶残狡猾,更重要的是运用诙谐性的语言,将他们“丑角”的一面暴露无遗。特别是汉奸伪军色厉内荏、懦弱无能、胆小爱财的特性,他们在与大刀队战斗时丑态百出,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这群丑恶的形象,将他们滑稽可笑的一面展现出来。例如小说第二部第十七章“夜战水泊洼”,八路军和民兵将一伙伪军包围聚歼,小说这样描绘伪军的各种丑态:“还有的,把脑袋瓜子钻进了兔子窝,囫囵个儿的身子舍在外头不要了!不过,人家的大脑并没失灵!你听,他的嘴还在兔子窝里嗡嗡地叫哩,‘八路军饶命啊!八路军饶命啊!……’也有的,好像一匹受了惊的大叫驴,一面狼嗥鬼叫地乱吱外,一面连滚带爬地乱蹿跶!”⑥驴脸、蛇形身子、母狗眼、草鸡样、稀泥样等动物性、粗俗性词语的使用将敌人戏拟为物,这正是民间诙谐文化中常用的降格,即贬低化和世俗化。把凶狠残酷的敌人形象彻底颠倒过来,这种形象的瞬间急剧变化,正是一种狂欢气氛的体现。巴赫金指出狂欢节上的脱冕、加冕礼仪形式会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对敌人的这种戏谑化、漫画化描写,正类似于脱冕的仪式,它会产生一种狂欢式的笑的特征,这种笑既冷嘲热讽了敌人,又肯定了抗日军民的英勇神武。 其次是广场式的狂欢化描写。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是把狂欢节的一整套形式以及它所体现的世界感受转化为文学的语言,他说:“狂欢节转化为文学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⑦民间诙谐文化的一个基本形式就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如愚人节、复活节游戏等。小说中类似于广场狂欢节的场景和形象传达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具有节庆性、再生更新和自由平等的精神。在《大刀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广场式的描写及其背后的狂欢化精神。小说中多次写到了这种广场狂欢的场景,例如开头和尾声。第一部开头是“闹元宵”,元宵节梁宝成等穷人们组织灶火队,舞狮、高跷、秧歌、龙灯……穷人们异常兴奋,因为为富不仁的白眼狼家里正在办丧事。穷人们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普通的节日,表达了对地主的仇恨,他们在日常秩序中无法抒发心中渴求“解放”的精神,但在类似狂欢节的诸多仪式中可以尽情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恨。狂欢节象征性地表达了民众对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和潜在的反抗情绪,以及他们的变更精神和自由向往。第二部第七章“训敌”,是一个典型的群众性的狂欢场面。大刀队在坊子镇抓住伪军疤瘌四一伙,游击队员们命令伪军站成一排接受梁永生训话。周围群众听到这个消息,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人人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开心大笑,高小勇等孩子们还开起了伪军的玩笑。在这样一个狂欢广场中,民众从战争的恐怖气氛中解放出来,当看到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伪军如此狼狈,人们真正感受到了摆脱压抑的自由气息。此外,小说对战斗场面也进行了狂欢化的描写。大刀队充满昂扬的战斗激情,群众以能成为八路军战士而自豪,战争没有带给他们惊疑和恐惧,在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带领下,他们充满了革命斗争和翻身解放的激情,以饱满乐观的精神投入抗战的洪流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在伟大转折时代,在对真理重新评价和更替的时代,整个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了狂欢性。”⑧ 运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诙谐的反面人物形象以及广场式的狂欢化描写,是《大刀记》对战争描写的一种方式。小说当然不是仅从这一个维度展开战争叙事,比如也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战争的恐怖等,但小说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从阅读接受来说,我们会体会到战争的游戏性、诙谐性和乐观的基调。实际上,此类作品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比如上文提到的《敌后武工队》等,还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以及法国的《虎口脱险》等影视作品。类似的作品在残酷紧张的战争描写中给我们提供了快乐的感受,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并被其中的乐观和激情所感动,为我方的胜利而欢欣,为敌人的狼狈而捧腹,这种阅读快感是区别于其他战争小说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与民间诙谐文化在小说中的相互依赖,为战争的书写制造出一种狂欢化的文化氛围,这正是《大刀记》留下的宝贵的文学资源。 也许《大刀记》提供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究,但它对《水浒传》的英雄叙事模式的继承,对新的卡里斯玛型人物的创造,以及对民间诙谐文化精髓的吸收,都为今天乃至以后的抗战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它必将为后人所吸收利用,再创新时代的文学精品。 ①雷达:《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文艺报》2006年10月14日。 ②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③[德]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 ④何言宏:《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⑤[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0页。 ⑥郭澄清:《大刀记》(第二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⑦[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75页。 ⑧[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