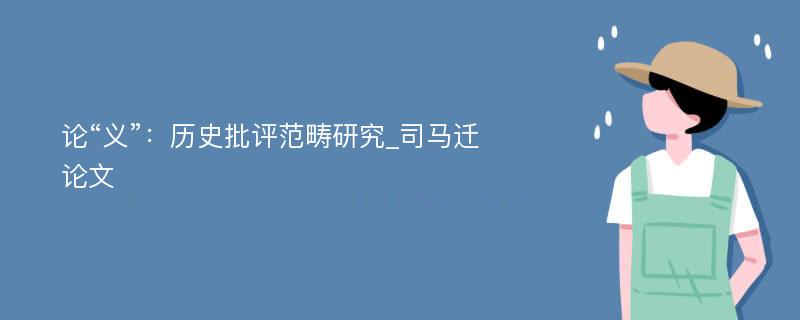
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范畴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史学批评之范畴体系中,“义”,居于中心地位。本文从“义”的解析入手,结合中国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了“义”范畴的内涵及层次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评析了历代史家关于史作如何体现史“义”的纷纭看法。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义”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历代学人在论史学时,经常要运用“义”、“义理”、“正义”、“道义”、“教义”……来表达见解。在“事、文、义”、“学、才、识”和“考据、词章、义理”这样三组相类的范畴群中,“义”范畴也居于较为中心的地位。本文试结合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一下“义”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作用。
一、“义”的解析
义,在古汉语中繁体字作“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义,已之威仪也,从我羊”。文中的“已”,当为“己”,因为从我,指的是自己。清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将“已”改“己”,云:“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己之威仪也者,仪当为义,通用仪字,本书,邈,颂仪也。释名:仪,宜也,得事宜也。”
从字形和本义上看,义通仪,指自己的威武美好状(羊大为美),又释为得事物之宜。这样,“义”的引申义就是“公正合宜”,“正义”;再进一步引申,就是“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
把本义和引申义结合起来看,就很有趣了,是否可以理解为:义,即把自我以为美好的东西,即: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贯穿于言行或述作中。我们所要讨论的“义”范畴,基本涵义就在于此。
最早从史著、史学中提出义的概念,当属孔子,见于《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段话无论在史学史上,还是在史学批评史上都是非常启迪后人的,文字虽较浅明,但思想却很深刻。第一层意思是说史著诞生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随着周王室的没落,旨在歌功颂德的《诗》也无用了,以严正笔法讥刺现实的《春秋》出现了。
第二层意思,各国史书或叫《乘》,或叫《梼杌》,或叫《春秋》,名称虽不一样,但却是同一类的史著。
第三层意思,说明了史著(也是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史著所载之事,就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业绩;将史事用文字修辞表达出来,就是史作;寓含在史作中的宗旨和观点,则是由孔子拟定和把握的。
那么,孔子在编修《春秋》时,赋予史著一种什么样的“义”呢?千百年来,无数学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然而这个问题又非辩不可,“义”就是史著之灵魂;离开了“义”,史著就是一堆无生命力的史料。弄清中国史学之开山——孔子“窃取”的“义”,当然是第一等要紧的事情。
二、“义”的侧重
对史义的讨论,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春秋》之义进行的。随着历代学者辩驳论难的不断深入,“义”范畴的内涵越来越充实,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清代四库馆臣在整理历代流传下来的、极其浩繁的注解《春秋》之书时,曾大为感慨:“《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包括《易经》,——引者注)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①a]
从蠡测《春秋》之义入手,进而探讨史学之义,历代学人主要有以下说法:
1.惩恶劝善之义
孟子不但指出了《春秋》中贯穿着孔子赋予之“义”,而且也提供了了解《春秋》之义的线索。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a]
这就指明,《春秋》是尊周王室的,是为周天子所作的编年史,其义在于讨伐乱臣贼子。《春秋》寓含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而要了解孔子,需凭借《春秋》;要加罪孔子,也同样凭借《春秋》。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体察出,在春秋战国这一“乱世”中,史家述作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还是较险恶的。礼崩乐坏,原有秩序大乱;权臣当道,可以加害于所不喜欢的史家。孔子费那么大气力修《春秋》,却又对其“义”闪烁其辞,结果要由后人来猜测阐发。其实,也不独孔子这样。楚威王傅铎椒,为了使楚威王能够通晓历史,“采取成败”,编了四十章的史书,名为《铎氏微》[③a]。“微”者,有微婉之词不便明言故也。有个姓虞的游说之士当上了赵国的上卿,故号虞卿,也写了一本史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④a]又是不能明言,只能取“刺讥”方式。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把《春秋》作为教材,在讲授时“有所褒讳贬损”,不写出来,而是“口授弟子”。弟子们过后再重说《春秋》,就造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孔子的作法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免时难”。然而对于《春秋》之义的准确传播,则是很大隐患。于是,鲁太史左丘明挺身而出了,他担忧孔子的弟子们“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此可见《左传》对于《春秋》之义的阐释是有一些权威性的。《左传》认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⑤a]又说:“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判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⑥a]
文字极简略的《春秋》,有了《左传》补充史事并阐发义旨,才使得其“惩恶劝善”之义为后人理解并发扬。四库馆臣充分肯定了《左传》对于理解《春秋》意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⑦]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司马迁承父司马谈之遗训,以著作《史记》拟孔子作《春秋》,并以当代孔子自命,因此对《春秋》之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运用很多材料和文字论说《春秋》之义时,显然也融进了自己对史“义”的理解。
他借用孔子之口概括六经各自的最主要特色, 突出了《春秋》之义,“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⑧]并指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⑨]。
司马迁对史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为推重,他对《春秋》之义的反复揭示,实质也是在阐说自己著《史记》的宗旨,亦是对史“义”的最高要求和最理想的描绘,请看他慷慨激昂的言辞: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以道义。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①b]
这不但是阐说《春秋》之义,而更是在强调《春秋》之义对于整个社会的指导作用,从普通人到君王,概莫能外。史书之义不但是理解史书的钥匙,而且也是理解历史的钥匙,还可以是指导世人立身行世的基本原则。司马迁所撰《史记》,就是本着上述意旨,取舍融铸了三千年通史,生动形象地绘出整个社会的立体图。从这幅大图画中,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君王后妃,文臣武将,隐士游侠,诸子百家;有经济政治,山川河渠,律历音乐。男女老少,客观事物,相互交织影响。个人生死荣辱,王朝兴衰替代,成败兴坏之理凿然分明。换言之,合格的史书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它不以空言教人,而是寓义旨于史事,因而能“深切著明”。
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广度的理解也超出了前人,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②b]即不仅仅是以讥刺来惩恶劝善,还有推崇圣德、褒扬周室之义。这也与他所撰《史记》有关。《史记》以推赞汉德为第一要义,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者,不可胜道。……主上明圣而德不存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b]这道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念念于心的夙愿。正因为《史记》有颂汉之义,所以司马迁也特别指明《春秋》亦有颂周之义。
究竟《史记》有没有继承《春秋》之义,后来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葛洪《西京杂记》是肯定的,认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扬雄则最先提出了“是非颇缪于经”说,“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④b]班彪、班固父子也认为司马迁违背了《春秋》之义,因而需要在《史记后传》和《汉书》中加以矫正,重新申明圣人之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严厉批评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汉书》对《史记》中所存在的所谓违背惩恶劝善之义的记载,只要是在汉代史范围内的,统统加以修正。然而后人范晔依然认为班固《汉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存在缺憾,“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⑤b]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封建正统史学的发展,对惩恶劝善之义的理解和运用,越来越具体、细致了,以至于后人总是挑前人的不足之处。
2.大道、名分之义
此义的探讨也是首先围绕《春秋》展开的。《庄子·天下篇》认为,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社会中,百家之学是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可以其不同的主旨,各显其能,“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并对于俗称为儒家经典的六部书,分别标明其主旨,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所谓“名分”,就是卑尊下上,各守其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滕文公下》对此也提到过:“《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看到周王室衰微,区别等级的礼乐制度遭破坏,诸侯恣行,大夫专政,“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⑥b]在《春秋》中严格依“名分”记事。司马迁对《春秋》此义有所注意,他举例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⑦b]世道之所以乱,就是因为“名分”遭侵蚀、破坏,人们没有各守其本分,致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着意记载此类史事,旨在申名分之义,警醒世人勿失其本,“《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⑧b]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⑨]司马迁在对《史记》结构的设计上,就突出了名分之义。对前代各种史书体裁进行选择、改造,“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立了一个以帝王为中心、区分人物等级的纪传体体裁。本记,记帝王之事,是全书之纲,“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①c]世家,记“开国承家”者,虽多系诸侯王,但也要与皇帝区分开尊卑序列,如刘知几所指出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②c]司马迁把本纪与世家比喻成北斗与众星、车轴与车条的关系,“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③c]。正是由于《史记》结构所具有的名分、等级特点,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喜爱,也符合天下一统,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此书遂成为“正史”之首,后世仿作层出不穷。继《史记》而作的《汉书》,更是进一步把名分之义发扬光大,班固在《叙传》中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东汉末年,荀悦在《汉书》的基础上,修成编年体《汉纪》。他在《汉纪·序》中提出撰史的五项基本原则,将“达道义”列为第一,“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从《汉书》中选取的内容,也明显突出了在道义、名分上的考虑,“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④c]这大概与他本人的位置和当时形势有关吧。时逢曹操执朝政大权,汉献帝是个傀儡皇帝,“恭己而已”,但心中却时时不忘诛除权臣,重振汉室。荀悦与从弟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荀悦“志在献替”,看来是拥汉的。然而“谋无所用”[⑤c],他寄道义、名分于史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见解的流露。
东晋的常璩也有类似荀悦的提法,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在达道义方面,《华阳国志》写入了相当多的三纲五常说教,在名分上不但尊中央王朝,而且更进一步将它们罩上“天命所归”的光环。
袁宏也是东晋时人,他的议论比常璩又发展一步。他把“笃名教”作为“史传之兴”的唯一主旨和动因。他总结前代几位著名史家的述作情况,赞扬了司马迁“扶明义教”,然而也还有不足,其他如班固、荀悦,做的就很不够了。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在指出前贤遗憾之后,他道出《后汉纪》的义旨所在:
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⑥c]
把义教说成是史书的灵魂,自然不独出于袁宏胸臆,而是刻有时代的印记。
所谓名教(义教),就是重“正名”、“定分”的封建礼教。源于汉,盛于魏晋南北朝。汉代曾把合乎统治者要求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以之进行教化,即“以名为教”,简称“名教”。进入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巨大势力的世族豪门,以名教观念为准则,相互标榜吹捧,操纵社会舆论。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正统史学也自然把名教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从荀悦、常璩到袁宏,他们均已脱离《春秋》而探讨史“义”。这表明史家对于史学批评的抽象能力已有所提高,已经超越就某部史著发议论或借题发挥的阶段了,能够较独立、自觉地审察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宋代史学又出现一个重名分的高潮,并且进一步发展为正统之辩和尊王攘夷之说,使史“义”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
欧阳修借孔子《春秋》发论,“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⑦c]。他在修《新五代史》时,慨然于五代世事之乱,战祸迭起,“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他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①d]
由于宋代民族间多有战事,欧阳修就从《春秋》中发掘尊王攘夷之义,尽力体现在《新五代史》中。他把居中原的王朝视为正统,把周边各族视为“夷狄”,作《四夷附录》,热衷于记载各族“服叛来去”之事。在本纪中也是严格按既定义例记载,“夷狄来,不言朝,不责其礼,不言贡,不贵其物,故书曰来”。[②d]他“著其屡来”,借以表明尊王室和正统所在。他说:“盖王者之大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来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③d]
三、“义”的显现
史作需有“义”,这是一致公认的,可是如何体现“义”,历代学人就争论不休了。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史作必须讲究褒贬义例,学习《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以宣王道,正人心。另一种意见则以为,只要把史事如实记载就可以了,寓义于事,善恶彰明,读者自有公断。第三种意见认为,史家可以把意旨在行文和论赞中揭示,但需慎加褒贬,谨防立论偏失。从纵向时间来看,自先秦到汉末,史家们主要持第二种意见。魏晋至隋,伴随着品评褒贬的世风,在史坛也出现了刻意以褒贬书法表达意旨的潮流,第一种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唐初,君臣和史家都有一股革新史学的气魄,摒弃前代史学专务褒贬之习气,第二种意见又占了上风。中唐以后,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日益深刻,统治者更加倚重纲常礼教“正人心”,“行教化”,褒贬书法愈加细密但也遇到一定的抵制。第一、第二种意见针锋相对,不断展开论战。再向前发展至清代,史家看法渐渐趋于第三种意见。以下择要述论之。
先秦至汉末的史家,一般都承认“《春秋》笔法”是存在的,但并未对此有过多的发挥。史书之义或是通过“寓论断于叙事”的方式,在叙事行文中自然表达;或是通过史书的序或书中的某一专篇(如“自叙”等)以及上书表文来集中阐明。没有出现两种意见的论争。晋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掀起了“褒贬说”的浪头。他强调,《春秋》是有微言大义的,孔子将“周公之志”、“周公之垂法”贯穿于“史书之旧章”中,从而修成《春秋》。换言之,就是以圣人之意驾驭了旧的史料,诞生了一部经典著作。杜预进而相当仔细地揣摩了《左传》如何阐发《春秋》之“义”,“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这是说明所发新“义”,重在“正褒贬”。
杜预在该序中还以问答的方式解释了《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问题: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言。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新。
所谓“一字为褒贬”,书人名字时,称字则是褒,称名则是贬。杜预也承认,仅凭《春秋》也不易搞清褒贬,还须凭《左传》以数句说明。因此,他赞扬《左传》在阐发《春秋》之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他本人再继续《左传》的工作,“推变例以正褒贬。例如,《春秋·宣公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由此推之,书名者是罪也。襄公二十五年,“晋栾盈出奔楚”。杜预加注云:“称名,罪之。”
杜预如此精微地抉摘《春秋》、《左传》中的褒贬之义,为后世专意褒贬者开了先河。
南朝宋人范晔在所著《后汉书》中,于纪、传之后大发议论,尽情予以褒贬。他很注重史家以论、赞的形式发表见解,并对以往史书的论、赞做过一番检论,“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他对自己在史事之外所发的议论相当满意和自信:“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④d]这些论赞均是为“正一代得失”而或褒或贬。清人王鸣盛看得很清楚,“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立言若是,其人可知!”[⑤d]
这一时期,“褒贬评论”俨然已构成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北魏崔子元上其父崔鸿《十六国春秋》的表中,就有这样的提法:“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①e]南朝陈人何之元著《梁典》(南梁史),意在“垂鉴戒,定褒贬”。[②e]隋高祖“以魏收所撰书(《魏书》)褒贬失实”,诏魏澹另撰魏史。[③e]
唐代立国,世风较前大有变化。唐初君臣重史,例证不胜枚举。然而其重史重在求前代得失兴亡之鉴,而不重褒贬评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渐趋衰败,统治阶级意欲以褒贬书法辅助教化,倡言在史书中突出褒贬的呼声又起。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史馆修撰沈既济上奏:“史氏之作,本乎惩劝,……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④e]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宰相监修国史韦执谊奏请禁止史臣在家修日历,理由只是“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⑤e]
但是,著史一味突出褒贬,是否一定有助于阐扬史义,有的史官已开始怀疑。大文学家韩愈曾任史官,他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⑥e]史官李翱也上奏抨击当时流行的《行状》(国史依据之一)作法,即“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了去掉褒贬虚词,“指事说实”、“据事自见”的撰述方针。他说:
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如果给魏徵作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果给段秀实作传,“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⑦e]按照这个意见,记载人物不必加任何褒贬字样,连“正直”、“忠烈”之类的定评之语都不要有,完全依事实照录,观之者通过这些事实自可以得出结论。——这已经有些“纯客观史学”的意味了。这也就是说,史“义”不必由作者口道出,而是要寓于史事之中。
李翱的话极大地启发郑樵。郑樵在《通志总序》集中阐说了自己的史学见解,其中对褒贬说的批评尤其激烈和系统。他的核心观点是: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
他批评自唐以来史家之迷误:
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
他认为褒贬之说已给史学带来极大危害,“伤风败义,莫大乎此。”他举例说:“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郑樵还从史学源流方面说明褒贬固非史作应有之义,指出《左传》“君子曰”,“皆经之新意”;《史记》“太史公曰”,“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有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褚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郑樵还列举事例说明,如不重会通之旨,轻易褒贬,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造成思想混乱,“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⑧e]
朱熹并不激烈地反对褒贬,但反对专意于褒贬。他认为,《春秋》之重心并不在褒贬上,“《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⑨]他主张,读史的关键是要求索义理,批评一些“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那么正确的作法是怎样的呢?“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凡观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便见得义理。”[⑩]朱熹对史“义”之认识,显然比前人广阔和深刻了,但如把握不当,其认识易流于主观或空泛之失。
进入清代,几位大学问家、大史家对史“义”的探究和解说都有相当的深度。顾炎武生当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之时,深感心学泛滥、学风空疏之弊,认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义,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①f]王鸣盛也主张要从实学中求“义”,而不能从“议论”及“褒贬”中寻求,这个道理对于经、史都适用。“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②f]钱大昕认为,“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拚,奚庸别为褒贬之词?”[③f]他批评“空疏措大”之人,“辄以褒贬自任”,只是善于高谈空洞的教条,“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不过是自鸣得意,其实并未得到史学真谛。这种人的议论有三种毛病:一是“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二是“不卟年代,不揆时势”;三是“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④f]
事实上,对于作者如何在史著中显现史“义”,以及读者如何从史著中体会史“义”,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争论的大体趋势是明显的。主张在史作中鲜明突出作者主观倾向,以褒贬评论实施道德裁判与教化,越来越缺少支持;主张在史作中寓义旨于史事,以善恶必书的方式客观反映历史,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后一种主张实践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四、“义”与“事、文”之关系及“义”的开拓
自孔子、孟子揭示史作(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后,绝大多数史家将“义”看作三要素之首。可以说,重“义”,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悠久而良好的传统。史学批评之重“义”主要有两个特征:
1.批评兼顾“事、文、义”,但以义为先
班彪撰《史记后传》,《略论》篇是史学史及史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献。该篇重点评论《史记》,从事、文、义三方面考察:其论“事”(史料、事迹):
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
其论“义”(主旨、观点):
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其论“文”(文笔、才华):
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另外还有一段文字论编纂方法。从上述文字来看,班彪对于“义”最关注,要求最严厉。《略论》对《史记后传》的自我评定和绍介,依然最突出“义”:
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也是按“事”、“文”、编纂、“义”的几个要素讲的,强调自己是以《春秋》之义刊正及续撰《史记》。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评论与班彪所评基本一致。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评论班氏及《汉书》,亦从事、文、义三方面评骘。其中论“义”,文字多,份量重。
在史学批评史上有这种现象,某位史家过分偏重“义”,忽略了“事”与“文”;而有的史家则偏重“事”与“文”,忽视“义”。这种对“义”把握的失衡状态,往往被其后的史学批评所纠正。
晋人孔衍发愿撰汉、魏诸史,偏重于“义”,“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⑤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删汉魏诸史,只是选取“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章次序,名为《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共26卷。他又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删《战国策》、《史记》(汉以前部分)名为《春秋时国语》、《春秋后语》,各十卷。孔衍本人很自信,自作序夸口说“虽左氏莫能加”。然而,缺乏史事,只有语录、观点的史著,是不受世人欢迎的,“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唐人李翰则对某些学者片面追求博学多才,而不重史学要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他首先谈到这些学者治史的盲目性,“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见闻固然广博了,然而却未抓住史学精髓,“是非纷然,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李翰形容这些学者尽管勤奋刻苦,却依然陷入困窘迷惑状态,“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他以《通典》为例,说明正确的作法是要端正治史方向,搞清楚治史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①g]
2.多角度多层次探求史“义”
从宏观上看,与“事”、“文”相对而言,史“义”是一个,即泛指宗旨、观点、理论。但每位史家所从事的各项研究,则是具体的,这就需要把握从属于宏观“义”之下的各种相对具体的“义”。中国史学批评对此也有所探索。
司马迁曾朦胧地论及《春秋》义蕴之多:《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②g]“《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③g]
北魏高祐曾指出:“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④g]
北宋程颐明确提出:《春秋》之义并非如后人所说的只是褒善贬恶,还有其它重要之义,需要沉心潜意,精细入微地体会。他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⑤g]
史学批评史上的三大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于史“义”的探索和开拓都很有贡献。
刘知几少年读史,即注意“大义略举”,“喜谈名理”。以后博览群史,“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史通》作为先秦至唐史学批评集大成之书,在展开史评理论的过程中,整理、运用了多种史“义”,如:
“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忤时》)
“求诸劝戒,其义安在?”(《惑经》)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宜王道之正义”。(《六家》)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世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叙事》)
“ 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
“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疑古》)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惑经》)
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涉及到了“义”的各个层次,如道德观、历史观、史学观、方法论等等。
他自述著《史通》缘由及主旨:“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⑥g](章学诚认为刘知几只是“讲史法”,他讲“史意”,是不够公允的。)
《史通》中贯穿的“四义”是怎样的呢?
所谓“与夺”,即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运用批评的武器去破旧立新。《史通》表达史学主张,态度鲜明,无暖昧之语。如《书志》篇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书)的作法,提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意见,主张取消《天文志》,删去《艺文志》,《五行志》中不系乎人事的内容应排除,再创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等新志。
所谓“褒贬”,以封建礼教标准去评判史家或史作,或赞扬,或贬斥,发挥封建史学维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功能。如《序传》篇在论自序作法时,批评司马相如“自序”记“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理无可取”。
所谓“鉴诫”,即探讨史学研究的经验与失误。《申左》篇对《春秋》三传的长处和短处进行细致的比较,其意义已不限于对三传的评判,亦表达了评定史书优劣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标准。
所谓“讽刺”,即是有些见解不便明言,而以较含蓄、曲折、隐晦之文字表达,主要反映在对现实的不满和讥刺。唐初政争激烈并颇富戏剧性。李渊登极是隋恭帝杨侑“禅让”,李世民当皇帝亦是李渊“让位”,武则天称帝要由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残酷的权位之争,却在形式上彬彬有礼的进行。《史通·疑古》大胆否定了古箱中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指出以“禅让”掩盖夺权之事,古今均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武则天在称帝前多次搞图谶、祥瑞的把戏,称帝后又多次利用祥瑞改元。唐中宗、韦后也都借符命而加尊号。《书事》篇写道:近古时代,“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
上述“四义”,与夺,侧重于探讨史书体例、内容上的当否去取;褒贬,侧重于评骘史书、史家的政治思想倾向;鉴诫,侧重于评论史学研究中的得与失;讽刺,则侧重于迂回表达对现实政治弊端的批判。
郑樵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创“会通”之义,并且将“义”奠定在坚实的“实学”基础上。他不满意“虚言之书”,重视亲身实践,重视史料考信,把社会现象和学术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把历史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考察,然后把研究成果全面汇集,综合整理,合“天下之理”,“极古今之变,”完成一部空前广博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志》。所谓“会”,就是“会天下之书”,将研究所需的材料全面搜集;所谓“通”,就是将古今“通为一家”,搞清楚来龙去脉。他形容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h]
章学诚对于史“义”之阐说是相当系统和深刻的,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殿军。
(1)论事、文、义之关系
章氏论事、文、义三者不可偏废,比前人更为透彻明快,“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他进一步做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这个比喻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有说服力。三者中,他还是最重“义”,“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②h]“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③h]
章氏一方面批评宋、明学者空谈义理、性命的弊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④h]讥刺从“人事之外”探求“义理”。另一方面也批评只埋头考据征实的汉学派,认为其不通史学之义,“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⑤h]这都体现出他对事、文、义关系的正确认识。
章氏还把事、文、义与才、学、识比较论说,显示出通识与创见,“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⑥h]这就是说,识与义、才与文、学与事,既有相通涵义,又不可等量齐观。因为才、学、识是评价一个良史的标准,而事、文、义的一般用法则有一些弹性。
(2)论史“义”贵在创新
章氏这个见解可以说是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和刘知几“一家独断”的继承和发展。“史所贵者义也”,[⑦h]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义是事与文的灵魂,更在于敢创新,敢与前人不同,“独断于一心”,这才能促使史学不断进步。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⑧h]这道出了史学千百年来更新发展的奥秘,也道出了史学批评的最重要主旨。凡是大有成就的史家、史评家,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就在于他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能够不随波逐流,从众人所趋处发现时弊;能够从古今变化中,预见史学新的突破口。假若没有创新,没有新的史“义”,史学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
注释:
①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春秋类》。
②a 《孟子·滕文公下》。
③a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④a 《史记·虞卿列传》。
⑤a 《左传·成公十四年》。
⑥a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⑦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
⑧a 《史记·滑稽列传》。
⑨a 《史记·孔子世家》。
①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b 《法言序》。
⑤b 《后汉书·班固传论》。
⑥b 《史记·儒林列传》。
⑦b 《史记·孔子世家》。
⑧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⑨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c 《史通·本纪》。
②c 《史通·世家》。
③c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c 《汉纪·序》。
⑤c 以上见《后汉书·荀淑传附荀悦传》。
⑥c 《后汉纪·自序》。
⑦c 《居士集》卷18,《春秋论》中。
①d 《新五代史·一行传序》。
②d 《新五代史·高祖本纪》徐无党注。
③d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论》。
④d 《宋书·范晔传》。
⑤d 《十七史商榷》卷61,“范蔚宗以谋反诛”条。
①e 《魏书·崔光传附崔子元传》。
②e 《陈书·何之元传》。
③e 《隋书·魏澹传》。
④e 《旧唐书·沈传师传》。
⑤e 《唐会要》卷63,“修国史”条。
⑥e 《韩昌黎集》七,《外集》,“答刘秀才论史书”。
⑦e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条。
⑧e 上引均见《通志总序》。
⑨e 《朱子全书》卷36。
⑩e 上引见《朱子全书》卷6,“读史篇”。
①f 《清史稿·顾炎武传》。
②f 《十七史商榷·序》。
③f 《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序》。
④f 《廿二史考异·序》。
⑤f 《史通·六家》。
①g 《通典·序》。
②g 《史记·孔子世家》。
③g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g 《魏书·高祐传》。
⑤g 《文献通考·经籍考》“春秋”类。
⑥g 《史通·自序》。
①h 《通志总序》。
②h 以上见《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③h 《文史通义·言公上》。
④h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⑤h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⑥h 《文史通义·史德》。
⑦h 《文史通义·史德》。
⑧h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标签:司马迁论文; 史记论文; 儒家论文; 汉书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