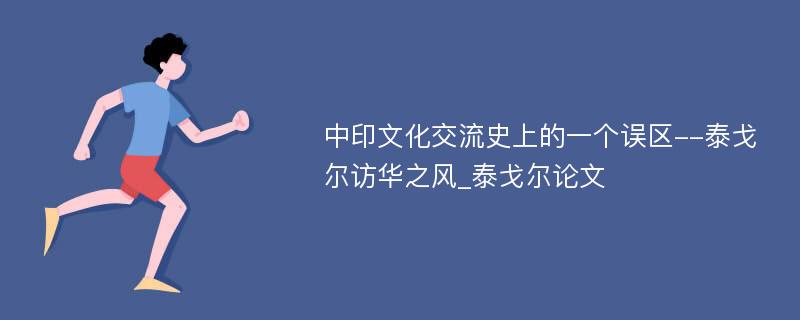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史上论文,文化交流论文,风波论文,中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4~5月间,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等人创办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随着他的到来,现代中印两国之间一次规模最大的文化交流也拉开了序幕。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交流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今天的人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这些误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对今天我们借鉴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仍不失有警策意义。
(一)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宗教家,也是“五四”后期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泰戈尔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是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1卷2号)上,是陈独秀翻译的《赞歌》,署名达噶尔著。此后就少有人注意了。而此时泰戈尔在欧洲和日本正是妇孺皆知的热门人物。泰戈尔是1913年以《吉檀迦利》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之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一个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英国女王也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而自1915年之后,这股泰戈尔热又由欧洲传到了日本。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外来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国最早的比较全面地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并受其系统影响的知识分子是郭沫若。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高潮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有机缘接近了泰戈尔的英文诗,结果一下子被这些清新平易的诗迷住了,于是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注: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自1921年起,泰戈尔的行踪开始广泛受到国人关注,他的作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章和杂志上,他的思想和人格开始被研究。1921年3月10日, 《小说月报》12卷3 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沈雁冰的短文《印哲学家太戈尔的行踪》,介绍泰戈尔在美国的活动;同年8月, 留德学生王光祈发表《泰戈尔之山林讲学》(《申报》,1921年8月4日);俞颂华发表《德国欢迎印哲台莪尔盛况》(原载《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1921 年8月10日转载);魏嗣銮发表《旅德日记》(1921年11 月《少年中国》3卷4期),介绍德国欢迎泰戈尔的盛况, 以及泰戈尔在德国的几次演讲,并对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作了一般介绍。
对泰戈尔作品的介绍,这一时期也逐渐多起来。1920年2月、3月《少年中国》第一卷八、九期发表了黄仲苏译的《泰戈尔的诗十七首》、《泰戈尔的诗六首》,并有对泰戈尔作品特色的精粹介绍;1921年1 月10日、4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4 号发表了郑振铎的《杂译泰戈尔的诗》,其中4号还有许地山译的泰戈尔小说《在加尔各答途中》, 并附跋, 而5 号上则发表了瞿世英翻译的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 1921年4月17 日《民国日报·觉悟》也刊出“译泰戈尔园丁集第二十三首”和“译泰戈尔园丁集二十八首”,译者为“大白”。对泰戈尔的研究,这一时期则有瞿世英、郑振铎的《泰戈尔研究》(《晨报》第七版,1921年2月27日——4月3 日)和关于泰戈尔的通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4月14日、15日); 冯友兰的《与印度台戈尔谈话》(《新潮》1921年9月1卷1号); 胡愈之的《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东方杂志》1921年8月18卷7号);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瞿世英的《演完泰戈尔的〈齐德拉〉之后》(《戏剧》,1921年10月30日)。
早期这些关于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从各个侧面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人格和艺术特色。泰戈尔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加上中印两国都属于被西方殖民甚苦的国家,中国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在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这位诗哲,并最终促成了泰戈尔来华及来华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邀请泰戈尔访华的是讲学社,直接发起人是瞿菊农、徐志摩等,中间的联系人是泰戈尔的朋友兼助手英国人恩厚之(L.K.Elmhirst),时间是1923年早春。
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可以想见,这个已誉满全球的印度哲人能答应来华,会在中国文化界引起怎样的激动与反响,恰如徐志摩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的信中所描述的:“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架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这些话虽然难免夸张,但却足以说明因泰戈尔来华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受到的震动。
自泰戈尔答应来华至1924年4月踏上中国土地前后这段时间内, 《东方杂志》(1923年7月25日,第20卷4号),《小说月报》(1923 年9月10日、10月10日,第14卷9、10号),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的《佛化新青年》(1924年5月,第2卷2号)上都出了“泰戈尔专号”; 《小说月报》第15卷4 号在“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内编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临时增刊;其他一些杂志如《民铎》、《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创造周报》、《文学周报》、《民国日报·觉悟》、《向导》、《中国青年》等都发表了泰戈尔的作品和有关文章。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 张君劢、郑振铎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也都有代表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
自泰戈尔下船至5月29日从上海赴东京,鲜花和掌声就包围了他。 上海的徐志摩、张君劢、瞿菊农、郑振铎,北京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岭,甚至溥仪,纷纷以各种形式欢迎泰戈尔来华。特别是5月8日泰氏六十岁生日那天,北京学界由胡适任主席、梁启超主持举行祝寿会和赠名典礼,赠泰氏中国名字“竺震旦”,会间由徐志摩安排演出泰氏名剧《齐德拉》,把对泰戈尔的欢迎推向高潮。
对于泰戈尔的来访,梁启超、徐志摩等表现出由衷的欢欣。梁启超此时已结束欧洲之行,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明到欲以中国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他坚信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将流行于世界,他的《欧游心影录》就记录了他这次的思想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国内的东西文化论争。主张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泰戈尔此次来华,梁启超当然恭迎有加。在欢迎泰戈尔的演说中他就不如夸张地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徐志摩对泰戈尔来华更是望穿秋水,他不仅时时伴侍泰戈尔左右,而且以泰戈尔弟子自居,甚至以父子相称,泰戈尔在华时劝人少读书,多静思,陈西滢据此将他看成批判章士钊、林琴南之流复古派的同道。其他如郑振铎、简又文、王统照,也都著文以示欢迎。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纷乱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泰戈尔的欢迎确也成了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二)
然而,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而且还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就在热热闹闹的欢迎圈外,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实际上,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和谐的气氛。有一次讲演,泰戈尔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北京有人说他是政客,不是诗人;要他还是做诗去罢,莫管人家的国事,甚至骂他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在这种尖刻、激烈的批评声中,他甚至取消了计划中在华的三次演讲。
对泰戈尔批判最力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沈雁冰、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鲁迅对泰戈尔的访华,也报以嘲讽。
陈独秀是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文章,如《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泰戈尔在北京》等,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到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他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 )瞿秋白则尖锐地指出泰戈尔要东方人对侵略者施以“慈爱宽恕”的“东方文明”的危害,他说:“东方和西方能否调和呢?无所谓东方,无所谓西方——所以更无所谓调和!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11日。 )沈泽民的批评则针对泰戈尔提出的“人类第三世界”的理论。所谓第三世界,按泰戈尔的说法,即是重精神、主静的东方文明最终战胜重物质、主动的西方文明后出现的一个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的真善美的世界。沈泽民认为泰戈尔这种理想的第三世界是虚幻的,是冥想主义的,是“闲暇的有产阶级的思想,”要“达到这人类第三期的世界,”泰戈尔的精神主义是不行的,反之,我们将更加努力去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泰戈尔的主张和我们不同便在于此。泰戈尔所说的第三期文明,实是一种已灭亡的农业和工业时代的文明,他漠视了进步的轨迹,结果当然陷于宗教之网不能自脱”,“在这一点上可谓迷恋骸骨,与中国现在一般国粹派,毫无二致。这种思想若传播开来,适足以助长今日中国守旧派的气焰,而是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注:《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 )郭沫若则根本否定泰戈尔的哲学可使东方民族起死回生,因为中国乃至东方衰弱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度,因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泰戈儿如以私人的意志而来华游历,我们是由衷欢迎;但他以公的意义来华,那我们对于招致者便不免要多所饶舌。”(注: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作为“五四”时期信仰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林语堂1924年6 月发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显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嘲笑姿态,讽刺泰戈尔以已亡国国民的身份,竟然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不免显得不伦不类。他说:“大凡身处亡国之境,必定使一人的精神感觉不舒服的。因而必生一种反应,思所以恢复国光的道理。暗杀啦、革命啦、宪法改革啦,都是一种谋复国光的道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办法,谓之精神安慰。”“使今日享盛名受优遇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乎无意中不自觉的提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注:林语堂:《翦拂集》, 上海书店影印本, 第179、182页。)这未免有“诛心之论”的味道。
如今,当我们这些当代人再回首看看这些文坛前辈对一个印度老诗人、一个对中国人抱有好感的印度诗人的批评文字,不免有点难堪,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也与他们自身对泰戈尔的理解有关,总之,泰戈尔受到批评,是由于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如今看来,只能说是一种时代的误会。
(三)
事实上,泰戈尔对来中国并非毫无顾忌,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而实际情况是,如果他到中国只谈诗,他的处境可能要好得多。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在泰戈尔身上看出的、或希望从泰戈尔来华所得到的,恰也不是他诗歌方面的成就,而是他此行所带有的救国济世的使命。如孙中山就曾亲笔写信邀请泰戈尔来华:“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尊崇儒者,乃我古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增华,亦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途经香港, 孙中山即从广州派人去看他,告知他自己有病,不能相会,并说:“中国的生命中心是在北京,印度代表的工作应该从北方开始”。(注:(印度)海曼歌·比斯瓦斯:《泰戈尔与中国》,“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泰戈尔此行并非是以诗人身份来中国单纯游历,而是带着自己的什么济世良方来中国宣传一种救国救世的道路的,是作为一个救世主的身份来中国布道招徒的,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他是来中国“开展工作”的。而泰戈尔似乎惟恐人们这样看他,所以他在4月18 日在华的首次讲演中,就首先声明他访华的目的。他说他此次来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道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好象是一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但他接着说到,他不曾想只看见工业主义、物质主义正日益吞噬着高尚的精神文化,因而惊呼中国文明面临危机,呼吁人们行动起来,竭力为人道说话,与惨厉的物质的魔鬼相抗;不要为他的势力所降服,要使世界入于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而打破物质主义。泰戈尔在华的谈话和讲演中,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一方面又处处流露、切切宣扬他的印度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于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而在当时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种主张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泰戈尔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就对中国当时科学救国的潮流微露嘲讽:“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站住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已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甚至他在受到激烈批评后,仍对中国当前的物质主义表示不解。如他在1924年5月20 日在上海慕尔鸣路37号园会上所作的告别辞中就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这些话显然是要让中国人放弃追求强国的目标,一味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聊过时日。 在国危民艰的时代背景下,泰戈尔的这种声音难免刺耳,不由不让人发火了。特别是有左翼背景、正鼓励民众通过艰苦的奋斗改变中国黑暗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泰戈尔的批评最力,他们的批评文章也不难看出其政治色彩,而事实也确如此。茅盾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曾谈及自己当时为什么写反对泰戈尔的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对于泰戈尔的希望》),他说:“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
这就表明,泰戈尔来华成为当时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了。茅盾在这里所说的“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显然是指那些对泰戈尔竭诚欢迎的知识分子或政界名要,如将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的梁启超,称泰戈尔‘老戈爹’的徐志摩,还有辜鸿铭、溥仪、陈三立等,而这些人当时所代表的思想本就已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泰戈尔与他们朝夕相处,吟诗唱和,难免要沾点晦气。鲁迅先生就曾语带讥刺地说过:“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像一大瓶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注:《论照相之类》,《语丝》,1924年11月。)
鲁迅、茅盾等人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用了种种苦心,竭力把泰戈尔变成可用于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这从他们对泰氏的过分的宣传、吹捧中可见一斑。他们织下的这层层华丽的帷幕,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也真应了郭沫若一针见血的断言。针对当时国内一窝蜂似地欢迎研究泰戈尔的不正常现象,郭沫若严正指出:在对泰戈尔的思想、作品没有作系统的考察研究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什么“泰戈尔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的演办一次神会。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就以对泰戈尔来华最热心、最真诚、最激动的徐志摩为例,从他介绍泰戈尔的文字中,人们只感受到一种不可自抑的情感的奔泻,在珠玑般晶莹华丽的赞美语句下,并没让人看出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有多了解,而只是让人觉得他满心崇拜泰戈尔。就如他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坦言所陈的:“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如其他有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注:《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不但徐志摩欢迎的是泰戈尔的精神与人格,当时颂扬泰戈尔的文章,无一不颂扬他的人格,把他说成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旅途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注:郑振铎:《欢迎泰戈尔》,《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当然,在欢迎或批判的人群里,并非没有对泰戈尔文艺作品的分析与研究,闻一多在《泰戈尔的批评》一文中就深刻地批评了泰戈尔诗的哲理性压倒了艺术性,认为他的诗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泰戈尔的诗是清淡,然而太清淡,清淡到空虚了;泰戈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秀丽到纤弱了”。但这样针对泰戈尔作品的批评毕竟太少了,大多数注意到泰戈尔作品的人多采取沈泽民的态度:“然而我们不是问这些事情(指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方面的问题——笔者),我们是问泰戈尔的思想,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是否要得。”(注:《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泰戈尔首先是个文学家,把他看作一个救世主, 或把他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联系,误解与批判就难免了。
泰戈尔的这次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次论争也是当时国内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论争促进了中印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加深了国人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的外来影响中,印度哲学和文学是一个重要源头,而这个源头的中心,则是泰戈尔。关于这一点,柳无忌先生后来总结到:“他曾经是我们一派新诗人的灵感的泉源,东方文化的伟大的支持者,在他身上,实现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诗歌的音奏,他对于人生的深刻见解,他的理想,他的伟大的精神的感召,深深地印在中国作家的心灵上,其痕迹也遗留在他们的作品中。”(注:柳无忌:《印度文学》中第八章“泰戈尔”,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2月初版。)
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根本性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泰戈尔与中国,印度文化、文学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这次争论的成败得失,对我们研究中外文化、文学关系,也不失为一个可贵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