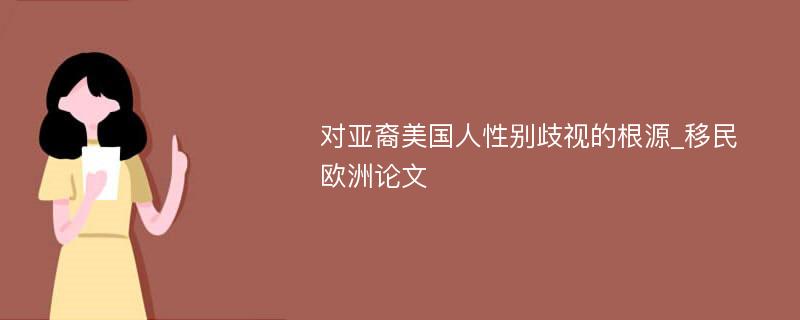
对美国亚裔种族化性别歧视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裔论文,美国论文,起源论文,种族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赵健秀(Frank Chin)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著名亚裔剧作家之一,他在华裔与日裔文学选集《哎咿!》(The Big Aiiieeeee!)中写道:因为“太长时间被忽视、被排斥在参与美国文化的创造之外,美国亚裔很受伤,感到悲哀、愤怒,同时也诅咒和困惑”。①
在主张美国亚裔同样是其自身传统文化的“选民”时,赵健秀使用了男性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他的”。这个文学选集没有将在当代拥有广泛读者群的美国亚裔女性作家的作品收录其中,诸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斗士》(Woman Warrior)和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这并不是由于赵健秀及其同事的疏忽,而是源于他刻意地对主流出版机构和媒体组织的抗拒。赵健秀认为,那些作品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想象,不是事实,也不是中国文化,算不上是美国亚裔文学”。②赵健秀指责谭恩美夸大了中国文化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他还公开地批评汤亭亭是“一个主张社会同化者”,迎合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歧视,称她的作品是“边城妓女的谈话”。③赵健秀将汤亭亭和谭恩美归为所谓的“伪美国亚裔作家”之类,认为她们服务于美国主流媒体,把亚裔男性宣传为女性化的和对美国社会有危险的,而把亚裔女性想象为极度女性的和性欲过度的。这样,原本来自同一文化环境的男性和女性就被划分开来。④
本文试图以一种批评的态度探询:为什么赵健秀认为亚裔美国人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为什么在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划分?首先,本文将做一个历史的梳理,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被视为特殊的社会性别角色时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其次,将做共时的探讨,讨论美国政府是如何强化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流行的对亚裔的看法:把亚裔男性看作女性化的和无性征的,把亚裔女性视为极度女性的和性欲过度的。此外,将分析传教士和媒体是怎样附和美国政府的这种歧视行为的。总之,无论是用历时的还是用共时的方法,都旨在解释亚裔美国人曾经历过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的起源和机制。
本文将运用性别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处于社会政治不平等境况中的亚裔美国人。目前对性别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采用的是乔茜弗·博罗兹(Jozsef Borocz)和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的研究方法。她们认为:“性别研究并非只是关于女性的研究,而是关于女性和男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涉及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一。”⑤这与弗洛拉·安西斯(Flora Anthias)和尼娜·尤阿瓦尔-戴维斯(Nira Yuaval-Davis)以及其他女权主义作者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她们认为这是“对固有的民族优越感和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进行批评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⑥
在本文中,“亚裔美国人”主要涉及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关于他们在国家层面、宗教方面和媒体宣传方面所经历的遭遇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当然,其他的亚裔美国人诸如日裔美国人、越南裔美国人等,也经历过与华裔美国人相同的种族化性别歧视。
政府层面:种族化性别歧视的历史基础
赵健秀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在他们的《种族主义者之爱》(Racist Love)一文中写道:“白人眼中的亚裔的形象很奇特,因为它是唯一的完全没有男子气概的、种族的刻板形象。……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指男性亚裔美国人——引者注)是为人所不齿的,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女人气的、柔弱的,缺乏英勇、阳刚和创造力等传统的男性气质。”⑦
白人眼中的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曾使早期亚洲移民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之苦,而且这种痛苦一直在延续,并被“性别角色体系”(sex-gender system)进一步强化,它是“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根据文化定义的性别角色来分配资源、财产和赋予人们特权”。⑧从19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性别角色体系”曾公然控制华人和其他亚洲移民的性别。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852年“只有19名中国女子居住在这个城市(旧金山),相对于2954名中国男子,这个比例是1∶155”。⑨据S·W·孔(S.W.Kung)的研究,中国移民中男子占绝大多数的原因主要与美国经济有关。在19世纪早期,美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亚洲劳工尤其是华工的输入则有效地补充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以及采矿业所需的劳力。⑩然而到了19世纪末,对亚洲移民的敌视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正如S·W·孔所指出的:“在1886年,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小姐为自由神像写下这样的碑铭:‘给我你们的疲惫、你们的贫困。’或许她表达出了大多数身在美国的人们的情感。她当时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国会在通过了1875年和1882年法案以及4年前的排华法案后,就已结束了门户开放政策。”(11)
据吴程建(Cheng-Tsu Wu)的研究,从法律上反对华人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的情况早在1875年以前就存在了。185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禁止亚洲移民从加州入境的法案,规定:“任何华人或蒙古人种的个人或群体,将不允许进入这个州,或在这个州的任何港口及其他地方登陆……登陆的华人或蒙古人种的个人或群体将……受到相应的惩罚。”(12)
在1882-190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至少30个内容与上述1858年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亚洲移民入境法类似的法案。(13)根据这些法律,不仅亚洲移民在美国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同对待其他有色人种移民一样,不允许亚洲移民加入美国国籍和获得公民权,因为这是“自由的白人”才能拥有的资格。
这一连串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根据美国政府的“性别角色体系”而产生出来,不仅长期将亚裔男性劳工与他们的配偶分开,还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他们被美国社会遗弃,但又是在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工作最努力的人。在阅读美国亚裔的历史时,我想,给他们最深的伤害是剥夺了其作为成年人和成为父亲的权利:不允许已婚者与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团聚,未婚者则没有机会去结识潜在的结婚对象。在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之下,亚洲女性若想移居美国则受到更严格的控制。那些已进入美国的亚洲女性移民面临着性别上和种族上的双重折磨,因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认为亚洲女性的性欲与欧洲裔美国女性不同,亚洲女性移民是妓女,是“诱惑年轻的白人男孩走向堕落生活”的人。(14)艾斯比利图(Yen Le Espiritu)对1875年的移民法有如下评论:“把焦点集中在界定亚洲女性的道德上,以此作为其进入美国的依据,说明了在美国的移民法中存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15)在这个法律颁行的15年中,美国的亚洲移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男、女性别比,达到了27∶1。(16)如此高的性别比导致亚洲移民中已婚男子的家庭生活几乎不复存在,而单身汉也不可能找到配偶。无情的国家法律不仅把亚洲移民男子同其配偶以及潜在的结婚对象分开,而且还不准他们与欧裔女性结婚。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明确地拒绝“中国女性和妓女”入境。(17)根据该法,“任何一个华人男子与一个美国女子结婚,将导致她失去公民权”。(18)
这一时期的立法机构被那些从种族上歧视亚洲人的美国人所控制。1878年,加利福尼亚州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来处理“中国人的问题”,结果是中国人被禁止进入加利福尼亚。投票的过程不但不公平而且是不合法的,因为在“152名代表中,有35人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欧洲人”。(19)美国移民法依据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标准使得亚洲移民不可能享有与其他移民同等的机会,更不可能同等地参与政治活动。
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性别角色体系”的合法化,不仅侵犯了美国男性亚洲移民繁衍后代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自由择业的权利。亚裔男子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诸如洗衣工、餐馆工和家政服务,从属于白种男人和女人。(20)一位从事家政服务的美国日裔男子曾这样悲叹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回想着我的生活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晚饭后,要刷洗所有的盘子、锅、杯子等,对我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当我走进饭厅,将所有的银餐具放入餐具柜时,我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穿着白色的外套和围裙!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我将脸埋在了双臂中……”(21)
正如伊莱恩·H·金(Elaine H.Kim)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一个没有女人、无性和无孩子的世界中,亚裔男子被从“成年人中剥离出来,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被判以‘永久的少年时代’”。(22)亚裔男子常常从妓女那里寻求安慰。艾斯比利图在对亚裔美国男子和女子进行研究时发现,绝大多数华裔男子“把妓女看作为他们大型的单身汉社区提供必需服务的人”。(23)在华人社区,这些妓女被认为是“叭哈柴”(baak haak chai)(24)或者是众多男人的“老婆”。(25)
本森·唐(Benson Tong)在一项关于19世纪在美国的华人妓女的研究《不顺从的女人》(Unsubmissive Women)中指出,华人妇女卖淫是通过一个由商人、政府官员和轮船公司勾结成的网络来实现的,例如美国驻香港的领事“常常自己就是商人,同样是这种罪恶交易的帮凶”。(26)这些华人妇女被带入美国后,常会受到暴力虐待,“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处于最肮脏的奴隶般的环境中”。(27)她们的工作以及她们的身体被许多具有不同身份的人牢牢地控制着,诸如妓院老板、黑社会分子、警察以及移民官员,这些人都对此交易收取保护费。(28)还有一些白人则以高额租金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妓院。(29)
19世纪中叶至二战期间,这种强制性地将美国亚裔男性与女性分开的行为被各种法规强化。据唐纳德·乔尔里奇(Donald Geollnicht)的研究,将华裔女性与她们的男性配偶分隔开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安排”,目的是“防止美国华裔的人口增长,并破坏美国华裔男子的生殖力”。(30)在亚洲男性移民繁衍后代的权利被美国法律严重侵犯的同时,他们的性行为还受到妓院老板的控制。由此而看,在这段美国历史中,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都被那些滥用政治权利和以此捞钱的人所压制。
当时在美国,当选的官员和选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种族化的政治利益:将有色人群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就是政治上和生物学上的隔离。换言之,形形色色的移民法是贯彻“性别角色体系”的工具。“性别角色体系”不仅反映在相关法律的条款中,也被一些官员公然表述。1882年,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约翰·P·琼斯(John P.Jones)在向选民演讲时说:“难道像我们这样更高级的种族还害怕与那些低等的中国人种竞争吗?反对中国人境的主要理由不能用来反对和我们同样种族的欧洲人……我们天生是自由的热爱者。而中国人在何时、何地哪怕是简单地表达过对自由的拥护?然后我要问的是,中国有什么贡献?压迫、野蛮、退化。一个文明社会完全是物质的,与精神无关,所有的事物都可用金钱来取代……”(31)显然,这是琼斯肆无忌惮地向选民宣传种族主义。
制造认同:传教士和媒体对政府的附和
在对美国亚裔进行种族化性别压迫的过程中,传教士、媒体与政治家一起编织了政治上的认同。赵健秀指出,基督教传教士和媒体曾参与政府对少数族裔进行性别压迫的策划。传教士和媒体都以特殊的方式对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形象进行控制并从中获益。传教士在种族化性别压迫中的所作所为附和了“性别角色体系”,这可以从他们的公开言论和他们针对美国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所采取的行动得到证实;媒体在种族化性别压迫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将美国历史上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以及传教士所声称的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转变为电视节目和电影,为“性别角色体系”推波助澜。(32)
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待亚裔美国人。正如赵健秀所指出的,白人主流社会以基督教教义为道德标准,作为被赦免原罪和被判有罪的分界线。这是一个暴力性的“道德武器”,用来征服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与白人说不同语言的人们。(33)
在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颁行之前和颁行期间,这个“道德武器”主要用来对付美国亚裔女性。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有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传道院,由唐纳德·卡梅隆(Donaldina Cameron)女士于19世纪末创建,被称为卡梅隆大楼。卡梅隆女士将这座大楼专用于安置那些从妓院逃跑出来的华人女子,并向她们传教。赵健秀指责卡梅隆女士的传教行为是“只挑选为中国男子提供服务的妓女”,他还指出:“妓院满是华人女子,只接待白人顾客,诸如卡梅隆大楼的隔壁邻居,真该死。”(34)
除卡梅隆大楼之外,还有另外的妓女改良所,如卫理公会派的传道院。据本森·唐的研究,有相当多的妓女从其老板那里逃出来,她们常常乐于居住在改良所中,然而,她们“更像是被当作囚犯来对待”。(35)在这些地方,作为曾经的妓女,她们的日常生活处于传教士的监督之下,事实上她们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来访者特别是男子均被严格地筛选过。(36)本森·唐坦率地指出,那些被援救的女子只不过是在过着另外一种关押生活:“隔离和界限严格的生活只是在性质上与妓女的生活不同。尽管有序取替了无序,端庄代替了陋习,这些女人仍然是被遗弃的。她们不能经历常人的平凡生活和与社会产生相互影响。”(37)传教士的救助事业就是计划将曾经的妓女感化为基督徒。本森·唐指出,由于大多数白人女性援救工作者出生于新教徒中产阶级家庭,于是教导的内容是向亚裔女子灌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38)的女性道德观念;而传教士的工作是反复地向这些曾经的妓女灌输“‘真正的女人’的箴言,那就是纯洁、虔诚和热爱家庭”。(39)在传教士的引导下,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被传授给亚洲女性移民。正如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所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中的“真正的女人”是一种殖民主义“崇尚女性阴柔”的类型,于19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这种“淑女的举止是帝国主义文明的支柱”。(40)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向亚裔美国人灌输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就是要证明白人对“愚昧民族”的殖民是“正当”的。
通过对传教士业绩进行夸大不实的报道,给人们以传教士是英雄而非殖民者和压迫者的印象。在当时美国的报纸和传教士的自传中,常常有多少女孩被“热心地拯救”的报道。(41)但事实上并不像传教士所说的那样在其教导下有那么多的亚裔女子皈依基督教。在1873-1881年间,卡梅隆大楼中有近百名寻求庇护的妇女,其中仅有10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1882年,有140多名华人妇女居住在旧金山华人街的卫理公会教派的传道院,然而最终只有34人皈依基督教。(42)而且许多曾经向基督教组织寻求庇护的妓女在她们婚后就断绝了与这些组织的联系。尽管如此,传教士却有自己的解释。一个援救工作者E·V·罗宾斯夫人(Mrs.E.V.Robbins)曾说:“要驯服野蛮人是最困难的工作。”(43)有的传教士则将亚裔妇女的反抗看作她们对白人社会的恐惧。(44)
传教士只努力援救亚裔妇女和向她们传教,却完全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即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美国人进行种族的和性别的压迫问题,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性和生殖权利被不公平的法律和恶毒的性产业老板所侵犯的亚裔男子。在援救亚裔妇女事业开始之前,传教士所做的完全是反面的努力,那就是为了提升他们自己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尽可能地诬蔑亚洲民族和文化。
传教士和媒体与政府紧密地站在一起,它们不仅同意政府对美国亚裔在种族上和性别上的压迫合法化,而且捏造出美国亚裔的刻板形象来误导大众。
1873年,天主教神甫J·C·布沙尔(James Chrysostom Bouchard)在旧金山做了题为《华人还是白人,哪个?》的演讲,在讲演中其种族偏见暴露无遗:“人们可以把一个忠实、善良的仆人开除,因为工资实在太高了。为此,可以接纳这样的一些不道德的人进入家庭,因为他会以较低的价钱工作,但这可能会使孩子们被这样一些不幸的、盲目崇拜的、堕落的、腐化的和懦弱的人种玷污和毁掉……我们缺少的是白色人种……只有这个种族被证实了能自我管理或具有真正进步的文明。”(45)
传教士从道德上诋毁美国亚裔,影响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大部分人。
同时,美国媒体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的作品也在误导民众。正如赵健秀所指出的,媒体“热衷于华人女子对华人男子的诘难”。(46)它们渴望继续传教士对华人女子的援救事业,重现植根于排斥亚洲移民法中的性别隔离。张莉莉(Lily Chang)在《华裔美国女孩是什么样子的》中写道:“一旦我们离开了唐人街的餐馆,我们更喜欢自由的爱人,(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情感和更热烈的风格。简言之:白种人。”(47)赵健秀毫不犹豫地批评张莉莉所持的“极端的认同转变的表述”和流露出的“白种幻想”。(48)据赵健秀研究,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仍被作为种族和道德上的他者出现在媒体上。在排斥华人移民法颁行和传教士援救亚裔妇女事业开展期间及之后,美国媒体始终在创造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作品误导大众,这些作品的内容包括合法化的种族主义和早期美国传教士对亚洲移民的歪曲性描写。
媒体对美国亚裔不断实施“形象控制”。(49)在形象的构建中,亚裔美国人被他者化。正如达雷尔·Y·哈玛莫托(Darrell Y.Hamamoto)所指出的那样,“形象控制”是“为使他们(指美国亚裔——引者注)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文化上处于边缘、政治上软弱和精神上被疏远”。(50)
伊莱恩·H·金、达雷尔·Y·哈玛莫托和吉娜·马尔凯蒂(Gina Marchetti)等美国亚裔学者在研究中都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作品中出现的亚裔有两种类型:“好的”亚裔和“坏的”亚裔。
伊莱恩·H·金认为,对于亚裔美国人,媒体作品有一种普遍性的描写倾向:“‘坏的’亚裔是阴险的恶棍和残忍的游民,不能被欧洲人所控制,因此都必须被消灭。‘好的’亚裔是可以被欧洲人英雄拯救的无助的异教徒,或是忠诚、可爱的合作者、伙伴和仆人。”(51)
达雷尔·Y·哈玛莫托对“好的”亚裔的研究显示,白人青年会去寻访贤明的亚裔,可是,一旦白人青年学会了他们所需要的本领,贤明的亚裔就成为他们社会中的下属,更是在他们的保护之下。(52)在涉及亚裔的电视节目中,“好的”亚裔的作用是消灭那些不可同化的“坏的”亚裔,同时要给人一种白人是谦逊的和无私的印象。“成年后的白人英雄被号召去保护那个在白人和‘坏的’亚裔手下饱受折磨的黄皮肤师父,以报答他传授特殊本领之恩。从表面上看,这种象征性的‘报答’形式似乎是无私的;而事实上,这种世代交替的倒置使学生重新得到在他的师父之上的一个优越的社会地位,从而保留这种拱形的白种人/统治-黄种人/从属的关系。”(53)
“好的”亚裔还可以是“无私的”和可有两性关系的年轻亚裔女子。达雷尔·Y·哈玛莫托对约翰·曼特利(John Mantley)的电视节目进行了研究。《荒野大镖客》(Gunsmoke)是一个亚裔女子作为白人男子的异性伴侣的故事。在《枪手》(Gunfighter,R.I.P.)中,亚裔洗衣工和他的女儿被三个流氓骚扰,洗衣工被杀害了,就在女儿要被侵犯的关键时刻,一个白人英雄出现了,他把这三个流氓打败,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是这个年轻亚裔女孩的照顾使他生还。这个白人英雄搬到她的家里,并不可避免地与她坠入爱河。在故事的最后,三个流氓又回来了,这个亚裔女孩跳出窗户转移流氓的注意力,再一次救了白人英雄一命。达雷尔·Y·哈玛莫托指出,在这类描写白人英雄和亚裔女子之间关系的电视节目中,亚裔男子被排除了:为了创造白人男子的英雄行为,他必须死去。这样,这个白人英雄取得照顾亚裔女孩的位置,既是社会的,也是两性间的。与描写非白人男子与白人女子之间关系的电视节目不同,白人英雄不受种族界线的约束,但得承认他继承了亚裔男子的财产,并得到了亚裔女子。哈玛莫托指出:“哪里出现族际通婚,哪里就有可被宽恕的过错,特别是通婚出现在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非白人女子之间。一个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结合使得这种族际通婚的形式更可被接受。”(54)安·斯托勒(Ann Stoler)指出,这是一种建立在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不道德的权利关系,这种族际通婚的类型是一种“性控制”的“基本类型和种族标志”的形式。(55)
基于这种种族的和性别的支配范式,在好莱坞和美国主要电视网络发展出了一个专门描述亚裔美国人的流派,吉娜·马尔凯蒂称之为“白人骑士”流派。(56)这个流派宣传的是种族化性别歧视,内容充满被阉割的亚裔男子以及白人男子对亚裔女子富有色情意味的想象。当亚裔男子受压制时,亚裔女子就被白人英雄拯救。这是19世纪晚期传教士对亚裔女性的救援事业以一种新的形式的重演。对“白人骑士”的基本叙述,被置于一个三角关系中:一个白人英雄、一个柔弱而美丽的亚裔年轻女子,以及一个“坏的”且毫无男性气质的亚裔男子。在这个流派的作品中,在为亚裔女子讨回公道之前,“坏的”亚裔男子常被白人英雄杀死。1985年好莱坞出品了电影《龙年》(Year of the Dragon),故事发生在某个唐人街。男主角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是一名律师,他代表着正义;男二号乔伊·泰(Joey Tai)是一个年轻的亚裔恶棍。显然,斯坦利·怀特和乔伊·泰之间是对手关系。斯坦利·怀特和乔伊·泰分属不同的种族,两个人都英俊并为各自不同的目的使用暴力。当斯坦利·怀特与美丽的亚裔女主播特蕾西·朱(Tracy Tzu)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受到乔伊·泰及其同伙的袭击时,斯坦利·怀特如同“骑士”般的行为使种族间的张力凸显出来。最终斯坦利·怀特打败乔伊·泰及其同伙,使唐人街恢复了秩序,并赢得了特蕾西·朱的芳心。根据吉娜·马尔凯蒂的分析,这部影片所表达的是,斯坦利·怀特“作为白人、男性和明确的异性恋者的英雄”,象征着白人父权制的社会秩序;而乔伊,泰以他“女性化的姿态接受了白人英雄的支配”。(57)
在历史上,传教士和媒体在控制亚裔美国人的形象上都追求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制造认同”(58)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且告诉公众“应该如何对待那些他者”。(59)正如B·威廉斯(Brackette Williams)所说,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典型,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生物学上被赋予的原始欲望,即比之‘异类’更喜欢‘我类’”。(60)经过美国政府以及传教士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亚裔美国人被强制性地归入“异类”,亚裔男性和女性在“性别角色体系”中被划为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分别与对亚裔体力劳动的需求和“我类”在性方面的需要相一致。
结语
赵健秀曾说:“如果所有的白人都已从美洲消失的话,现在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没有更多的白人来摆布我们,或让我们害怕、设法铭记或证明我们自身。为什么我们美国亚裔……必须团结起来?什么是‘亚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61)如果跳到美国的现实之外,赵健秀的想象或许可为他提供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他或许可拥有咫尺空间和片刻时间去寻找亚裔美国人的自我认同。赵健秀要寻找亚裔美国人的认同的行为,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行动的典型。恩洛(Cynthia Enloe)指出,这是“源自男性化的记忆、男性化的耻辱和男性化的期盼”,是由“对‘被阉割’的愤怒或是变成‘餐馆工的国度’”点燃的。(62)
对于这种按种族定义“我类”和“异类”的二分法,赵健秀只好不断地否定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亚裔身份的各种定义。陈耀光曾对美国华裔认同这样论述:“美国华裔的身份还有待定义。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我们不是什么:不是欧洲人,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黑人。为了使这个身份变得更清晰,我们必须首先‘抛开什么是中国的和什么是白人的’,然后试着达到一致……美国华裔的认同还不存在,随着它的不断积累,它将会出现。”(63)
美国亚裔社区中存在的种族化性别歧视也妨碍了亚裔对本族群的认同。艾斯比利图通过研究发现,种族化性别歧视是白人男性霸权主义的产物,她指出:“要赢得白人男性的爱,亚裔女性不仅必须放弃亚裔男性,而且必须放弃她们整个的文化。”(64)在这种意义上,美国亚裔男性遭受双重的阉割:一是来自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二是来自本族裔女性。这种处境与美国黑人男性相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曾诅咒“那些继续追随白种男人的黑人妇女”。(65)根据P·皮尔斯(Paulette Pierce)和B·威廉斯的分析,当时黑人妇女“与白种男人相通被视为一种制度上的构成,并成为一种常态”。(66)
美国历史上白人男性、亚裔女性和亚裔男性之间的这种三角关系,在各种情形下都是不正常的。首先,在历史上,美国政府不仅不给予亚洲移民公民权,而且建立了种族化的“性别角色体系”将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相互分开。这样,政府既是种族歧视者又是性别歧视者。其次,在各种代理人的帮助下,亚洲女子被非法走私到美国的性产业中,供亚裔“已婚单身汉”和白人男子消遣。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一个“隐蔽的皮条客”。(67)第三,美国的一些白人公民,如传教士和“白人骑士”,把亚裔女子从妓院里“援救”出来,成为充满矛盾的“行善者”,而且这种“善行”只针对美国亚裔女子。第四,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而言,美国的亚裔男子既是危险人物,要被“白人骑士”杀死,又是可被培养为皈依基督教的“模范少数族裔”。(68)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难以走出这种怪异的三角关系,这也反映在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冲突和对话中。种族意识深深地渗透于美国社会,生活在那里的亚裔为建立本族裔的自我认同,确实需要持续的努力。
在美国,种族意识在白人主流社会“塑造”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外在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意识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它从白人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非白人进行殖民时就已开始,并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种族意识充斥着一系列两极分化的概念,如文明的与不文明的、高尚的与野蛮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用了“类型学的分期”(typolosicai time)一词来说明这种思维贯式。他说:“类型学的分期成为一种资格衡量的基准,如文字出现以前比之有文字的、传统的比之现代的、乡村的比之工业的,以及一大堆此类的排列,这些成对的概念还包括部落的和封建制的、乡村和都市。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分期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它的矢量和自然的内涵。应代之以一种动态的衡量标准,这种衡量标准体现出国家的一种性质;然而,这种性质参差不齐地分布在这个世界上。”(69)
这种双重意义的从定性上的划分,将世界划分为变迁的与永恒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自我与他者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并将这种人为划分“合法化”。美国历史上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以及传教士和媒体对美国亚裔的歪曲描写,都是这种定性划分的结果。按照吉塞拉·卡普兰(Gisela Kaplan)的说法,这种国家的类型产生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它“采用了一种霸权的姿态,相信它自己的文化是更好的,因此相信自身有责任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播给他人”。(70)
当美国的多数公民相信这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时,“异类”在这个国家就易于成为种族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牺牲品。换言之,政府和白人公民都在促进“我类”的团结,但这种类型的“团结”是以牺牲本政体中“异类”为代价的。例如,1885年在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Rock Springs)发生的对美国华裔的大规模屠杀即是这种“团结”造成的恶果。据一个目击者说:“在暴乱中,那些掠夺者和抢劫者是(白种)男人、(白种)女人和(白人)小孩。即使那个原来教中国人说英语的女人,也在偷手帕和搜寻其他物品。”(71)
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美国亚裔自己的传统文化被美国主流社会对文化的定义所践踏。两种文化类型跨越彼此的边界,通过美国亚裔为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努力,形成一些新的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族群一样,美国亚裔的认同有待于完全摆脱种族的和性别的压迫及文化差异才能形成;也只有到那时,美国亚裔才有可能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
注释:
①②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1991,p.xi,xii.
③转引自Hsiao-Hung Chang,"Gender Crossing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Melus,Spring,22(1),1997,p.18.
④Sucheng Chan(ed.),Social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Lewiston:The Edwin Mellen Press,1989,pp.25-28.
⑤Jozsef Borocz and Katherine Verdery,"Introduction",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8(2),1994,p.233.
⑥Flora Anthias and Nira Yuval-Davis,"Introduction",Woman-Nation-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p.1.
⑦转引自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p.103.
⑧Gerda Lerner,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38.
⑨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4,p.3.
⑩(11)S.W.Kung,Chinese in American Life:Some Aspects of their History,Status,Problems,and Contribution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p.64,80.
(12)(13)Cheng-Tsu Wu(ed.),Chink!,New York: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2,pp.32-33,5.
(14)(15)Sucheng Chan(ed.),Social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p.138,19.
(16)Sucheng Chan,Entry Denied: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1882-1942,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p.106.
(17)(18)(19)Maxine Hong Kingston,China Me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p.156,156,153.
(20)(21)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35.
(22)Elaine H.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9.
(23)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31.
(24)这是粤语贬义俗语。
(25)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4.
(26)(27)(28)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46,126,31.
(29)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31.
(30)转引自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19.
(31)Cheng-Tso Wu(ed.),Chink!,p.129.
(32)(33)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Jeffery Paul Chu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p.xi-xii.
(34)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16.
(35)(36)(37)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186,186,186.
(38)英国女王A·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期间(1837-1901年),英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同时扩大对殖民地的掠夺,几乎享有对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这一时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39)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180.
(40)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48.
(41)(42)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187,189.
(43)转引自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188.
(44)Benson Tong,Unsubmissive Women: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p.189.
(45)Roger Daniel,Asian America: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Se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50.
(46)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27.
(47)转引自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27.
(48)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27.
(49)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87.
(50)Darrell Y.Hamamoto,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5.
(51)Elaine H.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4.
(52)(53)Darrell Y.Hamamoto,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p.7,8.
(54)Darrell Y.Hamamoto,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p.39.
(55)Ann Laura Stoler,"Making Empire Respectable: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ual Mora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of Colonial Cultures",American Ethnologist,12(4),1989,p.635,636.
(56)(57)Gina Marchetti,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6,212.
(58)Edward S.Herman and Noam Chomsky,X 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8,p.xi.
(59)Noam Chomsky,Media Control: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1997,p.12.
(60)Brackette Williams,"Introduction:Mannish Women and Gender after the Act",in Brackette Williams(ed.),Women Out of Place:The Gender of Agency and the Race of Nationality,New York:Routledge,1997,p.3.
(61)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Wong(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p.2.
(62)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4.
(63)转引自Elaine H.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175.
(64)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95,97.
(65)(66)Paulette Pierce and Brackette Williams,"'And Your Prayers shall be Answered through the Womb of a Woman':Insurgent Masculine Redemption and the Nation of Islam",in Brackette Williams(ed.),Women Out of Place:The Gender of Agency and the Race of Nationality,p.202.
(67)John Lie,"The State as Pimp:Prostitu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State in Japan in the 1940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38(2),1997,p.263.
(68)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p.110.
(69)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th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23.
(70)Gisela Kaplan,"Feminism and Nationalism:The European Case",in Lois A.West (ed.),Feminist 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7.p.9.
(71)Cheng-Tsu Wu(ed.),Chink!,p.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