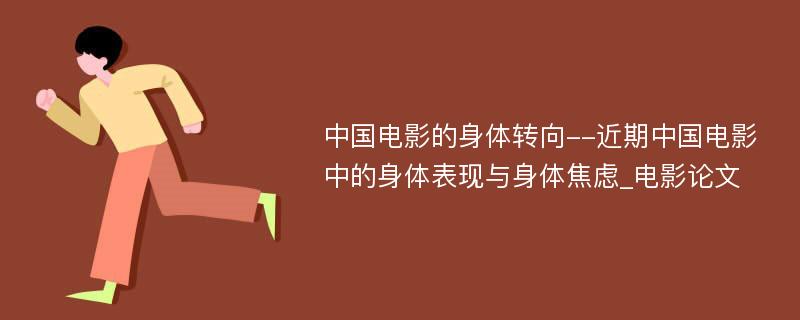
中国电影的身体转向——近期中国电影中的身体呈现与身体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焦虑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章子怡在《艺伎回忆录》中的身体裸露和激情场景经由网络传播,几乎成为中国2005年度最流行的电影/文化事件之一。后来网上证明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日本演员松坂庆子,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在网络剧烈的声讨中,章子怡的“国际影星”和“中国女子”的双重身份被富有意味地置换了。女性身体,特别是一个目前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年轻女明星的身体,再次引发了国民的某种身体焦虑和身份焦虑,尤其是当她与“日本”、“日本男人”扯上关系的时候。与此相关的链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五代的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女卫生员遭遇日本兵那个段落的“原初”版本,是烟鬼一枪打死了女卫生员。尽管我们从这个细节处理中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影片《桥》的某种影子,但其间蕴含的某种特殊“意味”却是独特的。一个年轻的女卫生员遭遇几个身强力壮的日本鬼子包围,几乎所有中国观众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文学的阅读经验来猜想下一步的细节,而可能发生的一切不仅事关女卫生员的“清白”,同时也事关民族的“清白”。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可以看成章子怡事件的某种前兆。民间对于日本的种种情绪,时常通过娱乐新闻(带有政治色彩)觅得宣泄的通道。
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电影中适度的身体裸露在国内已经不算什么太大的新闻。比起相对拘谨的电影,文学中的情色描写,绘画、摄影、彩绘、时装表演中的人体,已然十分“前卫”了,更遑说遍地开花的性用品商店。邬君梅、李冰冰、钟丽缇三女星为《时尚健康》杂志宽衣解带,虽说目的在于推动“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但还是引发争议,被许多人读解为情色之作。在近年的电影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相关的细节,比如黄健中的《银饰》因为女演员“露点”而受到的特别关注。碟片封面将主演字幕叠印在可能“露点”的地方,犹如一部裸露身体的欧洲片被日本人打上了马赛克,虽说主观意图良好,却也会更令人想入非非。有时候,适度的遮蔽才是更有诱惑力的挑逗。
与这些“电影事件”相关的是,在近年的电影创作中,包括王小帅的《青红》、顾长卫的《孔雀》、李玉的《红颜》、贾樟柯的《世界》、李虹的《诅咒》、张杨的《向日葵》、侯咏的《茉莉花开》、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章家瑞的《芳香之旅》以及华裔女导演伍思薇的《面子》中,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身体关注、身体呈现和身体焦虑。而这种身体焦虑可以读解为转型时期身份焦虑和精神焦虑的某种征兆。
一、《世界》:一个有意味的电影文本
每次看《世界》,我总是困惑于影片开头女主角赵小桃尖利地喊叫着寻找创可贴的那个长镜头。镜头随着赵小桃的走动穿越后台,进而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的视觉主题:由后台/化妆间指涉的空间(城市)与由赵小桃/女演员指涉的身体(女性)。
在贾樟柯的第一部剧情片《小山回家》中,已经有关于城市的视觉呈现。而其后来的《小武》、《站台》、《任逍遥》则多将空间置于城镇——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世界》的视觉主题与这几部作品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相关性,观众视线中的男女主人公说着山西话,而他们身处的却不再是偏远落后的小城镇,而是大都市北京市郊的“世界公园”。如果说,贾樟柯以往影片的空间主要倾向于一种纪录性呈现的话,那么,《世界》所呈现的却是一种视觉“幻象”,一个被现代中国建筑设计者制造出来的关于“世界”的空间幻觉。在这个密集着曼哈顿,英国大本钟、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金字塔等世界著名景观的空间里,身着“工作服”的山西民工更像是一群粉墨登场的扮演者。影片片头“不出北京,走出世界”字幕之后城市化/现代化的“世界”背景映衬下入画的捡破烂者,有力地揭示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多元混陈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在贾樟柯看来,“很多现代化景观是假景,比如说楼房、城市、地铁、城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假景,但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它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实景。但这些并没有改变我们什么,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具体的处境,那些原始的处境没有改变”。① 视觉空间的多元并存,恰恰是当代中国电影在城市空间呈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犹如那些视觉空间里人造景观的假定色彩,《世界》显现出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与空间有关,与身体有关。
一个有趣的事实,影片中人物约会的所有场地都不属于“个人”,显现出空间与生活其间的人的一种疏离。不但赵小桃的表演舞台属于一个想象的虚拟空间,即使是如小旅店等充满着生活质感的场所,也更像是一个“表演”的舞台。赵小桃与成泰生的第一次约会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旅店,成泰生要求赵小桃证明与前男友不再藕断丝连(前男友刚刚去了“真实”的乌兰巴托),而证明的方式是“身体”。这其实是现实中某种性别强权意识在影片里的投射。当这种证明遭到拒绝的时候,被成泰生认为是“装纯装处女”。以女性“身体”的“奉献”来证明爱情,不仅是影片中男性对女性的强制性要求,事实上也成为女性的无意识。赵小桃与成泰生的第二次约会空间是更加富有意味的。他们选择了“世界公园”里一架退役的作为旅游用途的飞机,赵小桃还穿着空姐的服装,这使得整个场景更像是一场虚拟的爱情表演。在虚拟的“世界”空间里,爱情也被虚拟,而真正的内涵却被抽空了。在观众带着欲望的视线里,爱情被抽象为一个符号,一次模拟的旅行,一个空洞的能指。两人的第三次约会则在看上去更加“私人”的赵小桃宿舍里。在这样一个私密的更利于爱情滋生的空间里,亲昵却被突然闯进来的那对不断吵闹的情侣给打断了。
与赵小桃和成泰生的关系形成对应/对照的,正是那对从后台吵到宿舍的恋人——焦虑的男人老牛和他的女友小魏。老牛的焦虑看上去属于爱情/精神焦虑,而其骨子里则是无法“控制”女性身体的焦虑,他无法真正“管”住女性身体,便只能用不断的怀疑、质问以至于焚烧自己的衣服(毁损身体)来去除焦虑,而引发的却是更大的焦虑。从叙事上看,他的焦虑终止于那场婚礼。而婚礼上女孩子们的祝酒词——“以杨贵妃、潘金莲、玛丽莲·梦露、麦当娜等一切美女的名义,为世界和平、妇女解放、脸无雀斑,干!”——在对宏大主题的调侃中显露了对身体(脸无雀斑)的关注。
尽管《世界》是一部关注身体的影片,但身体在影片里的展示却呈现为两极。一极是“世界公园”表演中女性身体及其服饰的美轮美奂。表演的场景越是华丽,越是虚幻,就越是映照出现实空间和现实身体的不堪。赵小桃与成泰生在宾馆完成身体“证明”的那个段落,两人拥抱的姿势都显得别扭,赵小桃穿着内衣的身体既显示不出美感,甚至也没有诱惑力。男女交欢的场景在影片中的身体呈现却显现出其“丑”的一面。而赵小桃的表白——“我也就这点资本了,你要是骗了我,我可是什么也没有了”——则再一次显露了人物对于身体的巨大焦虑。“资本”在赵小桃那里更多不是指向爱情,而是身体。身体的沦陷是一场爱情的赌博,事实上也是有关赵小桃身份焦虑的投射。
这种焦虑同样还体现在赵小桃与俄罗斯姑娘安娜的关系上。安娜在“世界公园”的表演,那种身体展示在中国文化空间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职业现实。而当赵小桃与安娜在娱乐城相遇和痛哭时,则明确将安娜如今在从事的“营生”不可置疑地指向“堕落”。身体的展示与出卖有不同的方式,间接地被当作“表演”或者“艺术”,直接的则毫无疑问是“堕落”。
当赵小桃向成泰生提出结婚,而紧接着的婚礼场景的主角却不是她。因有“温州女人”的介入,赵小桃穿婚纱的场景最终也只能是一场属于“世界”的虚拟表演。影片结尾贴着“囍”字的房间同样并不属于赵小桃,而是“别人”的。这是影片整个叙事进程中最后一个属于赵小桃和成泰生共同拥有的空间。在“别人”的空间里,煤气中毒成为一个意指性符号,按照导演的说法,是“想把影片结束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在世界公园之外,是那些假景之外的一个真归宿”。② 死亡成为一个“真归宿”——“我们是不是死了?”“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
导演认为赵小桃是“一个传统男性世界里想要捕获的一个东西”。③ 我一直很迷惑于赵小桃眼神的那种清醒和旁观。即使单纯在这个女性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裂隙的电影文本。从赵小桃作为女主角的身份、作为片中角色的身份看,她毫无疑问地都将成为观众的视觉/欲望对象,但影片却不断终止观众对于她的欲望性审视和解读。除了那几个舞台表演的华丽场景,赵小桃始终以一种“拒绝”的姿态成为成泰生“捕获”的对象,同时也意味着拒绝成为观众视线/欲望“捕获”的对象。而这种拒绝更多是“身体”意义上的。即便是在那个终于接受“身体”的段落里,导演也抹去了几乎所有与欲望有关的元素,无论是其更“中性”的视觉呈现,还是赵小桃靠在成泰生身体上以及拉开成泰生内裤观察的那种冷静,都明确无误地阻止着任何走向身体欲望的企图。充斥在赵小桃内心的,始终是失去“这点资本”的焦虑。倒是成泰生与“温州女人”的调情更具有欲望的暧昧性。
二、身体和身体焦虑:作为一个视觉主题
《世界》同时呈现了城市空间和女性身体这样的视觉主题。有学者在研究上海无声电影时指出:“如同其他国家的无声电影一样(俄国、斯堪的那维亚、德国、法国),现代性的矛盾透过女性的形象具体体现在这些女性的身体上。她试图在这些矛盾中过活,却往往失败,在电影终结时沦为一具尸首。如同19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那样,妇女既是现代都市性的寓言,也是它的转喻(metonymies)。她们体现了城市的诱惑、不稳定、匿名及晦暗不明,这些特征时常通过将女性的面孔、身体与上海的灯火交错并置并抽象成象形文字得以表现。用叙事语言来说,女主角成为社会压迫和不公的焦点;强奸、浪漫爱情的受阻、被抛弃、牺牲、从妓,都成为现代文明危机的隐喻。”④ 事实上,《世界》对女性身体的展露是极为有限的。中国人的身体焦虑并不像许多西方人那样是由狂欢带来的,也不像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是由压抑带来的。焦虑来自于某种无名的“恐惧”——对于失去“这点资本”的恐惧。
有意味的是,在李玉关于《红颜》的访谈文字里,我们发现了女导演创作这部影片的动因也与“恐惧”有关:“最早之所以写这样一个以16岁少女怀孕为发端的故事,跟我自己少女时代某种内心的恐惧感有关。”⑤ 在李玉的叙述中,即是对“突然就被发现怀孕了,并因此被学校开除”⑥ 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影片本文的叙事中得以呈现的时候,焦虑感却并非产生于女主人公小云,而是产生于她的母亲。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母亲“不要脸”的责骂是对女儿失去贞操的焦虑感的体现。在母亲眼里,“脸”是一个比身体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女儿未婚先孕的事实被曝光并导致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母亲的焦虑并非指向对女儿身体的担心,而是指向对失去“名声”的忧虑。尽管导演以“红颜”来命名这部影片,而对小云的身体展示却并不有意指向“性感”或者“诱惑”的价值判断。影片中出现的第一次洗澡镜头,小云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摄影机/观众视线中的身体裸露并不具有太多的性的诱惑意味。小勇偷窥视线中的小云洗澡,是影片里最明确地指向欲望的场景,但这个场景因为小云与小勇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而削弱了欲望色彩。在影片的大部分段落里,导演似乎并不希望将观众导向一种跟欲望和性有关的视觉主题,尽管女性身体是影片视觉主题的重要部分。而钱老板勾引小云遭到拒绝后所说的“你哭啥子嘛,就像你是处女一样,刘万金结过婚的都沾得你,我就沾不得”,让我们想起《世界》里成泰生遭遇赵小桃拒绝之后的那段郁闷之词。两个互不相同的电影文本在关于女性性权利的表达上,有着共同的批判性指向。以“装处女”来指责不顺从的女性,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男性无法控制和驯服女性性向的焦虑”。⑦
与身体焦虑的视觉主题相关,恐惧在近期中国电影里得到不断的表达。《青红》中那个简单粗暴的父亲对女儿的不断管制,终于在女儿与其男友发生关系之后达到高潮。父亲无法控制女儿身体的焦虑既是对女儿失去贞操的愤怒,同时也隐含着对其怀孕的一种深刻恐惧。而其内心真正的焦虑和恐惧,则是因为女儿如果跟当地男孩恋爱,就无法回城——回到“故乡”上海了。与《世界》以虚拟空间展示城市不同,城市在《青红》中呈现为缺席的存在。尽管城市以新潮服饰、地下舞会等各种视觉元素侵入,但真正的城市,青红的父辈们渴望回去的“故乡”,在影片本文的叙事中却始终是缺席的。与《青红》相似,《向日葵》同样有一个专断粗暴的父亲“压抑”孩子的故事,只是,这个孩子置换成了一个名叫张向阳的男孩。在张向阳的视线里,红帽子红围巾的滑冰女孩于红所呈现的优美的视觉表象在观众一方形成了同构效应。青涩初恋最终以于红在张父陪同下做人流为终结。与多年前的《爱情麻辣烫》相比,影片更多呈现了女性身体的困境,而不仅仅是感情的困境。而且,张向阳羞怯视线中于红主动的身体展示更加凸现了这种困境的悲剧意味。影片结尾的“生育”段落构成了与开头富有意味的回环。尽管《诅咒》并没有指涉前述影片那样与未婚女性怀孕有关的身体焦虑,但作为一部恐怖片,身体与心理恐怖一直贯穿着影片始终。因为女主人公田原的舞者身份,性感舞动的女性身体成为影片富有视觉表现力和欲望张力的视觉表象。女性的身体恐惧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失去身体的恐惧。影片开头的小美之死的视觉表象直接建构出恐怖氛围。此后,对于丧失身体的恐惧一直现实地(遭遇追杀)或者精神地(噩梦)出现在田原的生活里。二是对不能在女主角竞争中胜出、以舞者身份在舞台上展示身体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团长那里转换为对渐渐年老色衰的不安。三是对身体无法证明爱情拥有的恐惧。“每个人有太多的秘密,不想让人知道,有时候,保守秘密,是不希望对方受到伤害。”身体的激情与缠绵,男朋友的怀抱,反而莫名地加重着不安和猜忌,短暂的肉体欢愉丝毫无法掩盖和摆脱内心的恐惧。
比较而言,《面子》(Saving Face)则涉及了异域文化中华裔女性的多重困境。由陈冲扮演的妈妈还在为女儿的婚姻问题烦恼的时候,自己却怀上了孩子。因为“面子”而引发的身体焦虑在影片中呈现为剧烈的戏剧冲突。女儿威尔(Will)与另一个女子威恩(Vivian)的同性恋情不但借两人做爱的暴露场景直接予以展示,而人物意图用以“证明”爱情的,则是接吻——身体的接触。当威恩第一次向威尔索吻证明爱情的时候,铁栅栏的遮蔽巧妙地规避了尴尬;而威尔在机场追上威恩,威恩再次索吻要求证明爱情时,威尔犹豫了。在影片结尾舞会的场景中,两人拥吻的俯拍镜头则以身体的接触“证明”了爱情(即使是同性恋)的存在。
三、中国电影的身体转向
“身体转向”,是当代哲学文化密切关注的问题。“如果说,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自身分成两个部分,分成意识和身体,而且意识总是人的决定性要素,身体不过是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的话,那么,从尼采开始,这种意识哲学,连同它的漫长传统,就崩溃了。”⑧ 而在当代理论中,福柯引爆了人们对身体的极大关注,“福柯关注的历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的历史;那是个生产主义的历史。而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身体从它的生产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⑨“从尼采和福柯这里开始,历史终于露出了它的被压抑一面。一切的身体烦恼,现在,都可以在历史中,在哲学中,高声地尖叫。”⑩ 在“身体转向”的世界性思潮中,身体与哲学、身体与生命政治学、身体的性别政治、身体与消费文化、身体与空间等问题受到了空前关注,国内也相继出版了汪民安/陈永国主编的《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民安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岗/顾铮的《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相关文集。
中国电影对身体问题的压抑或者关注更多并非哲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在1949年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体问题在中国电影中一直是被悬置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复兴的时期里,《湘女萧萧》、《良家妇女》、《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指涉“乡土”的影片表现出对女性压抑主题的表达,而压抑的核心性毫无疑问是指向身体的。而同时期的《太阳雨》、《给咖啡加点糖》等城市电影的典型作品,却仍然把关注焦点落在精神焦虑,并非身体焦虑上。《本命年》成为城市电影中较早指涉身体焦虑的作品。
无论是出于电影审查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是出于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近期指涉身体焦虑的影片中对于身体的展示是非常有限的。而在身体焦虑的背后,经常蕴含着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元素,从而达到社会文化批判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转向,“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11) 《青红》中青红苦涩初恋的背后,隐含着一个父辈们渴望回城的社会故事。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回城的目标受阻,父亲不惜将女儿的男友以强奸犯的罪名送进监狱,社会批判的主题昭然若揭。在《向日葵》这部以“向日葵”为主体意象的影片中,童年的创伤记忆是作为一个宏大的主题出现在叙事中的,一方面是唐山大地震和毛泽东逝世,那曾经是20世纪的中国留给一代人的记忆;而此前张向阳窥见父母做爱的场景则成为社会创伤的一个前兆。“父亲”作为一个闯入者所带来的裂隙在地震后寻找“父亲”的段落中得以暂时修复。在《诅咒》的现实恐怖背后,同样是一个关于童年创伤记忆的故事——偷窥父亲与自己的钢琴教师做爱,母亲上吊,父亲将其遗弃在游乐场。《芳香之旅》中对于范伟扮演的男主角丧失性功能的展示,则包含了更加明确的政治批判意图。
学者张颐武在《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一文开头提到了《女模特的风波》这部很有意味的影片,“电影通过一系列的误识展开故事。误识导致了焦虑,也引发了矛盾的看法。接着到来的是一系列由‘身体’的展现带来的秩序的瓦解”。(12) 张颐武认为,影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时刻强调身体的纯洁和美好的含义,但身体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展现”。(13) 同样的悖谬在上述中国电影中依然存在。一方面是身体问题开始受到极大关注,另一方面却是真正的身体在电影中却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我说的不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表达,作为视觉表象的身体表达在今天的中国电影中依然是极有限度的,对于电影分级制的千呼万唤不出来就是一个证明。更重要的是,身体在中国电影中主要还是作为社会批判的手段,而身体本身,身体的欲望,仍然是被悬置的。同样的,身体也没有成为主要用于消费的视觉表象。起码在上述影片中,女性身体都不构成商业“卖点”。周蕾在分析《神女》时指出:“在镜头前,她身体的不同部分,如笑容、大腿、手臂、发式或漂亮的衣着,乃是社会被置换的欲望的所在地;尽管她身为母亲,该妓女通往其自身女性性欲望的路途却持续受阻,被警戒,并受到社会对女性贞操的父权准则的惩罚。”(14) 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本文所论述的电影。电影本文中女性欲望的受阻,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银幕前观众欲望的受阻和无意识的无法满足。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还比不上选美,“选美比赛以准美学的形式反复重申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意识形态”。(15)
注释:
① 贾樟柯、吴冠平《〈世界〉的角落》,《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第34—35页。
②③ 同①,第36页。
④ [美]米连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第48—49页。
⑤⑥ 李玉、关雅荻《女性视角下的世俗言说——李玉访谈》,《电影艺术》2006年第1期,第34页。
⑦ 孙绍谊《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好莱坞的上海想象》, 《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第37页。
⑧ 汪民安、陈永国《编者前言——身体转向》,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⑨ 同⑧,第21页。
⑩ 同⑧,第21页。
(11) 布莱纳·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译,《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第20页。
(12) 张颐武《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13) 同(12),第270页。
(14) 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4月版,第45页。
(15) 理查德·莱帕特《绘画中的女孩形象:现代性、文化焦虑与想象》,林斌译,《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第274—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