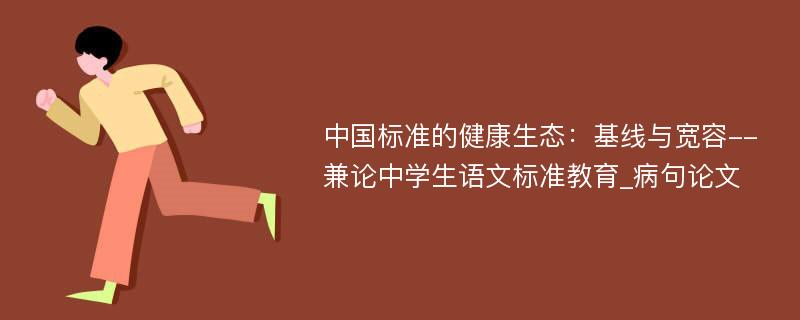
语文规范的健康生态:基准线和宽容度——兼议中学生的语文规范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准线论文,语文论文,中学生论文,生态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规范”绝对是个很微妙的词语,因为它本身就很难讲得清,需要费很多很多的口舌来解释:怎么做是规范的,怎么做又是违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规范”实在包含着人们太多的主观想法。至于语文规范,就更是个令人目眩的领域,因为语文不仅包含语言和文字,而且这两个要素又有本体和应用等多个层面上的复杂问题。
可见,要想说清楚“什么是语文规范”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那么,“语文规范”是不是真如一团乱麻,无从说起了呢?
一、语文规范的基准线
人们说“规范”,总是指向某种理想状态的。遣词造句、说话写文章,谁都希望辞能达意、文通字顺。表达出现障碍和失误的时候,所谓“规范”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写错了字,说错了话,还有提笔忘字,言不及义,等等,自然都不可能是理想状态,也就说不上“规范”了。可见,规范是一种底线。
底线就是一条基准线,超过了这个起码的界限,就会给他人的理解带来麻烦,不会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这条基准线划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有的:语言的各级结构单位都有着自己明确的基准线。
就汉语而言,我们可以把语言单位简单地分为字词和句篇。
1.字词与音形义
在字词的层面,有形、音和义的规范问题。一个字怎么写、有多少笔画、笔画的顺序都是有章可循的;这个字(或者词)怎么读,有没有多音、异读等现象也有据可查;至于这个字和词的意义,哪些是概念义,哪些是附加义,也都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
像《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常用字笔画检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等都是和字的写法有关的规范法规;像《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等则是关于词语的读音和写法的;而被社会规约所认可的字词的意义,多半要参照一些典范的工具书,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
2.句篇与病句
在句子和篇章的层面,语文规范的基准线就是:不可以出现病句。所谓病句,就是指不合规范的句子。病句作为一种反例,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所谓“语言规范”的具体要求。所谓规范,一是要符合语法的组合规则,二是要符合语义的搭配要求,三是要符合语用的表达习惯。因此,语文规范的基准线就是不可以出现语法病句、语义病句(这两项多与句子相关)和语用病句(多与语篇相关)。
(1)语法病句
语法病句是没有满足语法合格性而形成的病句。语法病句涉及的是语法的基准线,这条基准线主要是指词汇和句法方面的规范,相应的病句就有词汇病句和句法病句两小类。
与词汇相关的语法规则主要涉及词性、词法功能和汉语特有的语法现象——量词。对应的病句类型包括:词性误用、词法功能误用和数词量词误用。
句法的要求细致繁多,我们不妨以汉语的句法特点为基准线来进行分析。在汉语中,语序、虚词和结构都具有语法意义。因此,也就存在着三类对应的病句,前两类即:语序错误和虚词误用;结构类的错误则包括:成分残缺、结构纠缠和句式错误。在复句的范围内,还会出现关联词语的使用失误。
(2)语义病句
语义病句是没有满足语义合理性而形成的病句。语义的基准线在于逻辑。
这类病句表面上看并没有明显的语法错误,但往往会出现逻辑问题,表现为相互搭配的成分在语义上不能贯通,造成“搭配不当”,包括:直接成分搭配不当和间接成分搭配不当。
(3)语用病句
语用病句是没有满足语用有效性而形成的病句。满足了语法合格性和语义合理性的句子,还要满足语境以及交际行为对它提出的要求。
语用规则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都是针对话语理解而言的。成功的交际都要符合“会话合作原则”,这个原则包括质量准则、数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这就是语用规范的基准线。不满足其中任何一条的要求,都会造成理解的困难,从而形成病句。
由于违背这四种准则而造成的病句有:预设错误、表述重复、层次不清、指代失误等等。
可见,汉语的字词句篇都有着明确的规范标准,它们共同构成了汉语规范的一条基准线:字词作为储备单位,如果不达基准,将使语句支离破碎,令人不忍卒读;句篇作为使用单位,如果在语法、语义和语用层面无法全面达标,必然出现病句,影响交际。
因而,站在语文规范的立场上,我们还是建议在中学阶段加强字词的读写查检训练,学习一些母语的简明语法,了解基本的逻辑规则。遥想1951年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法修辞讲话》,开篇讲的就是“语法基本知识”。因为,语感从来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书读百遍”的基础上的,当学生对母语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还所知不多时,就很难谈及对语言规范的自觉实践,更遑论对母语的热爱了。“淡化以至事实上排斥语言知识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有损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语文素养的发展,都会降低语文教学的水平”。(刘大为,2003)
二、语文规范的宽容度
语文规范的基准线是一条底线,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以跨越雷池半步,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那么,语言实践是不是就只能依葫芦画瓢,毫无创意可言呢?
对于中学生而言,这个问题尤为突出。青少年时期,是个创造力井喷的阶段;又恰逢国家开放发展的年代,多元文化奔涌而来,观念的冲击和语言的融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猛激烈。语言作为最典型的文化敏感型符号,最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变革的面貌,最广泛地传播着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范型。
两个问题迎面而来:如何看待青少年的语言偏好?这些偏好(或日用语习惯)的本质又是什么?
1.中学生与网络语言
当今的中学生是和网络一起成长起来的,网络是他们的天地和空气。这种便捷极速的载体完全不同于笔墨纸砚的组合,交际的渠道和方式迥异。在这样的情形下,语言文字的使用有其特殊的要求,并带来文本命运的极大改变——雨后春笋式的新生和跌宕叵测的未来并存。
像又“囧”又“槑”的网络“热字”,“稀饭(喜欢)”、“偶(我)”等网络新词以及网络聊天状态下的全新句式等等,都有着某种应用的需要,带来特定的交际效果。这是新的语域特征造成的,网络语言顺应了新的语式的需求。因而,我们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承认网络语言的某些合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顺应了语域发展的要求,他们是语言变革的勇敢的弄潮儿,他们的语言实践符合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2.用语偏好与言语社区
用语偏好的问题往往被想当然地归属为语言规范问题,或者与信息化、青少年网络生存等问题生硬地相提并论。实际上,它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典型的“言语社区”问题。
美国交际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Gumperz)指出,言语社区具有下列特征:它是一种互动的社会范畴,以交际活动为主要目标;是“一种讲话人的非正式组织,将这些人组织起来的是一些思想意识和相近的态度,是语言方面的共同的标准和追求”(甘柏兹,1982)。
青少年的语言交际显然贴切地具有上述这些特征,中学生无疑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区,他们作为“一个讲话人的群体,其内部的某种统一性构成了与其他的群体的差异而区别于其他群体”(徐大明等,1997)。他们相互认同彼此的话语方式,采取相似的言语行为,共同构建了包括网络在内的众多语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事实”。
因此,只要他们的言语活动没有超越网络或小团体的范围,就应该看作是正常现象。语言创新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站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又根本不存在问题。健康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存在多个言语社区,中学生拥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很正常,人们依据年龄、性别、职业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的言语社区,都有着各自的表达特点。只不过中学生的这个言语社团事件频发,动静颇大而已,而这正是这个言语社团的秉性。
可见,对于中学生而言,语文规范并不与语言习惯相抵触,这显示了语文规范的宽容度。这种宽容体现在:在言语社区的内部(相当于一个语言应用的自治区)有着并且允许一些默认的交际规约,是可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但是跨越了这个言语社区,就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接受程度了。
中学生(尤其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需要强化这种“内外有别”的语言意识。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既要熟悉自己小群体的语言习惯,又要掌握规范正式的语言表达方式。缺乏“内外有别”意识或者只会其中之一,都是语言能力不健全的表现,都将影响到今后语言交际的实践乃至社会人格的发展。
三、语文规范与语文生态
综上所述,语文规范其实是个基准线和宽容度相结合的统一体。它以字词句篇的规则为底线,构成大众交流的基本保障;同时,它不仅认可用语偏好,并且在言语社团的内部还授予极大的自主权。
一方面,基准线必须旗帜鲜明,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语言学亟待加强字词句篇的基础研究,为社会的普及和应用提供稳定合理的依据;学校教育应该改变目前淡化乃至忽视语言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母语的理性认知只有通过教育学习而不是自然习得而获取,这是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语言制度和言语习俗是对整个社会影响巨大的社会事实,要特别注意语言现象和语域之间的适应性。规范的普通话只有在全民共同语的语域中才是正常的;而人们变化多样的言语生活则需要其他相适应的形式——层出不穷的语言潮流、丰富多元的言语社区正是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健康开放的最佳体现。要以宽容的心态看待青少年的语言偏好,引导他们在不同语域中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
可见,语文规范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必然有生机勃勃的语文生态:既有基准线,又有宽容度。既有周密科学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规范法规,让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又鼓励语言创新、适应社会发展。
语文规范有自己的生态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真诚合理地维护语文规范的生态健康,让青少年在科学理性的语文规范观念中熏陶成长,我们古老的汉语才会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