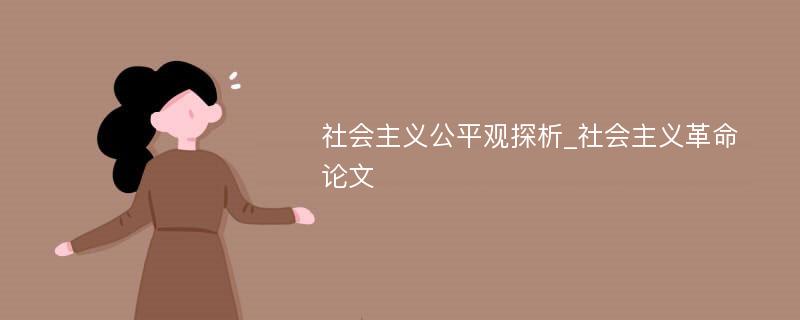
析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述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共同富裕,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的目的和手段就是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判断它的标准和核心依据就是公平原则。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而不搞两极分化,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公平的,贫富分化是不公平的;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则既是实现公平的条件,又是公平的结果。
2
怎么理解公平这一概念?
(1)公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它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还有政治的、法律的以及道德的等方面的意义。例如,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款,就是旨在体现和保护人们在政治上的公平。再如,保护和照顾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的原则主张,就更多地具有道德伦理色彩。
(2)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用超时代的、固定的眼光来看待公平问题。每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在解放被旧生产方式束缚的生产力的同时,都会以一种新的公平观来取代同旧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旧公平观。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今天看来很不公平的奴隶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使生产力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因而是公平的。其后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产生过与自身相适应的公平观。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分配方式来说,按劳分配是公平的,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和多劳少获都是不公平的;而到共产主义时期,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今天被我们否定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部队里,不仅没有人指责它不公平,反而极大地激发过部队的战斗力。
既然公平是一个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范畴;那么,每一个时代就都不可回避地面临一种严峻的选择——它必须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公平观,并以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政策把这种公平观凸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当然,这种选择有时是自觉的、主动的,有时是不自觉的、被迫的。当一种既有的公平观日益丧失合理性时,新的更加进步的公平观便会应运而生;而赞同这种公平观的进步阶级或社会力量便会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让社会接受新公平观。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着重关心的是公平概念的经济含义。而在经济范畴之内,公平一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即竞争机会的均等和经济收入的合理。
竞争机会均等的含义是:它在承认竞争根据或实力不一致(如人的能力、企业的规模和资金状况等)的前提下,允许每个经济主体自主参与或退出竞争,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在竞争过程中,对所有“参赛者”运用相同的规则。这一原则不涉及结果,只重视过程和程序。
在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是找不到竞争机会均等这个概念的。甚至,竞争机会已经不是均等不均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自己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只有执行国家指令和到国家的“大锅”里去盛一碗彼此一样的饭的权利。至于劳动者个人,既无择业的自由,也无换业的自由,一次分配定终身,像过去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一个企业里。在企业内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只能起到“奖懒罚勤”和培养一批又一批不思进取、怠工混饭的懒汉的作用。
排斥了市场机制,从而也排斥了平等竞争这一催人奋进的动力,经济的僵滞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前,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我们在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竞争规则的引进显得相对滞后;因而在纠正旧的不平等竞争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竞争。一部分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或乡镇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
何谓收入合理呢?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的收入同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成正比,既合理也公平。这里所说的贡献,主要指个人为社会付出的劳动,也包括不是由劳动构成的贡献(如金融投资等)。按劳分配是体现这种公平的基本原则;而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都是不公平的,都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生产效益日益低下。
3
目前,有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模糊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把公平错误地解释为收入的均等。不少文章提出, 传统社会主义突出了公平,忽略了效率,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传统社会主义突出公平的主要表现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这种观点既偷换了公平的内涵,又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也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作自己的标志。实际上,平均主义只能是小农头上的旗帜。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社会主义者是把这面旗帜同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起归入应当扫荡之列的。也就是说,搞平均主义,实际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而只把公平看作是收入或分配方面的问题,忽略公平在竞争机会问题上的要求,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见解。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分配状况,都是某一种竞争机制的结果,是被决定的东西。置决定性的因素于不顾,只想人为地维持或改变某种结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们对不公平分配状况的抱怨,归根到底是对不公平竞争机会的抱怨。例如,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者大发横财,生产优质产品的人却步履维艰。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也有类似情况。有的人因为有某种“背景”而较容易升迁和发财,而真正有才能的却不受重视。这些表现于竞争机会上的不公平,会使全社会的工作效率大幅度降低——当然,最终要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下降;而且它还会形成一种低效率和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2)公平的“物质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公平的实现程度是同物质财富的多寡直接成正比的。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才有了当前的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主张:认为只有强调并提高了效率,物质财富得到了增长,才能有条件考虑并实现公平。
“物质决定论”的漏洞在于,它不懂得公平在分配问题上关注的不是绝对量,而是份额,即一定的财富在应分配的个体之间的比例。谁能说上甘岭一个连的志愿军分享一个苹果不公平?谁又能说在物质上比抗美援朝时期富裕许多倍的今天,一个县长宁肯拖欠教师的工资也要购买进口豪华轿车是公平的?实际上,物质财富少时,未必不能做到公平;物质财富多时,也并非一定能够做到公平。
“物质决定论”者还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那就是,到底物质财富多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公平。可以肯定,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如果有谁自恃高明说出了一个哪怕是不准确的数字;那么,紧接着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达到这个数字之前我们做什么,放弃公平抑或是忽略公平,或把公平放到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物质决定论”者机械地强调财富多才能做到公平,很可能是由于在社会福利同公平的关系的问题上犯了糊涂。他们不懂得,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平,同样是一个份额或比例问题,而不是绝对量。在50—60年代,老工人拿着30—50元的退休金感到很幸福;而在今天,他们拿着10倍于先前的退休金也还满腹哀怨。在扶危济困方面,人们关注的也主要是“心意”是否尽到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该做的努力是否做到了。因此,才有“千里送鹅毛”之说。
(3)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矛盾关系, 认为追求公平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必然牺牲公平,两者不能兼得。因此,只能把某一方面放在优先地位,而把另一方面放在从属地位。我们不赞成这一观点。
时下流行的向效率过分倾斜的主张,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的。
本文的逻辑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当然,这种逻辑也有一个前提,即公平必须是真正的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之类)。我们认为,公平对效率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我们的公式是:没有效率不一定没有公平,但没有公平一定会降低效率。同时,我们也并不认为“有公平就一定有效率”。因为,决定效率的因素不光有公平。工具的先进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影响效率。效率是一定过程的结果;而公平则不仅表现在结果上,更表现在过程中。在结果产生之前,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因而必须先解决公平问题;否则,人们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竞争的预期结果也并非有利于优胜者,那就谈不上什么效率了。
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强调公平,以公平带动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强调效率的。其实,它并非一点也不顾及公平(如最低工资制、失业救济法、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法等的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公平;而恰恰是这种不公平,才使资本主义的效率受到了阻碍。社会主义要获得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只有在改变资本主义不公平的状况,实现更高程度的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要真心实意地想提高生产力水平,就要真心实意地做好生产关系的文章;要想尽快地提高效率,必须尽快地解决好公平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公平与否不是制约效率的唯一因素,也是制约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公平,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对象的拓展)就要大打折扣;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一点,已经被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17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一再地证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