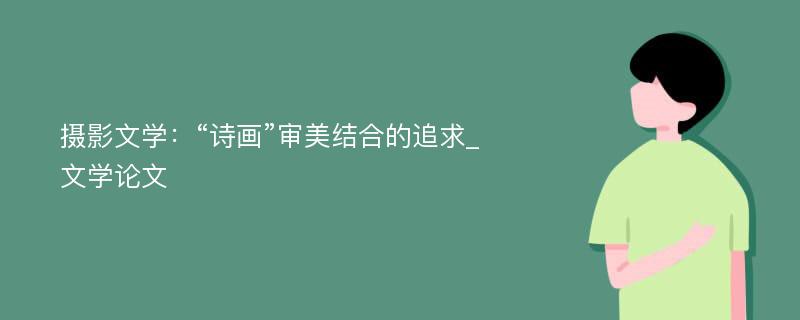
摄影文学:对“诗与画”审美复合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学正处在一个焦虑和困顿的低迷时期,文学期刊的市场境遇就是个有力的例证。不少纯文学期刊在时尚杂志的四面楚歌声中渐渐放弃了突破困境的努力,悄然“改装”者有之,凄然“闭户”者有之,“投亲靠友”者有之。大多数仍在惨淡经营中的文学期刊也很难说到底能苟延残喘到几时。少数几家有实力的纯文学刊物,虽然眼下“满树春光花正红”,其办刊人却惟恐“一夜花落万枝空”。有人以“穷途末路”来形容中国文学期刊的状况,也有人甚至认为“文学即将会消亡”,这些极端的说法其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纯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令人堪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境遇比起纯文学来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文化研究热和全球化浪潮面前正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向的时候,《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亮出了“审美复合”的旗帜,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主力部队的广泛参与下,在“图像与文字”的交叉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垦荒,累月经年,大见成效,出人意料地在文学和摄影这两个渐渐荒漠化的王国的边缘营造出了一片春意盎然的绿洲。对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艺术式样而言,从学理上对其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深入探究和反复讨论,可以说是一件十分令人振奋的学术盛事。
据余三定先生的考证,摄影文学最初是以连续摄影、摄影故事的形式问世的,它首先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中国的摄影文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之后,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自1982年《连环画报》上发表摄影小说《追求》以后,《青年文学》、《解放军画报》等30余家报刊相继辟出版面刊载摄影小说。80年代中期先后正式出版了《摄影小说选集》《摄影小说集》。1990年3月成东方在《人民日报》上率先提出了“摄影文学”概念。1993年成东方主编的《中华摄影文学》问世,1995年11月全国首届摄影文学理论研讨会举行并出版了《中国摄影文学论文集》。2001年1月,《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创刊,这是摄影文学界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当时就有人预言,这个《导刊》“必将对摄影文学乃至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现在的实行情况也正是如此。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创获。特别是有关摄影文学“审美复合”说的探讨,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学术启发意义。
成东方“审美复合”论者认为,摄影文学是作为审美和艺术的复合结构而存在的。摄影文学,是在对包括摄影和文学在内的其它艺术形态的肯定性否定中建构起来的新的艺术形态,是融合了人类主体长期的审美和艺术实践经验,积淀了摄影、文学等诸种艺术形态的审美特征,把审美
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现代复合性艺术。(马龙潜:《论摄影文学的复合艺术结构形态》,见2001年11月16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当然,“审美复合”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说到文学与摄影的“审美复合”,我首先联想到的是莱辛关于“诗与画”的研究。我觉得文学与摄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诗与画顺应工业化和高科技时代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图文关系。不同的是摄影机把画家变成了摄影师,摄影文学简洁的诗化文体使诗人和小说家踏响了媒介文风特有的轻快节拍。我们是否可以说,摄影文学其实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诗人和画家共同经营的一片绿地?
在《拉奥孔》这一经典性的美学著作中,莱辛认为,绘画的手段是“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的手段则是“时间中的分节声音”。然后艺术家所采用的手段对于他不单单是机械性的外在工具。这些手段与最本质的东西,与所采用艺术的特殊本性是相联系的。在“表现手段”和“被表现者”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内在依存关系。无论一个诗人如何勤奋努力,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把事物的感性形体画貌描画得像画家通过线条色彩所描绘的那样充分和现实。反过来也一样:无论一个雕塑家或画家多么有才能,他也不可能像诗人那样自由地表达随时间而发展着的运动、变化和情节。(弗里德连杰尔:《论莱辛的〈拉奥孔〉》,载《西欧美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对于艺术来说,题材与模仿现实的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种艺术所使用手段或艺术语言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任何艺术都能在最便于用它的特殊艺术手段加以描绘的方面显示自身的优越性,但也正是这些优越性使它必须遵循只有本门艺术才不得不遵循的特殊规律。莱辛认为,绘画以色彩和线条作为媒介再现空间之中“并列”的事物。因此绘画里被描绘的对象是排列在空间之中的“形体”,它们直接作用于画家的视角,画家将这种直接作用于视角的特性通过所谓的“自然符号”(这个概念用来描述摄影似乎更加贴切)传达给欣赏者。反之,诗以语词以媒介,词语的线性排列原则决定诗所描绘的事物在时间之中只能是“一个接着一个”,即使是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只能使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办法,将其人为地分为先后。因此,诗的描绘对象,是在时间过程中按先后次序逐渐完成的动作。简而言之,诗是线性的时间艺术,画则是立体的空间艺术。
那么,这样在空间中表现时间,或者说,怎样通过静物来摹仿动作呢?具体地说,一个画家如何像诗人那样去描绘动态事物,描绘一种内心生活、一个动作或者一段情节呢?我们知道,一个画家常常会把溪间流水变成山间的玉带,把辗转的思念描绘成凝固的泪珠,把瞬间的雷鸣电闪化作永久破碎的天幕,总之,一个优秀的画家,有时能让观众在一刹那间看到千百年的沧桑,能从少女的一滴眼泪中看到爱情珍藏的海洋。那么,画家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莱辛认为,画家的秘诀就在于“寓时于空”。“寓时于空”的手段至少包括两条诀窍:
第一是以“最富于包孕性的顷刻”来暗示动作或情节的发展。例如,“希腊化时代的《地母雕像》描绘地母独坐远望,期待爱女归来,以往的离愁和未来的欢聚一时都体现在她的双眸里。”(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第566页。)第二是以不同的组成部分暗示不同的时点,或以“集体行动”暗示时间的连续。
莱辛认为,“把在时间上必然有距离的两点纳入同一幅画里,例如玛楚奥里把抢劫赛宾族妇女和后来她们调和丈夫们与娘家亲属两段情节纳入一幅画里,以及惕香把浪子和他的放荡的生活,他的穷困和他的忏悔整篇故事纳入到一幅画里,就是画家对于诗人领域的侵犯,是好的审美趣味所不能赞许的。”(《拉奥孔》第98页。)但是诗与画毕竟有相通的地方。所以,这种所谓的“侵犯”并非绝对不允许。实行上,这种侵犯在诗与画中都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在创作一幅历史的作品时,画家很难找出一件众多人物同时在场且最能体现每个人的个性特征的顷刻,画中大多数人物的某些动作和姿态只能是略早或略迟于这一顷刻的。在这一点上,画家可以通过某种巧妙的安排来体现他的创作意图或独特匠心,例如把重要人物摆在突出的位置,次要人物摆在背景里等等。
同理,诗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擅长于描写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对空间中并列的静态事物的描写显然不像画家那样得心应手,诗人永远无法像绘画一样将人或物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所描绘的圣母,在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可能有一千种形象,而且这些形象总是变化无定的。绘画则完全不同,画至少在影像上能给欣赏者一个相对固定的印象。造成诗与画的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诗的媒介是语言和声音,即“人为符号”;语言无法把自然事物的形体和颜色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它必须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因此,诗人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激发和引导读者的想象。第二,自然事物的形象总是丰富多彩的,立体多维的,画家固然不可能从所有视角全方位地再现事物,但画家至少可以从某一个角度给观赏者一个统一的印象;诗人使用的语言,如果描绘静止的事物,它只能单线演绎一事或逐一罗列众物。单线演绎或逐一罗列往往会使读者感到厌烦,例如,任何一个读者从文字中读到的大观园都不可能像一幅画那样一草一木,生机勃勃,雕梁画栋,清晰如睹。
然而,诗人可以另用一种手法来突破语言媒介的限制,这种手法就是寓空间于时间中,寓空于时的方法,也就是化静态为动态,用暗示方式通过动作
描写物体。这是中西方诗人普遍采用的方法。莱辛在讨论诗与画的界限时,对诗与画的相通与互补也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画家可以选择“最富裕包孕性的那一顷刻”,诗人则可以利用“化静为动”、“唤起意象”、“化丑为美”、“化美为媚”等手段和画家一较高低。
朱光潜在《拉奥孔》第21章的最后一个注释中也以《陌上桑》和《诗经·卫风》为例:《诗经》的《卫风》写女子的美说,“手如柔美,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前几句胪列静态,后两句化美为媚,效果迥殊。这些说法,无疑抓住了莱辛美学思想的本质,但我们也注意到,对静态的胪列采取一味否定的态度似乎也是不可取的,如《卫风·硕人》中的后两句,如果离开了前几句的铺垫和衬托,其艺术效果必然会逊色许多。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手法应用得更广泛,例如,在《天方夜谭》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描写,比如说作者无法用语言描绘一位俊美的王子之美,作者只说那些梦想一睹其英姿的男男女女,纷纷提前多少个日日夜夜痴心地等在他将要经过的路旁。那些被这个故事吸引住的读者,就自然会把那王子想象为“最完美的形象”。从理论上说,有关诗与画的描述基本上都适用于文学与摄影。但是,摄影文学又完全不同于插画诗或诗配画,摄影文学在本质上是对传统诗画矛盾的一种超越,她应该是诗与画的有机融合,她甚至不仅仅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是诗即是画,画即是诗,诗画互藏其宅。所谓“诗与画”的“审美复合”,可否也作如是观?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图像化时代,一个供人们“看”而非供人们“读”的时代,它们以画面语言将观众置入一仿真的世界。画面叙事诉诸人们的感官而非心智,带来的是简便的直接的感官刺激,一种混合着人们生理冲动的全方位的灵与肉的享受,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震惊”而非传统艺术的“韵味”。摄影文学正是在图像化时代应“运”而生的,它是通过嫁接传统文学艺术与摄影艺术而孪生出的崭新的艺术类型,是语言与图像两种艺术共同孕育的新的叙述方式。
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多关于诗与画的精彩论述,例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文者无形之画,画则有形之文”。西方学者也有“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等著名论断。这些言论说明,古人对图文关系早就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今天,在有关摄影文学的讨论中,有学者从图文关系考察了诗与画的融合对摄影文学的启示意义。认为,“文学与图画、图像之间具有先天的沟通性,在高超的艺术家那里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这是摄影文学能出现并获得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南宋吴龙翰曾提出这样的理想:‘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摄影文学追求的正是这种诗画合璧、相得益彰、互启互补的艺术效果,突破两种艺术门类各自的局限,既能阐发诗中情,又能申明画外意,虚实相生,以有限寓无限。”(参见董学文,金永兵《解构与整合——对摄影文学中文学的功能性分析》)总之,摄影文学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家追求“诗与画”审美复合的一种新兴艺术门类,她理所当然要实现对传统诗画关系一种全新的时代超越。她必将把古人“画以诗凑成”或“诗以画补足”的“凑补技巧”提升到一个“诗画合璧、相得益彰”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