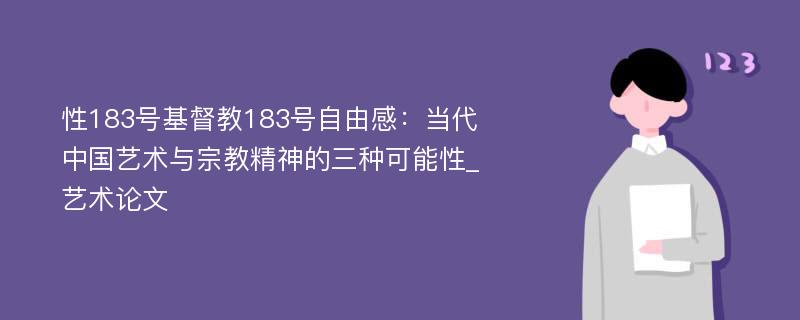
修性#183;基督化#183;自由感:当代中国艺术宗教精神的三种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三种论文,中国艺术论文,可能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艺术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危机,尽管这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爆发才变得显著起来。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玩世现实主义和艳俗艺术,再到与后殖民文化相关的21世纪商业艺术,都已经关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始终无法进入艺术本身的精神性层面,既缺少对艺术语言本体的追问,也没有个体精神价值的建立,更没有终极价值上的维度。质言之,中国当代艺术的危机,就是精神的危机。要解决这个危机,在我看来途径之一就是让艺术走向“绝对”,并以此与宗教感相通。
这里所言艺术的宗教性或宗教感,既是指严格的宗教形态上的概念,也是指后现代的泛宗教,即具有某种终极关怀或者把艺术本身当做宗教。在中国,就有着几种不同的形态。比如,一些基督徒艺术家自觉结合宗教信仰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无论是作品的符号形式还是其所体现的精神性,都明确指向基督教;此外,还有的艺术家则是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人画与禅宗的修行上,激活新的审美观照方式,而中国文化的所谓“审美代宗教”,这个“代替”就受到禅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修行,把绘画作为修禅的功夫;最后,还有的艺术家面对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处境,试图回到物质的精神性,打开新的个体性的生命信仰的可能性。
一、第一种形态:修性的审美宗教
尽管蔡元培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的信仰形态是“审美代宗教”,但一直没有严格的研究指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审美、以什么方式、代替为什么样的宗教,即生成为什么样的“样式”。随着学界对东西方美学的深入思考,这个论断开始变得清晰明确起来,这就是中国文人画传统以山水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整个绘画观念乃至生存美学风格,有着不同于儒释道传统的审美化形态;中国文人在接纳禅宗精神之后,在转化了儒家君子德能的修养和道家的生命观之后,以水墨山水画的创作和相关手法,尤其以董其昌所言的南宗绘画为代表①,形成了以“平淡”和“空寒”为意境的审美化的非神论的信仰。这是从中国传统内部生长和转变出来的一种宗教形态,具有某种世俗性和个体性,但是在审美的意义上有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情趣和精神取向。
在绘画语言上,这是皴法的生命触感和烟云淡荡所体现的生动气韵,以及空白所体现的去己和空灵的精神,让中国文人们在其间安顿生命,而且空白也是中国文化留有余地——“余”的思想——的体现,有着余韵,有着平淡的精神性②。
对于中国传统,平淡似乎是天生即有的,是生而知之而不可学的,甚至都不可能通过修炼获得,更不用说通过工作来获得了。平淡之为平淡,一直是针对不可能的经验,这是平淡与平庸的差异。尽管平淡可以平常得不露一丝痕迹,但平淡一直有着内在的生机和对余地的敞开,因此平淡不可能成为作品,它必须把整个作品转变为空白(blank-empty),留下来的也许仅仅是空白,但这空白敞开了未来。如果平淡之为平淡,一直是不可能成为作品的,是非功效的(unworking),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的禅意,任何物都不可能有着意义。但是,一旦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精神和虚无主义的挑战,平淡还如何可能呢?在中国传统中,平淡主要是通过“留白”来实现的,不是去画,而是要么通过反复画空白的边缘使空白生动变化,要么就是在画面到处呈现出不画的留白,让整个画面回响的是空白本身。当代中国绘画如何重新唤醒这空白的空间?如何创造新的平淡,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
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平淡其实已经在面对着这些问题,“不可能的平淡”才显得如此有力量:一方面,水墨的材质水与墨,都是现存品,不是专门的艺术材料,水是无处不在的,墨是日常书写工具,而且墨被水冲淡,画面上最终要表现的是飘散不定的烟云,烟云是变灭的虚无本体,是非烟非云的,这是对瞬间幻念的捕获;另一方面是留白,所谓的“不画之画”,就是让画面的材质本身——纸绢的白——显示出来,当然,有时候仅仅以淡墨轻扫空白,这是回到素朴上,回到对事物原初发生的余留上。
但是,到了当代中国呢?如何可能在画油画或者丙烯之类作品时,也达到平淡?油画留白是困难的。如何以新的方式体现“空白”或者“余白”的观念,转换出新的“余白”?同时,绘画如何接纳任一的瞬间?
我们看到一些画家面对了这些问题。其代表人物是周洋明、李华生和梁铨,他们的作品通过借鉴西方抽象主义的精神,转变了传统禅宗平淡的追求方式,走向艺术的工作,这工作形成了新的宗教性。
平淡,如果开始工作,那也是“虚无”在劳作,平淡的工作要求艺术家顺从于“无”,是让“无”自身生长出来,如同让-吕克·南希指出的③,在拉丁语中,res与rien,“物”与“无”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关联。虚无主义(艺术之为虚无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为含糊不清的)的后果或者说来源于:一方面,承认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一切都无所谓!确实要承认这个“无所谓”,一直要抱有这个“无所谓”的态度,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立场约束自身;另一方面,同时也要让虚无生长,不是因为什么都可以,以至于导致了什么都不做,相反,是要做,而且是精致地做,既是人为地做,也是让虚无本身生长,这不同于以往的虚无主义,以往的虚无主义滑入了任意性,也取消了人的作为性,现在虚无要体现出劳动的辛苦,即身体性,以及“从无创造”(creation ex nihilo)的想像力,这是使身体在虚无和作品之间成为关键的中介,或者说,作品也仅仅是身体的延伸,虚无也是身体的不可见性。而让虚无本身生长,这是虚无打开自身的虚空空间:无意义,一直保持为无意义,但是无意义却在继续生长,获得无意义的形式。
比如周洋明的作品就带来了新的平淡!那些尤为灰色的作品,画面极淡极淡,似乎什么都没有画,远看就是一片空白,近看却有无数细腻的笔触,画家一般是在画布上画一些极细的线或者点的笔触,竖行或者横线,笔触很细微,笔触的运行也很缓慢。而且一幅作品就要画几个月,每天如一日地画!还有水墨中代表性画家李华生的作品,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画布或宣纸上画线段或者格子,或者就是画纸绢这种材质本身就有的纹路,是一种缓慢而机械的劳作。评论家栗宪庭把这种繁复的手工过程称之为“佛教念珠”一般的操持,每一笔触都是在念经。周洋明自己在作画时,一笔一划之间有时也念念有词,李华生认为自己的书写就是受到听喇嘛呜噜呜噜念经而启发出来的,他们让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消耗在这个反复劳作的过程中。因此,评论家试图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修性”,亦即达到某种心灵的慰藉,似乎这是一种新的修禅方式,如此的讨论就把当代绘画与传统文人画的美学范畴关联起来了。
对于周洋明和李华生的作品,如同栗宪庭在《念珠与笔触》的展览前言中所解释的,这种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一幅作品有时持续三个月才能完成的艺术创作过程,可以称之为“劳功夫”,是一种需要功夫的劳作,是铭刻消逝的时间。而我们这里称之为“工夫”,既有功夫的含义,也有工作的含义,前者似乎更多指传统内功的操持,后者则是具体外在可见的工作。
那么,这种“工夫”是什么意义上的修身?这种机械的劳作是什么意义上的平淡?是佛教式的修为吗?是通过念经达到心灵的平静?或者是儒家式的修养——带有文化学习的修养吗?或者是道家的修炼——有着养生和呼吸调节的修炼吗?这种机械的重复劳作会不会导致身体的某种职业病?中国古代的画画是观养,是养生,所谓的“烟云供养”,被认为是可以使人长寿的!
周洋明的这些作品并没有明确的名称,而是仅仅署上一些日期,也就是这幅作品完成的时间。这是对一个个离散的无意义瞬间的被动铭写,不是去刻意标画它,没有了节日——艺术作品不再是激发艺术狂欢的手段,也没有了归属——没有目的和主题来引导笔触,笔触成为一个个离散的瞬间。这是没有意义的劳作,也是彻底的还原,这些笔触,在最初涌现的时刻,仅仅是无意义地划道道,现在,也并不走向意义,而是身体动作的重复。只有个体身体书写时刻的气息的记录,是身体书写时的力气。当身体书写呈现出疲劳状态,画面的真理时刻就会到来,比如手无法抵达画布高度,就停止下来了,不再继续画,画面的形式也就停止在这个时刻。
画布上的每一笔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笔与下一笔有时候会服从某种惯性,但是很快会被打断,因为身体的疲惫和自我的觉醒,以及对空白的敏感。当然动作的熟练与笨拙的转变,以及线段长短等等的无规律变化,画家受到情绪影响时对画面色彩的微妙调整,经常会出现打断与中断,带来了空白和停顿。
画面为“任一性”打开了空间,“每一个”或者“任何的一个”都有着自身存在的独立性。这种每天的工作,是否还是传统的平淡呢?似乎不是。传统的平淡需要修养,但是不可能如此工笔和细致,文人画与院体画的差别就主要体现为墨戏与工笔的不同,现在,平淡需要耐心地工作。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修养方式。这不再是古琴式的散淡演奏,而是新的“心琴”,是以自己的心来做琴,来演奏自身,或者说让自己的心被另一双手所演奏,不取悦于任何人,仅仅是服从这个制作过程!从这种“做心”的过程中,身心都得到了重新的调教,画家被所画的笔触和空白所调教,观众被画面本身的色调以及画面内在的动静的笔触所调教,这是艺术作品带来的新的教化方式。
周洋明把平淡转变为工作的方式来实现,这与福柯在他的《何为启蒙》中总结的波德莱尔对艺术和现代性之间的思考密切相关④。福柯认为当代性或者现代性的生存美学有着几个基本要素,即对当下流逝的非连续的时间之英雄化的表现(要在现时中把握永恒,而不是离开当下的现时性),这种英雄化还有着一种自我的反讽(试图以想象来想象不同于它自身的现时并且改变现时的面貌),这势必导致一种“苦行主义”(因为他必须设法创造他自己,必须强制一个人完成自己对自身的制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洋明有着颜色的作品,甚至洒上金粉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苦行主义的工作态度。尽管他自己是朴实的,画面是淡雅素净的,但是对每一笔的细腻表现,以及色彩的高贵,有着对美的热爱。画家本人的朴实,不妨碍他的作品本身体现出淡雅的精致。而这种自己对自身的创作只能在艺术中发生,这就是当下生活的艺术化。这也是福柯称之为现代性的生存审美风格的形成。在这里的讨论中,其实已经增加了一个要素,这就是中国传统美学对个体生命修身与自身关心的认识,当然,福柯晚期也注意到了这个自我关心的技术的修身的重要性。
周洋明曾经以很长时间,几乎一年之久,在两米大小的亚麻布上直接画“布面”的纹理,乍一看,这幅画根本没有任何画过的痕迹,如此轻轻地触及或者覆盖,彻底顺从了物的质地,画家空去了任何的形式和影像,仅仅面对眼前之物,因而触及的仅仅是物的漠然性。画家如此反复俯身作画的姿态,其实就是灵魂祈祷的姿势!
因此,这些笔触是从画布的表面内在生长出来的!新的平淡,乃是从物的漠然性中生长出来,是主体对质料漠然性的发现。周洋明的作品让观众惊讶的是,画面笔触本身内在生长的力量,似乎不是画上去的,画家并没有画什么,而是画布或者画面自身在生出这些笔触,如此淡然地触及,有着对欲望的治疗。画面不过是灵魂的皮肤,画布笔触的轻微战栗乃是灵魂的低语,永生的灵魂来到每一个笔触之中,还可以无尽地生长,永无止息!这是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的生成,不仅仅是某一个他者,而是生变为无数他者,或者说他者的他者——即世界本身!
另一位抽象水墨的代表人物梁铨,也自觉认识到对传统禅宗的转变作用,如同画家自己所言:现代艺术中禅宗哲学的回响微乎其微,不冷不热,可能油尽灯枯,销声匿迹,但都是禅的境界。因此,如何复兴传统的这种境界呢?梁铨试图在画面上不再固守于面面俱到的“满”,而转向对于“空”的追求,在其风格转变之时,画家的心情很平静。在画家看来,以画面来实现“空”的境界,可以说易如灵机一动,也可以说难如看山跑马。更为重要的是,画家认为,自己画面上的这种“空”与文人画的“空”不尽相同,文人画是以“空”表现“实”,但是如果单纯想表现“空”本身,又当如何行事呢?它绝非是落一笔那么简单,但是如若落了一笔,这一笔落在何处?落笔之处顿时就失去了“空”。落与不落之间不能有任何区别,否则一念之差,全局的境界也就随之成为梦幻泡影了。画家认识到,世界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它肯定是细致而真实的。画家要做的是:用微妙细节的喋喋不休来互相抵消实际效果,以期实现整体上的空泛化,这未尝不是实现“空”的一种思路,一如文人画以“空”来表现“实”;而反其道而行之,处理得当的话,恰到好处的“实”同样能够表现“空”的境界,以细节的堆砌来实现“空”的境界,平静、无规律而静谧的线条必须要彼此抵消引人注目的效果,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禅心之感,才能够让人感觉它们只是自己呈现在那里。我们在梁铨的作品上看到了他自己观念的充分实现。
就梁铨的作品而言,画家采取宣纸裁剪后染色再拼贴和装裱在画布上的方式来实现“满”和“空”的观念,一块块不同大小的方形宣纸的色块反复叠加在画面上,反复调整,直到线条色块之间找到某种内在韵律。这是把外在的装裱转换为内在的画面的建构模式,承继了所谓“三分画,七分裱”的“次要转变为主要”的装饰逻辑,进一步把“外在的”转变为“内在的”,带来无尽的延伸之感,把制作转变为涂画,这是边缘解构的手法。既强化了手工的制作性,但是又依赖拼贴的任意性,无论是上色还是线块之间的调整,都需要画家不断审读,不断按照视觉和观养的滋乐来调整,而且有着对空白和空间的思考。
这些平面化和涂鸦式的作品,也打破了文人画的精致,为平常生活留下了呼吸的空间,那些让茶的痕迹直接留在画面上,而且让这些微不足道的气息之间形成某种抽象的图式,都是对空间的重新打开。这在画家那些名为“老茶”的作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画面上一个个杯口状的圆晕染开来,有了干湿浓淡变化,而且在上色之后,在画出了暗格子的宣纸上呈现出或圆或缺的形态,似乎在彼此滚动,如同游离的细胞,画家让一种极端剩余琐碎的事物呈现出纯然的形状上的生动性。在名为“茶日志”的作品上,只有一些染色了的晕染与晕散开来的椭圆形,一圈圈茶杯盖出的印痕,每一个圈圈都在变异,在拓变,在画面上流动,似乎还有着茶的余热余温,在滋养着我们的凝视。而且因为水的晕散,色的浓淡和胶的塑形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印迹,似乎它们在倾诉自身无尽的妙趣,画家似乎再次恢复了禅宗的“正法眼”!画家把抽象的艺术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日常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转念“之间”成为抽象的艺术。这个转念之间如何调转而形成的?这是对平常生活的凝神观照。对于画家,这些作品都是“养”,是平淡的恬养,也是禅意的修养和生活的生养,再次把“看”与“养”联系起来,这是中国人的看视之道:是玄览,也是“观养”⑤。
在梁铨的作品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平淡。这是抽象的平淡,经过了理性逻辑化的平淡,因此,禅宗在现代转换中获得了理性秩序和心性调节的功能,并且以抽象的去除形象的图像展现出来,与传统的留白手法隐秘相关。
二、第二种形态:基督教艺术的实践
按一般估计,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五千万,这势必让一些基督徒身份的画家开始思考基督教艺术在中国的可能性,或者说,要提高宗教精神的品质就离不开艺术的纯化。因此,基督教绘画在中国也当然不应该是对圣经的简单图解,尤其在西方基督教绘画已经如此发达,但在20世纪基本消失,除在个别画家的创作中有所体现之外,已经不再是主流的时候。因此,在当前要画基督教绘画,必须有着一种创造性的融合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些努力,这是光气的融合,以及以水墨传统的书写性来创作具有基督性的水墨和油画作品,这在岛子和张建波的作品上体现尤为明显。尽管1990年代初期的丁方曾经以基督教的精神来塑造北方山石的肌理和场景,但可惜他后来并没有接续,因为这涉及到对绘画语言本身的转换和创造的较高要求。
中国传统艺术选择“水墨”语言不仅仅是巧合,道家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艺术,水之为水,并不是作为自然之物的水,而是已经转化为道家观念的“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水”,柔弱胜刚强之“水”,也是无常形之“水”,是指向生命的元素性之物,而且是无可规定的无味之物,但却最为体现生命之道;“墨”也不是所谓的黑色或颜色中的一种,而是玄色,是无色之色,或者是哀悼之色,是死色,是喑哑生命需要规避保护的暗示。因而,水与墨的相会,乃是一个无味之物与一个无色之物——之不可能的遭际,在氤氲之会的水晕墨章之后,却产生了无尽的新物象!这是从“无·无”相遇所产生的最大的艺术冒险,因而并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繁复出来的极多主义,而是“从无而余”的触发,触动“无”之玄机;在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后,则是触及“空灵”之境,产生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空灵的水墨观。
如果水墨语言的第一次选择与禅宗和王维等人的历史命运有关,那么,重新选择水墨,进入水墨语言原初的生成之中,以基督教的精神重新塑造水墨语言,又将会如何?这是重新创造历史,创造不可能的历史,艺术就是在面对这个不可能性!
从岛子自己称之为“圣水墨”作品上,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水墨之新的可能性。岛子以其明确的“圣秘主义”(Saintlism)的书写打开了新气象。如何成为圣秘的?那是接受来自他者或者一种灵异力量的灌注,那是对至高神圣之物的重写,这需要持久的等待,需要持久的熬炼,从而获得另一种时间性。在岛子看来,东方化的正教其实已经完成了一种很东方的范式,例如俄罗斯圣像画,在20世纪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有传承,而在罗斯科的色域绘画上也有所传承,而且超越了自我的偶像化,极大提升了精神性的深度。在中国现代艺术中,岛子认为林风眠晚年有一点圣秘绘画的追求,他提醒我们注意林风眠1989年后的作品,还有最早表达人类苦难的几幅失传的作品。“圣秘主义”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后宗教时代,就是“重写”神圣的历史和事件,“重写”不是模仿不是再现不是挪用,而是创造性的重写,在重写中追踪圣灵的踪迹。
而圣水墨是“属灵”的水墨:这是让中国传统的水墨语言转换为具有基督性的属灵的水墨。圣水墨是圣秘的水墨,而不是神秘主义的。因而,在岛子这里,“圣秘主义”是圣水墨的一个理念,区别于无神论和多神论。“圣秘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区分在于后者还是灵智主义的,是个体性陷入思想的迷狂,更多是个体主动性的体现,而“圣秘主义”更多是接受一种被动的陌异的力量,更多是顺服,而且有着对神圣之物的虔敬,对生命苦难的关注。岛子的“圣秘主义”和圣水墨,因而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绘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空灵的文人画,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和创新。
在与基督教的对话之后,如何让传统的水墨材料、水墨笔法、水墨意境都发生根本改变?水墨语言大致由这三个环节建构起来,因而变异也必然是全方位的。
首先看,水墨之为水墨材料,但“水墨”绝不仅仅是一种材质,我们前面说过,文人画选择水墨,敢于舍弃表现力更加丰富和强烈的色彩,本身就隐含了强烈的精神诉求:即用无余、无用或者“无·无”理念的冒险来赋予平常的材料以灵性。显然,并没有什么纯然的质料,一切已经被观念化了,反而要反省和还原掉自己先在的观念。那么,基督教的精神呢?如何对材质本身发生影响?不可能是观念的图解和人为的造作,那么需要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注入水墨?而且,选择什么样的基督精神呢?基督教的神学是异常丰富的,但是基督精神的核心,无疑是基督本人的受难,他的复活和爱的灵语,整个圣书的核心是神和人之间的圣约,是对弥赛亚拯救的等待。如何让材质,即水与墨体现出新的灵质?这需要注入新的灵质元素:只有真正的灵性可以灌注死去的水,激活呆板的墨,传统文化的空灵空间失去之后,如何还有一个画布或者纸上的空间可以打开?只有“灵”——陌生而强大的纯洁的圣灵——可以打开。但“灵”从哪里来?如果我们的文化自身已经改变很久了,那就只有求助于异质之灵,这是基督教所给出的“礼物”——即《新约·约翰》一书中“水、血、灵”三位一体的浇灌:“圣水”针对已有的枯竭污秽的“水”,这是生命的洗礼,生命需要新的洗礼仪式,需要被洁净,而基督生命的“水”则是生命的活水,是经过净化的;受难的“血”针对“墨”,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罪,在丧失了活力的生命之后,我们需要换血,或者说置换骨髓;而“灵”呢,则是让“水”与“墨”重新结合,让“水”与“墨”获得新的灵动性,这“灵”需要我们在祈祷之中耐心等待,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灵”可以让水墨发出光明,发出圣光,让死水成为灵水,让呆墨成为灵墨。“身体—血—肉”的肉身材料如同“宣纸—水—墨”,都需要灵来贯通,无灵就只是形似而已,没有神的灵质,就只是行尸走肉而已。
其次是水墨在画面上呈现的笔墨语言,也是笔墨功夫的体现。中国传统是以气势和气韵来铺排的,尤其离不开皴法的肌理效果,以及水墨彼此相破所带来的干湿浓淡等等微妙变化。但是,当代实验水墨只是把皴法改变为肌理效果,后继者则是在宇宙太极意识上大做文章,或者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但是要么只是个体的文化符号标记,比如丁乙的《十示》上的十字形依然流入装饰,因为缺乏对十字形精神的内在探索;要么只是西方语言形式的外在拼贴和组合,这已经到处泛滥了。而从画面的色和形上看,对“墨色”的运用,岛子的作品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墨的五色感,又带入了重力、光影的对比,基督教神圣的“光”与中国水墨富有灵性的“气”得到了融合,而这些对比是在生命的复活与死亡的对比的灵性品质中展开的。死去的墨如同受难死去的生命,需要重新生还;而“形”是继承与发展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符号,尤其是对天使形象和十字架的重写。从内在生命的灵化来置换中国文化生命的心灵,这首先体现在对光的表现上;其次从图像志来重写象征符号并且给予其新的意义,比如从十字架和天使的形象上可以看出对水墨精神的彻底重写;最后则是进入神圣历史,重写神圣的事件,比如对苦难史的重写。
再次是画面意境的改造。传统文化选取寡淡的水墨来表达生命的规避,是面对世俗生活无法更改的等级秩序,让个体生命在自然之中找到藏身之所。但是,在现代社会,是否这种淡雅或者枯冷的生命感受还有保留的可能性?或者说在一个欲望被肯定并得到膨胀的时代,这样的生命情调是否还有可能?如果不再虚假地、现成地重复传统的意境,起码也要面对时代的喧嚣躁动。因此,重新获得安静和枯冷的生命情调,在内在与外在之间找到一个退守和持守的距离,恰好需要内在的祈祷的力量,而基督教或者圣灵的语言恰好带来了这种可能性,一个不祈祷的生命如何能够面对欲望的强力?
另一位基督徒画家张建波主要是画油画。他最近的系列作品《预言》就是他个体生命的隐秘记录,也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画家内在祈祷的记录。不必讳言,作为一个基督徒,张建波是以祈祷来作画的,这使他的作品成为基督教所特有的圣灵叹息的书写:是圣灵在书写画家的生命,是圣灵的呼吸或者叹息在摇动画家的笔,是圣灵的光在逼迫他拿起笔如此书写。因此,张建波作品上那些颤栗的笔踪,那些不可读的痕迹,就如同祈祷的方言,是他自己也无法翻译、却不得不一次次倾诉的言辞!
张建波的绘画是对深渊涌动和光芒到来的记录,是对光的一次次召唤、一次次等待,是对光到来的期待,他的画面就构成对灵光的隐秘记录。形式优美,但又不确定,因为边界一直在颤动之中,但是,却有着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这是几微的时间性:这些笔触有着微波的荡动,有着细微的变化,有着细微差别的触感,如同心灵的呼吸被某种力量所调节,这些如同字迹的笔触之间有着内在的呼应,似乎在等待某个时刻——那是光到来的时刻,是圣灵到来的时刻,并且积蓄这几微的光芒,让光芒来调节这颤栗的呼吸。
张建波还自觉转换了中国传统书法式的用笔,画上的笔触之间有着草书的灵动性,无意之意,笔断意不断,意断气不断,那些既勾连又分开的婉转的书法线条,既有着草书的气韵,又有着生命呼求的形式。看起来在信笔涂画,但在层层覆盖之间,让色彩服从呼吸的节奏,那是圣灵到来和颤栗的节奏,笔触之间有着内在的彼此呼应。在画面上反复涂写,反复覆盖,一层层地上色,一次次地涂抹,最后调整出某种带有韵律的痕迹。张建波的作品尽管看起来是抽象作品,其实既有着传统书写性的用笔,也有着基督教的灵性,很好地结合了基督教和中国艺术的精神。
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艺术家在装置和行为艺术中体现出了基督教的反思精神,在这个方面,可以参看查常平的相关研究。
三、第三种形态:个体自由感的宗教
从西方而来的油画,乃至广义上的中国当代架上绘画,不得不受到虚无主义的渗透,在艺术面对终结的意义上,与虚无主义背景相关,有着双重困难。这是自杜尚以来,给绘画艺术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其后果是,它既扩展了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也导致了绘画艺术的无序。
其一,这是对艺术本身无意义的发现。通过即兴的创造与打断,任一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一旦杜尚把小便器这样的现存品翻转过来就当作艺术品去展览,这个瞬间的转换,就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在任一瞬间(Augenblick,instant),只要灵机一动,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品,怎么做都可以,尽管这个“无论怎么做”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无论怎么做”已经被肯定了,艺术为所有的非艺术打开了缺口,如同迪弗在《艺术之名》一书中思考的⑥。尽管艺术一直知道艺术本身并没有界限,但现在不是界限的问题,而是艺术真正失去了标准和界限。任一事物都是艺术品,但这也意味着任一艺术品都不是艺术,而仅仅是现存品。这个断裂开来的任一的瞬间,作为表现永恒时间和神话场景的传统绘画已经失去了功效,绘画如何接纳如此的任一瞬间?这成为根本的挑战。
其二,是对绘画材质的解放。这也与杜尚的转变有关,一旦杜尚自己不再画画,而是去做装置之类作品,一旦影像制作更加发达,为什么艺术还要局限在架上绘画?还要用如此这般的材质?以如此的方式?这里重要的不仅仅是媒材的转换和差异,而是媒材之为物本身,被彻底解放出来,物之物性彻底独立出来,所谓的物自体本身是不依赖于人和主体的,这种不相干的漠然性,要求绘画更加彻底地回到自身的起源,回到人或者主体对事物对象最初接触的时刻,对象自身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对这个事物本身之为“不相干”(non-relation)以及“漠然”(indifference)的经验。对于西方而言,绘画艺术已经在主体表现以及意志力的高扬上走到了极致,走向了“英雄主义”的暴力和技术控制的极端,现在,需要的是消除艺术本身的崇高以及艺术本身独特性的假象,还有画面上制造幻像来指引神性的假象,艺术不再是制造幻觉和幻像。
那么,对于绘画艺术,剩下的仅仅是极少之物。首先,这是回到事物本身的客观性或者客体性,如同波德里亚所指出的“物的客体性”,在我们看来,这是彻底回到物对于人的漠然性,回到艺术本身的非起源——还没有走向艺术品的时刻。整个世界都是现存品而已,似乎仅仅是上帝创世之后的剩余物,才能够找到艺术发生的惊讶和微妙性,不然还是在图像的幻觉中复制。这种客体的漠然性与波德里亚所言的客体性不同,更加漠然与不相干,这是物体返回到所处的空间,是空间的漠然性,并不是客体,而是客体的匿名性和空间的漠然性。其次,要么就是面对一个个的瞬间,一个个不可把握的意念,所谓的转瞬之念,尤其是幻念。幻念不是幻想和幻像(simulacre),而是不可把握、不可铭记与不可记录的消逝之物被更加彻底地幻觉化,是离散与消散的瞬间,是一个个任一瞬间的离散。这二者可以相关,比如离散打开的一个个瞬间之间的空隙,也是空间的漠然性。
如何接纳不可把握的瞬间,如何面对物质本身的漠然性,这对离不开图像以及技术的架上绘画而言,图像仅仅是多余的了,必须从属于瞬间的离散性和物质的非图像性,让物质本身显示自身。如同利奥塔在《非人》中说到的非物质的质料,这就是“余像绘画”的根本要求:图像之为图像已经是余像,因为物质本身的非图像性,物质的质料还不是形式化的,当然一管颜料有着管状,笔的形态不同也产生不同的触点等等,但是物质本身是不固定形态的,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是深渊和匿名性的,而瞬间的断裂和离散,也取消了图像性;更加彻底的是,不仅仅是剩余,而是双重的无余:不是图像的剩余,而是转向对不可能性的经验,是瞬间之像——不可能形式化和记录——只能是余像,同时也是材质本身的无像——材质本身的无规定性,也不可能形象化。
所有个体都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在此混沌中,如果生命不被吞噬,必须找到自己存活的空间,这个空间又恰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这是彼此之间的间隙(gaps)和间隔(spacing),必须保持这个时空的间隔位置(espacement),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透气、留白等等来实现的,通过材质本身的特性显示出来的。
因此有必要还原出中国艺术传统如何创造出如此的艺术形式,以及背后的精神观念,然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如何生成新的形式。本文所研究的这些画家,都在试图回应这个问题。
在一系列痕迹(trace)的还原之后,当代艺术就在于深刻认识到艺术的无价值与世界的无意义,就是对平常性一定方式的折射,从杜尚和贝克特以来,变得尤为明确了。这之后则是涂抹的涂抹(erasure,retrait):涂抹是对痕迹的再次消除。当涂鸦本身作为行为艺术的一种,也成为被肯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被架上绘画所接受时,涂抹就显示出艺术家动作的意义了。当然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绘画”时期,涂抹已经频繁登场了。涂抹对痕迹的消除,是为了把绘画自身的材质和语汇还原为对绘画自身的破坏,艺术一直要面对绘画自身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或者说,绘画一直要消除已有的视觉资本,以及已有的艺术史的建构,如果痕迹已经开始面对无意义,那么,涂抹则是面对最后的无意义。把无意义本身也要抹去,否则,这“无意义”也成为“有意义”的了——而这是不允许的!最为重要的是,涂抹的无意义在于这是向艺术家“动作”的还原,留下的只是艺术家身体动作的幻影。不同于前次的事物痕迹的表现,涂抹是对艺术家自己动作的发现,或者说,这是艺术家身体动作与画布之间关系、与颜料之间关系的运动性的关联。艺术家自身的动作姿态决定了涂抹的可读性。
然后走向无像:这是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抽象。在无意义中保持无意义,这个“保持”是艰难的,它不能走向任何超越的形式(无论是过去意义的恢复还是超越的指向),因而就显得异常脆弱无力,要么走向极少主义,要么走向新的幻觉,因为幻觉是从混沌中生发出来。“无像”的境界不同于涂抹的动作性在于,它要求动作回到光自身和力自身的关系上。如同西方的明暗法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色彩之间的关系,而是色彩向着光与非光之间的冲击:如果没有了光,如果光处于与黑暗的关系,那就不是黑色和白色之间色彩对比的问题,而是光本身面对无光,面对来自混沌的压力!不是先有“光”,而是“光”如何从非光或深渊中涌动出来。或者说,体现为痕迹在涂抹之中的力的形式,不仅仅是画家的动作,而是在画面上体现出来的力的形式,是更加内在的意志力的表现,以及对色彩向着光还原时,光面对黑暗挤压的力量。这个时刻,绘画已经不再可能还原,而是进入了混沌之中,承受混沌的冲击。看视的方向已经逆转,不再向着对痕迹的涂抹,而是被动性地承受混沌的挤压!因此,不再可能通过简化和还原来达到这个层面,只能掉转方向,承受来自生命和艺术本身的强大力量的击打,以自身的敏感和承受能力来回应混沌的冲力。
最后是进入混沌的深渊:混沌本身是无形无像的,混沌是力的纠集,甚至还没有形成势力以及力量,而是面对“无势”的状态,艺术家要面对绘画的不可能性,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不再是面对自身的动作的展现,不再是力的呈现,而是无力,无法面对混沌,在无力面对混沌中,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无力,让混沌自身显示。当然,这里也可以找到生命自身的不可摧毁的存在。
进入混沌的深渊,有着不同的方式。有些画家通过自己对恍惚的经验再次打开了画面空间,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恍惚在笔触上的实现是通过烟雨和烟云的流淌和渗透来形式化的,以此来打开混沌。这些画家在技术上结合流淌和涂抹,把西方富有表现力的颜料笔触的涂抹方式转变为更加轻柔的带有水性的流淌笔意,彻底转换了中国传统水墨的平面展开方式,把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波洛克的“滴洒”(drip)转变为中国式的“流淌”(drift)与“渗透”(penetrate)!对于“流淌”的大量使用,在画家刘炜的作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卫保刚、老丹和刘文中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加细腻化的处理,尤其强化了画面的内在渗透,笔触一层层打开了画面的内在空间,这是中国人以其敏感和柔软转换了西方人的激烈与悲剧性气质⑦。
“流淌”和“渗透”的本体意义在于它是当下瞬间以及个体身体的气息的迹象,因此,画面就接纳了破碎的瞬间。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流淌,而且也是内在的渗透,如同宣纸被水墨所渗透,这是传统的浸润感。浸润是由表面向着里面,架上直立的画法是自上而下的表面流淌,二者是根本不同的,渗透尤为体现出中国艺术家对自由的渴望,渗透的气息相通于流溢的自由。这就是这些具有个体发现的艺术家试图把艺术本身确立为个体性的宗教。
注释:
①关于南北宗以及平淡的思想,参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屠友祥校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关于“平淡”的讨论,参见拙著《平淡的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法国汉学家于连的著作《淡之颂》也集中讨论了“平淡美学”的意义;此外,德国汉学家和哲学家何乏笔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③Jean-Luc Nancy,La création du monde ou la mondialisation,Paris:Galilée,2002,pp.55-56.
④参见杜小真编《福柯集》中同名文章,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⑤“观养”观照方式的提出,参见拙著《平淡的哲学》。
⑥参见迪弗《艺术之名》,秦海鹰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⑦参见拙著对此相关问题更加深入的讨论(夏可君:《余像绘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