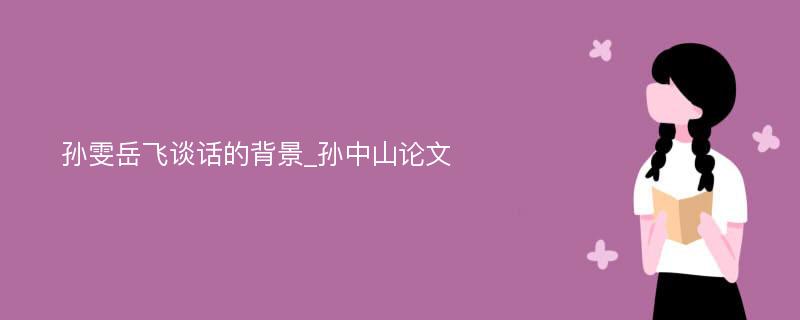
孙文越飞会谈的幕后台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前论文,幕后论文,孙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1-0110-12
1923年1月27日,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孙博士①说,俄国将放弃沙皇向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发表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文件,后来它被称为《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②。这是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的结果,是该报受孙、越二人的委托发表的,可将其称为会谈的台前。
孙中山在《联合声明》中开宗明义表示共产主义不能引入中国,这一条往往被一些学者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学者强调为孙中山如何坚持其三民主义的思想原则,西方学者索性以《孙中山对抗共产主义》③一类的题目或内容写了不少著作。这里固然有他思想真实的一面——怕“赤化”,也有他为稳住中国舆论和国民党内外同样的情绪,而做出的表态。
苏联史学界则认为这是孙中山联俄的开始。在提及这个文件时往往强调《联合声明》中的一句话:“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但是关于孙越会谈的详细情况,过去却鲜有记述。④
对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俄关系档案、1993年俄罗斯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上海工部局档案的零星记载等已有史料,可以发现一些看似零散的文件能够链接为一个完整的轮廓,并有助于揭示这个文件深层的尚鲜为人知的内容。本文将其称为《联合声明》的幕后。
一、《联合声明》中关于苏俄援助的各个层面
推翻北京政府,统一中国,是孙中山的夙愿,为此他需要一支强大的由中国国民党统率的军队。1919年孙中山整合各路人马组成中国国民党,但该党没有一兵一卒。1920年他回到上海,写作《建国方略》,规划未来中国的建设,索性将其叫做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计划,但在争取外国援助上却一无所获。
1919年也正是共产国际成立的年份,它遵循其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开始向东西方输出苏式共产主义革命,同时立即承担起苏俄外交的工具,向世界各国派遣使者。中国人熟知的鲍罗庭就是那时奉派到南美进行秘密工作的。孙中山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其军队产生了兴趣。而苏俄也希望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在其东线建立睦邻关系,于是俄共(布)远东地方组织便秘密派人到中国,孙中山凭其声望,成了这些人的联络对象。⑤
孙中山接触苏俄人士伊始,关注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如何依靠军队夺取政权。他再三宣传的也是要建立一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党军,所以他期望于彼邦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希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经过曲折的谈判,1923年产生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过去一般指苏俄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的援助。英文《大陆报》使用的标题是“孙博士说俄国将放弃沙皇从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可见对于这个文件的理解是见仁见智。无论如何,史料告诉我们的是,这背后另有玄机,是没有见诸报端的。
首先,笔者认为,《联合声明》中所说“苏俄援助”是肯定的,它是孙苏关系或曰苏联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方面。越飞到中国后不久就建议俄共(布)向中国提供400-500万金卢布的贷款,以示苏俄真诚援助中国人民,固然越飞意在击破帝国主义“只说好话”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表达的却是苏俄与帝国主义在中国角逐的意图,他所说在中国的情况下谁能出钱援助中国谁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者”或“救命恩人”的想法,释放出的却是通过有条件的援助以控制中国的意图,不过越飞总体上主张支持中国。他为自己受到中国舆论的热烈欢迎十分感动,并致函列宁等人报告了这个情况: “如果你们感受到这种不可言喻的热情……”,旨在请莫斯科务必践言,遵守其在1919、1920年所作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承诺。⑥
至于明确援助孙中山的思想,那是1922年底越飞和马林⑦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外交实践,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提出的:“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而不援助那些利欲薰心的军阀。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3年1月4日议决“肯定越飞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建议”,“支持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出”。鉴于该工作将通过共产国际渠道进行,外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同越飞同志协商,向政治局提出补充拨款的议案”。⑨
这样越飞到上海(1923年1月17日)前⑩,苏俄援助孙中山的方针已经决定。后来,援助是实际发生了的。据苏联统计,从1923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苏联给予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已经达到1100万卢布。(11)1924年6月仅仅为黄埔军校开学,苏联政府的预算即为229239美元(12),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的预算是58399港元。(13)到1924年底,仅黄埔军校一处的苏联顾问人数已经达到25人,有的甚至牺牲在中国土地上。(14)
第二,援助背后潜藏的军事政治干预因素。
共产国际对华外交遵循的也是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给其派往中国代表的指令中就有“激化中国同列强的矛盾”,在广州寻找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制造起义的人这样的内容。(15)
孙中山最早与之讨论过军事问题的刘谦及其设想也是一例。(16)此人系旅俄华工联合会内建立的俄国共产华员局远东阿穆尔省所设分会的“副首领”。(17)阿省分会由原中华社会党改组产生。
俄国共产华员局被俄共(布)当作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预备机构,原拟“移往中国”,其控制拟议中的“共产党”和输出苏式革命的性质十分明确。(18)而其机关刊物《震东报》封面上的“莫斯科共产党总筹办处”的字样,说明这个机构不仅“筹办”旅俄华人的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要“筹办”中国本土的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俄共赋予它的职能,同时传递着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理论促使东方苏醒并震动之的意图,安龙鹤便是该局派遣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旅俄华人代表。(19)
虽然俄共(布)赋予这个组织以革命性质,但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的张作霖却将“其会中之华人”说成“无业流氓”,他认为该会会长名“王宝贵”者,主持会务的“前社会党首宫甲辰即宫锡川”者也是这样的人。刘谦和该会成员积极参与了席卷俄国的没收有产者财产的行动。张作霖因该会“时常开会,均经该会文牍姜希暢发表意见、演说、鼓惑共产主义,反抗中国官府,种种谬论皆系目无法纪之言”,而呈请北京政府“速向俄远东代表优林严重交涉,以期饬阿省长官取消该会,国家幸甚,侨民幸甚”。(20)
刘谦等华工群体,为生活所迫漂落异乡,具有朴素的改变命运的诉求。但他们既远离政治和政权,又缺乏对社会问题的了解,见到苏俄出现“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景象,本能地接受了俄共(布)强有力的宣传,便认准苏俄革命才是世界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捷径,从而进入了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误区”或曰“盲区”。在俄共支持下,他们写了一封致祖国共产主义者的信,在他们眼中,北京政府是反动的、“愚蠢而罪恶的政府”,它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百姓和国家财产,是理应被推翻的对象。信中号召同胞走苏俄的路,团结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把矿山、铁路等都收归国有。同时,该信请同胞们不要反对一切外国人,因外国也有好人,这就是苏俄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有关机构将这个信件送到鼓动处,予以印刷和散发。(21)
刘谦遵循的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信条,他函请苏俄当局帮助新疆成立苏维埃,然后加入社会主义的苏俄。(22)在1920年来中国前,刘谦就已经开始在中俄边界的谢米巴拉廷斯克和七河省交界处募集旅俄华人参军。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也不明白这样的建议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和谐与领土完整。刘谦和安龙鹤等与社会党首领江亢虎有联系。(23)江亢虎也向列宁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他说早在1921年4月离开中国前(24),就同一些人酝酿过一个计划:组织起一支10,000人的军队,协助苏军占领外蒙古。(25)
张作霖十分了解华工联合会的情况,他知道“俄政府重要人”在阿穆尔分会成立大会上如何号召人们仿效苏俄,“以过激党派如共产诸政策,平均人民生计,于劳动家大有利益,既已实行国内,当普及全球,贯彻主张务达目的等语”。
中国外交部也知悉驻俄总领事陈广平在此次会上“登台发言,盛称孙大总统为我中华革命伟人,素抱民生主义,与俄过激党不谋而合。自让位项城后迄今十年,伪托共和,施行专制旧官僚之习气,军阀派之淫威,苦我同胞受其压力。若不铲除阶级制度,其将何以发展民权。旧国会选举孙文复为民国总统,已得俄国承认。凡我旅俄华侨果有爱国真心,自应互相引导,招致华人入会。本总领事当请示俄政府助以枪械粮饷,编制操练,开赴边境,侵入内地,遥与南军响应,助孙中山一举成功”。(26)有总领事陈广平出面,这种计划的性质就更加值得注意。若果真有苏俄军械相助“侵入内地”,那后果会不堪设想。
刘谦关于1920年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报告基本证实了上述情况。孙刘二人讨论的是利用旅俄特别是远东的华人组建军队,与孙中山的军队混编起来,把新疆作为军队集结地,听从设在远东俄国境内指挥中心的调遣,进军华北,攻打北京政府。(27)这种计划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来说,隐含的就不仅仅是干预性,甚至有颠覆性了。(28)
第三,孙中山危险的“让步”。无独有偶,孙中山也和刘谦一样,有过建立“新疆苏维埃”的想法。张作霖报告称,苏俄“外交部总长车林曾与粤东孙文结约,又为陈总领事怂恿,极端斯举,谋助华工会饷械为军事上行动听粤党之来粤者调遣指挥”。“现粤东孙党既以兼并广西,势必进兵闽赣滇黔川,态度已变,窥伺中原,鄂西告警。若新疆东三省再有俄邻利用华人资助饷械以扰边防,外患内忧深为可虑”。(29)不可否认,张作霖的话中含有许多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成分。北京政府鉴于这些情况,频繁颁饬其各封疆大吏注意防范,以免“过激主义”遍散国中。
孙中山在这个问题的“让步”,过去的研究著作中较少提及。建立“新疆苏维埃”便是孙中山为得到苏俄援助而在谈判桌外做出的危险让步。作为这个想法的背景,有两个因素应予交代。
一是孙吴联合政府。这涉及当时的中苏关系。因苏军1921年进占库伦时曾经允诺,歼灭那里的恩琴残部后即撤军,但迟迟未办,中国政府把苏俄撤军作为开始谈判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遭苏方拒绝。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苏俄1919年7月25日的对华宣言表示无偿归还中国,但后来食言。斯大林指示越飞不得以1919和1920年那两个宣言作为依据处理对华关系。(30)越飞无法摆脱这种胶着局面。
然而有一个人物——吴佩孚,让包括越飞在内的莫斯科及其赴华使者们产生了一线希望。一则吴提出的废督裁军在中国不无正面反应,二是吴答应在1923年初进军外蒙古(31),届时外蒙古问题便迎刃而解,一些苏俄使者访问吴佩孚后亲眼看到他的种种优势,例如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军队的实力等。(32)孙中山的声望和吴佩孚的实力,促使莫斯科形成了一个组成孙吴政府的设想。莫斯科希望出现一个亲俄政府,这样既能取代北京政府,又能对付张作霖,使苏俄在中东铁路地区的利益得到保证。
越飞巧妙地利用孙中山要推翻北京政府的心理,在致孙信中不无挑拨之意,称“北京政府确实唯列强的马首是瞻”(33),以此示好于孙。1922年9月26日越飞的军事顾问А.И.格克尔(34)带着越飞致孙中山的信由马林陪同来到上海时,孙中山已经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要求俄国帮助他在中国西北边陲或新疆省,建立一支由他指挥的军队。苏俄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可经新疆运至中国内地,从西北进军推翻北京政府。这是孙中山通过正式渠道向苏方提出其“西北计划”的雏形。(35)格克尔并不反对孙的想法,但是他此番来沪主旨是游说孙中山放弃与张作霖携手的念头,转而与吴佩孚联合,“建立一个由孙领导的政府”。那时孙会得到苏联支持。为此,越飞希望孙中山派遣代表与吴佩孚直接联系。(36)不过二人会谈时并未提及新疆苏维埃的事。
孙中山采纳了越飞的建议,便派张继带其信函北上。同时,鉴于越飞在履行其外交使命上寸步难行,所以想在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中得到孙中山从旁“配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此后张继充当联系人,往返孙、越之间,及时传递信息。
10月10日,张继由李大钊陪同会见吴佩孚。张、吴的会谈内容广泛,吴请孙中山放弃与“胡匪”张作霖的联络,而以孙正吴副的格局携手组建政府,同时利用吴佩孚的劲旅第三师落实吴的“兵工计划”,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治理和开发黄河。(37)即使这时,无论张继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向吴佩孚提出新疆问题。越飞通过马林要求孙中山多插手北京政府事务,不要倾全力于其南方,急于报陈炯明那一箭之仇,也不要因吴佩孚一度支持陈炯明,而对吴不信任。(38)
孙中山并不十分心甘情愿联吴,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急于得到援助,便产生了关于新疆苏维埃的想法,由张继在1922年11月向越飞私下转达。10月11日张继从吴佩孚处回到北京后,便在11月份把孙中山的具体计划告诉越飞:要求苏俄按照孙中山的“直接命令”,“派一个师占领东突厥的新疆省,当地只有4,000中国士兵,无力抵抗。邻省四川尽管有100,000士兵”,但孙认为自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为了尽快依靠苏俄援助推翻北京政府,孙中山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在新疆“那里可以建立任何性质的社会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这是一个具有军屯性质的计划,孙中山说他本人会到那里去,并在那里办一个中德俄联合公司,依靠德国技术开发当地资源,再开办一个兵工厂,这样既能造武器又能练兵。从地缘政治上看也是“有利”的,因为离苏俄很近。这个计划实施的前提是苏俄占领新疆。(39)至于吴佩孚,在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坚持自己的想法,在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他更主张联合后者。
越飞感到不快,他告诉孙中山,若孙不插手中央政府事务,那苏俄就只能依靠吴佩孚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暗地里,越飞认为孙中山的西北计划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40)况且在“官场上”孙中山是个人身份,若孙中山“在中国政府占有相应的地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越飞更多地是着眼于对全中国的外交,便对莫斯科说,若苏俄出兵新疆,那北京政府就会断绝与苏俄的任何交往,届时,苏俄“在中国事务中得到的就仅仅限于一个东突厥了”。(41)幸好这个计划没有实施,若苏军真的如孙所请派一个师前来,后果不堪想象,“请神容易送神难”。
第四,有助于解读“援助”性质的两个“计划”。这指的是越飞和孙中山讨论过的孙的近期计划和远期计划。
近期计划是:消灭陈炯明,然后北上至吴佩孚的势力范围汉口和洛阳,将吴击溃。在继续北上过程中,张作霖会把北京让给他孙中山,届时孙就以“统一的中国代表者的身份入主北京”。为实施近期计划,孙中山期望苏俄“在满洲挑起事端,将张作霖的军队从他占领的北京吸引到那里去”。当时越飞个人认为苏俄有可能“依据同孙中山的协定,进军满洲”。
另一个是长远计划,在近期计划难以实施的情况下采用。内容是:把国民党的基地移往中国腹地,到“穆斯林聚居的”新疆,离苏俄近一些的地方,以便同苏联“保持密切而直接的联系”。在行动上,这样“可以不经过吴佩孚的辖地”,而直接“通过甘肃、宁夏等省调动孙中山在那里的10万军队赴蒙古边界”,这一带是产粮区和资源丰富的省份,又恰恰位于通过库伦至苏联的“必经之路上”。这样便可以避开东南沿海方面可能出现的外国干涉,因为列强不敢“铤而走险”——“从海上派兵到中国腹地”。为了这个远期计划,孙中山希望苏俄帮助他在西北装备和训练10万军队,归他调遣,以备开赴“蒙古边界”。孙中山认为,只消一两年此事便可准备完毕,即可兴兵进行“最后一次‘北伐’,那就稳操胜券,届时列强的任何干涉都不足惧了”。
孙中山采纳了越飞提出的建议,用“融政治—外交—军事于一体的综合方法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越飞表示满意,便建议苏俄政府考虑这两个方案中涉及到的经费问题:能否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苏俄能否在必要时出兵满洲,把张作霖的军队引离北京;能否帮助孙装备10万军队,何时可以提供这些装备。(42)越飞本人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他提请莫斯科注意:孙中山若不能得到俄国援助,他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妥协,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就会长期拖延下去”。(43)
至此,《联合声明》关于“援助”的内容和性质已经清楚。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收到越飞的报告后,于1923年3月8日否定了出兵中国东北的建议,但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帮助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44)
回溯孙中山、越飞的会谈,人们固然能够理解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愿望,然而,他和国民党作为一支在野的政治势力,竟然要把答应提供援助的外国势力引入中国,不管它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都同样隐藏着太多的危险,都会造成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隐患。
二、外蒙古问题:孙中山的表态和越飞的困惑
上海英文《大陆报》在(2)下有一个小标题“Soviet's attitude”(苏联的态度),可以理解为这是越飞概括性的表述,是他应孙中山要求而“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俗称第二次对华宣言)。外蒙古问题列为(4),其前有一个小标题“Notimperialistic”(非帝国主义的)。文中有一句话:“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同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有了这个前提,孙中山才同意苏俄军队可以暂时不撤出外蒙古。孙中山之所以要求、越飞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对舆论做出的姿态。然而无论如何,孙的立场与中国中央政府是相对立、唱反调的。至于《联合声明》中所说“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这一说法也相当值得推敲。
首先,“庸弱无能”指的是北京政府“无力阻止”某些“行为”的发生。然而从中苏谈判的进程看,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北京政府是强硬的,它一直坚持苏俄先撤兵外蒙古再开始两国复交谈判的立场。(45)至于“赤俄”如何对付“白俄”,若发生在苏俄境内,自然另当别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并不需要别国派遣“维和部队”前来维持秩序或帮助其“庸弱无能”的政府。
不过,越飞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孤立,他得到中共的支持。1922年9月刚刚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此前后发表了许多文章,中共与孙中山的态度有相近之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表述是西藏、蒙古、新疆等省,若将其“统一为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所以应该先赞成其“自主”,然后“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46)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其机关刊物上,有人认为若收回外蒙古,就是“要替军阀多一块地盘,替帝国主义多了一块殖民地”。张国焘甚至因蒙古受到中国外交系、军阀、蒙古王公和中国奸商的“欺压”,而“称许”苏俄占领库伦。按照这种逻辑,就应该把这一片广袤之地拱手让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的苏俄了。(47)无独有偶,20多年后,到1945-1946年中苏谈判时,斯大林对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也说过“外蒙人民不愿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48)
越飞当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到中国不久便致函孙中山,就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小心翼翼地探询后者的看法。他先是说明,苏俄没有渗入外蒙古的意图,目前由于苏军的驻扎和“干预”,外蒙古才是“唯一没有落入”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中国领土”,苏俄若在当前这样的混乱时刻撤军,“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渗透进去。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撤出蒙古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越飞甚至明显地利用孙中山的心理,告诉他说北京方面“不管说什么事,动辄就问我们究竟何时从蒙古撤军,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大造声势要求我们从蒙古撤军”。(49)
孙中山收到越飞信后5天便立即回答,说他“同意苏军驻扎蒙古”,请越飞不要同北京政府谈判,等他到北京重建政府后再议。相应地,对于外蒙古,孙中山的打算也是等他入主北京后“再行谈判”,“若贵国军队立即撤出,则只有利于列强中的某一个国家”。(50)
越飞是否说了真话呢?否。他仅仅是在履行其外交使命。然而私下里,凭着一个人的良知,他感到困惑。因为他在中国亲身体会到苏俄1919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产生的强烈反响,他体会到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平等待之民族的出现。8月12日越飞到中国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是把他当作真诚的朋友和友好使者予以接待的,乃至东交民巷外交团“用一种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视,很含醋意”。(51)
8月23日越飞致函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报告了中国舆论的热情态度,不无难堪地说“苏俄驻军外蒙古”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但他记得列宁给他写信时说过:“突厥——这是指印度,是指我们的世界政策”,越飞作为外交官必须履行政府指示。但是他认为,苏俄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涉及外蒙古、中东铁路和俄国租界等问题时,必须恪守1919、1920年加拉罕宣言的精神,并“做出最大让步”。他说,我们俄国提出的要求应该适度,“不得有一丝一毫让人感到我们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简言之,通过谈判加深我们对被压迫人民的友情,展示我们的政策不同于任何亚洲国家”。(52)
然而,几天后的8月3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指示他“不得从1919-1920年间的一般宣言中做出同中国谈判的直接指令”,而且要请蒙古参加中苏谈判。这使越飞更加感到困惑。9月他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等人表述自己在对华外交第一线的难处:
如果我在自己的发言中不提1919、1920年我们的宣言,那就绝对不会激起人们对俄国问题如此高的热情……蒙古是我们对华政策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帝国主义者用以反对我们的王牌。他们千方百计在打这张牌……
如果在谈判中真正在一切方面考虑中国人民利益,使中国人民渴望的东西得以实现,帝国主义不给的我们给,那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会发展起来,深入下去……然而只要我们开始为我们制造的那个蒙古政府说话,那么在广大人民群众眼睛里,我们就和帝国主义一样了,所以,我认为你们的密码电报中关于蒙古政府参加我们就此问题谈判的要求是特别不恰当的。(53)
越飞感到愧对中国舆论,他和马林在同年底联合撰写了一个提纲,认为俄国对外政策应当“在民族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54)
然而越飞本人的困惑并没有解除,外蒙古的情况令人扼腕。历史的发展说明,无论从192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被斯大林赋予的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参加中苏两国正式外交谈判的特殊资格,以及斯大林为此让越飞再三说服国民党领导人,还是抗日战争后外蒙古的独立,都在苏俄政府的谋划之中。(55)从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角度来说,《联合声明》中担心的“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最后毕竟还是“酿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表态“现为苏联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最后他毫不隐讳,索性摊牌:“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卫之法律权”,否则“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56)蒋经国据理力争,说把外蒙古割离中国,中国不仅失却七八年“抗战的本意”,而且国民党会因“出卖了国土”而愧对中国人民。但斯大林强硬反驳:“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可以自己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57)
“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使人想起《联合声明》中关于北京政府“庸弱无能”的语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国,中国却最后失去了一大块领土。(58)由此可见,无论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越飞关于“非帝国主义”的表态,还是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第五条所述“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59)的表述,都不过是真正的外交辞令。
三、关于中东铁路问题
《联合声明》中表述,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铁路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联合声明》中的表述与一年多后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并无相左之处。但是有两个幕后情况必须予以交代。
一是,由于中方——中国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据理力争,中东铁路问题才得以化险为夷,以“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的语句出现于《联合声明》中。
苏俄认为,中东铁路为“反苏”的张作霖盘踞,他向俄“白党”提供栖息地,使之利用中东铁路进行危害苏联的活动,令后者感到芒刺在背。1922年秋季,当中苏正进行复交谈判时,苏俄军队已经在中俄边境集结。苏俄酝酿武力占领该路,快刀斩乱麻,一举歼灭张作霖的势力。中东铁路上一度剑拔弩张。就连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也认为应当派遣军队到中东铁路。(60)但在正式发给中国外交部的文件中,苏俄表示这“纯属虚传”。(61)
这一计划受到三个方面的反对。一是中国外交部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二是孙中山的反对。他先是致函越飞,表示对苏俄拟采取的行动不胜“惊愕”。他明白苏俄是为了其在中东铁路的利益而决定出此举动,所以请越飞相信,他不仅有能力“迫使”张作霖做出令苏俄“满意的保证”,将来执行与孙中山相同的对苏友好的政策,而且苏俄能够通过孙在“张作霖处达到一切目的”,“非帝国主义的俄国为英明治理国家定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62)
孙的信乍看起来意在劝说苏俄不要这样做,以免后者在国际上名誉扫地,造成外交上被动,引起英、美、法、日等国的干涉。其实孙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思考,即他写此信乃因苏俄的“军队逼近东北引起了他的担心”,恐苏俄会支持吴佩孚打张作霖,“也就是说最终还会支持他[吴佩孚]打孙中山”。(63)
事关重大,张继奉孙中山派遣于11月9日再次与越飞交谈,并将一封孙中山致列宁的信交给越飞。他告诉列宁等人,苏俄前“对中国的声明,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大的希望并争取了中国民心”,所以请苏俄“不要做出任何类似占领北满这样不理智的举动”,否则“中国人民定会将其视为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64)
第三个反对的声音,是由越飞发出的,他向列宁等人明确表示,苏俄不能这样做:
甚至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问题上,我们莫斯科存在完全错误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敢这样做,日本现在也不得不撤出中东铁路。外国都是在保护侨民的口号下把军舰开到中国水域。一支军队要有4-5万人,还要懂中文和中国习惯。俄国没有这样的军队;外国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在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活动……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没有哪个敢把兵直接开进来,而是以防范外国涌入为借口。这是华盛顿会议决定的。(65)
上信写于越飞得知此事之时,莫斯科收到信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向莫斯科陈述和建议,苏俄不能重蹈沙皇旧辙:
当初沙皇修建中东铁路时,主要是为了扩张和占领满洲……
放弃中东铁路,就等于表明不同意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中国人也坚信我们会把该路归还中国,那么再抓住中东铁路不放或要求中国人将其赎回,就等于继续沙皇的政策,并把中国人对我们的信任破坏殆尽。(66)
《联合声明》中自然不会反映这样的计划。后来苏俄也恐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而取消了这个打算。(67)然而苏俄对中东铁路绝不言放弃,越飞通过马林告诉孙中山,苏联“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中东铁路》不可能再给了”。莫斯科让越飞明确地告诉孙中山:苏俄“不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去支持他”。(68)
苏俄后来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完全遵循“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例如他们提出按照中:俄=3∶7的人员比例成立一个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委员会,要求孙中山亲自前去或派人游说张作霖接受苏方建议。(69)孙中山认为这是“一厢情愿”、“单方面的”,但为尽快得到援助,也不得不派遣汪精卫等人多次劝说张作霖,而没有结果。(70)经过极其复杂的交涉,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一直拖延到1950年。
《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幕后的交涉,是在中苏国家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苏联史学界过去强调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那么今天俄罗斯学者们的看法当更加客观,这就是无论莫斯科使者还是共产国际的活动“从来都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71)同样,我们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待《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也会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苏关系和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注释:
①有学者引述关于孙中山早期在夏威夷活动的文件,称那时文献中“Dr.Sun Yatsen”就是“孙逸仙医生”(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年,第287~288页),但在许多情况下,读起来似乎不太顺畅,如越飞给孙中山的信也称他Doctor(博士)。显然,此处用医生不如“博士”,所以只能理解“博士”为尊称。
②1928年《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用的是The Joint Statement of Dr.Sun Yatsen and A.A.Joffe。查“statement”意为“声明”或“宣言”,此处据内容看,译为《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更加确切。俄文是Совместное коммюнике“联合公报”。关于苏联何以当时没有发表公报的全文,参见拙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207~208页。
③如Maurice William,Sun Yatsen versus Communism,Hyperion Press,1932,reprinted 1975,USA.
④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档案Municipal Daily Report(1923年1月20日~2月2日)和Annual Report(1923)有英文资料,但很不完全。
⑤详见拙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7~71页。
⑥“越飞致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信”(1922年9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下同),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18页。
⑦详见李玉贞:《马林Henk Sneevliet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⑧越飞和马林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00~101页。
⑨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149页。
⑩迄今为止关于越飞与孙中山会见的日期,记载并不一致。详见拙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99页,注释77。据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452页),他们会见是1月22日,地点是“莫里爱路孙宅”。这是《民信日刊》23日的报道,应当是确切的。
(11)А.И.卡尔图诺娃编:《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通信》(Переписка И.В. Сталина иГ.В.Чичерина с полпредом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Л.М.Караханом (1923-1926) ,документы сост.),莫斯科:纳塔利斯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
(12)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987,第13页。
(13)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987,第40页。原文此处标示的币种是“美元”,据上下文看,应当也是香港元。档案中有时使用“墨西哥元”,这些币种与中国元的比价待查。
(14)P.A.,米罗维茨卡娅:《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тратегии Гоминдана),莫斯科,1990年,第54页。
(15)“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国外东亚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7页。
(16)有的书将其误译为“刘建”或“刘江”,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1)第6号文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
(17)据俄共(布)旨意1920年6月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后成立,同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予以批准。联合会中设立了一个具有组织和领导全俄境内华人党员的机构,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 (б),该局图章上刻的是中文“俄国共产华员局”,应当使用这个名称(详见拙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2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将此历史机构翻译为“组织局”,显然不妥。
(18)【苏联】《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аейшаяистория)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9~144页。党章总纲内明确了这个组织的目的:“为组织旅居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凡有华人共产党员的地方均建立隶属于俄共(布)委员会的华人共产党支部”。作为领导机关的俄国共产华员局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时设于莫斯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内,其所有重要问题决议的做出均须“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该局党章凡4条,其中明确要“在祖国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及支部,并同暂设于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华员局中央局取得联系。Р.А.米罗维茨卡娅在《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88年第2期再次公布,题目是《关于旅俄华人党组织章程》( Об Уставе организаций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в России)。
(19)1979年笔者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一文中曾使用“安恩学”的音译,经查实,安龙鹤才是其中文原名。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166,第4~5页。安氏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东铁路工作。1904年到俄彼尔姆,参加了当地反抗沙皇的运动和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活动。1918年在秋明组织中国支队,后参加红军。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参加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在华工和红军士兵中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近现代史》杂志,1959年第5期,第139页。
(20)(26)台北“中央”研究院藏中俄关系档案,外交部收咨(1921年6月21日发,23日收)。
(21)安龙鹤致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信(Письмо АнНенхака китайским коммунистам),原件无日期,据内容推断,因1921年该组织迁移至上乌丁斯克后基本停止活动。PFACIIH,全宗495,目录154,案卷5,第2~3页。
(22) РГАСПИ,全宗495,目录154,案卷5,第1~2页。
(23)(27)《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2页。
(24)江亢虎于1921年4月24日离开北京,经哈尔滨赴俄,在苏俄期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见其《新俄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25~35页。
(25) РГАСПИ,全宗492,目录1,案卷152,第7~8页。
(28)后来伍廷康(魏金斯基)、马林还同远东共和国有关方面讨论过此事的进行。《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3~114页。
(29)“黑龙江督军张作霖致外交部长颜惠庆电”(1921年10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档案03-32-319(2)。电文中所称车林(即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与孙文结约,不知所指。
(30)“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2年8月31日会议记录节录”,《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86~87页。
(31)“越飞致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信”(1922年9月),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20页;“越飞致契切林的信节录”(1922年11月1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0页。
(32)“格克尔与孙中山的谈话”(1922年9月2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04页。
(33)“越飞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9月15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97页。
(34)格克尔,全名Анатолий Ильич Геккер(1888.8.25-1938.7.1.),生于第比利斯,毕业于符拉基尔学院训练班和总参谋部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加入俄共,十月革命后被选为第38军参谋长。1919年2月任步兵第13师师长,同年5月至1920年2月任13军团军司令。1922年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副院长,同年7月出任苏俄驻华武官,1925-1926年在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任职。1929-1933年任苏联驻土耳其武官。1934年起在总参谋部任领导工作。1938年遭错杀,后获平反。
(35)《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97~99、104~106页。孙中山之所以通过正式渠道向苏方提出其“西北计划”的雏形,是因刘谦本人已在1920年穿过中俄国境时被打死。关于该计划,参见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及其夭折》(北京:《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及拙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62~391页。
(36)“格克尔与孙中山的谈话”(1922年9月2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05~106页。
(37)随波:《北京通信:吴佩孚与张继对于时局之谈话》,1922年10月19日《申报》。
(38)“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8~89页。
(39)《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6~117页。“东突厥”指新疆东部,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欠妥。
(40)“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89页。
(41)“越飞致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8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6~117页。
(42)“越飞致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摘录”(1923年1月27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69~171页。
(43)早在1922年8月31日,越飞在写给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信中就说苏俄要想“当中国的救命恩人”,就应当向中国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贷款。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2194,第115页。
(44)《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82页。
(45)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李玉贞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42~458页。
(46)君宇:《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向导周报》,第3期,1922年9月27日;该报为发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蒙古代表登德布在此次大会上的发言《蒙古及其解放运动》时写的编者按,《向导周报》,第5期,1922年10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47)君宇:《国人对于蒙古问题应持的态度》,《向导周报》,第3期,1922年9月27日;国焘:《还是赞助新蒙古吧》,《向导周报》,第8期,1922年11月。
(4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第576~577页。
(49)“越飞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8月2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78页。
(50)“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81页。
(5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610页。
(52)“A.A越飞致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斯大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信”(1922年8月23日),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8~9页。
(53)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2年8月31日会议记录节录,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86~87页;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14~16页。
(54)“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9~100页。
(55)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0、115号文件;“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8~89、101~104页。
(56)《战时外交》(二),第579页。
(57)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74年,第67页。
(58)《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1945-1946)》,载《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25~1459页。
(59)《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271页。
(60)(65)“越飞致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信(1922年12月14日)”,PFACHH,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75、71页。
(61)“外交部致苏俄代表节略”(1922年11月11日),“苏俄代表致中国外交部节略”(1922年11月1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7~399页。
(62)“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3页。
(63)“越飞致契切林的电报节录”(1922年11月10、13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9页。
(64)“孙中山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29~130页。越飞同张继谈话的内容与此完全相同,并且说明“孙中山要求把信转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9页。
(66)“越飞致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信”(1922年12月29日),РГАСПИ,全宗5,目录1,案卷2145,第95页。
(67)“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第53号记录节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82页。
(68)“达夫谦致斯内夫利特的信”(1923年5月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2页。
(69)“达夫谦、越飞致马林的电报”(1923年5月5日、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1~172、175页。
(70)“达夫谦致斯内夫利特的信”(1923年5月21、23日)、“孙中山致达夫谦和越飞的电报”(1923年5月2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6、178页。
(71)阿基别科夫,什里尼亚:《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与共产国际》(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документы),莫斯科:俄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张作霖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20年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吴佩孚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