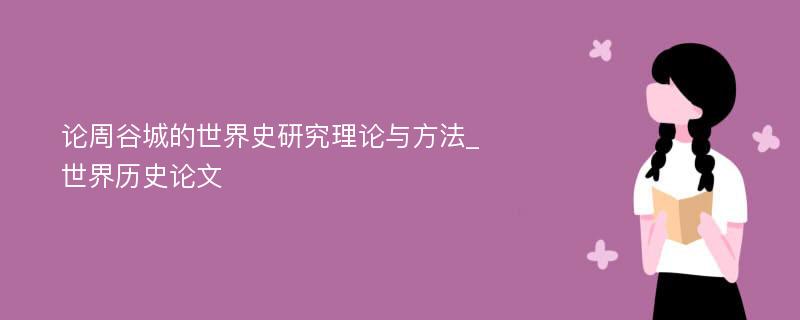
试论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城论文,世界史论文,试论论文,方法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至于中西兼顾、既熟悉中国史又熟悉世界史的学者,也是甚为稀少;而达到学贯中西和融会中西,两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和很大成就的大家,那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就在少如凤毛麟角的专门大家中,周谷城教授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相当突出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对中国史有着自己独到、精深的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和两大卷的《中国通史》;而且对于世界史也有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也写出了不少见解独到、精辟入理的论文和三大卷世界通史(第四卷因种种原因未完成)。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说是独一无二,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
周谷城教授的学问博大精深,涉及面甚广,本文不可能涉及他所有的学术见解和成就,主要只是想就他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些个人的感受。
周谷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哲学和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这在像他那样的老一辈学者中,为数并不很多。然而,尽管周谷城很早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但他始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而是坚持认真思考、深入钻研、实事求是,因此对于许多学术问题,都有着他自己独到的、有时甚至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在世界史研究中,他始终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种种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来构筑他的世界史体系和撰写有关论文。即使在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他都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坚持真理和科学精神,经常唱着与当时“革命气氛”很不协调的“反调”(实际上是科学和实事求是的道理)。为此,他遭到了团团围攻和严厉批判,有些时候甚至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对象。但今天看看那些“批判”他的所谓“檄文”,除了唱高调、扣大帽和可笑无知外,反过来却恰恰证明了周谷城勇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正直、无畏的学者品质,证明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的正确性和实事求是性。
周谷城虽然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但他从来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史学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并且还应该有一个层次更高的历史哲学。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历史完形论”(注:参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0页。以后所引用的周谷城的一些论点和见解,除出自此文集外,还引自《周谷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不再一一标明。)。所谓“完形”,即历史自身要“完整”,要有“全面、完整”的形态,或“全局性”之意;史学不应该把完整的历史割裂开来,弄得支离破碎,东一点、西一点地去反映历史;写历史既要构成“统一的整体”,又要“分别反映”,等等。周谷城还站在哲学的高度,从适用于自然界、社会界和精神界的“全局与部分”、“普通与一般”、“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共同规律的角度,深刻论述了历史中的全局与部分观念,即“部分与全局,同在而有别,有别而同在。部分不能不影响全局,但全局终必决定部分。部分离不开全局,全局为部分的最后决定者”,“这等道理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可得解释问题的方便”。周谷城特别重视历史的全局观念,为此他撰写了多篇论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周谷城从“历史完形论”的角度出发,逐一批评了中国史学常用的各种体裁的史书(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等)的共同最大不足——那就是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为此,周谷城主张历史应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如果要写出一部具有“历史完形”之通史或其他类型的史学著作,就必须以下列几个标准为必要条件,即:选材应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应以说明史事为标准,标题应以符合内容为标准。
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旧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乾嘉式的繁琐经院考据方法仍十分盛行,甚至被许多学者看作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事和“真正学问”,就连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新派学者蔡元培都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周谷城却很不赞同这种观点和治史的方法,他没有走同时代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老路,没有一头钻到考证和考据学中去,而是十分辩证他看待史料和考证的作用。他承认,“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史料“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但再多的史料并不等于就是历史,更不是“完整的历史之自身”。至于离开了全局的考证,甚至为了考证而考证,那是没有甚麽意义的,史料的考证必须取决于全局,而对于全局有关键性的东西却非考证不可;不能把历史弄成是一大堆零碎史料的堆积,“不能把个别史料的考释之和看成整体历史之有机组织”;有时史料太多反而比史料太少更麻烦,因为编排不好会把历史写得更糟;……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有些人企图用史观代替历史的另一种倾向,指出史观也非历史之自身,而只是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周谷城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客观的独立存在,并非是有了史学家的研究和著作后才存在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史学界中颇为流行的把历史看成是史学家主观产物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反对把历史分为“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以上诸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恐怕已不稀奇,但在60年前唯心主义史观还在旧中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能够这样坚决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却是很难可能贵的。
周谷城把上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也运用到了世界史研究之中,提出了许多精辟和中肯的意见。譬如,关于编写世界通史,他认为“今日世界通史的著作,仍是单纯堆砌零碎事件者多,阐明有机组织统一体者少。现在世界通史有如百科全书,按目录或索引检查,可以查到个别事情的知识”,而“阅读全书,了解世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则很不容易”。因此,他自己在编写世界通史时,则“首先考虑的是统一整体问题”,“力求得出世界史发展的统一整体,或有机组织”;“在仔细审核材料的同时,必须高瞻远瞩,注意整体”,“务必力求有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以便得出历史的规律性”。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偏重统一整体,材料不多,不免空疏;单有丰富的材料,而看不出统一整体的有机组织,则一定流于繁琐。这两者编写同时注意。”
关于如何编写世界通史,他明确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具体叙述时,应“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看重世界各国相互的关系”;研究世界通史不能不利用国别史,但简单地把国别史加起来也不等同于世界史;同样,各专史之和不等于世界通史,各朝代史之和也不等于通贯的世界各国历史。周谷城不仅仅只是在理论上坚持和倡导这些观点,而且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就是这么做的。他在编写世界通史时,自认为在寻找有机组织、希望得出统一整体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认为他编写的《世界通史》“不同于百科全书,不同于材料的机械堆砌”。他的这番话,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没有像大多数世界通史著作那样,把人类史与自然史割裂了开来,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人类史看成是自然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及自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自人类产生之后,人类史与自然史就互相交错,影响和作用在一起。在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中,进化、发展的观点贯穿全书——从宇宙的进化,到地球的进化,再到生物的进化,最后才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几者相加和相合,才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周谷城这种极为宏观的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正是我国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缺乏的,在我国解放后编写和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注:周谷城编写和出版《世界史》虽然是在解放前,但他在解放后再版时,没有对原著作更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通史著作从来都不把自然史(宇宙史、地球史、生物史等)放入人类历史之中,仿佛自然史与人类历史没有很大关系;也没有把人类历史放在自然史的统一发展中去考察和撰写,仿佛人类史不是自然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继续与自然史同步发展。在斯大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头批判的消极影响下,我国学者也很少提甚至不提自然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直到把自然环境看成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近现代)基本不起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相悖的。如马克思说:“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从这一点来看,周谷城确实是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和精粹。
周谷城关于世界史的另一个鲜明观点就是他始终反对把欧洲历史看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即欧洲中心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中国国力还很弱、国际地位还不高、还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欺辱的时代;在欧美史学家独霸世界史坛,而国内一些学者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甚至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候,周谷城就高扬以史实为据的科学治史精神,态度鲜明地举起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大旗,批驳了那些把欧洲史作为世界史中心的理论和观点,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这是与世界历史的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着我国的史学研究,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以苏联史学“马首是瞻”,跟着苏联史学界的观点转。然而由于苏联本身是欧洲国家,其文化和史学传统也都是以欧洲为主,因此苏联史学也没有跳出欧洲中心论的圈子,甚至把欧洲中心论翻版成“苏联中心论”。但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周谷城也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反对欧洲中心论。不过,周谷城并没有因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欧洲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或者创造另一个甚麽“中心论”(如以亚洲为中心,或以亚非为中心,甚至以中国为中心,像某些赶时髦、所谓“爱国”的学者那样),而是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和肯定了欧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因此,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第三卷中,还是将欧洲历史作为这一卷的中心或重点。因为,周谷城认为,“是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出发,还是从全局的本身开始?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开始,贯彻下去,必有所偏。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因此,我们认为周谷城对于世界史框架和全局的看法,对欧洲史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是唯物辩证的、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
周谷城研究世界史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他既具有十分深厚的国学和古文根底,同时又具有渊博的外国史知识和颇高的外语造诣,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一方面,他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以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另一方面,他又用中国史博大精深的内容去充实、丰富和完善世界史。他认为,如果用世界史的眼光来观看中国史,对许多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更明白,有高屋建瓴之感,正如全局可以订正部分的原理那样。例如,关于长期争论不休、意见分歧很大的中、外历史分期问题,周谷城认为可以用中外兼顾和对比,把中外历史发展一起进行考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搞比较研究会发生“生搬硬套”错误的那种学术氛围中,他仍十分重视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力求寻找中西历史的共同或相似之处,区分彼此的不同和差异之处,认为这样做,“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作出“更切合现实的考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或成果”,从而找出世界历史“分区并立,往来交叉”等发展规律。
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著作和文献中去寻找和发掘有关外国史的史料,利用祖国古代史家的成果为研究世界史服务。为此他特别撰文,介绍中国古代史家和史籍对外国史研究的情况,谆谆劝导和号召世界史研究者学习祖国古代史家研究外国史的精神、方法和资料;特地介绍和评价了许多祖国传统史学中对研究古代外国史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元周致中的《异域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明张燮的《东西洋考》、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以及二十四史、《通典》、《通志》之类正统史书中的有关部分,等等。
周谷城一生著作极丰,但他不写大批判式的、或应景式的文章和专著,从来没有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及种种极左的东西带入他的研究和著作之中,更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构筑他的世界史体系。即使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在我们国家极为浓重的年代里,他也不改初衷,坚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他的《世界通史》比较强调社会实际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化,较为突出文化和文化的作用,并且特别注重文化的传播、交流与相互影响。因此读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总觉得比起其他一些世界史著作来,特别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里写出的世界史著作来,要少了一些刀光剑影,而多了一些实际生活和文化的气息。周谷城认为世界历史是多元发展的,但多元发展中又有向一元发展的趋势,人类历史既是多元并立,又是统一整体;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各文明、各地区更多一些独立并存,但并存中又包含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到近代以后,这种互相往来和交叉更是日趋增多和频繁……周谷城把他的这些思想都贯穿于他的《世界通史》一书中:在第一卷,他采用的是诸区并立的写法,第二卷着重讲欧、亚、非三洲的互相关系与交往;第三卷则突出重点写欧洲……。
周谷城对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和作用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他再三强调,研究世界史,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历史,史学应该联系实际,“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他主张应尽快编写出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农村经济变迁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来教育和鼓舞人民,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此,他深刻指出了我国史学界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如“改造世界历史的活动走在前面”,而“研究世界历史的活动却落在后面”,研究世界史的人员大大少于研究中国史的人员、两者比例悬殊,极不正常;多次大声疾呼要大大加强世界史的研究,增强和扩充世界史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并对于怎样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至今看来,仍然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今年,是周谷城诞辰100周年、逝世2周年纪念。重读他的一些文章和著作,重温他的一些思想、见解和教诲,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的世界史研究工作,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和启发。WW吴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