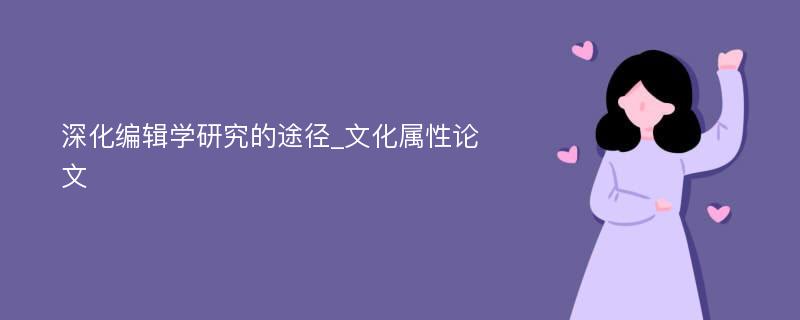
深化编辑学研究的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途径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出版科学研究主体和核心部分的编辑学研究,从80年代至今十多年来已取得很可贵的成绩。但是编辑学的理论建设仍需要拓宽和深化,尤其需要深化以增强学科的力度。本文就深化问题略述己见。
途径一:从零散中整合化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实践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分支学科和建立在多向研究的基础上的。目前编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具备了这种较为成熟的基础:从古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触及各个领域的编辑实践活动;各级编辑归及的专门出版机构;有一定覆盖面的部门编辑学研究:有大量的编辑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围绕编辑活动进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理论、探讨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型的低层次研究上,且是零散的、杂乱的,而非系统的、普遍的、本质的,缺乏理论高度和理论体系。要实现编辑学本质性研究,实现编辑学研究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越,必须把杂乱的、零散的研究加以整合化,进而归一化、本质化。整合化过程亦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1.将零散的、杂乱的观点整合化。编辑学研究中零散的、杂乱的观点都是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部门的编辑及其探索者站在各自独特的视角对编辑活动、编辑实践加以印证、总结而成的,如在对编辑概念的阐释上,有的站在编辑流程角度,有的站在稿件运行角度,有的站在文化传播大范围角度,或书籍角度、报刊角度、或音像影视角度、或电子读物角度等。由于处在各自的视角、各自的立场,因而对编辑概念的阐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我们必须寻找较精确较科学的编辑内涵,因为只有把这些零散的、杂乱的分散理解化而为一,去伪存真,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寻找到编辑概念的真谛。真正普遍意义的编辑学理论反过来又应可解释这些不同视角的不同见解。
2.将分支或部门编辑学整合化。分支编辑学蕴含着编辑学的普遍概念,通过分支编辑学亦可整合出编辑学的本质。目前分支编辑研究有一定的成效。按物质载体不同可分为:图书编辑学、报刊编辑学、学报编辑学、音像影视编辑学,前三种都已有专著出版;按内容不同可分为:文艺编辑学、科技编辑学、少儿读物编辑学等,部分有专著出版;按编辑分工不同可分为:决策编辑学、组稿编辑学、版式编辑学等,有许多论文。这些分支编辑学脱离了编辑工艺流程的总结阶段,达到了从编辑的某一方面较为广阔地探讨编辑学阶段,从各个不同分支编辑学的整合中,寻找它们的共同性、普遍性,从而整合出编辑学的本质属性。
3.编辑学研究尚处于需要整合的初级阶段,在理论框架和体系的建立初期,对编辑学研究不宜泛化、扩展外围,应集中——整合——本质化。其一,不应再扩展分支编辑学,如有人提出编辑经济心理学、编辑社会学、编辑美学、编辑心理学、编辑伦理学,这可以说是一种对编辑学的泛化。因为编辑经济学、编辑社会学等实际上就是把编辑和经济、社会放在一起,这只能说编辑和经济、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存在这种关系,因此不能把它变成“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也是如此,它们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们的触角无所不及,而不是编辑的专利品,因而也就不足以规范编辑的本质特性,对深入编辑学研究也毫无裨益。再者,不能单凭方式、过程泛化编辑学研究。单凭编次、排序、分类、搜集材料、整理加工等操作方式显然难以区分编辑活动和著述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有什么差别。这就像单凭构图、取景、用光、配色等无法区分绘图和摄影的本质属性一样,因为许多事物的方式、过程都是相通的,如上面提到的“编次、排序、分类、搜集材料、整理加工”,一个蔑匠的编织也大体如此,因此单以方式,过程来概括编辑本质并藉以建立编辑学的理论是不行的。
途径二:从邻体中本体化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靠近、借助、依赖另外事物而存在,任何事物的本体也是靠近、借助、依赖其邻体而存在。对某一事物缺乏认识时,我们可以先从它的邻体入手借以达到分析认识本质及其属性的目的。我们对编辑学的研究难以深入时,也可借助它的邻体通过观察、分析、比较、鉴别来达到深入编辑学研究的目的。
编辑学的邻体科学有:情报学、信息学、传播学、目录学、版本学、出版学等。其中编辑学与情报学、信息学、传媒学、目录学、版本学是交叉关系的相邻,与出版学是从属关系的相邻。
例如,我们从与编辑学属交叉型关系的邻体情报学中考察而认识编辑学的编辑概念:情报学中的“情报”含有高于语法信息的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在情报科学中,情报源产生情报都具有一定语义,它们属于主观情报,同客观信息量不同。如果单从量的角度而论,两份情报所含的信息量可以完全相同,但它们的涵义作用可能完全相反。所以情报的含义不仅涉及到情报发生者发出情报的含义的度量,还牵涉到情报接受者对情报的理解程度。从广义的角度讲,编辑实际上也是以信息(文稿等)为基点,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编辑学中也要考虑其发出信息和接受信息的关系和作用,但编辑落着点还在于作为信息的发出者。可以说,编辑物是情报源中的重要内容,大量的编辑产品是情报的信息基础。而情报又是衡量编辑效果的检测器,如在对编辑物的质量评比中,往往把复印率、文摘率、索引率、引用率作为编辑物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也就是编辑物或产品作为情报的运用利用程度。如果把编辑学和情报学放在文化传播这个大范围内来说的话,它们都是精神文化传播链条的重要关节。编辑是精神文化传播的初始阶段——从半成品(文稿、音像品等)经过选择、加工以生产出成品;而情报是精神文化传播的后续阶段——把成品推销到顾客手中的流通阶段。因而从情报这个编辑学的邻体中可以窥探出编辑的某些本质属性,界定编辑学在精神文化传播中的确切位置。
编辑学与信息学也具有紧密的交叉关系,信息是编辑物来源,编辑物也加入信息行列中作为其广泛的基础,编辑学也可以说是对信息收集、选择、整理、加工以大量复制传播的科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与编辑学也有着紧密的交叉关系。
因此,通过对编辑学邻体学科的研究,从邻体与编辑学这个本体的对比分析,可以靠近、窥见、探视和了解编辑学这个本体及其真正具有本质属性的内涵。因此,从邻体中本体化是深化编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途径三:从具体中抽象化
十多年来的编辑学研究,优劣并存。从数量上、广度上说是成绩斐然,但从理论高度上看则很欠缺,不能不说它们都是些经验色彩的研究。最典型的有两大类:一种是对编辑过程或编辑工艺流程的复述,“这种文章主要是将现在编辑工作当中的各个环节,诸如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样等编辑程序照本宣科地复述一遍;”(注:杜厚勤.编辑学理论研究之非是思考,载编辑学刊.1994年第5 期)另一类是对编辑活动的复述,以历史上某位名人的编述活动和言谈来诠释编辑学或经验。经验固然是有用和有益的,但经验没有普遍的品格,它们就事论事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们不能区分地指导特殊情况,也不具备广谱的宏观意义,只有科学理论才能指导更大范围的实践。布鲁克斯25年前就情报科学的理论建立时说过:必须把情报科学中起源依简单规则的操作经验,通过科学抽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注:王崇德.图书情报学方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重要的程度几乎对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编辑学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深化编辑学研究所进行的科学抽象化,其一“是要与编辑学现象直观相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编辑现象或编辑事物多种属性中,撇开非本质的属性,抽象出最本质的属性。”(注:任定华等.关于编辑与编辑学对象及期概念问题.《编辑之友》.1995年第1期)
例如,在揭示编辑概念时可以从书、刊、报、音像、影视、电子读物面对的共同点抽象出其本质属性:书、刊、报的编辑都是以现有的文稿(文字形式)开始进行选择、加工以期印刷出版,文章的署名权是作者而不是编辑;音像、影视、电子读物是借助电子的声、光、影对其歌曲、节目、制作品等进行加工以期制作成音像、影视、电子读物,署名权是作者、记者、演出者等,也不能是编辑。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选择、加工,都是从半成品(已经过作者、记者、演出者、编者最初、最原始的选择、加工)着手,都是期望复制以广泛地传播,其作用都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要。因而从中可以抽象出这样一条结论:编辑是把半成的精神文化产品剪裁、加工以通过某种载体复制物化后满足人们不同的精神文化需要,编辑学是关于把半成的精神文化产品剪裁、加工以通过某种载体复制物化后满足人们不同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科学。
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论是一切科学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在大量的具体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积累经验诚然重要,但如能通过整合化、本质化、抽象化而走向理论高度,并使之系统化、体系化、本质化,并又用理论指导编辑实践,则更为可贵和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