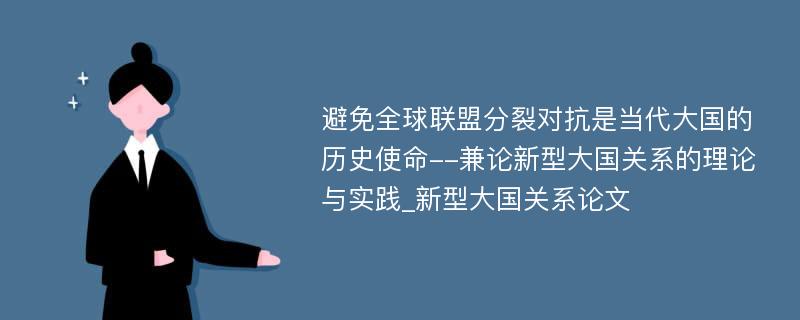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全球性论文,历史使命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014-12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目前大国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对话与合作伙伴关系有所增强;其次,国家利益仍是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主动力;再次,传统大国普遍陷入结构性困境;最后,新兴国家正成为大国关系的新主体。能否避免传统大国关系中的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局面,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之举。
一、当代大国关系没有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的本钱
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而言的。尽管历史上一直有大国与小国之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就有在某个地区内几个相对的“大国”争霸的记录,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国关系是在出现由几个大国有实力瓜分世界市场的背景下才开启的,并形成了传统大国关系概念。
传统大国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二是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传统大国关系不仅政治关系是分裂的,而且经济关系也对抗,没有统一的相关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主导意识的历史惯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这两个基本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相互间一直处于结盟分裂对抗的“冷战”状态。就当时的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而言,之所以会陷入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理论上未能科学认识当代世界的统一性是一个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世界统一性获得了越来越清醒、科学的认识,不仅坚持改革开放而且在国际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既不愿做超级大国,参与地区霸权、世界霸权的争夺,又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因而作为对大国关系发展的正面诉求而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尚存的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立足于避免大国关系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既符合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也是当代大国关系发展面临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自从和平发展时代到来后,尽管传统国际体系依然发挥着相当强的影响力,显示了某些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但是避免大国关系形成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同样也获得了史无前例、日益增长的掣肘力。①这个掣肘力就是:由于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已经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性全球体系,使当代世界更显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这个掣肘力也为传统国际体系转型、摆脱历史惯性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都依赖全球各地的他者自我实现的可能需求与可能提供的成果;尽管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但是都不得不承认他者存在的价值,不得不承认他者稳定发展的意义,不得不接受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救助,也不得不相互作出必要的妥协,不得不寻求适合各方需要的社会建构与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便在寻求矛盾对立统一中谋求各自的自我实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既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也是面对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共生关系的合理选择。因此当代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相互尊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高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具有现实需求,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符合所有大国的发展利益,显示了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要求,显示了当代世界统一性的历史规定。
当今世界,所有大国都处于共生性全球体系之中②,尽管各自对全球共生关系的依赖程度有差别,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是谁都只有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才能生存、发展,谁都只有在做大共生性全球体系这块蛋糕的过程中获得更大权力和更多利益。各自优化和优化选择全球性共生关系是任何大国的最佳选择。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就是遵循了这种最佳选择。如果说这种选择使曾经四分五裂的欧洲走上了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使曾经各自发展的大西洋两岸国家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那么未来的更大发展依然得依靠对业已形成的共生关系能否进一步作出优化和优化选择。两极格局的解体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共生关系的优化和优化选择提供了更为广宽的空间和机遇。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提出了这方面努力的必要性。
尽管美国依然有沿袭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欲望,但是一直面临难以为继的挑战。美国确实有一帮盟国、盟友,搞一些局部性“群狼战术”固然还有点本钱,但是成功率也有限,说明本事并不大,更不用说没有本事让其所有盟国、盟友都相信面对共生性全球体系搞全面性的全球对抗是必要而又值得的。何况,如果其他大国没有意愿与其做对手,这台戏也唱不起来。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唱这台戏既没有必要性又不值得,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面临禁运、封锁、制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但是最终都证明挑战发起者美国及其跟随者循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既困难重重,又都落得失败的命运,而中国反而变得更强大了,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国情又适合世情。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足够大的回旋空间而能不参与大国对抗,也有足够大的创新智慧来优化和优化选择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开拓空间,根本没有理由要“东施效颦”,拴在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尾巴上。
二、结盟分裂对抗并非处理大国关系唯一和不可避免的选项
正如任何事物均有两重性一样,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大国处理相互关系也有两重性。这种内生性动力的双重性源自于国家具有独立性、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的基本属性的双重性。如果说独立性、主体性属性赋予大国内生的竞争冲动,显示张扬的个体性,甚至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那么合群性、共生性属性的外在必然性是要与他者共生,形成共生关系;两者都是维护生存、发展、寻求自我实现所必需的。当然,大国自我基本属性的双重性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处理相互关系的动力双重性则是随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说两国之间,“当商品进不去时,士兵就要跨过去”,讲的就是变化的一种动因,表明不存在选择的绝对性而只有相对性,都是相对于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言的。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开启的国际社会共生关系,尽管出现了传统大国关系概念,但是传统大国关系的争斗不仅无法阻挡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发展趋向,而且共生性全球体系的逐渐孕育、生长、发展,也赋予大国关系逐渐具有体系结构性,使大国关系成为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性运动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无论是国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还是相互间关系出现显著变动,都逐渐出现了互动连锁性效应,即使各种危机也逐渐具有互动、联动性,经由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的传导机制而具有了外溢性、蔓延性。③这就告诉我们,共生性全球体系从其开始孕育、生长的那时起,就是作为共生关系的结构体系发展起来的,不仅大国之间的竞争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同在,而且大国之间的合作也需要由结构性矛盾转化而成。这当然均因条件变化而变化,然而最基础性的条件是大国之间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都存在于共生性全球体系之中,都必须适应共生性全球体系的体系结构运动变化需要。这就是说只能以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来应对,以便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与制度设计,既避免因结构性矛盾而使相关各方迎头相撞,又能为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合作创造条件、开拓空间。
不错,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政府来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但是任何大国自身基本属性的对立统一性的规定性要驱使其寻求这种可能性,必然要对他者为此“鸣其声矣,求其友矣”,因而出现了交往沟通、对话协商的需要。正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构建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趋势,出现了几乎所有国家都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趋势中来的盛况,显示了当代国家对认识相互关系的新的觉醒。尽管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但是既然这一趋势已经开启,那么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纠正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符合各国的发展利益,而各国也只能以寻求自我双重基本属性对立统一来寻求自我实现,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某种拘束。
当代的美国同样是独立性、主体性属性与合群性、共生性属性双重基本属性的对立统一体,这种属性的规定性使其处理大国关系的动力同样具有双重性:尽管依然具有引发与其他大国结盟分裂对抗的内生性竞争冲动,在美国主导下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依然具有历史惯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并不因“冷战”结束而解体,甚至还在继续拉帮结伙拼凑新的联盟,以面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于是中国等新兴崛起大国成了美国高度警惕的对象。尽管中国反复表明不威胁美国,但美国依然很难完全听得进去。美国甚至对其盟国、盟友同样具有相当高的警惕,不仅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监视,而且需要不断塑造共同的敌人,以便将他们如蚱蜢一样拴在一起,这或许与美国对当代世界统一性的认识相关联,似乎只有按美国的意志将世界统一起来,世界才有前途。但是美国处理大国关系还有另一面,即美国必须也只能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才能寻求自我合群性、共生性的自我实现,因而即使具有强烈的利己动机也必须为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合作共生创造条件,显示了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性力量的不可抗拒性。这就是说,尽管美国依然维系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但是仅依靠这种历史惯性已不能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不能不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实的匹配性。对美国的这种关注,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利己的动机和面临的困难,更要研究其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吻合性,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客观理性。
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的历史惯性是基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但是共生性全球体系生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创造某种新的条件,使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变成可调和性,这同样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2000多年前中国先贤荀况已经发现“人能群”。就是说人有智慧和能力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使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变得可调和,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这同样为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进入19世纪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所显示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凸显出来。面对各种危机、冲突、战争的不断爆发,对抗逐渐由局部性、区域性演变为全局性、世界性,进入20世纪后又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大危机”。当年的当事国家都对此几乎是一筹莫展。当年许多人都认为世界矛盾具有结构性,危机、冲突、战争都具有结构性,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不可调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不仅走出了曾经被许多人认为不可逾越的一系列困境,而且终于走进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尽管人们对此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根本而言表明人有智慧有能力“能群”,有智慧有能力科学认识世界范围的结构性矛盾,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因而能不断地从矛盾冲突对抗的困境、泥淖中走出来。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尽管确实存在众多一时无法调和利益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当今国际社会促进这些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合作的动力生成因素越来越多,包括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分工越来越细的跨国经营的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巨额游资都要寻觅生财之道;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必须由各大国共同参与治理;需要相互救助的情况经常发生,即使超级大国也不例外;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平等均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科学技术的创新,知识的创新等等,都需要人们展示“建构性思维”,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诸如此类的动力生成因素组合成促进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合作共生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没有意愿做超级大国,参与地区霸权、世界霸权的争夺,又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而是希望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而作为对当代大国关系发展的正面诉求,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而且科学地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向。尽管至今尚不可能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地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出现了消退、减弱的趋向。如果说欧洲曾经是传统大国关系的发源地,那么这种趋向今天也首先发生在欧洲,显现了“相反相成”的效应。所谓传统大国关系,在历史上最初仅涉及欧洲的大国关系。欧洲曾经是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的实践区。美国崛起后,传统大国关系才扩展到大西洋两岸,但是中心依然在欧洲。传统大国关系的结盟分裂对抗最终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在欧洲。说欧洲具有大国争霸的悠久历史传统或许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27年的争霸战争,至今依然吸引着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尽管与美国一起参与两极对抗,至今依然是美国盟国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还不时地与美国采取同心合力的行动,但是在内部关系上却结束了结盟分裂对抗,走上了一体化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尽管异常艰辛,却也显示了当代人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与制度设计的巨大智慧和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历史性转折,尽管人们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是可以随条件变化而停顿的,人们只能永远臣服于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是站不住脚的。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停顿的现象告诉人们:第一,尽管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已经延续了几乎5个世纪,但并不存在不受任何条件制约而具有无限延续性的可能。第二,当代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发展必然会迫使人们在寻求合作中寻求自我生存、安全与发展,人们也有智慧、能力与胆识直面结构性矛盾并创造条件将其转化为结构性合作,实现合作共生,因而迎来了国际制度创新蓬勃发展的时代。
按照传统大国关系理论,当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时,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我生存与安全都将不得不选边站,从而造成世界整体性的结盟分裂对抗。如果说这种局面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已并非完全如此,同样显示了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出现了消退、减弱的趋向。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两极对抗年代有中小国家选边站的情况,而且这种现象至今还存在,但是更多国家并没有选边站,尤其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几乎都没有这样做,因而曾经出现过声势浩大的“不结盟”运动,因而美国在今天要纠集一批国家对某个国家策动一场“狼群攻击”也并非易事。尽管一些国家至今在概念上是美国的盟国,但并非时时、事事都按美国意志冲锋陷阵、英勇献身。这些事实同样告诉人们:第一,如果说至今确实依然存在某些中小国家选边站的情况,但是在共生性全球体系高度发展的时代有足够大的回旋空间为自我发展获得条件,选边站不仅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有的国家明知对自己不利,但即使要想从选边站的“围城”中走出来也并非易事。第二,面对共生性全球体系的高度发展,各国与他国的关系都面临如何优化和优化选择的考验,以便首先满足国内民众改善生活、增进福祉的需要,因此对是否有必要“选边站”通常则变成一事一议,独立自主作出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还在延续,传统国际体系尚有存在的空间,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还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因此和平发展时代是传统国际体系与共生性全球体系并存的时代。在此时代到来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正在消融,这不仅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空间,而且也为国际体系转型、摆脱历史惯性提供了条件。当然新型大国关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要变为现实性,仍需要我们贡献出智慧和能力。
四、走出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需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赋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逐渐消失,相应的一系列传统观念也在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有必要研究可以取代的观念是什么,以便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新的观念层面上。
例如,当代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世界财富还是如何增值世界财富?是否需要用世界财富增值论取代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
如果说随“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开启国际社会后,几乎所有大国乃至崛起中的大国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分配世界财富以及如何为此抢占有利地位,因而发生了抢占世界市场的争夺,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大国关系的模式则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上逐渐变成一国财富的增值不仅并不是剥夺他国财富,并不意味着他国财富的减少,而且事实上给他国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增值的机会。不仅大国有财富增值的机会,而且即使中小国家也有财富增值的机会。传统的新兴大国崛起必定会抢占世界市场正在变成为全世界创造市场,必然会瓜分世界财富正在变成为全世界贡献财富,必然会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正在变成为传统大国继续兴盛创造条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固然获得了巨额增长,然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却也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不仅在向中国的巨额出口中获利,而且在向中国投资中获利,波音、空客等众多大公司大企业都是获利的大户,也因此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境外许多昔日的中小企业也因此变成了大公司大企业。因此确切地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仅为世界创造了市场而且为世界贡献了财富。所以在当代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用世界财富增值论取代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是有依据的。对各大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缩小他国财富增值的空间,而是如何管控与他国的矛盾与分歧、借助他国财富增值的机遇实现自我财富更大增值。
再如,当代大国关系变动是权力转移还是权力相关扶持?是否需要用权力相互扶持论取代传统的权力转移论与权力博弈论?
传统大国关系变动的过程是权力博弈、权力转移的过程,甚至还求助于战争。这种权力博弈、权力转移论关联着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按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理论,权力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的,权力的转移意味着财富的转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依然有人认为权力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应该为权力而斗争,美国也至今依然要坚持领导世界,但事实上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不是权力转移,而是各自的权力需要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通过相互支持来维护。战后这种大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尽管一些国家依然企图使政治权力成为财富的来源,但是这种机会正在变少而不是增多。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获取更多财富,根本上依赖本国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谁具有最大的比较成本优势谁就具有最大的竞争实力。就此而言,国家实力、国家的财富最终来源于比较成本优势。如果说这种比较成本优势也同样带来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是依靠他国的承认、依靠与他国的合作才能实现的。这种规则的变化客观上不仅大大削弱了为寻求财富而疯狂争夺政治权力的冲动,而且增强了寻求与他国合作实现自我权力的内生动力,显示了权力实现的相互性。当代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均具有共生性,各自的权力、利益之间都具有共生性,因而使各自的权力、利益得到自我实现才有可能,其内在的逻辑是权力实现的相互性而不是权力转移性。
第二,尽管一些国家依然企图使政治权力成为谋求、控制资源的工具,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在削弱这种必要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扩大了获取原生性资源的可能,而且提高了合理利用资源、充分发掘原生性资源利用潜能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集成创新、开发创造新资源的可能。如果说这也能带来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不仅是创造权力增量实现的,而不是从权力的存量中转移获得的,而且可能获得的巨大权力增量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只要想一想美国创造了互联网,不用一枪一炮创造了多么巨大的权力④,构成了世界霸权新的支柱,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权力不是叫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权力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同样是要获得他者的承认和需要,与他者有自愿合作的可能。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是以资源为纽带的。⑤如果说曾经的纽带是原生性资源,在带来共生关系的同时曾经也带来对抗与争斗,而今天正在进入由创新资源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创新能力,而且是相关各方的合作共赢。美国如果不放弃利用互联网作为攻击他国或监视他国的工具,必然会迫使他国不得不另辟蹊径,削弱美国在该领域的权力和财富也不可避免。显然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在根本上对美国是有益的。
第三,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赋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救助,国家权力的相互扶助成了常见的国际现象,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截然相反的矛盾景象。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际事务场域,既不存在一国可以独占的权力,也不存在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能维护的权力。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力救助同样显示了相关各方的真实需求。不仅仅基于道义,而是基于共同的或相似的利益,本质上是对对方某种权力的肯定,根本原因是相关各方的利益、权力的汇合点越来越多,不仅有日益增多的利益汇合点,而且有日益增多的权力汇合点。维护他者的某种权力就是为了维护自我的某种权力,具有相辅相成性。在国际活动的许多场合,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权的行使,都可以找到利益、权力汇合点的各种案例。发现和拓展大国关系的利益、权力汇合点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当代大国关系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其中一个重要切入点是要彼此客观理性看待双方战略意图中利益、权力的汇合点,尊重和支持对方的利益、权力合理关切,避免只要对方客观理性,而自己看待对方却不那么客观理性。如果过度强调对方战略意图与自己的分歧点,过分强调权力使用方式的分歧点,甚至以偏概全,不顾及双方战略意图的利益、权力汇合点,势必会将对方视为对手,这是非客观理性的必然结果。善于发现和拓展大国关系中各自战略意图的利益、权力汇合点,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的重要前提。否则欲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就会相当困难。
①金应忠:《论两个体系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1期。
②金应忠:《国际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③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
④杨剑:《数字边疆的权力与财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⑤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标签: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共生关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