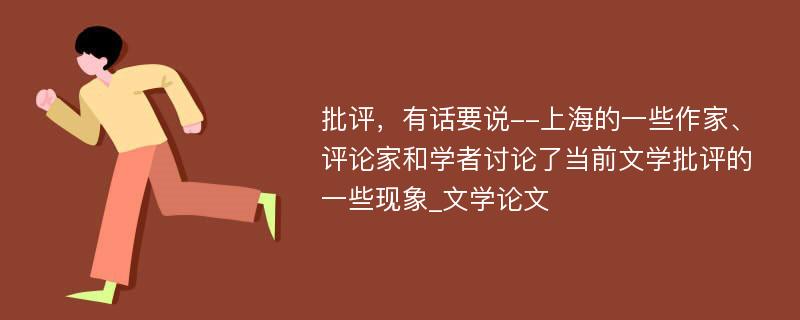
批评,有话好好说——沪上部分作家、评论家、学者座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评论家论文,沪上论文,学者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题:审视当前文学批评的若干现象
时间:1999年12月8日
地点:文新联合报业大厦
与会者:徐俊西(文艺评论家)
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安忆(作家)
秦文君(作家)
梁永安(复旦大学副教授)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王光东(上海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
召集者:文汇报特刊部《书缘》专刊
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
——勿把王朔金庸之“争”狭隘化
王安忆:客观地说,我觉得王朔批评金庸的文章写得不错,并且就这篇文章来说,王朔似乎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玩世不恭,相反倒是蛮严肃的,蛮有人文关怀的。我觉得王朔是借题发挥,他借骂金庸表达了对现在的人文环境的一些看法,其中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而媒体一再要求金庸出来作答,反而把这场讨论狭隘化了,变成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争执,变成两个作家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了。如果能把这场讨论向健康的方向引,可能会好一些。
王朔虽然是借题发挥,但他这人话不好好说。我觉得金庸表现得很好,因为王朔有些话很无理。从辈分上来说,一个是长者,一个是晚辈,也不能这样说话。换作我,理都不会理他。但金庸脾气很好,很大度,表现出宽厚的长者风范。
徐俊西:王朔的这篇文章倒不是痞味很重的,不是有意和金庸过不去,而是想借此表示他的一些想法。王朔要抓住一个能够引起轰动的对象,于是找了金庸这样一个最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人物,想通过骂他震惊一下文坛,因此故意把一些问题说得很极端(王安忆插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作惊人之笔,现在有人想借批名家自己出名,王朔倒不一定有这个动机。他文中的看法也不无道理,比如对金庸小说“套路”等的批评。
另一方面,我觉得金庸在批评问题上的大度,表面上很谦虚,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想吸取王朔文章中一些合理的东西,或者对王朔批评的偏差进行反驳,金庸的“大肚能容”,那种所谓的“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宽容,实际上也不利于批评的深入开展。在王金之“争”上,我觉得两方面都有态度问题。
秦文君:看王朔的文章当时觉得王朔心里有气,可能是因为金庸被捧得太高的缘故。金庸的作品在新武侠小说里面应该说是第一块牌子,但总的看来,它还是一种通俗的东西,文化含量、文学含量、灵魂性的东西比较少。王朔的批评可能与金庸在我们文学中的过高的位置有关,所谓物极必反。如果王朔的批评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吵架”,任其自生自灭,“吵”完之后,金庸还是金庸,王朔还是王朔,文坛还是文坛,那就没有达到实质性的目的,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王晓明: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这下子文坛有好戏看了”。文章说这两个人都是不好的人,现在他们自己“咬”起来了,说得很刻薄。这种心情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包括《十作家批判书》,大家不愿好好地认真严肃地面对一件事情,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抱着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好像自己置身于事外,这其实是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放弃,然后就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在旁边冷嘲,连热骂也没有。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
《十作家批判书》:当代文化的一个案例
——商业原则正向文化领域推进
徐俊西:看了《十作家批判书》,感觉里面很可能有商业的、个人出风头的动机,但客观上,毕竟文坛批评寂寞了这么多年,需要震荡一下,引起一些轰动,就不能用平常的、正常的手段,它就要采用策略。一个策略就是抓住一些大的对象,大家关心的那些人;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我要么不批,要批就把问题“上纲上线”,弄得很极端,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或许作家本身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不能排除出版商有商业炒作的动机。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可以对前些时无声无息的文坛有所触动。对名人包括大师,能从反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尽管有些是过头的,却能促使人们思考。文学艺术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东西,批评是很正常的;对目前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功过得失,并加以引导。
另一方面,我觉得批评不管怎么尖锐、直率,不要故意哗众取宠,丑化或者过分的挖苦,这种方式往往会使批评适得其反;本来你的意见也许有可能得到人家的赞同,但方式不当,反而会令人反感,更难以被人接受。比如《十作家批判书》中对《围城》的批评,你说它不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经典,可以,但你一定要说它是“伪经典”,好像它是冒牌货、假货,完全没有价值,这就不妥当了;文章的一些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说得有些过分,有些则是故意找茬,站不住脚的,如说《围城》作为一本小说,什么东西都有了,就是没有小说,这就不对了。批评最主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还是要以理服人。现在的这种批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容忍,但不是正常的批评,还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批评。现在有必要建立批评平台,倡导平等的、多元化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梁永安:我感觉《十作家批判书》跟王朔对金庸的批评还不太一样。王朔是借题发挥,他的语言方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他这个人的风格就是这样,但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还是比较严肃的,王朔想借此表达自己的价值观,里面有严肃的价值面;而《十作家批判书》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比较漫画化。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文章有一定的学术见解,如朱大可的那篇还是不错的;有些文章前面谈得还是可以的,但结论却一下子滑向谩骂。出现这一问题,我觉得可能要从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找寻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有农民传统的一家独尊、排斥其他的心理,对文学作品的评判也是如此,要么捧上天,要么批得一钱不值,不善于多元共存,特别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多种文化的合理成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利。
再者,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缺乏一种庄重,常常把很多东西都看成游戏。由于缺乏庄重,当我们面对现今文化上的一些“死结”,面对大的问题而需要用一种严肃态度来解决的时候,往往就会把它游戏化。我觉得这种风气是多种力量造成的,商业化的炒作与批评者不良心态的结合,再加上大众不健康的阅读心理。反过来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也按这个方式来对付它,把它痛骂一气,或挖苦一番,而要用建设性的、健全的、多元的、理性的思维来面对这一现象,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如书中钱钟书与鲁迅的比较那一部分谈得就很好,有些分析还是挺到位的。
秦文君:最先看到《十作家批判书》,是在一个从来不看文学的人那儿。他一看到这本书马上就买下了,我觉得这不是非常健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爱好文学、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你去买这本书,我很理解;他去买这本书还是一种窥探,骂人的书他就想看,他是带着这种本意去买的。如果文坛需要这种东西来吸引大众,我觉得不是文坛的光荣。我直感这本书文人的东西少了些,学术的东西少了些,比较刻薄的东西多了点。文坛永远需要批评,但要与人为善,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批评之后,我希望以后大家能有话好好说。
王晓明:《十作家批判书》中有些文章有挺好的意思,如朱大可评余秋雨的文章我曾在网上看到过,印象中这篇文章不像他的其他文章,说得还蛮清楚,蛮到位,当然也有不同意他的地方,但收入书中后,跟网上看到的印象是不一样的。这其实是图书包装、策划或者炒作的一个结果,是学理的文学批评的因素被商业炒作的原则重新组织起来的一种东西。因而这本书可以看作商业原则向文化渗透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化原则不仅作用在经济领域,而且开始向整个的文化领域全面推进,包括文学批评领域,因为现在它觉得在这个领域也有利可图了。商业的原则就是有利可图。
我最近就碰到过一件事情。一家出版社要将我最近两年的短文章结集出书,这当然非常好,但他们老是要改我的书名,老是要改我的目录,他们的出发点很好,希望这书卖得多、影响大,于是就不断地来跟我搞磨。出版社觉得不包装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一定要包装过之后才有市场。他们策划一本书时总有一个假想的读者群,认为读者是一定会喜欢他们所包装出来的东西的。而有意思的是,各个出版社的包装行为的假想读者都是差不多的。问题是商业原则对消费者的假定是否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效,怎么办?如果有效,它又说明了什么,我觉得类似这样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多。这本书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看成当代文化的一个案例来分析的。它里面有哪些对的哪些错的还不是主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
文学批评面临挑战
——媒体批评、学理批评及其它
王光东:来参加会议前,我和陈思和(王光东正随陈思和攻读博士——编者)就这次讨论的议题作过一次交流,我们的想法是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批评,一种是媒体批评,还有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批评。媒体批评应该说是受大众文化、商业炒作影响较大的,当然这种批评有时候可能也有学理批评的成分在里面,但由于炒作,它可能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因此它的意义就让人值得怀疑了。当然媒体批评的存在有它的意义,但与真正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距离。应该将这两种批评区分开来,对这两种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看待它。
我们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学理批评。学理批评是探索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媒体炒作所出现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分辨出来,不要受那个东西的影响。
罗岗:我们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很大的挑战。这里说遭到挑战倒不是因为王朔的批评,或者《十作家批判书》中有一部分文章写得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都不是这个意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朔包括《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实际上都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与其说是指向这些作家,譬如金庸,譬如钱钟书,倒不如说是指向我们曾经有过的对这些作家的评价。譬如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我觉得他更大的一个部分不是在说金庸究竟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曾经有多少人为金庸说了多少大话,过头话,说了多少让人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的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前提的话,就很难理解王朔为什么要这样来说话。譬如说,《十作家批判书》里面批评钱钟书的文章,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象,那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认为他为中国现代小说史贡献了两个作家,即钱钟书和张爱玲,这是专门设了专章来讨论的作家,只有鲁迅的小说是与他们并列的。有了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目的了。
第二个方面,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王朔他们究竟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这批人我更多的不把他们看成是媒体的声音。我觉得媒体不是一定要炒作,按照我们对媒体批评的理解,媒体应该有非常公正客观的书评制度,比如《文汇报》请人写的书评,是与出版社无关的。比如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国的《明镜》周刊还在批评他,说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媒体并不等于炒作。媒体,尤其是大的媒体完全可以,而且有可能提供一个公正的批评场所,所以我觉得王朔们并非代表了媒体的声音,他们更多的代表的是普通大众的声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金庸和王朔的事情成为一个事件,这事件的最大反应不仅仅是在报纸上,报纸上都是些作家或评论家在谈论;如果我们到各大网站的聊天室去看看,那里可热闹了,那些参与议论的人都没有名气,或者是金庸迷或者是王朔迷。他们有的也用类似这本书中的说话方式,而不是那种经过学术训练的批评家的方式,有点无所顾忌,也就是我们说的“街头巷议”,而“街头巷议”现在有了公正发表的场所。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些批评,都写得非常厉害,他们的批评中可能惟一的一个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们根本不懂。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倒不在于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怎么来强调学理性,或者是应该如何运用我们原来的一整套的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来进行文学批评,相反我们今天可能要面临的一个更困难的局面就是,像金庸、余秋雨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已不仅仅是普通的作品,他们也已不是普通的作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时代文化的一个象征,我们经常要举他们的例子来讲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依照原来的那一套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的理解来评价他们,则很容易得出与大众评判不相背离的结论。如果我们的专业文学批评工作者不把自己的目光作一个调整,我们则会不断地遭到挑战。
王晓明:文学批评的确受到了挑战。我觉得,九十年代不乏很好的批评家,但是九十年代的批评确实存在问题。八十年代的批评还能把握住文学的脉搏,有的批评甚至还把握得很准、很透彻,那个年代的批评的读者,大量的是文学圈以外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被当成文学批评来看待,而且还常被当成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来看待。因为当时的批评确实有这样的功能,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系。一些重要的话题,或者对当时社会最敏锐的一些发现,常常是由作家首先提出,然后由批评家来作出阐发和解释的,这样的批评才有力量,才有影响。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这个下降有一部分是应该如此,因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发展起来,原来由文学承担的功能分化成很多功能,大家共同来承担,因此文学的重要性相对来讲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一枝独秀。但是像今天这样,文学变得这么地不重要,我总觉得似乎不应该如此,或者说今天的文学还是应该并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些比较重要的位置的。我觉得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得太快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文学批评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实际的文学创作情况是一回事,我们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印象又是另一回事。今天中国还是有一些相当好的作家,在认真地创作,而且创作出来的作品相当不错。但是这样一些作家的价值,他们的工作、努力并没有在社会对文学的印象当中充分地反映出来,相反九十年代流行的、被舆论看好的那些作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不重要的,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流行的作家被杂志包装,被报纸宣传,可是深入下去一看,这些作家的东西跟流行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不具备特别的精神特点,立刻觉得索然无味。我觉得读者对文学的冷淡与这个有关,因为你跟我们想的没有什么区别,你没有提供给我们新的东西。莫言最近有一个小说集,其中有些小说相当不错,但没有引起注意,这就是我们文学批评的失职,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
钱谷融:几十年来我们没有正常的文学批评,从《武训传》批判以后,要么捧上天,要么打入地下,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文学批评的氛围。所以我觉得《文汇报》抓住这个机会开展这样一个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没有文学批评,文学要真正发展也就很难了。批评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批评方式也可以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格式。而不同的人所取的态度和方式源自他的学识、修养、个性和品格,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文学批评本来就不单是一种学术批评,它首先应该是文学的,应见出批评者的个性来。王朔的个性从他的批评中显露出来了,《十作家批判书》也是这样,批评者是没办法隐瞒他的优点缺点的。许多年来我们习惯将批评往意识形态上引,往政治上引,现在终于可以宽容各种声音了。但怎么使得批评真正正常起来,健康起来,真正把文学当文学,把文学论争引导到真正的文学批评上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