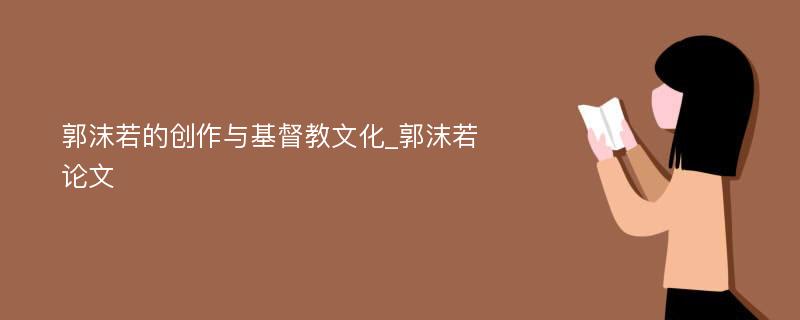
论郭沫若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基督教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是与欧风美雨的吹拂浸润密切相关的,其中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许地山、冰心、庐隐,还是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中郭沫若的创作中常呈现出独特的基督教色彩,虽然他的创作不像许地山那样努力描写充满基督之爱的苦难历程,不像冰心那样执意叙述洋溢着基督的博爱、宽恕的爱的哲学,但在他创作的艺术构思、忏悔模式、典故运用中,都可看到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一
作为创造社主要发起者之一的郭沫若,他的思想主张也常常影响着这个社团。创造社社员大约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郭沫若曾在《创造季刊》的发刊词《创造者》中全力赞咏创造者,他礼赞“作《神曲》的但丁”、“作《失乐园》的米尔顿”、“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他幻想着“首出的人神”、“开辟天地的盘古”,并将他们称作“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此中虽然溢出浓郁的泛神论的色彩,但其中也可见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在《创造周报》发刊词《创造工程之第七日》中,郭沫若在历数了“上帝,你最初的创造者”六天的创造业绩后,却谴责上帝第七天“便突然贪起懒来”, 责怪上帝创造的“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并宣告:“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起。”虽然其中有着对上帝的不恭之词,但创造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是肯定的。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也说:“不过我们不要想不劳而获,我们不要把伊甸园内天帝吩咐我们的话忘了。我们要用汗水去换生命的日粮,以眼泪来和葡萄的美酒。我们要存谦虚的心,任艰难之事。我们正在拭目待后来的替民众以圣灵施洗的人,我们正预备着为他缚鞋洗足。”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忆及创造社的刊物《洪水》的命名时说:“上帝要用洪水来洗涤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创造社所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从中亦可见一斑。
郭沫若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并不像许地山、冰心等有着皈依的背景、较长的历史,他接触基督教文化主要由于三个方面:他从《新旧约全书》中、从基督徒的夫人处、从富有基督精神的外国作家作品里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濡染。他忆及最初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时曾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1 〕将《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的郭沫若,他对《圣经》的内容十分熟悉的缘由大概也在于此了。1916年8 月郭沫若去东京的圣路加医院为病逝的朋友陈龙骥料理后事,与在此院中当护士的佐藤富子结识,两人很快“相与认作兄妹”,相识到相恋。佐藤富子“她是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的Mission Shool(意即传道事业学校)毕了业后, 她便立定志愿想牺牲了她的一生,在慈善事业上去。她便弃了她的家庭,由仙台逃到东京,在京桥区的圣路加病院……充了一名看护妇。 ”〔2〕在后来成为其妻子安娜的佐藤富子处,郭沫若得到了基督教的濡染。诺依(Roy )在《郭沫若的早年岁月》一文中指出:“……佐藤富子的理想主义和对宗教的笃信颖悟对郭沫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沫若曾在1916年11月给她的信中宣称自己要皈依基督教。虽然无法确知郭沫若自认基督徒有多长时间,但他随后的作品还是显示出他对新、旧约的熟稔。”〔3〕从郭沫若许多自叙传的作品中常常可见其信教夫人的身影,郭沫若从其信教的夫人安娜处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郭沫若的创作受到过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泰戈尔、梅特林克、但丁、哥德、莎士比亚、卢梭等人的创作,都是郭沫若所喜爱并深受启迪的。人们常常将基督教视为理解西方文学的一把钥匙,作为西方文化主要内容的基督教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渗透于产生西方作家的那片土壤之中,基督教的思想观念、故事传说,《圣经》的故事、典故、艺术手法、叙事方式等都对西方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郭沫若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那时是把我迷着了。我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4〕泰戈尔的宗教观以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爱”为核心,1922 年瞿世英指出:“泰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的表现东方思想;同时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动。于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时代精神之油,照耀起来,便成了他的思想。”〔5 〕泰戈尔的诗文中浸润着基督的爱的宗教,这使早期的郭沫若深受影响,他将泰戈尔的学说称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6〕。 郭沫若说初到日本时期“偶而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我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儿之死》”〔7〕。 有人认为:“《青鸟》这本剧本虽然表现他对于寻觅真理的态度,也可以说他彻悟真理后心境的描写和记录。但其中有许多部分与宗教有关系,梅氏之所谓真理,或者是基督教之所谓真理吧?”〔8 〕郭沫若也从梅特灵克的创作中感染了基督教思想。郭沫若对但丁的创作十分喜爱,他多次推崇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9〕的但丁,他的《神曲》“很久以来就是一切西方国家每天的精神食粮”〔10〕。《神曲》运用基督教神话传说素材,表达作者所追求的纯洁的基督教理想。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模仿了《神曲》的构思。郭沫若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他的创作也曾从“泰戈尔式”而转入“哥德式”的了。歌德的宗教境界、泛神思想、主情主义等,都使郭沫若“有种种共鸣之点”。〔11〕莎士比亚专家威尔逊·奈特认为:“基督精神自始至终贯穿着莎氏的作品。”“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每一个都是小型的基督。”〔12〕郭沫若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从中也受到启迪与影响。被歌德誉为开始了一个时代的卢梭“在一个颇具智慧和笃信宗教的牧师家里愉快地长大成人”,他是位基督徒。〔13〕卢梭的《忏悔录》以忏悔的形式赤裸裸地坦露他的思想感情。这种宗教式的忏悔方式也被郭沫若借鉴作为他创作的一种形式。郭沫若从众多外国作家的创作中,加深了对基督教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受到泛神论影响的郭沫若,他对宗教显然没有许地山、冰心那样深入和执著,他虽然较多地接触、了解了基督教文化,但他对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持批判的态度。在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双簧》中,以第一人称的反讽语调透露了作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作品描写在1926年北伐军攻破武昌城时,“我”代理邓演达去汉口的青年会作演讲。司会者以烦琐的基督教仪式开始了会议,唱赞美歌、作祈祷、致开会辞,“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祭坛来做燔祭”。“我”在作了革命的仪式后:“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基督耶酥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的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我”以中国人对入侵者的割地赔款证明其所说的观点,以反讽的口吻针砭了中国政府的腐败,也嘲讽了基督教教义的不适时宜,从中亦可见郭沫若对基督教的态度。在小说《一只手》中,郭沫若借一位瞎眼老人的口,抨击了基督教的虚伪:“他们还说什么天,还说什么上帝,这只是有钱人的守护神,有钱人的看家狗,说更切实些就好像有人的田地里面的稻草人。他把地狱的刑罚来恫吓你,使你不要去干犯有钱人的财;他把天堂的快乐来诳惑你,使你安心做有钱人的牛马。好,别人要打你的左颊,你把右颊也拿给他打;别人要剥你的外衣,你把衬衫也脱给他;资本家要叫你每天做十二点钟的工,你率性给他做二十四点,你这样就可以进天国,你的财产是积蓄在天国里面的。”作家在此指出了基督教的维护富人的利益、损害穷人的利益的真相,“损不足以奉有余”。郭沫若对基督教的批判在此也可见一斑。
郭沫若虽然能站在怀疑批判的立场上对待基督教,但他并未将基督教文化完全否定和抛弃,他曾多次推崇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1924年他在《孤鸿》一文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由看了《往何处去》的电影中的情节而生感慨。“感动我的不是奈罗的骄奢,不是罗马城的焚烧,不是培茁龙纽斯的享乐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罗马城,在路上遇着耶酥幻影的时候,那幻影对他说的一句话。……他在路上遇见了耶酥的影子向他走来,他跪在地下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酥答应他说: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郭沫若说:“……这句话真是把我灵魂的最深处都摇动了呀!……我那时恨不得回到你住的那Golgatha山,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感染了郭沫若。因而他在1925年写的《〈文艺论集〉序》中说:“……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这种为了大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显然带着基督钉十字架的牺牲色彩,此中或许也可窥见郭沫若对基督教义的接受。1944年郭沫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一文中指出:“希腊的叙事诗和剧诗,希伯莱的《旧约》,印度的史诗和寓言,中国的《国风》和《楚辞》,永远会是世界文学的宝库,原因大概是那些作品最贴切到了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肯定了基督教文化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主要部分的伟大价值和意义。
二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作家创作的影响表现在诸多的方面,有的作家从《圣经》中寻找创作素材,有的作家借鉴《圣经》故事的结构方式,有的借用《圣经》中的意象,基督教文化渗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之中。郭沫若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其创作中他常常采用基督教的意象构思作品,这使他的作品呈现了较浓的基督教色彩。他的《漂流三部曲》中《歧路》、《地狱》、《十字架》的篇名都借用了《圣经》的意象。小说虽然受到但丁的《神曲》描述人生的磨难、痛苦、与幸福三阶段构思的启迪,但每篇的篇名都充满了基督教的意味。作品以自叙传主人公爱牟的落魄人生和苦痛内心的抒写为主要内容。《圣经·约伯记》第28章23节说:“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按照上帝的指引行走路路畅通,而背离了上帝,则就会步入歧路和迷途。《圣经·何西阿书》第4章12节中基督说:“我的民求问木偶, 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上帝,不守约束。”基督教认为离弃上帝就会陷于罪孽,使人陷入歧路或步入迷途。《歧路》就以《圣经》的意象构思作品。爱牟从日本留学归来,因热心于文学事业而穷困潦倒,“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与他同回中国,以为“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但却事与愿违,在走投无路中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了日本。他“念起昔日清贫的团圆远胜过今日凄切的孤单”,他为自己使妻儿和他背道而驰而深感内疚。他将妻子晓芙赞为圣母玛利亚,而离弃了圣母也就意味着走上了歧路。《炼狱》的题名郭沫若自释为:“外文为purgatory。 基督教的说法:不完全的信徒,在进入天国之前,要先在地狱里锻炼灵魂,洗涤生前罪愆。这地狱就叫做‘炼狱’。但丁的《神曲》,诗人魂游三界,其第二界即为‘炼狱’。这篇的用意略取于此。”基督教将炼狱视为一些不完全的信徒死后灵魂寄寓的场所,它被看作是一个受苦和导向天堂的净化之地,灵魂在此为过去的罪行而受苦。郭沫若的《炼狱》描写爱牟离别妻儿后孤寂苦痛的生活和内心。在孤寂中的爱牟自暴自弃,“时而赌气喝酒,时而拼命吸烟”,“沉没在悲哀的绝底了”。朋友邀他去游无锡并未拂去其内心的烦忧,他把自己看作“是在茧中牢束着的蚕蛹”,他自视为“被幸福遗弃了的囚人”,“他不愿意再和幸福相邻,他只愿在炼狱中多增加些苦痛。苦痛是良心的调剂,苦痛是爱情的代价,苦痛是他现在所应享的幸福了”。他不愿再与朋友一起游苏州,独自回到上海,“又在他的斗室之中,过着炼狱的生活了”。作品以基督教的炼狱意象构思全篇,突出主人公“我的妻儿们都是被我牺牲了”的负罪之感,和为过去的罪行而甘愿忍受炼狱的磨难与苦痛的心理。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其中充满了牺牲和救赎意味。《马太福音》第10章38、39节中基督告诫人们:“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受尽了苦痛,然而为了拯救民众他甘愿作出牺牲。郭沫若的《十字架》借用了基督教的意象构思作用,描写爱牟收到妻子晓芙哀婉悲凉的来信,为晓芙“做母亲的心,做妻的心”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打动,他决意放弃故乡C城红十字会聘他当医生的优厚待遇, 奔赴日本与妻子一起担负起生活沉重的十字架,“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酥钉死在Golgotha山上的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复活在上海市了”。郭沫若以《圣经》中耶酥同钉十字架的强盗的典故,喻爱牟摆脱了炼狱的磨难和罪孽,又复活在人世间了。《罗马书》第6章6—8节中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的构思显然受到了基督教意象的启迪和影响。
郭沫若的《圣者》开篇引用了《马太福音》第18章4 节:“凡是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作品以孩子是圣者的意象构思全篇。小说描写爱牟买了花炮回家,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放起了花炮,“纵有天国,恐怕孩子们也不愿意进去的呢”。但后来在房中燃放的一只不响的花炮,射中熟睡在床上孩子的右眼上,孩子哭过之后又睡着了。爱牟抱着孩子充满了怨艾与哀怜,呆立后的晓芙“竟把她许久不曾过目的《圣经》寻出,坐在炉旁的一只藤椅上翻阅了起来”。爱牟回顾自己的漂泊人生,为孩子们跟随他的漂泊生涯而受苦受难深感内疚,“忏悔着现在,又追怀着过往,他在床上看看要睡去了,孩子一动又惊醒了转来,足足一夜不曾入睡。房中的静穆,也伴着他的女人读了一夜的《圣经》”。翌日受伤的孩子又欢蹦乱跳地游戏了,“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像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作品以一件小小的家庭事故,揭示主人公落魄的生活,突出了孩子的可爱与天真。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的第一章以《末日》为题,显然也取之于基督教的用语。基督教的末日与最后的审判、复活等相关联,《约翰福音》第6章39 、40节中耶酥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酥指出上帝差遣他,使一切信仰基督的人在末日都复活。郭沫若借用基督教“末日”的意象构思作品,描写爱牟全家要离开箱崎赴熊川温泉前, 准备将带不走的书桌、保姆车等卖给旧货商,旧货商的故意压价,爱牟便把东西送给运送货物的朴实老人。郭沫若将主人公在箱崎的最后一天称作末日,这也蕴涵着主人公摆脱苦难生活追求幸福人生的意蕴。
忏悔是基督教中的一种圣礼,在仪式中忏悔的罪人独自向神父坦白他们的罪恶,并因其内疚悔罪而得到赦免和宽恕。郭沫若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其创作中常常以忏悔的叙事形式坦露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突出人物在落魄处境中的愧疚负罪心态,小说《落叶》描述一幕爱情悲剧故事。中国留学生洪师武全力照料患肺结核的同学,受了肺结核的传染。他是一个旧式婚姻制度的牺牲者,却在医院与日本看护小姐基督徒菊子相识而相恋。菊子的父亲是东北牧师会会长,执意反对他们的恋爱。洪师武怀疑自己已身染性病,因此而觉得不能再受人纯洁的爱情,故拒绝了菊子姑娘,菊子为摆脱失恋的痛苦,只身离去奔赴南洋隐姓埋名,成了一片“委身于逝水的落叶”。洪师武“他只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只想一心一意预备着消灭罪愆,完全泯灭了自己的要求”。学医后他知晓自己所患并非性病,深感后悔,他终于皈依了基督,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作品主要由菊子的41封充满着忏悔色彩的信组成,情真意挚地坦露了纯情热烈的菊子姑娘哀婉孤寂愧疚哀怨的内心。菊子的信中充满着忏悔心态,如在第3信中写道:“……我们是做了多么可怕的罪孽哟! 你请恕我罪。快乐了的生活也只剩得可怕的罪恶的遗踪。我当怎样地向你谢罪,怎样地向你谢罪呢!啊啊,我眷恋着的哥哥!我自己真正是恶魔!真正可怕的恶魔!我把你引到可怕的地狱里了,我这可怕的女人呀!”一言一语都透出浓浓的忏悔意味。在第36信中,菊子劝告洪师武忏悔:“哥哥,你成了耶酥教信徒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哥哥你要成为信徒,便不得不从一切的罪恶离开。过去的事情你要毫无遮饰地忏悔才行。一遮饰便有贰心,这是最不好的呢!”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菊子的信中,处处透出浓郁的忏悔色彩。《湖心亭》描写“我”的亲戚逃难到上海寄寓在“我”家,妻子对此十分不满,怕卧病亲戚的病传染给孩子,要求丈夫替他们另找住处,引起夫妻之间的口角,丈夫一再愤愤地斥责妻子:“亏了你也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不害羞哟!”丈夫步出家门,在上海街头漫步,在城隍庙见人们随地大小便和小便坑的尿流入湖中,“我”愤愤的说:“——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为污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充满了主人公对民族的深深的忏悔意识。在乱杂的街市中走着的“我”又为与妻子的口角而忏悔:“她的一生为我和儿子们牺牲的够了,我究竟有什么权利能够要求她为百不相干的人再来牺牲呢?啊,你这个无情的伪善者!你不过怕伤你慈惠的假面子罢了!你不过放不下架子去替别人当差罢了!……”作品以主人公的所见所思为主要内容,突出了人物对民族对自我的深深的忏悔。《地下的笑声》描写了一个悲剧故事。弋阳和秀同在东京留学,学习音乐,他们相恋相爱,一同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被捕,后被“敕令出境”。回国后他们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投身抗日。在1939年的重庆大轰炸中,弋阳的左腿被炸断了,女儿也失散了。卧病在床的弋阳因感冒转为肺炎,须打盘尼西林针才有救,妻子秀为了爱而去向觊觎她的银行秘书借款购药,却付出了她的贞操。丈夫获救了,妻子却染上了性病,又传给了丈夫,端丽的秀因病而变得奇丑无比,病卧的弋阳因病而双目失明。虽然朋友鲁静芷大夫愿免费为他们治疗,但弋阳却离开了人世。作品以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抒写构成主要内容,在他们的心灵的坦露中,在执著的爱的表述中,都透露出深深的忏悔心理。弋阳说:“我是太自私了。我就靠了吸你的血,卑鄙地但又骄傲地,一直活到了今天。”秀对鲁大夫说:“你不要误会,不是我的先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是我做了对不起我的先生的事。”在他们深深的忏悔中却透露出执著的斗争精神、热烈的爱国激情。在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漂流三部曲》、《圣者》、《行路难》等作品中也都充满着浓浓的忏悔色彩。郭沫若作品中人物的忏悔,并不像基督教教徒通过忏悔而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拯救,而只不过在忏悔中表现出对自身过失的自谴自责,以希冀他人的谅解和宽容。这种忏悔的叙事方式虽然也受到了卢梭的《忏悔录》的影响,但更多地来自于其受基督教文化的濡染。
三
郭沫若由于曾将《新旧约全书》当日课诵读,因此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在其创作中,不仅常用基督教的意象构思作品,以忏悔的方式叙写内心,而且常常顺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引用《圣经》的典故,使其作品常常洋溢着基督教文化的色彩。《歧路》中描写归国后的爱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马太福音》第13章3~8节耶酥告诫人们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耶酥以撒种的比喻告诫人们“闻道者众,得道者寡”、“人生有命,前程各异”的道理。郭沫若借用了撒种的典故,突出了当时中国的黑暗腐败和留学生归国后的无奈与落魄。《喀尔美萝姑娘》描写留日学生与日本街上卖糖食的喀尔美萝的姑娘的婚外恋,在突出人物的幻美的爱的追求中揭示了留学生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小说叙写主人公对卖糖女的爱恋:“我现在另外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朋友,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酥,我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总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拿撒勒是耶酥的家乡,他在那儿长大。郭沫若以基督教的耶酥和佛教的王子,说明主人公对卖糖女的仰慕和爱恋。在描写主人公深夜独自去卖糖女白天卖糖的N公园时,作者写道:“我并不期望着要会见耶酥。”耶路撒冷是耶酥常常去过节、传道、行医的地方,耶酥的被捕、钉死、复活也都在此。郭沫若借用信徒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突出主人公对卖糖女的深深的爱慕。在描写主人公在S夫人家喝醉酒后,作家写道:“醒来便太苦了, 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作者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典故形容主人公寻觅去咖啡店作侍女的卖糖女无着落后的苦痛心态。《人力以上》描写日本友人S君的落魄和病逝。描写S君的几个女儿“她们并且从小以来便染上了一种偷窃的恶癖,村上的人背地里都在说闲话,连我的女人也不肯叫她们到家里来玩了。啊,她们这些代人受罪的羔羊!”《圣经·利末记》16章叙说大祭司亚伦将一头作为以色列民族的替罪羊而放入旷野,让它带走民族的一切罪过。“替罪羊”成为替人受过的代名词。小说以这个典故表示她们的无罪,是“社会的罪恶把可怜的幼女逼成偷儿罢了”,突出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落叶》中运用了不少基督教的典故,在基督徒菊子哀婉的书信中以基督教典故表述人物的心理。在第34封信中,菊子写道:“我们真的是回去的时候,上帝要迎接我们怕比迎接义人入天国还要怀着更多的喜悦罢。但是,啊,我!我这迷失了的羊儿,我离开了羊牢迷走出来的羔羊,我自己还有走回那可恋的旧巢的时候吗?假使是有,上帝是怎样地喜悦哟!”“天国”是基督教的理想之地,是上帝之国,耶酥传道之始就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作品将主人公的皈依基督以步入天国的典故作喻,写出菊子虔诚的信仰。“迷途的羔羊”是耶酥在《圣经》中多次向人们讲述的事例,以此喻应全力拯救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作者以迷途羊的典故,写出菊子姑娘愧疚的内心和摆脱苦痛的过去的决心。在第41封信中,菊子写道:“但在这样沉黑无边的旷野,一个人在这儿摸索,这是多么凄凉,多么危险哟。但是事情已经到了如此,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也甘受着这个苦杯,沉默着领受上帝的恩惠。”在《圣经》中施洗约翰在旷野宣传悔改的福音,疾呼人们改邪归正,但其主张不为人们接受。人们将没有得到反响的声音称作“旷野的呼声”。作家以“沉黑无边的旷野”写出菊子孤寂悲凉的处境。《耶利米哀歌》第4章21节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 哪,只管欢喜欢乐,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至露体。”基督教把“苦杯”比作悲惨的命运、生活的苦酒。小说以“苦杯”比作菊子所面对的不幸的遭遇、苦痛的生活。郭沫若在其诗歌、散文中也常常借用基督教的典故。如诗歌《恢复》中“我现在是已经复活了,复活了/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诗歌《西湖纪游》中郭沫若写道:“火车向着南行/我的心思和他成个十字/我一心念着西蜀的娘/我一心又念着我东国的儿/我才好像个受着磔刑的耶酥哟!”诗歌《“双十”解》写道:“一对十字架/表示着双料的耶酥/请来两国强盗/请来法利赛人/让人民加倍受苦/埋下头再搅它三十五年吧/中国必得解放/总有前途。”散文《掌握着旋乾转坤的权柄》中针砭权势者中“竟有出卖劳动人民的无耻犹大”。郭沫若作品中《圣经》典故的运用,丰富了其作品的表达手法,并使其创作时常透出基督教文化的色彩。
郭沫若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没有许地山那样的深入与深刻,也缺乏冰心那般的充满博爱的温馨,郭沫若是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来接受的,由于他深受泛神论的熏陶,他对基督教显然并未有虔诚信仰的意味,他只不过把它当作一种丰富其创作手法和表达方式的手段,虽然他也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某些精神内涵,但与许地山、冰心相比,郭沫若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仅处在较浅的层面上。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其小说创作中借用基督教的意象构思作品,以忏悔的手法抒写内心,用《圣经》的典故表达情感,都使其作品充满了主观的抒情色彩,洋溢着哀婉蕴藉的诗意,透露出悲凉凄婉的悲剧风格,这些不能不说是由于基督教文化影响之故。
注释:
〔1〕郭沫若《泰戈尔来华之我见》。
〔2〕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第4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3〕转引自Robinson 《Doble—edged sword》第26页,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Shatin,第26页,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Shatin,Hong Kong,1986。
〔4〕郭沫若《序我的诗》。
〔5〕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小说月报》第13 卷第2期。
〔6〕郭沫若《泰戈尔来华之我见》。
〔7〕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
〔8〕苏雪林《梅脱灵克的〈青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出版。
〔10〕布克哈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11〕《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7页。
〔12〕《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第4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13〕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第4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标签:郭沫若论文; 基督教文化论文; 基督教论文; 新旧约全书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神曲论文; 马太福音论文; 菊子论文; 歧路论文; 圣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