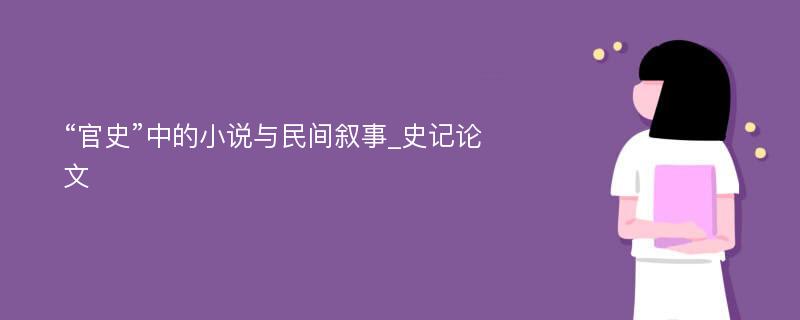
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史论文,说与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史与小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此已是学界共识。本人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探讨小说的起源,也曾论述到小说文体被孕育于子、史书中,经长期发展而获得独立的过程①。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可以表述为:历史书中其实包含着若干小说因子;再进一步,甚至不妨说有些史书与小说(萌芽态的、初期的小说)实在难分彼此。中国历代史书,种类繁多,除纪传体的正史外,尚有编年体者,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之类,更有数量不可胜纪的野史笔记、杂史杂传,其中都包含着成色不等的小说。尤其是后者,有些就简直被认为不能算史而是小说。如晋人王嘉所著的《拾遗记》,现在流传的虽是经南朝梁人萧绮整理撰录的本子,且所记多怪异之事,但看他的编排,倒完全是按三皇五帝禹汤周秦汉乃至魏蜀吴晋之序,所谓“文起羲、炎以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②,隐然史书的格局。故从《隋书·经籍志》起,至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中兴书目》,都把它收录在史部,或称杂史,或称别史、传记。自然,从唐至宋,批评《拾遗记》“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操觚凿空,恣情迂诞”之声亦不绝于耳,到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乃干脆将其移至子部小说家类中③。像这样作者本意或为撰史,又一度曾被列入史部而终被判为小说者,在古籍中远非《拾遗记》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后按曰:“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这是说,二者的区别主要只在所记事情的重要与否(真实与否并不追究)。事实上,被《四库总目》列为杂史的,如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裴廷裕《东观奏记》等,今人就并不承认其为史,而多视为小说,倒是被《总目》划入小说家类的大量唐宋人笔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因话录》、《涑水纪闻》、《归田录》、《邵氏闻见录》之类,今人却把它们视作“史料”,编为“丛刊”④。由此可见,中国古籍的史部书与小说实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小葱拌豆腐那样一青二白。
野史笔记、杂史杂传虽称史料,实多小说,如今已众所周知。但如果我说:即使所谓正史之中也有不少小说因子,或简直就是小说,恐怕就要引起争议了。是正史啊,里边怎么会包含有小说呢,难道史著和小说可以如此混淆吗!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本文除用小说这个词语外,还要引进“民间叙事”的概念⑤。
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是老百姓的里巷琐谈。里巷琐谈包括零星散乱、毫无系统、随生随灭的传言,也包括某些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故事。前者在流播扩散中,大量地消失了,但也有的会聚合成形,变为世代相承的传说。这些在民间永不间断、活力无穷的叙事活动及其产品,就是“民间叙事”的主要内容。当它们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有的进入史书,被认为是史文;也有的却被视为够不上史文的小说——其实,它们的来源都是民间叙事,内容多有交叉,性质本无二致。因此,我认为正史里有小说,确切些说,指的是包含其中的民间叙事。它们多数是史官、文人根据民间传闻记录加工,才由口头传说(也可称口碑或口述历史)变成文字记载。中国远古之史,全凭口耳相传。文字产生之初,笔录与口传仍是相辅而行。直到司马迁撰《史记》,大量素材都来自民间采访所得。《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都说到他撰写《史记》的过程,有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之语,可见其网罗面之广。而如《淮阴侯列传》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樊郦滕灌列传》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则可见其访求旧闻口碑的具体情况。司马迁著史,资料来源一是充分利用传世文献,一是亲自走访搜采,后者多传说故事自不用说,即使前者,本身也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虽然他在写作时曾进行严格筛选,把他认为“不雅驯”的东西删汰掉了,但毕竟留下不少民间叙事即小说的成分,《史记》一书浓厚的文学性就与此有关。后世的情况比较复杂,《汉书》以下的正史,编撰者文学才能不等,又多强调史述的地位、特色而有意排除或降低文学性,但仍不可避免地含有数量和成色不等的小说成分。这些书中的小说有些可能是史官从前代文献转录,也有他们根据惯例或想当然所作的编派,但那些在我们看来应属小说的部分,基本上还不是史官的有意创作,而往往是多少有些影子和来历的传闻。
本文所论即以所谓“正史”,即“皇上钦定”“悬诸令典”的“国史”——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为主,偶亦涉及地位近于正史的《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强调的是史稗之别,但就是正史,其所含的小说与民间叙事,至少亦可举出下列几种情况:
一、历史人物的奇异出生或离奇怪异之事被记入史书,小说化的民间叙事
如《史记》,《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代的情况不用说了,涉及传主的出生,往往包含着许多神话和远古传说,那可以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前身。到记述刘邦的《高祖本纪》,在司马迁当时,已属近代之事,照样有这样的小说化情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不但出生如此,长大后,平时也常见龙:“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还有所谓斩白蛇起义的故事,以及他起义后,其妻吕氏常能在云气下寻找到他的故事。总之,种种迹象暗示刘邦与龙的关系,即有帝王之相。这应非司马迁的虚构创作,而是典型的民间叙事,由司马迁搜集记录而己。
其他正史亦多此例。如《隋书·高祖纪》述杨坚的出生:“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这种神奇出生的记载,当然只能是史家对民间传闻(其初源可能就是皇家)的录载,在我们看来岂不正属小说家言?
《宋史·太祖本纪》述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替有金色,三日不变。”
《元史》讲述太祖铁木真十世祖勃端叉儿的出生是其母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白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勃端叉儿也。”至于铁木真本人,出生时其母月伦也有“手握凝血如赤石”的怪异。(卷一《太祖本纪》)
《明史》述朱元璋的出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又述其种种异兆,如他入皇觉寺为僧后,游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元至正十八年冬朱攻克婺州,“先一日,城中人望见城西五色云如车盖,以为异,及是乃知为太祖驻兵地”(卷一《太祖本纪》)。关于明成祖朱棣的出生,也很奇异。
可见直到清代,史官们仍旧相信这一套,或不得不模仿前史关于帝王奇异出生和生平中种种异事的记载,以证明这些传主都是真命天子。这些被写入史书的神奇传说,已经成为一种俗套,成为拙劣的模仿和翻版了。作为小说,纯系毫无创造性的照搬与复制。
但这种思维在中国很发达,不仅帝王,民间的高人名士也可以有种种神奇传说被记入史书。如《晋书》卷五八《周访传》载陶侃葬父于“牛眠地”,主贵极人臣。其本传则载,母丧时有二客来吊,化为二鹤冲天而去之事。前事与道教风水术有关,后者亦显系传说,至今流传在陶侃曾任刺史的交州、安南一带。《晋书》所载诸孝子传,亦多有此类精诚感动天地的传说故事。《宋史》卷三三二《滕元发传》载其“将生之夕,母梦虎行月中,堕其室”。有此灵异,故元发不但早慧,而且后来果成奇才,居官有政绩,治边凛然。凡此种种,均与志怪小说常见情节类似。
史书中甚至写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如《晋书·刘聪载记》述刘聪之子刘约死而复甦,对人说,在地下见到了己死的刘渊,刘渊己做了蒙珠离国的君主,他告诉刘约:三年后刘聪将死,将去担任遮须夷国的国主。这种活见鬼的故事,不完全是小说,而且是神怪小说吗?《隋书·韩擒虎传》也记述韩死后成为地狱的主宰阎罗王。这个故事就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
二 一件事重复地记录在多人身上,民间叙事在流传中有意无意被误植
《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载其知天长县时的断案故事:
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这是利用了对作案人的心理分析而识破其恶人先告状的案例。同样的事竟一模一样地发生在穆衍身上。《宋史》卷三三二《穆衍传》载:
(穆衍)第进士,调华池令。民牛为仇家断舌而不知何人,讼于县,衍命杀之。明日,仇以私杀告,衍曰:“断牛舌者乃汝耶?”讯之具服。
此二事情节完全相同,何以会那么巧发生在同朝的两个人身上呢?更巧的是,也是宋代的蔡襄《尚书都官员外郎致仕叶府君墓志铭》竟也记述了同样的故事:
南安盗截牛舌,其主以闻。府君阳为叱去,阴令屠之。即有告其自杀牛者。府君谓告者曰:“截牛舌盗,汝也。”讯之,伏其罪。⑥
如此说来,是宋代三个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用同一思路、同一方法判过一模一样的案件了。这种可能性显然不大,这里难免有张冠李戴的问题。按惯例,墓志铭当依墓主家属提供的行状或其他资料写成,可信性似应较强。倘若这位叶府君(名宾,字虞卿)的故事为真,那么,另两位名气比他大的清官只怕倒是附会的了。这使我们想到,很可能是史官把这个判案传说想当然或未细考而安在了另两个人头上。民间传说或故事小说就这样赫然进入正史。
民间传说的流传,会出现种种情况。一则传说因其生动而流传很广,竟使其主名渐渐发生模糊,到后来,这故事便被分装到几个人身上,这是一种情况(也有主名并不变,但故事发生地点却变了,成为几个地方都有而原产地难定的传说,如著名的梁山伯祝英台传说,就有原产地之争);另一种情况是,因某个传主名声响亮,遂有大量同类传说矢集其身,这便是民间传说学中所谓的“箭垛现象”,如鲁班是巧匠的箭垛,诸葛亮、包拯分别是智者和清官的箭垛。这在历史著作中亦均有反映。像上面的例子,就反映了这两种情况。很可能事情本来只发生在叶宾身上,因穆衍有名且其名与判疑案有关,故而被误植;而包拯破案名气更大,遂再次被误植。此类破案情节的小说性乃至戏剧性很明显,虽在史书中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细节,看不出有何虚构,仍不如视为素朴的小说为宜。
传说和民间叙事中主名的不稳定性,有很多例子。如唐人笔记《次柳氏旧闻》载:
肃宗为太子时,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同样的故事,据《酉阳杂俎》(续集四)却又发生在德宗、顺宗父子之间。而据刘觫《隋唐嘉话》卷上,这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唐太宗和宇文士及之间:“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土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新唐书·宇文士及传》就据此把它作为为人“机悟”之实例记在了士及名下⑦。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故事无论安装在谁头上,都不能不看到它的小说性质。贾岛、温庭筠和侯泳三人因骄狂和不识人而得罪皇帝(宣宗)和宰相(豆卢琢)的故事,也属同样性质;(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卷八)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严肃的史著,但取材不避小说。《资治通鉴考异》就往往列出其在多种野史小说的不同记述中选择,最后确定某一说入史的理由。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⑧,显然,在司马光看来,史文和小说固属不同文体,但却又是可以互通互渗、相互为用的。
三 历史过程在载录中趋于小说化
记述历史过程,有种种笔法。刘知几《史通》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他非常强调史笔的求实和简约,当然也就不能认同史著中的小说化文字。但诸朝正史作为纪传体的史书,是以人为中心的,其传文以人为中心来记事,便不能不写人的言行,甚至不能不全知式地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更不能不写许多情节、细节和对话,还必须写到人的命运和结局,在某些虽无足够资料却必须写出的地方还不得不采取悬想代拟之笔。而这些,正是小说文体的根本特点。史文这样写,自不免会把历史人物和事件写得富有故事性,有的甚至写出了戏剧性、传奇性。而这在客观上,就使史文向小说靠拢了,两种文体在不少方面显出了相近相似的特征。
司马迁《史记》中此类例子最多。其有关鸿门宴前前后后的描叙,和班固《汉书》对此段叙述的删削修改,很能说明小说笔法和史述的不同。拙著《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第五章第一节曾有较详细分析,此不赘引。从中可看出,小说与史述虽都是叙事的,但二者的不同,是在于后者仅保留史实的结果和框架梗概,如鸿门宴,史实是刘邦与项羽相会,两军对垒,形势紧张,但最后刘邦逃脱了项羽军营。但小说化的写法,就在这框架中补充大量细节、人物心理活动和对话。这些补充使史述变得精彩,但却大都不是史实(真的史实已不可能复原),不大经得起推敲。比如《史记·项羽本纪》细写项羽、刘邦、范增、项庄、项伯、张良、樊哙诸人在鸿门宴上的表现,直写到刘邦“起如厕”趁机逃跑,而留下玉璧玉斗让张良代为辞谢,项羽受璧而范增大怒。对这段情节,就有论者发问:“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⑨看来司马迁的精彩叙述并不能让后人信服。人们不禁要问:司马迁的这些描写从哪里来?回答只能是:既无史料依据,这些描写恐怕是他所搜集的口头传说,加上他的合理想象吧。史述与小说笔法对同一史实的记述,总是框架与结局相同(大的历史格局,如秦亡汉兴、刘胜项败之类,是无法改变的)而具体内容(过程)却可叙述得大不相同。只述梗概和结局的是历史;具体演绎,特别是演绎史述所留下的空白点,而又富于细节,尤其是戏剧性细节的,才是小说。《汉书》对《史记》的修改,主要就是改掉《史记》的小说笔法,降低其小说性,所以在史学界获得严谨之誉。当然《汉书》本身亦未能将小说成分排除净尽,不少段落仍颇具小说性。
关于史书含小说成分,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左传正义》及《史记会注考证》两卷论之甚多。其论《左传》之记言,“以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咳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的提问,指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又扩而广之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⑩。这就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沟通了小说家和史家,也沟通了小说与史述两种文体。
《史记会注考证》卷亦举出许多史述而用小说笔法之例。如苏秦挂六国相印归,其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以谢”而被笑“何前倨而后恭也”。刘邦称帝后,其父“拥篲迎门却行”而被问:“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今某之所业孰与仲多”。南朝宋沈庆之素被乡人所轻,通贵后,见之者皆“膝下而前”,沈乃言:“故是昔时沈公!”三事情节雷同,何以如此?钱钟书先生论曰:“盖事有此势,人有此情,不必凿凿实有其事,一一真有其人。势所应然,则事将无然。”又举蔺相如辅赵王赴渑池之会面折秦王事,谓其“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此乃史述而用推想增饰、虚拟渲染之文学手法也,必信其真实可信,则未免胶柱鼓瑟。至于刘媪交龙、武安谢鬼以及薄姬与高帝床头夜语“梦苍龙据腹”之类,益说明史家所述奇闻,显非史实。此卷更有一节将史著与小说之写法异同进行比论云:“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下乃举出“撰者己所不知,因付阙如”和“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两种情况,而这正给小说家留下施展的天地:“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馀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11)。然而“挥毫洒墨”的不光是小说家,也包括某些史家,于是这些“寻常琐屑”富于小说意味之事,就不免也要羼入史书中去了。
史载中有小说这一现象,发现者尚多,如吴世昌先生,就在论《礼记·檀弓》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时,指出了《檀弓》记事的小说性质(12)。
《资治通鉴》分年纪事,有些比较集中的段落,编者主观上虽无意追求小说化,但因有某些细节描写,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文学效果。如淝水之战一节,就因能在战局大形势下,紧扣中心人物谢安的心理及言行来写,使其颇像场景宏阔、人物鲜明、细节生动的小说,成为其书最具文学性的名篇。
四 小说片段直接入史
流传于民间口头的传说故事,可以被史官采入史书,那么,由文人笔录民间叙事而成的野史笔记,自然也会通过史官之手进入史书,包括钦定的正史。小说片段入史即指此种现象。
《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一向被视为其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大量采用野史小说。《四库总目》批评裴注有“嗜奇爱博”之弊,列举《袁绍传》、《钟繇传》、《蒋济传》诸篇引了《搜神记》、《异林》、《列异传》等小说,指出:“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颖。”其实《三国志》裴注引入小说的情况远非如此,除上述那些,它还引了葛洪《神仙传》以及《蜀本纪》、《越绝书》、《抱朴子》、《交广记》等书中若干荒诞不经的故事(13)。
《晋书》作于唐初,除当时尚存的诸家私史外,《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亦成为它的重要资料来源。当然,从小说到史文,具体表述有所变化。《世说新语》是按人的行为特色分类纪事的,一个人的事迹分在各门之中,并非每条同等重要,纪传体的《晋书》则以人为单位,自需将各人事迹加以选择与合并,叙述文字也尽力向史体的简约质朴靠拢。那些次要人物的传记本来简短,材料来源有的几乎全凭小说,即使像王导、周顗、庾亮、王衍这样的重要人物,采用《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也是触目可见。试以《王导传》为例来看(14),传中所记他被时人称作“管仲(夷吾)”见于卷二言语门(在《世说》是温峤语,《晋书》中改为周顗语,但情节相似);著名的过江诸人新亭聚饮,周顗叹:“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王导正色大言:“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也出自此卷;晋元帝即位,命王导登御床共坐,导坚辞之事,见《世说》卷二二宠礼门;王敦反,导率群从昆弟待罪,帝终不治导罪,此实由周顗他同萧上表力救而导不知,后周遇难,导因前嫌竟坐视,周被害后,导才获见其救己之表,深悔之,说:“吾虽不杀伯仁(周字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这段分见于《王导传》和《周顗传》的故事,就出自《世说》卷三二尤悔门;又王导力劝元帝取消夺嫡之议,使明帝得以继位,事见《世说》卷五方正门;王导养妾于外,其妻妒,将前往查责,导执麈尾驱牛急赶抢先往救,遭同僚讥笑,以及他一面义正辞严地回答挑拨他与庾亮关系的谗言,一面对庾的专权又内心不平,则分见于卷六雅量门和卷二六轻诋门。附在《王导传》后的其子孙各传,同样从《世说新语》中采录不少资料,这里就不再赘论了。
唐人野史笔记发达,两《唐书》编者从中采录甚多,文学性较强的《新唐书》更为突出。如《新唐书·列女传》所记47位妇女事迹,大抵采自笔记小说、私家杂记,只是史家对原材料作了筛选和删节。如房玄龄妻卢氏,史文载录了她当房微贱而病且死之时的忠贞节义,略去了《隋唐嘉话》中所记她的善妒,但也使我们明白她对房的深情确实不同一般,当唐太宗为房纳妾时她的猛烈抗争实在情有可原。李畲母教子廉洁故事,采自《朝野佥载》,基本没有改动。段居贞妻谢小娥传则直接采用李公佐的同名小说,文字则有所压缩。民间叙事就这样经由史官之手进入了史述。
《资治通鉴》有意识地选用小说,且于《考异》中陈说或选或汰的理由,上文已论。此处再举《考异》未及而直用小说之一例。傅奕是唐初贞观年间有名的辟佛人物,颇为司马光所欣赏。《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下,详细摘录了两《唐书》所载傅奕请除佛法的上疏,记述了他同萧瑀在李渊面前的激烈争论。略去他教子习儒及醉卧临终自为墓志“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15)的最后一笔,但却补上正史本传中所无的“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这一补笔显示司马光强调太史令这样执掌天象预报之责的官员应具严守机密的品性,其材料既非来自正史,当从别记小说中来。但司马光似乎觉得对傅奕的描述还不过瘾,于是在《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又补述了以下一大段: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司马光是崇儒反佛的,特意在此加进傅奕辟佛成功的具体事迹,两个故事的来源则是唐人李伉(一作冗)的《独异志》、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和宋初王傥的《唐语林》。两《唐书》对傅奕的描述虽已颇传神,《资治通鉴》直接采录笔记文字,更增添了浓厚的小说化成色。
以上述种种在我们看来,均是史书中的小说成分,举一反三可找到更多例证。从民间叙事经文人小说到史书记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简言之,大致是:口头流传的民间叙事→被文人学子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野史笔记或小说(记录可有多次,可有所加工,成文后重又流传民间,在民间口头再次增删,并再次被记录,如此反复不绝)→史官从民间口头和各种文人笔录中撷取史料编入史书,一部分纪传体的史书被承认为正史。
这个过程也可表述为:从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官方叙事;从民间口头叙事→作家文字的艺术叙事→史官御用钦定的经典叙事。这里的变化过渡,像光谱般的无级演变,中间固应有确定的界限,但却没有绝对分界。同时,始终存在一个逆向的过程,那就是从书面的历史再回到小说和传说,包括从历史文本重返口头演出的说书评话或文字写成的小说乃至重返民间口碑。中国的文史就是如此相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古到今,史述和小说两种文体都有一个萌生成长而至于成熟定型的过程,并且都是不断发展变化、呈开放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种表现为相分相背,一种表现为相混相融。
就史述与民间叙事的关系而言,其变化的显性倾向是日渐疏离:越古远的史著与口头传说关系越密切,因为那时书面文献缺少,不得不依赖民间口述史料。越到后来,史著与口头传说关系越疏远。正统史家既欲自矜崇重自高身价,因其深知史述与小说具有难解之缘,故有意格外强调自己所述是排除里巷传言的,是最真实可信的。后世诸史宁可多引文书档案,而声言与民间传说无干,宁可写得质木板滞而远避叙述的文采和描写的灵动,以致正史和口碑、口述历史日渐被分隔甚至呈对立状态。与此相应,小说文体独立后,小说家主体意识加强,亦有意与史述拉开距离。他们更加追求叙事的琐细化、个人化、主观化、心理化,追求时空的颠倒交叉,笔触探入跳荡无序的意识流,情节变换速率加快甚至出现超现实的飞跃。总之,努力追求史述所不允许的一些技巧和笔法。这可以说是史述文体和小说文体相分相背的趋势。
然而,却同时隐然存在着另一种相反的趋势——两种文体又不可遏止地靠拢和混融着。这趋势之所以能存在,实植根于两种文体都具有包容度极大的特点,从而给了它们的创作者以巨大的自由和广阔的驰骋空间。小说文体的自由在其古典时代已呈显无遗。比如,一篇之内,人称可以几变,叙述主体遂有多个层次。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可以随时交替,笔触可以上天入地古往今来不受时空限制,更可按需要和兴趣随处插入作者自己或别人所作的诗词歌赋种种他样文体的作品,其语言更可有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之别,声口各异,雅俗并用,庄谐杂陈,甚至嬉笑怒骂、戏谑无稽。越到近现代,小说文体的自由度越大,不但其文字百般变幻,就连曲谱和图画都可进入。史述号称比小说严谨,但亦有自由的一面。它虽主要是对史事的客观叙述,但无论独著抑或众撰,其文字同样可体现史家的个人习性和时代风格。史著中也可纳入种种文献文件乃至文学作品,从帝王的诏告敕令到臣下的疏表奏议,甚至辞赋杂著、歌谣民谚神话和各色民间传闻。史官固然主要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尽量客观的口吻进行叙述,但也不妨揣度人物,插入第一人称的心想或口言,甚至不妨悬拟(亦即想象虚构)某些对话和场面,尤其是正史中的人物纪传,文学性更强,从而使史述向小说文体靠拢(16)。当然,也正因自由,才使某些史著刻意与小说文体划界的努力得以实施(效果如何另当别论)。实际上,历史永远无法摆脱民间叙事和小说。今人尤其懂得民间“口述历史”的重要。近来世界上正有一个以口述历史补充纠正书写历史(特别是官方所编颁之史),而向口述历史,特别是社会下层人民生活史回归的潮流。口述历史,无论是采访编录所得,抑或形形色色的私记杂载、回忆录之类,即使主观上力求严谨负责,也总不免带有个人陈述的特点,与纷歧多样、变化不定的民间口头传说,有难分难解的关系。不同的人忆述同一件事,出现矛盾扞格是常见的。但这些个人色彩和往往文学性颇强的史料,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任何官方颁布的历史,都不是充分的历史,必须用民间口述历史来补充和修正,哪怕它难免包含小说的成分。
小说和史述文体的发展变化,就贯穿着这样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二者因各自特征逐渐分明而日益疏离,一方面则是跨越森严的传统鸿沟相互靠拢和融混,也就是既有顺的分流,又有逆的对流和回流,实即处于紊流状态。这才是小说和史述两种均以叙事为根本特征的文体发展演变的真实状况。
研究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文体与史学及历史叙述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叙事思维、叙事能力形成及发展史的理解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人的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的发展过程走过相当漫长的路,这攀登之路上树立着显示高度的若干里程碑。以真实简洁为追求目标的历史记述的成熟是一个重要阶段,《史通》就是这一阶段经验教训的总结。以虚构而能乱真为基本特征的创作小说出现,是又一个重要阶段,唐传奇的出现可谓里程碑式的标志。这以后小说、史述既分途发展又隐性渗融,而达到把小说写得像历史那样丰富宏伟有深度,则是叙事能力登上的又一层阶梯,这时文史更好地融合,自然地浑为一体。中国历代的小说家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好小说能为史留影,又足堪与史比美。《红楼梦》抵得一部康雍乾三朝贵族之家盛衰史,《儒林外史》从标题即可看出以小说为史证的意图。现代小说深受西方文艺影响,表现技巧的新变层出不穷,但在这根本点上并没有变。《祝福》何愧一篇《祥林嫂传》?《四世同堂》岂不堪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苦难史?适当的例子还多,它们均正合为普通人立传著史的新史学原则。把小说写得既是悦目可读的文学作品,又具有深刻厚重的历史价值,已成为真正优秀的小说家矢志追求的崇高目标。一位当代著名小说家公开声言自己的作品是为乡土“树起一块牌子”,因而一反过去擅长而惯用的对“戏剧性情节”的编织,而改用“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即更接近史书的笔法(17)。与此相反而实相应的是,历史类、纪实性或回忆录式的著作出现了通俗化、文学化乃至小说化趋势,力求把沉重的史述写得可读性更强,更富人情味,更有吸引力,以至于某些介于文史之间的作品,使评论者产生“历史比小说更好看”的感想(18)。其实,这种感觉的普泛性,从所谓纪实类图书的畅销上,就可看得很清楚。这可以说是上述文史两种叙事文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势在现当代的生动体现,也说明这两种文体之间的深刻联系和不解之缘,是贯穿古今的。
自古以来,史家利用小说以撰史,已形成惯例和传统,可是小说研究者对我国丰富渊深的历史宝库又利用得如何呢?往往因碍于习惯的文史之分而利用得很不够。中国古代史著量多质高,其中有小说研究取用不竭的资料,忽略它实在可惜。尤其是研究小说文体的起源和叙事特征,研究中国人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的形成发展这些问题,更需充分借重历史库藏。今天我们仍需打破对正统史书神圣性和神秘性的误信,尤需打破传统文史划分的人为界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史学家,在中国正统史书,甚至经书中,看出了许多“伪史”,指出它们大多属于古代神话传说。他们的工作,也可表述为:从古史中分辨出包蕴于其中的神话传说。他们的学术结论近年来受到很大冲击,甚至针锋相对地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但顾颉刚们有两点功绩不可抹杀,一是打破了对神圣经典的迷信,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一次解放;二是找到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渊薮,为中国的神话学、传说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开辟了园地。今天,我们从古史中发现、发掘小说史料,则是对传统人为的文史之分再作一次消解,是从另一角度对历代史著迷信的否定,也可以说是对古代文史的打通。而深入剖析小说和历史的不解之缘,既使表象模糊的事物呈露其性质复杂的本相,又有助于找到它们真正的界限,这对当下的文史沟通和分工,当亦不无好处。对于以往的历史记述,我们将会通达地不再斤斤于某些细节的真伪,而对于小说(乃至全部文学)的价值,我们却有了一个比较高明而可靠的衡估标准。
注释:
①请参《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五章第一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拾遗记》萧绮序,见齐治平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③见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十通”本或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④中华书局有“笔记史料丛刊”,分唐宋、元明和清数辑,其中不乏历来被视为小说(所谓笔记小说)之书。
⑤详参董乃斌、程蔷合著《民间叙事论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4、第5期连载。
⑥《蔡襄全集》卷34,陈庆元等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新唐书》卷100,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⑧司马光《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
⑨《史记会注考证》引董份语,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一册275-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⑩《管锥编》第一册,164-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1)《管锥编》第一册,303-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2)吴世昌《吴世昌全集》第二卷《文史杂著》1-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请参徐宗文《小议〈三国志〉裴注的真实性》,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10版。
(14)《王导传》,见《晋书》卷6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15)见《旧唐书》卷79,《新唐书》卷107。
(16)当然,史与文的界限并不泯灭,也不应混淆,即使文学性最强的《史记》,就全书而言,其性质仍应是史,因为它除列传、世家外,尚有大事记式的本纪,有纯属史体的八书、十表,就其全书来看,无疑应属史部。如果它真的只有列传一体,而绝无其他,性质属文属史,恐怕就更难说了。
(17)贾平凹《秦腔》,连载于《收获》2005年第一、第二期,引文见作者《后记》。
(18)请参《文艺报》2005年8月16日第3版,林一平对张宏杰《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小说家莫言作序)一书的评论文章《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标签:史记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读书论文; 晋书论文; 世说新语论文; 拾遗记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隋唐嘉话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西汉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