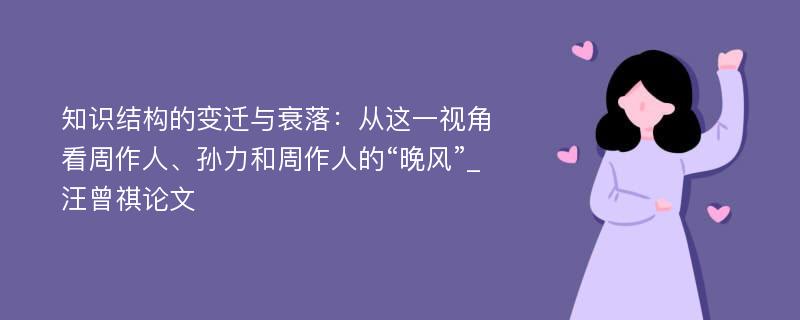
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孙犁、汪曾祺的“晚期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衰年论文,晚期论文,角度看论文,知识结构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坚持写作的人,因身体进入晚年,由健康而至衰退;或因各种遭遇,思想上发生剧烈的震荡,以至长期维持的文字和写作风格,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变化之后的作品里,人们有时会“遇到固有的年纪与智慧观念,这些作品反映一种特殊的成熟、一种新的和解与静穆精神,其表现方式每每使凡常的现实出现某种奇迹似的变容(transfiguration)”①,正是中国传统赞誉的“人书俱老”。另有一种变化之后的作品,却“并不圆谐,而是充满沟纹,甚至满目疮痍,它们缺乏甘芳,令那些只知选样尝味之辈涩口、扎嘴而走”②,过去中国文人称之为“苦词未圆熟”。 作家们的晚年之作,爱德华·萨义德称之为“晚期风格”(late style)。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少见到作家晚年的成熟和解之作,更多的是如深秋果实经虫噬咬之后的涩口、扎嘴。涩口、扎嘴之作能被称为“晚期风格”,而不是心智灭裂后维持的死而不僵,照萨义德的说法,作品就不但要证明其作者在思想或文字上与其此前有异,还要“生出一种新的语法”③。这种晚年生成的新语法,会“撕碎这位艺术家的生涯和技艺,重新追寻意义、成功、进步等问题:这是艺术家晚期照例应该已经超越的问题”④。中国传统通常称这晚年的改变为“衰年变法”,而细按其故,变法本身往往伴随着一个作家的知识结构变更。下面即将讨论的三位作家,都在衰年变法时伴随着知识结构变更——或者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 在谈周作人之前,似乎有个可能的误解需要澄清,即“晚期风格”,非即指“此风格出现于漫长人生或艺术生涯晚期、迟暮、末年之谓”,只要作品与其之前的作品“构成一种本质有异的风格”,就可以命名为“晚期风格”,因为生涯中期就会有“晚期风格的影子或种子”⑤。甚者如周作人,其生涯中后期的变化,与其生涯晚期一以贯之,因而其生涯中后期的作品,不妨就径称为他的“晚期风格”。 1932年2月25日,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这次连续八次的系列演讲,为后来的历史学家邓广铭(恭三)记录,周作人亲自校订后,命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交北京人文书店出版。这本小书为周作人的前期文章做了个自我总结,“把文学史分为‘载道’和‘言志’两派的互为起伏,所谓‘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他主“言志”而绌“载道”⑥。在文章事业的前期,周作人着意经营“自己的园地”,希望自适其志而排斥道德说教,如他自己所说,“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⑦。此后一段时间,周作人也常在书的前言后记中表达对自己“载道”之文的不满,“照例说许多道德家的话,这在民国十四年《雨天的书》序里已经说明,不算新了”⑧;“《苦口甘口》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话,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⑨。 1945年,周作人六十岁,在所写《立春以前》的《后记》中,周作人一改过往加于道德文章的反感,对“载道”文章的肯定,变得相当坚决:“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以前杂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还当尽年寿向这方面努力。”⑩而在《过去的工作》中,他甚至因这一改变,更改了对过去的认知:“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什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11) 周作人的此一转向,不妨看成他“晚期风格”的成形。此一转向固然与他事敌引起文化界的强烈反应相关,却也与他的内在思想息息相应。如王汎森所言,此一时期“周作人则专心致志于提倡一种新道德哲学”,虽然“大量写这类文字是在敌伪下做事时。这些文字可能一方面呼吁时人体恤沦陷区人民的现实感受,不要以道德高调的‘理’来评判他们;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希望人们考虑现实景况而予以谅解。心情及用意很复杂。不过,这些言论亦与其前后思想相当一致”(12)。周作人的道德意识以及他“前后相当一致”的思想,就是他自己梳理出来的所谓“非正统的儒家”。 “非正统的儒家”想法之形成,可从周作人推崇“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开始:“鄙人……于汉以来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13)“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14)随着认识的深入,这一思路延伸到更远的时代,周作人慢慢确立了“非正统的儒家”的说法,思维更形缜密:“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子,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么消极的。”(15)“单说儒家,难免混淆不清,所以这里须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16)至此,周作人所谓的“非正统的儒家”一系,基本梳理清楚——由上古的大禹和稷肇端,中经孔子、颜回和孟子发扬,由墨子承其余绪,落实到汉之王充,延之明之李贽,清之俞正燮。在周作人看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思想有益,却两三千年隐而不彰的传统。 这个传统,核心是“适当的做人”(17),避免过与不及。其阐发,即周作人反复致意的“两个梦想”:“在不久前曾写小文,说起现代中国心理建设很是切要,这有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18)“伦理之自然化”,就是承认道德伦理使人从生物中脱离出来,但同时强调,这种道德伦理的崇高,不可走得太远,否则容易成为不自然的伦理观。“道义之事功化”,即反对空头道德,提倡力行,所谓“道义必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19)。 循此以观周作人中后期至晚年的作品,包括翻译在内,草蛇灰线,固有踪迹可寻。简而言之,即凡事强调“重情理、有常识”的一面,而不取高远凌空一端。此一原则,周作人奉行至卒。在遗嘱定稿中,周作人特别强调了对所译《路基阿诺斯对话集》的重视,“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20)。持此对照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对路基阿诺斯评价,其重视之原因,可得而明:“Lukianos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21)在周作人看来,路基阿诺斯“疾虚妄,爱真实”的一面,及其对世间的明哲态度,正与其对“非正统的儒家”之提倡相近。 至此,或可讨论周作人的知识结构变更。他“晚期风格”之前的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倾向上,多致力于文学方面,正是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集”部。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这些作品“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过,即这使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的:它能使作者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读者虽得不到什么教训,却也不是没有益处”(22)。事敌之后,他的“文学小店”早已关门,自己也“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梳理出他自己称谓的“非正统的儒家”,且文章如“经传所广说”,欲有益于世道人心。此类文字,按之传统分类,可以划归“子”部——“诸子者,先王经世之意也”(23)。至此,周作人的知识结构,已由集部而转入子部,其所著述,也由文学作品而转为拟“子”,气象已然变换,非所谓文学家所能框囿。 让人稍觉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晚年周作人未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更新其知识结构,最终只能株守上一个时期的思想成果。更因其竭力反对的虚妄,在他活着的时候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他也未得子部《老子》“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之旨,不能顺天应人,以当世之道对待当世之问题,以致只好不断感叹着“寿则多辱”,郁郁赉恨而终。 相对于周作人,孙犁晚期文章风格变化之剧,让人咋舌。除去孙犁自己所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24)的“荒废期”(1957-1976),他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别,即由此前“荷花淀”“芦苇荡”《风云初记》的清新明媚一转而为“耕堂劫余十种”的枯槁疏简,更兼后期作品蕴含的沧桑之感,几让人有两世文章之叹。孙犁的这种晚年之变,大概更合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风格:“这经验涉及一种不和谐的、非静穆的(nonserene)紧张,最重要的是,涉及一种刻意不具建设性的,逆行的创造。”(25)除了当时每个人都经历的艰难时世,还有什么左右着孙犁的写作风格吗? 孙犁喜欢书,爱护书,是出名的,如他《书箴》所言:“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26)此爱好,孙犁贯彻终生。从孙犁的各类回忆来看,对他壮年期的写作起支配作用的书籍资源,主要是文学作品,古典类如《西厢记》《牡丹亭》《封神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等;现代作品则是各类译作,如鲁迅和周作人的翻译、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还包含当时流行的各类唯物史观艺术论著;新文学作品则如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废名、老舍、丁玲等人的著作;新报刊则有《大公报》《申报》《小说月报》《现代》《北斗》《东方杂志》《读书杂志》等。这一阅读序列,与新文学运动之后走上文学道路的人,并无显著的不同。 因为对书的热爱,“文革”结束之后,当大部分作家或陷入怨气冲天的回忆,或彷徨无所事的时候,孙犁却开始了一段让人心动的读书生活。孙犁晚期较早的一批文字,写在他包书的封皮上,以《书衣文录》志之。这些书,除去不多的文学作品,大宗是四部分类中的史部。文学是孙犁的“本行”,但晚年孙犁的读书爱好,发生显著的变化,如他自己所言,“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27)。“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28)因爱好的变化,孙犁写下很多读史笔记。其中,前四史孙犁均有涉猎,此外尚写有读《魏书》《北齐书》《宋书》《旧唐书》等的文字。另如关于《哭庙纪略》《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清代文字狱档》等的文章,也是关于历史著述的笔记。 孙犁读历史书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他能把自己身经复杂时代领受的特殊体验,融入对历史的阅读中。如读《史记·叔孙通列传》,孙犁写道:“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29)读《旧唐书·魏徵传》,孙犁如此评论魏徵的直谏:“魏徵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徵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徵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30)类似的评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乱”辞,即文章结尾的“耕堂曰”。如读《后汉书·马援传》末尾,“耕堂曰”:“马援口辩,有纵横家之才,齐家修身,仍为儒家之道。好大喜功,实为佼佼者。然仍不免晚年悲剧……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中。即远据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矣。”(31)孙犁读史书的笔记,此类言论甚多,从不游谈无根,而是观古知今,言辞中有对历史和时代的切肤之感。 甚而言之,孙犁读文学作品及与文学写作者有关的文字,也用了读史的方法。如读《刘半农研究》中,“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32)又如读《东坡先生年谱》,至苏轼被文字之祸,遭妇女恚骂,孙犁感叹曰:“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诸如此类的言论,足见孙犁观世之深,反身之切,判断问题之直截,已部分达到了“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的程度。 更有甚者,连孙犁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虽多涉人情,却也大多寥寥几笔,运笔更倾向史传,而非文学。即如几乎每篇小说末尾所缀“芸斋主人曰”,较之《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的就事论事,孙犁的感慨往往有纵论古今之概,让人大起苍茫之感。如《葛覃》结尾:“人生于必然王国之中,身不由己,乃托之于命运,成为千古难解之题目。圣人豪杰或能掌握他人之命运,有时却不能掌握自己之命运。至于凡俗,更无论矣。随波逐流,兢兢以求其不沉落没灭。古有隐逸一途,盖更不足信矣。樵则依附山林,牧则依附水草,渔则依附江湖,禅则依附寺庙。人不能脱离自然,亦即不能脱离必然。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创造不息,恪尽职责,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葛覃所行,近斯旨矣。”(33)此类议论,不似小说的曲终奏雅,更像是模拟史传的“赞”辞。 对“芸斋小说”,孙犁有自己的持平之论:“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34)而对其晚年文字风格,孙犁《谈简要》中的话,可为夫子自道:“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35)而这篇谈论简要的文章,发轫点是刘知几的《史通》:“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36)或许可以说,晚年孙犁,在文字上也开始追慕史书境界,讲究语言的质实有力,而不再斤斤于优美动人。这大概就是孙犁晚年作品,让部分人觉得干枯乏味的原因。 按四部的划分,孙犁晚年读书,用力在史、集两部,尤其倾心史传,而对经部和子部,则较少措意。关于经,孙犁说:“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又说:“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37)关于子书,孙犁说:“读子书的要点:一是文字;二是道理。”他对子书中的“玄虚深奥之作,常常不得要领”,而对子部中的“《老子》一书,我虽知喜爱,但总是读不好”;“《庄子》一书,因中学老师,曾有讲授,稍能通解”(38),但“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39)。对列于子部的释家书,孙犁则说:“对于佛经,我总是领略不到它的妙处,读不进去。”(40)从上所言,大略可以知道,孙犁为什么读的多为史、集之书了。 在这些晚期文字里,孙犁并没有虚设高标,让自己凌空蹈虚,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下自己的认识。这是孙犁诚恳面对自己的努力,因而也就保留着身上的累累伤痕,“并没有把它们做成和谐的综合。身为离析的力量,他在时间里将它们撕裂,或许是以便将它们存诸永恒”(41)。在阿多诺的语境里,这种撕裂的碎片是对全体性的否定,加深了晚期风格的深度。而在中国语境里,这种撕裂性表现,或许更是一个人向上之路的试探,达至更高的程度,撕裂的东西或许可以重新变得连续。比如,从孙犁的读书范围来看,史、集真的跟经、子有那么遥远的距离吗? 读史,孙犁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列传上,其力未达世家,更没有一窥本纪之究竟,且往往因社会动荡和自身经历,对历史只做冷峻想,其中的悲愤之情,也往往稍过。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天假以年,孙犁由史部的列传而至世家,而至本纪,而至书、表,更进而读《春秋》,则可由史至经,见到“天地不仁”生机勃勃的一面,更进一步认识自身在历史及当下的位置,从而在纷纭的史实中找到虎虎生气。而由读集部的“知人”,孙犁也可进而认识文学的整体,体会如《诗经》中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人物间种种不同的情感状态,从而丰富自身的认知范围,由丰富而达致单纯,不致枯槁。 其实,孙犁这样延伸的契机已经有了,“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42)。虽然话里仍有对经书的偏见,但倘若不是年老精衰、边读边忘,而是由读而爱,那么,孙犁是不是会有机会找到经、子中并非空洞而是向上的力量,达至丰富的单纯呢?孙犁是否也可以摆脱晚年予人的枯索寡恩之感,再现生命的勃勃生机呢? 1984年,孙犁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说自己的作品是纪事,不是小说,而汪曾祺的,却“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43)。为什么汪曾祺的小说是小说,而孙犁自己的,却是纪事呢?我以为其中的秘密,在汪曾祺小说的抒情性。这一抒情性界定,不包括他产量不高的1940年代和形势特殊的1960年代作品,而是指汪曾祺复出之后,1980年代末之前的小说。不管是《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还是《七里茶坊》《徙》《鉴赏家》,即便其中有疼痛,也表现为淡淡的哀愁,总体上仍满含对人世的爱意,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小说有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44)。因此之故,汪曾祺爱称自己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45)。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之关键,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其来源,汪曾祺自己归为儒家讲人情的一路。汪曾祺觉得,《论语》里的孔子是一个活人,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他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认为是很美的生活态度。他也爱读宋儒的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认为是蔼然仁者之言,对苦人充满温爱和同情。而其小说中淡淡的哀愁,汪曾祺也自报过家门:“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结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46)或许是因为1980年代早中期的作品多是温煦的旧梦,汪曾祺小说中对人世的温情和隐约的哀愁达至了和谐。这一时期作品中流露出的,是“一种更新的、几乎青春的元气,成为艺术创意和艺术力量达于极致的见证”。如果没有此后的衰年变法,汪曾祺的这一批作品,凝聚了他此前对中西文学、民间文学、戏剧、甚至书画的理解,而能以饱满的笔意出之,可以称得上是他“毕生艺术努力的冠冕”(47)。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汪曾祺陆续创作了《八月骄阳》《安乐居》《毋忘我》《小芳》《薛大娘》《窥浴》《小孃孃》等。此前小说艺术已臻完满的汪曾祺,忽然风格一变,文字由优美转为平实,即他自己所谓的:“我六十岁写的小说抒情味较浓,写得比较美,七十岁后就越写越平实了。”(48)有论者将他的这一变化称为“反抒情”,认为在这些作品里,汪曾祺不再着意铺排风景来烘托人的真善美,不再抓住细节来探测人性的深度和弹性,不再编织陡转、巧合来凸显世界的善意和生命的温暖,而是更多用力于矛盾、空隙、皱褶、破碎之处(49)。对这一变化,汪曾祺自己也很担心:“这种变化,不知道读者是怎么看的。”(50)此种心情,或许正是他在诗中所写,“衰年变法谈何易”(51)。 读者呢,几乎照例忽视了他此一时期的作品,关于汪曾祺的谈论,几乎牢牢锁定在他的抒情时期。后一时期的作品如《小芳》,连他女儿看了,都说不喜欢,“一点才华没有!这不像是你写的!”(52)在如此情势下,汪曾祺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肯定内在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在我看来,他对纪晓岚和毕加索的认识变化,尤其富有意味。 汪曾祺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分别为两类,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在他看来,唐传奇“情节曲折”“文辞美丽”,是“有意为文”;而宋人笔记则“无意为文”,故“清淡自然”,“自有情致”(53)。汪曾祺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传奇,可有意思的是,对继承笔记传统的《阅微草堂笔记》,汪曾祺却常致不满,并举纪晓岚对《聊斋》的批评为据,以证纪之不懂想象:“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54)因此之故,汪曾祺疑心鲁迅对《阅微》“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评语是揄扬过当,因他觉得此书“实在没有多大看头”(55)。 然而在《全集》失收的《纪姚安的议论》中,汪曾祺却看法大变,认为鲁迅对《阅微》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深刻的,很叫人佩服”。并认为鲁迅对此书叙事所下“雍容”二字,“极有见地”,非他此前认为的“过于平实,直不笼统”。更有甚者,他此前觉得“叫人头疼”的议论,也改换了看法,否则,他也不会在此文标题中冠以“议论”二字(56)。此一转变,大体可见汪曾祺晚期作品中平实风格的由来。此文或许暗示着他从对《聊斋》才子气的欣赏中走了出来,对作品的阅读心态更为开通,也始重平实雍容之风。这样的转变,是对文学概念的进一步扩大,也影响了汪曾祺对非文学类著述的评价,如他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就称其“是一个长篇的抒情散文,既是真实的,又是诗意的”。如此认识,将汪曾祺此前思想中分茅设蕝的想象与事实,渐渐融为一体。 汪曾祺是最早对西方现代小说有所借鉴的作家之一,所谓“我是较早的,也是有意识地动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57)。而1980年代早期的创作,虽然他经常强调,“我的一些颇带土气的作品偶尔也吸取了一点现代手法”(58),却很少在其中看到现代主义的影子了,更多表达的是向中国传统小说回归的愿望:“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民族传统。”(59)“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60)上面所述关于讲人情的儒家,也是这种向传统回归的表现。而至1991年,汪曾祺忽然在给朋友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变法,我是想过的。怎么变……现在想得比较清楚了:我得回过头来,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61)在一本书的重印后记中,他宣言:“我今年七十一岁,也许还能再写作十年。这十年里我将更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62)看了几篇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他也忽然文思大动,“我于是想改写一些中国古代的魔幻小说,注入当代意识,使它成为新的东西”(63)。以上种种表明,现代主义已重入汪曾祺视野。 在重新引入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汪曾祺对毕加索看法的转变。在1986年写的《张大千和毕加索》中,他引毕加索对张大千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并由此而引申,“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64)。毕加索推崇中国艺术的话,汪曾祺在不同场合引过,显然有一种对中国传统艺术得到现代巨匠认可的得意。而在去世前不久,他却忽得一梦:“毕加索画了很多画。起初画得很美,也好懂。后来画的,却像狗叫。”“晨醒,想:恨不与此人同时,——同地。”(65)破坏优美和好懂,而是鬼哭狼嚎,呕哑嘲哳,像难听的狗叫,这正是现代主义的风气,要毁灭清新完整之美。从汪曾祺晚期的作品来看,其主题的残酷设定,风格的略形简朴,荒诞感的显露,对人心和人生残酷底色的体察,都打破了他此前一个时期小说中的和谐之美。或许就像他自己写的,“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残酷的、粗粝的。对粗粝的生活只能用粗粝的笔触写之”(66)。这样的想法,不得不说与他晚年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吸收有关。 因此之故,汪曾祺晚期作品处处留下撕扯和裂痕,“没有呈现问题已获解决的境界,却衬出一位愤怒、烦忧的艺术家……搅起更多忧虑,将圆融收尾的可能性打坏,无可挽回,留下一群更困惑和不安的观众”(67)。应该注意的或许是,在汪曾祺这里,其撕裂性的晚期风格,不只是指向一种“面对存有(Being)时的有限和无力”(68),更可能是一种因知识结构变更而带来的向上表现,从而部分打破了过往小说几成定谳的固定认识,在小说中容纳下更多的东西(比如议论),思想也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就像汪曾祺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认识变化之后,进而有认识乾嘉之际的雄心,认为此时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他们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囹圄中挣脱出来,对人,对人性给予了足有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戴东原,研究俞理初,对纪姚安这样的学术地位并不显著的普通的但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对探索五四以来的思想渊源,是有益的。对体察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69)。一个人年龄会增大,精力会不济,笔力会减退,而这种虽至衰年,仍然保持精进之态,依旧努力更新自己知识结构的努力,才是让人振拔的力量,也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永锡难老”——这或许是汪曾祺,也是周作人和孙犁,带给人们的最有益的启发。 ①③④⑤(25)(47)(67)艾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化》,彭淮栋译,84、84、85、48—19、85、84-85、85页,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 ②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225页,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⑥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周作人:《雨天的书》,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⑧(15)(16)周作人:《药堂杂文》,1、6-7、12-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⑨(14)(17)(18)周作人:《苦口甘口》,1、64、63、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⑩周作人:《立春以前》,1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周作人:《过去的工作》,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2)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周作人:《药味集》,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7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0)张菊香,张铁荣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9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周作人:《欧洲文学史》,52-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2)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4-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3)张尔田:《史微》,6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4)(39)(42)《孙犁全集》第5卷,132、293、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孙犁全集》第2卷,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29)(30)(31)(32)(37)(38)(40)《孙犁全集》第9卷,336、210、164、422、404、120-122、128-130、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33)(34)(35)(36)(43)《孙犁全集》第7卷,198、171、238、224、223、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阿多诺:《论乐集》。转引自艾德华·萨依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化》,彭淮栋译,91页,麦田出版2010年版。 (44)(46)(55)(64)《汪曾祺全集》第四卷,300、286、297、84-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5)(58)(59)《汪曾祺全集》第三卷,301、302、28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8)(50)(57)(60)(65)(66)《汪曾祺全集》第六卷,61、61、60、495、488、3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9)翟业军:《论汪曾祺小说的晚期风格》,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 (51)《汪曾祺全集》第八卷,4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2)(53)(61)(62)(63)《汪曾祺全集》第五卷,246、249、183、164、2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4)语见《阅微草堂笔记》之《姑妄听之》跋,引自《汪曾祺全集》第五卷,2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6)以上引文自汪曾祺:《纪姚安的议论》,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68)阿多诺:《论乐集》。转引自艾德华·萨依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化》,彭淮栋译,89页,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 (69)汪曾祺:《纪姚安的议论》,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