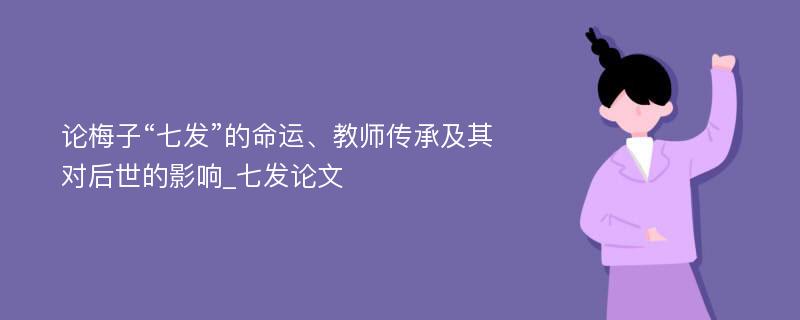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意论文,师承论文,后世论文,论枚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七”体成林,枚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诸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问世并产生影响后,拟作常会出现。有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固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有《二京赋》,西晋左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七”体之作为最。而汉枚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富赡著称。西汉一代不见拟作,但到东汉时期却形成了模拟《七发》的高潮。绵延魏晋齐梁不绝。到梁代竟有卞景其人汇编成集,名曰《七林》,得十卷之多。《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更记载有《七林》三十卷。“七”体之作蔚成大观。致使梁萧统《文选》特辟“七”体的目类。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亦予专门论说。《七林》一书至今已不传,但我们从晋傅玄所写《七谟》序中可知“七”体之作除枚乘《七发》之外,尚有汉到魏晋不少人的作品。至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一书的篇目则更多。而清代《渊鉴类函》则更收录了唐至明代的一些拟作。可惜的是,其中全篇存于今者不多。或留若干段落,或仅数句可见。
如果从作品命意的角度考察齐梁以前的“七”体之作就可以发现,枚乘的“七发”确实卓尔不群。《七发》设计了楚太子和吴客两个人物以为主客展开作品的内容。楚太子疾病缠身,吴客指出致病原因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所致。进而出言耸闻地指出“世之君子以要言妙道”可说而致瘳。在此已明白地表达了戒除昏靡的本旨。通过楚太子病情之愈否,明白地显示了取舍去就之路。其“讽谕”的命意,表明作者深刻的识见和苦心劝戒之诚。他在一片豪华背后发现了隐匿的危机,嗜欲之乐中潜藏着祸根。晋代挚虞《文间流别论》说:“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泰甚之词,而不没人讽谕之义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也论道:“及枚乘摛辞,首创《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交,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异口同声指明《七发》“讽谕”的命意,奠定了辞赋“讽”的立意基础。
《七发》之后的拟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一改其“讽谕”的基调,而为“颂扬”,并由此形成“七”作立意的传统,使《七发》成为绝响。其始作俑者,则是傅毅,“七林”发展的历程,这是一个转折点。傅毅《七激》展现的是出世与人世的思想斗争,并通过玄通子、徒华先生的主客答问方式展开。玄通子劝诱徒华先生违弃泉林,摆脱隐遁生活人世。他举妙音、美食、骏马、畋猎、聚宴等乐事,不获所愿,而后言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朦。达羲皇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守孔氏之宪训,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艺文类聚》卷五十七)专举东汉永平之年政教和顺、学术昌明的社会情况,尽颂扬之能事,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把汉明帝的功德推崇备至。徒华先生终于转变初衷,投身盛世。这最后的一笔,把颂扬的声浪推向高潮。在这里,并没有对诸般享乐给予否定、贬低,它们倒成了光明盛世的烘托陪衬。傅毅以下的拟作,皆准此为式,“颂扬”成为命意的基调,倒是曹植《七启》在“颂扬”的路数上唱了一个变调。他把主上当成了一个次要的人物,却把一位大臣捧成造就盛世的“圣宰”,着力推扬。这位大臣不是别人,正是乃父。因此刘勰对傅毅以下“七”体拟作论道:“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忠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魄,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骋郑卫之声,曲终奏雅者也。”(同上)洵乎所论,这些拟作,千篇一律,语言徒事华艳,夸博炫奇,读来不免生厌,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枚乘《七发》确实独能彪炳“七”林与辞赋之苑。
二
枚乘设计了以“说”疗疾的基本脉络,“说”七事以为针药,递次展开;又以楚太子听后病愈否以为抑扬取舍,从而为全篇设计了合宜的框架。为驰骋文辞开拓了空间。构思奇崛、巧妙,有分有合,驰张得度,全篇浑然一体,有力地传达了“讽谕”的本旨,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七”林余作没有继承《七发》的思想内涵,却全部因袭了这样的构思方式,结构全篇。正是因为它的新颖、巧妙,生动、有层次有起伏,富于表现力的长处。
语言可以疗疾,出人意表又是情理中事。这样的讲法,具有独创性并引人注目。在“天人合一”,万物统一于一个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西汉时代,这自然是可以接受的命题。语言是带有物质外壳的精神形态,思想观念;疾病则是发生于物质实体的人身上的物质形态的东西。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某些疾病又是由于人的精神、思想发生障碍而产生的。精神状态如何,往往又能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造成疾病、或促进健康。二者之间又是相通的。因此物质和精神性的东西就产生了联系。《文子》有言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胃,闭嗜欲,养生之末也。”精神因素成为决定身体健康与否的首要因素。语言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通过语言,端正思想,驱除杂念,强本固精,去邪除蔽,从根本上解决养生问题,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正是“言”可以疗疾的思想内涵。楚太子的病正是不善于正确处理自身与骄奢淫靡生活的关系,贪于嗜欲,耽于安乐所致。疾病表现于身体而根子却在于心,辩证施治,对症下药,治身则治标,攻心则治本。那么可以解蔽去惑的“要言妙道”,不是灵丹妙药是什么?使太子明了致病之由,戒除奢靡,挣脱享乐的泥淖,深求于天地万物的奥义,政教人伦的纲常,是去病的根本。邪与正,去与就,昭若日月。何去何从已明,霍然病愈,岂非理之必然?“言”可以疗疾,浅出而含意深刻、生动而有生活气息,这里绝没有方术之士的诳人之谈。涵咏其奇情妙趣,自然领悟其“讽谕”之本意。
言之为用大矣,其表现于去作者不远的战国时代的效果,再明显不过的了。其时,在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各个领域,语言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至万乘之国,小至一介之身,往往系这于一言而兴替。语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虽说此语慨乎言之,有些极端,但语言价值、作用由此可见。枚乘有鉴于这段历史,专取语言之一端,以艺术想象和夸张手法,又赋于治病的功能。借鉴之后,又有了创新之意。
吴客叙说七事并结合楚太子听后病情愈否以为抑扬的构思,前所未有,为枚乘所独造,十分新颖、巧妙、而且体现出艺术辩证法的意味,因为使其作的“讽谕”本旨获得鲜明强烈的显现。
我国是较早领悟到辩证法的国家。“奇正相生,正反相成”之类的认识早已形成。在文学作品中,对虚实、曲直、轻重、驰张等关系的处理,往往颇具匠心,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增强了作品的魅力,鲜明生动地传达出作品的内涵。《七发》即是一例。该作的思想核心是集中于末段文字来表达的,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主意,是“讽谕”本旨的落脚点。这当然是该作的重点所在;与其余逸乐之六事相比,这才是作者倡导的实质性内容,其余仅是虚晃的花枪如果作者不讲求曲直关系的处理,径情直遂地进入实质性内容,大量笔墨安排其上,这样似乎突出了重点,但艺术是忌浅露,忌平直的。这样处理很可能有声嘶力竭却苍白无力之弊,无明白表达“讽谕”意图之利,显得形貌呆板,意味寡淡。枚乘的作法是避实就虚,违直追曲,从反面作开了文章,非重点落了浓墨重彩。他先叙说了逸乐六事,层层递进,环环展开,以丰富的词汇和华丽的词采,描摹泼洒,这所谓虚的部分渲染得极为充分,极为鲜明,铺张扬厉,紧锣密鼓动。如果拿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旨作参照物来观察这段文字,我们感觉作者是那么从容,那么松驰地兜了一个大圈子。然而在一番摇曳多姿,扶摇直上之后,作者笔锋一转,以简洁的语言,一反发扬蹈厉的气度,强弓劲驽般亮出本旨。反衬之下,这末段的文字,如离弦之箭,划破长空,强劲无比,如高耸的山峰,兀立目前,凛然难犯;六事所构筑的琼瑶之台,陡然之间,瘫塌下来。加之楚太子霍然病愈的一笔,“讽谕”之意石破天惊而出,雄资英发而立。如果说《七发》有奇处,奇就奇在从反面作文章,却收到有力的正面思想效果。在生活中,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目的地,但艺术上的辩证处理,却可能是一条妙趣横生的坦途。
《七发》中吴客历述七事的构思,为“七”林作者所继承,或谓此一作法源于枚乘。清人梁章距即揭出其谬并辩其源:“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孙德谦的说法也大同小异,谓:“证之《孟子》犹不若‘说大人章’益为符合。”(《六朝丽指》)而范文澜先生认为《七发》为辞赋之作,从辞赋与楚辞一脉的角度探源,认为出于《大招》:“详观《七发》体构,实与《大招》符合,与其谓其为《孟子》,无宁谓其变《大招》而成也。”(《文心雕龙注》第2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并从《七发》与《大招》进行比较中,标其相似之处,言之凿凿。
《七发》叙说七事确与《孟子》有关章节和《大招》有相似之处。《大招》首言“魂兮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继而历陈四方凶险艰危。而后以“魂兮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它以定只”为纲,领起饮食之美、乐舞之盛、女色之艳、宫室游观鸟兽之大观和家庭安泰、国治民安之盛世,夸赞楚国之美。《孟子》也历叙诸事如大厦、美馔、侍妾、醇酒、畋猎、般乐等。二者叙说的内容相去不远。但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1)《大招》叙说诸事,语言丰赡,词采斐然,铺陈排比的特色明显。而《孟子》所述言简意赅,不事渲染。(2)《大招》叙说,不存褒贬,一视同仁统以为炫诱,招呼魂灵。《孟子》抑扬取舍,态度分明:“堂高万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骋畋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孟子·尽心下》)“齐桓晋文之事”中的有关文字,也是意存贬抑,由此可知。《七发》叙说逸乐诸事,并不专取一家,而广事铺陈,则从《大招》处多所借鉴。显扬褒贬,明示抑扬,则是继承了孟子是非分明的态度。枚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之成为具有创新意义的表现形式;并在这种新的形式中充填了新的内容。这绝非邯郸学步的简单模仿,而是匠心独运的创造。
三
《七发》是枚乘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力作,是辞赋创作史上较早出现的巨构,占有重要地位。其命意与作者的思想性格是密切相关的。枚乘明于治乱的识见,敏锐深刻的思想特征和敢于劝谏、不事阿谀的性格,早有表现。这和《七发》讽谕的命意,有着血肉般的关系。
枚乘早在文帝时代,曾是吴王刘濞的郎中。而刘濞是景帝前三年以“清君侧”为名制造“七国之乱”的祸首,其叛乱失败自杀均于是年。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以军功与宗室至亲的原因在于高祖十三年封为吴王。吴国有铜山和临海之利,刘濞开矿铸钱、煮海为盐以自富,并以为扩充国力军备之资,发展个人势力。文帝时代,刘濞的儿子在长安与汉太子博戏,被太子杀死,从此刘濞怀恨在心,蓄意谋逆。他起先诈病不朝,进而变本加厉地私擅鱼盐之利,加快扩充军队的步伐。汉太子立,是为景帝,前三年,刘濞借晁错削藩的机会,勾结楚、赵等六国兴兵反叛朝廷,“七国之乱”起。如果说铸钱、煮盐仅是刘濞违反朝廷禁令的不法行为,是诸侯拥土自重对中央朝廷集权统治的离心倾向的表现的话,那么儿子被杀,心怀异志,则成为吴王走向谋反之中的转折点,问题的性质就变化了。其后的一切行为都纳入了他有朝一日以求一逞的轨道。枚乘一区区郎中,在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面前,又是如何表现呢?
《汉书·枚乘传》上载“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枚)乘奏书谏。”这篇书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吴王书》。写作时间据史书所载推断,当即是文帝时代吴王之子被杀之后不久的事,并非叛乱前夕的举动。由于事件处于萌芽状态,反状未形,所以这封奏书并未明言后叛之事。正像《汉书·邹阳传》所说:“其言尚隐,恶指斥言。”但却把表面平静的事态讲得异常危险、严重、耸人听闻。枚乘十分敏感地指出,当此之时,吴王的命运已处于关系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其际“间不容发”。而进他指出“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当从根本着眼,从长计议,以免除祸难。要“积善成德”,不要“弃义背理”,以此制止吴王的不轨之图。这封奏书写得疾言厉色,而又扑朔迷离,云山雾罩,雷声隐隐,结合历史背景,方得其解。诚心劝导,成为全文的主调。通过这封奏书,我们可以看到枚乘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对事态严重性的清醒认识。敢于谏言、切中利害的勇气,也给人深刻的印象。以郎中之身,而有如此胆识,确乎不易。
吴王没有听从他的劝谏,枚乘遂与他人一起北走至梁,从梁孝王游,投靠阙下。枚乘去吴于前,刘濞造后于后,枚乘之去就,不仅表明了他政治态度明朗,又可见出先行一步免除覆巢之下完卵无存的明智。景帝前三年,枚乘在刘濞兴兵之际,于梁孝王处又致书吴王,以朝廷与吴楚七国力量对比之悬殊为有力论据,晓谕吴王,劝他迷途知返,悬崖勒马。
枚乘的《七发》是作于他从梁孝王游时。梁孝王是窦太后之少子,景帝的亲弟弟。其生活之奢侈,权势之显赫,无人可比。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他入朝时“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梁国境内有四十余城,加之所受赏赐,“不可胜道”。他广筑园囿,规模宏大,拟于天子。“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五十余里。”其财富之多难于想象:“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生前“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死后,藏府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可以想象,在梁孝王意气飞扬之际,其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枚乘的《七发》就是针对梁孝王骄淫奢侈的生活而作,他在钜富豪化的背后,看到了它的腐蚀作用。他通过《七发》讽谕梁孝王戒除奢靡,留心治国修身之道,故借吴客之口来劝谏梁孝王这个“楚太子”戒欲修身,避免重蹈吴王刘濞的亡国灭身的覆辙。其现实意义无疑是很深刻的。但梁孝王对枚乘的劝谏,并不当作苦口的良药,而其野心越来越大,依仗其在平吴楚七国之乱中所立的功劳,窥企大位,谋立皇太弟,后因大臣反对,未能得逞,于是怀恨在心,派人至京师刺杀子袁盎等十余人,景帝大怒,梁孝王虽赖窦太后庇护,免得致罪,但其恩宠却因之而烟消云散了。而枚乘却因此而知名,景帝后召拜其为弘农都尉。
刘邦初创天下,形势所迫,曾大封异姓诸王,以后又封宗室为王。广树“藩屏”并未达到维护汉室的目的,反而扶植了与中央朝廷对立的各方势力。政治局面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成为势之必然。刘邦生前为解决这一祸患,曾先后俘藏荼、败陈豨,除韩信,火彭越,诛黥布,翦卢绾,异姓王歼剿殆尽。对同姓王他则未及考虑其将来的危险和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他的《大风歌》表现出这位开国君主面对不安定因素而生的忧虑,其中诸侯王的存在,其势力和野心膨胀,必然酿成叛逆的出现,造成政治局面的动荡,“七国之乱”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汉朝廷削藩之策应运而生,有贾谊倡导于前,晁错、主父偃等实施于后。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维护汉朝中央集权统治,避免政治局面的动荡,社会的混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言,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对历史的前进是有利的。枚乘的行为,应该说维护的是汉朝廷,而从根本上来说,也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向,应予肯定。他所表现的思想识见,性格品质,确有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