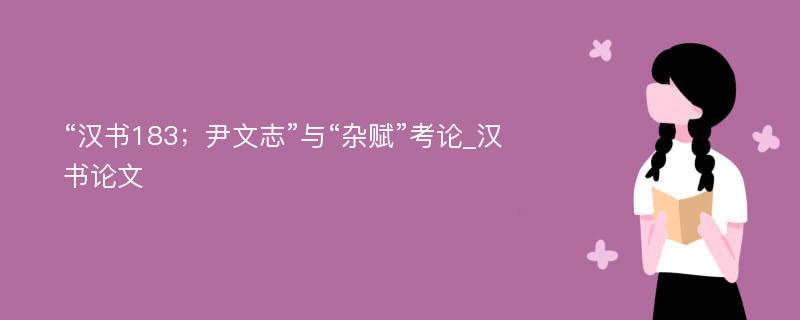
《汉书#183;艺文志》“杂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艺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志·诗赋略》把赋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是“杂赋”。“杂赋”共12家:《客主赋》十八篇,《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篇,《大杂赋》三十四篇,《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
这些作品全部散佚了,前人和今人曾对此作过研究和推测,我们首先从他们的探讨入手。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逸遗上·篇章》中说:无名氏杂赋“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章学诚继承胡氏的观点而更有发挥。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中说:“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刘师培也同此说,《论文杂记》云:“客主赋以下,皆无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旧作,汇为一编,犹近世坊间所行之撰赋也。”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论客主赋类说:“此十八家大抵皆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姚氏《汉书艺文志条理》云:杂赋十二家中以前十家为一类,“此十家以大杂赋居其末,则以前九家皆刘勰所谓小制之区畛可知也。”
刘天惠《学海堂集》卷七《文笔考》说:“诗赋家有《隐书》十八篇,盖隐其名而赋其状,如射覆之类。”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申论刘氏之说云:“杂赋有《隐书》,《传》曰: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饮》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
《杂赋》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杨倞以为就是《荀子》中的《成相篇》,“盖亦赋之流也”。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卢文弨说:“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郝懿行《与王引之伯申侍郎论孙卿书》说《成相杂词》本“瞽矇之词”。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云:“此类杂赋,名目甚多。要皆刘氏校书时就丛书篇帙中,区分类次,汇编而成。其各种标题,亦向歆所加也。《文心雕龙·诠赋篇》云:‘汉初词人,顺流而作;皋朔以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即谓此也。”
程千帆先生《汉志杂赋义例说臆》云:“子骏既依作述源流,叙赋为屈原、陆贾、荀卿以下三种,而民间所进,中秘所藏,书简缺脱,篇章总杂者,亦所多有。其中当不乏作者莫征,年代失考之作”,“故唯有著为变例,别录主题,以类相从,于凌乱之中,辟识别之径:或缘问对,或述情感,或标技艺,或举自然,以及动植之文,谐隐之篇,取譬草木,区以别矣。又以部次未周,人代难详,乃多冠杂字,诏示来学。若杂行出及颂德赋,当多属封禅之事;杂四夷及兵赋,当多属征伐之事,则又以主题不一,连类相称者也。”
王小盾先生《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云:“《汉志》以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客主赋(杂赋)代表赋的四种渊源,从其所列的篇目看,这四种赋之分,实乃近于歌的抒怀作品、近于辩的说辞作品、近于书记的写物作品、近于箴言的杂记作品的分别,而其依据,则可能是古所谓‘列士献诗’、‘百工谏’、‘史献书’、‘师箴’的伎艺分别。”
王琳先生《六朝辞赋史》则认为汉世咏物赋的描写对象多为“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即植物、动物、日常器物。在创作倾向上,它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京殿苑猎”“贤人失志”赋颇不相同,一般没有政治色彩。班固《汉志》将这类作品归于“杂赋”。
欧天发先生《杂赋与俗赋比议》云:“《汉志·诗赋略》区赋之属为四种,其四为《杂赋》。杂者,言无主名之作也。审其篇名,则盖当时民间谣诵之体也。”
诸家之说,可归纳如下几点:
1.“杂赋”是某一类赋作的汇编,包括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等赋作,也包括作者莫征、年代失考的文人作品。2.“杂赋”在形式上是民间谣诵之体。3.“杂赋”包括箴言类的杂记作品。4.“杂赋”中的《隐书》包括滑稽谐隐之言和占卜繇辞。5.“杂赋”中的《成相杂辞》是一种相当后世弹词的讲唱文学。6.“杂赋”包括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一般篇幅短小,如篇幅长,则特意著明。7.杂赋的总体表现风格是诙谐调侃。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启发很大。当然,其中的结论尚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美。我们认为,《汉志》首先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把“诗赋”从其他文种中分离出来,然后又根据“歌”和“诵”的不同,把“诗”和“赋”分开。最后又主要根据赋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对它的价值进行评判并分成四类:第一类“屈原赋”是刘向编辑的《楚辞》的雏形,这类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第二类“陆贾赋”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第三类“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类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为一类。最后是《杂赋》一类,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之讽谏之义微乎其微。前三家是文人赋,是口诵文学的书面化;杂赋一类,则基本上是口诵文学。(注:详见拙作《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待刊。)
这里,我还要从《七略》入手,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的论证。
一、《七略》“别裁法”对我们探讨“杂赋”内容的启示
由于同一书的内容比较复杂,《七略》在著录上采用了变通的办法,这就是后来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所归纳出的“互著”和“别裁”的例则。所谓“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包括这两类:一类是古书的单篇之本,后人收入全书,其单行之本,也不因此废弃,而是重复著录;二类是全书中某些篇章的内容或体裁判然有别于全书者,就分出来著录。(注: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按此章氏误,当为入‘孝经’)。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原注: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既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俱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说:“观于此(按即指别裁法),则书有单行本者,不必以既录全书于此,而彼一类中遂阙其目。又或一人著述已入集部,名其书曰某某全集,乃其中一种为彼专门之学,并可摘出别行,次诸他部之内,不嫌其割裂也。”孙氏的说法,在申述章学诚的“别裁”之说的同时,不自觉地纠正了章氏之说的不足。章氏所谓“别裁”,实际犯了这样一种错误:他认为先有《管子》这部书,然后才有《弟子职》;先有《大戴礼记》,然后才有《三朝记》。按《艺文类聚》卷55引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余嘉锡先生说:“言今在《大戴礼》者,明古本原自单行也。”(《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弟子职》的情况与此相类,1993年的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一份陪葬物清单中,就有《弟子职》,其书已不存,谭家健先生就认为“可能就是《管子》中的《弟子职》”(《神乌赋源流漫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2期。不过谭先生的原文是“《弟子职》可能就是今本《礼记》中的《弟子职》”,谭先生可能误记)。这说明,《弟子职》也先是单篇流传,然后才收入《管子》。)
《汉志》别裁著录,给我们启发良多。第一,由于诗赋在形制上、传播方式上明显的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曾是单篇流传着的,刘向、刘歆把“诗赋”单列出来,正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第二,《诗赋略》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从其他各类中别裁出来的。因为“六略”其他各略都是按内容分,并且归于作者名下,只有《诗赋略》是按体裁分的。这种逻辑上分类标准之不纯,体现着的正是刘歆目录学上的“别裁”观和文学独立的文艺观。
《诗赋略》赋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那么它们是从各位作者的总集中别裁出来的。
如“荀卿赋十篇”,学术界公认为就是《荀子》的《赋篇》和《成相篇》,它们就包括在《诸子略》儒家“荀卿子三十三篇”之中。
“贾谊赋七篇”,我认为也包括在《诸子略》儒家“贾谊五十八篇”之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曰:“《贾子》十一卷,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按,即《史记》、《汉书》本传内载录的《吊屈原赋》,《文选》载录的《吊屈原文》)”,则贾子赋七篇本包括在“贾谊五十八篇”之中,但宋人传本已佚夫其他六篇。余嘉锡先生认为“《新书》独载《吊湘赋》者,以此篇尤其平生意志之所在也”,恐非的论(注:引文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第53页。按,今本《新书》五十八篇不包括赋篇,《朱子语类》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耳,中间事事有些个。”《四库提要》云:今本《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越缦堂读书》遂谓“其为伪作无疑”。朱子及《提要》所论,说明今本《新语》窜乱良多,赋七篇也因此散失。至于说今本《新语》是伪作,则非是。《汉志》“贾谊五十八篇”乃贾子后学所编贾子全集,其中包括了贾谊平时的札记,与学生的讲学之语。像《连语》诸篇,内容不尽于告君,盖有与门人讲学之语。如《先醒篇》云:“怀王问于贾君”,而《劝学篇》首冠以‘谓门人学者’五字,都是明证。其《杂事》诸篇(《礼容语》、《胎教》、《立后义》)则平日所称述诵说的小故事。班固作《贾谊传》著录他的作品时,对其进行了压缩和改编。如《治安策》一篇,乃班固取十数篇删节连缀而成,故首言“其大略曰”,赞言“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也。后人习惯于读《汉书》,见《汉书》所载贾谊的文章首尾完整,既条理井然,又文彩斐然,乃不谓《汉书》根据《新书》而来,反谓《新书》割裂《汉书》,恰好是颠倒了事实。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考之甚详,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也有精辟分析。)。
“陆贾赋三篇”也包括在《诸子略》儒家“陆贾二十三篇”之中。《史记·陆贾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而《汉志》作“陆贾二十三篇”,那么这二十三篇除了《新语》十二篇之外,还包括陆贾的其他著述,《四库提要》所谓“盖兼他所论述计之”。陆贾的“他所论述”,今皆不存,未知是何体制,我认为是包括了他的赋作的。由今存《新语》十二篇看,陆贾文章,概具赋体,如第七篇《资质》的首段,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如不通观全篇,极易疑其为写物之赋。所以王利器说:“陆贾赋今不可得见矣,读《新语》之文,不翅尝鼎一脔矣。”(注: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新编诸子集成”版,第107页。)
《诸子略·杂家》有“臣说三篇”,班固自注:“武帝时所作赋”,可为诸子书中包括赋篇做一有力证据(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涛说:“《志》所引‘杂家’皆非词赋,此赋字误衍。”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谓“赋”字不是衍文。余说是,今从余说。)。
《汉书·司马相如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子虚赋》不题著者之名,二是《子虚赋》本是单篇流传。
《杂赋》一类,情况更为复杂,其一皆无作者,其二皆无年代,其三多以题材分类,其四多冠“杂”字。由前三条,我们可以知道,“杂赋”是从赋类作品中别裁出来的某类题材、某类风格作品的汇编,胡应麟认为“杂赋”为总集之体,确实是卓见。
“杂赋”不仅有从其他三类赋中别裁者,如从荀子赋中别裁出《成相》(注:杨倞《荀子注》:《成相篇》乃“荀子杂语”,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朱嘉《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从“枚皋赋百二十篇”中裁出之嫚戏之赋;有从“诸子略”别裁者,如从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裁出的“隐书”,从杂家“东方朔二十篇”中裁出之调侃赋(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新序》引‘大鸟不蜚不鸣’似即《隐书》之一,则《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互为隐语,亦似出于十八篇中。”又云:“东方朔赋意即在此十家杂赋之中。”按其说可从。《汉志》无东方朔赋,惟《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汉书·东方朔传》:“刘向所录朔书,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雋》、《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猎赋》。”又《枚乘传》附《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据此可考证,《东方朔传》所记《皇太子生禖》以下,都是他作的赋。又《东方朔传》:“朔书有七言、八言上下”,师古注引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按汉人不以七言为诗,而为杂俗之赋(说见正文)。东方朔的射覆之词有为七言者,其柏梁台对句亦为七言,则其七言、八言皆入“杂赋”欤?晋灼晋人,已视七言、八言为诗矣。《古文苑》录王延寿《梦赋序》云:“臣弱冠尝夜寝,见鬼物与臣战,遂得东方朔与臣作骂鬼之书,臣遂作赋一篇叙梦,后人梦者读诵以却鬼,数数有验,臣不敢蔽,其词曰”云云,是则王延寿少时曾读过或听人诵过东方朔鬼之赋,《梦赋》乃仿而成。);还当有从《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别裁而出者(注: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这些有韵之文,包括各种仪式文,如婚词、冠词、驱傩文、射覆词、占卜词等。)。
《七略》的别裁法,还通过杂赋类“杂”字给我们有所启示。
“杂赋”十二家中,只有“客主赋”和“隐书”两家没有“杂”字。由多冠“杂”字,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这类赋作的风格特征。第一,“杂”有“共”的意思,见于韦昭《国语·越语下注》和颜师古《汉书·雋不疑传注》(注:《国语·越语下》:“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韦昭注:“杂,犹俱也。”《汉书·雋不疑传》:“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颜师古注:“杂,共也。”),出土文献可进一步证明,如睡虎地秦简中有这样的句子:“县啬夫令人复度及与杂出之”,“与仓、乡杂出之”,“令其故吏与新吏杂先索出之”,“效者发,见杂封者,以题效之而复杂封之”等(注: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中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40页。),秦《挟书律》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之“杂”,也是总共之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杂赋是总集之体。
第二,“杂”有驳杂、不纯正的意思,与“正”对言。古代以庙堂礼乐为雅乐正声,其特点是庄重肃穆,而下层或娱乐性艺术所追求的效果是笑乐嬉闹,与正雅之乐相比,属于“杂俗”之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汉志·六艺略》中著录“雅歌诗四篇”,《诗赋略》中又著录“杂歌诗九篇”,与之相对。《汉志》六略共著录596家,书名中有“杂”字者48家,其中“方技神仙类”九家,“数术杂占类”三家,“数术天文类”九家,“诗赋杂赋类”十家。这些有“杂”字的书籍,《汉志》认为“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所以教也”,其内容的驳杂可想而知。所以这些佚赋以“杂”或“戏”冠于名中,应当包括一些民间演诵的赋作和文人创作的调侃取乐之作。
第三,“杂”字还有另外的意义。赋本来就是民间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下层艺人在表演这种艺术的时候,往往夹杂使用了多种手法,如诵唱伴以各种动作、表情等。尤其是优伶侏儒的参加,更使这种表演综合化了。从汉墓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俳优俑看来,都具有这些特点:滑稽戏笑,调谑娱人;短胖袒裸,畸形丑陋;抱鼓握槌,作敲击状;可见是杂以多种民间伎艺手段的(注:见郎绍君等主编《中国造型艺术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41页记载1957年四川成都天迥山崖墓出土的一尊东汉说唱俑。)。所谓杂赋之“杂”者,恐怕也有这层含义。汉代有百戏、歌舞戏、傀儡戏等,汉人就叫做“杂技乐”(《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汉文颖说),六朝人则叫做“杂戏”(《魏书·世祖纪》),也是就其表演时夹杂各种手法说的。我们引用一条后世的材料,予以间接地说明。南朝梁慧皎撰有《高僧传》,其中有《经师》、《唱导》两篇,专为诵经的僧人立传。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时,将这两篇合并成一篇,名曰“杂科”,他解释说:“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他用“糅”字解释“杂”字,非常准确。“杂赋”“不歌而诵”,不正是“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吗?
二、《七略》“小说家”与“杂赋”的对应给我们的启发
章学诚说《汉志·诗赋略》的分类,“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他虽未曾深入论述,却对我们很有启发。《汉志·诸子略》最后一家是“小说家”,《汉志》将赋分为四家,列入最后一家的是“杂赋”。“小说家”与“杂赋”,都相应地处于末流的位置。《汉志》虽对“杂赋”没有叙论,但从它对“小说家”的叙论中可以大概了解一些“杂赋”的信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是一种官职,专门搜集庶人之言传达给天子(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作于1937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潘建国先生补充了余先生的说法,认为“稗官应具有某种特别的指向,即泛指那些将如稗草一般‘鄙野俚俗’之内容说与王者听闻的官员”(注: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2期。)。
《隋书·经籍志》则更具体地说明“稗官”就是《周礼》中的“诵训”、“训方氏”,而且将“杂赋”与“小说家”混为一体了。根据《周礼》的记载,诵训的职掌是向国王转说四面八方、古往今来的故事,而且向王诵说各地的民情风俗、避讳、禁忌等(注:诵训,见于《周礼·地官》;训方氏,见于《周礼·夏官》。《地官》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训方氏则是以乐语形式为王诵“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注:《周礼·夏官》云:“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郑玄注:“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故书传为傅。”就是说,郑玄看到的《周礼》,这句的“传道”作“傅道”,“傅道”,即“赋道”。虽然郑氏根据杜子春的意见,把“傅道”改为“传道”,但作“傅道”当更合本义。“傅道”之“傅(赋)”,即“瞍赋”之赋;傅道,即用乐语形式的诵圣道之颂。)。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周礼》所载的诵训、土训、训方氏等,都是“王巡守,则夹王车”。张衡《西京赋》“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小学家时常伴驾出巡,随时等待“诵说”。
赋家在这一点上与小说家极为相似。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王褒传》也记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更令人寻味的是《汉志诗赋略》中的赋家,大半曾被皇帝召为待诏者,如吾丘寿王、光禄大夫张子侨、刘向、王褒、枚皋、严助、朱买臣、郎中臣婴齐、臣说、萧望之、扬雄、待诏冯商、汉中都尉丞华龙等。
小说家和赋家,同以待诏、侍郎之职活跃于帝王周围,上有所感,则稗官即兴说之,赋家即兴诵之。
《汉志·小说家叙论》如淳注屡为诸家所引,但却遗漏了很重要的一句话:“稗音锻家排。”“稗音锻家排”者,谓此“稗”字音如“排”,排与俳都从“非”得声,二字可通假,钱坫《说文斠诠》引《三苍》云:“俳,偶也。”“俳可训偶,知俳必是二人对语,时杂嘲戏,故俳亦曰俳谐。”《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曹植曾对邯郸生“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胡士莹、王运熙先生就认为曹植所诵的俳优小说是指那些诙谐有趣、宜于诵读的通俗赋作,包括《鹞雀赋》一类的作品。(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王运熙:《为汉赋家见视如倡进一解》,《文史哲》1991年第5期。)共同的口传方式使这两种文体在早期很难判然分开。
把“小说家”与“杂赋”比附,也是刘勰的意思。《文心雕龙》把文体分为“文”“笔”两大类,列在“论文”部分末尾的是《谐隐》,本篇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杂赋”。《谐隐》篇说:“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这是明确说把“谐隐”放在文末,就如同《汉志》将“隐书”放在赋末,将“小说家”放在诸子末。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对“杂赋”总体风格的分析与把握,顾实先生杂赋“盖多杂诙谐”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郭绍虞先生曾这样说:“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注: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郭先生这里所说的“赋”,当主要指“杂赋”。
以上所述证明,汉代的“杂赋”包括了大量的俗赋。当然,真正的民间俗赋是不可包括在《汉志》所说的“杂赋”中的,因为民间赋不可能进入中秘,就如同清代以来的民间唱本、小说不可能进入“四库”一样。但民间俗赋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汉志》“杂赋”中的俗赋,应当指的是这一类。或者说,汉代文人创作的俗赋主要包括在杂赋中,这样说恐怕更为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