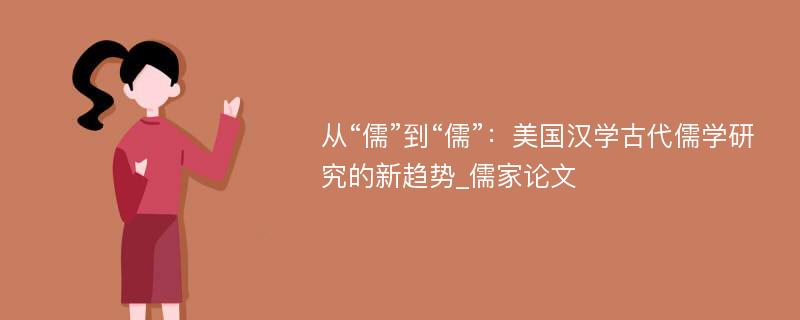
从“Confucian”到“Ru”:论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美国论文,上古论文,新趋势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学界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近十几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于先秦两汉儒家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了新的趋势。从表面上看,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开始使用“Ru”这一术语,而传统的“Confucian”一词则逐渐受到冷落。这种术语使用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学的研究视角从哲学逐渐转变到了历史,从关注儒家的同一性转变到了关注儒家内部的差异性。本文将详细考察目前活跃在美国汉学界的几个重要学者的观点,以探讨这些学者在强调区分“Confucian”和“Ru”的背后所试图传达的研究方法,进而揭示西方汉学界上古儒学研究新趋势的意义。
一、从哲学到历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对儒学的研究以哲学角度为主,当时活跃的汉学家们大多有着较高的哲学素养,通常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诠释儒家思想:或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分析儒家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相同之处——分析哲学家赫尔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写于1970年代的《孔子:即凡而圣》① 可谓其中的代表;或用儒家思想来反思西方哲学,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异——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David Hall & Roger Ames)合著于1980年代的《通过孔子而思》② 乃这一方法的典范。这两本著作在199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后,为中国学者所广泛借鉴③。它们在西方汉学界同样影响巨大,已故汉学家葛瑞汉在1980年代末所著《道之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辩论》④ 中专门讨论了“孔子和20世纪西方哲学”,对之前的孔子哲学研究作了回顾,其中主要提到的就是上述两本著作⑤。史蒂芬·威尔逊(Stephen A.Wilson)在2002年所写的一篇探讨“儒家思想中个人和伦理关系”的论文中,也以芬格莱特和郝、安的两部著作为讨论的出发点⑥。
芬格莱特与郝大维和安乐哲的研究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两者都将孔子思想和现实社会紧密相连。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芬格莱特的研究试图将孔子思想和西方社会紧密联系,以找寻孔子思想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实践可能性⑦。而郝大维和安乐哲的研究虽然方法不同,但是他们同样把孔子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榜样”⑧。不过,由于他们的哲学背景,无论是芬格莱特,还是郝大维和安乐哲,都简单地将《论语》中的材料视为孔子本身的哲学思想。他们在使用文献材料的时候,几乎没有对文本从历史的角度提出过质疑。这种对文献的处理方法,表明他们默认了儒家思想内部的统一性。
十多年来,美国汉学家们对于中国传统文献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学家们逐步摈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笔者将这种趋势称为“去儒家化”。所谓“去儒家化”,是指研究者否认有所谓的一成不变的儒家存在,不再以传统的“Confucianism(儒家思想)”来指称自孔子以降一直到清代儒者的思想,从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比传统研究更为细致的划分。主张“去儒家化”的美国汉学家主要从事上古到中古的中国历史和思想研究,他们几乎不再采用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而将目光直接注视在中国思想本身。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和戴梅可(Michael Nylan)等学者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些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分歧,但是他们都赞成一个观点:儒家思想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换言之,这些学者要脱下罩在众多古代思想家身上的“儒家”外衣,将思想家们当作真正的个体——而不是儒家中的个体——来研究。因此,笔者将这种趋势称为“去儒家化”。
在这些学者看来,用儒家思想来指称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和扬雄的各种不同思想过于笼统,容易忽略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从而让人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产生误解。因此,他们认为传统汉学将儒家内部各种不同的思想都简单地翻译成“Confucianism”是欠考虑的。不少学者提出使用“Ru”和“Confucian”两种翻译方式,来区分先秦儒家和汉以后的儒家。这种翻译的变化,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对于以前的西方汉学界忽视“儒家思想”内部差异的一种反动。二战以来,早期汉学家如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孟旦(Donald Munro)、倪德卫(David S.Nivison)⑨ 等人一直没有明确定义“Confucian”一词的内涵,从而将这一概念使用得非常宽泛。而目前西方学者们对于“Ru”和“Confucian”的区分,表明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日益细微,不再满足于笼统的比较研究了。
二、对儒家内部的多样性的反思
詹启华(Lionel Jensen)在1997年出版了《制造儒家思想》一书⑩,在书中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对于孔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也就是孔子从“Kongzi”变“Confucius”的过程。在详细分析了利马窦(Ricci)、金尼阁(Trigault)以及其他重要传教士的作品之后,詹启华指出:在当时,与中国文化——一种相异而优越的文化——的接触对传教士们来说是一种震撼,而这种震撼使得渴望分析并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们产生了一种默契,他们共同将中国的思想家孔子塑造成了神秘的“孔夫子”,并给予孔子一个拉丁化的名字“Confucius”。虽然詹启华的研究被不少学者所诟病(11),但是在笔者看来,其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正式对“Confucius”这一西方汉学界对孔子的标准翻译提出了质疑。詹启华的质疑并不拘泥于翻译本身,而是对于“Confucius”这一翻译的内涵提出了疑问。
詹启华对于“Kongzi”和“Confucius”的区分在学界马上引起了回应。1998年,白诗朗(John H.Berthrong)出版了《儒家之道的转化》(12)。书中虽然没有用大篇幅论证儒学(Ru)和儒家思想的不同,但还是在书的介绍部分简单讨论了“Ru”和“Confucian”以及“Confucianism”的差异,对“儒生”(Ru)一词是否就是指最早的儒家思想者(Confucian)提出了怀疑,并提出对“Ru”的内涵应该重新认识(13)。戴梅可对白诗朗的这一疑问极为肯定,认为是《儒家之道的转化》一书所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4)。在对此书的评论中,戴梅可说道:“毫无疑问,‘Ru’的内涵和远古时期的儒(Confucian)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任何时候一个人想要确认人数众多的‘Ru’中谁到底是真正的‘Confucian’,都会遇到定义的问题。”(15) 戴梅可进一步指出,白诗朗区分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和先秦儒家的研究方法,与宋朝的新儒家们否认汉代儒学正通行从而追寻新道统的观念相一致(16)。
在这样的背景下,戴梅可和其他一些汉学家提出用“Ru”来指称汉代以来的经学家,而用“Confucian”来指称独尊儒术之前孔子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在他们看来,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虽有所差异,但是他们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不容怀疑,而且《史记》中对于先秦儒家们的描述也有共同之处——这一共同之处在于先秦儒家都主张通过提高日常生活中的修养来改善社会,从而达到圣人之境界。戴梅可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早期儒者表明自己是孔子的真正追随者。”(17) 在戴梅可看来,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已经是一群用经学来追求政治权利的人,他们渴望的不再是“圣人”的境界了。
2001年,戴梅可出版了《“儒家”的五经》(18) 一书,书名中的“Confucian”上被加了引号,以表示并没有所谓的从先秦到两汉的儒家传统。她在书中解释了打引号的原因:“晚期学者所认为恒久不变的‘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儒家思想’这一术语是对不断发展的思想思潮的一种抽象化和简单化——这显然是有用的,但总是会误导别人。它既是思想思潮发展的产物,也同样是一个主体。”(19) 她明确指出:“我对‘Confucian’一词的使用仅限于自我认定的对孔子的教育和文化产物的追随者。……Ru,通常被翻译成Confucian,意味着‘经学家’。……虽然后期的程朱理学家只把自己学派内的成员称为Ru(儒),但是‘儒’通常被用来指代多种复杂的情况,意义和‘士’相近。”(20)
戴梅可在解读“五经”时,提供了大量历代学者针对同一文本所持的不同观点,向读者清楚展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从而为自己区分“Ru”和“Confucian”作了最好的注脚。她在书中反复强调:将孔子和“五经”相联系是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政治行为”(21)。她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汉学家的共鸣(22)。
因此,区分“Ru”和“Confucian”对于这些学者来说绝不是一种文字游戏或翻译趣向,而是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儒学研究观点和方法。如前所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汉学家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相对缺乏细分,当郝大维和安乐哲等人引用《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论据时,他们默认《论语》是可依赖的先秦文献,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础。但是1990年代以来,众多像戴梅可这样拥有历史学背景的汉学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文本的简单化处理,也越来越重视儒家内部的差异。即使是拥有哲学背景的汉学家们也开始探讨从《论语》出发认识孔子的可靠性。例如,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执教的艾文贺(Philip J.Ivanhoe)在研究《论语》时提出了“谁的孔子”这样的疑问(23)。
艾文贺的疑问基于对《论语·公冶长》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段文字的解读。他细致分析了从汉朝到清朝近两千年间何晏、二程兄弟、戴震和章学诚等五位学者对这段文字的不同解释,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儒家内部对于《论语》和孔子思想诠释的多样性。他最后指出,我们应当注意《论语》诠释的丰富性和儒家内部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时刻问自己,我们所理解的孔子究竟是谁的孔子。艾文贺的研究方法表明,哲学家们已经受到了历史学家的影响,简单地将儒家思想等同于孔子思想的时代已经过去。戴梅可和白诗朗等人将“Ru”与“Confucian”区分的主张,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
三、对先秦儒家内部统一性的质疑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们开始区分“Ru”和“Confucian”,对于具体如何使用这两个翻译,汉学家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与戴梅可用“Ru”指代汉朝经学家相反,以齐思敏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Ru”只能用来称呼先秦的儒家,而汉朝以后的儒生们虽然把孔子视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建立者,但是实际上却和先秦儒家的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拒绝把汉朝和汉朝以后的思想家称为“Ru”。虽然他们对于如何使用“Ru”有着分歧,但是从根本上讲,两者对于儒家内部多样化的认识却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的异大于同。对于先秦儒家和汉代以来思想的研究,这些主张“去儒家化”的学者们都尽量避免用“儒家”这样的词语来统称某一批思想家。近年来美国学者依然对传统的重要思想家诸如董仲舒、扬雄和王充非常重视。戴梅可计划翻译扬雄的《法言》和王充的《论衡》全文,齐思敏也非常关注扬雄,王安国(Jeffery Riegel)则长时间关注王充。他们强调,要避免用“儒家”或者“道家”这样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词汇来形容一个思想家。在愈来愈多的汉代思想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的情况下,美国汉学家们可以更加细致地进行儒学研究。从这一点上看,美国汉学家对于儒学研究的细分化的确是大势所趋。
齐思敏一直对儒家学派的提法持怀疑态度。通过详细考察孔子在汉代文献中的形象以及《论语》在汉代的传播状况,他首先提出汉代是“Kongzi”——先秦的孔子——变成“Confucius”——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孔子——的关键时期(24)。同时,他主张用Kongzi来称呼战国前的孔子。齐思敏明确指出,《论语》和汉朝文献中的孔子形象,是汉朝学者刻意塑造的结果。他认为先秦的孔子思想并没有与政治权威如此紧密地相连(25),现在英文中Confucius一词,已经包含了太多的汉朝以来的孔子形象,因此他主张将真正的孔子翻译成Kongzi。
同时,齐思敏在其《物质道德:古代中国的伦理和身体》一书中指出:就历史的角度来看,用“Ru”来指称先秦儒比用“Confucian”更加准确(26)。在他看来,先秦时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礼仪文化知识为生的人,孔子虽然是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随者,不同的儒生有着不同的礼仪传统,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27)。齐思敏的这一观点是对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孔子之前》(28) 结论的回应。夏含夷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儒家的各个经典的产生都是在孔子之前。齐思敏显然对此表示赞同。齐思敏认为,西方人习惯使用的“Confucian”一词由于词根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儒生都是孔子的门人。所以他觉得用“Ru”一词来指称先秦儒家更加准确(29)。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和“Confucian”一词相比,“Ru”没有那么多歧义,但是“Ru”的真正内涵并不清楚(30)。和詹启华一样,齐思敏也引用了章太炎和胡适对“儒”的考证,但是他最后的结论依然是我们无法给“Ru”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可见,齐思敏对于儒家内部多样化的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比戴梅可更加深入。如前所述,戴梅可主张用“Confucian”一词指代先秦儒生的理由是她认为先秦儒生的共性大于差异——先秦儒生都是孔子思想的追随者。对于戴梅可来说,儒家内部最主要的差异是先秦儒家和汉代儒家之间的差异。而齐思敏则在承认汉代儒家内部多样化的同时,更进一步强调了先秦儒家的差异,否认了孔子在先秦儒家思想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笔者认为他对于“去儒家化”的主张更为彻底。
“去儒家化”的研究态度和齐思敏的研究方法直接相关。齐思敏非常重视出土文献,他把近40年出土的材料视为研究先秦思想的最重要资料——因为这些材料没有被汉代经学家们所篡改。因此,从包山到郭店的各种出土文献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他希望用这些材料来审视那些被人忽视或误读的传世材料,从而对先秦儒家思想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过,他对于出土文献并非盲目相信。他明确指出,“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用静态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构建一个贯穿两千年的‘对话’的想法是必然有问题的”(31)。他只希望通过融合出土材料和(与出土材料同时的)传世文献,以尽可能地展现儒家思想的多样性。
四、对认识孔子可能性的质疑
但是,有些汉学家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对于儒家传统连续性的否认,他们不但要“去儒家化”,甚至要“去孔子化”。所谓“去孔子化”,就是强调文献资料的历史局限性,否认我们可以认识孔子“真实面貌”的可能性,从而从根本上淡化甚至否认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陆威仪就是这一类学者的代表。
和齐思敏一样,陆威仪也主张以“Ru”代替“Confucian”,而且他也用“Ru”指称先秦儒家。同样,通过对《史记·孔子世家》文本的解读,陆威仪指出“Confucius”一词所代表的孔子是经过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包装之后的孔子,与先秦的孔子形象相去甚远。因此,他也主张用Kongzi来称呼先秦的孔子。但是陆威仪的态度显然更为激进。如果说詹启华区分“Kongzi”和“Confucius”还是为了揭示西方传教士们对于孔子的“塑造”,而齐思敏所强调的也不过是先秦孔子和汉代孔子的不同,那么陆威仪在《古代中国的写作和权威》(32) 一书中则是通过揭示司马迁“对孔子的神话化”(33),以告诉读者认识“真正”孔子的不可能性。
对于《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形象和司马迁自己的联系,杜润德(Stephen Durrant)在1995年出版的《司马迁之镜》一书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34)。杜润德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历程就是司马迁自己生活经历的反映。陆威仪对此表示赞同(35)。不过,陆威仪的研究走得更远。他把孔子、周公以及伏羲相提并论,认为汉以来孔子的形象和后两者一样,代表着一种神话化的政治权威,而这种从伏羲到周公最后到孔子的政治权威是通过《易经》的流传得以实现的。陆威仪指出:汉代以来,通常认为伏羲是传说中八卦的发明者,《易》在周文王和周公手中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而孔子则是《易》的编辑者,汉以来的这一说法正是为了塑造从伏羲到孔子的政治权威。通过《易》,孔子虽然只是素王,却拥有了向后人预言王朝兴衰的强大力量。众所周知,伏羲的存在只是一个神话。至今学者仍然无法考证伏羲的确实身份。将孔子的形象和伏羲相等同,这直接意味着对孔子认识的不可能性,而承认认识孔子的不可能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否认儒家思想和孔子的密切联系。
陆威仪对于孔子形象的解构是他对中国上古文本解构的重要一环。在《古代中国的写作和权威》一书中,他还对屈原形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屈原只是一个虚构化的人物(36)。这种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不少美国汉学家的赞同。杜润德和鲍则岳(William G.Boltz)都对陆威仪的研究评价甚高,甚至认为该书是葛瑞汉《道之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辩论》以来二十多年中西方汉学界最重要的著作(37)。马丁·斯文森(Martin Svensson)和查尔斯·霍克布(Charles Holcombe)也认为《古代中国的写作和权威》堪称经典(38)。这表明陆威仪的“去孔子化”观点已经成为了美国汉学界的一种潮流。
这些学者对于儒家思想和孔子的还原,和民国时期章太炎、胡适等人在《原儒》、《说儒》中试图寻找儒家的原本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信古派,都是根据考据材料对历史进行重新分析,他们所怀疑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点而不是史料本身。而这些西方汉学家深受解释学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在强调文本本身力量的同时,否认通过文本认识真正历史原貌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只是代表司马迁的观点,而不能用来作为研究先秦孔子的资料。陆威仪始终将《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载的孔子经历称为故事,并认为《孔子世家》和《公羊传》一样,对孔子的描述都是为了适应汉朝自身政治和文化的需要(39)。我们从中只可能了解为何司马迁要如此描写孔子,而不可能认识真正的孔子。他对于《孔子世家》之史料价值的判断,彻底否定了通过《史记》了解孔子的真正生活的可能性,从而将自己也带入了困境。如果还原孔子的结果就是否认可以真正认识“孔子”,“去儒家化”的最终结果就成了“去孔子化”,孔子变成了一个不可认识的神秘人物,那么研究孔子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儒家内部的差异性足以抹杀儒道之间的差异,那么历史上儒道之分究竟又是为何?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五、结论
西方汉学家对于“Ru”和“Confucian”的区分,似乎和孔子的“正名”思想相一致。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儒”的内涵不明确,那么对于所谓儒家思想的研究就会是空中楼阁。就目前来说,对于“Ru”和“Confucian”的界定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且笔者个人认为也不会有最终的定论。关注多样性或者同一性,这只是方法论的不同,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随着美国汉学家对于汉代以来文献的分析日益细致,儒家内部的多样性也许将在相当时间内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区分“Ru”和“Confucian”的情况下,对于如何使用这两个术语,汉学界应早日达成一致,否则将会造成不必要的语义混乱。
同时,包括“Ru”在内的拼音术语在汉学界的日益流行,在表明美国汉学研究摆脱西方哲学术语束缚的同时,也意味着汉学家可能面临与非汉学家之间的交流困境。如果普通西方读者需要首先了解各个拼音术语的意义才能管窥汉学研究,那么这对汉学研究的推广也许是作茧自缚。毕竟,美国的汉学研究从二战后开始繁荣,就是一直与现实相紧密联系的(40)。也许,汉学家们在将儒家思想内部细分之后,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儒家思想内部的多样性与现实相联的问题了。
注释:
① Herbert Fingarette,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Harper and Row,New York,1972.
②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
③ 参见高书文:《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317页。
④ 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Open Court,La Salle,IL,1989.
⑤ 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Open Court,La Salle,IL,1989,pp.22-31.
⑥ Stephen A.Wilson,“Conformity,Individuality,and the Nature of Virtue:A Classical Confucian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Ethical reflection”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edited by Bryan Van Nord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94-115.
⑦ Frederick Sontag,“Review of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in Religious Studies,Vol.10,No.2 (Jun.,1974),pp.245-246.
⑧ 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Open Court,La Salle,IL,1989,p.30.
⑨ 如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倪德卫《儒家之道》(The Ways of Confucianism,Open Court,1996)等书中,都用“Confucianism”和“Confucian”来指称不同的“儒家”学者。
⑩ Lionel 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11) R.Po-chia Hsia,“Review of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in History of Religions,Vol.41,No.1 (Aug.,2001),pp.71-73.
(12) John H.Berthrong,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Westview Press,1998.
(13) John H.Berthrong,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Westview Press,1998,p.6.
(14) Michael Nylan,“Review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0,No.4,Oct.,2000,pp.632-637.
(15) Michael Nylan,“Review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0,No.4,Oct.,2000,pp.632-637.
(16) Michael Nylan,“Review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0,No.4,Oct.,2000,pp.632-637.
(17) Michael Nylan,“Review of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0,No.4,Oct.,2000,pp.632-637.
(18) Michael Nylan,The Five“Confucian”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19) Michael Nylan,The Five“Confucian”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3.
(20) Michael Nylan,The Five“Confucian”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2.
(21) Michael Nylan,The Fire“Confucian”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7.
(22) Robert F.Campany,“Review of The Five‘Confucian’Classics,”in History of Religions,Vol.43,No.3 (Feb.,2004),pp.258-261.
(23) Philip J.Ivanhoe,“Whose Confucius? Which Analects?”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edited by Bryan Van Nord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19-133.
(24) Mark Csikszentmihalyi,“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in the Han,”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edited by Bryan Van Nord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4-162.
(25) Mark Csikszentmihalyi,“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in the Han,”i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edited by Bryan Van Nord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4-162.
(26) 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Brill,2004,pp.16-17.
(27) 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Brill,2004,pp.15-16.
(28) Edward L.Shaughnessy,Before Confucius: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SUNY,1997.
(29) 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Brill,2004,pp.15-16.
(30) 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2004,p.17.
(31) Mark Csikszentmihalyi,Material Virtue: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Brill,2004,p.2.
(32) 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33) 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219-238.
(34) Stephen Durrant,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SUNY,1995.
(35) 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218.
(36) 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177-192.
(37) 参见杜润德和鲍则岳对该书的评论,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封底.
(38) Martin Svensson,“Review of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0,No.4 (Oct.,2000),pp.614-619; Charles Holcombe,“Review of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1 (Feb.,2000),p.189.
(39) 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237.
(40) 魏思齐:《美国汉学研究的概况》,《汉学研究通讯》总102期,2007年5月。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论语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孔子论文;
